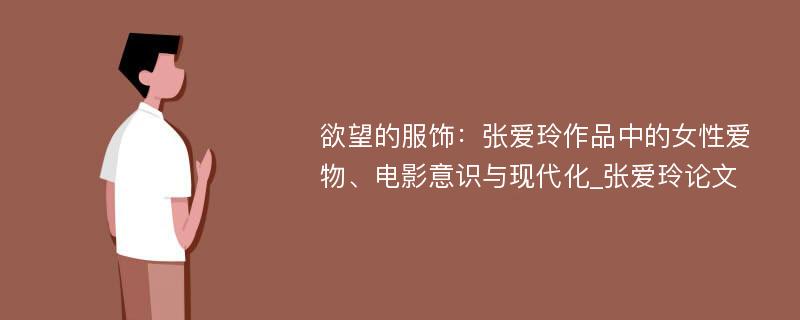
欲望之衣: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恋物、电影感与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欲望论文,女性论文,作品论文,恋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私语》(1944)里,张爱玲这样叙述母亲和姑姑出洋前与她告别的情形:
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又没有教给我别的话,幸而佣人把我牵走了。①
母亲的离去以及之后在父亲和继母家里的生活,留给年幼张爱玲的该是无尽的伤痛,但是在回忆里她只写了母亲的那身绿衣绿裙。衣服成了痛苦的目光的转移点,也成了痛苦留在记忆里的标志。在《童言无忌》(1944)里,忆及继母的悭吝和不善,张爱玲也只写了一件衣服,是她被迫从继母那里继承过来穿的“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②。五十年过去了,张爱玲在《对照记》(1994)中又一次谈起继母过门时带过来预备施舍给她的两箱嫁前的旧衣服,显然对这段往事仍耿耿于心,那一章末了声称自己后来一度成为“衣服狂”(clothes crazy)③。
张爱玲的这一自我表白,让人联想到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里的“恋物癖”一说。孩子(男童)偶然瞥见母亲的下体,发现和他不一样的身体构造,这不一样却没有被理解成仅仅是不一样,而被看作是缺损,于是阉割的忧惧造成对真实现实的“视而不见”。在恋物癖的原始场景中,目光的转移和凝滞是整个心理变化的外在体现。当母亲的身体在儿童的目光中消失时,后者却在物体上找回了记忆。这一物体因而既充当了屏蔽和转移创伤的作用,也为回忆提供了线索,使得恋物者能相对安全地面对创伤,面对造成创伤的本体。这似乎很适用于解释张爱玲的个人经历,恋物起始于创伤,衣服成了目光在创伤压力下随意而又宿命的选择,成为记忆的胶着点。但是,这个理论似乎难以解释衣服在张爱玲的生活和作品中所担任的纷繁众多的角色。
对于张爱玲本人来说,穿衣有意无意透露女性意识和自我。在《对照记》这本她去世前一年出版的简短的图文并茂的自传里,她回忆自己的祖母把父亲和姑姑小时候穿成“阴阳颠倒”的事情。祖母给姑姑穿男装,用男性化称呼,张爱玲认为这样做“似是一种蒙昧的女权主义,希望女儿刚强,将来婚事能自己拿主意”④。书中还收有她那几张颇为著名的时装照,有她穿着祖母的被面改出来的裙装与李香兰的合影,还有她“完全不管别人的观感”、穿上用大红大绿广东土布做成的上衣作“飘飘欲仙”状的单照。不过,最著名的大概是她上穿清装大袄下着旗袍带着睥睨众生的神情的那一张,那身奇装让看照片的人多少有一点点疑惑和不安,这感觉大约正是她想要的效果⑤。不由想到张爱玲为她的《传奇》再版设计的封面上那个“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的”“现代人”⑥。这现代人非男非女,面目不清,他/她的出现打破了居于画面中心穿着清朝服饰在幽幽玩骨牌的女人和她的奶妈以及小孩子所构成的安稳的传统家庭气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幅杂拌儿的画可以看成是作家的自喻。张爱玲,一个书写传统和现代交接时期生活的“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一个敢于将传统和现代大胆穿在一起的女性,炫衣又炫文,可算作是那个时代前卫的行为艺术家了,衣服是她的纹身和宣言。
衣服当然也可以拿来大作文章。张爱玲在1943年先用英文在《二十世纪》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式生活和时装》(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一文,洋洋洒洒如同书写衣服文化史,不到一年后又将其改写成中文的《更衣记》,在《古今》杂志上发表。衣服成了她观史察世的透视镜,也成了她小说里最常见最重要的话题、道具、意象和譬喻。张爱玲写衣服,举轻若重,踵事增华,仿佛恋恋于绮罗万象,但她更写衣服表象后面的矛盾、欲望、幻想和记忆。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恋衣之人多是女人,写衣亦即写女人。对研究张爱玲作品的人来说,“恋衣癖”不仅仅提供了一个了解作家本人写作动机的重要线索,也为探索女性主体性和文学文化现代性提供了一个管窥视角。在以下的分析中,笔者将结合女性主义理论、电影理论和白话现代主义理论分析张爱玲怎样以衣写人,特别是她怎样以“恋衣”之女人书写“现代”⑦。
二
仔细再读弗洛伊德的“恋物癖”理论和张爱玲的文章小说,我们意识到此恋物非彼恋物,因为我们看到弗氏强调的是男性视角、男性经验和心理,男性主体论不言而喻。然而就其所论的恋物机制,尤其是回避现实转向他物这个自相矛盾又带自欺成分的心理过程而言,或者如果“去势”(castration)忧惧可以理解为一个带普遍意义的创伤性经验的比喻的话,恋物癖未必不可能用于描述女性。事实上,在许多女性主义理论研究者那里,恋物因为与欲望和主体能动性息息相关,因而有了新的意义,理解女性恋物癖成为理解女性主体的一个特殊渠道⑧。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我们看到了弗氏恋物论戏剧化却又微妙的变奏。在向我们展现纷繁迷人的物质世界外表的同时,作家也向我们暴露表象背后的猥琐卑鄙和不堪一击的虚妄。更重要的是,她向我们揭露了女性自身的矛盾——恋物的女性明明知道华丽背后的丑陋,然而她却偏过头去……这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里有最精美的表述。
一个来自上海的女学生,在拜金的香港堕落,沦为高尚社会的风尘女子,这是《沉香屑:第一炉香》故事的主干。通俗剧里常见的人物、背景材料和冲突结构,它都有。故事本身也可以被当作社会小说,告诫那些涉世未深的良家少女,须在道德约束和欲望之间做出正确选择。可是张爱玲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教诲世人的案例,而是一个长长的解释。只因堕落并非一天完成,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作家更意在描绘人物“下落”过程中的几起几浮、“痛并快乐着”的奇异而矛盾的心情。看过这篇小说的人都会有一个印象,简单来说,就是“华丽”。富丽精巧的文字显然适合对奢靡的物质世界精描细画,而纷至沓来的意象则让人目不暇接,那种带着略略晕眩的惊奇之感,也正是作品女主人公葛薇龙初识繁华时的感受。故事开头没多久,葛薇龙搬入香港姑姑的半山豪宅,从此一个清贫家庭出身的女学生逐渐蜕变成社交界的交际花。张爱玲描写薇龙初来乍到时的忐忑不安和小心翼翼的笔触,显然带着很深的《红楼梦》痕迹。不过,虽说二者寄人篱下的心思相仿,但葛薇龙身处的世界显然大不同于林黛玉看到的贾家。后者官宦家族的富贵带着理所应当的秩序感,前者则是殖民地治下畸形颓废的摩登景象。葛薇龙“叹世界”的冒险之旅是从一个挂满衣服的壁橱开始的:
薇龙上楼的时候,底下正入席吃饭,无线电里乐声悠扬,薇龙那间房,屋小如舟,被那音波推动着,那盏半旧的红纱壁灯似乎摇摇晃晃,人在屋里,也就飘飘荡荡,心旷神怡。薇龙拉开了珍珠罗帘幕,倚着窗台望出去,外面是窄窄的阳台,铁栏杆外浩浩荡荡都是雾,一片蒙蒙乳白,很有从甲板上望海的情致。薇龙打开了皮箱,预备把衣服腾到抽屉里,开了壁橱一看,里面却挂满了衣服,金翠辉煌;不觉咦了一声道:“这是谁的?想必是姑妈忘了把这橱腾空出来。”她到底不脱孩子气,忍不住锁上了房门,偷偷的一件一件试着穿,却都合身,她突然省悟,原来这都是姑妈特地为她置备的。家常的织锦袍子,纱的绸的,软缎的,短外套,长外套,海滩上用的披风,睡衣,浴衣,夜礼服,喝鸡尾酒的下午服,在家见客穿的半正式的晚餐服,色色俱全。一个女学生哪里用得了这么多?薇龙连忙把身上的一件晚餐服剥了下来,向床上一抛,人也就膝盖一软,在床上坐下了,脸上一阵一阵的发热,低声道:“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坐了一会,又站起身来把衣服一件一件重新挂在衣架上,衣服的肋下原先挂着白缎子小荷包,装满了丁香花末子,熏得满橱香喷喷的。
薇龙探身进去整理那些荷包,突然听见楼下一阵女人的笑声,又滑又甜,自己也撑不住笑了起来道:“听那睨儿说,今天的客都是上了年纪的老爷太太。老爷们是否上了年纪,不得而知,太太们呢,不但不带太太气,连少奶奶气也不沾一些!”楼下吃完了饭,重新洗牌入局,却分了一半人开留声机跳舞。薇龙一夜也不曾合眼,才合眼便恍惚在那里试衣服,试了一件又一件,毛织品,毛茸茸的像富于挑拨性的爵士乐;厚沉沉的丝绒,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歌;柔滑的软缎,像《蓝色的多瑙河》,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了全身。才迷迷糊糊盹了一会,音乐调子一变,又惊醒了。楼下正奏着气急吁吁的伦巴舞曲,薇龙不由想起壁橱里那条紫色电光绸的长裙子,跳起伦巴舞来,一踢一踢,淅沥沙啦响。想到这里,便细声对楼下的一切说道:“看看也好!”她说这话,只有嘴唇动着,并没有出声。然而她还是探出手来把毯子拉上来,蒙了头,这可没有人听见了。她重新悄悄说道:“看看也好!”便微笑着入睡。⑨
在这两段里,我们不仅“知道”薇龙的衣橱里挂满了各式衣服,知道这是一个精于算计的姑妈在她身上下的一笔投资或赌注,而且真切地“看到”衣服的层层细节——颜色、样式、质地、甚至声音;我们更“看到”人衣之间微秒的互动,尤其是后者激发的欲望和想象。现代作家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常常直入内心为之代言,描景绘物会事无巨细,以求写实效果,却往往人是人,物是物,各不相干。张爱玲在这里不吝笔墨描写“衣服”的细节,目的其实不是为状物而是为写人。葛薇龙的衣橱打开了一个奢华生活的门缝,让这个出身贫寒的女孩子瞥见了一个另外的世界,内心产生强烈的震动。在上面所引的第二段描写里,衣服更飞离了衣橱,进入了女孩子的梦和潜意识,和她的身体的欲望交织在一起。由此,葛薇龙的衣橱也让读者窥看到人物的内心深处。事实上,这种种关于衣服的细节远远超出了情节的需要,而当细节的量达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不妨说,细节有时会成为反戏剧性的力量。它转移了读者对故事的注意力,它让戏剧性冲突偏离了主航道,但是没有这些细节去描画薇龙最初内心的震撼、斗争和屈服过程,人物不会这么具有立体感,故事往后的发展也就不会那么顺理成章。并且,这些看似“多余”的细节引领我们去听故事的“弦外之音”,不仅看到了个人和金钱社会的外在冲突,而且看到了这种冲突在人物心里的内化。葛薇龙的衣橱指向了故事的内核——恋物欲。
有人会问,张爱玲小说里这样近乎放恣的细节想象和描述是否本身就是恋物欲的表现?这种对细节的耽溺是否掩盖了细节背后的真实?研究好莱坞经典电影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电影评论家们,会抓住好莱坞摄影镜头对美丽女性面部显示的浓厚兴趣这一条,指出这种艺术倾向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男性恋物欲和商品恋物欲相交织力量下的产物。电影对迷人的女性面部和身体的特写,正如对商品进行精美地包装,诱人的外表掩盖了资本剥削的丑陋和女性身体商品化的真实。是的,张爱玲的小说常常带有某种电影感,像前面所引两段里有声有色的状物写人完全可以直接搬进电影。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在这一场景末尾,镜头逐渐逼近放大葛薇龙的半梦半醒的美丽的脸,在停顿几秒钟之后,转向她满屋零乱的丝绸罗缎。然而,张爱玲的小说并没有耽溺“色相”,而是揭露“色相”之后的不堪,是对恋物欲的反动。在她的小说世界里,女性并非恋物的对象,而往往是恋物的主体。张爱玲的女主人公,无论善恶好坏,绝不是好莱坞经典电影特写镜头里的女性——空洞的静止的影像“奇观”(spectacle)、男性性幻想的媒介和投射。恋物的女性在张爱玲的文字里是不安的、充满欲望的、自恋的,却不是被动的。这当然跟她的女性视角不无关系,而她的写法也是重要原因。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张氏文字叠床架屋,却毫不累赘,叙述语言极富弹性,对人物心理描写更是伸缩自如,能出能入。只写薇龙的穿衣和脱衣,写她的自言自语,没有大段的内心独白,却把一个完整的内心挣扎过程展现出来了。
在葛薇龙的香港,物质已不再是身份阶级的特殊体现和体验,它摆脱了阶级和其他传统价值的束缚,成了自在的商品。这种物质的蜕化和女性的商品化之间不仅是主题的相互映照交织,而且是有机的共生共长。张爱玲写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批判小说,以期控诉资本主义对个人的腐蚀——拜金恋物导致滥情或无情。相反,在小说的女主人公葛薇龙身上,我们看到她的恋物和痴情何其相似:都是试图借“物”来满足内心的无名的欲望,借“物”来遮挡不堪的真实。薇龙的悲剧不在于她的恋物和痴情,而在于她自始至终的清醒。一方面,作者让我们看到,薇龙的恋物是一个自觉的选择,她对华丽背后的肮脏交易有着敏锐的直觉——“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然而末了,她的怀疑和不安被“叹世界”的欲望冲动取代,“看看也好!”——与其说这是一个爱慕虚荣女子的自我安慰之言,不如说是普天下对欲望有着巨大好奇心的人的共同心声。衣服成了薇龙遇到的第一个“情人”,她放下了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防线——精神防线。这之后的所有抵抗证明都是徒劳的,自欺欺人的。三个月后,当她再打开衣橱时,她对于这样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⑩。另一方面,作者也让我们看到,薇龙对自己痴情于花花公子乔琪有着深刻的认识。在她目睹乔琪和婢女之间的苟且之后,有这样一番心理剖白:“她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浪子,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的她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11)然而对真相的了解并不能改变她的选择,薇龙服从了她的不可理喻的欲望。葛薇龙,这个眷恋锦绣云衣的女子,最后从“半山”跌落到“海角”:
……从此以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与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但是她也有快乐的时候,譬如说,阴历三十夜她和乔琪两个人单独的到湾仔去看热闹。湾仔那地方原不是香港的中心区,地段既偏僻,又充满了下等的娱乐场所,惟有一年一度的新春市场,类似北方的庙会,却是在那里举行的,届时人山人海,很多的时髦人也愿意去挤一挤,买些零星东西。薇龙在一档古玩摊子上看中了一盆玉石梅花,乔琪挤上前去和那伙计还价。那人蹲在一层一层的陈列品的最高层上,穿着紧身对襟柳条布棉袄,一色的裤子,一顶呢帽推在脑后,街心悬挂着的汽油灯的强烈的青光正照在他广东式的硬线条的脸上,越显得山陵起伏,丘壑深沉。他把那一只手按在膝盖上,一只手打着手势,还价还了半晌,只是摇头。薇龙拉了乔琪一把道:“走罢走罢!”她在人堆里挤着,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头上是紫黝黝的蓝天,天尽头是紫黝黝的冬天的海,但是海湾里有这么一个地方,有的是密密层层的人,密密层层的灯,密密层层的耀眼的货品——蓝瓷双耳小花瓶、一卷一卷的葱绿堆金丝绒、玻璃纸袋装着“巴岛虾片”、琥珀色的热带产的榴莲糕、拖着大红穗子的佛珠、鹅黄的香袋、乌银小十字架、宝塔顶的大凉帽;然而在这灯与人与货之外,还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12)
薇龙和乔琪的结合当然不是小说的高潮,至少不是戏剧性的高潮,因为戏剧性是要让所有矛盾冲突激化,为的是成就一个有力感人的结局。戏剧性高潮源于不妥协,而薇龙和乔琪的结合是妥协。对于薇龙来说,婚姻不是矛盾的结束,而是更艰难的开始。然而通俗剧里的眼泪、控诉和安慰,张爱玲不愿给我们。在小说的结尾,张爱玲仍然不放过她的女主人公,用“残酷”的文字和意象让薇龙越过“物”的迷障看清现实和未来,直面色背后的空——它的虚无和荒凉。薇龙在天地物之间得到的启示,是近乎于佛教里勘破红尘的悲天悯人。而她所能怜悯的只有她自己,她没有一个来世可以委顿,她所能够做的只是把现实和未来推到脑后——“不能想,想起来只有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这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里,她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13)。此时,物品成了救命的鸦片,有毒,但可以纾解恐惧,屏蔽残酷的真实。在薇龙身上,我们看到一种奇异的坚决饮鸩止渴的坚决。这是一种无关革命理想的“宁死不屈”。这种对毁灭的拥抱是非理性的,来自于个人内心那“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14)。正是因为这种坚决,一部本来是煽情的“文艺片”脱下了它的俗套,有了悲剧感。
葛薇龙以及张爱玲的许多其他女性人物,都是所谓的“不彻底的人物”。她们显示的现代性也是不彻底的、充满矛盾的。张爱玲的女性很多像葛薇龙一样,走出传统家庭和父权社会,她们走进一个更广阔的现代社会空间。虽然这个空间并没有准备好诸如葛薇龙之类的女子的到来,或者这些女人也并没有获得真正应对现代生活的技能和经验,然而她们毕竟走进了历史。张爱玲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写女性恋物,是为了写自我意识与主体欲望的提升,写她们的委曲求全、幻想和自欺。像葛薇龙这样的女人或许是失败者,可是正是在她们的挣扎和犹豫中,张爱玲让我们看到传统和现代交接时的模样和声音——那是“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15)。
三
一个已婚的成熟妇人爱上了她的房客,在一个雨后的下午,将他的大衣挂起,然后静静坐在大衣下,让“衣服上的香烟味来笼罩着她,还不够,索性点起他吸剩的香烟”(16)。这一幕发生在张爱玲的另一个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一个看似无关大局的小细节,成了小说情节的转折点。之前一直在理智和欲望间纠缠不清、下不了决心偷情的男主人公佟振宝,不意中偷窥到这一切,被这个叫娇蕊名字的艳丽的女人彻底征服了。小说这一节颇似电影场景。我们可以想象:振宝的眼睛即是镜头,娇蕊虽在注视下,却只沉湎于她自己营造的欲望的幻想里,毫无感觉自身的欲望勾起观者的欲望。然而,小说的电影感并不能让我们将二者等同。在这里,张爱玲的文字似略胜电影摄像机一筹。这是因为,读者跟随振宝的目光,不仅将娇蕊看在眼里,亦因这目光在文字中反射振宝本人而了解到他的怯懦和伪善。读者事实上是同时看到了两个人,看到了男女间主动和被动关系模糊却剧烈的变化,也看到了他们关系里深埋的心理错位。我们通过作者使用的自由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speech)式的叙述,看到振宝的眼光和心理视角显然是习惯性的居高临下:
振宝像做贼似的溜了出去,心里只是慌张。起初是大惑不解,及至想通了之后也还是迷惑。娇蕊这样的人,如此痴心地坐在他大衣之旁,让衣服上的香烟味来笼罩着她,还不够,索性点起他吸剩的香烟……真是个孩子,被惯坏了,一向要什么有什么,因此,遇见了一个略具抵抗力的,便觉得他是值得思念的。婴孩的头脑与成熟的妇人的美是最具诱惑性的联合。这下子振宝完全被征服了。(17)
此前,作者用了相当长的篇幅勾画振宝的“去势”忧虑以及因而产生的对保持性心理优势的强烈需要,振宝的自鸣得意看起来似乎顺理成章。在这一段中间,张爱玲用了自由间接引语让叙述意识时而游离在外,时而与人物的心理意识合二为一。作为读者,我们很容易会认同振宝的视角和观点,忽略作者的存在,忽略埋在语句里的微妙的反讽。而张爱玲的独到之处,却正在这反讽——不露声色地让人物自我揭露。我们还应看到,这种反讽在暴露男性视角的同时,也向我们暗示男性观者和女性被观者之间的沟壑——振宝看到的娇蕊“痴心”、任性、孩子气,这是他想看到的,也是他能接受的解释。然而细读此节,我们发现,娇蕊衣下点烟的举动,固然是其娇媚可爱的又一证明,但与之前两人打情骂俏时不同,在这个看与被看的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交流的目光,偷窥者和被偷窥者各自活在各自的世界里、想象里。在这里,我们须甩脱振宝的引导性目光再来看一看女主人公,看一看她奇怪的举动。
小说初始,衣服是男性欲望的聚焦点。振宝的猎艳方式之一大概就是任由目光在女人的衣服上逶迤,先有巴黎妓女的黑蕾丝纱底下的红衬裙,然后是初识王娇蕊时她穿的各式随便而又风情万种的衣服——“松松合在身上”的纹布浴衣和露出深粉红色衬裙“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曳地长袍(18)。可是,在上述那一幕偷窥的场景中,我们看到衣服也同样凝聚了女性的欲望。它一方面揭示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恋物倾向——前者的窥淫带着侵略欲和自恋,而后者则沉浸于自我陶醉和自我满足。另一方面,读者看到的并不是女人恋衣的无邪的“好奇”,而是极其隐私的举动。它让振宝想入非非,却给我们带来困惑:热情似红玫瑰的娇蕊这么做,究竟是因为爱上了振宝这个男人呢,还只是借“物”抒“情”——一种没有具体对象的自淫(autoeroticism)?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说,娇蕊是张爱玲笔下一个代表女性之谜的人物?张氏的高明之处在于,她把这样一个经典的谜团放在了一个看似普通简单的女性身上,一方面以对话叙述等“显/实”的方式来表现她俏皮大胆的一面,另一方面以“隐/虚”的文字,如第三人称的描述和重影(overshadowing)人物刻画,呈现人物的复杂性和抽象性,或更确切地说,呈现男性想象以及男权文化想象中不可捉摸的女人心/性(19)。和《西厢记》里的莺莺一样,娇蕊的爱欲因为简单而彻底,让振宝如张生一样心生畏惧。因为那简单和真实后面是他们无法把握的东西,于是欢愉过后隐隐的恐怖渐生渐长。张生以“天之尤物”一语斩断情缘,振宝则要打造维护一个完美的“对的世界”,看似不通情理,其实是过分理智,而过分理智也是一种疯狂。
张爱玲一笔双雕的反讽写法让读者无法完全认同振宝的恋物视角,也让娇蕊的自我沉溺的举动在文本中成为一个超出叙述结构的细节之谜。有趣的是,多年以后,这个谜在香港电影导演王家卫的影片《花样年华》(2000)里得到延伸,我们在张曼玉扮演的苏丽珍那里看到“娇蕊还魂”,虽然居住在60年代香港拥挤的公寓里的苏丽珍并无娇蕊那般风流。事实上,她正是因为谨守“妇道”而压抑自己的欲望,最后既没有跟男主角周慕云上床,也没有一起情奔,选择离开香港到新加坡重新开始生活。但是,如果说张爱玲让娇蕊近似放荡的衣着风格迷惑了振宝和读者们的道德感,王家卫也是以衣诱人。影片将浓烈的怀旧悼念情绪泼洒到女主人公绚烂的衣服上。仪式一般,苏丽珍穿上一套又一套精致如画的旗袍,照亮了每一个庸常粗鄙的生活角落和过道。在吸引和他一样被爱人背叛的周慕云的同时,她也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乍一看,影片赤裸裸的影像恋物完全是女性主义电影论者所批评的典型案例——电影影像中的女性成为男性恋物与商品恋物的两种物化过程的交汇点。一方面,电影镜头恋于片中女性的魅惑和神秘,它极力展现的是激发男性爱欲和膜拜的女性形象,父权/男权社会真实的两性关系和女性身体引起的焦虑因而被转移或掩盖;另一方面,女明星银幕内外光彩照人的形象使商业电影得到华丽包装,而商品背后的劳力剥削和资本运作的真相,在其熠熠生辉之外表下亦消失不见(20)。然而细看《花样年华》,摄影机下的女性身体的恋物倾向被影片所表现的女性自身的欲望所颠覆。苏丽珍没有消失进画面而成为静止的视觉对象,她每一次的盛装出场,都为我们带来惊奇和尊重。一方面,她的“一寸寸都是活的”的衣服线条让人觉得女主角仿佛是在一件一件将内心压抑的欲望穿在了外面;另一方面,她几近肃穆的神情消减了“色”相。我们还看到,欲望作为这部电影的内核,不是纯粹从一个男性视角出发展现的。在他极具个人风格的散漫的叙述里,导演王家卫添加了一个张爱玲式的女性恋物情节。在电影的尾声,苏丽珍来到新加坡寻找周慕云,她拨通了周工作的报馆的电话,却没有说话。又趁着周不在,溜进他住的旅馆房间。在一连串跟踪的镜头里,我们看见她奇怪的动作:她在房间里东瞧西看,她的手指滑过周慕云的随身物品和床榻,她拿起了他的香烟夹。像娇蕊一样,她点燃了烟,却并不去抽它。接下来的镜头里,前景是香烟在烟灰缸里燃起的袅袅轻烟,背景里是苏丽珍在躺椅上享受烟味和它唤起的回忆和想象。在电影镜头里,我们看到了“物”唤起的女性欲望,这和振宝所看到的情形几乎是一样的,只是电影里没有了振宝的偷窥的目光和自以为是的解释。对电影整体来说,这一恋物情节打乱了之前我们对这个几乎是经典的罗曼蒂克故事的想法,女性由诱人的人变为主动的欲望钩沉者,通常故事里的所谓失之交臂也被解构成女主人公的有意为之。影片结尾周慕云以嘴对向吴哥窟墙洞诉说秘密的画面则更具阴性象征意味。在绵长的掠过废墟的长镜头画面里,苏丽珍所代表的无法实现和满足的欲望扩展成一个对特定年代的缅怀以及对时间、历史、青春的抒情。电影对物与女性、欲望和记忆的关系的处理仿佛得到张爱玲细节美学和感性美学的真传。
四
要全面深刻地理解张爱玲作品里的女性恋物,还需要把作家和作品放在更广大的现代性语境下来看。张爱玲对衣服的踵事增华其实反映了一种所谓的“白话现代主义”的美学。
“白话现代主义”理论的核心是都市文化场所及其他公共领域里出现的“感官—反射”(sensory-reflexive)经验和话语。这一理论概念是芝加哥大学电影研究学者米莲姆·汉森(Miriam Hansen)首先提出的(21)。它的哲学基石其实是本雅明广义的“感知”美学理论,强调文化与科技、经济以及社会现代化变迁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将原本不属于美学的研究对象,如大众文化、商品文化以及城市经验与空间,亦纳入研究范畴。汉森理论的出发点和重点是经典好莱坞电影的现代性。她认为,这一时期的好莱坞电影作为福特汽车时代的美学媒介,以其多元性、朝气和活力、以及包含男女平权思想的进步意识,成为“现代性”的化身(22)。好莱坞电影作为第一个国际性的跨文化的白话现代主义话语(idiom)之所以在他国能成功,不仅仰赖其具有普世意义的叙事结构和先进的摄影技术,而更是因为它展现了一个容纳百川的现代视野和现代经验。另外,虽然汉森没有具体谈到文学意义上的白话现代主义,她用“白话”一词却保留了这一概念在广义上的语文含义——白话是夹在官方语言/国家话语和地方土话/俚语之间的一种中间形式(23)。白话现代主义与严肃文学和实验性电影所代表的经典现代主义不同,后者含有“反抗、否定或者削弱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消费逻辑的成分”,而白话现代主义靠拢观众,努力拉近和大众的距离,通过商品消费一整套系统帮助建立起一个公共领域。它对传统类别的作品不是一概拒绝和摒弃,而是在其之上做各种变换和修改(24)。
汉森所提出的这一理论概念具有宽泛的理论潜力,它不仅适用于研究亚洲各国现代化伊始时期的本土早期电影,而且对研究中国的其它大众艺术形式,尤其是同时期的白话大众文学,也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看到,正如好莱坞电影里的宽广的现代性视野和复杂的现代性经验以文化转译(cultural translation)的方式在中国20、30年代的早期电影体现出来,现代欧美文学也通过翻译形式对民国早期的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写作起到深刻影响(25)。白话大众文学通过公共领域的“感官—反射”机制大范围地传播了新的社会观念和主体想象。学者李海燕在其研究中指出,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在建立文学公共领域和资产阶级身份这两个方面独树一帜地作出了贡献(26)。其中,她特别指出鸳鸯蝴蝶派以言情至上代替传统儒家道德至上的颠覆性(27)。而我们可以推断,这种颠覆性会因小说的大众性和流行性而得到推广和深化:“他们的不忍流泪向他们自己证实了他们的感性,指向共同的人道,也赋予他们一种既个性化又有普遍意义的身份认同。在阅读和哭泣中,读者被转变成能够走到一起的公共群体——一个伤感主义流行的群体。”(28)
张爱玲与鸳鸯蝴蝶派不仅有很深的渊源,而且二者都以“言情”介入现代性(29)。他们的作品的流行显示出类似电影的白话现代性。具体到张爱玲这里,这种现代性还可以这样解释:其一,电影影像的现代性与它所投射出的文化想象空间和视觉意识(optical consciousness)不光充满都市的繁荣和摩登景象,也暴露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思想意识的冲突和矛盾,而且常常以女性形象作为其表现现代性的矛盾隐喻。同样,张爱玲也在她的小说中为读者推出了一个广角镜头结合近镜头下矛盾重重、多元流动的现代世界,绚丽与不堪共存,传统和摩登毗邻。张爱玲的成功有赖于这样的与时共进。其二,张爱玲在出版界和文化领域引发的争议和赞扬,读者评家明星式的追捧,电影和戏剧改编的热潮,她个人的特立独行甚至家世背景以及私人生活种种所引来的大众想象,都让她的作品如同流行电影,汇入了白话现代主义的“感性—反射”的公共空间。其三,她的作品吸引了一个广大的日益复杂和多层次的现代读者群。张爱玲作为畅销书作家深谙现代大众/商品文化的矛盾性——它给像她这样的职业作家/女性作家同时带来了自由和限制。面对这样的现实,她表现的是既迎合也抵抗的态度。关键的是,她能在体系内和传统题材上做出新的尝试和创新,以“要一奉十”的写作原则成就了现代文学的亦雅亦俗的神话(30)。
张爱玲作品和张爱玲现象固然可以看作是白话现代主义的代表案例,但她的反讽的写作手法的穿透力,她的个性化的女性主义美学和历史观,尤其是她的关于“物”和(女)人关系的重新思考和想象,都使得她的作品超越了白话现代主义所强调的感官性和集体体验大众性为主的现代性。这一点仅从衣服这个细节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方面,和早期电影一样,张爱玲的小说以及散文都表现出对现代生活和现代性审美的关注,特别是对日常生活题材格外的偏好(31)。衣服作为日常生活最重要的细节在张爱玲的散文和小说中俯拾皆是。事实上,张爱玲本人对时装和色彩的敏感、她的绘画才能,都使她的小说和散文无一不予人以强烈的视觉效果。然而另一方面,和电影对“物”的直接展示不太一样,张爱玲写物从来不是纯粹的“写实”,不胶着于物的表象。各方论者对张爱玲的“意象美学”早已论述颇丰,此处不再赘言(32)。并且如前所述,她使用的自由间接引语式的叙述策略和反讽手法让她的笔锋具有一种比摄像机更具穿透性、揭露性的力量。不过,张爱玲之所以能将大众化的情节叙述演变成现代传奇,能在白话现代主义的美学号召力上更进一层,不仅要归功于她的女性化的文字感官性和灵活性,更得益于她的女性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化历史观。张爱玲在《更衣记》里这样调侃:“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33)这是张爱玲式的幽默和敏感,她看到了女性和“衣服”之间奇妙的联系。女性从一件男人身上可穿可脱可补的衣服,从“本身是不存在的”衣服架子,成了嗜衣恋衣之人,说明了时代的飞跃。然而,张爱玲不是高唱物质现代化的简单论者。华丽或摩登的衣服下并不是自由的女性,而常常是迷惑于物欲和自身欲望的半新不旧的现代人。在前面的文本分析中我们看到,张爱玲写衣服,不但写“物”和表象,更写表象后边的女性欲望、幻想和矛盾。她的鲜明的女性主义观使女性人物从被恋之物变成恋物的主体,成为挣扎在物欲和人性之间的矛盾的“人”。也因此,她的作品里的女性形象不再是空洞而华丽的表象、男性欲望的符号和投射,她们甚至也不再仅是白话现代主义电影里表现现代性矛盾、表现传统性别意识和现代性相冲突的“隐喻”。
衣服凝结了张爱玲个人童年的伤心的回忆,充当了她飚扬个性、与世俗抗讦的道具;它是她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藉之想入非非的欲望媒介,也是作家对她们或远观或近瞧、抽丝剥茧式的心理探测器,而衣服更唤起作家对历史、传统以及对过去生活集体记忆的联翩浮想。在《更衣记》的开头,张爱玲以她惯有的叙述腔调这样开始她的衣服史: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富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
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34)
衣服虽轻,可以载史。它的语言不是符号,而是真实的与身体接触过的物质和记忆。这是张爱玲“恋衣”文字的现代性和历史性:所有属于记忆的,也是历史的;所有属于美的,也是历史的;所有属于感觉的,也是历史的;所有属于身体的,也是历史的。
注释:
①张爱玲:《私语》,《张爱玲典藏全集》第3卷,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页。
②张爱玲:《童言无忌》,《张爱玲典藏全集》第3卷,第6页。
③④⑤张爱玲:《对照记》,《张爱玲典藏全集》第5卷,第40-41页,第56-57页,第65-83页。
⑥张爱玲:《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张爱玲为《传奇》增订本(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版)写的序言,《张爱玲文集》,安徽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页。
⑦有关张爱玲作品里对衣服的描写,参见黄子平《更衣对照已惘然》,许子东、梁秉钧、刘绍铭编《再读张爱玲》,山东出版社2004年版。另参见张小红《谁与更衣》,金宏达主编《华丽影沉》,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
⑧“女性恋物”这一概念首先是英美文学研究者提出来的(Cf.Naomi Schor,"Female Fetishism:the Case of George Sand," in Bad Objects,Essay Popular and Unpopular(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另参见 Majorie Garber,"Fetish Envy,"Ottolfr,Vol.54(Autumn,1990),pp.45-56)。
⑨⑩(11)(12)(13)(14)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一炉香”),《张爱玲典藏全集》第7卷,第126-127页,第144页,第157页,第160-61页,第1611页,第157页。
(15)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典藏全集》第3卷,第16页。
(16)(17)(18)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第123页,第123页,第112、117页。
(19)所谓“重影人物刻画”可以看作是虚写人物的一种方式,振宝在娇蕊之前的两段艳遇不光为后来振宝心理发展做了铺垫,而且也将娇蕊的个案扩写成抽象的群体化的女性,她们同属于男性幻想中深具诱惑却隐含危险的女性。
(20)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将弗洛伊德的恋物癖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商品恋物理论结合起来,对好莱坞经典电影中女性塑造和由此折射的文化想象作出批判。弗氏理论里的个人恋物所依赖的心理机制和所生发的心理想象,被扩展理解成双重的文化集体无意识——资本社会与父权社会对两性差异的盲点的交集,而电影影像(image)中的女性成为男性恋物与商品恋物的两种物化过程的交汇点(CF.Laura Mulvey,"Some Thoughts on Theories of Fetishism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ulture",October,Vol.65,(Summer,1993),pp.3-20)。
(21)“白话现代主义”这一理论最早是芝加哥大学米莲姆·汉森(Miriam Hansen)在她2000年发表的一篇叫作《大批量生产的知觉: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好莱坞经典电影》(The Mass Production of the Senses:Classical Cinema as Vernacular Modernism)的文章里提出。该文载Modernism/Modernity 6.2(1999),pp.59-77。同年,汉森在美国的《电影季刊》(Film Quarterly)上发表文章《堕落女性,冉升的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Fallen Women,Rising Stars,New Horizons:Shanghai Silent Film as Vernacular Modernism),将白话现代主义理论运用于分析中国早期电影和中国现代性。该文的中文翻译见包卫红译文,载《当代电影》2004年第1期。
(22)参见Miriam Hansen,"The Mass Production of the Senses:Classical Cinema as Vernacular Modernism"。以下引文亦为作者译。
(23)(24)参见汉森2009年即将发表的论文《白话现代主义:全球电影跟踪》。
(25)参见潘少瑜《爱情如死之坚强:试论周瘦鹃早期翻译爱情小说的美感特质和文化意蕴》,载《汉学研究》第26卷第2期,2008年。
(26)(27)(28)Cf.Haiyan Lee,"All the Feelings that are Fit to Print:the Community of Sentiment and the Literary Public Sphere in China,1900-1918," Modem China,Vol.27 NO.3,July2001,p.296,p.304,p.301.
(29)王德威在《半生缘,一世情:张爱玲与海派小说传统》里梳理张爱玲与海派的关系,指出张爱玲的作品虽然多发在鸳鸯蝴蝶派的同路杂志,也“擅写半新不旧人家里的情事恨事”,但她的“五四训练,西学背景”又让她不同于前者(参见金宏达主编《华丽影沉》,第391页)。关于张爱玲与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的交往,参见周的回忆短文《关于〈沉香屑:第一炉香〉》以及水晶的《水晶注》,水晶编《替张爱玲补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30)张爱玲:《论写作》,《张爱玲典藏全集》第4卷,第59-60页。
(31)虽然汉森在她的文章里注意到张爱玲的作品,但也许因为研究领域的差别和语言关系,她没有具体也无法深究这个问题。
(32)孟悦在她的《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文章里就详细谈到张爱玲把“物”转化成意象的问题。该文收录在金宏达主编《镜像缤纷》。另参见许子东《物化苍凉——张爱玲意象技巧初探》,许子东、梁秉钧、刘绍铭编《再读张爱玲》。
(33)(34)张爱玲:《更衣记》,《张爱玲典藏全集》第3卷,第53页,第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