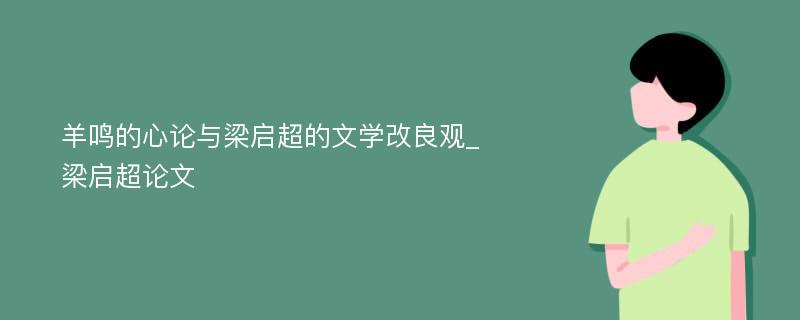
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心论文,文学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2)06-0722-07
一
清末民初的文学思想发展,“西方的冲击”当是一个主要因素,西学赋予了近代学者文学观念的新质。但过分强调西方文学的影响,就很容易忽视传统文化的复杂内涵和发展动力。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一定程度上是在传统文化领域里滥觞酝酿的。在19世纪末儒家思想文化论争中,阳明心学以其独特的禀性和特质,成为思想改革和维新的内在动力和精神向导。文学改良“咸与维新”,自然会受到阳明心学的濡染。
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以“良知”和“致良知”为主干,是有明一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说。他继承陆九渊“心即理”的基本命题,认为心是宇宙的本原,是“天下之大本”[1](第279页)。他进一步通过“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的反理性推导,把“心为天地万物之主”的唯心观贯彻得更彻底。这个心,王阳明又称为“良知”、“灵明”。“良知者,心之本体。”[2](第61页)“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2](第72页)“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3](第971页)所以“良知”既是万物之本体,又是天赋的理性,还是道德意识的主体。王阳明把主体和本体合而为一建构和演绎“心即理”时,强调理乃“吾心良知之天理”,心即“吾心之良知”,遵循的是心(良知)——物——心(良知)的思辨结构。
作为本体的“良知”,王阳明认为是人性普遍固有、不假外求的,“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然而“良知”并非现时现存,必须借外力发现。于是他把“良知”和“致知”结合起来,构成了“致良知”说。“致良知”的起点是“人心中各有一个圣人”[4](第116页),目标是“人皆可以为尧舜”[1](第280页)。故所谓的“格致”或“格物致知”就是指立诚、正心、修身等内心道德修养。王阳明从肯定心体与存在(人的存在)的内在关系出发,把天理从心外移入心内,主张“化天理为良知”,把“良知系于天之维”转化为“系于人之维”,实现了从超验本质向个体存在的回归,意味着“人”的发现。因此“致良知”昭示着一种启蒙的思想路尚,当然启蒙之义重在道德人性层面。
从超验的天理回到个体良知,自我成为本体论意义上的承担者,良知表现为主体的内在要求,心体蕴含着个体性原则。但是王阳明把理想自我理解为内圣的人格。按其本义,内圣的追求总是拒斥自我的封闭,要求实现群体价值。就其现实形态而言,个体的存在总是蕴含着与他人的共在。由此便演绎出自我与群体的关系。同时王阳明将万物一体说引入群己关系之域,以此定位自我与群体、存在与共在的关系。万物一体在广义上既涉及天人之际,亦指向人我之间。就天人关系而言,万物一体意味着超越天人的对峙;就人我之间而言,其内在含义则是主体之间从分离走向融合,亦即所谓“无有乎人己之分”。万物一体的主题就是打通主体间的关系,它抑制个体原则的强化而朝群体的方向演化[5](第6-12页)。
与心体的个体规定和经验向度相应,王阳明注意存在的感性之维及多重样式,视人的感性生命和情志为主体应有的规定。但修养进学、去欲存理的正心是其根本,因此他强调诚意“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以诚意为主”贯穿其哲学始终。两者的统一即为“心统性情”、“体用一源”的心体观念。他强调现实活动的心即是己发之心,也就是意。心学的根本在于诚意,诚意是复明和体现良知之心的境界。王阳明的“诚意”论追求的是在生命的整体性原则下,普遍和特殊、感性和理性的统一。这个基本要求,把儒家的理性教育路线转化为感性体认,同时也是心通过感性体认把日常的感性经验转向理性超越。感性体认的中心地位和中介作用,使阳明心学内在地具有一种美学精神,而诚意成为一种人生审美化的理想追求[6](第47-49页)。
阳明心学是社会面临巨大转折前夕的思想曙光。它倡言仁政,宣讲爱民,具有一定的民主性精华;它夸大主体精神,培养正气,批判官学,指斥时弊,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它简易直截,内涵丰富,又具相当的开放性。因此,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近代知识分子,为寻求救民救国的真理,都自觉地从阳明心学中汲取养料,铸炼匡世济民的思想理论武器。梁启超青年时代,“修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康“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梁启超惊叹其学之新颖、高深、锐利、明快,顿时拨去心中迷雾,“自是决然舍去旧学”[7](第16页)。此后又生崇拜之情,称他为“千古大师”[8](第41页);盛赞“晚明士风冠绝前古者,王学之功不在禹下也”[8](第126页)。于是阳明心学成为他强大的心力资源。
梁启超学涉中西,对中西政治文化采取双重的认同态度。在中西文化精神的对话中,梁启超借用了阳明心学提供的理论平台和思想工具,用王阳明“六经注我”思维方法,把西学融进传统经学体系之中。梁启超受到日本道德和政术不平衡的感悟,将“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即阳明心学,当做新的国民道德的一个要素,并提出“正本”、“慎独”、“谨小”三个纲领。他还认为梭格拉第(苏格拉底)、康德、黑智儿(黑格尔)是与王阳明“桴鼓相应,若合符节”的,所谓“泰东之姚江,泰西之康德,前后百余年间,桴鼓相应,若合符节”[8](第139页)。并把康德、黑格尔的道德主义与阳明心学调和为一。以心学作为沟通中西思想的工具,在《新民说·论自由》一文中表现得尤为典型。他主张发挥“学贵自得”、“独立不惧”、“人定胜天”、“克己复礼”的精神,立大志胆识,树信心勇气,去心中奴隶。在心学的思想领域里,把西方和传统的思想观念阐释得淋漓尽致。《新民说》的理论依据是英国近代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梁启超突出强调了群与一、整体与个体,即“拓都”与“么匿”的关系,把后者对前者的决定作用绝对化。由此他引出国家、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认为一旦人人成为新民,即可由个体的自强而达到中华民族群体的强盛,中国的变革也就完成。其中包蕴着阳明心学“内圣外王”、“万物一体说”要求引己入群的思想理路。
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当然是服膺政治的需要和改良的理念。他把文学与政治链接,既沿袭和重申了儒家的文学传统,又受到了日本和西方文学事象的启悟。而阳明心学提供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工具促成了中国文学传统和西方文学观念的契合,使中国文学传统得以延伸和转化。
二
“小说界革命”是在近代政治的促进和西洋小说的影响下产生的。梁启超的小说“新民救国”理论主要是受泰西政治小说的启发。当他发现小说的启蒙作用后,立即和“改良政治”联系起来,并竭力引进政治小说的样板。他认为,“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9](第56页)后来,进一步把西方“政界之日进”归功于“政治小说”[10](第35页)。其实梁启超对西方小说的实情存在很大的误解。欧美、日本的小说并没有左右当时的政局,也不存在“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的情形。显而易见,梁启超对西方小说的硬性移植和主观夸大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焦虑和一种策略性的思考。但我们不能仅仅认为梁启超只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忽略了他的心学背景支持。梁启超的这种观念,即使大家认定是他自己心造的幻影,但梁启超本人是非常真诚和坚信不疑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和坚信就源于他唯心主义的思想和认知模式。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篇就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写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我们从这段话中可理出如下思路:小说不可思议之力——新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新人心、人格(达到新民目标)。小说“不可思议之力”是什么呢?梁启超随后进行了阐释,即“熏、刺、浸、提”四种力,究其注解,就是“心力”。由此呈现出梁启超的思维逻辑为“心力——事物——人心”,这与王阳明的“心——物——心”的思辨模式如出一辙。在论述小说的四种力时,梁启超认为“熏、刺、浸”三力是“自外而灌之使入”,而“提”之力是“自内而脱之使出”。他把前三种力归根于“提”之力,以此力为“度世之不二法门”[11](第7页)。这表明梁启超所强调小说的“魔力”源于本心,小说对外在世界的作用是“内出外化”。其中暗含着“心为本体,事发己心”的观点,流露出王阳明“众理具而万事出”的心学观念。
在关于小说作用的论述中,梁启超不仅认为“小说为国民之魂”[10](第35页),还认为“小说可以支配人道”,并且把小说的堕落作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11](第8页),社会治乱均因小说之故。这些论述活脱出他的“小说造世界”观念。他的小说理论实际是只凭主观意识即可决定客观世界之变化,有形而上学和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倾向。应该说这与他从阳明心学得来的主观唯心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我们还须在进一步的追问中使这个问题明晰起来。第一,小说为什么能够新民?梁启超在这个问题上首先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人人都有爱人之心,爱国之情,救世之志。每个人都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可以被激发,并且能够接受先进思想的改造。这明显是王阳明“人人心中有一个圣人”、“众心一源”理念的现代演绎。基于此,小说改造人心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第二,为什么一旦造就“新民”就达到了“群治”,也就是说梁启超在“新民”和“群治”之间划了个等号。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事实上已超越了小说是为了启蒙民众的观念,把小说当成了社会政治现代化的力量源泉、发展途径、革新工具。这种观念的形成当然有其来历的。梁启超曾一再说:“人间世一切之境界,无非人心所自造。”[8](第116页)“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12](第12页)认为社会观念的变革可以决定一切,有什么样的思想便能形成什么样的事实,这是王阳明“心外无事、心外无物”的翻版。梁启超把个人性的小说欣赏和全民化的观念革新等同起来,把新民与群治等同起来。就文学而言,这是夸大了小说的社会作用,忽视了小说接受的个体性差别;就哲学而言,它否定了经济、政治等物质力量的决定作用,抹杀了具体实践的过程性。
“诗界革命”应“新学”而生,是近代西学东渐的文化走向的反映。梁启超说:“盖当时所谓‘新诗’,颇喜寻扯新名词以表自异”[13](第136页)。“新名词”是指外来的音译词,它的文化意蕴就是资产阶级的新思想,由此表明这些“新诗”就是维新志士研讨“新学”的文本记录。由新学而写新诗,其思想背景是出于当时“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14](第22页)。这显示了他们受到王学影响的历史文化动因。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诗界革命”时,“新诗”已从宣传“新学”提升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13](第137页)。因此,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三条标准: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第三“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15](第189页)。
“新意境”有时代生活的内容,但主要还是指新的思想和忧时感世的爱国之情。梁启超称黄遵宪,“阅历世事,暨国内外名山水,与其风俗政治形势土物,至于放废而后忧时感事,悲愤抑郁之情,悉托于诗。故先生之诗阳开阴阖,千百万化,不可端倪,于古诗人中,独具境界。”[14](第4页)梁启超以“现实”和“情感”来界定“境界”的内涵。但他又认为“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16](第45页)。显然在主观唯心论支配下,梁启超的“现实”应是心的投影。他所强调的是寄寓在诗中的情感。创造“新意境”必须有新的思想,只有用新的思想来写新的生活,才达到这个要求。梁启超说:“吾尝推黄公度、穗卿、观应为近世诗家三杰,以言其理想之深邃闳远也。”[13](第135页)梁启超就是从深刻的新思想的角度来肯定他们的。这里的新思想应该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他又称之为“欧洲意境”。
黄遵宪曾说:“吾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17](第127页)梁启超就是依循他阐释的形式规范和艺术精神来演绎“旧风格”的。无论是“比兴之体”,“单行之神,排偶之体”,还是“伸缩离合之法”、“《离骚》乐府之神理”,他所强调的是表现手法和艺术手段中蕴含的内在风骨、格调和神韵——这些都是发之于心、感之于心的质素。梁启超看到了创作实践中“旧风格”和“新意境”难以统一,“新语句与旧风格常相背驰”[15](第189页)。然而梁启超有意无意地忽视这种矛盾性的存在,坚持强调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个中缘故自是受到心学影响。他说:“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13](第136页)因此重胸中之意境而轻外在之形式。其次,他唯心地认为形式与胸中所设的内容,兼容于诗境中。心为本体,意为心发,言为心用,言传意达,自是言意一源,故毋须强调。梁启超所强调的“新语句”是针对“新诗”使人无从索解的“新名词”而发。他受王阳明“直捷简易”的语言特点影响和出于宣传新思想的目的,主张诗歌写作采用通俗又充满活力和表现力的民间词语,让人易于接受,能引起情感的共鸣。
基于相同的考虑,梁启超提出了“新文体”的概念。“至是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为新文体。”[18](第23页)这是对“新文体”作的一个概括。他以王阳明的“诚意”立说,主张散文创作须发于至诚、意气用事,有奋发向上的精神,充满热情和朝气。梁启超的文章在熔铸西方进化论、民权论等先进思想的同时,字里行间充斥着浓烈的革命豪情和强烈的感染力。他的文章是“赤子之心”的倾泄,纵横恣肆,雄浑豪放,震撼人心,令人张脉偾兴而为之感发兴起。同时梁启超秉承阳明心学反对权威、破除传统之自由精神,主张行文随心所欲,打破传统散文形式上的陈规俗套、清规戒律。“以自家之胸臆,立一定之准绳……若者为双关法,若者为单提法,若者为抑扬顿挫法,若者为波澜擒纵法。”[16](第72页)故梁启超文章腾挪跌宕,婀娜多姿。在语言上,梁启超取王阳明“直截明诚,活泼有用”之精神,注意吸收群众语言、外国词语,注入新鲜活泼的口语和不拘一格的句式,从而使文章体情状物真挚可爱;读时流畅自然,饶有风趣,沁人心扉,故风靡一时。
三
梁启超的文学“三界革命”是以宣扬欧洲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思想和启蒙精神为核心内容和价值取向的。他把文学作为宣传思想、改良群治的工具和手段。毋庸置疑,他的文学观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而政治功利性必然会排斥文学自身的审美性。在梁启超的文学主张中,确实有许多非文学的因素。但梁启超虽然没有恪守纯粹的艺术自律性,也不是像别人误解的那样只强调文学的政治工具作用而忽视文学的艺术特性。在他复杂的文学思想中,包含着强调文学作为艺术的自主性和自律性的要求。这是因为阳明心学所赋予梁启超的思想特质,调适了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和艺术审美性的矛盾冲突。
如果从他的著述中对其文学观进行“抽绎”,“情感”无疑是贯彻始终的话语。梁启超开创的“新文体”就是“笔端常带感情”。他的文章激情澎湃,感情浓烈,冲破传统散文的束缚,“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而在《译印政治小说序》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就是从小说能娱悦性情的维度阐释和倡导政治小说,并从人的感情和审美心理着眼,提出“厌庄喜谐”说、“浅而易解、乐而多趣”说、艺术审美心理移情说。在论及戏剧时,梁启超盛赞“一部哭声血泪之书”的《桃花扇》,因其“文章感人”而“冠绝前古”[19](第496页)。同样,梁启超主张“忧时感事,悲愤抑郁之情,悉托于诗”,欣赏寄寓着深邃闳远的精神理想的诗歌。更甚的是,他从心力决定论出发,引用一个眇目跛足的教师作军歌帮助斯巴达人克故的故事,极度夸大诗歌以情感改造世界的作用,希望“诗界革命”有此能事[13](第135页)。
梁启超对情感的注重,受到传统诗学“言志说”、明清小说戏剧言情理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也不乏阳明心学带来的文学感悟。从梁启超对文学中情感因素的分析,不难发现在心性和情感的关系上,阳明心学提供了他可以依凭的思想资源。他以情感为中心突出移情作用,着意文学审美产生的“虚牟一世,亭毒群伦”的价值功能。具体地说,就是重视文学由移情而达到移人的效果。他还认为人的情感愉悦的激发是人内心固有的心理因素被调动和激活,非外物所赋予。这正是王阳明“心统性情”、“体用一源”的美学思想。梁启超情感的内涵,不是个人化的亲情、友情、爱情,而是能决定国家兴亡、社会治乱、民族存亡的爱国热情和热忱,是一种具有凝聚力、亲和力的仁爱之心,也指奋发图强、坚毅英勇的精神意志。这情就具有“内圣外王”、“去欲存理”的心学色彩。在梁启超文学思想中,情感实现了两个转化:一是把先进的思想理念(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观念)转化为自我直接体认的生命境界和情感,二是把自我个体生命活动的情感、观念、欲望提升为宇宙生命本体化和整体世界的具体化表现,使情感化为普遍的理念,并且可以外化为物质力量改造社会。在世俗情感中梁启超注入了现实关怀和治世理想,其思维态势呈现出阳明心学的感性体认和理性超越相统一的美学精神。不过,梁启超文学思想的“主观性”、“内向性”是传承心学观念时自然形成的,他并没有从哲学、宗教和伦理的理念中自觉解脱出来。所以他论述情感时,只强调它是一种普遍共有的人性特征,忽视情感的世俗性和个体性差别。在具体的小说创作中,激情有余但个性不足,如《新中国未来记》,他没有把爱国激情化为艺术的情感,只是一种政治理想的演述。晚年的梁启超把情感作为文学的本质,认为情感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也就是创作的原动力,并强调:“最要紧的工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挈,向里体验。”[20](第72页)这正是对于“心统性情”、“心为万物之本”的体认。
梁启超以“吾国之王学”明“三界唯心”之真理,将“心力”和“三界唯心”说加以混合,调制出文学创造的源泉——“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即灵感。他在“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3](第214页)的思想基础上,契接佛教“三界唯心”之说,认为现实乃我心创造,人类文化的发展就是精神对物质的不断征服,是天才人物自动的精神创造。人人心中都有一种足以拯救自己并拯救世界的潜在力量,通过培养发掘,“自强其心”便能转化为外在的物质力量,可以成就一切,拯救一切,创造一切。消除“心中之奴隶”,不受任何限定的自由可以使人的潜在创造力和心理能量释放出来。因此他认为一切伟大的创造性事业都起源于灵感激情:“此心又有突如其来,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者,若是者,我自忘其为我。无以名之,名之曰‘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烟士披里纯’者,发于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刹那顷。而千古之英雄豪杰……以至热心之宗教家、美术家、探险家,所以能为惊天地泣鬼神之事业,皆起于一刹那顷,为此‘烟士披里纯’之所鼓动。故此一刹那间不识之知之所成就,有远过于数十年矜心作意以为之者。”[16](第71页)人的心体不为外境所束缚,不为外物所役,无挂无碍,即可独立特行自由自在地创造思想、改造世界。同样,文学作品乃作者“心力”瞬间释放的结果。随后,他进一步指出了灵感的特征:“‘烟士披里纯’之来也如风,不能捕之;其生也如云,人不能攫之。”那么怎样才能获得灵感呢?他说:“可以得之之道一焉,曰至诚而已矣。”[16](第71页)在文学接受上,梁启超以禅宗的顿悟立说。他在阐述小说四种力时,认为“薰”之力虽用渐,但也有“刹那刹那”的心理活动,并且“遂入其灵台而据之,成为一特别之原质之种子。”“刺之力用顿……在使感受者骤觉,刺也者,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禅宗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11](第7页)显然梁启超分析文学接受心理时,非常注重明心见性、自然显现、不假思维的“顿悟”。
无论是强调创作灵感还是阅读顿悟,梁启超都是基于一个阳明心学的逻辑:除去主观理念对良知的直觉感悟,就别无他法借助外力去复明人心中的“良知”。他试图以内省的方式,把宇宙、生命和众生“合并为一”,进而加强人们的道德情感的修养,赋予人心新的内涵和时代的意义。正是梁启超遵循王阳明的观点,把道德修养看做一种完全意志自由的内心体验,因而特别重视“求之于心、体之于心、验之于心”的灵感、直觉和顿悟。同时也赋予了文学一定程度的主体性和自律性。
四
梁启超希望借助文学启迪民智、涵养民德、振奋民心、改造国民性。“国民性以何道而嗣续?以何道而传播?以何道而发扬?则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21](第35页)他赋予文学以启蒙的功能。同时他大力推崇王阳明的“致良知”,在阳明心学背景中建构自己的文学观念。他认同“尽人所同有”、“不学而知”的良知,强调“言良知而须加一‘致’字”,并且更乐意把良知阐释为道德伦理意义上的良心与德性。显然,他的启蒙思想暗合了阳明心学的逻辑思路,或者说是阳明心学规范了梁的文学启蒙性。因此,在梁启超的文学观中,注重的是唤醒人们爱国爱民的“热度情感”,激励民众发奋英勇坚毅顽强的精神意志,陶冶人们纯然至善的道德情操。
到明朝中后期,阳明心学发展为多个派别。其中王艮创始的泰州学派因“不满师说”,于王学“多所发明”,提出了“身本论”的主张。王艮认为,身为本,而心须依附于身,故当尊身、修身、保身。概而言之,就是要求承认、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要求承认、重视人民的物质需求和生存权利;要求承认、肯定人的私心人欲;要求个性解放、自由平等;要求冲破封建束缚等等。实际上心学已从王阳明的强调人本位的思想启蒙发展为更重视个人权利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与泰州学派超越阳明心学的发展流向一样,承祧近代文学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启蒙性层面也实现了双重跨越。尽管“五四”新文学也高举“改造国民性”的大旗,借西学启蒙民众,但在逻辑思路和思想内涵上与梁启超迥然而异。在中西社会的巨大落差中,梁启超认为是制度上的不足,故援西入儒以改良政体。他采取一种“中西对等”的思维模式,自然难脱封建思想的巢臼。这在运思逻辑上,和王阳明大体一致,即启蒙是求诸内心而非依凭外界,追求道体而非解放个性,是道德教化式的启蒙和现实关怀性的全民启蒙。而“五四”精英,已认识到文化上的不足,力图冲破封建思想的一切藩篱。因此,梁启超的启蒙是“民”的发现,“五四”文学启蒙是“人”的觉醒。“五四”新文学强调的是个性情欲的解放、民主自由的要求、人格尊严的体认。这种文学启蒙是指向自我而非面向群体、追求个体而非乞求道德的启蒙,是自然人性论的启蒙和终极关怀的启蒙。它如泰州学派一样,秉持了世俗化和通俗化的文化思理。如果从心学发展的角度比较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性和“五四”文学的启蒙性,它们的内在品质无疑存在着一脉承递的关系。
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同时肇始了现代文学的两脉流向。一方面,他出于改良政治的需要,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使文学沦为政治的工具,是中国20世纪文学“工具论”的开山者。他的文学观念深深烙在后来者的身上,以后一段时期里文学被不断庸俗化,梁启超难辞其咎。另一方面,他从唯“心”观出发以心体的范畴规定文学,把文学引向人的内心,强化了“文学是心学”的观念,体认了文学的主体性和自律性。其潜在影响也不可小觑。这两种看似互相矛盾的倾向在梁启超的文学观里能有机统一并产生双重影响,其中的契机、理路乃至意义确实值得深思。
收稿日期:2002-05-25
标签:梁启超论文; 心学论文; 王阳明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文学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良知论文; 儒家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