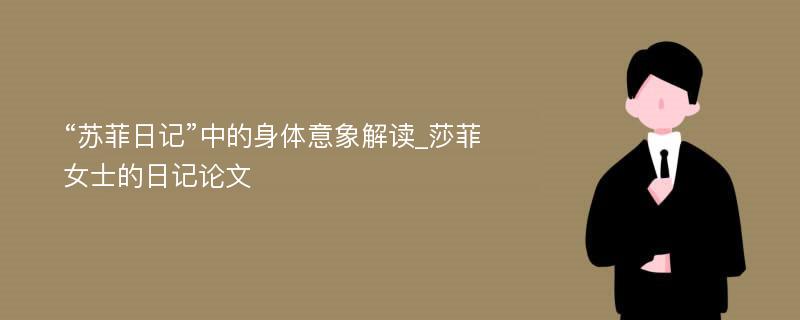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身体意象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女士论文,身体论文,日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身体不仅是一个生物存在,更是一个社会文化建构。身体能够感觉到痛苦和快乐,也能够成为思想的对象。重读丁玲(1904—1986)的经典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我们看到丁玲的这部作品不仅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而具有特殊的文学魅力,更由于作者在小说里使用了对疾病及有病的身体的描写这一独特手法深刻揭示了小说的主题,控制小说情节的展开,并进而界定了小说女主人公莎菲的内心世界及其个人身份认同。丁玲凭借对人物内心世界,对当时时代精神,以及对人物个人情感世界和心理矛盾的深刻洞悉,创作出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正是通过对疾病及有病的身体这一独特文本的透彻把握,丁玲为我们展示了莎菲这位“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新女性的代表、“旧礼教的叛逆者”如何以其新思想与传统社会背景的交互反应,及其这种反应如何在女性内心情欲世界所激起的矛盾。① 因此,对莎菲身体疾病和内心情欲世界的描述正揭示了当时不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和较量。透过对身体疾病的文学解读,我们可以看到莎菲如何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内化和个人化的过程,以及传统社会的外在要求如何转化为莎菲内心世界的压抑与矛盾。由此,莎菲的主观世界、内在自我与女性身体统一了起来。身患疾病不仅是个人的生理问题,同时也是社会病态的症状,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社会关系的独特视角。
不受传统家庭的约束、摆脱婚姻的束缚、享受着自由的生活方式,在当今后现代社会或许是件极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由于机缘巧合,如果一个女性生活在传统社会,又无法遵从传统道德规范、无法担当传统女性角色,那么,她极有可能会面临着全面崩溃,不仅精神痛苦,肉体也会经受灾难,最终会陷入沮丧、忧郁和病痛,甚至会面临着死亡。当代美国著名作家及文艺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在其著作《疾病的隐喻》中指出:“任何形式对社会规范的背离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病态”。② 巧合的是,丁玲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主角莎菲同样经历了桑塔格所描写的背离传统社会及试图打破传统女性角色的过程。当莎菲试图遵守传统社会行为规范,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生活时,她就必须抛弃女性自我,面临着自我崩溃;而当她违反传统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时,她就必然陷入病态。
首先,莎菲的疾病与她所处的人文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故事一开始,莎菲就突出地感觉到冬天的寒冷和寂沉沉的四周;她不得不把自己用被子裹起来“关在屋子里”;③ 她要“面对四堵粉垩的墙”和“白垩的天花板”;她听到的是“难听的声音”;她从“洗脸台上的镜子”中看到的是自己扭曲了的形象。④ 因此,她精神上“烦恼”、“生气”、“焦躁”、“生嫌厌”;她肉体上感觉“头痛”并“咳嗽”。虽然莎菲没有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对一个“新女性”的压迫与摧残,但是莎菲反复地使用“屋子”、“墙壁”和“天花板”等压迫性形象,以及诸如“寒冷的冬天”和“刮风”等富有摧残意义的隐喻性字眼,清楚地表明了莎菲这一“五四新女性”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完全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生活,反而被一种无名的、综合的、外在的力量所控制。同时,医生还警告躺在病床上的莎菲,不要阅读、不要思考,这不仅限制了她的行动还控制了她的思想。她感觉到被动、压抑、窒息与幽闭;她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和自我;她不但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反而被一股无名的力量所限制、胁迫、操纵和伤害,而所有这些现在都可以用来界定女性在传统社会的角色。更有甚者,在寒冷的冬天能给她带来些许温暖的小火炉这时也熄灭了,这似乎是在表明,唯一能改变这寒冷状况的外部力量似乎也消失了。另外,这毫无变化的环境还给莎菲带来一种刻板、一种被命运事先裁定的感觉,而那些单调的声音则预示着短期内不会有任何变化的希望。
面对这些不利的环境因素,莎菲作了各种努力和挣扎试图摆脱她的不适、忧郁和焦虑,更重要的是要挣脱外部力量所强加于她的传统女性角色。莎菲的这些努力其实从一开始当她还处于那幽闭的小房间时就可发现。由于受疾病的限制,莎菲必须躺在病床上,但是她的行为却表明,她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作为一个病人的命运。她不仅在病床上辗转反侧,寻求最佳位置,释放病痛的折磨,她甚至试图通过寻找新的住所和搬家来改善她的环境及她的内心生活。她写道,“为了保存我的美梦,为了免除使我生活的力一天天减少,顶好是即刻上西山”。⑤ 她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期待着能够从一地到另一地,通过环境的某些改变带来内心精神世界的相应变化,以此来改善自己内心世界的矛盾状况。
在表明莎菲反叛外部势力的行为时,丁玲特别描写了莎菲的厌食症并产生了特殊的效果。莎菲拒绝饮食和不能饮食或许表示她的病痛和内心痛苦,但更可能是莎菲为了证明她尚有控制事物的能力而拒绝进食,表明她至少还能控制她生活中的某一部分。正由于她无法掌控自己,她才更需要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女性自我。在这种背景下,莎菲为了掌控自己的生活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应看作是获取个性独立的有益尝试。因此,掌控自己的身体与掌握外部世界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莎菲把热牛奶看作是“玩”,是“为免除烦恼的养气法子”具有积极意义,⑥ 可以看作是莎菲对外部世界的能动反应,是一种确证自己存在和身份的独特方法。
莎菲的疾病与女性情欲世界也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关于疾病与情欲之间的关系,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也有论及。她指出:肺病具有“情欲催化作用”,往往会使“情欲加剧”,并且能“产生巨大的情欲诱惑力”。⑦ 虽然桑塔格在书中并没有给出肺病与情欲之间在生理上内在必然的关系,但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故事却为桑塔格的这一论断提供了注脚。就莎菲来看,她不仅患有肺病,她还咳嗽、失眠、厌食;她渴望理解,渴望能有人与她做伴,并以此摆脱寂寞。为此,莎菲不惜与她的另一女友蕴姐发展一种特殊的关系。为了赢得蕴姐的爱抚,莎菲需要借助于“装病躺在床上”来达到目的。更有意思的是,当她们还在上海的时候,莎菲会一遍又一遍地央求蕴姐为她唱明代汤显祖的著名戏剧《牡丹亭》选段来驱除她的“哀戚”和“淡淡的凄凉”。⑧ 考虑到这出戏的剧情和内容,莎菲的这一要求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出戏的魅力在于女主人公杜丽娘为自己选择了伴侣,安排了理想的婚姻,战胜了压迫女性的社会规范,实现了自己的欲望,并最终嫁给了梦中情人柳梦梅。《牡丹亭》确实表现了女主人公杜丽娘被压抑、被禁制的生命渴望;有很明确的反抗压抑人性的封建意识的倾向。从表面上看,似乎并不存在明显的社会力量。然而,作品又确确实实写出了封建意识作为一种社会势力对杜丽娘的压抑,使人感到她在一张看不见的罗网中苦苦挣扎。通过这一典故的运用,丁玲通过作品表达了莎菲类似的憧憬。在听蕴姐演唱的过程中,莎菲似乎看到了其中的一个场景,在那里她似乎正享受着与杜丽娘一样的自由和甜美爱情。
在评论中国传统社会中这种典型的才子佳人模式发展起来的“知己”关系时,美国学者毛若姆·爱泼斯坦(Maram Epstein)指出,这种关系具有颠覆性,因为它破坏了儒家伦理中关于家庭的价值系统,而这一价值观向来要求个人履行家庭责任。然而同时,这一关系也可用来光大儒家思想中的其他因素,如真诚和诚实。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这一知己关系类似,莎菲与蕴姐的关系表明,她们敢于冲破强加于女性身上的社会羁绊去共同追求新的社会价值观。
如同《牡丹亭》中所表达的“女性主体地位”一样,莎菲日记也展现了一个典型的背离男性社会的女性文本。这一女性文本不仅赞美了女性之间的知己关系,更直截了当地表明这一事实,即莎菲“这一新女性不仅把男性当作欲望对象,更把女性纳入欲望范围”。⑨ 这一关系证明,莎菲和蕴姐之间都不是互为“能指”关系,互不隶属于对方,各自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她们都不再是对方的“他者”。相反,她们处于一种相互平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统治与驯服、训诫与听从的传统性别关系无处藏身。然而,这种关系为传统道德观所不容,因为它破坏了阴阳结构和儒家伦理中的婚姻结构,颠覆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说,莎菲和蕴姐的关系不仅跨越了传统性别界限,还打破了传统社会中的性别定义和价值观。
从写于12月24日的第一篇日记到写于第2年3月3号的最后一篇,莎菲不断地抱怨她脆弱的身体、她可叹的健康状况以及迫近的死亡。其中有好几次她病得非常严重,她的朋友不得不把她送进医院。其中有一次,她咳嗽得厉害以至咳出比酒还红的血来。在1月15日的日记里她写道,“我的病却越深了。什么也于我无益。死却不期然的会让我一想到便伤心。每次看见那克利大夫的脸色,我便想:是的,我懂得,你尽管说吧,是不是我已没希望了?”⑩
持续地对自己的疾病和健康担忧和抱怨对很多人来说或许可以减轻痛苦,但莎菲的抱怨却把她的病与她女性的情欲世界联系起来;进而,这情欲世界又与真实的自我联结在一起。这其中,莎菲作为肺病患者,她是如何看待她的疾病、如何理解她的情欲世界及自我等是问题的关键。以前,评论家在评述莎菲时大多集中于她在表达爱情和情欲时的直接性和主动性,但更具启迪意义的却是莎菲疾病与情欲之间较隐秘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深入探讨莎菲疾病的作用对我们理解她的情欲世界和自我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将会看到,莎菲如何意识到病痛对身体的影响,身体上的病痛如何用于建构矛盾的、但却是欲望着的自我。最终,莎菲只有通过真正了解她的情欲世界才能进而理解并得以建构一个真实的自我、真实的身份和真实的主观世界。
其实,莎菲的疾病与她的情欲世界之间的联系从日记一开始就可捕捉到。当她抱怨她被关在屋子里、面对着压抑的天花板以及四堵难以逾越的墙壁时,她一方面可能是在表达她的总体感觉,但另一方面她也可能是在描述她那受压抑的欲望情感。二者之间虽然不同但却有交叉。而她那疾病的症状,如咳嗽、失眠和厌食,都可以看作是对被压抑欲望的一种加了掩饰和伪装的表露。身体的虚弱和病痛并不能驱除欲望,也不能阻挡欲望的释放。相反,正如在与蕴姐的关系中那样,莎菲在利用她的疾病。莎菲与有着“欧洲中古骑士风度”的凌吉士之间的爱情关系不能不说与她的疾病也有相当的关系。然而这一关系却无意间暴露出莎菲内心世界更深层次的矛盾和冲突;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越密切,莎菲内心的矛盾也随之越尖锐。当她初次面对凌吉士时,她一方面作为一个新女性敢于表达自己的欲望,同时又受制于自己内心深处已内化了的中国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压抑自己的情感并陷入矛盾。这样,当莎菲遵循传统社会规范的时候,她就必须放弃自我;而当她公然蔑视传统时,她与传统社会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当莎菲发现凌吉士的传统本质时(要求他未来的妻子在家招待生意上的朋友;生养几个白胖儿子等),这一矛盾却又转化为莎菲的现代独立女性自我与凌吉士要求莎菲回归传统女性从属角色的冲突。
可奇怪的是,虽然莎菲对凌吉士的传统本质很失望,但她在情欲世界仍对凌吉士报以热望。她试图在情欲世界把传统与现代的分歧打碎,但却失败了。这表明,情欲世界是一个认识自我、确认自我的重要领地;思想上的差距并不能靠强烈的情欲来磨平。按照拉康的镜像理论,自我的发现和认同总是通过一个外在于自身之外的他者。拉康表示:我们寻找自我,而当我们找到他时,他却外在于我们;自我总是作为一个他者而存在。从莎菲在情欲世界的绝望挣扎可以看出,她对自我的认识并不是从自身得以印证的,反而是从与凌吉士的交往中发现的。她的自我不仅与凌吉士的传统人格相拒斥,而且在情欲世界也同样无法得以融合,反而通过情欲世界的隔膜最终发现一个真实的自我。茅盾先生在其所著《女作家丁玲》(1933)一文中也认为,“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11) 性爱上的矛盾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情感问题,而是一种关系、一种冲突。冲突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受压抑的真实的自我。处于性爱矛盾中的莎菲好像分裂成两个不同的莎菲,其中一个莎菲正在走向异化,而另一个莎菲却在走向自我。异化中的莎菲试图否认她真实的自我,走向自我的莎菲使自己看清内在自我的要求和本质。性爱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性爱拒绝任何虚假和冷漠。处于性爱矛盾中的莎菲透过自己女性的身体展示的却是一个复杂的文本。通过这一文本,莎菲得以清楚地看到她女性的身体如何与她女性的心灵相通;女性的身体又如何与她完整的自我相统一。确实,通过这一矛盾,莎菲更深入地认识了自己、了解了自己、也重新界定了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莎菲从凌吉士那儿所寻求的并不是性爱本身,而是从一个“他者”那里寻找一个与自我的新型关系,而这个与自我的关系却只能从一个与他者的关系中得到。这一关系毫无疑问为莎菲提供了一个独特机会使她能洞悉自己的主观世界、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认同。
莎菲的疾病不仅与内心矛盾有关,同时也与死亡欲望发生关系。当莎菲面对多重矛盾冲突时,她感觉到“药与病已毫无关系”;(12) 虽然有凌吉士陪她谈话但她的“病却越深了”。(13) 同时由于“一种纠缠”和“另一种纠缠”不断地折磨,(14) 莎菲发出“多无意义啊!倒不如早死了干净”的哀叹。(15) 为了摆脱这“缠缚”她“如是之久”的“痛苦”,为了“不会再感到这人生的麻烦”,(16) 为了“不愿再去细想那些纠纠葛葛的事”,(17) 更为了摆脱“比死还难忍的苦境”,(18) 莎菲想到了死,并“感到”“死的预兆”。(19) 其实,当莎菲“又开始痛饮”“为病而禁了的酒”的时候,(20) 她实际上选择了倾向于主动地寻求死亡,试图用肢体行动来改变思想意识,用毁灭自我的行为来调节失衡的矛盾心理。这种死亡欲望表明,精神自我与身体开始分离和异化;身体不再是自我的一部分,而是作为自我的敌人;莎菲内心精神上的矛盾与痛苦已到了必须毁灭自我的地步。这时的莎菲好像不再是她自己,她完全崩溃了,她好像受制于一个外在的“他者”的指使,完全受他者的操控;她内在思想和精神上的矛盾和冲突似乎正离开原有的精神居所,向一个具体的物质载体转移,而她的身体似乎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精神化身。这时,作为精神化身的身体,承载了她所有精神上的苦痛。当这一精神载体无法负担她所有精神压力时,莎菲一次次地想到死亡。对莎菲来说,死亡不仅是一个对身体物质存在的威胁,更是一个心理活动。死亡可以轻而易举地、迅速地驱除欲望和矛盾;同时,选择死亡也可以使莎菲最后一次控制自己、最后一次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由于这些便利和诱惑,莎菲于是就向承载精神矛盾与痛苦的物质载体,即她自己有病的身体发动了攻击,试图通过毁灭物质载体来消除无形的、精神上的矛盾与痛苦。
茅盾先生在评论这部小说的女主角莎菲时曾指出,“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背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21) 然而,莎菲的“绝叫”并不仅仅是发自声音上的,这一“绝叫”更是以其女性身体作为特殊文本表达出来的。这其中,莎菲的疾病及其有病的身体在表达其“创伤”时更是负有特殊的使命和意义。在论及疾病在文学作品中的内涵与意义的时候,苏珊·桑塔格也指出:疾病“表达了一种人们对事物不满的感觉”;(22)“疾病是通过身体说话的个人意志的表现,它是展示内心世界的语言,是自我表现的形式”。(23) 由于莎菲通过疾病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涵以及意识形态上的特性,疾病作为身体语言确实产生了一种文化效果。莎菲不仅重新发现了她真实的自我,还重新发现了她的身体和她的欲望世界以及身体和欲望世界所具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莎菲的死亡欲望只不过是一种希望,这个希望试图终结当时压迫在她身上的传统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建立在这个形态基础之上的旧的社会权力机构。
注释:
①(11)(21)参见茅盾《女作家丁玲》(1933),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25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⑦(22)(23)Susan Sontag,Illness as Metaphor.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8,p.56,13,73,44。
③④⑤⑥⑧⑩(12)(13)(14)(15)(16)(17)(18)(19)(20)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丁玲文集》第2卷第45、46、70、45、74、60、52、60、79、61、61、62、75、62、6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⑨Lydia H.Liu,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