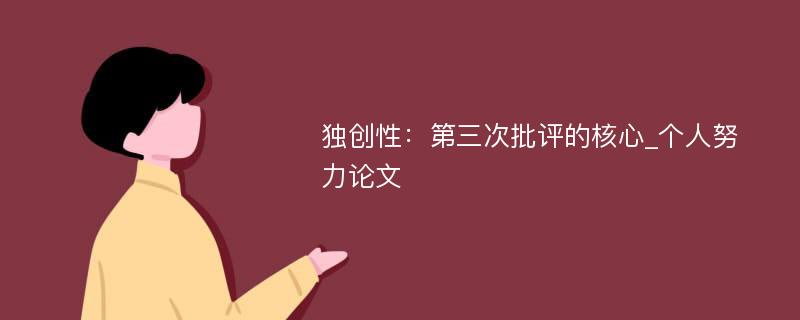
原创:第三种批评的核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三种论文,批评论文,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应该说,围绕“第三种批评”的讨论已达五年之久。她虽然不像人文精神问题争论得那样热闹,但她的个体性、多元性、超越中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姿态,以及在目的上产生中国当代学者自己的话语的努力,已经不同程度上地获得了学界和批评界较为广泛的认同,并开始在部分学者中间化为一种积极的实践。而这期间,以克林顿为首的一些西方首脑,开始在他们的国家尝试走一条既不同于老牌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右翼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并以其有目共睹的成效,无形中又强化了“第三种批评”的功能和可行性,而使得“‘第三种批评”具有了一种世界性背景。尽管“第三种批评”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并不以这种背景为依托(“第三种批评”在1995年提出伊始尚不具备这样的背景支撑),但对不少喜欢看西方人眼色行事的中国学者而言,这个背景却是管用的——它使得对“第三种批评”的一些怀疑者开始缄口不语,也使得一些原来缄口不语的学者开始若有所思;最重要的是:西方的“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的“第三种批评”的呼应,已经传达出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超越先前的二元对立模式,致力于一种思想原创性努力,已经成为中西方政治家和学人面对本国现实问题的一种不约而同的努力。
问题在于,由于“第三种批评”之“三”具有一种走向“个体化价值”立场之倾向,或者很容易被理解为多元中之一种,而“个体化价值”立场在内涵上又过于宽泛——它可以包涵个性、个人体验和阐释,也可以是指个体之创造,这就使得一些关于“第三种批评”的讨论,无论是支持者还是质疑者,均没有在“原创”的层面上来理解“个体”,也没有将“原创”作为“第三种批评”的最高境界来对待,自然就更不会将“个人阐释——个体创造”作为一个努力的过程。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个体化价值”立场与绝对的相对主义混同,“个体化价值”成为一种不需要进行创造性努力的天然存在。这就将“第三种批评”所讲的原创性之“三”(在区别既定知识中创造新的知识)与生存层面上的个人选择、感受、阐释的个人自由性之“三”混淆了,从而也混淆于80年代批评界提出的“我所批评的就是我”这一批评观。相对主义批评之所以容易受到批评界的质疑,相对主义批评之所以容易与“第三种批评”所讲的“个体”混同,天然性个体之所以不能区别批评的价值之高低,原因正在于在理论层面上,我们没有区分好生存层面上的“个人”与存在层面上的“个人”的不同及其二者的关系。而真正的多元,只能定位在存在层面上,不能定位在生存层面上。生存层面上的多元与杂乱无章并无区别,而存在层面上的多元则是不同思想的对话。生存层面上的多元以“个人感受”为基本单位,而存在层面上的多元则以“个体创造”为基本单位。从“个人感受”到“个体创造”,我称之为“本体性否定”的过程。“第三种批评”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利用“个人感受”转化为个体的思想之创造。应该说只要是一个健康的人,“个人感受”每个人都有,但“个体创造”之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也恰好证明了这个转化的艰难和必须。
二是“第三种批评”所讲的“个体化价值”,即便不在哲学层面上进行思想创造之努力,她也必须将此作为“价值悬置性”立场来对待,并以此为审美依托,对既定的思想和观念进行全方位的反思与批判——原创,在此是以审美形态保存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告别了20世纪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批判方式——以西方现成的思想为批评尺度,也产生了一种新的批判形态——对中西方思想同时予以批判。举例而言,如果说西方思想“重法不重人”,而中国传统思想又“重人不重法”,那么,对中西方思想的双重批判,则既要求我们摆脱两者的互为批判,也摆脱用“融汇”的方法来批判西方不重人、或批判中国不重法的互为批判的变异形态,而要求用新的思维方法来改造西方的“法”与中国的“人”之间的二元对立——西方的法不一定是中国现代需要的“法”,古代的人也不一定是中国现代所需要的“人”。这样,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人”与“法”孰轻孰重,而在于什么样的人与什么样的法以及进行什么样的组合。这就势必要改造中西方既定的人的观念和法的观念,从而也改造中西方既定的相互克服的人观念和法观念。这样的一种双重局限分析,才可以将中国当代现实问题的特殊性显现出来,也才可以将由这种特殊性所期盼的理论原创性显现出来。因此,“第三种批评”既不赞同以现成的西方思想来对中国当代现实发言,也不赞同在不触动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对既定思想理论的修补,而主张以基本原理的原创性努力为批评尺度,来发现既定理论的问题,暴露既定思想的问题。因此她可以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来概括“第三种批评”的价值立场。
三是“第三种批评”之“三”,不是在中西方之间不偏不倚,也不是中西方融汇,从而既与中国传统的“中庸”区别开来,也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性完美理想区别开来。实际上,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而言,“不偏不倚”与“中西融汇”在根柢上是相通的,它既表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只能在既定的二元关系之间徘徊,也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充满堕性的、非创造性价值取向的传统,正在当代延续。因为“不偏不倚”是以自我调节和自我克制为前提的——由于它不能脱离既定二元的规定,所以它不可能导致创造;“中西融汇”则是指对既定思想的组合,并受既定思想之阈限——至于“融汇”何以成为可能?“融汇”的方法是什么?“融汇”成什么?建立在愿望基础上的“融汇”,是无法告诉我们的。这就是“中庸”了几千年的古代文明,也没有自发地产生新的文明,“融汇”了一百年的中国当代文化,依然是文明之碎片的原因。究其根源,那是因为“中庸”状态和“融汇”状态与既定二元世界的“差异”,是靠“取长补短”的完美来显示与对立的二元之区别的。比如以“天人对立+天人合一”来显示与“天人对立”与“天人合一”的区别的。然而这没有缺陷的“天人对立+天人合一”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特的理论和思想,也不可能产生一个新的逻辑起点,更不可能具备实际的操作性。因为既是对立与冲突,就不可能合一,除非改变“天人对立”中人对天的优越性,也改变“天人合一”中人对天的依附性。而这样的一种改变,是不可能被“融汇”所能说明的。这样的一种改变,也就不是在二元“之间”,而是在二元“之外”了。
言下之意,这就自然涉及到“原创”的基本方法问题。可以说,“原创”之所以使不少学者心向往之而又敬而远之,其中关键点在于我们以往只能将创造诉诸于灵感或袭来的意识,归之于天才所为,而基本上没有对原创方法的理论探讨。即便有之,也是在“勤奋、刻苦、沉思、逆向思维”等大而无当的素质和技术层面上进行。实际上,这些技巧在依附性的治学方式中也可以存在。比如逆向思维,就是生存世界矛盾运动的“两极”性方式。而所有的矛盾运动,其实都并不必然地导向创造——所以当大家都向左,而你偏向右的时候,你还是在既定的现实中,而与原创无缘。这一点同样表现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不中即西”的虽然是逆向的、但仍然是依附性的生存方式中。因为在根本上,大自然的任何事物都在矛盾运动之中,当所有其它动物并没有在矛盾运动中产生创造性飞跃时,那么人的诞生在根本上就并不是矛盾运动的产物,更不是一个“逆向思维”可以解释的。人的生活中可以有矛盾运动,但人的创造则不依赖于矛盾运动——这个命题本身,就成为我们超越矛盾运动的一个原创性命题。
在《否定本体论》和《否定主义美学》两部书中,我将“原创”的方法大致归纳为“批判与创造的统一”,用来告别传统的脱离创造的批判和脱离批判的创造。而在这样一个“批判与创造的统一”中的“批判”,其含义是指“双重局限分析”,而“双重局限”的具体操作方式则是“W”图式。 “双重局限分析”为原创意义上的“批判”规定了具体的性质和内容,使得这种批判迥然区别于传统的“克服”、“取消”式否定和辩证否定。撇开原创性否定的存在性和个体性特质、“克服”、“取消”式否定和辩证否定的生存性和群体性特质不谈,二者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双重局限分析”不是以一种现成事物的长处来“批判”另一种现成事物的短处,而是用当代现实问题来暴露“天人对立”与“天人合一”的“共同局限”。这个局限必须是双方共同的“局限”,才是原创性批判所要谈的“局限”。而“克服”、“取消”式否定和辩证否定要么不谈“局限”问题,批判是以“替代”为鹄的(并不迫问替代的事物和被替代的事物是否有性质的差异,如中国的农民起义),要么其“局限”就是以一现成事物的长处来比较另一现成事物的短处所显现的“局限”(如中国人不重视逻辑思辩),而弥补了这样的局限也就意味着完美(但迄今为止,我们从未见过一种完美的文化,也从未见过既重视逻辑思辩又重视印象把握的文化)。这样一来,“双重局限分析”的“局限”观,就区别我们约定俗成的“局限”观,其操作方式体现为:对当代现实“问题”的把握,是进行“双重局限分析”的首要环节,但并不是任何问题都能成为原创性批判之问题。或者说,原创性批判之“问题”,不应该是用现成的理论所把握出的问题——比如我们不能说中国人不重视逻辑思辩是“问题”,也不能说中国人缺乏人对天的优越性征服或对象化意识(即“天人对立”)是“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只有在西方这样的理论对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有效性意义上,才能够成立。而文化的不可通约性注定中国人永远不可能成为西方人,也永远不可能成为重视逻辑思辨或有“天人对立”意识的民族,更不可能成为一个以西方理论为坐标的全球人。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在理论上很难论证中国人实现“天人合一”向“天人对立”转变的可能性、必然性,而且,20世纪“全盘西化”的新文化运动实践,也或以其价值破碎、或以其“小圈子性”证明其不可能。如此一来,我所说的问题,便必然是现有思想和理论把握不好的问题,即当代中国文化现实既不是缺乏“天人对立”的问题,也不是缺乏“天人合一”的问题,而是一个讲发展变化不能像西方那样的“进步性”变化、讲和谐也不能像中国传统那样的“非创造性”和谐之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中国的而且是当代的“特殊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反观出中国“天人合一”的“非创造性”局限,也可以反观出西方“天人对立”的“彼岸”对“此岸”的优越性、进步性局限,于是,建立一种同时能弥补这双重局限的“元理论”,才可真正谓之为“原创”。我所提出的“本体性否定”这一概念,即是内含批判与创造的统一性、但创造结果与批判对象又是平等、不同而并立的两个世界的新型创造观念与和谐观念。用这个观念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会产生人与自然(包括人与自身的自然性)是性质不同的两个世界的结论。这两个世界既不是进步的关系,也不是衰落的关系,历史不同论由此确立。更重要的是,人类理性产生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本体性否定”的关系中利用理性、利用灵感,由此和西方所有的非理性哲学构成区别,也与创造只能诉诸于灵感的传统创造观念与创造方法构成区别。
其次,如何从当代特殊问题对既有观念的批判中得出富有原创性的思想逻辑起点,便是我在《否定主义美学》中所说的“W ”图式所努力解决的问题。而“ W”图式便是“本体性否定”借助理性工具的一个尝试,虽然它不等于黑格尔认识论中所说的“正、反、合”。因为“正、反、合”或“否定之否定”是每一个有理性思维的人都会有的、也无时不有的认识性活动——就像每个人都有其本能一样。因为人的对象化意识产生之后,文化的承传性就会使它成为人的一种文化性本能。但正如人的对象化意识不等于人的对象化意识何以产生一样,人的“正、反、合”认识可以产生个性差异和认识差异,但却不一定能产生创造性成果——其原因就在于创造性和认识性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W ”图式也由此与“否定之否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理性化活动。准确地说,“W”图式是一种创造性理性化活动,并分为两个“V”字型批判程序。第一个“V” 字型批判程序主要以我们对当代现实问题的感受和问题发现,来剥离出既定思想的局限性。这个否定环节要求我们悬置既定观念对我们把握现实问题的制约与影响,与此同时,直面现实感受内容的特殊性,分析出既定观念的局限性。这个时候,我们对现实的特殊的感受性内容,就以对既定观念局限性的言说反衬出来。比如,我们对当前人与天的感受性内容,就可以以“天人合一”不重视创造,“天人对立”又不重视人与天的平衡性关系体现出来。但这个时候,具有原创性的思想还处在审美性的孕育状态,我们还不清楚这种既有创造性、又有平衡性的天人关系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进入第二个“V” 字型批判程序。这个否定程序要做的工作是:以既重视创造、又重视平衡为我们对当代思想的感受性内容,再次反观“天人合一”中的“平衡”与“天人对立”中的“冲突”之“否定”观念的局限,以此发现出中国“天”对“人”的“克服”和西方“人”对“天”的“克服”这一克服性否定观念之局限,从而显现出“非克服性”否定观念、创造观念之萌芽。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否定观念和由这种否定观念支撑的“天人”关系,只能是不同、平等、并立的关系。“否定”,只不过是不满足于既定世界、通过再造一个与否定对象性质不同的世界来完成自身的意思罢了。这样,今天的天人关系,就应该是“天人分立”的意思了。这个意思,虽然不能说就是“原创”,但无疑体现出“原创”的某种努力。这种努力,也就是“第三种批评”最终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