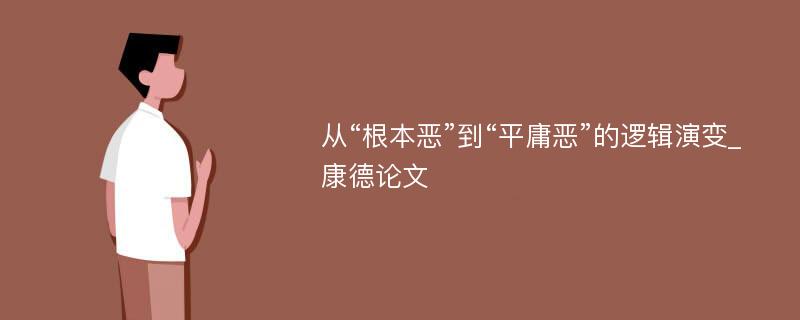
“根本恶”到“平庸的恶”的逻辑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庸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阿伦特在对政治伦理探讨的过程中,面对极权政体内在自反性产生出的“恶”进行彻底的批判,完成了由善之必然至恶之实然的政治哲学理论转向。需要指出的是,阿伦特对“恶”的彻底批判不是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完成的,“根本恶”中有诸多的逻辑冲突和不完善之处,直至《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平庸的恶”概念的提出,才真正构建起对“恶”的批判体系。 一、作为恶体系起点的恶——“根本恶” 从纯理论的角度上讲,讨论“根本恶”和“平庸的恶”不能脱离阿伦特政治哲学的范畴,脱离了此范畴,如同脱离了水研究鱼儿是怎样游泳的一样不科学。国内有些学者对我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道德冷漠现象,诸如看病不交钱医生不给看等现象,归之于“平庸的恶”。这样拿着阿伦特的笔到处圈圈点点,有过度诠释之嫌,作者只是拿着现成的“平庸的恶”解释社会现实。但是这种没有经过自身理性思辨的理论完成态,还没有对自身涌现其意义,并且,“无论是‘根本恶’还是‘平庸的恶’,都是极权主义体制制造的‘政治的恶’”。(刘英)所以,我们应该回到文本之中,以文本意图为出发点,澄明“恶”的生根之基和“恶”理论的辩证体系。阿伦特对“恶”的考察肇始于对极权主义的考察,提出了“根本恶”的观点。所谓“根本恶”是极权主义极端的政治之恶,是过于膨胀的国家暴力机器支配着社会秩序,个人的自我空间被挤压到为零的状态,人的自由主体性被压榨到人之外,国家机器实现了对人的绝对统治,也实现了政治对人的本质的吞噬。但是这绝不是精神意义上的人之非人,而是在现实意义上将人归之于政治机器的原材料,极权主义在自我运作的过程中绞碎人的肉体。极权主义是阿伦特对存在主义最恐怖状态的描述,远远超越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作为无声客体的“畏”“烦”等感性化概念。极权主义摧毁了人“畏”和“烦”的现实载体,人之存在残酷到了无处存在的程度。极权主义实现了对人类社会的全方位浸透,人的信仰、公共空间、甚至是日常生活也被填满国家意识形态,秘密警察如影随形,恐惧四面逼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极权主义统治之下,没有社会,没有人,只有国家,这是最为可怖的国家组织形式,人成了不必要的存在,即“极权主义尝试将人变成多余”。(阿伦特,2008年,第570页)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说道:“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不是改变外部世界,或者社会的革命性演变,而是改变人性。”(同上,第572页)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人性成了虚无性的存在,这正是“根本恶”的核心机制。对“人性的改变”的批判,比对极权主义血雨腥风的野蛮杀戮的控诉,更加深入地触及到极权主义的根本,因为杀戮者还可能有残留的人性,这一点残留的人性还有化魔为佛的希望。但是人性之改变也就意味着人和人性的绝缘,这种“改变”具有不可逆性,恶人一旦为恶,只能紧紧跟随极权主义飞旋的步伐而不能止歇。所以,极权主义的本质力量是把人性推到了道德悬崖的边上,人性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当口。在恶为实在本体的世界中,整部人类文明史的人性根基被抽拔掉。对人性而言,历史上任何一种专制主义都成了仁慈的化身,不仅作为历史的人被扼杀掉了,作为自由性而存在的人、作为特殊人类之我的个体性和作为人类大我的群体性更被窒息在此岸世界之中。由于人性被瓦解,世界成了无标准可以选择的肆意游离态,人心中的魔鬼成了肉体的主人,破坏一切成了极权主义的唯一信念。正是在这种以恐怖主义为驱动力的政治机制的渲染之下,粗暴地曲解尼采,把“重估一切价值”(尼采,第91页)从哲学语境中抽拔出来,断章取义地作为破坏的主导性原则,无所忌惮地破坏一切。阿伦特在二战结束以后,反思这段疯狂史的时候,指出有些人犯的罪恶远远超越了历史中的任何暴君,功利主义原则不能解释他们的行径,他们的疯狂和残暴在历史和思想史之外,“人们不再能够根据自我利益、贪婪、渴望、怨恨、对权力的欲望、怯懦等恶的动机来理解和解释;因此,愤怒不能报复它,爱不能容忍它,友谊不能宽恕它”。(阿伦特,2008年,第572页)所以,所谓的“根本恶”是对这种撑破历史之网的最新最残暴的恶劣行径所打上的理论补丁,它在一切都不能产生之处产生。 但是“根本恶”不是对人性灭绝的纳粹残暴行径的形象概括,它本身不是恶人为恶的手段和目的,只是作为没有理论批判点的应急之独创。对“根本恶”概念的提出,阿伦特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她是想用现象学还原极权主义,于是追问极权主义何以产生、探究政治伦理学的根源。但是她面对这种历史空前的用鲜血作为水泥垒砌骨头而成的极权主义制度,根本没有办法找到可以被理解的政治伦理前提,因为政治伦理的前提是人的动机,但是人的动机和人性是作为同一场域不可分割,极权主义又灭绝人性,于是政治伦理在极权主义成为不可能。面对这种空场,阿伦特只是摘取了康德“根本恶”概念的形式,没有取其内容,因为她觉得极权主义之恶超出了哲学史理解的范畴,所以“根本恶”在阿伦特那里只是表象深渊性的词汇,以此作为极权主义的政治伦理之基。由于没有历史样本,也没有哲学史的支持,阿伦特只能苦苦在“没有扶手的思想”中独立前行。“极权主义”就是悬空打转的封闭圆圈。所以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出来了“平庸的恶”作为对“恶”理论的修补。至此,阿伦特极权主义的政治伦理学批判体系才算完成。 二、“根本恶”的封闭逻辑和自我否定之必要 “根本恶”上没有人类动机的确切来源,下没有人民大众心理内在的传导机制——即几个极权主义者如何引导了极权主义狂潮,甚至“阿伦特没有涉及到道德与罪恶的责任问题,直接否定了人类的道德承担问题,也就同时否定了道德存在的可能”。(王义、罗玲玲)换言之,这种形态的“恶”甚至丧失了自身的对立面,这是绝对抽象化之物。所以,“根本恶”也就没有突破黑格尔封闭逻辑的诅咒,它成了悬空的抽象存在物,单从极权主义的语境本身,“根本恶”就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根本恶”概念的哲学无根性。任何哲学新概念的创新都要经受哲学的反驳,但是单单“根本恶”的概念是经不住哲学史的反问的。我们都知道,阿伦特的“根本恶”的概念借自于康德,虽然内涵和康德的“根本恶”有天壤之别,但是康德哲学是可以作为阿伦特政治哲学的镜像映现,在康德对“根本恶”的辩证追问中我们可以察觉到阿伦特的理论不足之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是康德的后期之作,在“根本恶”出场以前,康德考察了人的与生俱来的两种能力,即按照道德之善律令行动的能力,即“意志”(Wille);既可以遵循道德律令行动也可以违背道德律令而行动的中性行动能力,即“任意”(Willkür)。所谓“根本恶”,简而言之,就是“倾向”(Willkür)由于在欲望的支配下选择了朝向恶的一方,破坏了人的道德本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康德的“根本恶”概念似乎没有阿伦特的“根本恶”那么强的理论映现现实的能力。但是康德的“根本恶”本意不是为了用抽象概念修饰现实,不是描述现实世界中种种惨无人道的行为,而是为了给社会现实的恶现象找到道德哲学的伦理依据,即“根本恶”是人之为恶的终极原因。阿伦特也模仿康德将纳粹的恶性归结为自己创生的“根本恶”,但是作为归结终点的“根本恶”由于没有哲学根基,是悬空的。所以我们再考察一下康德的“根本恶”的哲学之根据,让阿伦特“根本恶”的哲学无根之处自行显现。 康德的“根本恶”是建构在三大批判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建构在以纯粹理性批判为前提的实践理性批判之上,即纯粹理性为基,实践理性为实,“根本恶”为果。康德的“根本恶”在实践理性批判那里沿袭了道德依据,在纯粹理性批判那里沿袭了哲学认识论依据,所以康德的“根本恶”的伦理学依据和哲学依据都非常厚重。简而言之,建构在纯粹理性批判认识论基础之上的实践理性批判道德论是康德“根本恶”的必要前提。所以康德的“根本恶”也就表现出来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的先天性原则、开放性原则和自由性原则。“根本恶”的先天性原则主要是为了反驳伦理经验主义,“为了称一个人是恶的,必须能够从一些、甚至从惟一的一个有意为恶的行动出发,以先天的方式推论出一个作为基础的恶的准则”。(康德,第3页)其开放性原则主要体现为书中的道德进步观:恶的行为是受先天原则的任意(Willkür)所驱使,但是任意(Willkür)本身还有一种向善的可能,并且人的先天原则中还有按照道德之善律令行动的能力,即意志(Wille),道德之善命令是和人的概念交融在一起的。所以,善在道德中表现得更有力量,善正是打破恶的诅咒走向开放和自由的力量。其自由原则主要体现在实现恶的必要前提是人的自由行动和自由选择,但是作为道德载体的人必须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由此可以看出,康德“根本恶”的三大原则是和人性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阿伦特的“根本恶”却自断了和人性之间的关系,她的“根本恶”表现出了人性的空场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极权主义是对传统政治形态的断裂还可以成立,那么“根本恶”却是断裂思维的泛化,因为其所指的单调性和采取粗糙手法切断了和哲学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对现实之爱之深切的理论断根。 第二,“根本恶”的逻辑滞空性。阿伦特的“根本恶”内在的逻辑冲突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没有化解,并且阿伦特本人也没有给“根本恶”太多的内涵,其逻辑布展仅限于政体之恶的内部,“根本恶”在书中只是一个静止的范畴,逻辑被非理性的修辞滞空了。比较而言,康德“根本恶”内部的诸多矛盾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辩证为一种深刻的理论交织。比如自由原则和先验原则的冲突,“人生来是恶的”这个先天本性和“恶是人的自由选择”之间的冲突。如果说人生而为恶,恶的行为就不可能是自由原则运作的结果。康德是通过延展了概念的纵深维度来实现这一矛盾的统一,即他先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为(遵从客观的道德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行于一切被觉察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同上)而“人生来是恶的”则是因为“人,而且是一般地作为人,包含着采纳善的准则或者采纳恶的(违背法则的)准则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无法探究的)原初根据”。(同上,第4页)从表面上看恶的自由原则和先验原则有着不可调和的悖论,但是在理论纵深应用到应有的深度上,我们会发现二者其实是契合的,即作为自由原则的恶是主观性依据,而作为先天原则的恶是源始性依据。再如自由性原则和开放性原则的冲突,善恶是人的自由选择。康德又如何确保道德一定是向善的力量大于为恶的力量呢?作为人的自由选择的善恶只是自然层面的善恶而不是道德层面的善恶,康德认为人只有在信仰的帮助下,即“一种我们所无法探究的更高的援助”(康德,第33页)之下才能确保善的绝对优先能力。由于康德的难题是时代性的难题,所以我们先抛开作为信仰层面的自在之物不谈,康德毕竟借助于信仰的力量化解了“根本恶”内在的逻辑冲突。所以从康德“根本恶”的交织逻辑看来,阿伦特的“根本恶”没有向哲学打开大门,没有精密的辩证逻辑,也没有向现实和未来开放,根本恶只是根本恶的本身,所以“根本恶”只能是悬空的抽象封闭物。 第三,“根本恶”陷入存在主义抽象人本的悬空性。理解阿伦特和她的哲学母体——存在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是理解阿伦特“根本恶”为何封闭的关键所在。学术界大多认为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难以归类,从存在主义出发却不从属于任何一种主义。但是我们在细细阅读阿伦特的文本之后,不难发现阿伦特的前期思想内核依旧是存在主义无处立身的现世焦虑感和为突破这种焦虑感所作的努力。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逻辑在阿伦特的文本中作为隐形的推动力弥散在字里行间,这种近距离的“他者”渲染是不能忽略的。她在政治哲学领域里的建树,也是基于一种存在主义之上的“被抛”: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是基于对时代“被抛”之境的历史考量,归结为“根本恶”也类似于海德格尔的“畏”“烦”和萨特的“焦虑”等主体情绪;她的“劳动”“工作”和“行动”等概念是人类无法逃脱的宿命,人因生理需求而劳动(Labor),因服从资本的统摄力而工作(Work),因人“被自由”而行动(Action)。尤其是考察极权主义的起源时提出的“根本恶”的概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海德格尔“畏”“烦”“死”的补充,主体“被抛”的主观体验中注入了“恶”的冷漠补充,这是一种“存在论层面上的政治问题”。(见王寅丽)所以,“根本恶”依然蕴含着“存在者”的论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根本恶”的不足之处正是存在主义的失足之处,因为这种悬空的人本主义的控诉是回答不了纳粹的反人类逻辑,充其量只能算是形而上学自反性的深刻冷峻。并且,由于存在主义用理性张扬非理性成分的方法论浸染,阿伦特的论述也是借助于理性表达非理性的成分居多。这样的后果就是“忽略人即使活在一个邪恶的集权暴力的统治之下,发生邪恶的过程中,个人仍然有不能逃避的责任问题”。(陈瑶华) 三、恶体系的完成——“平庸的恶”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是阿伦特的后期之作,《极权主义的起源》提出了“根本恶”(Radical evil)的概念,1968年又提出了“平庸的恶”(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学术界对此的看法颇有争议,有些学者认为道德名词“恶”的形容词“根本”(Radical)和“平庸”(Banality)是完全对立的,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是源和流的关系。在众多作者之中,见解颇为独到的是徐贲。他认为“平庸的恶”是在追问“专制制度下的个人负有怎样的道德责任”。(见徐贲)但是他所作的工作,还是在于区分极权主义的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和道德责任,没有重视“恶”体系中的内在逻辑发展。所以我们还是回到阿伦特的文本中,在深入其文本深层次的语境之后,剖析出来的内在逻辑是:人性被异化为“无思想”,这样上可以连接“根本恶”的人性动机起源,下可以接上“平庸的恶”作为极权主义运转的大众机制,最终生成“恶”的政治伦理批判的辩证逻辑。 第一,从“根本恶”到“平庸的恶”的理论中转站——“无思想”。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对劳动、工作和行动的考察,是为了明晰“我们正在做什么”。(阿伦特,2009年,前言,第5页)而行动的时代背景却是“无思想”,“无思想——不顾一切地莽撞或无助地困惑或一遍遍重复已变得琐屑和空洞的‘真理’——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同上,前言,第4-5页)正是对作为时代特征的“无思想”的批判,建构起以“劳动”“工作”和“行动”为理论轴心的行动哲学。在这本书中,阿伦特通过对马克思的研究和批判回归了理性,也接上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所以《人的境况》是阿伦特的学术转折点。在这本书中,阿伦特主要考察了人之为人的境况,即对人在世条件的深刻探析。在这里,阿伦特指出了人的境况异质于人的本性的地方:“人的境况不等于人的本性,与人的境况相对应的所有人类活动和能力的总和,都不构成类似于人的本性的东西。”(阿伦特,2009年,第3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阿伦特在这里已经大大拓展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关于“人性生死攸关”和“人是多余”的单一论调,用作为具体个人的“人的境况”来弥补极权主义中作为整体性的人性的被迫空场。极权主义妄图消灭人的主体性、自由性和道德性,单个的人处在极权主义的境况之下是消极坐以待毙,还是积极奋起反抗呢?这在于人的自我的判断和选择,阿伦特所谓的“积极生活投入于其中的世界是由人的活动所造成的物组成的”(同上),意指人有反抗“根本恶”的行动维度,而那些没有反抗的人,正是构成“无思想”这一时代特征的主要力量。“无思想”作为“根本恶”和“平庸的恶”的中转站,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这里已经完成了理论上的承上。怎么启下的呢?简单说来,“无思想”正是造成“平庸的恶”的罪魁祸首,但是放在当时的思想史背景之下,“无思想”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 第二,“无思想”的滥觞导致“平庸的恶”。“无思想”和“平庸的恶”有什么关系呢?阿伦特在二者之间画上了等号:“无思想就是平庸(banality),其特征是站在别人立场上的思考能力不充分。”(孙传钊)艾希曼由于“无思想”,盲目地执行纳粹政府的运输命令,200万生灵涂炭和他有直接关系。艾希曼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完全是一个空心人的状态,只会陈述一些单调的陈词滥调,在他身上甚至找不到对犹太民族的恨意,他本人不带任何感情而行动,只是单纯地关心自己的晋升,表现出典型的“平庸的恶”的特征。艾希曼以上级命令为至善,命令是他行动的唯一源动力。如果说功利逻辑解释不了“根本恶”,但是“平庸的恶”却落入了功利逻辑的彀中。这是一个为了功利把灵魂出卖给地狱众魔(恶体系)的人。单纯的晋升之心让艾希曼没有距离审视和反思命令的合理性,狭隘的功利自我也不会让他从别人的立场上来思考自己的无思想之恶果。平庸者的无思想另一个特征就是自我语言被抽空,所言都是作为恶魔“他者”浸透的自我保全式话语,谎言和单调重复渗透到整个话语系统之中,所以在法庭上,众人难以和艾希曼进行沟通。在恶的运转不息的链条中,他没有任何是非善恶的概念,道德伦理被抽空。并且他本身没有任何作恶的动机,只是默然遵从运转的恶的体系来行动,如果他不是纳粹的鹰爪,历史是不会记住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明显特征的人物。同时,艾希曼无任何道德愧疚的心安理得让阿伦特感到吃惊,但这正是让阿伦特感到恐怖的地方:不是只有穷凶极恶的恶魔可以毁灭世界,以艾希曼为代表的庸碌之人同样可以毁灭世界,并且犯下了如此滔天大罪,艾希曼本人还表现得心安理得。正是这群具有“平庸的恶”的空心人,极权主义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所以,只有通过“平庸的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根本恶”,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才能彻底完成。 第三,“平庸的恶”对于“根本恶”的扬弃。在前文中,通过康德哲学之镜的审视,阿伦特的“根本恶”表现出哲学无根性、逻辑滞空性和抽象人本的悬空性。“根本恶”的失足之处不在于批判了极权主义制度,而在于仅仅批判了极权主义制度。阿伦特仅仅批判了极权主义大规模的洗脑式宣传方式,但是没有揭示出极权主义宣传的受体,即产生大量的“无思想”具有“平庸的恶”的承载者。所以“根本恶”不仅没有向作为未来社会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敞开,也没有彻底批判极权主义本身。如果没有艾希曼这样的平庸顺从者,何来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根本恶”只有和“无思想”“平庸的恶”三位一体化之后才能完成对极权主义的彻底的批判。这样不仅有了高高在上的“根本恶”,也有了具有“无思想”的“平庸的恶”对“根本恶”的默然支撑者。在现代资本主义时期,“根本恶”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作为“根本恶”的逻辑外化,“平庸的恶”正是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利器,对当代社会伦理危机的批判是应有之义。需要指出的是,在“无思想”中介的阶段,马克思成了阿伦特逻辑转向的学术资源,虽然阿伦特也批判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考察,尤其是对作为统治和支配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存在物的资本批判影响了阿伦特,正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写的“一”——资本的彻底批判中,给了阿伦特突破“根本恶”这一封闭怪圈以充分的学术预备。 阿伦特是怎样扬弃“根本恶”的呢?她说道:“恶绝不是根本的东西,只是一种单纯的极端的东西,并不具有恶魔那种很深的维度,这就是我真正的观点。”(阿伦特等,第166页)阿伦特本人也意识到了“根本恶”的理论缺陷,因为“根本恶”的前提是人性的断层,恶优先于善而存在。通过在《人的境况》中对公共领域的考察,她对于“劳动”“工作”和“行动”虽然还有存在主义的消极阴影,但是从理论的宏观气质上她认为人类还有希望。经此转折,善被阿伦特提高到第一性的高度,这正是“平庸的恶”的深刻内涵。所以,她后来这样阐述“平庸的恶”和“无思想”之间的关系以扬弃“根本恶”:“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况且,涉及恶的瞬间,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带来思考的挫折,这就是‘恶的平庸’。”(同上) 需要指出的是,“平庸的恶”的提出只是标志着阿伦特作为政治伦理批判的恶体系的完成,但不是阿伦特本人思想的终结。“平庸的恶”也是作为中介性的存在,是阿伦特从政治转向哲学的关节点,其中也涉及到如何拒绝“无思想”。她在现代社会中,给帕斯卡尔“人是一株能思想的苇草”立威,指出正是人的思想才是黑暗中永不熄灭的灯火:“只有人致力于思考,而不是受思想囚禁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思想是一种新式武器。”(Arendt,p.83)以个人的“思想”和“判断”来抵制专制,拒绝体制对人的同一化塑造,坚持自我的多元性,在“沉思”后的“行动”中确立人的本质,这正是阿伦特从政治领域转向哲学领域的起点。标签:康德论文; 人的境况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极权主义的起源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阿伦特论文; 人性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