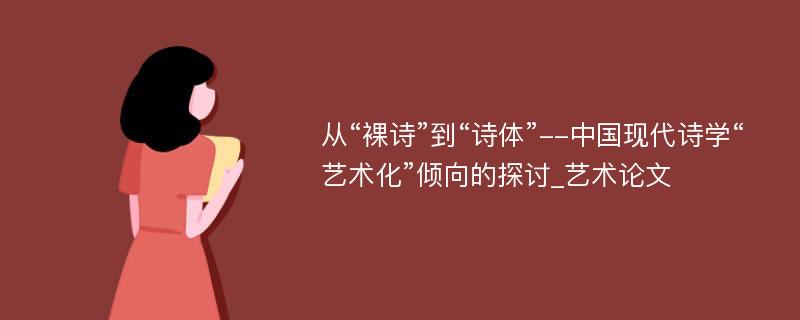
从“裸体的诗”到构造“诗的躯壳”——中国现代诗学中的“艺术化”倾向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躯壳论文,的诗论文,中国论文,倾向论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0)05-0058-06
一、早期白话—自由诗及诗学主张的“非艺术化”倾向——现代诗学艺术化倾向的发生背景
中国现代白话—自由诗创作是伴随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发展起来的,它实现了诗歌形式的大解放,为中国诗歌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但就在白话—自由诗创作日渐鼎盛之际,其弊端也日益呈现,突出表现为概念化、理念化、过于强调写实和混淆诗与非诗的差别等。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白话—自由诗的“非艺术化”流弊。鉴于学术界从创作方面探讨这一问题的较多,本文侧重于从诗学理论方面来分析。
中国现代新诗创作从“形式大解放”开始,新诗人们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厌恶形式的倾向。文学革命的首倡者胡适认为文胜质是旧体诗词的主要缺陷:“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理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1]这也是新诗创作所要避免的。郭沫若则视形式为诗人的镣铐,在形式方面主张绝对的自由与绝端的自主。[2](P213)另一位新诗人俞平伯也以极端厌恶的语气谈到形式:“我最讨厌的是形式。不但那些音律句法底老谱,叫人皱眉不消说了;就是那些学问上的偶像,所谓‘道气’,当做诗的时候,也恨不得远远请他们去。”[3](P614)宗白华在一封信中也颇为坦率地承认:“……因我从小就厌恶形式方面的艺术主张,明知形式的重要,但总不注意到他。”[4](P240)新诗人们厌弃的“形式”主要是指诗歌创作中的艺术规范与技巧,对形式的排斥已成为初期白话诗坛的一种普遍性倾向。
早期白话诗学有意识排斥“形式化”因素(这里主要是指格律、声韵、节奏等与诗的形式密切相关的因素)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早期白话诗人以“情感”为新诗的重心,并且标举“自然”作为评价诗歌的主要标准。
中国诗歌自古就有“诗言志”和“诗缘情”的传统,《诗大序》中的一段话被经常引用:“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蹉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段话旨在说明诗起源于诗人内心的情感冲动,情感在诗的形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性发现、情感解放的新思潮背景下,新诗人们高度认同并发展了这个观点。胡适认为情感是文学的灵魂,文学如果没有情感就成了木偶和行尸走肉。[1]康白情把诗看做是主情的文学,诗人则是宇宙的情人。[5]创造社作家对情感的强调更是无以复加。郭沫若把直觉喻为细胞核、情绪喻为诗的原形质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成仿吾则把诗人视为感情的宠儿,并且把情感和理智对立起来。“文学是直诉于我们的情感,而不是刺激我们的理智的创造,文艺的观赏是感情与感情的融合,而不是理智与理智的折冲。”[6]可见,在诗的创作中突出情感的重要性是新诗人们的共识。
虽然诗的抒情性并不是新诗人的发明,但早期新诗人对情感的看法与传统的“诗言志”和“诗缘情”观念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新诗人更强调情感的原生态与自发性,排斥有意识地对外在形式的追求。他们认为情感的直白宣泄和倾诉本身就是诗,形式自然孕含其中。郭沫若就多次阐述他的“体相如一”的一元论诗歌观念。在他看来,直觉与想像是诗的本体,只要把这些写出来,便“体相兼备”,无需在形式上刻意求工。只要是纯真自然的抒情文字,本身就是优美的形式:“然于自然流露之中,也自有他自然的谐乐,自然的画意存在,因为情绪本身是具有音乐与绘画二作用故。情绪的吕律,情绪的色彩便是诗。诗的文字便是情绪自身的表现(不是用人力去表示情绪的)。我看要到这体相如一的境地时,才有真诗好诗出现。”[2](P213)在评雪莱的诗时,他再次谈到:“……体相不可分——诗的一元论的根本精神确实是亘古不变”[2](P212)。郭沫若认为有“体”自然会有“相”,因此不必着意于“相”,这是他早期诗学主张的一个核心。由以情为主走向对形式规范的有意识抵制对郭沫若来说是一种必然:“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为诗。”[2](P211)在他看来,外在形态的追求纯粹是多余的。需要说明的是,郭沫若并未取消“形式”,这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在他为诗开创的公式中,“形式”也占一席之地:
诗=(直觉+情调+想像)+适当的文字
他所否认的,是那种把某一特殊的形式如格律视为诗的普遍形式的诗学观念,而强调“形式”更多地是内在性而非外在性因素。他提出了“内在韵律”(Zntrinsic Phythm,或无形律)的见解,这种内在律和注意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长短、宫商徵羽的外在律不同,它指的是顺应情绪的自然消涨而形成的音律,这种音律绝少带有人工的因素:“诗应该是纯粹的内在律,表示它的工具用外在律也可,便不用外在律,也正是裸体的美人。”[2](P201)“内在律”和“体相如一”论的实质是相同的,都反映了郭沫若强调“自然”而排斥有意识的人工雕琢的见解。
郭沫若的这种观念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新诗元老之一的俞平伯也认为只要有了真纯自然的动机,自会有体相兼备的诗:“我认为诗律既不难,而且有很精严的规则——自然的法则——存在,但是我们却不要管它,不要有意地遵守它,只乘着‘兴会’做我们底诗,它自会如形影的来符合我们。换句话说,人底盛兴和谐律底盛兴是相伴着而同源的,我们不愁有好诗而没有好的调子啊!”[7]总之,在新诗人们看来,形式只是附着于感情之上的伴生物,有意识地追求形式的完美是不足取的。
只要有真挚的情感,便不需艺术的修饰的美,这种“非诗化”亦即“非艺术化”倾向占据了初期白话诗坛,有人形象化地将这种重质轻文的倾向比作裸体美人:“新诗是西洋的裸体美人,旧诗多数是上妆登台的梅兰芳。”[8](P234)对此,新诗人们不以为忤而欣然接受。俞平伯也曾说过:没有了装饰,美人仍能独立存在,故最可贵的就是这种裸体的美。[9](P632)郭沫若更是多次表达他的“裸体的诗”的观念:“我相信有裸体的诗,便是不借重于音乐的韵语,而直抒情绪中的观念之推移,这便是所谓散文诗。这儿虽没有一定的外形的韵律,但在自体是有节奏的。就譬如一张裸体画的美人,她虽然没有种种装饰的美,但自己的肉体本身是美的”[2](P331)。对“裸体美”的欣赏形象化地反映了新诗人们重内在而轻形式的艺术倾向。
由于过分强调自由,白话—自由诗的弊端和白话—自由诗学的偏颇日益暴露,纠正这种倾向的片面性,重新重视诗的艺术美,也就是迟早要发生的事。
二、新诗“艺术化”观念的萌芽与自觉——对白话—自由诗学的补充与修正
当然,白话—自由诗学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并不是绝对没有涉及诗的艺术形式问题,这是因为诗歌毕竟是一种精炼的艺术,完全脱离形式来谈诗是不可能的。一些草创期的新诗人在其充满自由主义论调的文章中对形式美问题也偶有涉及。在这方面宗白华、康白情以及由汉较具代表性。宗白华为诗下的定义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底情绪中的意境。”[10]这与胡适论诗以“表情表得好,达意达得好”为标准有着明显的不同。宗白华对由郭沫若提出而为新诗人们广泛认同的“诗是‘写’的不是‘做’的”的观点有着更深一层的理解。他认为要达到“能写出”的境地,要经过必要的诗艺训练。他刻意强调这一点,因此主张新诗应该吸收音乐、绘画以及建筑雕刻等技艺来提高其艺术性。关于形式的见解,他和郭沫若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在宗白华看来,“形”并非是如郭沫若所说的随情感自然流露而体相兼备所具有的,也并非是情感赤裸表达的伴生物。“形”更多地产生于诗的艺术化过程中,这同时也是提高审美性的过程。他强调:“我们对于诗,要使他的‘形’能得到图画的形式的美,使诗的‘质’(情绪思想)能养成音乐式的情调。”[10]“形”不仅不是质的附属品,而且对“质”还是一种凝炼和强化。正因如此,宗白华才一方面注意到诗人的人格修养,一方面又格外强调“要作诗的艺术的训练,写出自然优美的音节,协合适当的词句”[10]。在他看来,“形”并非是可有可无的美人的化妆或简单的打扮整理,而是构成诗的有机体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宗白华和郭沫若等人的不同之处。在批评实践方面,宗白华也把“形”作为衡量诗歌艺术水准高低的一个重要尺度。他善意地指出郭沫若诗在形式方面的不足:“……不过我觉得你的诗,意境都无可议,就是形式方面还要注意。你诗形式的美同康白情的正相反,他的诗,形式构造方面嫌过复杂,使人读了有点麻烦,你的诗又嫌简单固定,还欠点流动曲折……”[4](P240)委婉地对郭诗不注意形式而造成的诗形单调、缺乏弹性提出了批评。由于宗白华基本上还是赞同胡适、郭沫若以精神实质为新诗内核的主张,他没有对自己的艺术化见解进行过多的强调,也未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主张。
另一位新诗人康白情在一定程度上也谈到了诗的艺术化问题。他认为音韵、平仄等形式因素是有一定作用的:“音呀,韵呀,平仄呀,清浊呀,有一端在里面,都可以使作品愈增其美,不过总须听其自然,让妙手偶得之罢了。”[5]这表明他对诗的外形的关注是以“自然”为前提的。
田汉的见解和上述两人相似。他既指出诗要以情感为其生命,又强调形式的不可缺:“不管诗与散文如何变迁,总不能不承认诗歌为情的文学。我们情动于中而发于外的时候,其为言为动必带以节奏……所以诗歌者,是托外形表现于音律的一种情感文学!”“诗歌者以音律的形式而写出来而诉之情绪的文字。”[11]这和宗白华为诗下的定义相仿。
总之,上述新诗人对新诗艺术化问题的论及虽然不充分,但其中毕竟包含了一些可贵的艺术化的因子,这些因素并未成为独立的诗学倾向,而只是被包容在初期新诗学的主导倾向之中,但毕竟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伏笔。
真正站在新诗的立场就艺术化问题提出建设性批评意见的,是李思纯、陆志韦和郑伯奇等人。
李思纯,字哲生,成都人。1920年赴法国留学,学习法国文学,1923年回国,到东南大学任教。在《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1920年)一文里,他侧重讨论新诗艺术方面的不足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他认为在新诗成长过程中,形式问题不可忽视:“我认为诗的形式,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他与诗的艺术,有着甚深的关系。”[12]和宗白华的观点相仿,李思纯也认为“形式”是外在的、艺术的、人工的;“这诗的外形,诗的外象,即是所谓‘形式问题’,艺术的作用,完全属于形式的方面,外象的方面。”[12]他不赞同那种认为新诗“美在内容而不在外象”的观点,而强调新诗发展必须兼顾艺术问题。他还以图画、雕刻、音乐为例,说明艺术的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形,新诗也不例外:“诗创作的事,形式的艺术,与艺术的形式,确乎是其中一个问题。我们不希望诗体的改革,永远为幼稚粗浅单调的新诗,而希望他进步成为深博美妙复杂的诗。”[12]李思纯同时认为中国诗从古体到律体再到词曲的发展,都是根据语言的自然与音节的谐和,并非人为地制造枷锁。以律体为例,他认为平仄是“为求音节的更谐和而天然造成的规范。并莫有谁人,能具这样伟大的力量,强定平仄,而能使全国从风的。”[12]他驳斥了那种把律体诋为矫揉造作的论调,指出律体的产生正是根据语言与音节的自然。早期白话—自由诗人崇尚自由,厌恶形式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把反格律推向极端,如康白情所说“因为格律底束缚,心官于是无由发展;心官愈不发展,愈只在格律上用工夫,浸假而反能满足感官;竟嗅不出诗底气味了。于是诗排除格律,只要自然的音节。”[5]这样就否定了格律存在的合理性,格律的价值也就荡然无存。李思纯瞩目于新诗的发展前途而诚恳地呼吁诗人们正确看待格律问题,他甚至设想用律体来丰富新诗的艺术表现:“我们的新诗,是否还有创为律文的必要呢?这也是当研究的问题。”[12]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诗界革命初期也曾尝试用律体作白话诗,他在1916年就作了一首白话律诗《江上秋晨》,不过他的朋友任叔永、朱经农等认为这不是白话诗,胡适只好作罢。[13]李思纯在诗艺自由主义高涨之际特别强调了诗的形式建设的必要性,其清醒与警觉是难能可贵的。在他看来,新诗的主要缺点是太单调、太幼稚和太漠视音节,这些都表现在形式方面,同属新诗艺术建设方面的问题。他认为诗与散文的区别主要是在音节方面,一般的俗歌俚谣之所以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就是有适当的音节。他希望新文学家们从建设新诗的长远目标出发,切实关注诗的艺术化问题。他对新诗在艺术建设方面的具体意见有两点。首先是多译欧诗输入范本。他以绘画作比,说明新诗既然是艺术的一种,就必须要进行艺术的模仿与训练。[12]其次他还建议融化旧诗及词曲的艺术。他特别指出胡适和康白情在具体的创作中就融化有词曲的音节。在这篇长文的结尾,他再次强调艺术化对新诗建设的重要意义:“总而言之,国人如不安于现今单调粗拙幼稚的新诗,以为不满足,为欲进步为深博美妙复杂的诗。那么,于我说的形式及艺术上的种种问题,总得留意一下。”[12]在给宗白华的一封信中,他也表达了新诗要多从欧美输入范本,进行“艺术的训练与养成”的主张。[14]应该说李思纯对诗人艺术修养和诗的艺术化的强调更切中早期白话—自由诗的流弊。虽然宗白华和康白情等人也曾对诗人的艺术训练问题亦偶有涉及,但只是泛泛而谈,没有把艺术化问题作为新诗发展的迫切课题。李思纯的较为系统的新诗艺术化主张显然是有意识地为纠正早期白话—自由诗学的偏颇而发的,显示出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和可贵的理论自觉。
稍后于李思纯,把注意力集中到形式方面并有意识进行新诗艺术化创作尝试的,是陆志韦。在《我的诗的躯壳》(1923年)一文中,陆志韦阐述了自己的诗学主张。他结合自己的创作感受来谈,因此较李思纯更为细致入微。在陆志韦看来,美的精神应该有美的表现,美的灵魂应该蕴于美的躯壳,因此在白话诗创作初始他就格外注意形式问题。他曾受李商隐、李贺以及维多利亚前诗人们的影响,注意诗的语言的锤炼。他认为节奏对于诗来说是不可少的:“文学而没有节奏,必不是好诗。”[15]他反对完全把天籁的口语作为诗的基础,因为这样会使新诗过于散漫。和李思纯一样,陆志韦批驳了那种极端自由主义的反形式诗学主张:“当代为新诗运动的先生们连这一批选择都在排斥之列,以为这样就不免限制美术的自由。我不能不说这种豪放的主张显然因误解美术的意义而发生。”[15]显然,陆志韦所说的“美术的意义”就是指诗的艺术性而言。他接着说:“诗应切近语言,不就是语言。诗而就是语言,我们说话就够了,何必做诗?诗的美必须超乎寻常语言美之上,必经一番锻炼的功夫。”[15]这是对早期白话—自由诗“明白如话”诗风的反拨,强调诗应超越日常言语的层面,经过艺术的锤炼与深化。节奏并非都是现成的,有时必须竭力经营,即“半靠经验,半靠天才”,[15]这是针对早期白话—自由诗过分依重“天籁”,缺乏必要的艺术锻炼和审美规范而言的。清代诗人袁枚在谈到诗歌创作时曾说“盖有从天籁来者,有从人巧来者,不可执一以求”[16](P123)。陆志韦所持的观点与此相仿。
创造社的郑伯奇也较早注意到了新诗的形式问题。他为白话—自由诗学敲响了警钟,呼吁新诗人们重视形式美:“形式上的种种制限,都是形式美的要素,新文学的责任,不过在打破不合理的制限,完成合理的制限而已。就诗而言,绝律试贴之类不合理的制限,是应该打破的,流动的melodie,铿锵的rithme,乃至相当调和整齐的forme,都是应该更使之完美的制限。”[17]同时郑伯奇也就“小诗”谈到了新诗在形式美上的缺陷:“……这两年来,流行所谓‘小诗’,其形式好像在来的绝句,小令,而没有一点韵调之美”,“‘小诗’的形式美是必要的,因为形式的制限越完美,其传达感情更深,动人的力量更大。”[17]郑伯奇特别指出形式和规则不纯粹是一种束缚,它能强化所要表达的情感。这与早期白话诗人把规则视为枷锁镣铐的观念相比,有了更为辩证和深入的认识。
李思纯、陆志韦和郑伯奇等人的新诗艺术化主张,显示出敏锐的艺术洞察力和可贵的理论自觉,虽然他们的理论主张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大的反响,但在新诗艺术化进程中这些见解都有着不可忽略的地位。
随着新诗创作的深入发展和其弊端的日益呈现,白话—自由诗人内部的诗学自由主义倡导者也开始进行反省。对“自然的音节”颇为欣赏的周作人意识到新诗过于自由散漫而应有所节制了:“我觉得新诗的第一步是走了,也并没有错,现在似乎应走第二步了,我们已经有了新的自由,正需要新的节制。”[18](P885)真正从理论和实践上完成“新的节制”这一任务的,还要靠1926年兴起的新格律诗运动。
三、新格律诗运动与新诗艺术化观念的成熟
1926年以《晨报诗镌》为阵地的一批诗人把对新诗形式美的关注推向了高潮。刘梦苇、闻一多、徐志摩、饶孟侃、朱湘等人从理论到实践上进行的新诗格律化探讨标志着艺术化观念开始发展到了独树一帜、自成系统的地步。如果说是李思纯、陆志韦等人最先发出了艺术化的呼声,那么闻一多等人则把这种声音扩充到整个诗坛,使其几乎成为替代诗艺自由主义的诗坛新潮。
新格律诗派完成了由“自然的音节”到形式化音节的转变。“自然的音节”这一特定术语由胡适首倡而为新诗人所普遍接受。胡适把“自然的音节”视为新诗的方向,在《谈新诗》一文中作了详细的阐释。他认为诗的音节是内在的,全靠两个自然成分,一个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一个是句子内部用字的自然调和,这些都是“天籁”——不能刻意追求,和平仄、韵脚等有意识的形式美追求不同。[19](P245)“自然的音节”旨在反拨旧诗过分注重格律的流弊,试图把旧体诗词过分雕琢形式的偏颇扭转过来,因此得到新诗人们的普遍认同。朱自清把“自然的音节”和“人工的音节”对立起来,扬前者而抑后者:“新诗底音律是自然的,铿锵的音律是人工的;人工的简直,感人浅;自然的委细,感人深……”[20](P49)“自然的音节”反映了诗人们用新的诗美原则来对抗传统的“形式美”的价值标准和较为严格的诗艺规范,对新诗创作突破旧诗樊篱、自由洒脱地抒发情感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自然的音节”的具体策略和“形式大解放”的总体指向是相一致的,因此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诗艺自由主义的风气,使新诗创作更加不注重诗的审美特性和艺术规范。
有鉴于此,继起的新格律诗派特别强调音节的艺术化(亦即形式化)。闻一多提出了“音尺”的范畴,认为汉语诗句有“二字尺”和“三字尺”,它们能使整齐的句法与调和的音节同时实现。饶孟侃则指出,音节不单纯是字面的声音,它包含有格调、韵脚、节奏、平仄等因素。其中格调是指段的格式,音节要有格调才合乎自然的规律:“没有格调不但音节不能调和,不能保持均匀,就是全诗也免不了破碎。”[21]韵脚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它“能把每行诗里抑扬顿挫的节奏锁住,而同时又能把一首诗的格调缝紧”[21],使诗的音乐性增强,铿锵成调。关于节奏,饶孟侃和闻一多、徐志摩的观点一致,他认为和谐的节奏是新诗存在的基础。他同时也强调了平仄的作用,认为抛弃平仄即是抛弃音节中的节奏和韵脚。由此可见,新格律诗派的音节观念和早期白话诗人存在着较大分歧,前者追求艺术美,因而主张形式化的音节,强调诗的和谐美,而后者则执着于自然美,因而崇奉自然的音节,追求诗的单纯美。
新格律派诗人们正式提出,“构造诗的躯壳”的口号,号召诗人们致力于新诗的艺术化(或“诗化”)运动。1921年在清华读书时的闻一多便深信:“美的灵魂若不附丽于美的躯体,便失去他的美了。”[22](P42)完全的形体是完备的精神惟一的表现是新格律诗派共同崇奉的圭臬,徐志摩疾呼:“我们信我们自身灵里以及周遭更多的要求投胎的思想和灵魂,我们的责任是替他们构造适当的躯壳,这就是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现;我们信完美的形体是完备的精神惟一的表现;我们信文艺的生命是无形的灵感加上有意识的耐心与勤力的成绩。”[23]徐志摩强调诗是艺术,因此必然要诉诸于人工,刻意于外形:“我们觉悟了诗是艺术,艺术的涵养是当事人自觉地运用某种题材,不是不注意的一任题材支配。”[23]“艺术化”成为诗人们关注的焦点,怎样为“裸体美人”披拂上美丽的外衣成为当务之急。
新格律诗学标志着新诗艺术化理论的初步形成。新格律诗学针对早期白话—自由诗学的偏颇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主张来补偏救弊,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结语
就现代诗学进程而言,这去的批评界大都视白话—自由诗学为惟一正宗,对注重形式建设的诗学主张不太重视。毋庸讳言,白话—自由诗学对突破旧诗樊篱、创建不拘一格的诗学体式起到重大作用。但也应该看到,由于白话—自由诗学着眼于“破”,在“立”上,则存在着较大不足。“破”自有其合理性,但“立”也刻不容缓。由“破”到“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也是诗学发展的合理要求。如果说白话—自由诗学功在于“破”,那么新格律诗学则功在于“立”。没有前者所开创的诗体大解放的格局,新诗会一直在老路上原地踏步,而如果没有新格律诗派等所推动的新诗艺术化进程,新诗也会在自由散漫的路上走向漫无依归的穷途。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而从前者的“破”到后者的“立”则是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进步。而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李思纯、陆志韦等人的艺术自觉,则是从白话诗学到新格律诗学的不可或缺的过渡。
从理论上看,在新诗学的艺术化倾向中也包含着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内涵,尤其是关于艺术与自然关系的诗论。诚如美国著名评论家M.H.艾布拉姆斯所说:“诗歌中自然的成分包括艺术,并产生于自发性与意识的相互渗透。”[24](P188)诗歌创作中艺术与自然,美与真的关系是很微妙的,“自然”与“真”诚然是诗歌创作的必要前提,但“艺术”与“美”对于诗这种独特的艺术来讲更是必不可少的。艺术是“自然”的一种升华,纯粹的“自然”是不可能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的。诗毕竟是一种精心构思的艺术,用日常语言的标准来取代诗艺规范(形式规范)无异于诗的取消与自杀。新格律诗派为新诗发展补上了必要的一课,通过对诗的艺术形式的探讨和实践使新诗走上了艺术化的道路。从标举“自然”到崇奉“艺术”,从要求打破一切束缚自由的镣铐到欣然于戴着枷锁跳舞,从势衷于“裸体的诗”到刻意构造“诗的躯壳”,不但不是现代诗和诗学观念的倒退,反而是一种进步和深化。
收稿日期:2000-0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