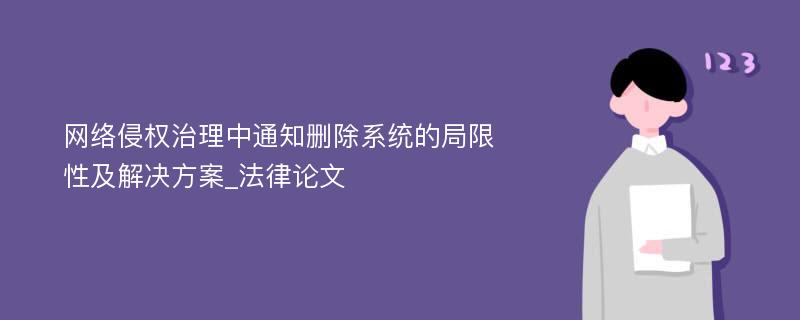
网络侵权治理中通知移除制度的局限性及其破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局限性论文,移除论文,制度论文,通知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知移除制度是我国应对网络侵权所设立的重要制度之一。自2000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网络著作权纠纷解释》)确立该制度以来,其已在我国运作长达15年之久。无论是实务界还是理论界,均对通知移除制度在网络侵权治理中的地位给予较高评价。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曾多次强调:“要维护‘通知与移除’规则的基本价值,除根据明显的侵权事实能够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明知或者应知的情形外,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赔偿责任应当以首先适用‘通知与移除’规则为前提。”①然而,与对通知移除制度“寄予厚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网络侵权并没有如该制度所预期的那样得到抑制,相反,网络侵权愈演愈烈。据北京市版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内包括百度、优酷、土豆、迅雷在内的日浏览量排名前十位的资源分享网站,均载有大量被用户上传的他人作品,从而不断引发大规模、群体性的侵权浪潮。②同样,近年来法院受理的涉及网络著作权的案件迅猛增加。③ 为何通知移除制度未能如立法者所预期般有效抑制网络侵权的发生呢?④究其原因,除了理论上对其认识混乱⑤和实践中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等因素外,通知移除制度本身的不足也导致了该制度在实践中的运作效果不佳。当前学界对通知移除制度的研究,多集中于从规范层面探讨如何解释与适用相关规定,比如通知合格与否如何认定、不合格的通知能否产生法律后果、何为“及时”采取了“合理措施”等,⑥而对通知移除制度的实践运作状况及效果则缺乏足够关注。但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所强调的:“(对通知移除制度)既要防止降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认定标准,使‘通知与移除’规则形同虚设;又要防止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第三方利用其网络服务侵权消极懈怠,滥用‘通知与移除’规则。”⑦但令人遗憾的是,被虚设和滥用正是当前通知移除制度运作的真实状况。为何会出现这种局面?本文试图通过对通知移除制度运作状况的实证考察,揭示通知移除制度的局限性,以期消除对通知移除制度的不合理期待,并对促进我国网络侵权的有效治理有所裨益。 一、通知移除制度局限性的现实存在 依照通知移除制度的设计初衷,该制度运作的理想状态是:权利人将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等文件发送给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通知后进行审查,若通知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便及时移除相关内容,并告知内容上传者;如果通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则通知权利人补充相关文件;如果通知所指的内容不构成侵权(如属合理使用等),则网络服务提供者应选择不移除该内容。此外,用户也可通过反通知要求恢复被移除的内容。⑧ 通过通知移除制度的运作过程可知,其有效运作的条件主要有四:一是权利人愿意采取通知方式解决侵权纠纷;二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愿意及时移除侵权内容;三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会移除非侵权内容;四是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当移除了非侵权内容,用户在得知自己内容被不当移除后,愿意通过反通知要求恢复被移除的内容。在这四个条件中,就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理想的状态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合格的通知后会及时移除相应的侵权内容。但在很多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权利人的通知后并没有移除⑨相关的侵权内容,相关事实举例如下。 第一,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因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通知后未移除相关内容而引发的诉讼。比如,在“袁腾飞与博瑞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法院认定:“袁腾飞发现博瑞公司所管理的网站中存在涉嫌侵权的作品后,委托律师向博瑞公司发出要求停止侵权的律师函,该律师函中明确了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联系人及方式等有关信息……现无证据显示博瑞公司在收到律师函后采取了任何必要措施,博瑞公司的行为构成帮助侵权行为,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⑩又如,在“新传在线公司诉土豆公司案”中,原告主张“曾发函要求被告停止侵权未果”,故而诉至法院。(11)该案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评选为“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30年典型案例”之一,案情具有较强的典型性。 第二,因网络服务提供者未根据通知及时移除侵权内容而发生的公共事件也为数不少。比如,酷6公司副总裁姚建疆曾指责优酷公司在版权保护方面表里不一。优酷公司曾推出24小时删除机制,承诺只要权利人告知网站中存在影片侵权,优酷公司会在核实后的24小时内立即予以删除。然而,在酷6公司就其独家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神枪手》、《兄弟无间》、《孔雀东南飞》等40余部影视剧向优酷公司发送了侵权移除通知函及版权预警后,优酷公司对此却置若罔闻。酷6公司在与优酷公司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诉至法院。(12)又如,搜狐公司与激动网公司成立“反盗版联盟”,指责优酷公司对侵权作品屡次闪躲,对侵权通知不予及时回应;韩寒等组成作家维权联盟,指责乃至起诉百度文库侵权,因为其许多作品屡遭侵权却不能及时得到删除。(13) 第三,虽然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通知后移除了相关内容,但侵权内容很快再次被上传的现象多见。比如,在“上海全某网络科技公司与东阳某影视发行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法院认定:“在案删除记录表明:某网上存在同一用户上传大量涉案视频以及不同用户上传[人教版]系列涉案视频的情况,上诉人在接到被上诉人的通知后知道并删除了‘yongfangyuan’‘网联游侠’上传的大量特级教师辅导英语视频、[人教版]系列英语视频后,理应知晓该等用户上传的视频以及其他用户上传的同系列视频很有可能是侵权视频。然而,上诉人在被上诉人连续发了三次通知后,仍然未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同一网络用户上传节目视频以及其他用户上传同系列节目视频。”(14)事实上,北京市版权局2011年发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指导意见(试行)》第5条已对通知后仍反复侵权的现象有所回应,由此表明此种现象在现实中普遍存在。 第四,不同行业领域的网络公司对网络侵权采取宽严不一的政策也显示了网站在网络侵权问题上的态度不一。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电子商务类网站对网络侵权的打击力度普遍高于娱乐视频类网站。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电商类网站在执行通知移除制度方面比视频类网站做得更好,但从日常新闻报道中可侧面感受到这个事实。此外,不同类型网站对相似的网络内容采取不同措施是更为典型的体现。举例而言,淘宝的淘花网与百度的百度文库都曾因推出用户上传文档服务而受到作者的指责,但两者的回应却截然不同。淘花网立即停止了相关活动并发布了道歉声明,而百度文库却我行我素。(15)这些现象表明,网站对侵权问题的治理态度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通知移除制度的实施状况。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发现,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很多时候并没有依照通知移除制度的要求,在接到合格通知后移除相关侵权内容。当然,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并非在收到通知后不采取任何移除措施,事实上,其往往有选择性地移除一些未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内容,而不移除一些引起广泛关注(往往也是对权利人权益损害较严重)的热点内容,尤其是一些热门影音作品。可见,从立法目标与实现效果之间的显著落差来看,通知移除制度确实存在实施效果有限的尴尬局面。 二、通知移除制度局限性的成因分析 通知移除制度的实施效果有限,这集中体现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侵权通知后,往往并没有及时移除相关侵权内容,这与一些人的预判并不一致。有人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了避免承担侵权责任,会在收到侵权通知后及时移除侵权内容,这也正是立法者所预设的逻辑推论结果。然而,这个推论忽略了影响网络服务提供者作出行为选择的因素,除了法律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且法律往往并不是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事实表明,网络服务提供者有时会遵守通知移除制度而采取移除措施,有时又会罔顾法律的规定而宁可承担责任也不移除侵权内容。因此,全面考察通知移除制度运作过程中影响网络服务提供者行为选择的各种因素,是解释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何有选择性地移除侵权内容这一问题的关键。有必要从人的行为符合理性自利要求的理论预设出发,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在通知移除制度运作过程中涉及的成本与收益作出分析。 一般而言,网络服务提供者不遵守通知移除制度的成本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被诉风险。需要明确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若未依权利人的要求移除相关内容,并不意味着其必然会向权利人承担侵权责任,因为权利人未必就此提起侵权诉讼。因此,网络服务提供者被起诉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对权利人而言,是否提起诉讼也须考量成本与收益,而权利人维权所得不足以支付其维权成本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江苏省音像制品分销协会会长冯晶曾表示:“两年来,我们协会打了300多起官司,结果倒贴了80来万元!”(16)因此,现实中常常发生权利人(多为名人)指责某知名网站侵权,表示将通过诉讼维权,但最终又不了了之的现象。这表明权利人很多时候更愿意选择通过其他途径而非诉讼途径来解决纠纷。因此,即便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依权利人的要求及时移除侵权内容,其承担的也只是被诉的风险。 第二,败诉风险。网络服务提供者被起诉未必一定会败诉,目前我国网络侵权纠纷的审理和判决尚存在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在所难免。如曾引起广泛关注的百度音乐盒案和雅虎音乐盒案即是典型。(17)两案案情相似,被告百度公司和雅虎公司都向用户提供音乐搜索服务,原告也都曾向被告发送过侵权通知,但最终法院的判决却截然不同。在百度音乐盒案中,法院认为,原告无法证明百度公司对原告通知以外的其他侵权内容明知,故其无需承担侵权责任;但在雅虎音乐盒案中,法院认为,根据权利人已经发送的侵权通知,被告雅虎公司应知其他相关侵权内容的存在,故需承担侵权责任。(18)这种“同案不同判”现象不仅可能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所适从,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违反通知移除制度的法律后果心存侥幸。 第三,侵权损害赔偿金的承担。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被法院认定为构成侵权,将承担一定数额的损害赔偿金。然而,从实践情况来看,法院判决网络服务提供者支付的侵权损害赔偿金数额往往并不大。以国内视频领域市场占有量第一的优酷公司为例,根据其在美国上市时发布的招股说明书,自2007年至2010年9月,优酷公司每年被提起侵权诉讼(以著作权侵权纠纷为主)的数量分别是2起、34起、252起和160起。在这总计448起著作权侵权诉讼中,大约70%的诉讼以双方和解、原告撤诉或法院判决驳回的方式结案。在此期间,每年度判决优酷败诉的赔偿金额分别为10万元、40万元、140万元和10万元。(19)可见,与影视作品权利人动辄提出的上百万元的侵权损害赔偿金诉请相比,网络服务提供者实际承担的损害赔偿金可能有过低之嫌。 第四,刑事责任成本和行政责任成本。尽管法学中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分属不同法律部门,但对当事人而言,这些责任都是影响其行为选择的成本。就刑事责任成本而言,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选择有较大影响的是公司人员因网络犯罪而需承担的刑事责任。就行政责任成本而言,除了行政处罚之外,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最有影响的行政责任可能是吊销其相关经营许可证。可见,相较而言,刑事责任成本和行政责任成本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影响可能比民事责任成本更大。但从实践来看,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多适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自己主动上传侵权内容的情形,如2012年7月,天线视频董事长等6人因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成为我国首次因通过网络侵犯著作权而获刑的公司人员。(20)公司因网络用户上传侵权内容被吊销营业许可证的情形目前尚未发生。(21)因此,在出现足够多的因网络服务提供者未执行通知移除制度而被课以严厉的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的“先例”之前,刑事责任成本和行政责任成本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行为选择的影响力可能有限。 第五,公司形象的损失即公司社会评价的降低。不遵守通知移除制度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往往会遭到相关社会主体的指责。这些主体包括权利人、同业、相关协会和组织乃至政府部门,但需注意的是,其往往并不包含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至关重要的投资人、广告业主以及网络用户等“衣食父母”。(22)尽管社会的指责可能会影响投资人和广告业主对相关企业的信心和预期,但很少发生投资人或广告业主指责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的情况。至于网络用户,公认的事实是,尽管我国网民尊重与保护著作权的意识不断增强,但总体而言并不强。(23)网络用户最关心的是网站体验的舒适度,而影响体验舒适度的重要因素便是网站内容的丰富程度。可见,指责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的主体往往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并无直接利害关系,因而往往也不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最需要争取认同的主体,这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形象损失在抑制其侵权行为方面的影响有限。 上述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不遵守通知移除制度所可能承担的主要成本,而其不遵守该制度所可能获取的收益主要在于网络用户注册量、用户流量的增加以及用户忠诚度的增强,这是因为网站内容的丰富更有可能吸引用户注册、登陆和浏览该网站。比如,视频网站Mofile的一位前高管曾透露,从2007年至2009年,我国大部分视频网站超过70%的页面访问量依靠盗版内容维系,它们多集中于电影、电视剧、动漫及MTV。(24)而用户数量和流量的增加又会带来更多投资者的关注和广告业主的青睐,这会为公司带来更多的融资机会,也会为公司的快速成长乃至上市提供更大的可能性。这有助于公司在同业竞争中率先胜出,继而完成“正版化”的转型。在这方面,优酷公司的发展历程便是典型。 而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认真遵守通知移除制度,其往往并不能获得声誉的显著提高,因为权利人和同业竞争者等相关主体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网络服务提供者却要承担用户流失的重大风险,包括用户注册量与访问量的减少以及用户活跃度的降低,因为移除用户上传的盗版内容既会降低网站内容的丰富性,也会打击用户上传自制内容的积极性。(25)这种局面进而会影响投资人和广告业主的选择。这意味着除非网络服务提供者初始便拥有充足的资本来购买正版内容,否则,其遵守通知移除制度将会使自己面临“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以致在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从上述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遵守和不遵守通知移除制度可能承担的成本和获得的收益的比较可以看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遵守通知移除制度虽然存在可能承担法律责任、面临形象损失等风险,但其也完全可能获得用户访问量快速上升等收益,且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后者的重要性往往超过前者。基于此,网络服务提供者对通知移除制度予以“选择性守法”的现象便“在所难免”。甚至有人指出:“网站利用技术手段伪造大量用户,通过服务器大批量上传盗版内容,曾是行业通行的做法。”(26)“VC资本的狂热助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页面访问量(PV)的恶性竞争,甚至催生了灰色产业:为了在视频竞赛中胜出,一些视频网站雇佣了专门的盗版内容片源组织,以用户的名义向网站上传盗版内容。”(27)可见,希望网络服务提供者能自觉移除被通知的侵权内容,无疑是“天方夜谭”。 三、通知移除制度局限性的形成机理 通知移除制度的实践效果不佳,直接原因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权衡守法和违法的成本与收益后,往往会作出“宁可违法也不愿移除侵权内容”的选择。这种“有意”违法的“理性”选择,虽然具有道德上的可非难性,却是人性自利特质下难以轻易“撼动”的客观事实。这不仅打破了立法者对通知移除制度实施效果的美好预期,也揭示了该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重要缺陷——违背了“任何人不得为自己的法官”的基本程序正义原则。 “任何人不得为自己的法官”,这是近代法确立的一项基本程序正义原则。(28)在通知移除制度的运作过程中,上传侵权内容的是网络用户,而非网络服务提供者,故从表面上看,存在直接利益冲突的是权利人和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被立法者预设为“中立”的第三方,独立判断收到的通知是否符合立法规定的要求,并根据该判断作出是否移除相关内容的决定。因为惟有作此预设,通知移除制度才能真正如立法者预期般运作。然而,这个预设判断显然与真实状况相悖。如前所述,是否移除侵权内容,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具有密切乃至重大的利害关系,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网络公司的发展和兴衰,网络服务提供者显然难以在收到权利人的通知后作出中立的判断和决定。因此,由利益关联密切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通知是否合格的判断者以及相关内容是否移除的执行者,直接违背了基本的程序正义原则,也“理所当然”地导致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对通知移除制度予以选择性守法的客观现象。 由此可见,立法者在设计通知移除制度时,所预设的前提——网络服务提供者会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客观、公允地判断通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并据此决定是否移除相关内容——并不成立。因此,通知移除制度的实践效果与立法预期之间出现了明显落差。那么,在“任何人不得为自己的法官”的程序正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环境下,为何立法者还会设计出此种看似“漏洞百出”的制度呢?对此,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就《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答记者问予以说明:“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纠纷往往涉及金额很小,在现实中缺乏通过行政或者司法程序解决的必要性。为此,《条例》参考国际通行做法,建立了处理侵权纠纷的‘通知与删除’简便程序。”(29)可见,通知移除制度的设立主要受到成本因素的影响,并系借鉴国外经验的结果。 第一,通知移除制度提供了网络侵权当事人之间自行解决纠纷的机制,有助于减少国家机关的干预,并减轻国家机关的负担。对此,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一是虽然有一些网络侵权纠纷涉及的金额较大,但大量纠纷涉及的金额较小。对这些涉及金额较小的纠纷,立法者希望当事人之间能自行快速解决,从而避免动用行政或司法资源。二是如果网络侵权中的所有纠纷都只能通过行政或司法途径解决,则是国家机关难以承受之重。其实,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内容的海量性特征使得国家机关“应接不暇”,进而常常选择采取“权力下放”的做法。比如,我国对影视作品设有严格的申报立项和审片制度,如果没有国家的许可,电视剧等不能立项、制作和播出。(30)然而,网络上兴起的海量自制剧、微电影等视听作品使得传统的监管机构面临巨大的监管负担。最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12年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要求按照“谁办网谁负责”的原则,对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一律实行“先审后播”,即视频网站(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播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之前,应自行安排视频审查员进行内容审核,审核通过后方可上网播出。(31)可见,当“有限”的国家行政和司法资源面对“无限”的网络内容时,将“权力下放”至网络服务提供者等社会主体,已经成为务实的选择之一。通知移除制度,便是希望由网络服务提供者来分担法院的部分“裁判权”和“执行权”,由其判断通知合格与否、所通知内容侵权与否,并对侵权内容执行移除措施。 第二,我国的通知移除制度是对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DMCA)中通知移除制度(Notice and Takedown Regime)的借鉴。实现网络侵权纠纷部分由当事人自行解决的法律机制可有多种选择,比如美国采取的通知移除制度、加拿大采取的通知制度(32)等。加拿大的“通知制度”是一种用于解决网络侵权的制度,权利人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内容,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通知后不负有移除义务,只需将该通知转发给上传内容的网络用户即可。而我国法上通知移除制度的设立受到了美国DMCA的深刻影响,这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反映。其一,从条文表述来看,我国关于通知移除制度的立法条文与美国DMCA的相关规定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在我国的立法文件中,《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通知移除制度作了最典型、最全面的规定。而其所规定的通知移除制度条款与美国DMCA的相关规定如出一辙。其二,从文献资源来看,国内学界关于通知移除制度的研究采用的几乎全是美国的相关文献,且主要是美国DMCA的相关规定及其评论。 由此可见,尽管通知移除制度的实践运作存在诸多障碍,但该制度却存在比较法上的基础,并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纠纷解决成本,减轻国家机关的干预压力。除了前述官方说明中提及的这两项原因外,笔者认为,通知移除制度的设立,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现实根源,即互联网技术对传统法律救济途径造成的冲击。 当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时,受害人最合理也是最传统的救济途径,是向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主张权利。正如杨立新先生所言:“造成被侵权人损害的,全部原因在于利用网络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其行为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为百分之百,其过错程度亦为百分之百。”(33)然而,互联网技术的特点导致这个传统的救济逻辑在网络环境中失灵。详言之,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历程来看,当前互联网技术存在三大特点:一是匿名性,二是无界性,三是随着web 2.0技术发展起来的众多用户参与性。(34)匿名性使得网络侵权中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主体的真实身份难以被发现,或发现的成本较高。无界性导致权利人通过诉讼实现权利救济的成本大大提高,乃至可能使诉讼得不偿失。因为诉讼管辖原则上是“原告就被告”,无界性使得权利人可能面临跨地区诉讼,这一方面提高了权利人的救济成本(包括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权利人诉讼救济的不确定性风险。众多用户参与性则进一步增加了权利人诉讼救济的困难。互联网的这些特点所共同导致的结果是,权利人向侵权用户主张权利的传统救济手段根本无法操作,或操作的成本非常高昂。 显然,如果仍然依循传统救济途径,将意味着在多数情况下权利人事实上难以得到救济。因此,无论是权利人还是立法者,都将目光投向了网络环境中的另一关键主体——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利所有者、集体管理组织和政府将网络服务提供商视为在数字传播的瞬间链条中,能够控制使用者行为的最可行的聚点(point)。这样,在版权领域规制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历史一般被理解为,国家和版权所有者试图通过网络服务提供商网关,重新获得控制中心权,以期在网络环境下继续管理内容和使用者行为。”(35)为实现通过控制网络服务提供者来预防用户侵权,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但各国的相关立法和实践普遍未认可这一方式。事实上,多数国家采取的选择是,在一定条件下课以或免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然而,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是在权利人难以从侵权用户处直接得到救济的情况下发展出来的一种救济选择和要求。因此,基于不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课以过于严格的责任,以及需对权利人权益予以保障的需要,我国立法者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课以网络服务提供者一定义务,要求其协助权利人消除网站中的侵权内容,若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履行该义务,则需就此向权利人承担责任,此即通知移除制度。 四、通知移除制度局限性的破解之道 前文对通知移除制度局限性的成因和形成机理的论证,揭示出破解该制度局限性的以下三种可能途径:一是扭转互联网匿名性等特点对传统法律救济途径的影响,使权利人能够有效地向直接实施了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主张权利。二是改变通知移除制度的设计方式,使其不再违背“任何人不得为自己的法官”这一基本程序正义原则。三是改变网络服务提供者在通知移除制度运作过程中的成本收益关系,使得其违法成本超过收益。以下分别就这些途径的可行性、制约条件以及应对措施等加以分析。 第一,通过推行网络实名制等方式,实现权利人对网络用户侵权责任的追究。在网络侵权中,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往往是网络用户。但因网络匿名性等特点,网络用户常常脱离于责任追究之外。故若能有效地追究网络用户的侵权责任,无疑是解决网络侵权泛滥问题的“釜底抽薪”之举,通知移除制度局限性导致的负面影响也自然能得到消除。为明确网络用户的身份,网络实名制是目前最可能采取的制度安排。然而,由于实名制可能导致的对用户隐私的潜在威胁、对言论自由的可能限制等,是否推行和如何推行实名制,争议之声不绝于耳。(36)笔者无意对网络实名制的应然选择作出评判。从实然状况来看,2012年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6条已确认,我国将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网络实名制。在这个既有立法选择之下,如何在保障用户隐私等的同时,实现对侵权用户责任的有效追究,或许才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点。 目前,我国相关司法解释采取的由法院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或公安机关调取被告用户身份信息的做法,是实现网络用户隐私保护和责任追究之间平衡的有益尝试。比如,2011年公布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9条规定:“被侵权人在提起民事诉讼时不能提供被告真实身份的,法院应根据案件实际,告知其可以电子证据中标记的IP地址或者网络名称暂作为被告,并根据案件实际作如下处理:(一)被告是网络用户,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调查被告在其网络的登记、注册资料;同时可以申请法院向公安机关网络安全监察部门调查该网络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2014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规定》)第4条第1款也规定:“原告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涉嫌侵权的信息系网络用户发布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的请求及案件的具体情况,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向人民法院提供能够确定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信息。”可见,我国司法实践已经渐渐认可了通过法院获取网络用户身份信息的做法。尽管该制度的具体操作仍有需要明确之处,但已为权利人有效追究网络用户的侵权责任提供了制度支撑,也有助于消除通知移除制度局限性造成的弊端。 第二,改变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侵权内容的判断者和移除侵权内容的执行者的地位,比如设立第三方机构来审查侵权通知,或改采前述加拿大式的“通知制度”等,从而避免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审查和决定是否移除侵权内容。关于设立中立的第三方来审查侵权通知,国外也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设想。比如,有美国学者认为,通知应首先发送给美国版权局(the U.S.Copyright Office),而不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由版权局对通知是否合格、有效进行初步审查。(37)另外,加拿大式的“通知制度”也是部分国家采纳的用于应对网络侵权的方式之一。比如,加拿大在2000年立法时并没有接受美国DMCA创设的通知移除制度,而是自创了“通知制度”。该制度较之通知移除制度的优势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只作为被动的通知者(将权利人发送给自己的侵权通知转发给上传内容的网络用户),而不再作为主动的侵权与否的判断者与执行者。上述两项制度虽然都能改变我国目前通知移除制度违背程序正义原则的设计方式,但其可行性则值得斟酌。由第三方机构来审查侵权通知合格与否,首先,其面临由哪个机构来担任第三方机构的难题。其次,第三方机构在作出判断后,是否有权直接移除网站上的侵权内容?如果可以,这又将带来网络安全的隐患。最后,如果第三方机构判断有误,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可见,若采取该途径,仍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事先探讨和解决。类似地,对于加拿大式的“通知制度”而言,由于我国已长期采纳和实施了通知移除制度,当下作出此种制度调整的社会成本将非常可观。而且,若采该种通知制度,将网络服务提供者从判断通知合格与否的角色中摆脱出来,将导致该判断压力部分转移至法院,会加重法院的审判压力,而缓解法院的审判压力,正是我国采纳通知移除制度的初衷之一。因此,在我国若改采加拿大式的“通知制度”,仍需对可能造成的利弊影响作充分评估。综上,虽然设立第三方机构审查侵权通知或采用加拿大式的“通知制度”有助于避免网络服务提供者在通知移除制度运作过程中“非中立”的弊端,但这些“替代方案”也存在潜在的诸多障碍,是否可取仍需进一步评估考量。 第三,提高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违法成本,进而改变其“选择性守法”的行为选择。既然当前可能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通知移除制度违背程序正义原则的设计安排,那么可以考虑的退而求其次的方案是:改变网络服务提供者在通知移除制度运作过程中的成本收益关系,使其违法成本高于收益。根据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成本与收益的分析,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成本主要在于法律责任的承担和商业形象的损失,而收益则主要是商业利益。由于对商业利益得失的干预较为困难(也不适宜干预),故从制度层面来看,改变网络服务提供者成本收益关系的可行途径在于提高网络服务提供者违法后的法律成本。(38)而这也正是2014年6月公布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所采纳的思路,即将原来的法定赔偿金最高额从50万元上调为100万元。“在实践中,关于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赔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法定赔偿占压倒性多数。”(39)据称,之所以上调法定赔偿金上限,主要针对的就是网络侵权现象。(40)笔者认为,《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所采取的提高网络服务提供者违法成本的思路是可取的,但通过上调法定赔偿金最高额的方式是否能在实践中发挥预期的效果则令人怀疑。事实上,如果我们考察审判实践中法院判决的法定赔偿金额便会发现,此种对策方式可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当前法院判决的法定赔偿金一般都不会超过10万元,多数都只有1、2万元或2、3万元,(41)远未达到50万元的上限。可见,我国当前存在的问题并不在于50万元的法定赔偿金上限限制了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追究,而在于法院并没有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课以较高的赔偿金。因此,希望通过提高法定赔偿金上限来强化对著作权人的保护,究竟能产生多大的现实意义,仍有待观察。 基于此,本文认为,我国当前的首要任务并不是简单地在《著作权法》中调高法定赔偿金的上限,而是要加强对网络侵权损害赔偿金认定规律的认识,即法院为何不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判决高额侵权损害赔偿金应成为破解通知移除制度局限性的突破口。从目前的各种相关事实来看,这或许有政策考量因素的影响,因为在治理网络侵权的同时,信息产业的发展也同样重要。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宽严程度将影响信息产业的发展。以优酷公司为例,其2011年的净收入是8亿9 760万元,而其采购正版影视作品的成本是2亿4 340万元,占净收入的27%。(42)假如因为法律责任的加重而导致正版影视作品的授权成本水涨船高的话,将造成优酷公司的内容成本提高。而即便在当时的成本情况下,优酷公司2011年的净亏损仍达到1亿7 210万元。依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定,2010年上市的优酷公司如果无法在3年内实现盈利,将面临停牌退市的风险。(43)因此,如果在开始阶段就对优酷这样的网络公司课以较高的侵权赔偿责任,将可能严重影响我国相关网络公司乃至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学者认为:“美国在Groster案件之后,著作权人重拾在DMCA中失去的疆域,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网络产业的发展表明其不再需要倾向性的保护”;“从现状来看,我国网络产业的发展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对网络产业的扶持仍然是立法所需重点考量的公共政策。”(44)据此,不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课以较重的侵权赔偿金,或许是我国平衡内容产业和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方式之一。当然,上述只是我国未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课以较高赔偿金的可能原因之一,更综合全面的原因,无疑需要更多的深入研究。 因此,如何合理裁判网络侵权的损害赔偿金,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面临的难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没有对此问题作出回应,《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规定》第18条只是作出了“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在50万元以下的范围内确定赔偿数额”的模糊规定,其可操作性仍待加强。事实上,对此问题,我国也有部分地方法院已经开始作出探索。比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的若干解答意见》第33条至第35条针对“在网络环境中侵犯文字、美术、摄影、影视、音乐等作品著作权适用法定赔偿方式确定赔偿数额应考虑哪些因素”作出了尝试性规定。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则在《关于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赔偿标准问题座谈会会议纪要》中,尝试通过作品首播的时间来确定和统一全省的赔偿标准。这些地方法院的实践经验和探索无疑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可以合理期待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正在组建设立的知识产权法院,也将对网络侵权损害赔偿金的探索尤其是赔偿金确定标准的统一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在理论界,也已有学者注意到网络侵权损害赔偿金酌定因素不明而导致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和法院不同判决间差异较大的问题,并提出了类型化法定赔偿制度的设想。(45)故当务之急应是认真总结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和规律,梳理影响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损害赔偿金之确定的各种因素,从而为《著作权法》等法律的修改和适用提供真正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建议。 第四,有效发挥“知道”规则在我国网络侵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使其成为破解通知移除制度局限性的“替代性”制度。我国相关立法为应对网络侵权,不仅规定了通知移除制度,同时也确立了“知道”规则,即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侵权存在而未及时采取措施,也需承担侵权责任。通知移除制度的局限性,会导致权利人对该制度失去耐心和期待,进而放弃通知,选择直接起诉,根据“知道”规则主张权利。同时,通知移除制度的局限性也可能强化法院对权利人主张的认同,因为若法院不支持权利人通过“知道”规则来主张权利,而通知移除制度又难以奏效,这将意味着对权利人的保护“雪上加霜”。因此,法院认同权利人根据“知道”规则主张权利的判决在我国实属常见。而法院对“知道”规则的认同,又促使权利人放弃通知移除制度而改采“知道”规则。因此,与美国等一些国家相比,“知道”规则在我国网络侵权治理体系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相关事实也表明,目前我国已经存在大量通过“知道”规则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司法判决。(46) 我国相关司法实践对“知道”规则的倚重,可通过与美国“红旗测试(red flag test)规则”的比较,得到更明显的反映。美国DMCA规定了“没有意识到侵权行为明显的事实或情境”,且立法报告中将其具体化为“红旗测试规则”,并明确表示即便版权人没有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其也可能满足“红旗测试规则”。(47)但实际上美国司法实践中很少有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符合“红旗测试规则”,进而认定其不能享受“避风港规则”保护的判决。正如有美国学者所说:“至今为止,(法院)从未根据‘红旗测试规则’认定成立‘明显知道’。事实上,除非网络服务提供者收到了符合法律要求的侵权通知,版权人事实上几乎不可能证明其知道。”(48)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法院对“红旗测试规则”尤其是其主观方面的要求作了非常严格的解释,即除非版权人发送了符合法律要求的侵权通知,否则网络服务提供者始终不会被认定为满足“红旗测试规则”。(49)美国的这一做法与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以知道(或应知)来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过错并判决其承担侵权责任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我国相关司法实践对“知道”规则的倚重,或许与通知移除制度的实施效果有限,进而改采“知道”规则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相关。可见,“知道”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实践中破解通知移除制度局限性的“替代性方案”。 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1]18号)。另参见奚晓明:《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政策与理念》,《知识产权》2012年第3期。 ②参见王坤宁:《阻止资源分享平台群体性侵权浪潮》,《中国新闻出版报》2011年6月30日第5版。 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09年)》,http://www.court.gov.cn/xwzx/fyxw/zgrmfyxw/201004/t20100420_4342.htm,2014年8月20日访问。 ④网络侵权的泛滥与通知移除制度的实施效果不佳关联密切,这可从我国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直接侵权和网络用户侵权两种情形的治理效果中得到反映。北京市版权局有关负责人称:“经过多次打击互联网直接侵权盗版行为治理行动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对资源分享平台上用户大量上传而形成的大规模、群体性侵权事件,至今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行政或司法保护措施。”(同前注②,王坤宁文。)比较网络服务提供者直接实施侵权和网络用户实施侵权这两种情形,两者在社会环境、民众观念等变量上相同,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直接侵权可通过侵权责任法直接追究其责任,而网络用户侵权一般不能直接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而是要先采通知移除制度,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收到通知后未及时移除,才能追究其责任。因此,网络用户侵权未能得到有效治理,这表明通知移除制度未能有效解决网络侵权问题。 ⑤关于通知移除制度在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认定中体系性地位的认识混乱,参见徐伟:《通知移除制度的重新定性及其体系效应》,《现代法学》2013年第1期。 ⑥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网络侵权责任的理解与解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郭寿康、马宁:《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思考》,《知识产权》2012年第11期。 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条第6项。 ⑧这是对我国通知移除制度的一般性描述,但如果严格依据我国现有立法条文的表述,通知移除制度在著作权和著作权以外的其他权利上,其规则可能并不完全相同。比如,反通知规则只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被明确认可,而在包括《侵权责任法》等在内的其他立法中并没有被明确规定。但也有学者认为,《侵权责任法》对通知移除的规定背后已当然包含了反通知规则。参见杨立新、李佳伦:《论网络侵权责任中的反通知及效果》,《法律科学》2012年第2期。 ⑨为行文简洁,本文所称的不移除包括了完全不移除、不及时移除以及移除后再次反复上传三种情形。 ⑩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闽民终字第223号民事判决书。类似案件如“崔海亮等与爱名网络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案”,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新中民四终字第178号民事判决书。 (11)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8)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书。 (12)参见《优酷24小时删除机制形同虚设侵权内容未见删除》,http://www.techweb.com.cn/news/2010-02-04/534950.shtml,2014年8月1日访问。 (13)参见杨涛:《期待“韩寒诉百度”吹响网络版权保护集结号》,《羊城晚报》2012年9月19日。 (14)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一中民五(知)终字第61号民事判决书。类似案件可参见“何瑞东与李向华、天津理想慧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津高民三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XX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诉上海XX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犯著作财产权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9)浦民三(知)初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书。 (15)参见颜亮、黄敬、田志凌:《淘花网、百度文库侵权风波始末——对免费下载说“不”》,《南方都市报》2010年11月21日第GB24版。 (16)《赢了官司输了钱,音像制品赔本维权是谁的尴尬?》,http://news.xinhuanet.com/xhfk/2012-02/21/c_122730482.htm,2014年5月6日访问。 (17)关于案件的评析,参见王迁:《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263页;谢冠斌、史学清:《网络搜索服务商过错责任的合理界定——再评“雅虎案”与“百度案”一审判决》,《知识产权》2008年第1期。 (18)参见7家唱片公司诉百度公司音乐搜索服务著作权侵权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一中民初字第7965、7978、8474、8478、8488、8995、10170号民事判决书;11家唱片公司诉雅虎公司音乐搜索服务著作权侵权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二中民初字第02621~02631号民事判决书。 (19)参见“优酷招股说明书”第20页,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442596/000119312510260191/df1.htm,2014年8月21日访问。 (20)参见陈博:《天线视频盗播案宣判:罚款200万 董事长被判刑》,《新京报》2012年7月31日。 (21)2014年“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中,快播公司因传播淫秽、色情内容而被吊销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并有多名人员涉嫌犯罪而被刑拘,新浪公司也因“涉黄”而被吊销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这可能是一种刑事责任、行政责任趋于严格的现象。不过,快播公司和新浪公司被吊销许可证的原因是“涉黄”,而不是因为侵害知识产权或人格权。 (22)根据优酷土豆公司公布的2013年年度报告,其收入主要来自在线广告业务,2011年、2012年和2013年的广告收入分别占净收入的94.8%、90.1%和89.2%。参见http://ir.youku.com/phoenix.zhtml?c=241246&p=irol-reportsannual,2014年5月1日访问。 (23)参见吴秋余:《八十多家版权方集体起诉土豆网》,《人民日报》2009年2月3日第11版。 (24)参见陆地:《中国视频网站盈利的拐点何时到来》,《视听界》2011年第4期。 (25)对网站而言,保持用户上传自制内容的积极性往往非常重要。因为在web 2.0时代,这是网站保持用户对该网站的依赖性和活跃度的重要途径。从实践情况来看,大多数网站都会对用户上传内容给予奖励(激励政策),这也体现了用户上传内容的重要性。 (26)同前注(24),陆地文。 (27)谢灵宁、张晶:《视频史前传》,《第一财经周刊》2010年第10期;冯颖:《视频版权费一路高涨的逻辑》,http://www.sarft.net/a/41396.aspx,2014年8月10日访问。 (28)关于程序正义的“中立性”要求,参见陈瑞华:《程序正义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103页。 (29)“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就《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有关问题答中国政府网记者问”,http://www.gov.cn/zwhd/2006-05/29/content_294127.htm,2014年8月1日访问。 (30)比如,《电视剧审查管理规定》第4条规定:“国家对电视剧实行题材规划立项审查和电视剧发行许可制度。未经电视剧题材规划立项的剧目,不得投拍制作。未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电视剧,不得发行、播出、进口、出口。禁止出租、出借、出卖、转让或变相转让电视剧各类许可证。” (31)参见刘明江:《“先审后播”对视频网站过错认定的影响》,《电子知识产权》2013年第4期。 (32)关于加拿大的“通知制度”,参见谢利尔·哈密尔顿:《加拿大制造:确定网络服务提供商责任和版权侵权的独特方法》,[加]迈克尔·盖斯特主编:《为了公共利益:加拿大版权法的未来》,李静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219页。 (33)同前注⑥,杨立新文。 (34)See Christopher S.Yoo,Innovations in the Internet's Architecture that Challenge the Status Quo,Journal on Telecommunications & High Technology Law,Vol.8,Winter 2010 pp.85-90. (35)同前注(32),迈克尔·盖斯特主编书,第204页。 (36)关于网络实名制的争议,参见韩宁:《微博实名制之合法性探究》,《法学》2012年第4期;杨福忠:《公民网络匿名表达权之宪法保护》,《法商研究》2012年第5期;周永坤:《网络实名制立法评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37)See Jeffrey Cobia,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Takedown Notice Procedure:Misuses,Abuse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Process,Minnesota Journal of Law,Science & Technology,Vol.10,No.1,2009,pp.404-405.需要说明的是,该文作者提出此立法建议的理由主要是基于避免通知移除制度被滥用而限制言论自由等,与本文的考量并不完全相同。但在解决问题的途径上,与本文此处的思路相似。 (38)这也正是美国法上通知移除制度效果尚可的重要原因之一。 (39)罗莉:《论惩罚性赔偿在知识产权法中的引进及实施》,《法学》2014年第4期。 (40)在2012年公布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中,就已基于网络侵权的考虑而将法定赔偿金上调为100万,参见《〈著作权法〉:著作权赔偿上限拟提至100万元》,《华商晨报》2012年4月6日第C21版。2014年公布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延续了这个修改。 (41)相关数据可通过优酷公司公布的公司报告得到反映,另外也可参见赵雪:《电影盗版:一场审判难以终结的“暗战”》,《科技日报》2010年8月2日第3版;杜思梦:《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向电影网络侵权宣战》,《中国电影报》2010年8月5日第6版;《影视片商出“鲜招”打响“网络维权”战》,http://ip.people.com.cn/GB/12312665.html,2014年5月3日访问。 (42)参见优酷公司2011年公司报告。 (43)盈利压力可能是优酷与土豆两大视频公司合并的原因之一。事实也显示,2013年优酷土豆公司首次实现了盈利(参见《优酷土豆首次盈利领跑行业》,《华西都市报》2014年3月1日第A12版),但紧接着的2014年第1季度优酷土豆公司净亏损环比增加了780%(http://www.techweb.com.cn/internet/2014-05-23/2039565.shtml,2014年8月20日访问)。这似乎也从侧面表明了优酷土豆公司尽力通过“考核”的压力。 (44)史学清、汪涌:《避风港还是风暴角——解读〈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知识产权》2009年第2期。 (45)参见刘满达、刘海林:《论网上著作权侵权损害中的法定赔偿制度》,《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 (46)比如,三元影视公司与土豆公司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33号民事判决书。 (47)See DMCA S.Rep.No.105-190,at 45(1998). (48)See Liliana Chang,The Red Flag Test for Apparent Knowledge Under the DMCA § 512(c)Safe Harbors,Cardozo Arts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Vol.28,2010,p.203. (49)See Amir Hassanabadif,Viacom v.YouTube:All Eyes Blind-The Limits of the DMCA in a Web 2.0 World,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Vol.26,Annual Review 2011 pp.417-419 pp.435-436.标签:法律论文; 网络侵权论文; 网络服务提供者论文; 法律救济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互联网侵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