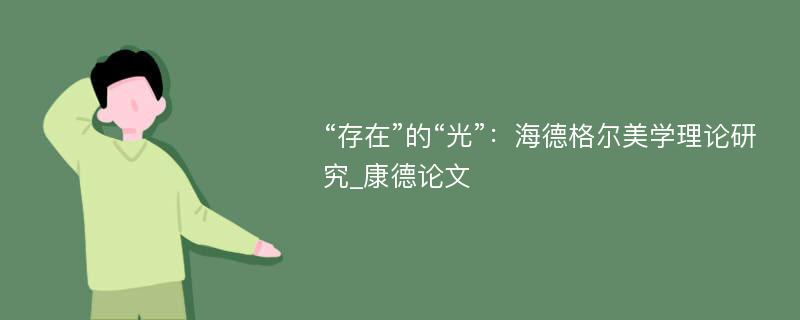
“存在”之“光”——海德格尔美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在什么是“美”这个问题上人们几乎失去了追问的勇气,甚至开始排斥对美的追问(这一排斥在西方体现为对美学这个学科的否定,在中国体现为拒绝追问美“是什么”),但美作为人类文明的三块基石之一(另两个是真与善),却又不允许我们轻易将它绕过,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最伟大的思想家,在建造自己的思想体系时,都会从自身的思想体系出发,提出对美和艺术的看法。正是这些看法,构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作为观念史的“美学史”,构成了一个“美的观念”的链条,这个链条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环节,是海德格尔关于美的看法。
海德格尔是一个西方文明的反思者,这种反思由于深入到西方文明的根基处而产生了一种颠覆性的影响,现代文明的一些基础性的部分,如形而上学、科学、真理观、人道主义、诗等都被质疑或者被赋予了某种全新的意义与形态。那么,在这样一场反思中,西方的“美”这个观念受到了什么样的质疑?又获得了些什么样的新东西呢?按照惯常的多少有些夸张的看法,海德格尔推翻了形而上学,超越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想继续追问一下:在后形而上学的、非主客二分的思想之中,“美”会被如何理解呢?这就构成了我们研究海德格尔关于美的思想的初衷。
一
什么是“美”?海德格尔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通过对康德美学的阐释与评价道出了自己对于“美”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海氏毫不客气地指出,叔本华和尼采都曲解了康德的美学。有曲解就有正解,那么,正解是什么呢?首先应该回答,康德的什么观点被曲解了?“对康德美学的曲解牵连到康德关于美的一个断言。康德的定义是在《判断力批判》2-5节中发挥出来的。‘美的’东西是纯粹和单一的愉悦。美的东西是‘纯粹’欣悦的对象。在这样的愉悦中美的东西作为美的向我们敞开自身,同康德的话说就是‘无利害关系的’,他说:趣味是通过取悦或厌恶来判断一个对象或某种表现方式的能力,无关利害。这种愉悦的对象就是‘美’”。[1](P108)曲解之处在于“纯粹愉悦”和“无关利害”,按海德格尔的说法,叔本华的曲解在于就此而引发出审美是纯粹漠然的静观,而尼采把叔本华的这一曲解视作康德本身所要表达的,因而坚决地予以反对,提出审美状态是“醉”,这当然也是一种误解,因为这一反对就站在误解之上。
那么,康德把美的东西定义为“无利害的愉悦的对象”意味着什么?特别是“无关利害”意味着什么?海氏认为康德实质上是通过这一论断提出了美的本质的问题。“他询问在我们发现我们遭遇到某些美的东西的情境中,我们的行为应当如何使其自身得到规定,从而我们把美的东西视为美的。我们发现某些美的东西的决定性根据是什么?”[1](P109)海德格尔认为应当这样理解康德的无利害说:“在康德建议性地说出这决定性的根据是什么,因而也就是美本身是什么之前,他首先以否定的方式说了那决不可能使自身成为这个根据的东西,也就是利害。把‘这是美的’这个判断强加给我们的不论是什么,绝不可能是利害。”如果从“否定即是肯定”的角度思考康德的这种否定性论断,那么他的肯定的一面是什么呢?海氏认为是,“为了发现美的东西,我们应当让和我们遭遇的东西纯粹以其自身所是样子,以它自身的状态和价值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不是事先从其它角度——我们的目的和意图,我们可能的享受与利害——去思考它。”[1](P109)这句话——让存在者以其自身所是的样子、以其自身的状态和价值出现在我们面前——体现着海德格尔对美的根本看法,“美不是别的,就是在自我显现中将那种状态带上前来。”[1](P78)这里所说的“那种状态”是指与美相关的感受状态。这里的关键在于自我显现。是谁在自我显现?是存在者。存在者按其所是的显现出来就是美——这难道是说并不存在所谓的美本身,也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美,美的只是存在者的“显现”,而且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谁”显现?按海德格尔在此的说法,“显现”本身才是我们苦苦追寻的“美”。
这才是海德格尔对美的根本看法,他认为康德的无利害说并不是要通过把利害排除在外的方式而抑制住与对象的关系,“对康德的误解正在这里,对象首次作为纯粹的对象涌现出来,这样一种呈现就是美。‘美的’这个词汇意味着显现在这一涌现的光芒中”。说美是事物的纯粹显现,并且把这一观点加给康德,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完全可以说,这就是海德格尔本人的美论。让我们比较一下海氏在《艺术作品的起源》一文中对美的定义,就会发现这两个定义是统一的。
海氏说:“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2](P276)更明确地说:“美与真理并非比肩而立的。当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它便显现出来。这种显现——作为在作品中有真理的这一存在和作为作品——也就是美。因此,美属于真理的自行发生。”[3]而这里所说的真理的自行发生无非就是指无蔽之真理的现身和纯粹对象的自我显现。作为美的本质,二者是同一的,这个同一能够避免这样一种误解——纯粹对象就是美,这恰恰是叔本华以误解的方式从康德那里获得的美的本质。海氏的纯粹对象并非就是以现象学直观的方式,通过无立场、无方向、无前设的直观达到事实本身,纯粹对象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存在者之澄明的状态,存在者之澄明并不是要把存在者从它所处的世界中提取出来,也不是要斩断它与其他存在者,乃至人的诸种关联,恰恰相反,是要进入它的关联世界中。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有在世界中的对象才是纯粹的对象。但是,说美是纯粹对象的自我显现,是真理的显现,这样的定义并不全面,因为我们势必会追问,“显现”为什么就美?
二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系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审美状态”,他认为美作为显现,总是指在审美状态中的显现,是真理或纯粹客体在审美状态中的显现,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循环解释:一方面美将审美状态带上前来,另一方面只有在审美状态中美才显现出来。对这个循环的唯一的解释是,美的显现就是审美状态的产生,而审美状态的产生也就是美的显现,二者是同一的,二者都超出了自身的限制而相互否定,最终结合为一体。海氏从两个方面论述这种结合。“醉(尼采所说的审美感受状态),那构成主体之状态的东西,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客观的,看作一个实体,对它而言美仅仅是主观的,因为根本就没有美本身。”[1](P123)这是对主体概念的突破,“醉作为感受之状态摧毁了主体的主观性。经由对美的感受,主体已经走出了它自身;它不再是主观性的,不再是一个主体。另一方面,美也不是一种如纯粹表象之客体般的在手之物。作为一种协调,美在根本上决定着人的状态。美突破了处于一定距离、本己而在的‘客体’之限制,把客体带人与‘主体’之本质的、原初的关联。美不再是客观的,不再是一个对象。审美对象既非主观的,也非客观的。”美和审美状态都已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这是在美学领域中对主客二分法的批判和超越,超越的结果是海德格尔把美的问题归结为审美状态的问题。他说:“尼采美学的两个基本词——醉与美,都在同样的角度上指示整个审美状态,指示在审美状态中展开的东西以及充满审美状态的东西”。[1](P123)
对审美状态的这样一种阐释和强调似乎隐藏着这样一种深意:审美状态并非是主体的某种精神状态,而是“存在”的本然状态。美既然是存在者自身的显现,那么存在者自身必然就处在一种纯粹的显现状态中,而这种纯粹的显现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审美的状态——只不过是存在者之允许被审美的状态,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海德格尔可以接受的推论:相对于遮蔽状态而言,审美状态=无蔽状态。只有这样一种解释我们才可以理解海德格尔所说的审美状态是非主体性也是非客体性的。(注:在此,我们认为海德格尔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也就是《康德书》中所体现的思想方法是我们这一推论的佐证,在该书中,海德格尔把康德的先验想象力等同于“存在”,等同于“自然”,而先验想象力在康德的美学中充当着一个本源性的地位,是审美的发生之域,而在此处,在《尼采》中,海德格尔显然也认为审美感受是一个审美发生之域。)这一思想是有新意的,我们对审美状态的惯常理解总是把它同主体的心意状态结合起来,而海德格尔对审美态度的观点,对美的观点把我们引向了一个在他之前没有人问过的问题:事物具于何种状态时候才是可以对之进行审美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现象学问题,也就是问,存在者的何种存在状态是可被审美的?按海德格尔对康德美学的解说,存在者之存在的“显现”就是它的审美状态,也就是说存在者的无蔽状态就是基于其自身的审美状态。
从海德格尔对审美状态的强调中我们似乎可以说“显现”之所以美是因为审美状态,但是审美状态为什么就“美”?说“美”就是无蔽之真理的显现,那么无蔽之真理的显现为什么就美?这两个貌似钻牛角尖的问题追问出了海德格尔关于美和存在之关系的问题。
三
海德格尔认为“美既不能在艺术的问题中讨论,也不能在真理的问题中讨论。毋宁说,美只能在人与存在者本身的关系这个原初问题范围内讨论。”[1](P187)也就是只能从存在论/本体论的角度反思美的本质,这是欧洲形而上学美学的伟大传统,这一传统之伟大,在于它让美超越于一切表面的、日常的和短暂的现象,让美总是以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高的范畴那里得到自身的本质和规定性,从而把美与超越、永恒、深沉联系在一起,隐藏在这一传统背后是这样一些伟大名字: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黑格尔、尼采;构成这一传统的是这样一系列范畴:数、理念、上帝、绝对精神、强力意志。这一伟大的传统的最新成员,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这一伟大传统总是从这样一个角度赋予美以崇高意义,即,作为世界的本源和本质,这些最高范畴以感性形式显现于诸存在者之中,就如神立身于凡人中时有光环显示他是神而非凡人一般,这些感性显现的范畴也有自己的光环,叫做“美”。这个伟大传统赋予了美以伟大意义,对形而上学之最高范畴的膜拜现在在现实生活中变成了对“美”的膜拜,美由于其本体,从来都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它成为了一项崇高的事业,成为了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传统的代表性命题是黑格尔所说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命题的代表性在于,随着最高范畴的更替,这个命题可以置入任何时代,这个命题的现代版,就是海德格尔的“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现身方式”。
“无蔽的真理”就是海氏所说的“存在”,海德格尔认为在“存在”与“美”之间,在人的生存论上有这样一种联系:“对存在的观照是人的本质特有的,因此,只有当我们弄清了对存在的观照不是作为人的一种纯粹的附属物而出现时,他才可能作为一个人被理解。对存在的观照作为他最内在东西而属于他。”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愈是安然地与存在者相处,感到他们自己在存在者中现实性,存在愈是在人面前‘自我封闭’起来,对人而言,存在的封闭性带来的结果是他被遗忘击中。”常常处于存在的被遗忘状态,因此,必须保持对存在的观照。但是,它“很容易被搅乱并被损坏,因为它往往是需要重新恢复的东西。”因此,“需要那种使存在之观照的这种恢复不断复活与维护成为可能的东西,那只是某种直接的,在被遭遇之物的变动外表中显示存在的东西,完全陌生而又是易见到的东西。在柏拉图看来,这就是美。”[1](P189)在海德格尔看来,也是这样。
显然“存在”既是美的本质,也是美的功用,人无法在流变的世界中——领会与观照存在之本质,相反,存在的被遗忘状态却是生活的日常状态,要打破这种遗忘状态,海德格尔将这种伟大的使命给了美,他认为“美是最直接提升我们,迷住我们的东西。美一方面作为一个存在者与我们相遇,同时又解放我们,使我们得以观照存在。美是一种在自身中不同的东西;它可以是直接感性外表,同时又向存在飞升;它既是迷人的,又是自由的。因为正是美将我们从存在的忘却中夺走,并肯定了对存在的观照。”[1](P190)坦率地说这段话并不新鲜,说美是存在之显现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美学的共识,这一传统基本上都把美作为中介和桥梁,都要赋予“美”以形而中的意义,所谓形而中,就是指,一方面美是指具体的感性现实,另一方面,它又可以超越感性现实并显现最高范畴,这一最高范畴在海氏这里是“存在”。以存在的角度反思美,海氏说:“就美最真实的本质而言,它是在感性王国中最闪亮光辉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它作为这种闪光而同时使存在光耀(照亮存在)。存在是那种人们一开始就在其根本上对其抱有喜爱的东西;正是在走向存在的路上,人被解放了。”[1](P191)
对美的本质的这种看法基于对于下面的这句话的阐释,“只有美才享有这一点,即它是最光亮的和最值得爱的东西”,[4](P250d7)基于对柏拉图这句话的阐释,海德格尔把美的存在方式与光联系在一起,这一联系本身就是一个传统,是基督教哲学中的光的形而上学对美的存在方式的阐释,海德格尔就此存在方式这样认为,“美被称之为最光辉的东西,是在直接的、感性的多变外表中光耀四方的东西。”[1](P191)这一思想在伽达默尔那里产生了共鸣,他在《真理与方法》之中的几个论断几乎可以看作是对海德格尔这句话的注解。“美并非只是对称均匀,而是以之为基础的显露本身。美是一种照射。但照射就意味着,照着某些东西,并使光亮所至的东西显露出来。美具有光的存在方式;”“美的东西只是作为光,作为光辉在美的东西上显现出来。美使自己显露出来。实际上光的一般存在方式就是这样在自身中把自己反映出来。光并不是它所照耀东西的亮度,相反,它使它物成为可见从而自己也就成为可见的,而且它也唯有通过使他物成为可见的途径才能使自己成为可见。”[5](P615)
这几句话和海德格尔关于美的看法如出一辙,也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海氏说的“美作为闪光同时使存在光耀”,特别是最后一句,美在本质上就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林中空地,因使它物之存在成为可见的,故使自身也成为可见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前面所说的审美状态与美的统一得到了阐释,二者在本质上都近似于“林中空地”,故此二者是统一的。美之本质是照亮存在,存在之被人喜爱,是因为走向存在之途就是获得解放之路。去掉这句话的逻辑中项,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美之为美,在于人之解放。
美在海德格尔看来是这样一种过程:“美让对立者在对立者中,让其相互并存于其统一体中,因而从或许是差异者的纯正性那里让一切在一切中在场。美是无所不在的现身(Allgegenwart)。”[6](P62)正是这样一种“让并存于统一体中”,决定了美不仅仅是某种显现或者光耀,而是生成意义上的“让……显现”,是让作为整一的存在显现。这就是海德格尔对美所下的另一个定义:“美是原始地起统一作用的整一。这个整一只有当它作为起统一作用的东西而被聚合为整一时才能显现出来。”[6](P162)这显然是一种“体用合一”,“即体即用”的思想,是从美之用的角度对美的规定。当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时,他所说的显现无非是指感性化、具体化,但这种“感性化”、“具体化”又是指什么呢?它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如果说显现就是获得物质形态的话,那么这一“获得”在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获得究竟是指获得什么呢?我们认为海德格尔以上对美的几个定义就是对“显现”与“获得”之内含的揭示,就是这样几个词:统一、聚合、解蔽、光耀、约束。这几个词就是海德格尔对“显——现”这一过程的解说,在下面这个对美的定义中,这一点更为明确:“美乃是整个无限关系连同中心的无蔽状态的纯粹闪现。但这个中心却作为起中介作用的嵌合者和指定者而存在。它是把其显现储备起来的四方关系的嵌合。”[6](P62)四方者,天地神人,美作为显现,就是对四方的嵌合。因此,这一系列的动词:统一、聚合、解蔽、光耀、嵌合,就构成了海德格尔所说的——“美”。
让我们记住海德格尔对美的这一系列定义:
“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2](P276)“美让对立者在对立者中,让其相互并存于其统一体中,因而从或许是差异者的纯正性那里让一切在一切中在场。美是无所不在的现身(Allgegenwart)”。[6](P62)
“希腊人所谓的‘美’就是约束”。[7](P132)
“美是原始地起统一作用的整一。这个整一只有当它作为起统一作用的东西而被聚合为整一时才能显现出来。”[6](P162)
“美乃是整个无限关系连同中心的无蔽状态的纯粹闪现。但这个中心却作为起中介作用的嵌合者和指定者而存在。它是把其显现储备起来的四方关系的嵌合。”[6](P223)
“美乃是存有(Seyns)之在场状态”。[6](P162)
收稿日期:2004-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