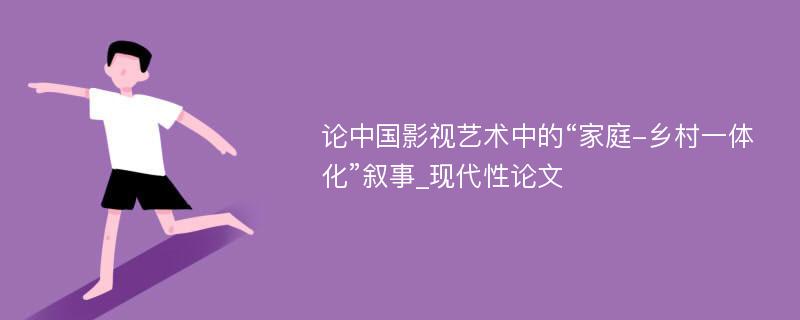
论中国影视艺术的“家—国一体化”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艺术论文,影视论文,国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当前中国影视艺术的生产来说,“古与今”、“中与西”等维度上的矛盾交织、激荡、叠合和生成构成了其现实的规约性语境和重要的文化生态。而在某种意义上,“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可以看作是其中基本的命题。在我看来,如果以此一命题为焦点进行学理层面的拓展、深入和细化,那么,诸如“民族性”、“本土化”、“西方性”、“全球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等重要范畴均可以纳入其视阈内进行观照,并作出相应的读解和阐释。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正确理解还有益于我们在当代语境中自觉地把握中国影视艺术的规律,进而促进影视艺术生产的发展。在这里,本文试从“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辩证考量出发,重点来论述中国影视艺术的一种重要叙事特点——“家—国一体化”叙事,并结合一些典型文本对其美学内涵和艺术特征进行详细阐述。
一、“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辩证关系
作为一种现代艺术样式,中国影视艺术的基本特征就是以其现代视听语言和感性影像系统来表征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在这里,就“现代性”而言,马克斯·舍勒指出,现代性的转变是一种“总体转变”,它既包括社会制度层面的结构性更新,也包括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存体验层面的结构性转变,而且,后者的转型比前者的转型更为根本。[1] 而所谓“体验”,它是指包括人们的感受、情感、欲望、想象、幻想、理智等在内的整个生存直觉,是人们对自身生存境遇与生存价值的深切体认;它往往把切肤之痛与心灵之忧、身体快感与精神狂欢、本能愉悦与超然享受等交织在一起。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尤其是指人们在改革的时代生活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中对自身生存境遇的一种独特感受和体会:它不仅包括精英人物的思想和认识,更包括普通民众基本的日常生活方式、价值规范、审美趣味和心理状态等。对中国影视艺术的创作来说,我们同样可以认为,“正是这种切身体验,构成任何政治或思想大厦的坚实地面。可以说,对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体验,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地面。”[2](P2) 或者说,中国影视艺术的现代性归根结底表现为体验的现代性,正是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构成了中国影视艺术的基本的审美维度。
以电视剧为例,在新时期初期,从噩梦中醒来的中国人沐浴着改革的春风,对革故鼎新的时代精神有着真切的感受,因此,在荡涤积疴、开辟新路的时代潮流中,《乔厂长上任记》、《新星》等作品带有深厚的、狂飙突进的时代烙印,其振聋发聩的主题、锋芒毕露的锐气和昂扬向上的基调,以及针砭时弊、呼唤改革的非凡气势迅捷地表达了人们渴望新生活的现代性体验。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广发展和时代生活的激烈变迁,人们的现代性体验在作品中也折射出新异的面目。比如,《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这一“农村三部曲”把镜头聚焦于变革大潮激荡下关东普通农民的情感波澜,并穿透到“人心”中做文章,谱写了一曲当代中国农民观念更新、迈向现代化征程的悲壮之歌。而像《苍天在上》、《牵手》、《车间主任》、《大雪无痕》、《省委书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品,更是表明了中国电视剧已将艺术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腠理,并细致地表现了人们生存境遇中纷繁复杂而又真切生动的现代性体验。尽管作品大多有着对现代生活中诸多片段、偶然、瞬间的描绘,但创作者却能借助敏锐的感觉,洞察时代生活的主题,捕捉个体人格和个体心理的变迁,进而使片段牵挂着整体,瞬间系缚着时代,让生活表层的偶然现象折射出时代的内在光辉,并浓墨重彩地描绘出世纪转型期人们精神历练的诗意轨迹。由此看来,就当前中国影视艺术的创作来说,创作者要把握和彰显出中国人现代性体验的精神脉络和基调就势必要处理好“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点同时也是我们审视中国影视艺术民族特色与现代品格的逻辑起点。
然而,在面对“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时,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艺术理论,我们常常陷入“首尾两端”的泥淖,进而常常呈现出诸多艺术失衡现象,并引发出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比如,有些反映当代中国改革的电视剧作品“将复杂的人际关系两分化,简单地把剧中的人物设计为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两大营垒。”有的作品则“将现实的体制弊端道德化,人为地把改革中遇到的阻力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归结为思想品质恶劣、道德作风腐败的个别干部的违法乱纪。”有的作品甚至“将纷繁的历史运动纯净化,习惯地靠单向思维把新旧杂陈、各种单向力相互作用的现实生活形态,净化为我们在理论框架上归纳出来的社会矛盾模式,用抽象的历史理由来随意裁剪多姿的生活现象和‘合力’运动。”[3](P110) 有的作品“诱使观众把改革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个别英雄人物身上,”它们“虽然写的是当代生活,却恰恰缺少时代感和当代性。”[4](P28) 这不能不说与人们对“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理解密切相关。
在这里,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5](P535) 我们认为,在处理“传统性”与“现代性”两者之间的关系时,“传统性”要有“现代性”的维度,“现代性”要有“传统性”的维度。具体说来,在两者交织、激荡、叠合、生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辩证地观照以下几个层面:第一,“传统性”与“现代性”是同时进行的两个“过程”的属性描述,其中,前者着重“传统”的传递过程,后者着重“现代”新元素的入进过程,因此,在考察任一特性时都应该把一体之两面的另一特性放入考量的架构之中,并经由两者的恒常互动去审视其内在的质素和品格;第二,在具体的观照中,我们要将“历史/文化/社会”的情境作为基础,同时,又要以“现代性”为基本视点和旨归,以便探讨“传统”是如何在受到一些“新元素”的刺激、影响下作出某种程度的改变而成为“现代”的;第三,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仅必须注意我们原有的“传统”是什么,了解哪些是阻碍发展的,哪些是促进发展的,以及传统得以加速改变的可能途径,而且,还必须认清哪些是影响传统的“新元素”,以及它们通过诸如“接纳”、“排斥”、“回归”、“反思”、“整合”等环节对传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第四,我们还要审视这些“影响”经由一个有选择能力和变通能力的自主个体既把传统秉承了下来,又作出了创新的转化,进而形成了怎样的、新的、现代的价值信念体系与生活方式,产生了什么样的“现代”及现状。[6](P57)
应该说,对“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这一辩证考量具有实际的意义。就中国影视艺术表征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来说,我们借此可以看到,“家—国一体化’叙事”是中国影视艺术一种重要的叙事特点。对此,我们接下来可以结合一些典型文本对其美学内涵和艺术特征进行详细论述。
二、“家—国一体化”叙事的美学内涵
我们知道,中国有着悠久的家—国一体化和政治—伦理一体化的历史文化传统:一方面,国家政治通过家庭/社会伦理而进入现实人生,并借助对伦理道德规范和典范的肯定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伦理的规范性和道德的自律性又转而成为了政治秩序及其稳定性的维护和说明。弗·詹姆逊曾说:第三世界“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7](P235) 在这里,如果我们不将“民族寓言”的内涵仅仅理解为狭小的政治投射,而是可以包含更为深广的本土意识和本土问题,以及民族形式的深层因素,那么,将某些中国影视艺术文本看成是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就有其适切性。而这种“适切性”又会进一步向我们敞开关于“家—国一体化”叙事的意义面向,即,在审美的维度,“家—国一体化”叙事往往通过家庭的悲欢离合来寄寓民族/国家的盛衰变迁,进而使观众在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的过程中接受文本中隐含的意识形态。
在中国影视艺术的艺术实践中,“家—国一体化”叙事的运用有着充足的历史、美学原因:第一,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审视,正像“国家”一词所显示的,“国”与“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中,“国—家”融合、“家—国”一体铸就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孔学,或曰仁学,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和代表。”[8](P20) 而这种以“仁”为核心的社会人生理想,具有浓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理性色彩。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作为一种深层积淀的民族文化结构和集体无意识力量,它至今依然有形无形地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价值取向。第二,从艺术传统的角度考量,有学者认为,有关“家—国”故事的伦理喻示是“中国绝大多数电影工作者创作的基石。这种伦理结构是结构的结构——处于最深层的能动结构。[9](P36) 事实上,在电影艺术中,从郑正秋、蔡楚生到谢晋,“家—国一体化”叙事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其“能动结构”往往以家庭为中心场景而展开广阔的人生境界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并将家庭的悲欢离合与民族/国家的盛衰变迁紧密结合起来,从而生动形象地映照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社会的兴衰起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姊妹花》、《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创作实绩的取得与“家—国一体化”叙事的运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第三,从文化属性的角度来考察,作为一种现代艺术样式,影视艺术具有鲜明的“大众性”,换言之,影视艺术是一种大众审美文化形式。尤其是电视剧,作为一种“家庭艺术”,一方面,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风波可以映照出整个社会和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家—国一体化”的叙事策略和机制在社会文化与审美心理层面极大地尊重了中国老百姓的审美习惯,因而,其民族特性和现代品格与大众性、平民性、通俗性等有着相当契合的面向。
就电视剧而言,《有泪尽情流》可以说是一部成功运用“家—国一体化”叙事的典型文本。在叙事模式和叙事结构上,作品主要围绕几个家庭而展开,其间,又重点塑造了马小霜、白羽屏、田立春、周家文等几个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但在艺术形象的美学意涵上,创作者没有将这些人物的悲欢离合局限于“家庭”的一隅,而是将其放置在改革开放以来深广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进行审美观照,进而构成了作品特定历史时期“个人—家庭—社会”立体化的伦理关系图景。具体而言,如果说“家/个人”是作品叙事的起点和中心,那么,“国/社会”则是其落脚点和重心,即,作品从“家/个人”出发,却没有使笔墨“伸缩于描写身边琐事和人民生活之间,”“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10](P242) 而是将改革开放以来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都推为背景,把马小霜们的家庭生活、爱情婚姻、人生际遇和时代生活联系起来,并在这波澜壮阔的背景上描绘了她们“下岗”后“困惑—奋斗—新生”的心路旅程,展现了她们心理状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诸方面的深刻嬗变,这就使得作品以其所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广度而超越了题材本身。不仅如此,尽管作品在叙事模式和叙事结构上借鉴了传统,但其内容却有着深刻的现代性转换。和传统的艺术表现相比较,作品中“家庭”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虽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和谐,但有本质的不同。在五四时期,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呼吁彻底砸烂旧的象征秩序和政治文化,求助于新的象征秩序和政治文化;巴金的《家》更是把成年巴金的思想与信仰投射到少年觉慧的身上,并成就了一部论证新文化运动合法性的民族寓言;“文革”结束后,以“伤痕”、“反思”等形态出现的许多作品也往往通过“家”的悲欢来检视十年“文革”所留下的阴影与创伤……尽管以上不同时期的文本对家庭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审美观照有着不同的形态,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社会”是作为“家庭”的压制性对立面而存在的,但是,《泪》剧所展现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现实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对以往那种压制性结构力量的否定与纠偏。这就使得《泪》剧升腾出一种深刻的哲理,并成为我们审视当代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形象文本。
实际上,《泪》剧一开始就借助女主人公“抢抓”男性用品的一场戏展现了一个典型的“家—国”寓言。就马小霜及她当时的家庭生活条件来说,她去抢抓一堆男性用品的行为是令人费解的。然而,在这里,如果我们在叙事的表层将马小霜行为和动机的分离看作是现实生活逻辑标准下的“不真实”,那么,这种“不真实”恰恰对艺术逻辑标准下的“真实”起到了突出和放大的效果:一方面,马小霜没有去“抓”的必然性(更遑论动作的执著与夸张),二方面,马小霜还根本不知道她“抓”到的是什么,因此,这庶几可以表明,马小霜不合情理的行为强调的只是她“抓”的意念本身——这无疑可以看作是她在丈夫死去,自己下岗,生活与心灵陷入双重困顿之时的预言和预演。不仅如此,这种“抓”的意念还可以折射出“马小霜们”那种随社会转型而来的心理真实,那种在惶惑、迷惘和无情的生活激流中“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般的生命本能的真实。如果我们更进一步从当代中国文化现代性的高度来审视,那么,对那些置身于当今时代生活中的芸芸众生而言,“抓”的意念还浓缩着一个关于第三世界人生处境的民族寓言——一个充满着失落与诉求、传统性与现代性、现实性与未来性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式文化价值冲突的民族寓言……
三、“家—国一体化”叙事的艺术特征
综观中国影视艺术的创作,“家—国一体化”叙事在许多作品中都有明显的表现,那么,在艺术特征上,它又有着哪些显著的表现呢?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第一,“伦理泛情化”的叙事策略。
苏珊·朗格曾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把艺术符号化的作用就是为观众提供一种孕育感情的方法。”[11](P51~458) 实际上,“情感”是人性中最普遍、最本质的内容,而情感的小视角又可以折射出社会生活的大视阈,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伦理泛情化”就成为了中国影视艺术“家—国一体化”叙事的题内应有之义:一方面,“家—国一体化”叙事借助大众文化的“煽情”技巧就可以开辟一条打动大众、赢得大众的艺术传播通道,进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目的;另一方面,“家—国一体化”叙事中的伦理情感往往是一种突出的社会功利性的情感,它不只是通过讲述一个善恶有报的古老寓言来对观众进行一番情感抚慰,而是特别注重通过普通人物的情感变迁来折射社会现实矛盾和时代风云,尤其是其充沛的社会/政治激情可以缝合进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图。
在这里,检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些电视剧作品,我们就可以看到,无论是塑造“人民公仆”的作品,还是表现“当代模范人物”的作品,它们大都有着家庭/社会伦理关系的叙事线索,并以“利他与利己”、“爱与恨”、“义与利”等伦理冲突来编织叙事结构,用煽情场面来设计叙事高潮,用道德典范来完成人格的塑造,用伦理情感来包装意识形态,最终将平常或不平常的事迹转写成一个个充满道德伦理意味的人生故事,进而通过人物忍辱负重、重义轻利的道德节操和苦难、坚贞的伦理情感来唤起观众心理上的认同与感情上的共鸣,使人们在受到情感抚慰和心灵滋润的同时也得到思想的陶冶与道德的提升。比如,在《好爹好娘》中,由于“人民公仆”不再具有“卡里斯玛”式的超人力量,或得到其他超人力量的庇护,因而,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无奈与困境,“人民公仆”们往往通过那种任劳任怨、兢兢业业、自我牺牲的政治信念和价值观念来影响叙事结构中对立双方的力量对比,通过道德品质和伦理感化来争取矛盾各方的支持和理解。在作品中,基于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田茂林忍辱负重、委曲求全,默默地在生产建设的第一线尽职尽责,无怨无悔。而实际上,这种在“身陷困境的主人公”与“民众的拥护”,“主人公的感人事迹”与“民众的敬仰”之间进行“正反拍”的修辞手法也确实取得了令人倾心服膺的思想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其次,在《农民的儿子》、《郭秀明》等作品中,史来贺、郭秀明们都堪称是时代的楷模,民族的脊梁,但创作者却很少展示他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立场,甚至政治业绩、领导能力这些按常规应该着力表现的东西都被淡化了,相反,作品将一个个充满苦涩意味的英雄模范事迹转写成一个个现代伦理故事,并极力渲染主人公们无私奉献、集体本位和鞠躬尽瘁的道德境界,以及他们身上闪耀的普通人的品性、传统的美德、崇高的节操和与老百姓血肉相连的感情,进而,在极富人情色彩的煽情中使观众接受这些形象,同时,也接受他们所负载的意识形态倾向。
由此可见,中国影视艺术的“家—国一体化”叙事中,“伦理泛情化”一方面使作品的意识形态主题注入了伦理情感,另一方面又把意识形态内涵融入到动人的剧情中;一方面使作品不直接宣传政府的政策、方针,另一方面又通过向大众文化的靠拢,变宣传教化为潜移默化,使政治倾向赢得了观众的认同,并进而强化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合法性。这对于具有悠久伦理传统的中国来说,确实具有特殊的意义和效果。
第二,着重于“家庭”、“社会”、“政治”的三种叙事结构。
诚如上文所述,在某种意义上,“家—国”故事的伦理结构是中国绝大多数电影工作者艺术创作中的“能动结构”。在这里,进一步进行仔细地加以甄别,这种“结构”还可以细分为三种分别着重于“家庭”、“社会”和“政治”的三种叙事结构。
有研究者在研究“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的创作”时指出:“从郑正秋、蔡楚生到谢晋等,他们的电影创作构成了一种一脉相承的伦理情节剧创作传统,”并在其发展和演进中形成了鲜明的美学追求和艺术特征。[12] 在这里,如果从“家—国一体化”叙事的叙事结构角度审视,郑正秋、蔡楚生、谢晋电影创作的突出特点和不同可以概括为他们是分别着重于“家庭”、“社会”和“政治”三点之上。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差异也显现了电影艺术“传统”与“现代”的嬗变轨迹。
郑正秋作品最突出的审美原则就是具有浓厚的、鲜明的“家庭”伦理色彩。其作品主要以家庭或社会伦理为题材内容,以人物的悲欢离合为中心,并借助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使作品中的家庭伦理关系折射出社会性的主题。比如,《孤儿救祖记》、《姊妹花》等。当然,30年代以后,由于当时特殊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等原因,以及左翼电影创作思想的影响,郑正秋肯定并热情称赞“前进的批评家的努力”,希望努力发挥电影的社会作用,使“电影负着时代前驱的责任,使它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舆论,彼此互相推动,从社会的心理建设达到社会的环境改造。”[13](P4) 因此,在其艺术视野不断扩大的同时,其作品中的社会真实性内容也不断加厚。而蔡楚生的创作既与以往的艺术形式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但同时又有着明显的区别。这集中表现为,蔡楚生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扭转了20年代重点表现传统家庭伦理道德冲突的方向,并朝着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尖锐矛盾的目标前进,因此,在主题内涵上表现出极其强烈的“社会”伦理色彩。比如,在思想内容上,《渔光曲》富有真实感和深刻性。作品刻画了贫苦的渔民与富裕的渔主之间的对立,以贫苦渔民悲惨生活和不幸命运唤起观众的巨大同情,这就给人物的戏剧性命运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感情基础。《一江春水向东流》则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深沉的时代感和历史感,以及史诗性的宏大构思和艺术概括力,深刻地揭示了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的现实面貌,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内容庞杂、头绪众多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关系浓缩到家庭的命运变迁中,并以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对社会矛盾和政治理想进行了审美观照。而在谢晋那里,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其“家—国一体化”叙事往往把人物的命运和社会生活、时代剧变紧紧扭结在一起,并偏重于“政治”的一面。比如,《天云山传奇》“从50年代中叶写到1979年,用一个漫长的历史背景来展示,细腻地揭示了恋人、夫妻、同志、朋友的内心世界;写了不同遭遇、不同性格的人物之间不同命运的矛盾冲突,而且,把每个人个性的形成同整个世界的变化紧紧地结合在一起。”[14](P81) 而《芙蓉镇》中的社会、时代、政治等内涵更是空前地深邃、厚实。作品将艺术的视点对准了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命运起伏不定的人物的心灵深处,把人性的善恶、美丑与不同时期的政治浪潮相交融,从“芙蓉镇”这一小镇上几个普通人物十几年的命运浮沉和变迁中,折射出人性的被扭曲,并以此来反思历史,剖析现实,进而透视整个民族在那段无情岁月里的历史性的苦难和创伤……
第三,“交融性”和“交叉性”的二种叙事形态。
检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电视剧创作,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作品因娴熟地运用了“家—国一体化”叙事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当然,由于语境的变迁和艺术的发展,“家一国一体化”叙事在继承的基础上还呈现出发展的一面。在这里,依据“家”与“国”在作品中的存在形态和喻指关系,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交融性”和“交叉性”两种叙事形态。
就“交融性”的“家—国一体化”叙事来说,其中的“家”与“国”是融合在一起的,换言之,有关“家”的故事投射出的是“国”的民族寓言。比如,在《情满珠江》中,作品从“文革”一直写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它以一个家族为纽带,以一个男人与三个女人的情感冲突为叙事线索,描绘了一幅幅社会生活与人心、人情的变革画卷。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人们的痛苦往昔,可以看到生活奇迹般的变化,还可以看到走上富裕之路的人们又经历着怎样的灵魂挣扎和精神洗礼……在这里,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等这些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二元对立都通过“家—国一体化”的叙事而转化为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在《有泪尽情流》中,马小霜们“困惑—奋斗—新生”的心灵历程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进程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可以营造一个温情脉脉的家(马小霜),或可以勉强维持或保留一个家(田立春、郑秀水),那么,随着计划经济时代不可逆转地远去,马小霜们就必须重新踏上建构新的“文化家园”的漫漫历程。
就“交叉性”的“家—国一体化”叙事而言,其中的“家”与“国”是并行存在,交叉发展的,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烘托、相辅相成的关系。比如,在《省委书记》中,政治经历和家庭生活两条线索齐头并进、交叉互补,而外部动作的纵横捭阖与人物内心的细微刻画使处于困境中的贡开宸形象显得真实而丰满。在这里,“交叉性”的“家—国一体化”叙事使作品拥有了双重的表现视角:一是表现出某种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命题;二是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为着眼点,展现出主人公的情感世界,进而使人物和所述之事更富有亲和力和感染力。可以说,在近些年的改革剧作品中,这种“双重视角”普遍存在。再比如,在《和平年代》中,在处理“家—国(军队)”关系上,作品超越了以往那种要么将家庭关系作为叙事的附件和铺垫,要么将家庭关系游离出军队生活的局限,并特别以秦子雄为中心编织了一张高密度的人伦关系网:
秦子雄:“红箭”大队大队长
闻皓夫:军长、秦子雄的岳父
闻璐:军区报社记者、秦子雄的妻子
闻勇:军部参谋、后任“红箭”大队教导员、闻璐的哥哥
章大军:原“红箭”大队教导员,与秦子雄自幼即为朋友
慕容秋:海军歌舞团副团长、原与闻勇是夫妻,后离婚;与秦子雄曾有过恋爱关系;离婚后又与章大军有感情纠葛
……
正是在这种高密度的人伦关系网中,作品的叙事既以“军人家庭”及其人物关系为背景和依托,又流转于家庭与军营之间,“情场”与“战场”成了军人们生活状态与职业状态的两极,也正是在这种由亲情、爱情和军事、国防交织而成的叙事中,“家—国(军队)一体化”的叙事收到了实际的效果:一方面,家庭与事业的冲突反映出时代变迁的丰富信息,另一方面,“主旋律”的思想意蕴以生活化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并且,在作品细致、绵密的叙述中,当代军人“家国一身事”的立体形象得到了突显。而这既使人物的生活充满了人情味,也使其“主旋律”叙事有着实在的生活附丽。
有学者在论述当代中国的“文化现代性”时指出,文化因素的多元并置使得“任何单一的文化因素和文艺现象往往丧失或根本不存在其典型性。”这庶几可以表明,“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向现代化迈进的艰难进程之中,其文化模式和价值结构还有待于形成现代品格或现代性。”[15](P3) 显然,21世纪的中国文化不再是以必然性的结构来推演其历史行程,毋宁说是多种叙事话语拼合而成的精神地形图。然而,“文化现代性”又并非一个搅拌机,并非任何一种叙事话语都可以扔进去搅拌了事,因此,就中国影视艺术的“家—国一体化”叙事而言,最关键的还是要回到叙事话语发生、发展的变动过程与具体环节,以便看到它在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同时,又包含着内在的分离、转折与断裂,看到它在复杂的历史情势中所表现的可能性,以及那些发展的脉络,那些更新的动力所标示的趋向。
标签:现代性论文; 艺术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电影叙事结构论文; 文化论文; 寓言论文; 社会论文; 家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