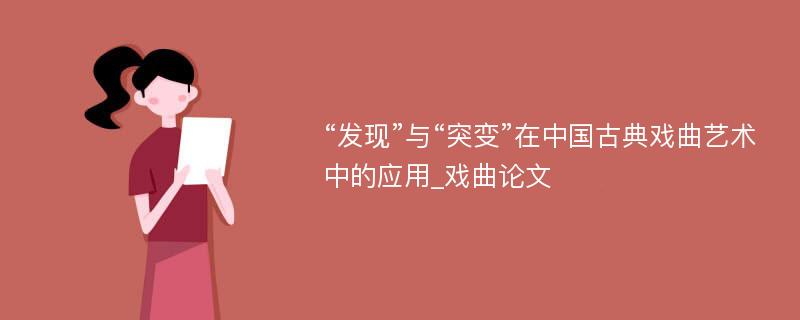
“发现”与“突转”在中国古典戏曲艺术中的运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中国论文,古典论文,发现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现”与“突转”本是源出于西方戏剧美学理论范畴的两个重要概念术语,我们这里将它们引入我国古典戏曲的研究,并非有意强拉硬扯,穿凿附会,故作新奇时髦之谈。因为古今中外的戏剧,尽管特色纷呈、各有千秋,然而在戏剧创作的基本理论与艺术技巧、手法诸方面,却又毋庸置疑地必然存在着许多相似、相通、相同之处。比如“悬念”这一西方戏剧理论推崇备至的概念术语,在元杂剧的创作中虽然没有它,但若就具体创作实践而论,可以说元杂剧的剧作家们实际上早已经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着这种技巧、手法,并且业已取得了相当良好的艺术效果。(注:关于中国戏曲对“悬念”使用的研究文章举不胜数,例如姜明吾《浅论戏曲“悬念”的设置》,见《陕西戏剧》1983年第2 期;许金榜《元杂剧中“悬念”的运用》,见《艺谭》1983年第3期。 )有鉴于此,笔者这里亦不揣浅陋,拟就有关中国古典戏曲对“发现”与“突转”的运用问题抛一管之见。未妥甚或谬误之处,企望方家学者斧正。
一、对“发现”“突转”的释义及其阐发
在正式行文之前,首先对“发现”与“突转”的两个关键词语作一番梳理廓清、诠释及阐发,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是我们深入探究有关问题的前提与基础。
“发现”与“突转”从字源上考证,均出自于《诗学》。众所周知。《诗学》是西方先哲亚里斯多德在熟悉并研究业已出现的大量优秀剧作基础上,着重针对古希腊戏剧(主要是悲剧)之艺术成就与创作经验给予及时总结和高度概括的一部理论性巨著。它所总结和概括出的许多理论原则,对后世戏剧创作产生了重大的指导、借鉴作用与持久深远的影响力,雄霸西方文坛达两千年之久。其中“发现”与“突转”,便是亚氏对古希腊戏剧家在结构布局、安排情节方面所成功使用的两种独特技巧、手法的准确把握与精辟界定。
何谓“发现”?亚氏对它的解释是“指从不知转变到知”,(注:亚里斯多德《诗学》“第十一章”,转引自《文艺理论论丛》1958年第2期。)并举出了《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 《俄狄浦斯王》两剧为例证。前者主要剧情是描写伊菲革涅亚不知俄瑞斯特斯的底细,险些误杀了他。后来她得悉他的真实身份——原来竟是自己的亲弟弟这一特殊人物关系的“发现”,遂使得一场流血悲剧得以避免。后者的关键性情节则在于报信人无意中披露出俄狄浦斯的身世,导致“杀父娶母”内幕的昭然若揭这一事件真相的“发现”,便无情地将悲剧主人公俄狄浦斯——那位万民拥戴的贤明国君推至毁灭的绝境。
“发现”有哪些种类(或曰情形)呢?亚氏划分出了五种,具体包括:第一,凭标记的;第二,剧作家任意安排的;第三,由回忆引起的;第四,由推断而来的;第五,从情节中产生出来的。亚氏非常推崇第五种,认为这种尽量摒弃纯粹偶然性(如第一种发现)或主观随意性(如第二种发现)等因素,在情节的发展进程中依循可然律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发现”是最好的,就象《俄狄浦斯王》中“杀父娶母”真相的“发现”那样,“能通过合乎可然律的情节引起观众的惊奇”。
依据亚氏的上述见解,我们可以对“发现”的涵义及其特征加以补充性的说明与阐发:所谓“发现”,系指剧中尚未被人们(或剧中人,或观众;但相对而言,应主要是针对剧中人的)所知晓的某种(或某些)特定、特殊人物关系,以及某种(或某些)事件端倪(或曰内幕、真相)的披露与挑明。人物关系与事件端倪两者比较而言,应侧重于前者,换言之,即“发现”主要是对某种(或某些)特定、特殊人物关系的发现。(这里有必要提醒人们注意,前面例举的《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真相的披露,其实须首先有赖于俄狄浦斯真实身份——“身世”的“发现”;若无俄狄浦斯与先王及王后的那种父子和母与子之特殊人物关系的重大“发现”,“杀父娶母”的真相或许仍将潜形匿影,而永远不会为人们所知晓!)
那么,何谓“突转”呢?对此亚氏解释为:“指情势向相反的方向转变……从顺境到逆境(一般指悲剧)或从逆境到顺境(一般指喜剧)……是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而发生的”(注:亚里斯多德《诗学》“第十一章”,引自《文艺理论论丛》1958年第2期。 )亚氏仍以《俄狄浦斯王》一剧为例:剧中报信人原本为着除俄狄浦斯的恐惧心理,孰料“事与愿违”:他的一番话无意中恰恰披露出俄狄浦斯的真实身份。戏剧情势由此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使俄狄浦斯从处于主动追查杀害先王凶手的顺境,陡然跌入极其被动、尴尬而又无可逃避的逆(绝)境中,逼迫他不得不承受因“杀父娶母”的罪责而招致的严厉惩罚!
根据亚氏有关“突转”的论述,我们同样可以并应当这样来理解和看待“突转”:系指戏剧情节在其发展进程中,依循可然律或必然律的内在逻辑性,而产生的“由顺境至逆境、或由逆境到顺境”(亚里斯多德语)的突然变化与重大转折。即如前述“发现”主要是侧重于指对某种(或某些)特定、特殊人物关系的“发现”那样,“突转”因其着意于情节发展的那种突发性逆转和变异,故而主要应限于情节的范畴。
二、“发现”与“突转”在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无“名”而有“实”
对西方戏剧理论经典——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作了一番考证之后,我们不妨再回过来浏览一下中国的戏剧理论。中国戏剧的发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以其独具华夏民族特色、自成一派体系的“戏曲”艺术著称于世。中国古典戏曲宛若一座博大精深、浩瀚幽遂的文化宝库,其中拥有着形形色色、无限丰富的戏剧专用术语,什么“生、旦、净、末、丑”,或者“当行、本色、冲场、吊场、砌末、收煞”等等,可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简直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如果搜寻一下有关“发现”与“突转”的专门阐述(注:参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李修生主编的《元曲大辞典》、陆澹安编著的《戏曲词语汇释》、袁世硕主编的《元曲百科辞典》等。),其结果却未免不尽人意:我们直接找不出这一专门的概念术语,顶多是从一些戏剧理论家的散言断句中,可约略窥见到“发现”与“突转”某种朦胧、模糊的面影。如“格局之妙,令人且惊且疑”(注:(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引自吴毓华等编《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253页。)“一转再转,每于想穷意尽之后见奇”(注:(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引自吴毓华等编《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253页。)“格善变,词善转,便是能手”(注:(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引自吴毓华等编《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253页。)“迩来词人,每喜多其转折,以见顿挫抑扬之趣。不知太多,领观者再索一解未尽,更索一解,便不得自然之致矣。”(注:(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引自吴毓华等编《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253页。)“《琵琶记》出神入妙处,……只就本题一字播弄(意即所谓“不离本题”——笔者注)……愈转愈妙,愈出愈奇,斯其才大手敏,诚有不可及者。”(注:(清)毛纶《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总论》,引自吴毓华等编《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306页。)
尽管古典戏曲理论中明显匮乏“发现”与“突转”的专门术语,但它们作为中国古典戏曲剧作家们最惯常运用的结构布局、安排情节的重要技巧、手法,却又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客观存在。
中国古典戏曲中成功运用“发现”技巧、手法的事例举不胜举,这里仅以《赵氏孤儿》(悲剧)、《望江亭》(喜剧)等剧作稍加说明,《赵氏孤儿》的故事背景是春秋时期晋国权佞屠岸贾陷害忠良,将老臣赵盾满门抄斩、唯有襁褓中的孙儿(即“赵氏孤儿”)一脉尚存。剧中以力欲斩草除根的屠岸贾为一方,不惜身家性命的程婴、公孙仵臼、韩厥等忠臣义士为另一方,围绕着“孤儿”展开了一场曲折惊险、摄魂夺魄的“搜孤”与“救孤”的殊死较量。剧中一个至为重要的关键点即在于“孤儿”真实身份的“保密”,(针对屠岸贾及孤儿而言:倘若屠岸贾早已发现此秘密并杀了那个孤儿,恐怕也就不会有这出闻名中外的大悲剧了)该秘密一直拖延到孤儿长大成人的二十年后,才由程婴吐露出来。这一人物关系的“发现”敲响了权佞屠岸贾的丧钟,也为那场腥风血雨的忠奸斗争最终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得悉内情的“孤儿”遂亲自擒拿奸贼,报仇雪冤!《望江亭》主要剧情是写花花太岁杨衙内久已觊觎谭记儿的美色,风闻她与秀才(后中状元,任潭州县令)白士中缔结良缘,便欲加害。皇帝偏听偏信其诬告而颁下“标取白士中首级”的敕书和势剑金牌,杨衙内奉旨一路赶来问罪。值此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面对已悉知凶讯而一筹莫展的丈夫白士中,谭记儿于中秋之夜只身闯险,巧扮风流渔妇,在望江亭上将好色贪杯的杨衙内及其走卒播弄得神魂颠倒,趁势智赚势剑金牌与敕书。当次日杨衙内洋洋自得地闯入县衙,欲拿白士中治罪之际,不料才发现手中的武器——势剑金牌和敕书早已丢失。此“发现”使得原先这位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钦差变成好不尴尬、狼狈不堪的被告,不得不摇尾乞怜;白士中夫妇则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关于“发现”的种类问题,我们在这里也稍予说明。由于剧作家设置于剧情中的“结”大大小小、各种各样,因此剧作家为解“结”而使用的“发现”相应地也会有大大小小,是多样化的。此就是说即使是在同一部戏剧中,剧作家也可能多次使用“发现”手法。如《望江亭》中实际就是前后写了几次“发现”:杨衙内对假“渔妇”谭记儿的暗送秋波当成自己的“情场得意”,此属于一种错误的“发现”;杨衙内在公堂上意外“发现”手中的武器——势剑金牌和敕书不翼而飞;垂头丧气的“落汤鸡”杨衙内最终又“发现”那风流渔妇正是县衙夫人谭记儿!导致剧情发生“突转性”效果的“发现”,我们不妨称之为“大发现”,其余的那一些“发现”则可称其为“小发现”。(如《望江亭》中的前后两次“发现”即可叫做“小发现”,中间那次“发现”则应称作“大发现”)由此来看剧作家究竟应在情节发展的哪个环节上运用“发现”才最好的问题便简单得多了:一般说来,那些“小发现”大都可设置于戏剧的开头、剧情发展的中间阶段等等,而“大发现”则通常多安排在戏剧的高潮阶段(往往与结局较临近)。此外,“发现”之中以哪种情形最为上乘呢?当然应是那种能引起“突转”的“发现”,(一般属于“大发现”)即如亚氏指出的“能同时引起‘突变’的那种‘发现’”。由于这个问题在文章后面部分将详尽论述,故此处从略。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戏剧中,巧妙运用“突转”的范例可谓俯拾皆是。如川剧《乔老爷上轿》中写白面书生乔溪半路之上,被恶棍无赖蓝木斯误当成女人抢拉上轿,企图霸占,使乔溪身陷尴尬困境之中。正当他焦灼不安、苦于无法脱身之际,不料花轿被误抬入蓝木斯妹妹蓝秀英的闺房之中,由此发生灾消福降的“突转”:蓝秀英问明真相后,对乔溪顿生爱怜之意,并与之双双拜堂,喜结良缘。再如京剧《秦香莲》中“杀庙”一场戏写的是,韩琪奉驸马爷陈世美之命前去暗杀秦香莲母子,秦氏母子毫无反抗能力,恐必惨遭毒手无疑。观众不由得会替她们母子二人暗暗担忧。但情节发展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突转”,其结果偏偏与观众的预料、猜测适得其反:韩琪从秦香莲那里问明事实原委后,非常同情她们而实在不忍滥杀无辜;但若不杀人又无法回去交差,只得拔剑自刎。秦氏母子非但大难不死,反而掌握了陈世美蓄意杀人的确凿证据——那把钢刀。这一“突转”直接促成了后来秦香莲状告公堂、包公断案“铡美”的结局。
关于“发现”与“突转”在中国古典戏曲中的这种无其“名”而有其“实”,推究起来也许并非仅为中国戏曲艺术所特有的一种现象。现实生活中常见这样一类饶有趣味的事情:一个孩子呱呱降生,其父母由于望子成龙心切,搜肠刮肚地要为他起一个如雷贯耳般响亮动听的名字而终末得,就很可能把“命名”事宜暂时搁置一段甚至较长的时间。但人们并不能因该孩子暂时无“名”,就否定其作为一个鲜活生命个体的存在!纵观中外文学史,亦不乏此类无“名”而有“实”的典例:象十九世纪三十至九十年代末兴盛于欧洲文坛、成就斐然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流派,在当时就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而是到二十世纪之初才由前苏联文学奠基人高尔基所提出,并为大家普遍接受并约定俗成下来。当然中国古典戏曲中存在着许多无“名”有“实”现象,与其自身发展的历史,尤其是戏剧艺术的发展同作为其升华的戏剧美学理论的发展之间不合常规的“非协调性”,是密不可分的。众所周知,中国戏剧的产生较之于欧洲要晚得多:欧洲早在古希腊时代就迎来了一个戏剧艺术高度成熟并空前繁荣的壮观景象;而中国戏剧的真正成熟是直到元代以元杂剧为标志。作为戏剧艺术之升华的戏剧美学理论的产生亦然:欧洲戏剧在其第一次戏剧艺术高潮之后不久,就诞生了对其进行及时总结、高度概括且以富有创新性和体系性、能够对后世戏剧艺术的发展及其繁盛产生持久深远的“导向”式重大影响力的戏剧美学(或曰哲学)理论巨著——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而中国戏剧美学理论的初步成熟,已是在元杂剧衰落许久的明清时代。一般说来在一种成熟的戏剧艺术形态产生之后,通常总会伴随而来有关的理论性研究并出现与之相应的较为成熟的戏剧美学理论。但中国古典戏剧艺术与戏剧理论研究之间的发展却呈现出一种整体上不合常规的“非协调性”——成熟形态的戏剧艺术在中国并未能出现与之相应的成熟的理论性研究及其戏剧美学理论。作为成熟形态的中国戏剧所经历的元代杂剧、明代传奇、清代地方戏三阶段,仅仅在其中间阶段出现过局部性的接轨贴合,此即明传奇时代戏曲创作同戏曲理论批评得到较为密切的结合。中国传统的戏剧理论研究,多散见于各式各样的笔记、诗歌、文章、序跋之中,专门性论著甚少(严格说来,李渔的《闲情偶寄》也难以称得上一部地地道道的戏剧理论专著),其理论涵盖的深度与广度及其影响力,无疑都是相当狭窄而有限的。即使到了属于中国戏剧理论较为繁盛的明清时代,象何良俊的《曲论》、王世贞的《曲藻》、徐渭的探讨南戏源流与发展的《南词叙录》、魏良辅的论述昆腔声乐原理的《曲律》、王骥德的全面阐述戏曲音律问题的《曲律》等,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往往如散金碎玉,不成体系,仍未脱评点式的稚嫩状态。真正改变中国戏剧美学理论稚嫩状态的要推李渔的集中中国古代戏剧理论之大成的《闲情偶寄》的问世。作为一位具有丰富戏剧创作和舞台演出经验的清代剧作家,李渔广泛汲取了前人的理论成果,联系其时戏曲创作的现状,并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在“词曲部”和“演习部”里对戏曲理论予以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和阐述,使《闲情偶寄》得以成为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发展史上最富有概括性、体系性的著作,代表了中国戏剧美学理论的最高成就,尽管李渔探索建树中国戏剧理论体系的开拓之功不容低估,但他的某些见解观点依然属于因事而发、就事而论的随笔、偶感与心得,因而显得零乱、重复,有时难免蜻蜒点水,仅仅看到外表现象,未及深入到本质性的探究。即如他对戏剧结构问题的探讨。在创作理论上他推重结构与格局,扭变了历来人们把词采、音律视为剧本创作的全部内容的风气,这一点弥足可贵。所谓戏剧结构,不仅是指剧本的结构,而且是指舞台行动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组织。李渔所说的“结构”,正是指剧本的构思应能适应舞蹈行动的完整性。他在“词曲部”中讲述“结构第一”、“词采第二”、“音律第三”、“宾白第四”、“科诨第五”、“格局第六”,这些显然是指文学剧本的结构。我们这里仅仅试图从现代戏剧美学这所谓“戏剧构思”的具体层面上来理解把握“结构”问题。李渔主张戏剧结构务使承上启下、血脉相连,着重崇尚传神和风韵,即所谓“重机趣”:“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针对情节的安排设置,提出“密针线”、“脱窠臼”、“戒荒唐”等一些基本原则与技巧、手法:而在格局方面,他较为详尽地涉及到戏剧开场、收场(即大收煞、小收煞)、第一折、主角与配角在折间出现的关系等问题。对上述有关问题,由于李渔能大多从如何适应观众心理与契合戏剧结构自身需求的视角出发,因而不乏科学性的真理意蕴,很大程度上谙合戏剧艺术的内在规律性。但即使是这样一部集大成之作的戏剧论著,也令人遗憾地未能对“发现”与“突转”问题展开较之以往清晰明澈的解释,它所能给予人们的充其量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暗示。此具体见于如下两段论述:“宜作郑五歇后,令人揣摩下文,不知此事如何结果。……戏法无真假,戏文无工拙,只是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戏法、好戏文。猜破而后出之,则观众索然,作者赧然,不如藏拙之为妙矣,”(注:李渔《闲情偶寄》,引自张生筠《县念:戏剧结构的重要艺术手段》,《牡丹江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水穷山尽之后, 偏宜突起波澜。或先惊而后喜,或始疑而终信,或喜极、信极而反致惊疑。务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备,此为到底不懈之笔”。(注:李渔《闲情偶寄》,引自张生筠《县念:戏剧结构的重要艺术手段》,《牡丹江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这里虽然在李渔主要是讲述戏剧的“悬念”问题, 但象“突起波澜”、对“想不到、猜不着”的戏剧“下文”的“猜破”,在涵义上与“突转”和“发现”还是大致存在着某种显而易见的对应性。
三、“发现”与“突转”为中外戏剧家惯常使用的原因探略
中国古典戏剧作家们在高度重视并大力使用“发现”与“突转”方面,为什么会与外国剧作家不约而同、不谋而合?这种“雷同”现象究竟于神使鬼差般的偶然巧合,还是自有其戏剧艺术内在规律性使然?对此我们理应加以辨析。
先谈“发现”问题。常言道“事出有因”。为什么剧作家在结构布局、安排情节时必须要使用“发现”这一技巧和手法呢?那是因为剧中存在着为人们(剧中人或观众,以前者为主体)尚不知晓、但对剧作家而言又必须得在合适的时机(即剧情发展进程中的某一重要环节、关键点上)向人们披露与挑明的,某种(或某些)特定、特殊人物关系以及事件端倪(或曰内幕、真相)。亚氏在《诗学》第18章第1 节中曾提出过“结”与“解”这两个重要概念:“结”是指剧外情节(交代往事)和从开场到情势转入顺境(或逆境)的部分;“解”则指的是从转变开始到终局的部分。在笔者看来,剧中尚未被人们所知晓的某种(或某些)特定、特殊人物关系以及事件端倪,其实便堪称剧作家在剧中精心设置下的最大且最重要的“结”,而“发现”正是此“结”被“解”不可或缺的中介与途径。
那么,剧作中的“结”在情节发展进程中“发现”来临之前,究竟是对剧中人与观众暂且都“保密”好呢,还是仅仅对剧中人暂且“保密”更妥当呢?应当看到,这两种“保密”情形都是存在的。第一种,所谓“对剧中人与观众暂且都保密”,也就是把观众与剧中人都蒙在鼓里,使之如坠迷雾中茫然不知,暗中探索。即如布瓦洛所说的:“要纠结得难解难分,把主题重重封裹,然后再说明彰显,将秘密突然揭破,使一切顿改旧观,一切都出人意表,这样才能使观众热烈地惊奇叫好”(注:布瓦洛《诗的艺术》,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页。)第二种, 所谓“仅仅对剧中人暂且保密”,就是让剧中人物间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扭结,而观众对此一目了然,如狄德罗所言:“可以使所有角色都互不相识,但得让观众认识所有的角色”(注:狄德罗《论戏剧艺术》,见《文艺理论译丛》1988年第 1期。)两种做法以谁最为可取呢?在亚氏那里是肯定后者,如他在《诗学》“第十四章第四节”中所言,“当时不知情,事后才发现。如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伊菲革涅亚及时发现俄瑞斯特斯是她弟弟”。而狄德罗借助比较更是推崇后者:“由于守密,剧作家为我安排片刻的惊讶;可是由于把内情透露给我,他却引起我长时间的焦虑……对霎那间遭受打击而表现颓废的人,我只能给以霎那间的怜悯,但假如打击不是立刻发生,假如我看到雷电在我或者别人头顶上聚集而长时间地停留于空际不击下来,我将会有怎样的感觉?”(注:狄德罗《论戏剧艺术》,见《文艺理论译丛》1988年第1期。) 狄德罗身同体感式的分析无疑是十分正确而合理的,因为它更符合一般观众对戏剧的观赏心理:希望剧作有清晰明了的情节、脉络分明的线索、长时间的(可理解为环环相扣的)悬念(亦即所谓“结”),自始至终牵系着他们欲知分晓的迫切期待与“解谜”心理,直至帷幕落下。正因如此,古往今来的戏剧,除了极少数以专门追求离奇怪诞、惊险刺激效果为能事的一类之外(如西方近代出现的所谓“巧凑剧”),一般均采取只对剧中人“保密”的结构布局。
既然如上所述,剧中人多为剧作家蒙在鼓里,人物间彼此不知底细(只有观众是通晓内情的),那么如何自然而巧妙地使用“发现”这一技巧、手法,也就成为衡量剧作家结构布局之艺术性高下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就无怪乎中外剧作家们如此那般地重视对“发现”的运用了。
“突转”之所以倍受中外剧作家们的青睐,究其实或许与它较之于“发现”富有更多自身所独具的艺术功能有很大关系。概括说来,“突转”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独特艺术功能:
第一,可造成戏剧情节的曲折多变、跌宕起伏、一波三折,并获致某种出奇制胜的强烈戏剧性效果。
常言道,斗转星移,始可见东方欲晓之奇景;风谲云诡,方显出波浪起伏之壮观;抑扬顿挫,往往金声而玉振;山重水复,每每柳暗而花明。就戏剧而言,惟其有了“突转”,遂使得戏剧情节的发展富有了一种动态中的“曲线美”:时而象“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的奇峰突起,时而又似“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幽谷蜿蜒。如此若石径穿云、盘桓迂行,于“山塞疑无路”之绝处,达“弯回别有天”之妙境。而每每为剧中人及观众所始料不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那种“突转”,常常总发生于戏剧矛盾冲突异常尖锐激烈的关节上,可谓雷声骤鸣、波澜突起,能造成观众“或先惊而后喜,或始疑而终信,或喜极、信极而反致惊疑”(注:李渔《闲情偶寄》,转引自吴毓华等编《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第340页。)因而最富于那种山奇胜制、 撼人心魄的强烈戏剧性效果。
第二,有助于揭示、挖掘人物性格和表现、深化剧作的主题意蕴与思想内涵。
“突转”具有上述功能是因为,适逢“突转”之际,往往便是戏剧矛盾冲突发展至激化喷发的高潮,而高潮恰恰又总是人物性格得以最充分呈示、主题思想得以最集中展现的时机。如前面所述《秦香莲》“杀庙”一场毫无反抗能力、似乎必死无疑的秦氏母子竟安然无恙,本来应该让别人死掉的刺客韩琪自己反倒命丧黄泉(自杀)。这一场“突转”不仅扣人心弦,同时也将人物的面目与性格凸现得鞭辟入里、活灵活现:陈世美的借刀杀人,足以暴露出其寡廉鲜耻、丧尽天良的丑恶嘴脸,及其阴险狡诈、毒如蛇蝎的性格特征;而韩琪对无辜的秦氏母子的不忍加害,乃竞至自戕之举,则最充分彰显出他的同情弱小、心地善良、嫉恶如仇、舍生取义的侠义性格。常言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然而在反动腐败的统治阶级当权的黑暗年代里,要做到这一点却又是非常不容易的。如川剧《卧虎令》写东汉光武帝姐姐湖阳公主的内监总管唐丹一惯依权仗势、无法无天、作恶多端。元宵佳节之际,他在花灯闹市纵马行乐,踩死一观灯民女。百姓捉住他评理,他非但不思悔改,反又肆无忌惮地将另一无辜少女活活打死,激起极大公愤。京都洛阳令董宣受理此案,他利用唐丹有恃无恐的心理诱使其画押招供,判定死罪。本来案子至此便可了解,但剧作家为了更进一步地揭示与深化“惩恶锄奸、呼唤正义”的主题思想,却巧妙地运用了“突转”手法:即将行刑之际,传来“押送朝廷御审”的圣旨。董宣心时明白“御审”就是不审,乃放虎归山。他虽为正直清官,但无奈王命难违,不由得内心矛盾重重。经过一番犹豫踌躇,不得不违心地推翻原判,改为“不予处死,但须厚葬死者,安抚死者亲属。”这一“突转”向人们照示出“惩恶锄奸”、为民伸冤之正义斗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大大突出并深化了剧作的主题意蕴与思想内涵!
通过观瞻成功运用“突转”的大量中国古典戏曲作品,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归纳出某些规律性,此即剧作家在其创作中运用“突转”时应当遵循的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关于“突转”的设置(即在剧情中的“位置”)问题。“突转”究竟应该用于情节发展的哪一个阶段才好呢?这应根据每个剧作情节发展的具体情况来设置,或前或后,或居于中间,常各有所不同。故不能一概而论、强求一律。如《打金枝》是将“突转”用在了戏剧开端,《白蛇传》是置于中间(第三场“惊变”)《西厢记》也是在中间稍后(第四折“赖婚”)。《赵氏孤儿》则将“突转”(具言之即程婴待“赵氏孤儿”长大成人的二十年后,才把内情和盘托出,屠岸贾遂由“赵氏孤儿”百般爱戴崇仰的养父,陡然转变成其不共戴天的冤家死敌)推迟到了戏剧的最后一幕。
第二,“突转”应力求做到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因为一方面,“突转”如果不能超出通常人们的意料之外,恐会落平庸无奇之俗套,难以动人心魄、引人入胜,而另一方面,“突转”倘若不合乎情理,则可能蹈滑稽荒诞之辙,无法令观众信服。这里要做到合乎情理,最关键的一点便是“突转”应牢牢地以人物性格为内在依据。高尔基曾指出:“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如果说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是“土壤”,那“突转”便是生长于这片沃土之上的一株奇花。剧作家如果脱离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求“突转”而故意兜圈子绕弯子,其结果只能是弄巧成拙,经不起推敲,严重背离了艺术真实,因而必定缺乏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如《秦香莲》“杀庙”中的“突转”,既直接关系着剧中人物的生死存亡,并以其如山洪暴发不可遏制的态势,方推波助澜地促成戏剧高潮——“铡美”的到来,同时它也决定着全剧结构布局的成败得失。惟其居于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要求这场戏即要“转”得忽然新奇,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同时又须以人物性格为依据,具言之即韩琪不杀秦氏母子反而自戕,契合其心地善良、同情弱小、嫉恶如仇、舍身取义的侠义性格,“转”得自然天成,让观众感到合乎情理。否则,“一节偶疏,全篇破绽出矣!”(注:李渔《闲情偶寄》,转引自吴毓华等编《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第355页。)
第三,应恰当处理好“突转”与“铺垫”之间的关系。任何一种类型的戏剧,其情节发展“由顺境至逆境至顺境”的转变,从总体格局上讲属于一种渐次进行(即所谓“渐变”)的节奏模式,剧情的发展呈现为由量变到质变,亦即从“渐变”至“突变”的嬗变轨迹。此“渐变(量变)”相对于“突转(质变)”而言,一般也就是所谓“铺垫”。没有铺垫,也就难以有“突转”,铺垫是“突转”的前提与基础,“突转”乃为铺垫之合乎逻辑的某种自然发展。故而如何恰当地处理好“突转”与“铺垫”之间的关系,便显得至为重要。李渔就曾谆谆告诫剧作家们“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欲其照应,欲后者,便于埋伏”。(注:李渔《闲情偶寄》,转引自吴毓华等编《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第342页。 )《西厢记》堪称中国古典戏曲中巧妙处理“突转”与“铺垫”两者关系的一部不朽杰作。该剧中的“突转”无疑应是“赖婚”:即崔夫人悍然抵赖原先准允女儿许配张生的承诺,而突然改让莺莺对张生“以兄妹相称”。此“突转”给早已彼此互有情意的一对恋人不啻当头泼了一桶凉水,使之顿然惊慌失措、一筹莫展;也委实令观众瞠目结舌、始料不及。该场戏发生在第二本第四折,属于全剧中的第八折。在它之前七折的剧情就崔张二人爱情发展来看乃处于上升阶段(即“顺境”),但其间也小有波澜,而这些波澜恰恰正是剧作家王实甫为“赖婚”一折的大波澜(即“突转”)所作的必要而有力的铺垫。第一,从老夫人的“贯串性动作”(指人物对某事物或问题的一贯态度与表现)来看。她对莺莺是暗遣女仆红娘“行监坐守”,可谓时刻监视、处处防范,惟恐女儿做出什么不轨之事来。自然对女儿与张生的那种“自由恋爱”根本不放在眼里,反而嗤之以鼻、横加指斥。由此说来,老夫人的恪守封建礼教、看重出身门第,正是其后来翻脸不认帐的思想源所在。第二,从“寺警”(即“白马解围”)与“赖婚”的顺承关系来看。《寺警》一折写叛将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欲强行霸占莺莺,否则将对寺庙内的所有人尽行杀戳。莺莺提出如有人能退敌解围、情愿结秦晋之好的计策,无计可施的崔母无奈之下只能同意。这里剧作家非常明确地在向观众表现,崔母的许婚极其勉强,完全是出于被迫无奈的(而非主动的)。因为堂堂相国府三代不招白衣女婿,怎能想象赘个落魄秀才?仅仅因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难临头,火烧眉毛,权且先保全性命要紧,其他的一切尚可暂容后图。正是在这种心理驱策下,老夫人遂降格以求。所以一俟贼兵退去而大难消解,她就很快恃权仗势,自食其言,悍然赖婚(仅允许两人存在“以兄妹相称”的关系)。可见,老夫人的“赖婚”之举早已有所蓄意,是有着一定心理准备的,贴合其思想、情感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因此决非出于那种一时心血来潮式的偶然。
四、对“发现”与“突转”之关系及其两者与戏剧内容之间关系的辩证审察
以上笔者对“发现”、“突转”的分别探究,仅是出于行文论述的方便。实际上,两者之间有着难以分割的某种内在联系。亚氏十分推崇“发现如同时引起突变(亚氏亦将此称作“发现与突转的拍合”),那是最好的形式”。这里就相当明确地指出了两者之间所存在着的那种内在逻辑性联系:由于“发现”而引起“突转”,前者为因,后者为果,两者构成明显的因果嬗变关系。遍览古今中外的优秀剧作在艺术上的成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往往都与剧作家注意妥善处理并写出具有因果关联的“发现”与“突转”密不可分。象《俄狄浦斯王》中正是由于俄狄浦斯“身世”的发现,才使得这位贤明国君陡然由顺境跌入逆境,不得不为“杀父娶母”的罪责而承受毁灭性的惩罚:刺瞎双眼、放逐他乡。中国戏剧作品中如《白蛇传》里许仙为了揭穿法海的谎言,以证实妻子根本不是什么蛇精,屡屡用黄酒敬劝,执拗不过的白素贞饮后药性发作而显出真形。此“发现”使夫妻关系陡然间发生了逆变突转:由原来的恩爱笃深变成产生严重的裂痕,许仙竟对妻子弃置不顾,径直跑到金山寺里去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另一方面在于,“发现”与“突转”在《诗学》中虽主要是被亚氏作为戏剧结构布局、安排情节的技巧范畴(亦即“形式”因素)来探讨的,但它又并非单纯属于某种“技巧”(或手法)的形式方面的问题。亚氏本人就曾指出:“悲剧所以能使人惊心动魄,主要靠‘发现’与‘突转’,此二者是情节的成分”。他认为戏剧(以悲剧为例)包括六个组成部分(即“六成分”),“结构”(即布局,情节安排)首当其冲,最为主要;而结构之中又尤以“突转”最为关键。这里亚氏实际上是在不知不觉中又把“发现”、“突转”当作构成戏剧情节的某种内容因素来探讨,这种似乎彼此有些矛盾的见解,其实涵盖着某种深刻的辩证性内核,是很有一些道理的。事实上也常常的确如此。因为无论“发现”或“突转”,就全剧结构而言,它们乃为整个情节发展链条上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堪称某某场面或细节;而若具体就剧中人物关系来看,它们往往是某一组外部或内心动作的总称,隶属于某种“行动”。如果我们将戏剧情节结构比喻为一个完整的圆,那么“发现”与“突转”便是该圆环上不可分割的某段“弧”。这里“形式”本身便等同于“内容”;也就是说“发现”与“突转”,其实早已经成为戏剧内容(即情节)中无法剥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在推崇主要作为某种结构布局、安排情节的重要技巧、手法的“发现”与“突转”的大前提下,不妨也应该将其视为某种戏剧的内容因素,这样的认识或许能更辩证而全面。
标签:戏曲论文; 戏剧论文; 艺术论文; 俄狄浦斯王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赵氏孤儿论文; 闲情偶寄论文; 望江亭论文; 李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