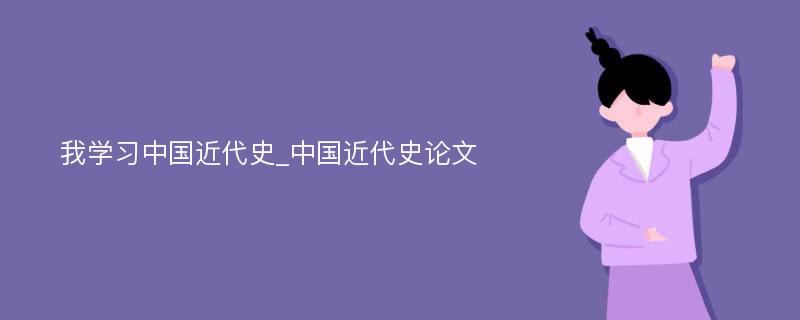
我学中国近代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学论文,中国近代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我正在北平华北大学二部史地系学习。8月下旬的某一天,系主任尚钺同志约我到办公室谈话,主要内容是副校长范老(人们对范文澜同志的惯称)主持的历史研究室准备从学员中挑选几位旧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本科生去读研究生,研习中国近代史,享受供给制待遇,他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去。范老是当时名满天下的著名历史学家,无论学识、人品,都是我极为崇敬的偶像,所以很爽快地答应服从组织安排。于是我和傅耕野、刘明逵、高大为、王涛等7个人经范老亲自调阅档案后被选中。9月初,我们就到设在东厂胡同的研究室去报到。
一、“二冷”精神
历史研究室是华北大学所属的一个研究机构,由范老兼任主任,有20几个人,编制很简单。研究人员只分研究员与研究生两级:一些从老区来的长者都是研究员,我们先后调进来的年轻人都是研究生。范老亲自主持全室的研究工作,指定刘桂五同志管思想和生活,荣孟源同志管业务学习。除范老一人享受小灶待遇外,大家都是吃大灶,集体住,只有周六可以回家,周日必须回来开生活检讨会,管理制度相当严格。
在我们报到的第二天,范老召集全室人员开会,除了讲研究室的传统和规章外,他以很大一部分时间讲“坐冷板凳”和“吃冷猪肉”的道理。他要求我们以这种“二冷精神”去做学问。他可能从我们的眼光里看出我们对“吃冷猪肉”困惑不解,所以又操着绍兴官话比较详细地阐释了“吃冷猪肉”的含意。原来过去只有大学问家才能有资格在孔庙中的廊庑间占一席之地,分享祭孔的冷猪肉,而要成为大学问家的第一步,是能“坐冷板凳”去苦读。至今想来,范老这次“二冷精神”的教导,对我一生的读书学习,一直起着重要的影响。的确,以往许多大学问家都是“坐冷板凳”坐出来的,汉朝的董仲舒成为大学问家,就在于他“三年不窥园”。范老没有止于“二冷精神”的言教,更重要的乃在于身教。在从师范门时,我们都集体住在东厂胡同1号的后院厢房,范老自居前院,终日坐在大玻璃窗下攻读,似乎是有意监督学生们,不让乱上街,以渐渐养成“下帷苦读”的习惯,真是用心良苦。每当我们想偷偷溜出去从他窗前经过时,范老总是手不释卷,笔不停挥,时不时抬头望一下窗外,我们只好惭愧地退回去,不久也就没有人再做这种试探了。范老还规定,工会分发影剧票,研究生一律不参加,以免分心。我们开始总是坐不住,或是坐在椅子上胡思乱想,久之也就不再心猿意马,而习惯于坐冷板凳,书也读得进去了。这就为自己一生从事学术工作奠定了硬件的基本功。
二、专攻一经
我在大学读历史专业时,重点放在汉唐这一段,没有听过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课程,对近代史可谓知之甚少。如今安排我转攻中国近代史,真不知从何入手。看了一些陈恭禄、贾逸君等人写的旧中国近代史著作,仍然找不到门径。乘一次给范老送资料的机会,我贸然向他请教入门途径的问题,范老很温和地让我坐在对面,说:“你是援庵(陈垣)先生的学生,应该懂得‘专攻一经’的道理。”我惭愧地回答:“我的近代史知识很浅薄,不知选哪部书去读。”范老想了一想对我说:“你就从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入手,要随读随写笔记,以便日后使用时翻检。笔记可以不太追求文字的严整。”当时我根本不知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是何书,但又拘谨得不敢再问,唯唯而退。后来我向荣孟源同志请教,才从资料室借到此书,为了谨慎从事,我没用公家发的黄草纸订本,而是特地买了一册较正规的笔记本来写读书笔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前后一共连续读了一年多,写了足足3册笔记,每朝1册,可惜在“文革”时期,被愚昧的勇士们扔到书堆里烧毁,只剩下压在满地堆积的杂物堆下的第1册,至今有时抚读,犹感黯然,一面怀念师恩,一面惋惜我当年的辛勤。从残留的这册笔记中可以想见当年的治学痕迹,笔记的第1页记着全书的概况: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八十卷
中华民国十八年故宫博物院用抄本影印
大学士文庆等纂辑 杜受田是始受命者
咸丰六年九月进呈
范围:
进呈表:“自道光十六年议禁鸦片烟始,至二十九年英夷不进粤城通商受抚止。先后十四年间,恭奉上谕、廷寄以及中外臣工之折奏,下至华夷往来之照会、书札,凡有涉于夷务而未尽载入实录者,编年纪月,按日详载,期于无冗无遗。”
凡例:
“谕旨谕内阁者十之二三,谕军机大臣者十之七八。”
“谕旨标明谕内阁字样,廷寄谕旨标明谕军机大臣等字样,同日连奉谕旨数道标明又谕字样。”
“疆吏奏章准驳均经胪载,其奉旨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者,覆奏亦经详载。惟仅交该部议奏者,多系照例之事,该部俱有册档,覆奏概未载入。”
“各省钦差大臣及沿海督抚照会、夷酋公文有关筹办机宜者,一并附载……择其稍有关系者,照原文附录于各折之后,以存其实。”
“宣宗成皇帝庙讳概以甯字恭代。”
“凡原当标题某日者一律改书甲子。”
我在笔记本首页记这些内容是为便于了解和阅读全书,因为这些就是全书的序(进呈表)和凡例。这就养成我以后每读一书时,必先读序跋、前言和凡例的习惯。
这80卷读书笔记的每条记录,有多有少,后半部分由于逐渐熟练,写得比较简要,兹举例如次:
卷一
(1)道光十六年丙申四月己卯,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鸦片烟禁。(p.1-4)
……
(5)十月甲寅,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奏:反对弛禁提出弛禁之害有戾于是非者三暗于利害者六。要求皇帝“察其是非,究其利害,立斥弛禁之议,仍请敕下在廷诸臣,悉心妥议,于烟入银出有可永远禁绝之方各陈所见。”(p.1-4)
这些条前的号码是文件编次的顺序,年后的干支是甲子纪年,月后的干支是日期,最后的括号内号码是书中的页次,提要中是要点,如系原文则加引号。经过如此认真细读后,我不仅初步掌握了鸦片战争以来重要史实的脉络,而且熟悉了重要的历史人物、有关事物的联系、清朝文书制度等等。有些似懂非懂的内容就别纸记录,留待从他书中去追查,如文件中常见的“廷寄”字样,虽然从《凡例》中约摸知道,这是皇帝不经过内阁的文书程序,而是经由军机大臣直发受文件者,具有一定的机密性,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后来读到《枢垣纪略》一书时,有一条有关廷寄的材料说:
上谕亦有二:巡幸、上陵、经筵、蠲赈及内臣自侍郎以上,外臣自总兵、知府以上黜陟、调补及晓谕中外,谓之“明发”;告诫臣工、指授方略、查核政事、责问刑罚之不当者,谓之“廷寄”。“明发”交内阁,依次交于部科;“廷寄”交兵部用马递,或三百里,或四五六百至八百里以行。
于是对廷寄有了较详的了解,后来也对学生做过解说。
大约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我把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粗粗地通读了一遍,写了3册笔记,颇有所得。虽然后两册和我的其他手札笔记等均被烧毁,但仅此劫余1册在日后仍获益滋多。后来我又读了《清季外交史料》,上下贯串,近代史事脉络,大体清楚,再读其他成著,就深感便捷。有时并能由此触类旁通,知道许多近代的重要历史人物及其观点论述,引发我进而读更多的书,掌握近代史事,中国近代史遂成为我终身学术工作的核心。抚念及此,深感范老的师恩难忘。看来专攻一经不仅有奠定基础之效,且能由此伸延博览,令人有可能迈入学术殿堂。可惜这种看似繁难实为捷径的方法,并不为一般学子所接受。
三、从根做起
我们到研究室最早分配的工作是整理人城后移送和收缴来的北洋军阀档案。成立了一个档案整理组,有贾岩、唐彪、傅耕野、王涛、陈振藩、房鸿机和我等人,贾岩和唐彪任组长。整理地点在黎元洪花园的八角亭里。这批档案是从未整理过的原始档案,杂乱无章,尘土飞扬,又没有很好的卫生措施。一天下来连眼镜片都被灰尘蒙得模糊不清,但当时革命热情很高,只知道服从工作需要,从无一人抱怨。彼此看到对方的花脸也只相视一笑。大约经过4个月的光景,袋装档案文件已按形式分为私人信札、公文批件、电报、电稿、密报、图片和杂类等扎成无数捆上了架。继而将对档案进行史料分类整理,人员有所增加,地点也搬到干面胡同一所宽敞的院落中,工作条件也大为改善。就在工作程序转换之际,室里集中了几天学习理论和有关北洋军阀这段历史的书籍。范老也在这时与大家座谈过一次,他对大家的辛劳表示慰问,讲了档案与研究工作的关系等等,其中有一段活,我印象深刻而且终身受益。范老讲话的大意是,从档案中搜求资料如披沙拣金,确实很艰难,但这是研究工作“从根做起”的重要一步。只有这样,才能基础广泛而扎实。从此“从根做起”的教诲就深植于我的头脑之中。
整理档案工作开始之后,我们将档案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四大类,下面还有一些二级类。每个人把一捆捆档案放在面前,认真仔细阅读后,在特制卡片上,写上文件名称、成件时间、编号和内容摘要,并签上整理者的名字,然后按类上架。这次因为经过第一次的去污整理,工作室环境也较好,大家心情舒畅,常在工间休息时和宿舍里交流阅档所得,相互介绍一些珍稀有趣的资料。有时我认为很有用的内容,还在第二天去追踪查原档,随手抄录下来,日积月累,我渐渐地积累了两册黄草纸本的资料。同时为了查对档案中的事实和加深拓宽这方面的知识,我又读了大量有关北洋军阀的著作,眼界逐渐开阔,钻研问题的信心也日益增强。并了解到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很好地展开,以往一些著作多半过于陈旧,而且数量也不甚多;而新著又几乎没有,有关论文也只是零星短篇。因此,这确是一块颇有开发价值的用武之地。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整理档案工作已接近尾声。我对北洋军阀这一近代的政治军事集团从兴起到覆灭的了解,已有了一个大致轮廓,对错综复杂的派系关系也掌握了基本脉络,奠定了我将以一生绝大部分精力致力于北洋军伐史研究的基础。半年多的整理档案工作虽然比较辛劳,但收获是很大的。这一专题性的整档阅档工作,不知不觉地把我带进了从未完全涉及过的学术领域,极大地影响了我一生的学术道路。不久这批档案南迁至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当时名为史料整理处),唐彪、王涛等人随同南下,另一部分人另行分配任务,我则应南开大学之聘到天津工作。
1951年春,我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后不久,主讲中国近代史的吴廷璆教授奉派赴朝慰问,就把课程交给我,幸亏我有前此那段“专攻一经”的功底,竟能不负所托地承当此任,而在吴先生回国后,因见我已有承担的能力,便明确由我主讲中国近代史,一直延续下来,于是中国近代史就成为我在教坛上的主讲课程之一。与此同时,我并未放弃我对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工作。到津的第二年,我在《历史教学》杂志上连续发表题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讲课记录,虽然还不很成熟,但却是我第一篇北洋军阀史方面的专文。从此正式进入北洋军阀史研究的程序。与此同时,我还受荣孟源等同志的委托,在津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收集有关图书,这项工作后虽因人事变动而中辍,但我却意外地接触了不少有关北洋军阀的资料,为我日后撰写《北洋军阀史略》做了必要的准备。
1957年,我完成了《北洋军阀史略》一书的编写。这是经荣孟源同志推荐,由湖北人民出版社邀约,我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文的基础上,加以扩大、改订和充实,历时年余而完成的。我在撰写过程中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将北洋军阀集团的兴衰变化作为一个历史整体进行考查,探求其成败兴亡的内在联系。这部著作虽然篇幅不大,但它是我的第一部专著。我很自信它为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开拓了新领域,也为后来学术界研究这段历史做了点基础工作。这部书也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注意,日本先后有两家出版社出版日译本,成为一些有关学者案头的参考书。
在《北洋军阀史略》出版后的20多年中,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项工作几近中断。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氛围大为改观,许多新知旧雨频加关注敦促,希望我重整旗鼓,增订《北洋军阀史略》。我也深感时代的支持和鼓动,燃起了重理旧业的热火,于是搜集资料,选用助手,拟定方案,重新撰写,并对研究对象、编写范围、分期问题、特点地位进行充分研究,着手增订,终于在1983年完成了36万余字的《北洋军阀史稿》。这部新著不仅比《北洋军阀史略》在篇幅上增加3倍,条理较前清楚,论证较前缜密,而且论述范围也有所扩展。我充分自信,《北洋军阀史稿》在当时确是这一领域惟一的一部专著,对军阀史和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北洋军阀史稿》完成后,很自然地引起我30年前参与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的情思,而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希望丛刊成为完璧。我接受了这项任务,从1986年开始,组织人力,搜集资料,整理标点,特别是不忘情于挖掘档案。经过7年的努力,至1993年全书告成。这套资料共分5册,第1至4册系按北洋军阀的兴亡历程分4个阶段,并围绕各阶段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选编六七十万字资料,各成1册。第5册则包括军阀人物传志、大事记、书目提要、论文摘要与附表等。总字数达300余万,补足了全套丛刊资料,也了却我30多年的愿望。
一套资料,一部史稿,应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基本完备结题;但我隐隐感到,这项“从根做起”的研究工作,似乎还留有微憾。于是我决心重新改写《北洋军阀史稿》,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通史性著作——《北洋军阀史》。从1994年起步,我在我的几位学生和两位日本学者的共同参与和研讨下,拟定章节,撰写要点,搜集资料,分头撰写初稿,然后统一体例,损益增删,润色文字,六易寒暑,终于在2000年完成了这部百余万字的世纪之书——《北洋军阀史》,并交付出版。这部新著较之《北洋军阀史稿》显有改观,篇幅约增3倍,内容颇多更新充实,虽尚难称尽善,但已尽我心力。
我对北洋军阀史的研究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漫长路途,堪以自慰的是感到此生没有虚耗,因为我做了一件有益于他人的事。但我更不能忘怀的是,当我初涉学术门径时,范老要我以实际行动从事“从根做起”的磨练,在漫无边际的档案海洋中,摸索寻求题目、方向,甚至是一生的学术事业。
“从根做起”确实艰难烦劳,不易“立竿见影”地获得效应;但我极其真诚地希望:有志于学术的后来的学者们,能在将要步入学术殿堂之际,不妨“泡”在档案之海中,“从根做起”,去寻求自己的学术未来!
我没有系统的治学经验,只是应编者之约,零散地谈些在学术道路上感受最深的两三点,但这些确是我一生受用无穷的两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