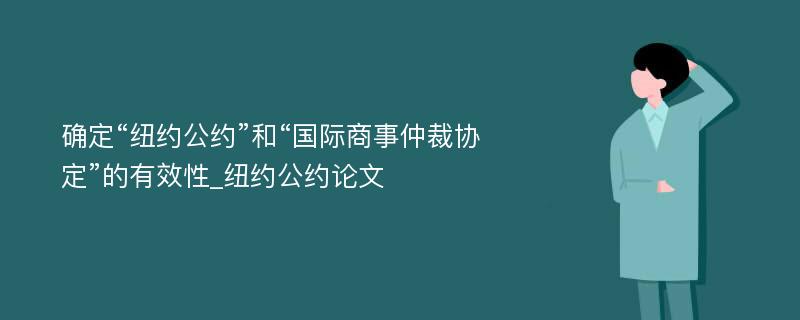
《纽约公约》与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事论文,纽约论文,公约论文,效力论文,协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09)07-0006-05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是从事国际商事交易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就他们之间在此交易中已经发生或者将来可能发生的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协议。仲裁实质上是解决争议的契约制度。当事人同意把他们之间已经发生的或者将来可能发生的争议提交给作为私人裁判官的仲裁员或者仲裁庭仲裁解决。而作为一项合同安排,仲裁应当受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支配,至少理论上如此[1]。各国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关于如何认定国际仲裁协议的有效性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此问题上并不存在普遍的国际公约。
在各国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的立法与实践中,由于各国国内法对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作了不同的规定,导致不同国家的法院和仲裁庭对同一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作出不同认定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法院和仲裁庭都适用什么样的法律决定国际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其法律依据是什么,发展趋势又如何,始终是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中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结合联合国在纽约主持制定的1958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① 关于仲裁协议的相关规定和中国内地有关国际仲裁协议有效性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对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及其认定,作一评述。
一、《纽约公约》对仲裁协议的相关规定
《纽约公约》对仲裁协议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公约第2条和第5条。
第2条的规定是:(1)当事人以书面协定承允彼此间所发生或可能发生之一切或任何争议,如涉及可以仲裁解决事项之确定法律关系,不论为契约性质与否,应提交仲裁时,各缔约国应承认此项协定。(2)称“书面协定”者,谓当事人所签订或在互换函电中所载明之契约仲裁条款或仲裁协定。(3)当事人就诉讼事项订有本条所称之协定者,缔约国法院受理诉讼时应依另一方当事人之请求,命当事人提交仲裁,除非法院认定上述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者不能履行。
《纽约公约》第2条首先规定了缔约国法院应当承认与执行当事人之间业已订立的仲裁协议,且仲裁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在当时情况下,仅列举了当事人签署的或者互换函电中载明的仲裁协议。随着电子计算机和因特网的普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了《电子商务示范法》和《电子签名示范法》,在这两个示范法中,书面形式被赋予了广泛的含义,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以及其他一切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均可以认定为书面形式。联合国贸法会在2006年修订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中,也反映了电子技术的发展对仲裁协议的书面形式的影响,因而对仲裁协议的书面形式作了更为广泛的规定。此外,该条第3款还规定了缔约国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关于诉讼事项属于仲裁协议项下的管辖范围时,应当令当事人将此事项提交仲裁解决,但法院认为仲裁协议无效者除外。也就是说,如果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无效,就可以对协议项下的事项行使管辖权。据此,《纽约公约》还是将认定仲裁协议有效性的问题交给了各国法院。
公约第5条第(1)款第(1)项规定了缔约国法院在被请求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时,如果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证明,签署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根据应对其适用的法律为某种无行为能力者,或者裁决所依据的仲裁协议根据当事人约定适用的法律为无效协议,或者在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法律的情况下根据裁决地国的法律为无效协议,执行地法院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依据上述五项仲裁协议作出的仲裁裁决。至于缔约国法院如何根据《纽约公约》关于决定裁决所依据的法律而认定仲裁协议无效,则留给了被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家法院决定。
二、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认定的适用法律
尽管《纽约公约》将决定仲裁协议有效性的问题留给了各国法院,公约对如何确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的适用法律,还是做了规定。这一规定主要体现在第5条第1款(a)项中。据此规定,当事人向执行地国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公约项下的裁决时,如果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该裁决作依据的仲裁协议当事人根据对其适用的法律为某种无行为能力者,或者协议依当事人共同选择的应当适用的法律为无效,或者未指定此项法律时根据裁决地国的法律为无效仲裁协议的,执行地国的法院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该裁决。
根据《纽约公约》的上述规定,我们可以将确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的适用法律,解析如下:
(一)关于签署仲裁协议的当事人行为能力的适用法律
如果仲裁协议的签署者在签署此仲裁协议是根据应当适用的法律为无行为能力者,则其所签署的仲裁协议为无效协议。那么,究竟何谓对当事人应当适用的法律呢?一方面,按照国际私法的一般原则,国际民商事交易当事人的行为能力,适用各当事人的本国法。即在自然人的情况下为其国籍所属国的法律认定其是否有行为能力,在法人的情况下由该法人所属国的法律作出认定。另一方面,如果根据当事人本国法没有行为能力,但是根据行为地法为有行为能力,法院仍然可以认定其为有行为能力。
在各国确定仲裁协议当事人行为能力问题的司法实践中,在对每一个具体案件进行审理时,由受理案件的法院根据《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对该特定仲裁协议的当事人行为能力应当适用的法律作出认定。
(二)关于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适用法律
关于如何确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适用法律,《纽约公约》规定了法院应当首先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的主观标准。如果当事人之间没有约定,则适用仲裁地法律的客观标准。
1.主观标准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
仲裁本身就是当事人约定的自愿解决争议的方法,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又是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基石。正如英国著名国际贸易法专家所言:“仲裁实质上是解决争议的一种合同制度。当事人同意把他们之间的争议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争议提交给作为私人裁判官的仲裁员或仲裁庭解决。作为一项合同安排,仲裁应当受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支配”[1]。如果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了该协议的适用法律,法院则应当按照当事人约定的适用法律,决定该仲裁协议的适用法律。
2.客观标准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
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仲裁协议大多体现为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当事人专门在该条款中规定仲裁协议应当适用法律的情况,极为罕见。如果当事人没有在仲裁协议中专门就仲裁协议的适用法律作出约定,根据国际私法中国际合同适用法律的一般原则,则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那么在国际商事仲裁协议中,与该协议有最密切联系国家,就是仲裁地国。因此,《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规定了如果被申请承认与执行的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所依据的仲裁协议如果根据裁决地国家的法律为无效仲裁协议,则执行地国家的法院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
三、尽量使仲裁协议有效原则
通过仲裁的方法解决国际商事交易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已经成为包括我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各国和各地区商人在他们订立国际商事合同中普遍采用的争议解决方法之一。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按照许多国家有关仲裁的立法与实践,当事人只要在协议中明确地表达了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意思,通常就应当尽量满足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他们之间争议的意愿。至于仲裁协议存在的缺陷,可以通过适用相关国家法律的方法加以弥补,尽量使仲裁协议有效。例如,早在1993年,香港高等法院在审理Lucky-Goldstar International(HK)Limited v.Ng Moo Kee Engineering Limited一案中,原被告均为在香港注册并在那里设立营业所的公司。其中原告是韩国一家很有名气的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子公司,1990年12月3日,原告与被告订立了向后者出售5套电梯的合同。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规定:“由于本合同所引起的或者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或纠纷、违约等,如果在有关当事人无不正当延误的情况下不能友好解决,则应在第三国依照该国法规根据国际商事仲裁协会的程序规则仲裁解决。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双方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争议并提交香港法院解决,原告律师对本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的效力提出异议,认为仲裁协议中规定的仲裁机构事实上并不存在,更不用说程序规则了。但是法院则认为,从上述协议看,当事人之间通过仲裁解决他们之间争议的约定十分明确,此项约定并不因为选择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仲裁机构而无效。必须提起注意的是:该条款规定在第三国并“依照该第三国的法规和依据……仲裁程序规则仲裁。”而这里的“法规”(rule),就是“法”(law)的意思。既然当事人选择的仲裁机构并不存在,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程序规则。在此情况下,仲裁应当根据原告所选择的第三国的法律进行。因此,双方当事人仍旧可以选择他们可以接受的国家的仲裁法律与实践进行仲裁②。
近年来,有些国家的法律对国际仲裁协议的有效性的适用法律作出的专门规定中,同样体现了尽量使仲裁协议有效的原则。例如,根据瑞士国际私法第178条(2)款的规定,国际仲裁协议的内容只要符合以下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均为有效:(1)当事人选择的法律;(2)符合管辖争议事项的法律;(3)管辖主合同的法律;(4)瑞士法律③。瑞士法对国际仲裁协议有效性认定方面做出的较为宽松的规定,代表了法院在认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问题上的发展趋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提出的关于我国仲裁法建议修改稿④ 第76条的规定“仲裁协议的实质有效性依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如无此选择,符合下列规定之一的,即为有效:(1)与仲裁协议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2)仲裁地的法律;(3)适用于争议事项的法律,特别是主合同的准据法;(4)国际仲裁协议有效性的一般原则;(5)本法第14条。”⑤ 同样反映了尽量使仲裁协议有效的原则这一发展趋势。
在目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趋势是更加尊重当事人的意思。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按照许多国家有关仲裁的立法与实践,当事人只要在协议中明确地表达了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意思,通常就应当尽量满足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他们之间争议的意愿。至于仲裁协议存在的缺陷,可以通过适用相关国家法律的方法加以弥补,尽量使仲裁协议有效,而不是动辄根据本国国内法认定仲裁协议无效。
四、中国内地法院认定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适用法律的立法与司法实践
(一)立法实践
鉴于国际仲裁协议属于国际合同的一种⑥,我国现行合同法规定的确定涉外合同适用法律的一般原则,同样适用于确定国际仲裁协议的适用法律。我国《合同法》第126条的规定:“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就是说,如果当事人在国际合同中选择了合同应当适用的法律,则应当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如果没有选择,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我国法律的规定,符合国际私法关于确定合同适用法律的一般原则。此外,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书面形式的规定,同样适用于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要求⑦。
我国仲裁法第16条对仲裁协议的构成要件作出了如下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1)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2)仲裁事项;(3)选定的仲裁委员会。”该法第17条和18条还对无效仲裁协议做出了专门规定,包括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或者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的仲裁协议。如果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
鉴于国际(涉外)仲裁协议具有涉外或者国际因素,对于适用什么样的法律确定国际仲裁协议的有效性,除了我国合同法第126条规定的涉外合同适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外,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还专门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⑧,该《解释》第16条就人民法院对涉外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应当适用的法律作了如下规定:“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审查,适用当事人约定的法律;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但约定了仲裁地的,适用仲裁地法律;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也没有约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约定不明的,适用法院地法律。”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解释,与我国合同法第126条的规定是一致的,也符合国际私法关于国际合同适用法律的一般原则。
(二)司法实践
中国内地法院对适用国外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特别是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简称ICE规则)作出的涉及仲裁协议有效性问题的案例,同样存在一些典型案例。现选择其中的两个有代表性的案例加以说明。
1.旭普林公司案
在旭普林公司案⑨ 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条款是:“适用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仲裁,仲裁地点在中国上海”。本案仲裁协议并没有规定仲裁协议的适用法律,仅规定了仲裁适用的仲裁规则和仲裁地点。鉴于作为与仲裁协议有最密切联系的仲裁地点在我国上海,因此,适用我国法律对本案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作出认定,并无可置疑。我国法院根据我国《仲裁法》第16条的规定,一个有效的仲裁协议(条款),应当同时具备通过仲裁解决争议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明确的仲裁机构三个方面的内容。本案所涉仲裁条款从字面上看,虽然有明确的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规则和仲裁地点,但并没有明确指出仲裁机构。因此,应当认定该仲裁条款无效⑩。
事实上,在旭普林公司于2003年4月29日向无锡新区人民法院提出了请求法院确认本案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以前,沃可公司早在2002年10月10日,就向无锡市开发区法院就其与旭普林公司之间的争议提起诉讼,开发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对该案有管辖权。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年2月20日作出的(2003)锡立民终字第074号民事裁定中,同样确认了开发区法院对本案所涉及的工程承包合同纠纷所享有的管辖权。当开发区法院于2003年4月29日受理了旭普林公司提出的要求法院确认本案仲裁协议效力的诉讼请求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无效的决定应当经辖区所属的高级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确认的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本案的批复中认为应当认定该仲裁条款无效。
2.瑞士公司案
然而,在1995年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瑞士公司案(11) 中涉及的对仲裁条款效力的认定中,中国公司与瑞士公司签署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措辞如下:“因本协议产生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纠纷主要应按照申请时有效的国际商会的规则(不包括调解程序)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仲裁应在伦敦以英语进行。仲裁裁决具有终局效力,对双方均具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此案的答复中认为“当事人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因无明确的仲裁机构而无法执行,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12)
海口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院的答复,最终认定该仲裁条款无效。上述仲裁协议之所以无效,其所依据的也是根据我国仲裁法第16条关于仲裁协议效力的规定。即适用我国法律作为认定本案仲裁协议有效性的准据法。就上述仲裁协议而言,当事人并没有约定仲裁协议的适用法律,但是对仲裁适用的规则和仲裁地点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适用ICC规则在伦敦仲裁。笔者认为,如果说在旭普林公司案中法院适用我国法律认定仲裁协议的有效性符合确定国际合同法律适用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和《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规定的话,在瑞士公司案中,法院仍然适用我国法律认定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则值得商榷。因为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点在英国伦敦,进而英国法与本案中的仲裁协议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应当适用英国法而不是我国法作为确定本案仲裁协议有效性的准据法来认定该案仲裁协议的有效性。我国法院适用我国法律认定本案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则有悖于《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
我国现行仲裁法对于仲裁协议有效性的认定作出的规定过于苛刻,特别是对常设仲裁机构的名称,必须作出约定,否则仲裁协议无效。这种规定对于我国仲裁是可以的,因为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临时仲裁存在的余地,除非是双边投资保护协议规定的适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进行的仲裁。但是在国际实践中,几乎所有的国家法律都认可通过临时仲裁庭的方式解决一般的民商事纠纷。而《纽约公约》项下的外国裁决,不仅包括由常设仲裁机构管理下由仲裁庭作出的裁决,同样也包括临时仲裁机构(庭)作出的裁决。我国法院也有义务承认与执行临时仲裁庭在我国境外作出的裁决。
五、结论
《纽约公约》仅规定了仲裁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将最终认定仲裁协议有效性的权力赋予了相关国家的法院。由于各国法律对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作出了不同规定或者法院解释的不同,因而具有同样措辞的仲裁协议按照一国法律为有效协议,但按照另一个国家的法律就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现行各国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立法总的趋势是尽量使仲裁协议有效。我国现行仲裁立法与司法实践对于仲裁协议有效性的认定作出的规定往往过于苛刻,司法实践中对特定仲裁协议的解释各异。笔者认为,在对我国仲裁法进行修订的过程中,应当将尽量使仲裁协议有效的原则反映在仲裁法中,在司法实践中涉及对仲裁条款的解释时,也应当更加注重仲裁条款所反映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通过仲裁解决合同争议的真实的意思,尊重当事人对争议解决方法的共同选择,而不是动辄认定仲裁协议无效。
(全文共10,382字)
收稿日期:2009-04-13
注释:
① 《纽约公约》由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制定,1958年在纽约召开的国际商事仲裁会议上通过,并由45个国家签署,故称《纽约公约》。我国政府于1987年1月22日提交了加入该公约的批准书,公约于同年4月22日对我国正式生效。我国政府在提交批准书时对公约作了两点保留声明:即互惠保留声明和商事保留声明:(1)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在互惠的基础上对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该公约;(2)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认定为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适用该公约。截至2009年3月底,该公约共有缔约国144个,关于具体缔约国的名称,可参见http://www.uncitral.org/uncitral/en/uncitral_texts/arbitration/NYConvention_status.html.
② 关于该案的案情和法院的判决细节,参见赵秀文:《香港仲裁制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4-88页。
③ 关于瑞士联邦1987年国际私法的全文,可参见李双元、欧福永、熊之才编:《国际私法教学参考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432页。
④ 关于该建议稿的内容,参见《北京仲裁》,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2辑,第9-10页。
⑤ 建议稿第14条的规定是:“仲裁协议是各方当事人同意将他们之间的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特定法律关系上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一切或某些争议提交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可以采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单独协议的形式。仲裁协议应当具备以下内容:(1)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2)仲裁事项;(3)能据以确定的仲裁机构。”
⑥ 即通过仲裁的方法解决争议的合同或者协议。
⑦ 我国现行合同法第11条对合同书面形式的规定是:“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⑧ 2005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75次会议通过,法释(2006)7号。
⑨ 即德国旭普林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Zublin International GmbH)诉中国无锡沃可通用工程橡胶有限公司(Wuxi Woco-Tongyong Bubber Engineering Co.)案,关于该案案情及其评论的详细论述,参见赵秀文:《从旭普林公司案看我国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的监督》,载《时代法学》,2007年第6期;也可参见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国际法学》,2008年第4期。
⑩ 参见肖扬总主编、万鄂湘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编:《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2004年第3辑(总第9辑),第36页。
(11) 即瑞士诺和诺德股份有限公司诉海南际中医药科技开发公司经销协议纠纷案。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诺和诺德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际中医药科技开发公司经销协议纠纷案的报告的复函(1996年12月20日,法经[1996]449号)。载宋连斌、林一飞译编:《国际商事仲裁资料精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4月,第474页。
标签:纽约公约论文; 法律论文; 仲裁条款论文; 合同管理论文; 有效合同论文; 仲裁协议论文; 实践合同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国际仲裁论文; 最高人民法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