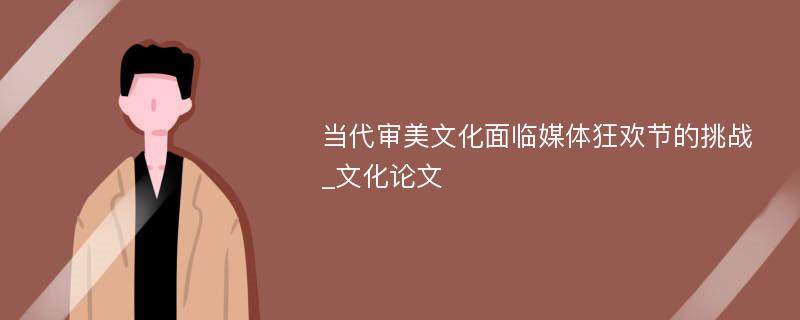
当代审美文化面临媒体狂欢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媒体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科技力量所支撑的新兴艺术品种和艺术手段大量涌现的时代,电影、电视、录像、VCD、DVD、卡拉OK、光纤通信、卫星传播和多媒体电脑互联网络……这些都是当代高科技发展所创造的诸多新兴文化传播手段,他们携带着与其技术特征相兼容的艺术符号形态,以无法抵御的力量挤入我们的文化生活,并迅速占据了我们的文化视野。这些新兴的文化传播手段突破国家、民族、区域的自然阻隔,有效地重新改划了艺术世界的版图分界。无论留守传统部门的人是如何感伤或抗议,一个传媒技术主宰、渗透艺术形态的时代已经如期到来,它不仅改变了审美文化的形式内容,同时也在改变审美文化的本性。
大众传媒把不同年龄、身份、性别的群体卷进了共同的文化氛围中,传递着多元的价值观,并把现代意识、消费意识、文化审美意识揉合在一起,无形中解构了以往高度同质性的文化结构。价值观念的多元性、模糊性、复合性是这一过程的伴随状态。所以,笼统的把当代审美文化中的媒体狂欢看成“文化祸水”或一味顺从于商业利润之手都是不可取的,重要的是如何在更为广阔和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的文化背景下去分析、梳理和规范。
形象文化/视觉文化(image culture/visual culture)在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世界,几乎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代名词。丹尼尔·贝尔说:“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一说法乍听来有些让人不解,因为以往的文化虽是以印刷品和出版物为载体,终归也是诉诸人的视觉,可何不称其为“视觉文化”?这就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概念“视像”。这“视像”不同于以往美学或文艺理论中所说的“形象”、“意象”,它与电视、广播、报纸、广告、商标等大众传媒的崛起密切相关。我们看到,当今世界正被高科技和传媒的狂欢所占据,广告、电视和媒体以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方式对社会进行着全面渗透,并且随着电子媒介和机械复制的急剧增长,视像文化已不仅局限于艺术领域,而成为公共领域的基本存在形态。在这种状态下,整个社会体系逐渐丧失其保存历史的能力,历史感淡化乃至消失,人们开始生活在一个永恒的现在和永恒的变化之中,以往社会的那些保留信息的传统正在被悄悄取代。影像以其优越的可视性表现出对文字的压制,它所具有的套话和碎片的形式,不仅削弱了叙述,而且表现出与纯粹叙述的不相容性,以电视和报纸为主要媒体的大众文化给我们一种从心到身的深度抚慰,直至渗入我们的下意识,他们改变了我们对于世界的感觉方式。在打开的电视和报纸面前,我们的大脑成为了一个受动而畅通的频道,各种连绵不绝的直观形象直接轰击我们的视网膜,而根本无需经过大脑的思维转换,于是我们似乎又返回到了婴儿般的无邪状态,丧失了对文学作品和现实世界进行“阅读”的能力。视像不仅排除了文字的可能的歧义性,而且给我们一种绝对客观的“真实”——一切都被削平为视像的表演。视像以最广泛的形式把自身物化为一种实在,并且用这种实在代替一切存在,只是这些视像已完全丧失了其意义内涵而只剩下了物质外壳。物质的光辉被技术延长了扩张了,并且被转换成了无限生成的视像,与此同时,视像对传统艺术中的意象也造成了直接的冲击和瓦解。传统艺术中那蕴藉悠远的审美想象被中止了,对意象的深层体验和追寻不再具有深远意蕴和耐人寻味之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审美距离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物(人)与物的直接关系——欲望与满足,包含在意象之中的主体性也出现了空场。具体说来,现代视像文化对传统审美意象的冲击和瓦解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传统文学中的意象是一种追求深度模式的表意系统,而视像则无需导向深层次的所指,只注意如何被复制与拼贴,是一种没有原本的摹本,是完全出于机械制作的隐匿了创造与个性痕迹的类象。
意象是一个凝聚了中国艺术精神的特殊的审美范畴,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因而“立象以尽意”进而“得意而忘言”的传统,“象”是构成中国文化独特审美趣味的核心因素,通过“象”而非西方所推崇的语言去追寻那“言外之意”、“象外之象”、“韵外之致”,“象”必须体现“道”,体现“气”,才成为审美对象。审美观照也不是对于孤立的、有限的“象”的观照,它必须从对于“象”的观照推进到对于“道”的观照。意象的存在是为了“尽意”,进入对道的观照,这是一个不断上升和超越的过程,所指最终可以超越能指,而能指则不断地接近所指。
反观现代文化产业的视像,我们看到的则是平面化取代了深度,表层的视觉刺激正在取代另一种深层的智力游戏。它讲求以各种形象的浮华重彩来达到强烈的视觉效果,以一种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强烈的视觉吸引力来诉求观众,构成反形式美的夸张效果,关注的是意义的表层化和简化效果,从而彻底抛弃了传统意象与其“象外之象”之间的具有无限张力的对应关系。在对视像的无限欲求中,视像游戏阻止了自我与世界的意义交流,对意义的领悟已非常稀薄,甚至不复存在。面对视象,人类有可能成为视觉心理上的速食主义者,沉溺于过渡的图像化、幻觉化的世界,追求简单、快速、刺激,无须费力、无须用脑,想象的空间因此而萎缩,成为一味沉浸于观看的颓废者。审美被“观看”引向了浮泛的表面与感性,眼睛的观看遮蔽了心灵的体验,审美成了一种表层的视觉刺激。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心理距离的缩短与消失则造成了往返于物我融贯过程的审美体验的缓弱与停止。
其次,就艺术符号与实在的关系来看,意象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张力,二者之间有着若即若离若隐若现的审美距离,这就为意义的凝聚和生发创造了可能,也为对意义的发现和感悟留下了充分的空间。意象的形成基于实在的物象又不仅仅局限于其自然形态,而是超越表面的物象限制,把主体的意向引向实在的深层,进而去把握内在的“道”,即“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这种对意象的把握代表了一种人以实在世界本身为根基的对实在世界的发现和理解。
现代视像的构成逻辑则是一种直接的合一,它取消了能指与所指之间复杂的张力和差异,打破了表层与深层、边缘与中心、实在与真理之间的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于是,意义的生成空间被挤压成一个平面,蕴含在“象”之中的“意”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詹姆逊曾明确地指出,后现代文化的一个主题就是复制,就是视像的大规模生产复制。传统的惟妙惟肖的艺术描绘已经被一种对对象巨细不分的精确复制所取代。通过这样的精确复制,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已被降到逼真的模拟,能指和指涉物同一就意味着把艺术作为实在表象的同等物而不是它的表征和象征。于是,艺术和实在的界限消失了,艺术已成为实在的一部分,镜头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论模式,因为符号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实世界,而仅仅指涉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和产生符号体系本身的真实性。由于视像的生产依据的是自身的逻辑,因此它可以制作出现始终没有的却又比现实物象更加真实的“超现实”的视像,于是,现实和视像之间的界限也被消解了,影像的极度真实取代了日常现实,人们不再是通过真实之物来理解这世界,他们通过媒体看到的是媒体与其他媒体之间不断参照、拆解、重构、排列、组合、复制、转录、拼接而成的“超真实”的“超文本”,一个“模拟”组合的、数码复制的世界。这种复制和再复制使得世界走向我们时,变得主观而疏离。
再次,意象的形成依据的是主体性原则,具有独一无二的“韵味”,其形成过程也就是一个个人化过程,而现代视像所依据的则是技术理性原则,是一个非个人化过程。
无论在艺术创作还是在艺术欣赏过程中,意象都充分体现出主体性原则,它既是客观之象,更是心造之象。对意象的追求实际上就是主体对对象的挖掘、发现和重构的过程,它并非事先给定,一成不变,而是有赖于主体自身的能动性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交互作用的动态建构。意象为主体提供了“空白”和“召唤结构”,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对意象的阐释和解读也就是审美经验的交流史,或者说是一场对话,一个问答游戏。意象的艺术属于本雅明所说的“韵味的”艺术阶段,它与艺术家当时当地的经验、感觉、联想等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密不可分,并且具有时空上的不可重复性,所以它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艺术作品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存在,决定了它的历史,它既不能被取代,也无法被复制,借用英国学者吉登斯的话来说,就是属于一个“本地生活在场的有效性”。
相比之下,视像生产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它更多地是依据一种技术原则。由于复制技术的出现,即使是艺术作品的最完满的复制物,也会缺少一种成份:它的时空存在,即它在其偶然问世的地点的独一无二的存在。本雅明在其影响深远的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一文中,就对艺术从传统的追求“韵味”的方式向现代大批量复制的文化形态转变作了精彩论述。它肯定机械复制作为生产力对文艺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机械复制在世界上开天辟地第一次把艺术作品从它对仪式的寄生性的依附中解放了出来”,然而,“真确性”、“独一无二性”即艺术的原创性和“韵味”作为文艺的本真存在特性和批评标准却被彻底颠覆,导致了传统的大动荡——作为人性的现代危机和革新对立面的传统的大动荡,其扫荡文化遗产的传统价值的一面也是可以想见的。正如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工业社会具有一些工具,可以把形而上的东西变成形而下的东西,把内在的东西变成外在的东西,把心灵的探索转化为技术的探索。当视像作为一种工业生产的产品时,无限的可复制性使其被抽去了传统意象的独特韵味、独一无二性,也抽去了包含在意象之中的主体性,甘愿或不得不就范于技术的无限可能性和工具理性,并最终服务于某种非审美的目标。各种画面的瞬息万变的切换和传媒多频道全天候的持续播出,中断了人的独处内省,而表面的自由选择模式则又掩盖了其播出的单向度属性和这种“无回应话语”的不平等话语权力实质,这无疑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剥夺和入侵。
在媒体狂欢所构筑的异彩纷呈的形象世界里,感官享乐的直接性否定了审美体验过程的必要性——过程被作为奢侈品截去了,快感变为直接的供给物,而形象则成为纯粹的直观。结果是,艺术的感性价值和观赏性成为基本的并且是惟一确定的价值,而理性价值、意义因素甚至情感价值都变成了可疑的附属物,人们不再重视艺术的所指而是注意它的物质性和多样性,而这物化形象的多样性实际上是一种标准化的单调性,即纯粹技术性的表现。技术性是一切物化形象的规定,给它们着上了吞蚀一切存在和生命光辉的阴影。于是人自身也被“物化”了,忘记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停在路途当中或是误入歧途回不到自身,回不到家。当代人在形象中栖居,但是却不能构成诗意,正是因为人诗意的栖居,乃是人的此在不被忘却的本真状态。或许我们不必夸张人类生存的神圣性,也不必夸大现实的灾情而过于忧心忡忡,在大众传媒诞生以前,也同样有劣质的文化,只是随着时间的淘汰,大多已退出了我们的视野。同样道理,优秀的作品,健康而充满生机的作品,在大众传媒中也同样存在,而且永远会存在。问题是如果人连自己真正的需要都会忘记,他的确会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回馈,会忘记自己的生命存在。我们并不反对技术,技术本身无罪,技术至上才是盲目,对技术失去了道义和诗学的控制才是人间地狱。生命之境离不开外在的物态,但更重要的是人的心态,是人精神的自救和自强——永远保持一种文化的内省,不断获取给养又不断清除污秽,给自己的每一个日子留下真情实感,留下人心的自然。因此,审美文化有责任提醒人们返回自己的存在,返回生命本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