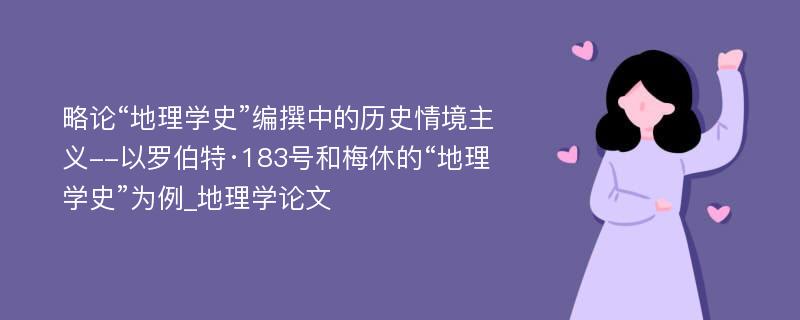
历史语境主义地理学编史思想述要——以罗伯特#183;梅休地理学史研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罗伯特论文,语境论文,为例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4)01-0136-12 地理学史的研究与当前地理学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不对称关系,奈尔·史密斯(Neil Smith)最近还批评道:“地理学家普遍地并不擅长于撰写他们的历史”①。这种不对称关系,最主要的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地理学史的忽视,这种情况自然地理学比人文地理学还要严重②;二是地理学编史方法论很大程度上与科学史编史方法论没有保持一致的进步性或批评性,其中在西方地理学传统内表现为以现代地理学为目标的“辉格主义”(Whiggism)、“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科学主义”(scientism)、“编年主义”(anachronism)、“进步主义”(triumphalism)强纲领建构③,在非西方地理学(比如中国地理学,特别是古代部分)传统内的非本位建构,也即唐晓峰所说的“反向格义”方法论问题④。 除此之外必须注意的是,假如我们将视角放到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之后科学史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sociology of science knowledge)、科学的文化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语境论(context theory)、女性主义(feminism)、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人类学转向(anthropological turn)等方面⑤,那么在科学实践论的层面上,所谓的西方地理学传统和非西方地理学传统之间的严格界限就有消解的可能,也即地理学中西方霸权话语的消解。这需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地理学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实践性;二是作为科学的地理学发展的时代性;三是不同地区的地理学在科学的地理学方面是如何发展的。而三者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地理知识形态的差别性问题,与以现代地理学为目标的建构地理学史相比,批评性地理学史最重要的问题即现代地理学之前地理学知识形态在科学性与非科学性之间的张力,因为除非保持了这种必要的张力,否则一味地强调地理学的时代性和地方性将导致极端的历史相对主义的“完全不可通约性”(completely incommensurability)问题⑥。人类学家奈克·贾旦(Nick Jardine)的总结不仅申明了需要保持这种张力,而且说明了给予任何一方优先权时的危险: 假如不是贫乏的话,没有主位的客位科学史是空洞的,因为它不能参与到过去科学实践者的生活世界中去。它也是傲慢的,因为在缺乏对古人的认识和理解的前提下,假定了他们对科学发展的有益理解毫不相干。没有客位的主位科学史是盲目的,因为它的任意性和盲目性使其放弃了过多的有益于研究历史生活世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知识。同样地,这也是傲慢的,它假设即使如此盲目也能够使历史上的文化本土化。一种对历史上的差异性持有应有尊重的科学史必须尝试主位和客位的结合以切合多样的主体和目标。⑦ 这里所说的没有主位的客位科学史,就指的是强纲领性的实证主义科学史,没有客位的科学史则是强纲领性的与现代科学没有任何关系的科学史,只不过用人类学的术语说出来而已。 本文将以英国地理学史家罗伯特·梅休(Robert J.Mayhew)为代表的英国地理学史研究为例,尝试阐明其历史语境主义编史方法论(contextualism historiography)基础上的英国近代地理学时期的知识形态,这是与实证主义地理学史不同的考察路径。以此为基础,本文将说明不同地区具有差别性的传统在科学实践论层面上撰写非“科学主义”强纲领地理学史的合法性问题。但本文并不主张完全否定业已建构起来的“科学”地理学史,而是坚持地理学史具有建构性,“科学”的地理学史建构可以体现“进步”性和知识的积累性,但并不一定要用直线性的、必然性的“进化”模式来建构。 一 地理学史引入历史语境主义方法论的必要性 在后历史(post-history)的层面上,地理学的科学观和历史观在近几十年来正在改变。在科学观方面,戴维·利文斯通(David N.Livingstone)的“地理学意味着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地方的不同事物,地理学的‘性质’总是需要协商性的”在大多地理学史论著中均可见⑧,并且,利文斯通主张地理学所拥有的应该是复数的想象、传统、历史,而不是单数的⑨。很显然,利文斯通所说的复数的地理学史,不仅指的是在西方地理学传统内的事,同样也是西方地理学传统之外的事,而且它们应在SSK所说“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信条中的公正性(impartiality)和对称性(symmetry)原则上来叙事⑩。 在这个层面上,迈克·赫费南(Mike Heffernan)的批评是非常到位的: 直到最近,地理学史都是将不同地理学的复数的活动、视角用狭隘的、非批评性的术语写成合法于现代的历史。地理学史都表现为一种智力真空,独立于外部的经济、社会、政治或文化力量。(11)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单数地理学史的这种偏见,普雷斯顿·詹姆斯(Preston E.James)和杰弗里·马丁(Geoffrey J.Martin)所著《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12)。非常有趣的是,该著第2版中译本的书名用的是副标题,即《地理学思想史》,不少学者认为实际上应按原书主标题来译,强调地理学的多元传统,但实际上,译为《地理学思想史》或许是最恰当的了,虽然第4版中译本改为了《所有可能的世界》。因为严格地说,詹姆斯并没有写出真正的“所有可能的世界”,至少在中国地理学史上是这样。在詹姆斯的版本中,中国地理学只在中世纪地理学和近代地理学部分出现,但关于中世纪时的中国地理学实际上是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名家约瑟夫·李约瑟(Joseph Needham)所著Science & Civilisation in China第三卷中地学部分(13)的简写版,詹姆斯在科学和科学史观方面都没有超越李约瑟。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詹姆斯对“两小儿辩日”的评论是:“估计到在上述情况下苏格拉底会讲些什么,在文化态度上的两种根本不同处就看得很清楚了……事实上,中国地理著作的记载是极为可观的,只是这些记载偏重于所观察的事物和过程,较少理论的公式”(14)。这是詹姆斯科学史观的重要体现,从这点来看,詹姆斯并不承认中国地理学对于他所理解的地理学有多少贡献,只不过是学界所说的“李约瑟问题”在地理学史的反映而已(15)。至于中国近代地理学,则被詹姆斯分配到了英美流派和原苏联流派中,对于中国古代地理学的近代转换只是给出了一个勉强的说明。在马丁版本中,中世纪时期的中国地理学与詹姆斯版本保持了一致,但却删除了中国近代地理学部分。 詹姆斯和马丁所说的“所有可能的世界”,实际上多少有些虚假承诺的成分。不仅如李旭旦先生所说“对于西方地理学的介绍过于偏重”(16),而且如利文斯通所批评的,《所有可能的世界》(17)是以一种现代地理学的标准来评价、书写的地理学史,书写历史的合法性联系着的是一种地理学“进步”的国际主义重构,是一种选择性的、歪曲的、理想化的历史(18)。 但也很显然,詹姆斯和马丁的这种编史方法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地理学史家。唐晓峰回顾中国地理学史研究的历程时,竟然发现我们对自己地理学史的建构多有失去主体的倾向,他称这种方法为“反向格义”,原因在于这些地理学史较多地参照现代西方地理学的体系和方法来写,却没有发现作为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主体的“王朝地理学”(19)。 在可以接受的层面上,这些地理学史著作,只是地理学史之一种,即以现代地理学为标杆的地理学史。至于其他时代、其他地方的地理学史,并不是这些地理学史著作的主线。假如将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地理学史称为跨文化的地理学史的话,那么“跨文化”一词仅指不同地区的类型的文化则只是“空间”类型的说明,但同样重要的是“时间”类型的文化差别。因此,任何科学史都必须承认是跨文化史,而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了科学史中“史”的核心关系,这种关系的建构根本地在于方法论问题,而非书写篇幅的多寡。 如何处理地理学史中的这种跨文化关系呢?这里有两方面的研究进展值得我们借鉴:其一是国内唐晓峰及其弟子潘晟的工作,这是国内已经熟悉的了,是典型的地域跨文化地理学史比较分析文本,不再赘述;其二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梅休和爱丁堡大学查尔斯·W.J.威瑟斯(Charles W.J.Withers)的研究,尤其是梅休的工作,这是国内学者所不熟悉的,也是本文的重点。 二 历史语境主义地理学编史思想的渊源 历史语境主义的思想渊源,最主要的有两方面:一是梅休从政治思想史方法论上获得启示;二是威瑟斯应用了SSK理论。当然,他们的思想渊源实际上有交叉的地方,现分别叙述如下。 在与梅休的交流中,他告诉笔者他的思想主要地受教于“剑桥学派”,对地理学史的研究集中于18世纪的英国地理学(2013年2月7日给笔者的电邮,以下只注日期)(20)。读者可能注意到,本文标题用的是“历史语境主义”而不是“剑桥学派”。实际上,“剑桥学派”只是该学派人物所在地的指称(21),依据其方法论核心则被称为“历史语境主义”。梅休教授给笔者的邮件中同时说明他的思想直接地受益于“剑桥学派”迈克尔·欧克夏(Michael Oakeshott)和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影响(2013年2月7),二者均是明确提出“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代表人物。 历史语境主义与相关的编史方法的根本差别有两点(22):一是强调“历史”,二是强调“语境”。历史语境主义的研究方法首先与“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研究方法有关系。所谓概念史方法实际上是试图通过研究文本的语言和结构来认识不同时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其关注的并不是对概念进行词源学(onomasiology)考察,而是通过语义学(semasiology)来分析特定概念在不同时间和空间里的含义。按方维规的意见,随着西方思想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有三种不同的历史研究方法:一是德国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或可称为“历史语义学”(Historische Semantik)模式;二是英美的剑桥学派所倡导的“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模式,强调一定语境中文本的原始意义(也即本文所说“历史语境主义”);三是法国的“话语分析”(analyse du dis-cours),或称“概念社会史”(socio-histoire des concepts),强调话语背后的语言形态或社会背景(23)。虽然三者都不排斥文本、语境、话语、背景等范畴,但历史语境主义与其余二者的根本差别在于:主张应摒弃研究者的主观意图,关注构成文本的语言习惯和作者信念,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概念的含义,基于此又通过概念的研究来透视社会。在这里,社会的变动会导致概念含义的变动,而概念的变动反映了社会的变动。 在此,如何理解“概念”对于理解历史语境主义是至关重要的。但这里需要首先区别“观念”与“概念”二词。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历史学家的技艺》(Apologie Pour L' Histoire,又译《为历史学辩护》)中曾认为人们在改变风俗习惯的时候,没有改变使用词汇的习惯,这一事实常常使历史学者犯下错误,他们自认为是一个新词,而这个词实际上很早就已存在(24)。也就是说,单个的语词有着明确的意义,而概念则未必,概念比语词有着更宽泛的意义;观念比概念更宽泛,而且通常是“常数”,概念则是变动的、复数的(25)。从这一点可以理解历史语境主义为何选取“概念”作为分析点。 那么,“历史”及“语境”又意味着什么呢?德国史学家莱因哈特·柯史莱克(Reinhart Koselleck)被认为是概念史研究的象征性人物,他的核心思想是: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概念和基本概念是对现实的社会历史的反映,概念史方法的要义是通过概念的研究来透视社会。与此相反,斯金纳等人却认为“概念”的含义是变动的,批评将“概念”视为不变的社会因素的概念史研究实际上没有“历史”(26),思想史观念研究也就应当关注一些重要概念在“历史语境”中的变化(27)。斯金纳承袭维特根斯坦(Ludwig Whittgenstein)“概念即工具”(concepts are tools)的观点,认为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概念,而只存在不同的使用概念的(争论)历史(28)。 因此,历史语境主义的要义实际上可总结为:将具有变动性的概念作为分析思想史的关键或平台,以基于不同时代语境中的变动中的概念来折射变动中的社会。类似地,地理学编史学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的要义可以先验地承诺为:将具有变动性的地理概念作为分析地理学史的关键或平台,以基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语境中的变动中的地理概念来折射变动中的地理学史。 历史语境主义地理学编史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威瑟斯对SSK理论的应用。不过,威瑟斯的思想实际上与梅休基本保持了一致,或者说他只从SSK那里寻求了必要的大家所共同接受的部分。SSK是科学史的社会学转向的产物,而且是最激进的流派。科学史的社会学转向始于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所建立的科学社会学,特别的是默顿1942所建立的“默顿规范”(CUDO:commonality or communism,universalism,disinterestedness,organized skepticism)(29),但在这里社会因素只影响知识生产的速度,对知识的性质未“染指”。SSK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不满于“默顿规范”的信条,宣称SSK“作为一种社会学研究,它主要关心的是科学知识的形式和内容,而不是科学知识的组织或分布”(30),同期的爱丁堡学派主将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同样强调:“存在于知识之外的东西,比知识更加伟大的东西,使知识得以存在的东西,就是社会本身。”并且提出了四条著名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信条:因果性(causality)、公正性(impartiality)、对称性(symmetry)和反身性(reflexivity)(31)。布鲁尔的“强纲领”信条一方面打破了实证主义科学史的理性主义信条,另一方面为科学内容的比较性研究提供了可能。公正性原则强调:“当对真理与谬误、合理或不合理性,成功或失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称性原则强调:“同一些原因应当可以说明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32)这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对实证主义科学史“辉格解释”的批评,意味着错误的甚至倒退的、非理性的、非现代的科学知识都应纳入叙事框架。 布鲁尔的“强纲领”信条引导了科学空间向两个方向研究:一个是在SSK内部,通过对库恩文本的进一步激进解读,从“强纲领”转向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典型的是“实验室研究”;另一个是被“科学的文化研究”、“地方性知识”理论和“后殖民研究”者所接受,与SSK一道批评实证主义科学史的一系列理论预设。 威瑟斯告知笔者他的思想是因为熟悉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西蒙·谢弗(Simon Schaffer)、布鲁尔等人的著作而感兴趣的(2013年2月12日),谢弗和布鲁尔实际上是SSK学派的同一代人物。威瑟斯表示:“假如你有一种科学史,而在这里‘科学’(着重号是笔者所加,下同)在不同时代并不意味着同一种事情,那么你也能有一种‘科学的地理学’,在这里‘科学’在不同地方并不意味着同一种事情。(2013年2月8日)”因此,威瑟斯对SSK学派思想的吸收,注重的是公正性和对称性信条,至于社会因素对知识性质的彻底“染指”这一极为激进的、饱受批评的思想则不是重点。这是他的思想与梅休思想极为相似的根源。 但必须指出的是,在坚持公正性和对称性信条的前提下,我们不主张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地理学完全不可通约,相反,我们将提议“对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否则,地理学史将无法获得一个全人类的图景,而是破碎化的,无法相互理解的,孤立的历史。当然,这种承诺不应是先验的,情感性的,必须到地理学的实践中获得证据、解释。 三 历史语境主义地理学编史思想的要义 历史语境主义地理学编史思想的要义有二:其一,主张地理学史是一种跨文化史,地理学在不同地方、不同时代并不是同一回事,也就意味着地理学史是复数的(33);其二,主要旨趣在于地理学作为一种非体制性事业与社会和文化的关联,这种关联通过文本分析更为适宜。这里的“文本”,实际上指的是能够分析社会文化意义的文本,而不是直指其科学性的内容,这些文本在类似于詹姆斯和马丁的地理学史著作中存在被忽略或曲解的问题。 “Contextualizing Practice in Intellectual History:a Comment”一文是梅休编史思想的代表作之一(34),这篇文章倡导一种基于欧克夏的科学哲学和斯金纳的语言语境主义的新编史学方法。他吸收的欧克夏思想主要是“解释历史需要基于历史及探索历史”(35)。欧克夏本人承认关于历史作为一种认识结果具有主观的一面,即柯林武德所说的“(历史证据)是当历史学家回答问题时组装的”(36),因此,欧克夏认为不同历史中的事件的“意义”(significance)需要不同的解释模式,而这种模式在于历史中事件、行动或思想的“蕴涵”(meaning)。梅休认为,欧克夏这样做避免了巴菲尔德所批评的“辉格史”(37)。因此,梅休通过欧克夏的思想看到了一样东西:历史需要被自己所解释,思想史的目的必须去理解思想是如何被表达的,而这一点斯金纳的语言语境主义则指明了方向。虽然梅休引述了斯金纳的很多主张,但最根本的是斯金纳乞求按历史自己的方式解释历史,“这要求恢复他们原有的概念(而不是按照某种暗含的、预设的主体话语方式去理解)”,而这种恢复正是历史语境的方法:“为了理解特定的作者应用一些特殊概念或争论所写的历史,我们首要的是抓住通过应用这些特殊概念在特别主题、特别时间下所写历史的性质和范围。”(38) 基于这样的追求,梅休致力于历史语境主义的地理学编史思想20余年,另一篇代表作“The Effacement of Early Modern Geography(c.1600-1850):a Historiographical Essay”批判性地表达了他的地理学编史思想要义: 本文从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和苏尔(Carl O.Sauer)所认为的现代地理学“创建人”开始讨论。他们发展了一种“本质主义”编史学:假设地理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以此标准评判地理学史,将近代时期置于这样的地理学的开端; 地理学史应该与它自己的过去相联系,在过去的历史中来理解,而不是能被现在的实践所能理解的眼光。(39) 在这篇文章中,他再叙欧克夏的思想,批评麦金德、哈特向和苏尔等以及后来的地理学史家们将复数的地理学史写成了单数的地理学史:地理学的过去被简单地建构成与后来的定义相一致的定义。 除此之外,梅休告诉笔者他近来受尼采(Friedrch J.Nietzsche)的影响较大(2013年3月12日),而他新近的“Geographies Genealogies:Origin Stories,Nietzsche and the History of Geography”一文确实表明了这一点(40),而且提出了更富启示的见解。该文首先批评了哈特向和苏尔等的本质主义科学史观: 哈特向和苏尔都企图说明地理学是什么样的以及应该如何,用以证明地理学史的书写说明了地理学一直是这样。更确切地说,两人都发展了“真正”的地理学的起源史,地理学应该是这样的历史,在本质主义的框架内寻找过去发现这种探索的重要学者。(41) 进而,梅休将哈特向和苏尔的这种本质主义观照下的寻找地理学之父或撰写地理学史的方法称为“神话”(42)。这一诊断或许是受斯金纳所称的“时代误置”(anachronisme)启示,或者说斯金纳说得更深刻。斯金纳的“时代误置”指的是:“我们发现某一位作者持有某种观点,而实际上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意图,只是碰巧使用了类似的术语”(43),这形成了学说神话(mythology of doctrines)、连贯性神话(mythology of coherence)、预期神话(mythology of prolepsis),这三个神话的含义实际上可以视为“辉格解释”的翻版,也更能深刻解释梅休所说的“神话”。梅休认为,哈特向和苏尔将不同时期的地理学都认为是当代的地理学的基础,被纳入“现代”地理学的分类中,并且设定“可辨别出的单一的(或者仅止是多个地点的)起源是可以找到的”(44)。因此,他引入了尼采的谱系(pedigrees)思想来分析这种观点的片面性。 首先,他批评本质主义思想在梳理地理学谱系时存在一种含蓄的假设:“在思想谱系中存在自古至今的区分,在这个链条中越近的思想要么更好,要么至少‘接近于我们’,因此对我们更有价值”(45)。 其次,他说明了本质主义地理学史本身可能导致的误解,用以说明的是两位“伟人”——斯特拉波(Strabo)和波力比阿斯(Polybius)。 在本质主义地理学史中,斯特拉波是地理学之父,而波力比阿斯则是历史学之父。但梅休认为这种盖棺定论不足为信,因为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既不是我们对其著作有十足的认识,也不是我们对其生平有十足的把握,相反是历史成见。历史成见往往认为斯特拉波写出了《地理学(Geographia)》,波力比阿斯写出了《历史学(History)》。但实际是,这样的书名标题是“被贴上标签”的(46),这只不过是因为在原文中斯特拉波称其著是一本“地球的描述”,但实际上可以具有一系列的头衔,因为geographia、chorographia、periegesis、periodos ges、periodeia tes choras等词都表征的是对古希腊人已知世界的文学性、诗歌性的一系列多样内容的表述(47)。波力比阿斯在地理学史家那里就没那么幸运了,往往被称为是历史学家,但有如下理由同样对地理学是重要的:历史学家需要理解叙述涉及历史的自然事件发生的原因;地形对于解释战争过程是重要的;波力比阿斯具有现在所称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48)。而且仍有疑问的是,斯特拉波的《地理学》只有17卷,而其所著《历史学》则有43卷;波力比阿斯在其40卷的《历史学》中第34卷是对所知世界的地理描述。因此,“地理学之父”或许并不仅止一个人。 假如将梅休的意见与“寻找地理学之父”的地理学史相比,则会发现后者存在相当的局限性:一方面是其“寻找”会导致辉格式的误解;另一方面是这一“寻找”将会失去太多的应该纳入地理学史叙事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学史仍是需要进行大力建构的历史。类似工作部分地已体现在威瑟斯(49)和利文斯通(50)的著作中,其要义是:这种书写复数的地理学史是关注不同地理空间、地方和环境的地理知识(的复数史),这意味着在过去的社会中应将地理学视为变化着的概念。换句话说,在辉格式的地理学史叙述中,充满的是实证主义的气息和评判,当应用“地理学”一词时,对于古代部分与现代部分似乎被看成是同一种东西的进化史,而实际上是一种误解。 四 历史语境主义的转型 地理学研究及其启示 如前所述,历史语境主义被认为是研究转型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方法。梅休将其引入地理学史研究,关注的是近代地理学。他们对近代地理学的研究是采取历史语境主义方法的,这里主要论述从他们的研究中所看到的近代地理学形象。这种表象当然不是本质主义者所看到的那样作为一种纯科学的前史或基础史,这对于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梅休和威瑟斯的英国近代地理学在时间界限上大致是1500至1800年之间。他们所描述的这一时期近代地理学形象与本质主义者的差别在于两点:其一,地理学作为一种知识(他们论述时多用的是确定的“地理知识”术语而不是“地理学”);其二,地理学作为一种“关联性”社会文化活动。 “The character of English geography c.1660-1800:a textual approach”一文是梅休应用历史语境主义分析近代地理学史的典型文本,他在该文中以地理著作为考察对象将1660-1800年的地理学特征陈述为“文本传统”(textual tradition),其具有“双胞特征” (twin character): 一方面,与商业性和实用性紧密相关的功利主义关怀(文本对象是政治家和商人,公共演讲和商业学院鼓励充满野心的商人去阅读地理著作;出版条件同样充满商业竞争并鼓励剽窃;作者本身则更多地是为生计而写作);另一方面是强调基督的及古典的学识的人文主义教育的一部分(著作写作源于对古典文明及圣经的有用;语法学校和大学建立了由人文主义学识所决定的地理著作和地理信息收集的阅读环境;一些作者为写出反映古典的、历史的、圣经的地理著作终生努力)。(51) 因此,梅休认为近代地理学与后来作为一门学术事业的地理学学科有着本质之不同,后者是体制化的、较多独立性的知识生产活动。Landscape,Literature and English Religious Culture,1660-1800:Samuel Johnson and Languages of Natural Description(52)一书通过再现18世纪关于景观的描述争论阐述了18世纪的景观描述的浓重神学印迹,以及牧师们不同的神学观导致的描述手法的差别,借此揭示这一时期英语世界地理智力活动仍然深陷一种基督的和古典的意识中。对18世纪景观的文化表征的兴趣引导他关注16-19世纪的英格兰地理学,这构成了他此后二十余年学术生涯的最重要部分,代表作是Enlightenment Geography:The Political Languages of British Geography,1650-1850。该著作通过地理知识(而不是地理学)印刷体制的政治学分析,揭示这一段历史中英国地理知识生产的直接关联是政治讨论(53)。这些都说明:“近代地理学”与后来的“(现代)地理学”泾渭分明,不是一回事。 这样的思想当然还反映在了Historical Cultures and Geography,1600-1750一书中(54)。梅休当前正致力于考察马尔萨斯提出“人口论”的背景及其学术响应以及当下实质性的误解,书名暂定为Untimely Prophet。 在此,借鉴梅休和威瑟斯的研究思考历史语境主义地理学编史方法对于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将是有意义的。 对于中国地理学史来说,王庸的结论是有些丧气的,因为他参照西方地理学来写中国地理学史时,结论是:“严格地说,除掉地图和西方科学输入以后的地学之外,在中国学术史上实在是很少可以称为地理学的。”(55)尽管如此,他还是在知识史的层面上梳理出了中国地理学史发展的一个线索。到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时,中国古代有无地理学已不再是问题了,是一种承诺。因此,他们将西方地理学体系引入,再按时间顺序挑选与之有关的材料来书写(56)。到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编写巨著《中国古代地理学史》时,干脆直接以西方现代地理学体系纲领来写,章节安排是学科体系纲领,次要的才是各学科内的发展史(57)。 上述三著受到了唐晓峰的批评,认为其方法论是“反向格义”的,即参照西方现代地理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发展史(58),其中当然已暗含辉格史的倾向了(59)。因此,除了这种建构性之外,我们还需要“还原”。(60) 假如接受已发表的意见的话,那么唐晓峰所称的“王朝地理学”可以被认为是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还原”式建构(61)。因为很显然,他没有参照西方地理学那套(概念、术语、逻辑等形式)来写中国地理学史,所用的材料当然也是不同的,地志在这里不是属于历史学,而是取得了很高的地位:“在讲述地理历史沿革时,历史是一种解释、一种证明。在这里,不是地理服务于历史,而是历史服务于地理”(62)。在这里,实证主义地理学史所放弃的材料,如各种地理志、地方志、游记、古地图、正史、杂史、文集、诗集、民谣、山水画、金石碑刻等等(63),成为了“王朝地理学”的基础,用以分析的概念也是中国原始文化中的,用以解释的也是中国原始的文化观念,这明确表明:中国古代所称的地理学与现在所称的地理学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反映王朝制度的知识形态,而后者是作为一项探索地理环境的制度性、独立性事业。 除此之外,借鉴于历史语境主义编史方法,实际上为中国地理学史研究保留了足够的空间。比如在《所有可能的世界》里,詹姆斯和马丁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给出了一种典型的“殖民研究”的解释:“当符合这三个条件时(64),新的专业领域就产生了。从研究对象,到学科、到专业,到专业的传播,这构成了一个研究领域发展的过程”,并在序言断言:新地理学从德国开始,然后传播到法国、英国和俄国,再传到美国,“在上述五个国家中,由于对地理学性质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产生了地理学上的不同的国家流派。地理学通过这五个国家传播到了全世界”(65)。而实际上,“后殖民研究”科学史家主张近代早期的“科学”是通过将林林总总的知识概念“类并”(conceptual syncretism)而形成复数的“科学”概念的(66),或者是通过“知识凝聚”(appropri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67)的方式(68)。中国近代地理学表现出了类似过程,尤其是中国近代科学和地理学著作中有着强烈的从“格致”到“科学”(69),“舆地”到“地理”、“地学”、“地文学”等概念的转换过程(70)。借助于概念演变的研究,将有益于更为客观的中国近代地理学交流史研究而非单向的传播史。 回顾全文,可以认为历史语境主义对以现代为标杆的地理学史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其最重要的启示是:其一,基于公正性和对称性原则,地理学史理解为知识形态史可能比较适宜,理解为狭义的科学史则可能会误解地理学成为科学学科以前的历史,并无意间忽略了更为广阔的地理学含义;其二,作为知识形态史的地理学史,其叙事纲领可以借鉴概念史分析方法,为分析不同知识形态的地理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保留足够的空间,而不是一味强调地理学的进步性、科学性,不同地区、不同时代地理学对于社会文化的有益性并不一定需要进步性和科学性来强纲领地评判;其三,作为知识形态的地理学,任何有益于人类的内容都具有纳入叙事的合法性,地理学史的研究至少应对其有益性给予特别的阐释。 而中国近代地理学转型中的概念“类并”或“凝聚”则表明,在承认地理学多样化的同时,普遍性仍然可以在历史的“临界点”前后获得连续,这种连续性同样在跨区域间表现出来。因此,在非强制性原则下,地理学史的建构可以在多样性(包括空间的和时间的)与普遍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 [后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科学学院Robert J.Mayhew教授和爱丁堡大学科学与工程学院Charles W.J.Withers教授的多次指教并提供了部分重要文献;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汤茂林教授和外审专家对本文初稿提出了宝贵修改建议;雅典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学院Manolis Patiniotis教授提供了他富有启示的最新研究成果。特申谢忱! 注释: ①Neil S.Imperial Errantry.Antipode,2012,(4):pp.553-555.引文见第553页。 ②Wainwright S P.Science studies in physical geography: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Progress in Physical Geography,2012,(6):pp.786-812. ③这些术语表征着以现代科学形象为目标的科学建构特征,综述性文献见:Wilson A and Ashplant A G.Whig history and present-centered history.The Historical Journal,1988,(3):pp.1-16;Alvargonzález D.Is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ssentially Whiggish? History of Science,2013,(1):pp.85-100。地理学中提出此类批评的文献见:Livingstone D N.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history of geography:Interactions and implications.History of Science,1984,(3):pp.271-302;Mayhew R J.Contextualizing practice in intellectual history:A comment.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1994,(3):pp.323-328;Mayhew R J.The effacement of early modern geography(c 1600-1850):A historiographical essay.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1,(3):pp.383-401;迈克·赫费南:《地理学史》,萨拉·霍洛韦,斯蒂芬·赖,吉尔·瓦伦丁主编,黄润华等译:《当代地理学要义——概念、思维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19页。 ④唐晓峰:《“反向格义”与中国地理学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81-91页。 ⑤这些元科学转向的文献见著名科学史杂志《ISIS》最新的总结Galison P.Ten Problem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Isis,2008,(1):pp.111-124. ⑥克拉瓦尔著,郑胜华等译:《地理学思想史》(第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7年,第2-3页。 ⑦Jardine N.Etics and emics(not to mention anemics and emetics)in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ces.History of Science,2004,(3):pp.261-278.引文见第275页。 ⑧Livingstone D N.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a contested enterprise.Oxford:Blackwell,1992,p.28. ⑨Livingstone D N.Geographical Traditions.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1995,(4):pp.420-422. ⑩布鲁尔著,艾彦译:《知识与社会意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11)赫费南:《地理学史》,萨拉·霍洛韦,斯蒂芬·赖,吉尔·瓦伦丁主编,黄润华等译:《当代地理学要义——概念、思维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页。 (12)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马丁,成一农,王雪梅译:《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第4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3)Neetlham J.Science &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ume III,The sciences of the ear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 (14)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9页。 (15)“李约瑟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反思见孙小淳:《从“百川归海”到“河岸风光”——试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第3期,第95-100页;蔡仲,郝新鸿:《“百川归海”与“河岸风光”——对当代中国科学史学的方法论反思》,《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74-80页。 (16)李旭旦:《〈地理学思想史〉述评》,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页。 (17)以及迪金森(R.E.Dickinson)和霍华思(O.J.R.Howarth)所著The Making of Geography、迪金森所著The Makers of Modern Geography、弗里曼(T.W.Freeman)所著A Hundred Years of Geography。 (18)Livingstone D N.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history of geography:Interactions and implications.History of Science,1984,(3):pp.271-302。评述见第271页,举例见第294页。 (19)论述“王朝地理学”作为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主体的工作见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Tang Xiaofeng.From Dynastic Geography to Historical Geography:A change in Perspective towards the Geographical Past of China.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 International,2000年;潘晟:《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目录学考察(一)——《汉书·艺文志》的个案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1辑,第81-87页;潘晟:《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目录学考察(二)——汉唐时期目录学中的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1辑,第122-131页;潘晟:《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目录学考察(三)——两宋公私书目中的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辑,第148-160页;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潘晟:《汉唐地理数术知识的演变与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167-181页;孙俊,潘玉君:《〈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述评》,《地理学报》,2012年第8期,第1149-1152页。 (20)为尽可能地避免交流中的误解,本文所提及重要思想时均以原始文献分析。 (21)同样的理由可称为“盎格鲁-澳大拉西亚学派”,依据代表人物的学科背景或教育背景还称其为“从业史家”(Practicing Historians),从学派影响上还被称为“共和(修正)主义” (Republican Revisionilsts)或“新史家”(New Historians)。详见孔新峰:《“语境”中的“语境主义”:昆廷·斯金纳政治思想史研究发微》,《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1期,第34-36页。 (22)科学编史方法论通常分为实证主义、思想史和社会学三种,详见袁江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学编史学教程简介》,《中国科技史杂志》2005年第4期,第370-378页。本文所说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论与思想史方法论有较多共同特征,实证主义方法论是历史语境主义编史方法论批评的主要方法论,不再赘述。社会学方法实际上指涉的是SSK所影响的编史方法论,强调社会对科学知识内容的影响,后文有简要介绍,地理学史此种方法论的应用主要是特雷弗J.巴恩斯(Trevor J.Barnes)对现代加拿大经济地理学史的研究,其此方面工作唯一的中译文本见巴恩斯著,汤茂林等译:《“发明”英美经济地理学》,谢泼德,巴恩斯主编,汤茂林等译:《经济地理学指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23)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页。 (24)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25)孙江:《概念、概念史与中国语境》,《史学月刊》2012年9期,第5-11页。 (26)Skinner Q.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Vol.1,The Renaiss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xi. (27)Tully J.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Cambridge:Polity Press,1988. (28)Richter M.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A critical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33. (29)默顿著,林聚任译:《科学的规范结构》,《世界哲学》2002年第3期,第56-60页。 (30)拉图尔著,刘文旋、郑开译:《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页。 (31)布鲁尔著:《知识与社会意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27,7-8页。 (32)布鲁尔著:《知识与社会意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33)关于这一点,笔者之一贾星客特别指出并不应该走向绝对的历史相对主义。批评的目的是达到具体语境中的对话,而不是将不同文化的地理认识、概念绝对地对立起来,或者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特别地,他主张不同地区的地理学史有着一些共性的层面,尤其是现在所说的地理学的普遍性要素,而这些普遍性要素构成了现代地理学的基础,历史上不同地区均对这些普遍性要素有着或多或少的贡献。这些普遍性要素,主要地表现为得出了“正确的”、“科学的”认识,并以此推动了地理知识的累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全人类的地理学史”。除此之外,对于“复数的地理学史”,他认为不能仅是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地理学史,还应包括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生产方式等“指标”的复数形式。梅休和威瑟斯的表达并未道出这两层涵义,但在SSK的层面上,也即社会影响知识生产内容的层面上,这两条“指标”是成立的。比如,在SSK的对称性、公正性原则下,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与近现代的科学地理学差别就直接地与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相关。 (34)Mayhew R J.Contextualizing practice in intellectual history:A comment.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1994,(3):pp.323-328. (35)Oakeshott M J.Experience and its mod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3,P.145. (36)Collinwood R G.The idea of history (rev.ed).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69。或见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47页。 (37)Butterfield H.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1。实际上,科学史中对实证主义科学史的辉格解释批评主要是由该文引起的。 (38)Mayhew R J.Contextualizing practice in intellectual history:A comment.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1994,(3):pp.323-328.引文见第324页。 (39)Mayhew R J.The effacement of early modern geography(c.1600-1850):A historiographical essay.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1,(3):pp.383-401.引文见第383、401页。 (40)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没有主标题,见Mayhew R J.Geographies Genealogies.In:Livingstone D and Agnew J (eds.).Handbook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Sage,2011,pp.21-38. (41)Mayhew R J.Geographies Genealogies.In:Livingstone D and Agnew J(eds.).Handbook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Sage,2011,P.21. (42)一个重要的插曲是,哈特向曾给出了一个类似于“辉格”的经典说明:“如果带着地理学应当如何如何的先入之见来进行研究,并按此在过去的作者中寻找与我们意见相投的人,然后又把他们置于与似乎持有不同地理学观点的人相对立的地位,那就无法取得我们这两个历史研究的目的了……相反,这却容易歪曲地理学过去的发展和先辈地理学家的思想,以求切合于论争的目的。”(哈特向著,叶光庭译:《地理学的性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7页)但哈特向显然主要地还是以实证主义科学观来写历史的,而且他将地理学视为一种经典的区域描述科学,由此引发了著名的“例外论之争”(见叶超,蔡运龙:《地理学方法论变革的案例剖析——重新审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之争》,《地理学报》2009年第9期,第1134-1142页)。 (43)Skinner Q.Vision of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60. (44)Mayhew R J.Geographies Genealogies.In:Livingstone D and Agnew J(eds.).Handbook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Sage,2011,P.27. (45)Mayhew R J.Geographies Genealogies.In:Livingstone D and Agnew J(eds.).Handbook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Sage,2011,P.31 (46)尤其是对于斯特拉波的《地理学》之命名,Mayhew在论述之前直接怀疑道:“假如这本著作这样命名是史实的话”。见Mayhew R J.Geographies Genealogies.In:Livingstone D and Agnew J (eds.).Handbook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Sage,2011,P.29. (47)笔者无法翻译如上术语,为2013年2月11日梅休给笔者电邮中对上述词语的解释。 (48)Mayhew R J.Geographies Genealogies.In:Livingstone D and Agnew J(eds.).Handbook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Sage,2011,pp.32-33. (49)Withers C W J.Encyclopaedism,modernism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geographical know ledge.Transactions,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1996,(1):pp.275-298; Withers C W J.Geography,scien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arly-modern Britain:The case of Scotland and the work of Sir Robert Sibbald.Annals of Science,1996,(1):pp.29-73. (50)Livingstone D N.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a contested enterprise.Oxford:Blackwell,1992. (51)Mayhew R J.The Character of English Geography,c.1660-1800:A Textual Approach.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1998,(4):pp.385-412.引文见第406页。 (52)Mayhew R J.Landscape,literature and English religious culture,1660-1800:Samuel Johnson and languages of natural descriptio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4. (53)Mayhew R J.Enlightenment Geography:The Political Language of British Geography,1650-1850.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0年。 (54)Mayhew R J.Historical Cultures and Geography,1600-1750.Bristol:Thoemmes Press,2003. (55)王庸:《中国地理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2页。 (56)侯仁之:《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 (57)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编写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年。 (58)唐晓峰:《“反向格义”与中国地理学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81-91页。 (59)孙俊,潘玉君,汤茂林:《从科学史到思想史:中国地理学史研究的理路分析》,《地理研究》2013年第12期。 (60)还需要注意者,本文作者之一贾星客主张,在超越的意义上,通过抛弃绝对的“自我中心”和“他者中心”的观念,“格义”就可能变成“会通”。 (61)见评论文章孙俊,潘玉君:《〈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述评》,《地理学报》2012年第10期,第1149-1152页。 (62)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94页。 (63)潘晟:《时代性的地理陈述与阅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辑,第5-16页。 (64)指地理学作为独立学术学科形成的条件:一是学科范式的形成;二是学科体制的形成;三是地理学被社会接受并获得支持。见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页。 (65)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第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4页。 (66)Elshakry M.When Science Became Western:Historiographical Reflections.Isis,2010年第1期,第98-109页。 (67)“appropriation”一词中文有“占用”、“占有”、“挪用”、“专有化”等译法,作者主张译为“凝聚”,以避免殖民主义研究的倾向,强调基于人类学所述的“主位”与“客位”相统一的知识生产过程,而非强势的殖民生产过程。 (68)Patiniotis M.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History of Science in the European Periphery Meets Post-Colonial Studies.Centaurus: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spects,2013年,DOI:10.1111/1600-0498.12027 (该文由作者提供,目前仅见网络版摘要: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1600-0498.12027/abstract)。 (69)Elman B."Universal Science" versus "Chinese Science" :The Changing Identity of Natural Studies in China,1850 -1930.Historiography East and West,2000年第1期,第68-116页。 (70)见阙维民:《中国高校建立地理学系的第一个方案:京师大学堂文学科大学中外地理学门的课程设置》,《中国科技史料》1998年第4期,第70-74页;张九辰:《中国近代地学主要学科名称的形成与演化初探》,《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1期,第27-34页。标签:地理学论文; 科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历史地理学论文; 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地理论文; 历史学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科学史论文; 地球科学论文; 思想史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