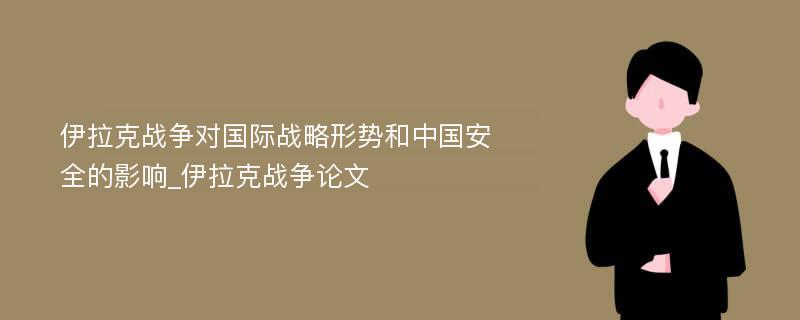
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战略态势及中国安全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态势论文,伊拉克战争论文,战略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无论是战争爆发还是战争结局都没有大悬念的伊拉克战争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一场“先发制人战”,打响了美国在新世纪初实施“先发制人”国家安全新战略的第一炮;它是一场“民主改造战”,美国企图通过军事手段达到推翻萨达姆、建立亲美政权的政治目的,继而开始在中东地区的“民主化”改造进程;它是一场“世界秩序战”,它引发了在建立什么样的世界新秩序问题上的激烈较量,导致了力量对比关系的全球性分化组合。伊拉克战争是冷战结束十余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一场战争,将对21世纪初叶的世界战略态势和中国安全环境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战略企图
“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美国对伊动武的借口。“解除武装、交出政权”是美国对伊动武的直接目的。推行新的霸权战略,建构新的世界秩序,开展新的文明改造,经略新的地缘政治,是这场战争的深刻战略企图。
(一)推行新的霸权战略
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战略的推进经历了两个阶段,现已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冷战型霸权”阶段。这个阶段从冷战结束之后一直到九一一事件之前,主要表现为美国冷战思维猖獗,霸权气焰嚣张。美国称霸所要解决的世界安全问题主要是冷战后遗症问题,包括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和海湾战争。九一一事件后,美国霸权战略的推进进入第二阶段,即“反恐型霸权”阶段。震惊世界的九一一事件虽然极大地挫伤了美国的霸气和锐气,但也为美国推行霸权创造了新的机遇,提供了很好的借口。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将数万大军派驻中亚,在东南亚开辟了反恐的“第二战场”,反恐成为美国推行霸权最具欺骗性的一面旗帜。以伊拉克战争为转折,美国霸权战略的推进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新帝国霸权”阶段。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帝国论”在美国政坛甚嚣尘上,颇有市场。这一理论认为,面对21世纪混乱无序的世界,国际社会需要一种符合人权和现代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的“新型帝国主义”;这种“新型帝国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的综合体,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实力超群的惟一超级大国,是“新型帝国主义”最具资格的代表;“新型帝国主义”的重要使命是“使落后国家的文明和统治获得新生”,而对恐怖主义、“无赖国家”和“失败国家”,则要进行坚决打击和铲除,以建构世界“有序的民主秩序”,按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一统天下。美国也确实具备这样的实力和条件。一方面,美国实力超群,拥有绝对的战略优势。2002年美国GDP总额高达10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额的30%,另一方面,反恐为美国推行新帝国霸权提供了很好的机遇,所以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借口,就是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联系,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实力加机遇”,就形成了美国推行新帝国霸权得天独厚的条件。伊拉克是美国推行新帝国霸权的最大的敌人。2002年9月20日,布什政府颁布了他上台以来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认为美国在冷战结束十多年来第一次找到了真正的敌人,一是国际恐怖主义,二是“邪恶轴心”势力。在美国看来,伊拉克是美国的双重敌人:伊拉克既是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后台,萨达姆政权与本·拉登“基地”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伊拉克又是“邪恶轴心”势力的首要国家。因此,美国推行新帝国霸权就先拿伊拉克开刀。
(二)建构新的世界秩序
伊拉克战争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事件本身,其政治意义远远重于军事意义。因为这是美国在21世纪初发起的旨在构筑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重要战略行动,是美国称霸世界庞大战略计划中的第一步。随着这场战争的结束,人们粗略地看到了美国构想的“世界新秩序”。首先,这个“世界新秩序”将由美国主导。上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勾画了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蓝图。该报告宣称,美国将保持世界上最强大的能够打败任何对手的军事力量,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对其第一军事大国地位构成威胁,也不允许任何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对美国扩展民主势力的战略构成威胁。如果出现这种威胁,美国将果断地予以消除。其次,美国将依靠超强的实力,采取“先发制人”战略,打出一个“世界新秩序”。2002年初,布什在《国情咨文》中首次发出了“先发制人”战略信号。《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先发制人”正式确定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布什政府认为,对任何可能威胁美国利益的国家和行为,都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予以消除。布什在2003年3月17日的演讲中公开声称:“在敌人既不宣战也看不见敌人的时代,等待敌人首先发起攻击再加以还击不是自卫,而是自杀。”(注:[日]《时代》周刊2003年4月5日。)因此,“消极的自卫无异于被动的自杀”,“在自己遭到攻击之前就把敌手干掉”,就成为“先发制人”战略的经典表述。伊拉克是当今国际社会公开挑战美国霸权的典型国家,美国对伊作战将形成一种范式,即今后无论谁挑战美国利益,谁就将有可能变成第二、第三、第四个“伊拉克”。再次,通过加强联盟,营造一个“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和平”。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是建立在特定联盟基础上的,这既有以北约和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轴心的西方阵营联盟,又有打着“反恐”旗号所组成的松散的国际反恐联合,还有此次临时拼凑的对伊作战联盟。美国选择伊拉克实施“先发制人”战略,以杀一儆百,为建构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开好头。
(三)开展新的文明改造
“文明的冲突”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社会占主导的理念。这一观点认为,对西方世界构成最大威胁的是文明冲突,尤其是伊斯兰教文明、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美国政府认为,要想消除文明冲突,必须对伊斯兰教文明进行重大改造,向穆斯林世界输出美国的“民主”与“自由”,“为阿拉伯国家建立民主秩序”,使伊斯兰教文明与西方文明尽可能地和睦相处。事实上,在阿富汗战争尚未打响前,美国政府就开始秘密策划军事打击伊拉克的方案。2001年9月17日,布什总统在一份“绝密”文件中,就向军方授意制定攻伊计划(注:[英]《每日电讯报》2003年3月18日。)。2001年9月20日,美国的新保守派人士联名致信布什总统,要求美国通过军事方式对伊拉克实施“民主化”改造,认为“这是一个对美国具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目标”(注:[美]《外交政策聚焦》2003年3月2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哈斯主张美国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积极地推进中东“民主化”进程,启动新的美国中东伙伴关系方案,以缩小穆斯林世界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民主差距(注:新华社华盛顿2003年3月20日电。)。2003年2月26日,布什发表演讲,为即将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贴上了“民主化”的标签。显然,对伊作战是美国以伊拉克为突破口,对伊斯兰教文明进行改造的战略步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伊拉克是否真正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在于美国改造伊斯兰教文明的方针已定。如果萨达姆接受美国的苛刻条件,美国就可能实施“软改造”;如果萨达姆不接受美国的条件,美国只能实施“战斧式的硬改造”。这也就决定了小布什发动的对伊作战与老布什发动的海湾战争有重大的区别。老布什主要是为了在军事上教训伊拉克,而小布什则是要全面改造伊拉克,对伊作战仅仅是全面改造伊拉克计划的最初方式和手段。通过军事打击伊拉克,实现“倒萨”目标,在伊拉克建立一个亲美政权,输出和培植西方式民主,为改造伊斯兰教文明树立一个样板,这才是小布什的真正目的。可见,改造伊斯兰教文明是美国21世纪初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经略新的地缘政治
九一一事件重构了世界地缘政治结构,改变了美国的安全战略观,使中东地区成为攸关美国21世纪国家安全的核心区域。这一地区是国际恐怖势力的滋生地和国际反恐斗争的主战场,是欧亚非三大洲的战略结合部,是世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储备最密集的地区,谁控制了这一地区,谁就能够主导世界。仅以石油为例,中东是世界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其石油储量占世界石油总量的65%。伊拉克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已探明的石油储量高达1120亿桶,占世界石油储量的10.9%,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居世界第二位。据美国官方统计,目前美国石油需求量中的55%依赖进口,到2020年这个百分比将增加到65%~70%(注:[美]《外交政策聚焦》2003年1月16日。)。美国企图通过伊拉克战争,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资源,继而主导整个中东地区石油资源战略格局,影响世界石油资源战略态势。这样,美国就可以利用伊拉克丰富的石油这张“牌”,取代沙特,打压欧佩克,制约俄罗斯。因此,对美国来说,控制了伊拉克,就等于掌握了21世纪世界石油安全的战略主动权。
可见,军事打击、军事管制、建立亲美政权、民主改造是美国“攻伊倒萨”战略的四步曲。
伊拉克战争对世界战略态势的影响
伊拉克战事虽然短暂,但对世界战略态势却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世界战略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分化组合,单极与多极的较量更趋激烈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霸权欲望急剧膨胀的典型表现,标志着美国进入了新一轮霸权扩张期。但制衡因素也不断增长。法、德、俄反战联盟对美国发出了挑战,许多弱小国家也公开谴责美国的霸权行径。世界范围内的反战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美国陷入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孤立的境地,对伊战争成了“孤独的霸权扩张”。这与九一一事件后世界大多数国家支持美国进行反恐战争形成了鲜明对比。
伊拉克战争引发了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与俄罗斯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传统的以北约为纽带的西方联盟受到冲击,欧洲地区的利益关系面临新的分化和整合。第一,法德俄与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磨擦是多年来各种矛盾的集中表现。这场摩擦的实质并不是要不要推翻萨达姆的问题,也不是要不要使用武力的问题,而是美国如何对待法德俄所期望的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政治地位问题。虽然今后有关国家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会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关系,但这种深刻的政治分歧难以弥合。因为法德俄与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磨擦远远超出了伊拉克问题本身。第二,美俄关系在经过短暂改善后又陷入了困境,俄罗斯以改善与美国关系为重头戏的“西进”战略难以如期推进。俄美两国从各自利益出发,双边关系仍有调整和发展的余地,但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前两年的水平,俄罗斯将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继续牵制美国,并把“西进”战略的重心转向发展与欧洲核心国家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上。第三,欧洲进一步分化,各种矛盾困扰着欧洲。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反战派和以英国、西班牙为代表的主战派将欧洲的政治版图重新划分。北约的改造与转型将成为今后美欧争夺的重点。无论对法德还是对美国来说,今后都需要北约,都希望对北约进行改造,“北约的欧洲化”和“北约的政治化”将是今后北约改造与转型的矛盾焦点。欧盟政治军事一体化将在曲折中艰难前行,北约和欧盟双东扩战略难以并行不悖地发展。法德轴心将进一步加强,以期构成欧洲新权力中心。法德轴心的强化将把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向前推进。总的来看,美欧战略联盟关系不会因伊拉克战争而解体,既联合自强又相互依存,既谋求合作又相互斗争,将是今后美欧关系发展的基本特征。
(二)“文明冲突”难以平息,民族宗教矛盾将此起彼伏
以伊拉克为突破口对穆斯林世界进行“文明改造”,是美国“攻伊倒萨”的战略本质。然而,九一一事件后,世界进入了“大众恐怖主义”时代。这场战争的后果很有可能是激化文明的冲突,而不是缓解文明的冲突,美国因此将陷入文明改造的困境。第一,伊斯兰教文明与美国的基督教文明是两种不同质的文明,通过民主改造伊拉克,企图使伊斯兰教文明“美国化”,无疑是天方夜谭。美国在伊拉克推行“炮舰民主”,期望在中东地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改变其国内体制和推进民主化。但这会引发地区局势的不稳定。20世纪大多数在美国强行干预下实现体制转换国家的失败就足以说明。第二,长期以来,美国推行偏袒以色列、打压巴勒斯坦的中东政策,是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的重要根源。据对中东国家最新的民意调查表明,在美国战略盟友的沙特阿拉伯,被调查人中对美国表示不满的高达95%,在摩洛哥占91%,约旦占80%,埃及占79%(注:[俄]《独立报》2003年3月21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3年3月23日。)。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绪将使美国“改造”伊斯兰教文明的企图难以得逞。第三,伊拉克战争将进一步激发中东国家的反美情绪。第一次海湾战争制造出了“基地”组织,第二次“海湾战争”有可能催生一个个新的“基地”组织,以反美为焦点的民族宗教矛盾将此起彼伏。军事击败萨达姆对美国来说可谓是轻而易举,而政治改造伊拉克必将困难重重。推翻萨达姆是预示着中东出现第一缕“民主”的曙光,还是激发反美的“伊斯兰圣战火花”,恐怕连美国人自己都心怀疑团。
(三)中东地缘政治日益凸显,大国地缘战略面临调整
美国对伊作战具有深远的地缘战略价值,即通过军事控制伊拉克继而控制整个中东,将美国的欧亚战略联为一体。或者说通过军事控制伊拉克,把其纳入美国势力范围,使伊拉克变成美国在中东的第二个“以色列”,建构新的战略“桥头堡”,对其他中东国家产生地缘政治辐射效应。5月2日布什在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的同时,抛出了解决巴以问题的中东“和平路线图”。这既是美国在控制伊拉克的同时,通过巴以问题的解决,实现主导中东事务的战略,又有极力消除伊拉克战争的负面效应、转移国际社会视线、安抚中东国家的策略考虑。伊拉克的重建和中东“和平路线图”的实施,将直接决定美国中东战略的命运,影响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
在此背景下,世界大国和大国集团的地缘政治战略将做新的调整。中东地区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将成为大国矛盾的焦点。如何对待这场战争的政治创伤,如何参与战后伊拉克的重建,如何与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新政权建立关系,如何与主导中东事务的美国打交道,将是今后大国和大国集团战略调整的主题。
(四)世界军事斗争形势将更加复杂,全球军备竞赛会愈演愈烈
美国推行赤裸裸的军事扩张政策,将引发世界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欧盟军事一体化进程有望加速推进,法德军事合作关系将进一步加强。俄罗斯将把加强军事实力作为重振大国雄风的战略支撑。中东国家为了防止成为美国下一个教训的对象,将更大规模地购买先进武器装备。被美国列入重点打击对象的“流氓国家”和“无赖国家”,将采取更加冒险的方式加紧扩充军备,力图以武抗美。朝鲜继续强化军备的方针不会改变。日本将继续搭乘美国“反恐”、“攻伊”战车,走向世界军事大国,“先发制人”将成为日本未来的防卫战略。南亚大陆的印巴将展开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总之,国际军控与裁军的进程将严重受阻,世界有可能出现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激烈的军备竞赛。
伊拉克战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一)伊拉克战争将影响中国周边总体战略环境
中国尽管不是美国“先发制人”战略打击的现实目标,但美国在亚太地区频繁实施这一战略直接影响中国国家安全。
首先,亚太地区将成为美国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的重要目标。美国有可能以伊拉克为“模式”和“样板”,对亚太地区其他国家进行同类改造。这将影响中国总体战略布局,缩小中国亚太外交空间,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使中国在亚太地区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得不直面美国的强力存在,不得不频繁与美国进行正面周旋。
其次,美国在伊拉克得手后,肯定会腾出手来解决它所关注的其他问题。如果美国以强硬方式解决朝核问题,将使中国面临直接压力,东北亚安全环境有可能发生复杂的变化。
再次,如果美国对伊拉克的战略得逞,将引发中国国内政治的联动,中国不仅面临更加严峻的民族宗教矛盾,而且面临更大的“西化”压力,中国维护国内政局稳定的任务将更加突出和繁重。
(二)伊拉克战争将影响中国周边军事形势
美国以亚太地区为战略重点的军事力量存在的明显加强,使中国面临更大的军事压力。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部署将呈现出东(东亚)西(中东和中亚)为重、南(东南亚、印度洋)北(东北亚)策应、巩固重点、全线推进、战略合围、联为一体的战略特征。
首先,美国将把东西两线作为亚洲军事力量部署的重点区域。在西线,美国军事实力空前加强。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集结了30万大军,在中亚驻扎了两万余人的军队。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在伊拉克仍将部署至少6万大军,使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维持在15万人的规模,并企图将中东与中亚的军事力量联为一体。在东线,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并没因伊拉克战争而被削弱,反而有所加强。2003年3月初,美国国防部决定调派12架B—52战略轰炸机和12架B—1战略轰炸机前往关岛,以增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威胁力。
其次,美国军事重返东南亚的步伐明显加快,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菲律宾、新加坡等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
再次,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正在形成点面相串、区域相联、总体战略合围的态势。美国在亚洲的总体兵力今后将多达25万人,大大超过在欧洲地区10万驻军的规模。
在美国以武称霸战略的驱动下,亚太地区有可能出现新的军备竞赛,安全环境趋于动荡和复杂。中国周边主要国家和地区军备竞赛趋势的加强,将使中国面临更加复杂的军事斗争形势,不排除因热点问题激化而直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可能。台湾当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中国统一大业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三)伊拉克战争将使中国面临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
伊拉克战争是对国际反恐战争合法性的严重背离,是对国际反恐斗争正义性的严重扭曲。在这场战争的负作用下,国际恐怖势力将在积蓄力量后重新整合,恐怖威胁会有增无减。从北高加索、车臣地区经中东、中亚到南亚、东南亚这个广阔的U形区域是国际恐怖势力猖獗和民族宗教矛盾交织的高危弧形地带。中国正位于这一地带的腹地,处于国际恐怖势力和民族宗教矛盾环形合围的中心。在这个高危弧形地带上任何矛盾的激化,都将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使中国面临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
(四)伊拉克战争将使中国石油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中国是一个石油消费大国,2002年石油消费总量位居世界第三,2003年有望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中国石油消费的1/3靠进口,2002年进口石油多达7100万吨,其中一半来自于中东地区。美国主导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将使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由依赖阿拉伯国家为主转向依赖美国为主,从而增大美国对中国的能源牵制。美国主导中东石油资源,有可能导致国际能源力量对比的失衡和油价的不稳,从而影响中国能源安全战略。因此,适时调整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尽快建立中国的石油战略资源储备制度,是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保证。
标签:伊拉克战争论文; 军事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石油资源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石油美元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世界现代史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