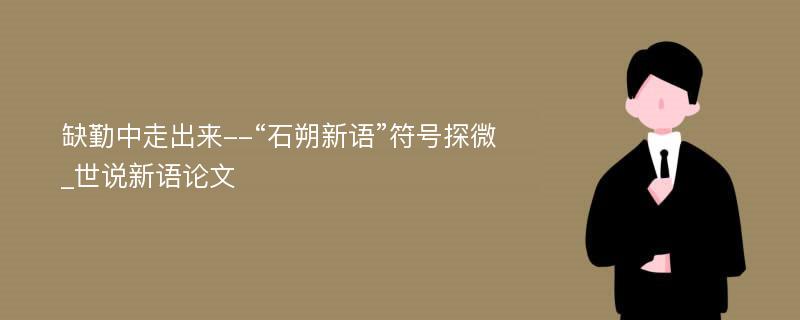
以缺席的方式出场——《世说新语》众庶符号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论文,方式论文,世说新语论文,探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说新语》1130则故事的叙述中,时常出现种种十分微妙、极为隐秘的点划之笔,它们如此细弱不彰,幽隐难识,而感应殊方,玄意幽远,它们矫如游龙,翩若惊鸿,难以言称,难以语宣,因此千百年来,读者对此保持了意味深长的沉默。笔者今欲破此千古玄默,发此龙踪鸿影,也委实万分艰难。种种形迹,色色妙影,何可一语而彰!
一、人的遮蔽:众庶符号的初步指认
在《德行第一·华、王之优劣》里有这么一段叙述: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则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②
故事的表层是叙述两位汉末名士在逃避战乱的过程中,就是否允许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同船避难之事流露出的前后不同的态度,以此彰显二人高下有别的胸襟与眼界,及其道德责任感和意志力量对于他者苦难的最终承受力。故事的叙述十分精彩,寥寥数语,人物的内在精神与外在形貌即一同毫发毕现。
然而,正当我们醉心于刘义庆的精妙之笔而直趋那个遥远的时代、关注时代精英们活色生香的人格表演时,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毫不起眼的形影:那个要求一同避难的乘船人。这个陌生的乘船人的确太具有令人忽视的一切“特征”了,他在文中出现的唯一作用几乎就是卸掉人们对其关注的眼神,引人他顾:无名、无姓,不知其身份、地位、来处、去处,没有形貌、表情、动作、语言,所有这一切特征汇聚成了一种声音:“请忽视我!”于是千百年来我们都听从这种召唤,忽视了“它”。如果不是逃难、乘船等具体的生活情景尚能引起我们向“人”的动作方面作出联想的话,我们几乎要怀疑他是不是人了。这个被抽掉了人的一切具体特征的空洞的乘船人只是一个“人”的符号,表明他仅仅——然而——却是本质地以“人”的形式和资格出现并隐匿。由于这一符号的“空性”特征,使之反倒领有了含容人的一切特征的功能,故此这一符号乃是一种具有普泛能指意味的人的符号,是一种代表芸芸众生的“众庶符号”。刘义庆在进行故事的叙述时显然不想赋予这个“众庶符号”以任何人的征象,他的全部目的就在于凸显华、王二人的人格优劣,乘船人只是刘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不得不然的必要设置。
如果说乘船人尚有因逃难、乘船等具体的生活情景能引起我们对其身份、动作作出朦胧猜想的话,另有一类故事则连这种猜想的可能也被取消了。《雅量第六·祖士少好财》记载: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在这一段里,引起笔者关注的并非祖士少和阮遥集二人各自对钱财与木屐的癖好,而是将此二人各自对物的沉溺引向前台并作优劣分判的“人”(“人有诣祖”)和“或”(“或有诣阮”),与前文的乘船人相比,这里的“人”和“或”在人的具体个性特征方面被抽象的更干净、更彻底,连与之相关的生活情景也被取消了,因而其作为具有泛指功能的众庶符号也就更纯粹。尽管“人”和“或”同时均发出了“诣”和“见”的动作,但这恰恰只能说明这是符号的“人”和“或”发出的符号动作,而与生活着的个性没有半点关涉。
经过如此淘洗,“人”和“或”等开始以一种纯净的姿态升格为指涉一切名不见经传的众庶的符号,它们没有任何个体的个性,但却含纳了一切个性;不牵涉任何生活的细节,但却随时可与活跃于前台的名士们的生活境遇关联起来。从特殊性层面而言,“人”和“或”因被抽掉了人的一切个体特征,无法如同真实的魏晋名士和历史人物一样同台演出,因此构成某种个体的人的缺席;从普泛性层面言之,“人”和“或”却又泛有人的一切特性,以绝对的人的意识与前台的演员进行深度对话,从而构成某种绝对的人的出场。这个“人”和“或”在《世说新语》的众多叙事段落中反复出现,它们或播撒而为万殊,或收凝则为“人”“或”。一方面积极渗透到各个叙事段落、结合具体的语境,化现成具有对话功能、微具个性色彩的众多变相(乘船人即其例);另一方面又从具体细节中抽身,升华为历史人物展开其生存本相的纯粹意义场,行踪无定,默而玄微。由于其本身没有人的任何表情和个性,无法以活生生的纯粹的个体显形,因而一直为我们乐于被细节激动的心灵所忽略,但它们却是刘义庆展开叙事、切入历史、勾画魏晋风度而无法逃避、挥之不去的魔影,是《世说新语》的文本形式和意蕴的隐秘而实在的建构力量。不仅如此,由于任何文本与其他文本都存在某种互文、镜鉴、阐释关系,我们更可由此探讨这种众庶符号在其他文本中的变相以及相关的功能显现,思考由其秘密创生的历史意识和文化精神。
二、人的缺席与出场:众庶符号的表意层次
《世说新语》以记载被正史遗落的片断史事、勾画人物风神姿容、透视人性千般变化为要义,在重视人的社会性、伦理性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语境中首次将笔触直指个体的人以及人性本身,披剥万象,发露神理,显现人性峥嵘,被现代学者推为代表了人的觉醒的文本。四百余年间的贵族、名士、士族大姓纷纭上场,总共127姓、684人,一一过堂。“竹林七贤”、王羲之、谢安,庾、郗、殷、褚各露神姿。如何准确而深入地描画出这众多名士贵族的内在神韵,的确令人颇费思量。然而刘义庆的书写行为出人意表:在文本的宏观形式格局上,刘义庆游弋于经典与子史的边缘结合部,创造了将孔门四科、史传、诸子的文本形式杂糅为一的新形式,布下了类似于围棋高手布局、有利于后着跟进、随意驰骋的“大模样”格局。全书起于德行,终于仇隙,三十六品决不游离于人之外,而是般般指涉人性,是对人性展开的三十六层医学似的CT切片分析,因这种分层透视,人性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德行与邪险并生,雅量共仇隙同行,任诞掩映方正,豪奢凌夺鄙吝,一个意蕴空前饱胀的“人”就被这种“大模样”的形式结构所引生。在微观层面,刘义庆设计1130则笔记,将“大模样”的宏观形式结构所创造的“类”化的人性播撒于其中,与具体的细节结合,于是种种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活生生的名士们乃活跃起来。
正是在这一书写进程中,“人”“或”这种众庶符号不经意的滤过刘义庆的指缝参与了文本形式与意蕴的建构以及人物性格的塑造。在每一条短短的笔记中,只有“人”“或”所代表的“绝对意义上的人”不失时机的潜入,像光源一样从文本深处遥照前台,作其烘托与掩映之功,那被聚焦的具体的人物个性才能在这些短促的语段中迅速彰显。笔者始终认为,刘义庆对“人”“或”的书写并没有刻意经心,没有达到一种深度自觉而使之成为某种引人注目的语言技术,故此长久以来被读者所忽视。与他精心设计的“大模样”格局和三十六品分层透视相比,“人”“或”所代表的众庶符号毋宁说是为某种力量的吸摄而参与到刘氏的行文之中,是为展开魏晋名士鲜明的人格精神的需要而呼唤着众庶符号的出场。
“人”“或”在微观层面对文本建构的方式委实十分微妙,它们因势赋形,变化万端。概而言之,大体有如下几式:
(一)泉岩激响
即如流泉激于石岩,声腾于外。众庶符号本身并无确切的人格面貌,但它们能够发出某种符号动作,激发主体人物的动作言语,显见其内在人格精神。这种方式在《世说新语》中占有了最多的数量。《识鉴第七·傅嘏论三贤》:
何晏、邓飏、夏侯玄并求傅嘏交,而嘏终不许。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谓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杰士,虚心于子,而卿意怀不可交。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隙。二贤若穆,则国之休。此蔺相如之所以下廉颇也。”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劳,能合虚誉,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何晏、邓飏有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内无关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之,此三贤者皆败德之人耳。远之犹恐罹祸,况可亲之邪?”后皆如其言。
此段中,“诸人”究为何许人不可详知,但他们能因荀粲劝说傅嘏与何、邓、夏侯之交,可见大约也是此辈中人,这是语境赋予了“诸人”以如许意义。晋人品物鉴人之风甚盛,若不是这些不知名的“诸人”(众庶)因荀粲说合傅嘏,则无从激发傅嘏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我们也无从知晓三贤的本质。这些无以名之的众庶不言而动,如沉默的石岩激响流泉,将傅嘏的内在人格精神、社会对三贤的反响、乃至于整个晋代的品物鉴人之风一起向我们揭开,并与同这种揭开一同出场。
复有《任诞第二十三·雪夜忆友》载: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人问其故”一语断断不可略而不置,若非此“人”之问,则无王子猷之答,王的回答为其不可思议的动作提供了一种解释,其纵情适性,潇洒出尘的性格乃跃然于目前。人之问与王之答即如岩泉相激,晋人的任诞豪纵之情便腾跃于我们内心。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缺席者即驾船者或船夫,由于他并没有直接参与同主人公王子猷的对话或动作,我们也就阙而不论了。
(二)双绽花枝
两个以上主体人物借助于众庶符号各显其内在本性,如枝发双朵,彼此映照,共酿春意。这种方式在文中也占有一定数量。《德行第一·谢奕放老翁》:
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太傅(指谢安——笔者注。)时年七八岁,着青布绔,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老翁如枝,谢奕、谢安俱因此枝而绽放,他们各自抵达了自身的精神制高点:谢奕的从谏如流和谢安的弱而悲悯,人性的两种优美表现形态俱各绽放在老翁这一“枝条”上,而文中对主体人物的细节描绘更使这种人性美的绽放有寓目摇神之妙。
复有《任诞第二十三·桓子野吹笛》载: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此中“人”“客”都十分幽隐,王子猷和桓子野的光焰遮蔽了“人”“客”的容颜,他们所起的作用也正如枝条之用:借助于“客”的指认和“人”的“相闻”,素昧平生的桓、王乃得神交,惺惺相惜,共显其任诞之风。魏晋名士们独立而任纵不羁的精神生活借此“枝条”得以展现。使“客主不交一言”的神韵得以可能的却是“客云”、“人云”,没有“客云”、“人云”的居间传达,知音的情节就难以展开。
(三)默然引照
与前二法相比,“人”“或”已无言无动,但符号的在场意味着某种精神的在场,这种精神的在场引得主体人物发出与之相关的某种意志反应,有如镜照之用。如《雅量第六·顾雍闻子丧》:
豫章太守顾邵,是雍之子。邵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
此中“僚属”“宾客”乃为“人”“或”在具体语境中的化现,是典型的众庶符号。它们虽默无言动,但顾雍却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才表现出对于丧子之痛的克制,从而折射出晋人试图对周代以来血亲伦理之情的某种痛苦超越。沉默的“僚属”们如一面镜子,鉴照着晋人的此种努力。
复有《方正第五·何充正色》载:
王含作庐江郡,贪浊狼籍。王敦护其兄,故于众坐称:“家兄在郡定佳,庐江人咸称之。”时何充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敦默然。旁人为之反侧,充晏然,神意自若。
此中之“照”比上段更妙,有双层鉴照之功:何充与王敦的正面冲突为明照,而其厉声直言与“旁人”的反侧惊心为暗照。暗照比明照更有力,不仅照出了世故与耿介的人格渊殊,更照出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底蕴:一方面强调权力独尊,下级服从上级,另一方面又倡导犯颜直谏、公理为先。矛盾的理念铸造了对立的个体价值选择以及相应的人格类型,“旁人”的出场将这种文化底蕴带向了前台。这种默照之式在书中处处可见,今不妨再出《文学第四·刘尹答殷中军》一例以证:
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写水着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
此中“诸人莫有言者”的默照之功犹为有力,刘尹对殷浩深刻哲学问题的绝妙回答正得“诸人”无知的沉默而显,晋人的玄思也因此“照”耸动人心。
(四)暗启玄音
行文中连“人”“或”的符号标记都没有了,但符号的精神能量仍在(也许是“大象无形”?)并且能够启动主体人物的内在神韵。笔者曾十分犹疑这能否作为众庶符号建构文本的一种方式,思量的结果仍然确认这确乎是一种极为隐秘的文本构建法则:“人”“或”虽渺无行踪,泯然无迹,但它们以主体人物某种“对象化的精神”而“在”。此“在”着的精神与主体人物一体相关,有如空谷中飘荡歌吟的回响,山谷的回声是对人事的表征。在文中,“暗启玄音”之法传达的往往是主体人物最深刻的理念和情致。《文学第四·简文论佛经》:
佛经以为祛练神明,则圣人可致。简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然陶练(指道家炼丹活动——笔者注。)之功,尚不可诬。”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学术价值取向自由而多元的时代,儒家的正统地位并不如两汉得到普遍的尊奉,新道家兴起,同时佛经翻译迎来第一次高峰,这使儒、佛、道三家互释成为可能,著名的魏晋玄学因之产生。此段中晋简文帝对学佛致圣的思索和道家炼丹之功的认识传达的正是多元价值取向下新思想发生的时代之音,因为当时整个时代都在进行这种精神探索,故此我们不妨认为简文“自言自语”的“玄音”应有其感发的精神场地,但因并无具体的个人够格与简文的深刻疑虑对话,故而“人”“或”隐去,只留一种精神默然承听。事实上,也恰因这种对象化的时代精神存在着,故能引动简文的哲思。
复有两则有关桓温的笔记。《言语第二·桓公北征见柳》: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言语第二·桓公入峡之叹》:
桓公入峡,绝壁天悬,腾波迅急。乃叹曰:“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如何?”
在这两段中,桓温的“自言自语”发出的都是情绪浓烈的深沉慨叹:前者是对生命易逝、人生如寄的感喟;后者则深叹忠孝难以两全的人生价值选择。语境告诉我们:桓温发此感慨时周围不可能没有人,不可能没有众庶,但他似乎并不需要某个具体的人作出回应,他们只要聆听就是了,这就造成既无需“人”“或”符号标记的到场、而众庶(群体)之精神又不可缺席的格局。他的独语实非自言自语,是这种对象化的群体精神存在着,启发了其含蕴哲思的“玄音”,此音传达了整个时代共有的困惑。
综上所述,以“人”“或”为表征的众庶符号用四种方式参与了《世说新语》文本形式与意蕴的微观建构,不仅最终完成了文本形式的整体创新,而且使魏晋人物的精神风貌纤毫毕现。经过上文细致的分梳和整理,我们发现众庶符号对于文本的建构力度呈现由浅入深、由显至隐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中,一个规律鲜明地显现出来:当“人”“或”具有某种形影,即如果语境赋予众庶符号以相对具体的言语、动作、身份时,此众庶符号必定只能诱发主体人物单方面的性格侧面(“泉岩激响”、“双绽花枝”中皆是),此第一层;当“人”“或”进一步退隐,仅具符号资格,即众庶默无言动时,主体人物乃显现精神全体或显其最鲜明突出的性格(“默然引照”数例可证),此第二层;而当“人”“或”完全从表层隐去,只留精神在场时,主体人物便有某种形而上的深情和哲思感发(“暗启玄音”已见),至此,“人”“或”就化作了纯粹精神,取得了主体人物对象化的形式而与之达成深刻共鸣,共同传达出形而上的时代之音,此第三层。“人”“或”涉入文本越具体,越只能激发主体人物单方面的性格因素,而随着“人”“或”本身的个体性格因素渐次弱化乃至于完全消隐时,主体人物的深层性格便愈益凸显,终至于跃升为整个时代特有的某种情绪和思想(简文的佛道之思与何、王、向、郭的玄学相通;桓温的人生短促之叹是阮籍情绪的翻版,都具有代表性)。如此,众庶符号与主体人物之间便构成了一种你进我退、你弱我强的互反关系。随着关系的展开,众庶符号所代表的不同类型的人的精神也随其创造的主体人物在不同的层面显现,亦即四种文本构设方式带来了“人”“或”内在人格寓意的三层出场,使得《世说新语》在最深的精神意蕴层次妙义纷错,花烂映发,幻影层叠。这大约正是此书具有无穷魅力的原因所在。
三、自否定:众庶符号对文本的辩证建构
“人”“或”等众庶符号何以有如此妙处呢?我们有必要在哲学层面给予回答。前文已述及:看不出刘义庆在使用众庶符号时有某种深度自觉性,他倒是在随意处分众庶时颇有点“自觉”。但他终究无法逃脱众庶的魔影,名士贵族们独特的人格显现强烈呼唤着“人”“或”的到场,这就折射了一个深刻的哲学原理:辩证法。大道无方,此“道”就是辩证法。此“道”神奇之处乃不可思议,黑格尔说:“辩证法在同样客观的意义下,约略相当于普通观念所谓上帝的力量。”③他又说:“无论知性如何常常竭力去反对辩证法……它(都)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其他各级意识和普通经验里的法则。”④这种法则运用于《世说新语》的文本构造及其解释中显然是有效的。
刘义庆对人性进行的三十六层分层透视颇具形而上的静态观照意味,这种透视达到了十分精致的地步,三十六种人性类型也非常符合人性的整体真实。但他不可能把这种静态描述永远进行下去,他固然可在宏观格局上作此设计和描述,而一旦涉及微观的事业,即涉及具体人物的具体性格,对这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动态展开性和自我反思性的人物个性生命进行把握时,这种静态的分层透视与描述便不起作用了。正是在这个层面,辩证法开始悄悄潜入,抓住了刘义庆的手,进行人物性格的创造性书写并同时展示辩证法自身的魅力。
黑格尔说,辩证法的灵魂就是否定,而且是物的“自否定”。这种否定就是物永远对自身说“不”,并且进一步对“不”说“不”。因对自身说“不”而产生有差别的、与自己相异的他物(但这“他物”决不是此物之外的某物,而是同一范畴之内自己对立面的映现);因对“不”说“不”又回到自身,从而保持物的前后一致的同一性,达到对自己的肯定。因此物之所以保持前后一致的同一性其实是自否定的结果。“象我们曾经看到那样,同一无疑地是一个否定的东西,不过不是抽象的空无,而是对存在及其规定的否定。而这样的同一便同时是自身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否定的自身联系或自己与自己的区别。”⑤在因自否定而产生的对立双方中,“每一方面之所以各有其自为的存在,只是由于它不是它的对方,同时每一方面都映现在它的对方内,只由于对方存在,它自己才存在……在对立中,有差别之物并不是一般的他物,而是与它正相反对的他物;这就是说,每一方只有在它与另一方的联系中才能获得它自己的(本质)规定,此一方只有反映另一方,才能反映自己。”⑥
黑格尔的思考对我们探索刘义庆的微观书写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人”“或”之所以与同魏晋名士一起显现原是人性自否定的结果。一种精神要表现自己,它就必须借助于自己的对立面来表现。魏晋名士贵族们为了表现自己的高贵、优雅、玄思以及特有的时代精神,它们就必须借助于与之存在种种差异性的众庶符号。我们看到众庶符号所代表的精神似乎与名士们有异,实则根本一体相关,是辩证法的否定本性遇合具体语境之后在三个层面的显现。
魏晋名士贵族们是一个个性张扬,崇尚自由的群体,惟其如此,他们的个性确乎千殊万类,形形色色。为了表现这形形色色的个性,“人”“或”乃将自己的一切特征抠掉或抹平,从而获得一种随物赋形的自由,因此“人”“或”看似一种简单粗朴的符号,实则暗含了一种随感赴应的绝对自由精神,这就确保了前文述及的四种法式带来三层出场这种“以缺席的方式出场”之奇特效应的发生。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老子·四十五章》)老子的洞达智慧算是揭开了众庶符号的功能本质。
“人”“或”对《世说新语》的文本构设法式及其体现的辩证法精神为我们思考其他文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国古代散文中有时出现的“主”“客”对答,汉赋中“子虚”“乌有”等符号的设置,绘画中的“留白”,以及哲学上“空”“无”范畴的提出等等,在在让我们瞥见了“人”“或”的幻化之身。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显形的文学、哲学、史学、艺术的构成史,就是“人”“或”的魔影飘忽滑行的历史,是否定性的辩证法永恒潜入的历史。以此而言,“人”“或”甚至具备了一种普泛的隐喻意味。
注释:
①笔者检索1990-2011年21年来有关《世说新语》的研究论著共860余篇(部),统计其研究方向及论题涉及魏晋玄学、魏晋风度、审美风尚、宗教情怀、文学趣味、价值取向、社会习尚、女性地位、文献梳校、语法范型、字义疏证等二十余种,但尚未发现如笔者此文之切入角度。
②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4页。按:小标题为引者所加。以下所引《世说新语》原文均出自此书,因有篇序,极易翻检,不另外一一注明页数。个别文字断句,据该书1993年修订本。
③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79页。
④黑格尔:《小逻辑》,第179页。
⑤黑格尔:《小逻辑》,第250~251页。
⑥黑格尔:《小逻辑》,第254~255页。
标签:世说新语论文; 刘义庆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文化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读书论文; 人性论文; 小逻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