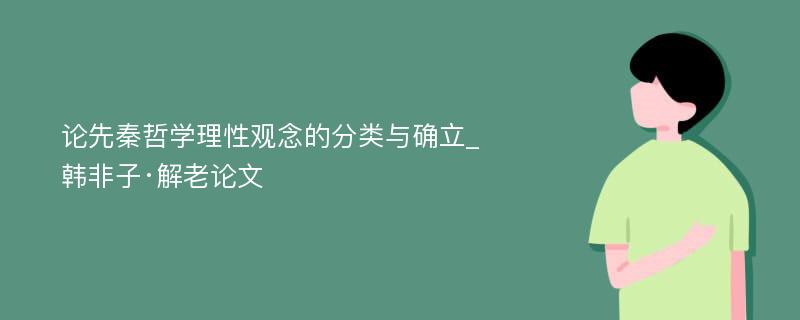
论先秦时期哲学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理性论文,观念论文,哲学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哲学传统中存在与西方哲学经典概念理性相对应和意义趋同的概念。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理性”,也存在哲学理性观的历史演变。《易传·说卦》提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理与性对举,意蕴主要涵括自然事物的本性与内在规律,属于认识论范围。《后汉书·党锢传序》谓:“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这里“理性”概念指个人品性修养,属于修养论范围。南北朝《刘子新论》的《辩乐篇》谓:“淫泆、悽怆、愤厉、哀思之声,非理性、和情、德音之乐也”;其《和性篇》则谓:“理性者使刚而不猛,柔而不懦,缓而不后机,急而不懁促”。这里“理性”概念指中和适度的伦理审美律则,属于伦理学范围。唐代佛教律宗道宣祖师在《广弘明集·启福篇序》中强调通过内心体验妙悟真谛,“明则特达理性,高超有空”;佛教典籍《四教仪集注》(下)在阐释“理即佛”时谓:“但有理性自尔即也”。这里“理性”概念指称佛学“空理”,具有宗教思辩的本体论意义。宋代程颐强调:“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河南程氏遗书》卷22下);朱熹也提出过“理之性”(《朱子语类》卷95)。这里“理性”概念指称儒家伦理学与哲学本体论相统一的伦理本体,理性与德性在本体层面上相统合。由此可知,“理”与“性”为同一层次的本体范畴,组合而为“理性”概念,具有哲学本体论意义;“理性”概念基本上包括认识论、伦理学(及修养论)和本体论三种视界;道宣与程颐的理性概念从本体论义域发展为伦理学与本体论相统一的义域,可以用来指代中国哲学的理性观念。中国哲学理性观念主要包括本体理性、自然理性、伦理理性三大基本类型,相应于西方理性之宇宙理性、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基本涵义〔1〕。中国哲学理性观念的历史演变经历了先秦时期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秦汉时期理性发展的伦理化主导取向、魏晋至隋唐时期理性发展的本体化主导取向、宋明时期理性发展的本体化和伦理化相整合的取向、近代时期理性观念的转型新变五个发展阶段。本文试就先秦时期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及其特点加以专题阐述。
一、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
先秦时期理性的观念建构奠定了中国哲学古典理性的理论基础,它主要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即自然理性、社会理性、本体理性和逻辑理性,这些理性类型规范了中国哲学古典理性范畴发展演化的基本格局。
1.自然理性(“天地之理”)
先秦时期,“理”作为普遍的抽象概念已经进入哲学思维领域。具有哲学范畴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理性概念的最基本内涵是指一切物理、事理、条理、规律,即自然理性。《易传·系辞》所谓“天下之理”就包括天地自然之理,即指世界万物发展变化的内在本性和必然规律。荀子认为天地万物有其自身的固有特性和运动规律,这就是“物之理”,它表现为宏观“大理”和微观“色理”,即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总规律和具体事物各自的本性特质和特殊规律。“求可以知物之理”(《荀子·解蔽》),事物的规律之理是可以认知和必须探求的,要求主体“尽其理”(《荀子·大略》),充分地把握和利用自然理性。庄子所谓“天理”、“万物之理”(《庄子·养生主》),是指天地万物固有的内在规律和客观必然性。“万物殊理”(《庄子·则阳》),更指明事物本身各自的特殊规律。庄子反对“悖于理”而主张“顺于理”,即遵循客观事物的天然本性和自然规律,因为它是相通于自然无为之道的。韩非指出“物有理,不可以相薄”(《韩非子·解老》),物各具其理,形成自己的独特属性而不相混淆。作为一种客观性存在的“定理”,其消长变化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他进而指出:“得事理则必成功”(《韩非子·解老》),强调只有按照事物的本性和规律办事,才能实现预期目的而取得圆满成功。
先秦儒、法、道诸家都赋予理性概念以自然之理的涵义,“物理”、“事理”、“成理”、“定理”等均指称自然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为“大理”和“异理”(或“殊理”),既注意到天地万物的总体性普遍规律,同时又注意到各个事物的具体属性和特殊规律。所谓“必然之理(《商君书·画策》)和“其理不竭”(《庄子·天下》),则揭示出自然界事物客观规律的必然性和发展性特点,并强调“明理”、“通理”、“循理”,表现出利用自然理性服务于人类自身的自觉意识。
2.社会理性(仁理和法理)
先秦时期的社会理性主要由儒家的仁理和法家的法理所构成。儒家以仁义为宗论理,主张礼制仁政德治,创立了伦理理性(或称道德理性)。《易传·说卦》所谓“性命之理”,即包括社会人事之理和道德伦理基本涵义。“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易传·说卦》),把道德伦理原则视为人类的天然本性和绝对存在,具有天赋色彩。孟子认为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为仁义礼智之端萌(《孟子·公孙丑上》),人心同然之“理”,就是仁义礼智美德。主体自身这种仁义理性既有天赋性质,又有一种自我完善的修养要求。孟子还强调五伦之义,“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这种仁义伦常理性原则是对孔子仁爱精神和礼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用礼来涵盖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制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礼也者,理也”(《礼记·仲尼燕居》)。礼制被确认为理性,仁义礼智和伦理关系成了伦理理性的基本内容。荀子反对孟子的先天道德观,强调礼义规范是人为制定后天习成的。他主张以“礼义文理”来节制和化导人的贪欲恶性,使亲疏有别、贵贱有差、尊卑有等,从礼义教化角度崇扬“礼之理”,使其万变而不乱,有序而得宜,“礼岂不至矣哉”(《荀子·礼论》),礼义理性成为不可移易、至高无上的终极原则而绝对化永恒化了。
法家则赋予理性以法的内涵,亦即法理。法家学派代表人物以法为本而建立法治理性,慎到首倡以法为治国之理,商鞅主要从社会实践角度施行了法理,韩非全面发展了“法之理”。他强调治国任法,严刑峻法,“故治乱之理,宜务分刑赏为急”,即以区分刑罚奖赏为要务,使法令刑罚成为强国利民的工具,并且指出执政者必须“任理去欲”(《韩非子·南面》),“任理”即是任法理,突出法治而摒弃人治。韩非批评郑国子产任智不任法的失误,强调“修其理”,即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制法规以达到治民防奸的社会效果。法家认为法理是治国理民的法宝,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儒家着重于从社会伦理道德角度论理,使理性范畴道德化和抽象化;法家偏重于以国家法令刑罚制度论理,使理性范畴法制化和功利化。
3.本体理性(绝对道体)
先秦时期本体理性以老庄的道本体论为主要代表。老子以普遍性质的道来说明世界的起源,认为道是“先天地生”的宇宙本原,出现于上帝之先,以自然无为为最高原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本体之道具有无限的创生能力,产生万物并决定万物的发展变化。老子的道论为整个世界的生成和变化探寻统一而抽象的总原则,有着绝对的终极的本体意义。它承认道作为世界万物的最终根源是一种兼具物质性和精神性的本体理性〔2〕。 庄子把老子的道论发展为超越一切物质的神秘的纯精神性的宇宙本体。这种道体先天地而存在,化生天地万物,是超验超象的客观化的绝对观念或精神实体。在庄子看来,道与理是相通的,“道,理也”(《庄子·缮性》);但道与理层次不同,道先在于和支配着天地万物而成为自本自根的宇宙本原,而理是道内在于事物的具体自然性质和变化规律。就宇宙本原的意义而言,道比理层次更高;就事物的特性和规律而言,道与理意义相当,理成为道的外化表现。道与理虽有绝对与相对之别,但又是相通同极的〔3〕。由“人理”到“天理”,都遵循自然无为之道, 与宇宙精神相往来并合而为一。总之,老庄的道本体论作为一种非神格性本体之理,反对全知全能的上帝和天命观,试图从自然界本身寻求说明世界的终极原因,标志着对理性认识方面的概括性和抽象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先秦时期天道论(本体之理意义)有天道有神论(天道有为思想)和天道无神论(天道无为思想)之别。商周以来传统的天道有神论(上帝论和天命观)是一种简单的神学目的论,认为冥冥中有一个主宰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有人格意志的神,它作为一种超自然存在在本体意义上接近于绝对理性,是神圣化永恒化的精神实体。天道无神论即老庄的道本体论,它以道为宇宙的本体和世界万物存在的根据。在宇宙本原意义上来说,天道有神论和天道无神论同居于本体理性的层次,其区别在于神格性和非神格性。
4.逻辑理性(“名实之理”)
先秦时期的“名实之理”开启了古典逻辑理性的意义建构。孔子的正名思想性质上属于政治伦理观念,但透露了关于概念(名)和事实(实)关系的看法,显示了逻辑理性的萌芽。惠施的“合同异”论由事物同异的相对性而推出万物“毕同”的结论,强调由这种抽象统一而达成“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神秘境界。公孙龙言离异而不及任何合同概念,其“离坚白”论在思辩特点上视名词概念为永恒的孤立存在,割断了特殊概念与一般概念的内在联系。惠施的逻辑思想从个别中抽取一般,从差异中抽取同一,片面夸大了事物性质攸同的一面;忽视了事物之间质的差异,相对主义色彩较浓。公孙龙的逻辑思想实质上把具体事物的性质孤立地加以夸大,否认其间统一关系,陷入了诡辩论。墨家的逻辑理性力图使逻辑学从伦理学的缠绕中挣脱出来,把形式逻辑作为一种独立科学来对待。墨辩主张“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并阐述了“名”、“辞”、“说”三种基本思维形式。“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墨子·小取》),即要求名词概念必须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语言符号要能准确地表明判断内容,进行推理时要正确揭示出因果必然律。墨辩指明了归纳和演绎综合运用的类取类予的思维方法,并提出了“或”、“假”、“效”、“辟”(譬)、“侔”、“援”、“推”的多种推理方法。荀子的名辩思想包括“名”(概念)、“辞”(判断)“辩”(推理)的逻辑思维形式结构。他还提出别名到共名的概括和共名到别名的限定的方法,兼顾“以一持万”(《荀子·儒效》)和“疏观万物”(《荀子·解蔽》)即归纳和演绎两种推理形式的综合应用,并着重强调了名实必须相符、同异必须相别的原则。
先秦时期的“名实之理”把理性范畴的涵义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领域扩展到人类思维领域,开拓了理性观念的思维空间,丰富和发展了古典理性范畴的涵义。特别是墨辩和荀子建立了基本的逻辑思维形式结构和逻辑推理方法,推动名理朝着逻辑科学的方向发展。
二、理性建构的基本特征
先秦时期对理性范畴的涵义作了基本规定,以“物理”标名而为自然理性,在于揭示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的运动规律和必然趋势;以仁理、法理标名而为社会理性〔4〕,主要包括社会人事关系、 伦理道德原则和法令刑罚制度;以绝对道体标名而为本体理性,在于揭示宇宙万物的最终根源和总体依据;以“名理”标名而为逻辑理性,在于揭示逻辑思维形式的基本法则。这样,先秦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构成了中国古典理性观念的基本内容,奠定了古典理性观历史演变的基本格局。秦汉以后,古典理性观念主要沿着自然理性、伦理理性和本体理性的方向演化和发展的。逻辑理性虽然有所发展并在发展中重视科学理性思维方法及实践操作功能,但并非从纯形式角度探讨名实关系,又主要侧重于概念论,不完全等同于西方传统逻辑学。汉初黄老学派《经法》进一步阐发名实之理,认为必须“审察名理”,“循名究理”(《经法·名理》),即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形式对事物的名实关系和运用变化规律进行考察探究,使所得的正确认识与事物的形名一致。南北朝《刘子新论·审名》则提出“课言以寻理”的观点,承认概念的形式理性内涵存在,强调与客观理性一致的言理兼通(逻辑形式)。由于中国古代逻辑科学发展的内外机制条件的限制,逻辑理性虽曾有过一定的发展和科学运用的实绩,但终究未能形成独立的科学体系。
先秦理性观念的建构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理性观念与古代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论密切关联。荀子论自然理性而推崇“坚强以持,分别以明”的科学精神和“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荀子·大略》)的求证态度。惠施的名辩思想与当时数理自然科学知识积累密切相关。他的合同异逻辑观点因“历物之意”而建立在科学抽象认识的基础上,并力图从逻辑上论证宇宙的矛盾性与无穷性的统一存在。墨学的名实之理同样以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论为基础,非常重视实践的验证方法,把理性思维和经验观察结合起来,名辩不仅依靠形式推理,而且据以客观事实。理性范畴与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紧密相连,使得自然理性获得了客观实在性和实验参证的名格。第二,理性观念与伦理学畸型结合。这主要表现为理性观念的伦理化趋向。不仅是孔、孟、荀对伦理理性内涵规定和类型确立的创成,并把伦理理性加以政治化而形成仁政与德治学说,而且连属于思维领域的逻辑推理也受到伦理化的影响,所谓“正名治国”即是强调名理要符合社会政治伦理标准,孔子关于“正名”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规范,要求角色按各自名分实践行事。尽管荀子划分了伦理正名和逻辑正名及惠施把“正名定分”的政治伦理观念转向遍为万物说的历物论的逻辑分析,但名理并没有摆脱伦理学的阴影。荀子把逻辑理性思辩之旨归结为“推礼义之统”(《荀子·不苟》),公孙龙强调“正名实而化天下”(《公孙龙子·迹府》)。先秦时期理性范畴的伦理化趋向不仅限制了理性本身的深入性探讨,而且直接成为汉代道德理性主义的渊源。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先秦时期以天理论人理,因而不同的理性类型之间有沟通,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深刻影响到理性本身的内在联系和理性观念的整体流变〔5〕。
注释:
〔1〕参见黄南珊《论西方理性观念的整体流变》(载《学术论丛》1994年第4期)和《西方理性概念内涵分析》(载《晋阳学刊》1995 年第1期)。
〔2〕老子的道论兼具物质性(由气所赋)和精神性双重特点, 是对宇宙本体的一种模糊性认识,可以用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提出的原始思维的物质性与精神性互渗现象的观点加以解释。
〔3〕先秦时期, “道”是“与理相应”(《韩非子·解老》)的理性概念,但有异同之辨。在指称原理、准则和规律的意义上两者相同,同属于自然理性。但“道”为“万理之所稽”,“道尽稽万物之理”(《韩非子·解老》),道已包容和统摄万理,万理归于道之一源。在老庄那里,道已经升格为本体理性,鲜明地显示出本原性、绝对性特点。
〔4〕儒家伦理理性在汉代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强权维护和尊崇而被定格为经典化和法典化的绝对权威,又经《大学》《中庸》《孝经》《白虎通义》和董仲舒的畸化推衍而被系统化、神圣化和体制化了。它标志了中国哲学理性观的道德理性主义实质。
〔5〕本文写作参考了徐荪铭、蔡方鹿、张怀承、岑贤安、 张立文所著《理》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谨加说明并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