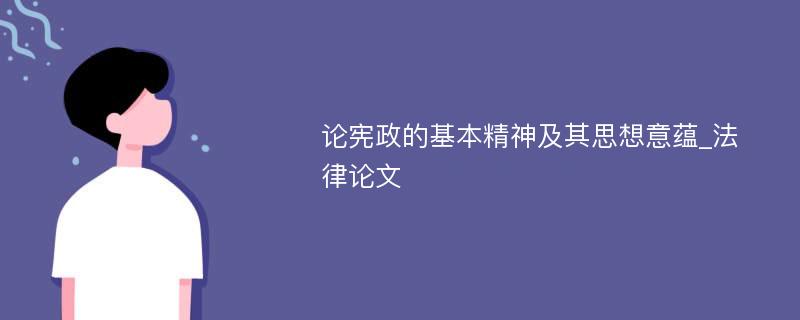
论宪政的基本精神及其思想蕴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政论文,蕴涵论文,思想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学
在当代,政治制度应以宪法为基础已得到普遍承认,建立宪政已成为从传统国家步入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为什么现代政治制度要建筑在宪法之上?宪政应当体现的基本精神是什么?这些问题却并没有被人们所完全理解。
一、宪政的基本精神
宪政精神是宪政的内在规定,宪政是宪政精神的实现形式和制度安排。因此,要把握宪政精神,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宪政。所谓宪政(constitutionalgovernment),是立宪政体的简称。指由社会多数人制定的或被多数人承认的宪法性法律(通常指成文宪法)所确定的公共权力的组织、相互关系、职责权限、活动规则以及旨在保护公民权利的政治体制。宪政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秩序主要表现为法律秩序,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均纳入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法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最高的权威性。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能否将公共权力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这不是因为公民个人的守法不重要,而是因为公共权力是社会权力集中化的代表,作为社会的中枢系统,承担着将具有利益差别和冲突的群体整合为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公共权力本身的运行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整体的运动状态。只有当维护公共秩序的主体本身处于秩序状态时,社会整体才可能是有秩序的;也只有当制定和执行法律的主体服从于法律的控制时,社会才可能建立起普遍的法律秩序。建立宪政是社会法治化的首要任务。
宪政与无限权力是不能共存的。它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把公共权力纳入法律的严格控制之下,这是对无限权力的根本否定。从理论上说,无限权力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权力行使具有任意性。这并不是不承认权力握有者具有理性能力,而是说如何行使和怎样行使权力取决于权力握有者的暂时意念。二是权力行使的空间范围没有明确的界定,可以干预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和任何领域。三是权力被赋予绝对的权威,表现为对行使的结果不负责任。不受限制是无限权力的本质特征。现代政治制度所以要以宪法为基础,就是要通过制定宪法的形式为公共权力设定根本的规则──提供合法性来源,规定行使的依据、标准和程序,确定界限,明确责任。宪法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制度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在于它应当反映和容纳社会公民和各种政治集团的要求。这是宪法权威性的来源,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人类的政治斗争史已经证明,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将一个或若干个重要的社会利益群体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或不能找到满足其需要的有效办法,那么,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宪法仅是一种法律文件,但这种形式的产生,在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作用在于,为各种政治集团合法地、和平地解决政治分歧提供了基础和框架。使人类为实现长治久安的理想找到了一种现实的、可行的办法。这也是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暴力冲突,付出了血与火的代价之后,所创造的最重要的成果。“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来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①正是在个意义上讲,宪法不是公共权力握有者(政治代表)的意志表达,更不是社会政治集团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是一种社会契约,是社会成员的政治约定,是人民产生公共权力并约束公共权力的政治决议,是公民权利的宣言。立宪政体的本质特征是,宪法是政府的“前提和基础”,“宪法是一种先于政府的东西,而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一国的宪法不是其政府的决定,而是其建立政府的人民的决议。”②宪法的签定标志着一种新的政治关系和政体的确立。在这种新型关系中,社会所有成员和集团都必须服从宪法的权威。南非新宪法的颁布,从根本上说,不是某一个政治派别的胜利,而是南非人民共同的历史选择。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新南非的诞生。
没有宪法就没有宪政,但有宪法不等于就是宪政。宪政不仅要以宪法为基础,而且要以一部特殊的宪法,一部体现着特定精神的宪法为基础。这种特定精神构成了立宪的基本法则,即无限权力不应存在,一切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都根植于宪法之中。那种把宪法对政府权力的授予,视为对政府权力的保障的看法是一种误解。授权本身就意味着限制,即政府必须服从于宪法所授予的目的的制约。没有得到宪法授权和不依法行使的权力都属非法。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这一精神所体现的两个宪政原则是:第一,公共权力是人民通过宪法授予的,不得行使宪法没有授予的和禁止行使的权力;第二,公共权力不得侵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而且有义务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深刻地把握宪政的基本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无法区别宪政与民主的差异,也不能认识宪政精神对民主原则的超越价值,更不能理解二者结合的意义。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或一种政治设计,就其探讨的主题而言,不过是柏拉图创立的,并被以后的思想家所继承的政治哲学传统的继续,即什么样的国家是理想的国家,谁应当统治这一问题。尽管不同的思想家的结论迥异,但这一主题并没有变。民主的基本涵义是实现人民的统治。近代民主制度对古希腊民主思想的重大发展,就是通过创立代议制的形式将人民的统治的理想,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内变成一种可操作的现实。代议制(人民通过定期的、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选举的方式,授权自己的政治代表行使公共权力的体制)是现代国家实现民主的必然选择,这种选择相对于君主专制而言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这种政治设计本身仍然存在着一种无法彻底摆脱的风险,即人民选出的政治代表与人民相背离的危险。而且这种背离的危险在通常的情况下,又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所以又有着极大的欺骗性。因此,仅仅依赖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议制是无法消除公共权力在常态下的任意性的。在一定意义上讲,宪政的产生是为了克服民主的局限,以成文宪法为主体的一整套法律制度作为既定的规则,为公共权力的行使确立标准,并限制公共权力的自由裁量。通过这种明确的、公开的、具有强制性的外在约束,使公共权力的运行规范化、合理化。宪政与民主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二者的价值基础是共同的,即为了实现和保障公民的权利。但二者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民主是从积极的一面强调公民参政实现公民的政治权利;而宪政是从消极的一面强调限制公共权力来保障公民权利。宪政精神超越于民主的逻辑,同时也克服了传统政治哲学的局限之处在于,无论是谁应当统治,不管是哲学王、君主,还是公民及其代表;无论是以上帝的名义,还是以人民的名义,都不应具有无限的权力,都没有绝对的权威。这才是宪政精神的独到之处,也是其价值所在。
二、宪政精神的思想蕴涵
在存在着利益差别和冲突的条件下,公共权力是保障人类社会处于秩序和文明状态的一种实质性要素。然而,历史展示给人类的,不仅有公共权力的合理运用所呈现出的辉煌历史,而且还有公共权力的滥用所造成的历史性悲剧。与其说这是公共权力的辉煌和悲哀,倒不如说这是人类本身的辉煌或悲哀。因为公共权力并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一种力量,实际上它是人的力量的一种表现。公共权力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因此,人类在认识公共权力的同时,不得不对自我本身进行思考。宪政精神作为指导宪政建设的基本法则和原理,也必然蕴含着一套关于对人性及公共权力的看法和观念。这种人性观和权力观实际上构成了宪政精神的思想内核和认知基础。
在人类的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主张实行法治的思想家对人性的看法及表述上尽管存在着差异,但有着一个共同的基本点,就是认为人是不完善的,人性是有缺陷的。人的不完善性一方面表现在人的认识活动要受到环境和条件的制约,而且,人的理性能力本身也具有不完备性、非至上性,甚至荒谬性;另一方面,人又是有需求、欲望和冲动的,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需求也具有相悖的一面。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人可能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侵害他人或社会的利益,违背社会正义。另外,从人的实践活动角度说,人的实践活动具有个人性,即实践行为的实施及方式是通过个人行为表现的。这就决定了人的实践活动具有特殊性和非确定性的特征。因此,为了防止个人对他人及社会的侵害,为了消除或减少政治生活中的任意性,建立一种稳定的社会期待,这就需要制定规则,将个人的独特的意志和行为置于非人格化的普遍的支配力量之下。而能起到这种作用的,只能是具有明晰性、确定性和非人格化的法律。法律制度的作用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创造为个人的自由所必需的政治条件。在一定意义上讲,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是针对人的某种不完善而设计的。弗洛伊德曾表述过这样的思想,凡是禁止的,往往是人们所欲求的。承认人的不完善,本身就包含着承认人的创造物也不具有绝对的意义。法律包括宪法通过一定的程序也是可以被修改的。
将人的不完善性与肯定法的重要性联系起来,进而论证法治优于人治的理论传统是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他认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③他把法律看成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性的体现,具有一种为人治所无法做到的“公正性”。因此,“由法律遂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祇和理性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④在中世纪,随着基督教在欧洲文化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作为基督教文化核心内容的人的“原罪说”也在西方广为传播,并对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人的不完善观念不但被近代的一些思想家所接受,而且被加以系统化,成为批判封建专制的有力思想武器和设计未来政治制度的理论依据。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洛克从历史的反思中告诫人们:“谁认为绝对权力能够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⑤被称为美国“宪法建筑师”的詹姆斯·麦迪逊在阐述制宪精神时,用简洁的语言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与建立有限政府的内在关系。他指出:“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⑥这就是说,承认人的有限性,不仅要承认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有限性,更重要的是承认所有人的有限性;也不仅要承认人的暂时有限性,更主要的是承认就最终意义上讲,人的有限性是无法超越的、是不可克服的,这是问题的实质。如果相信社会中存在有全智全能的人,或者相信人经过修炼可以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那就等于说,人类现实活动的意义在于发现这种具有全能人格的人,并把权力交付给他,其他人只需俯首贴耳唯命是从就行了。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凡是政治专制盛行的地方和时期,往往都是和这种崇尚圣人明君、权威崇拜的文化相联系的。德国的哲学家费尔巴哈说得好:“凡是将自己交付于神的全能的人,凡是相信一切发生的和存在的事情都是出于神的意志而发生和存在的人,他就永远也不会想法去消除世界的缺陷,无论自然的缺陷或社会的缺陷。”⑦由此可见,是主张人治还是法治,寻求无限权力还是有限权力,在这不同的选择背后,蕴含着两种不同的人性观。
与人的不完善的观念相适应,尤其是受到近代形成的渴望自由、追求平等、尊重人权的人文精神的影响。一些思想家对公共权力普遍持有谨慎的和防范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公共权力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恶”(洛克语)、一种“免不了的祸害”(潘恩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把公共权力称之为社会的“累赘”和“肿瘤”。“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⑧公共权力所以被看作是一种必要的祸害,就在于公共权力的存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公共权力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因为社会产生着它所必不可缺少的某些公共职能。而当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对立和冲突的力量危及社会自身的生存时,特别是社会成员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以致没有多余的时间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时,社会公共职能的独立化就不可避免,公共权力就必然成为维系社会公共秩序、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另一方面,公共权力自身又具有扩张性和腐蚀性,这种倾向有可能造成对社会和公民权利的侵害。所谓扩张性,是指公共权力作为一种支配力量,本质上是一种意志的强加,特别是由于对强制力的垄断,使它具有了“不顾其参与这种行动的人进行抵抗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⑨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是任何其他社会组织难以与之抗衡的。公共权力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总具有无限扩张的倾向和滥用权力的危险。孟德斯鸠在揭示权力的扩张性时指出:“越是有权力,就越是拼命想取得权力;正是因为他有了许多,所以要求占有一切”。⑩“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1)
所谓腐蚀性,是指公共权力对人具有腐蚀作用。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公共权力对社会价值的分配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公共权力的这种角色使它具有了某种交换价值,即被用来交换其它价值的价值,而且,公共权力的握有者又有着自身的利益要求。因此,“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而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线的诱惑。”(12)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国家看成是一种祸害的。“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13)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首先要破除的就是对国家的迷信和崇拜。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产生国家崇拜的原因,是把国家看成“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事物的崇拜。”(14)需要强调的是,恩格斯所说的国家──公共权力,不是特指某一种国家类型,而是就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言的。恩格斯的思想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那就是,要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我们需要防范的不仅是掌握权力的个人,而且也包括公共权力本身。“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15)孟德斯鸠曾提醒人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6)这实际上也是宪政精神所蕴涵的基本思想。
注释:
①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版,第14页。
②《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6页。
③④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篇1253a,第Ⅲ第1287a。
⑤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6页。
⑥〔美〕《联邦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⑦《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70页。
⑧(13)(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6页、第334页、第336第页。
⑨汉斯·格恩,赖特·米尔斯合编:《马克思·韦贝尔文选》,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80页。
⑩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6页。
(11)(16)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12)〔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4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