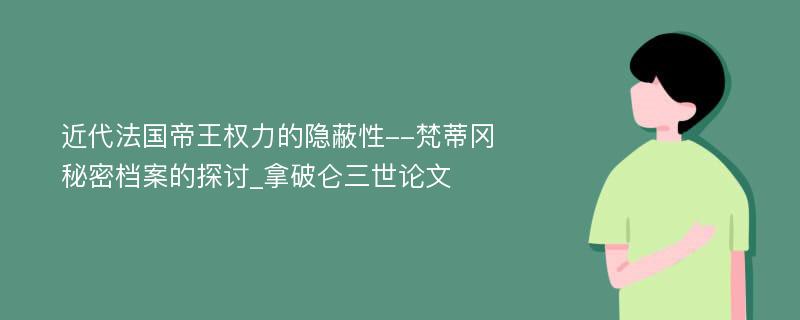
法国近代保持或重获君主权力的隐匿言行——梵蒂冈有关秘密档案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梵蒂冈论文,法国论文,君主论文,言行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中期,法国的政治生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1830年复辟王朝垮台后,波旁家族如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曾尝试夺回统治权力。奥尔良王朝于1830年建立,它曾促进工业革命,而后陷入困境,因此主张维护正在实行的统治权力。波拿巴家族是法国君主权力舞台上的后来者,当时它希望不断加强第二帝国的统治力量。简言之,保持手中的统治权,或者企图再次掌握统治权,谋求和维持统治权力是上述三个王族的共同点,也是19世纪中期法国政治制度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于这些王族而言,渴求江山永固或盼望枯木生花,事关家族的兴衰存亡。宪法、宣言、政变、起义等已经公开地展示了这些王族的政治意图,但是它们通常限于说明基本原则,而秘密档案往往能够进一步充实粗线条式的历史梗概。“梵蒂冈秘密档案馆”所收藏的文献,为法国君主权力的保持与重建提供了佐证,使权力得失的历史显得更加有血有肉。由于法国的绝大多数居民信奉天主教,这些王族都曾努力寻求罗马教廷的支持。
梵蒂冈有关秘密档案
“梵蒂冈秘密档案馆”(Archivio Segreto Vaticano)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加深对于法国的波旁、奥尔良、波拿巴家族争夺君主权力历史的了解。笔者曾以“欧洲大学”(设在佛罗伦萨)教授的身份,获准进入梵蒂冈秘密档案馆,查阅与法国相关的秘密档案。在红色纸盒内保存着重要文件:“教皇陛下庇护九世与君主及私人的通信,第二部分:法兰西”(Correspondenza epistorale di S.S.PioⅨ con sovrani et particolari.Ⅱ.Francia),它们分别收藏于三个淡灰色的纸夹中:A.“法兰西—君主”(Francia-sovrani,1846,11-1877,4,共392页,反面五号,下同);B.“法兰西—私人”(Francia-particolari,1848,3,6-1856,4,12,共285双页);C.“法兰西—私人”(Francia-particolari,1856,5,7-1876,10,1,共444双页)、“与主教们的通信”(Corispondenza coi Vescovi,1862-1874,共934双页,多为来自法国各地教会的信函)与“圣彼得的财政”(Denaro di S.Pietro,1862-1874,共795页,个别文件属1835年)。上述档案共2850页,为1846-1877年的文献,包括大量信函,其中少量信函未标明日期①。
有关信函涉及波旁、奥尔良、波拿巴这些法国王族,尤其说明它们曾如何维护手中的王权,或追逐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些文献当中,拿破仑三世与庇护九世之间的往来书信数量较多②。寄给教皇的信件属于来函,一般为原件,而教皇的书信多为抄件,即发出信件的底稿。盒中也有教皇与其他国家君主,例如玛丽—特丽萨的通信,但是数量十分有限。在此全部通信中,笔者未曾见到关于法国1848年革命的内容。若干信函实际并非机密,却因收发信人的重要地位而保存在这个著名的秘密档案馆内。档案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它使许多人与事真相大白,但是有时也只能显露冰山的一角,毕竟档案馆只能收藏到它能够获得的文献。
法国王族有关人士与庇护九世的通信大体上包括数类内容:波旁家族的政治幻想、奥尔良家族的政治愿望、波拿巴家族的政治原则。
波旁家族的政治幻想
1830年7月,法国发生革命,倒行逆施的查理十世垮台,波旁王朝终于完全结束在法国的统治。查理十世亡命英国,但是波旁王族一直企图东山再起。查理十世于两年后从英国的爱丁堡迁到了捷克(当时属于奥地利帝国)的布拉格,3年后来到也属于奥地利帝国的戈里齐亚(Gorizia,现属于意大利),他于1836年在该地死于霍乱。1830年8月2日,查理十世让位给儿子路易(1775-1844年,又称“路易十九”)。路易生性软弱,当日他便将继承权让给了侄子亨利(1820-1883年)。这个亨利与庇护九世有过某些交往,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亨利此人即波尔多公爵与尚博尔伯爵,在史书中经常称作尚博尔伯爵。波旁王朝派妄想让他重登王位,因而称他为“亨利五世”。路易十六于1793年断头,其子所谓“路易十七”死于1795年。路易十八于1824年死去,身后无嗣。1830年,亨利获得了继承权,他成为这一家族唯一的“王位继承人”。他的父亲贝利公爵已于1820年遇刺身亡。亨利肩负着家族的重托……
正当波旁家族妄图复辟的时候,1848-1873年期间,它与奥尔良家族曾有分分合合的交往。奥尔良王朝于1848年被推翻,从此它也企图重新掌权。第二帝国时期,尤其第三共和国初年,波旁家族与奥尔良家族曾企图推翻共和制度,恢复本家族的王朝。1871年7月补选后,国民议会的650名议员中,共和派占据多数,波旁王朝派近80人,奥尔良王朝派约270人。为了对付共和派的强大势力,上述两个家族曾考虑联合行动。但是,这两派的政治目标存在着明显的距离,波旁家族倾向专制的王权,而奥尔良家族则主张君主立宪甚至保守的共和。双方的“融合”于1873年8月达到高潮,但是10月29日尚博尔伯爵指出应该“消除误解”,他决不放弃“亨利四世的白旗”,“我个人微不足道,我的原则高于一切”。此后,两个家族分道扬镳。1883年,“亨利五世”死去,波旁家族男嗣断线,家族复辟无望③。
在那时的政治形势下,“亨利五世”与庇护九世保持着联系,梵蒂冈的秘密档案中可以找到相关的文件,它们数量有限,内容并不复杂。
1860年1月14日,亨利给教皇撰写一封长信。“当我们可爱的伯父(路易十九)去世之时,当我本人成为波旁家族的首领之时,我曾面对整个欧洲,抗议法国王位合法继承中所发生的变化。”“我到处反复地大声宣布,我从未拒绝我自己的权利。自我出生以来,根据法国王朝的古老法律,我便获得了这些权利。我愿意为祖国的真正利益服务。”“我由衷地相信,为了世界安宁与传教自由,同样需要罗马教廷在俗权方面的威望。对于教皇的君主权利与独立自主的一切损害,便尽对于其他君主的权利与独立自主的损害。”亨利表示“这就是我的信念、我的情感”④。宣称拥有传统悠久的王位继承权、表示拥护教皇权势、恳求教皇给予支持,这些是该信函的内容,换言之波旁家族希望披着天主保佑的神圣外衣,在法国重建波旁王朝。
另有三封书信内容大致相同。1866年12月12日,亨利对教皇写道:“很久以来,我未曾亲身为您效力,因为我担心自己将给您增添麻烦。”只需“教皇发出召唤,我将十分荣幸地飞奔到您的脚下,以便提供服务,保护心爱的与尊敬的教皇”。1870年初,教皇国面临被意大利王国全部并入的危险,亨利于3月15日致函庇护九世:“此时,敌人加倍使用暴力进攻教会,我对您表明自己的忠诚。”4月18日,亨利在淡灰色的信纸上再次袒露忠诚于教皇的胸怀。1871年恰逢庇护九世当选与在位25周年之际,亨利于6月2日专函致贺:“十分荣幸地向教皇陛下表示我的庆贺、我的祝愿与我的忠诚”,“企望看到善良战胜邪恶、信仰战胜不信宗教、权利战胜革命。”⑤
“权利战胜革命”,这是亨利的关键词句,即应由他代表波旁王朝派,在教皇的扶持下,重登法国的王位。此处“邪恶”应是对于刚刚发生的巴黎公社的攻击,而“善良”则意味着资本的政治。1866年以前亨利的政治积极性并不突出,1870年前后他的言行明显增加,他曾赞许与奥尔良王朝派的“融合”。他与庇护九世的信函虽然不多,但是重夺统治权力的野心昭然若揭。
从1830年被推翻至1883年亨利死去与男嗣断绝,波旁家族曾经坚持政治活动,目的在于重新掌权。他们为此采取各种手段,其中争取教皇的支持尤为重要。波旁家族的行为显然不符合时代的特性,不能回答法兰西近代社会的基本要求,淘汰这个王族是历史的必然。
奥尔良家族的政治愿望
奥尔良家族由于1830年7月革命而在法国掌权,这个“七月王朝”经历了许多困难。1832年春,霍乱流行,仅在巴黎大约16000人因此瘟疫而死亡,首相C.Perier也未幸免于难。同年6至7月,共和派在巴黎造反。1831年和1834年,里昂丝织工举行起义。19世纪40年代,流血冲突基本消失,社会矛盾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宴会运动”吸引了许多社会人士,反映出人们相同的、近似的甚至相反的愿望。从总体上看来,“宴会运动”是对于君主立宪制的挑战,是向路易—菲利普发出的决斗信号。
对于重大危机的临近,存在着认清与否、估计何时爆发,以及采取哪些应急措施的问题。1847年,国王路易—菲利普表面镇静,直至年底他还在唱着高调。12月27日,路易—菲利普发表御前演说:“在受到敌对的或缺少理性的激情所造成的风潮当中,一种信念鼓舞着我与支持着我。这就是在立宪君主制之内,在国家各大权力合作之内,我们有着若干办法,能够克服一切障碍和满足我们亲爱祖国的一切物质需求。”⑥这位君主只强调“物质需求”,否认国家在政治上的要求。
实际上,在上述冠冕堂皇的御前演说之前10个月,路易—菲利普私下向教皇表示心中的不安。1847年2月23日,这位法国国王致函庇护九世。“十分尊敬的教皇:教皇陛下始终给我以信任,我深深地感到了巨大的支持。为了完成上天赋予我的伟大使命,我必须得到这种支持……任何人无法怀疑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协作。”⑦需要支持,这就是认识到已经身陷困境。在那个时代,御前演说时坚持大唱高调几乎成了法国君主的习惯行为,但这也正是使人们通过反方向思考,能够意会到局势的困难程度的一个窗口。
对于局势另有一类认识,拉马丁、托克维尔、巴尔扎克等人曾经发表明智的预言。早在1843年,诗人拉马丁警告人们:“我们法兰西,5年之后将发生革命,我对此坚信不疑。”⑧身为议员的托克维尔于1848年1月29日在议会讲台上指出:“我深信无疑,我们睡在一座火山之上。”“你们没有感到欧洲大地又在颤动吗?你们没有感到天空中又刮起了革命风暴吗?”⑨作家巴尔扎克曾前往乌克兰探望情人韩斯卡,于1848年2月15日返回巴黎,当天他在给韩斯卡的信中写道:“今天我在巴黎,我们如同坐在火山上一般。”⑩七月王朝的统治者或许不曾听到,或许听而不信上述尖锐透彻的言辞。拉马丁提前5年的估计真是令人佩服,二月革命终于来临,这位诗人成了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掌舵者,而法国国王只有亡命异邦……
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利普宣布退位。由于长子费迪南—菲利普于1842年死于车祸,他将王位让给长孙巴黎伯爵(1838-1894年,名为路易—菲利普—阿尔贝)。3月2日,路易—菲利普自叹“如同查理十世那样!”也逃到了英国,他于1850年8月26日在那里去世。那时,巴黎伯爵年仅12岁,他的叔叔即国王的次子路易·奥尔良(1814-1896年,内穆尔公爵)代表全家恳求庇护九世的支持。9月4日,路易·奥尔良致函庇护九世:“教皇陛下,我现在告知您,我们沉痛地失去了国王(路易—菲利普),他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热爱的父亲。您对于我们一家,尤其对于我父亲历来十分关怀,这使我相信在此悲痛时刻,教皇陛下将分担我母亲以及全家的痛苦。”庇护九世于23日复函,表示对于法王去世的高度同情(11)。
奥尔良家族虽然渴望重登宝座,但是实际上它日益离开国家的权力中心,它与波旁家族的互相争斗也加大了这个距离。随后的数十年之内,我们在梵蒂冈秘密档案中,仅见到两封与奥尔良家族相关的信函。
1871年12月9日,路易·奥尔良在信中“希望教皇陛下同意”他的女儿马加丽特公主与瓦迪斯瓦夫·查尔托雷斯基(Ladislas Czartoryski)亲王的婚姻。12月11日,该亲王另有专函请求教皇批准他的婚姻,并说明这是“遵循波兰自古以来的习俗”(12)。当时,奥尔良家族或多或少地与教廷保持着联系。
奥尔良家族的“王位继承人”巴黎伯爵曾主动争取与波旁家族的“王位继承人”尚博尔伯爵“融合”,以便联合起来在法国恢复君主制度。1873年10月,这种和解的尝试主要由于波旁家族的顽固态度而失败(13)。
上述数封秘密信函以简洁的文字表明:在漫长的岁月里,奥尔良家族的成员们曾努力争取罗马教廷的支持。他们渴望完成“上天赋予的使命”,即在法国维持或重建本家族的王朝、代表金融资本的王朝。
奥尔良家族曾经取代波旁家族,一度与时俱进地领导国家,但是它的若干错误政策束缚了自己的脚步。有待迅速展开的工业革命、关于共和与民主的社会要求都召唤着新的政治力量去掌握国家航船之舵。
波拿巴家族的政治原则
拿破仑一世垮台后,波拿巴家族的成员们得到了数任教皇的关照,庇护七世、利奥十二世、庇护八世与格列高利十六世皆是如此。1859年以前,拿破仑三世与庇护九世之间较多书信往来。有关波拿巴家族的信函共20余封,包括如下内容:主动争取支持与友好祝愿;政策改变后坚持维护教皇国的最后权益。拿破仑三世从未完全停止对于教廷的帮助,他认识到为了更好地统治法国,天主教教会的支持不可缺少。由于第二帝国处于强势地位,拿破仑三世多讲自己对于教会的支持,此举必将引来教会与教徒对于自己的支持。
1848年12月20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法国总统。虽然他以3/4的选票当选,在这个大多数居民信奉天主教的国度,争取教皇的支持仍是一项紧迫的工作(14)。梵蒂冈秘密档案馆收藏的信函足以说明问题。一封不见日期的信函,从内容看来应为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总统后,即1848年末或1849年初发出。这位波拿巴写道:“由于公民的投票,我晋升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我希望向教皇陛下表达崇敬的、孩子对父亲般的忠诚。”教皇用意大利文写的回函也不曾标明日期。“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我向您表示祝贺,您由于伟大的法兰西民族的意愿而成为总统。”(15)写信双方互相表示了友好的态度。
1851年12月举行政变至1852年12月正式成立帝国,波拿巴总统在此期间积极采取措施,完成了从共和向帝制的转变。1852年2月6日,他致函庇护九世:“我作为基督徒与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所承担的义务,在于关注法国教会的需求和它的光辉形象。这个义务使我恳求教皇陛下弥补教会近年来所遭受的各种损失。”“在共和国的范围内,我相信,教徒们的利益是我目前唯一的利益。”“对于我领导的共和国表示信赖的信徒们的利益是我唯一的利益。”在原则表态之后,他提出一个具体要求。“我希望,枢机主教的职位将由波尔多的大主教(原无姓名)来承担。我也希望,这个职位……可由图尔的大主教莫尔洛(Morlot)承担。他们的功劳同样值得奖赏,他们的德行感化着基督徒大众。”“我请求教皇陛下能够愉快地任命有关大主教为枢机主教,并为他披上神圣的红袍。”(16)法国总统允诺保护教会与教徒的利益,又企图促使教皇任命法国的大主教为枢机主教,进一步保证法国的利益,首先是保证波拿巴王朝的利益。
拿破仑三世与庇护九世的通信和当时的政治局势密切相连。1867年4至10月,拉达齐(Rattazzi)出任意大利王国的首相,他曾“没收修会的财产”,“削减主教的薪水”,“听任加里波蒂去准备攻打罗马”……(17)正当危机日趋严重之际,拿破仑三世采取强硬态度,维护教皇与教会的基本权益。他于6月18日去函告知庇护九世:“我的职责在于为天主教谋求福利,并使道德的与仁慈的伟大原则获得发展”。10月末,法国远征军到达罗马。11月3日,法军在罗马以北的门塔纳打败加里波蒂的志愿军,从而给了教皇国以巨大的支持。1868年2月6日,拿破仑三世的另一封信也说明他保卫教皇领地的决心。“我荣幸地向教皇陛下重申,将不遗余力地保护教皇的领地”(18)。
1870年9月4日,法兰西第二帝国垮台。9月20日,意大利王国的军队进入罗马,教皇领地并入意大利王国,教皇丧失世俗权力。1871年1月26日,罗马重新成为意大利的首都(19)。在此欧洲局势与君王权势发生剧变之后,同年6月19日,拿破仑三世以潦草的笔迹给庇护九世写信:“值此教皇陛下任职(25)周年纪念日,表示我的忠诚与我的祝贺。然而,我使用上述词语时,曾经犹疑不决。”(20)在这一封信里,下台君主与战败皇帝的忧伤心态暴露无余。
拿破仑三世于1873年1月9日去世。梵蒂冈保存着他的最后信函之一,此信未写日期,应为1872年12月末所写。“皇后与我一同对教皇陛下表达十分诚挚的祝愿。请为她与我祷告。”(21)
上述所引书信主要是争取支持和友好祝愿的内容,但是不应贬低这些文献的价值。法兰西是一个欧洲大国,罗马教廷拥有数亿的信徒,其中包括法国的绝大多数居民。这两种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的领导人之间的联系、沟通乃至互相依靠和利用,本身就是欧洲社会的存在与活动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
我们还应看到第二帝国的有关政策发生变化时,法国与教皇国的关系同样显示出历史的价值。1849-1859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与第二帝国政府实行保护罗马教廷的政策。1859年5月出征意大利时,拿破仑三世曾公开承认:“1/4世纪以前,我的哥哥为意大利的高尚事业而牺牲。当时,我的母亲将我从奥地利人的魔爪下救了出来。”“为了意大利的高尚事业”和“为意大利做些事情”,成了干涉有关事务的招牌。如此政策出于两种考虑:维护意大利的分裂将有利于法国扩大自己的影响;与教皇亲近将有助于赢得法国民众的支持。19世纪50年代末,局势发生变化,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运动迅速加强,第二帝国被迫改变政策,力求折中,即促使意大利和教皇都做出让步,以便从中取利,这种对双方施加压力的政策得到秘密档案的证明(22)。其实,早在1856年4月4日的密函中,拿破仑三世已经开始做原则性的表白:“教皇陛下,我无法使天主教徒的待遇优于其他基督徒。实际上,各大国都在要求保证基督徒的利益。”(23)
1859年局势迅速变化。1月26日,法国与撒丁王国订立秘密盟约,共同进行反对奥地利的战争。4月27日,奥军首先进攻撒丁军。5月3日,法国向奥地利宣战。6月4日发生马真达战役,法军获胜。6月24日,索尔费里诺战役,奥军又遭失败。但是,此时战局发生转折,普鲁士开始对法国施加压力,加富尔违背事先商定的协议并且急于采取行动统一国家,法国广大天主教徒担心教皇的权益可能遭到过大的损害。拿破仑三世迫于形势,立即采取对策,于7月11日和奥皇签订预备和约,11月交战诸方签订和约。撒丁王国收回了伦巴底,并在统一全国的活动中获得进展,后于1861年建立意大利王国(24)。意大利民族统一的行动势不可挡。
正是在此种形势下,1859年12月27日,拿破仑三世向庇护九世发出信函。此次“战争期间与战后,我比较关注教会的处境。在促使我突然缔结和约的一系列原因中,包括必须考虑革命所引起的忧虑”。“尽管我效忠教皇陛下,尽管我的军队驻扎在罗马,我仍然不可避免地对意大利日益发展的民族运动表示某种程度的支持。意大利民族运动由于反对奥地利的斗争而兴起。”两个月后,1860年2月28日,拿破仑三世在另一封信中说明相同的意图。他感谢庇护九世于去年12月25日的来函(档案盒内未见),并借此回函“表达思想”。“我始终认为,对于信仰天主教的人们而言,一国君主或宗教领袖之间的协调不可缺少。”“我心中一向蕴藏着两种情感,即支持意大利的独立自由与维护教皇的世俗权力。协调这两项事业的利益时,将遇到种种困难,对此我未曾心怀幻想,我仍将全力以赴,争取完成此项任务。凡在法兰西利益所容许的范围之内,我将信守上述诺言。”(25)首先是法国的利益,其次是兼顾意大利与教皇国双方的利益,拿破仑三世历来如此。
经过战争与缔结和约以及秘密书信的往来,第二帝国对于意大利与教皇国的政策的变化,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同时,另有一公开出版物从侧面衬托出上述政策的转折。1859年,巴黎出售一本46页的小册子,书名为《教皇与会议》。它指出“从宗教的与欧洲政治秩序的双重利益的角度看来,十分明显地需要教皇的世俗权力,但是这个权力意味着什么?……教皇如何既当教皇又当国王?”如何能将教会的首领与国家的首脑聚集于一身?该书作者强调教皇的精神力量,主张办法在于教皇的“领地不必十分广阔”,它应为“有限而够用”。“土地越小,君权越大!”(26)
迫于法国的压力,也迫于意大利民族统一的压力,教皇只得让出罗马尼、马尔克与翁布利亚等领地。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也是第二帝国支持意大利统一、逼迫教皇让步与保护教廷基本存在的新的政策的结果。秘密信函与公开书刊的互相配合,达到了有关人士所设想的效果。
从所藏的档案看来,1859年春天至1860年夏日,庇护九世对拿破仑三世政策的转变,既保持着尊严,也怀着无可奈何的态度。他在1859年3月12日用意大利文致函法国皇帝,恳求法国保护教皇国。“法兰西是慷慨的与杰出的民族,也是宗教的卓越的护卫者。”此外,教皇在1860年8月2日的一封信件里,曾笼统地向拿破仑三世表示良好的祝愿。“我一向祈告天主,求他帮助您以及皇室一家。”(27)显然,教皇及其国家离不开法国的支持。
在教皇陆续做出重要让步的情况下,法国终于不忘维护教皇国的最后“阵地”,两封并非皇帝与教皇的书信提供了具体的史料。1866年4月2日,教皇国驻法国马赛的总领事向教廷报告:法国将派舰队去保护教皇国与打击加里波蒂。“为了反对加里波蒂的侵犯,此处满怀热情而迅速地组建了一支远航舰队,它的目的在于护卫教皇国的沿海地区。它的组建不曾遇到多少困难。未见特殊的武器,仅为从土伦港派遣若干艘已经武装好的舰船。”(28)1866年12月,法军撤出教皇国。1867年10月加里波蒂攻打教皇国,11月匆忙赶来支援的法国远征军在门塔纳打败加里波蒂的志愿军(29)。直至拿破仑三世垮台以后,1870年9月20日,教皇领地才并入意大利王国,教皇丧失世俗的政治权力。
法国方面的另一封信件也证明第二帝国曾给予教皇国以支持。1968年6月3日,巴黎—里昂—地中海铁路开发公司的经理致函教皇国有关人士:“多年以来,对于教廷在瑞士为教皇国军队所征募的士兵的运送,本公司已经实行减价……今后,该项有利措施仍将继续实行。”(30)对于教皇国有关事务的优待,显然不会白费心机,至少如此安排能够博取教皇国与法国天主教徒们的好感。
此外,梵蒂冈秘密档案馆内还收藏着拿破仑三世之子即皇太子欧仁—路易致教皇的若干信函,时间为1868年4月至1873年12月31日。这些信件的主要内容在于请求教皇为他们祝福,以及向庇护九世祝贺新年与祝愿身体健康。无疑,这位落泊的皇太子不无重返法兰西、登上君主宝座的幻想。
主动求援、全力支持、逼迫让步与保存最后的利益,这就是数十年间波拿巴家族以及第二帝国对于教皇及其国家的政策。路易—波拿巴作为总统、皇帝与流亡君主所书写的秘密信件,直率地说明或隐约地表示出同一个意思:一切为着法国的利益,更确切地讲是为了波拿巴王族对法兰西实行统治的利益。就此而言,波拿巴家族与波旁家族和奥尔良家族处于相同政治权力的盘算之中。
波拿巴家族曾经以强权治乱世,第二帝国时期完成了工业革命,但是经济上的进步不能掩盖政治上的落后,多次改革仍然无法保证法兰西社会的顺利发展,毕竟帝制是一种应该抛弃的政治形式。不符合时代前进要求者,迟早将退入历史的深处。
保持手中的统治权或夺回已经失去的统治权,这是法国王族之间的生死搏斗,它曾经不同程度地左右法国近代的社会生活。君主制(王国或帝国)也是人类历史的重要一页,它作为一种政治活动方式,曾促进国家的统一,加强地区的交流……它也暴露了丑恶的一面,如争夺继承权力,互相残杀,镇压反抗……19世纪的欧洲,君主机制还有着巨大的力量,况且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反对君主制与身为共和派,即可能遭到逮捕、囚禁甚至人头落地。法国的历史、欧洲的历史,离开了君主制便无法解释。直至当代,君主制的影响不曾完全消亡。例如,法国的波拿巴家族及其支持者还在进行文化等活动。又如,1993年10月16日,路易十六之妻玛丽—安托瓦内特断头的忌日,巴黎的协和广场上曾有2000人的纪念活动,其中包括17岁的青年,一年长者竟然称她为“伟大的人物”。
君主权力的得失、王族统治的生命力、政治机制的存亡,并非凭借主观意愿,而是取决于时代的条件、社会的要求。马基雅维里早已指出:“我认为,一位君主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会得心应手;同样地,如果他的行径与时代不协调,他就会不顺利。”(31)任何在法兰西执掌或企图重获国家统治权力的家族和个人,必须面对社会的要求,必须适当地回答这些要求。一个王族保持或重获统治权力、一个家族内部统治权力的继承或转移,都是测量该王族是否有能力与时代一同向前进的一种重要的尺度。近代法国王族的隐匿言行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它们各自追求的政治目标。
注释:
①档案盒内的有关标题多为Corispondenza,而不是现代意大利语中惯用的corrispondenza。笔者借此机会感谢已故好友Eluggero Pii教授,笔者翻译意大利文的档案时,他曾给予真诚的帮助。
②庇护九世为意大利人,原姓Mastai-Ferreti,生于1792年,1846-1878年任教皇。
③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419、424页。布罗伊:《奥尔良主义》(Gabriel de Broglie,L'orléanisme.La ressource libérale de la France),巴黎1981年版,第323-327页。
④《梵蒂冈秘密档案》(Archivio Segreto Vaticano.Correspondenza epistorale di S.S.Pio Ⅸ con sovrani et particolari.Ⅱ.Francia),第165页。
⑤《梵蒂冈秘密档案》,第236-237、263、264-265、276页。
⑥缪拉:《第二共和国》(Inès Murat,La Ⅱe République),巴黎1987年版,第71页。
⑦《梵蒂冈秘密档案》,第51-53页。
⑧德雷菲斯:《法国基督教民主史》(Francois-Georges Dreyfus,Histoire de la démocratie chrétienne en France),巴黎1988年版,第44页。
⑨托克维尔:《回忆录》(Alexis de Tocqueville,Oeuvres complètes.t.12.Souvenirs),巴黎1984年版,第37-39页。
⑩缪拉:《第二共和国》,第76页。
(11)《梵蒂冈秘密档案》,第47-48、49-50页。
(12)《梵蒂冈秘密档案》,第300-301、302-303页。Ladislas的父亲是Adam。1831年波兰宣布脱离沙俄而独立,阿达姆曾任民族政府的主席,失败后流亡法国。
(13)布罗伊:《奥尔良主义》(Gabriel de Broglie,L'Orléanisme.La ressource libérale de la France),巴黎1981年版,第317-327页。
(14)吉拉尔:《第二共和国》(Louis Girard,La Ⅱe République),巴黎1968年版,第171页。
(15)《梵蒂冈秘密档案》,第23-26页。
(16)《梵蒂冈秘密档案》,第72页。
(17)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21-522页。
(18)《梵蒂冈秘密档案》,第242-243页。
(19)19世纪50-60年代,一些意大利人对教皇的权势加以谴责,如“买一根绳子……用来吊死教皇”。马志尼:《论人的责任》,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页。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16-517页。
(20)《梵蒂冈秘密档案》,第286-287页。
(21)《梵蒂冈秘密档案》,第373-374页。
(22)塞甘:《伟大的路易—拿破仑》(Philippe Seguin,Louis Napoléon le Grand),巴黎1990年版,第249-253页。当塞特:《从12月2日至9月4日》(Adrien Dansette,Du 2 decémbre au 4 septembre),巴黎1972年版,第173页。
(23)《梵蒂冈秘密档案》,第98-99页。
(24)郭华榕:《法兰西第二帝国史》,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237-240页。
(25)《梵蒂冈秘密档案》,第153-155、179-182页。
(26)1859年2月英国出面调停,3月俄国建议召开国际会议解决意大利问题。《教皇与会议》(Le Pape et le congrès),巴黎1859年版,第9-11页。1994年笔者在佛罗伦萨寻找此书时,承蒙意大利著名教授Salvo Mastellone先生赠送此书。笔者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27)《梵蒂冈秘密档案》,第131-132、171-172页。
(28)《梵蒂冈秘密档案》,第63页。
(29)这支远征军是法国当时“纪律、装备与指挥都比较优秀的部队”,它轻易地打败了敌人。卢:《拿破仑三世》(Georges Roux,Napoléon Ⅲ),巴黎1969年版,第329页。
(30)《梵蒂冈秘密档案》,第111-112页。
(31)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8页。
标签:拿破仑三世论文; 法兰西论文; 法兰西第二帝国论文; 路易十八论文; 意大利战争论文; 亨利七世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政治论文; 奥尔良公爵论文; 教皇论文; 拿破仑·波拿巴论文; 亨利八世论文; 天主教论文; 亨利一世论文; 君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