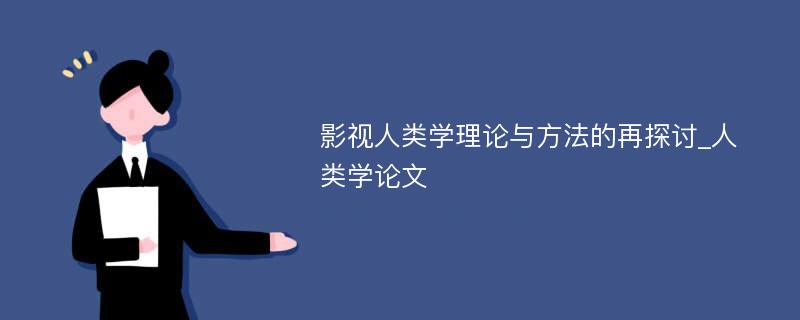
“影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理论论文,方法论文,影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利用电影摄影机和录像设备来形象地纪录和保存人类学的田野资料,大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只靠口头和笔头搜集记录田野资料的传统做法,为田野作业开辟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研究天地。但作为一门边缘性学科的影视人类学,迄今还没有公认的定义和研究方法。据一些影视人类学者的见解,认为人类学电影是“电影语言和科学的严肃结合”(J ·尧奇Rouch)。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有其自身特点的表达方式, 主要是运用具体的镜头画面的有机组接,以表现视觉形象内容的一种艺术方式;作为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的人类学、民族学或社会学,也有其学科所确定的特点。人类学和电影相结合,就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这种结合当然要体现出二者自身的特点和优长,才能相得益彰,如果只强调突出某一方的内涵而不顾及甚至损伤了另一方的特点,则这种结合至少是不成功的。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学电影就是用影视手段来表现民族学原理的影视片”,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K·G·海德Heider)。关于影视人类学的定义,有过许多争论,目前影视人类学比较倾向于不要急于下定义,主张“其边缘性的状况能够持续相当一段时期,使得这一年轻的学科不至于落入固定僵化的学科规范之中,或者不至于发展成枯燥的官僚主义学科。”(注:Rouch,Jean:"The Camera and Man", See pautHockings Editor:"Principles of risaul Anthropology", Secongedition Mouton de Gruyter 1955.P.97:P.16。)
一
一个多世纪来,人类学领域里虽然先后出现了许多学派或流派,充斥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和争论,但是,对于影视人类学来说,我们必须知晓和掌握的是当代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关于文化的基本观点。
本世纪60年代以来,当代人类学出现以文化的观点来观察研究人类行为的理论。人类的行为虽然以生物性为基础,有着许多作为人的共同的属性,但是也存在着大量的因为社会的、文化的或环境之不同而形成的相异性,这些都是属于观察研究的范围。文化人类学表明,不同的文化对于行为和性格的塑造差异很大。当代人类学家在这些异同中探求文化的模式、变迁的规律,给予科学的解释,是研究的主要层面。当代人类学对于文化的参与观察研究具有“全貌性”(holistic)、“透视性”(perspective)和“解释性”(explanatory)的特点。因为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犹如一个历经了漫长岁月的复杂机体,其中各个部分是环环相扣接的,欲了解某一社会或文化,就必须从它的各个方面进行观察研究,以取得一个较为整体性的认识。在这个认识的过程中,要求观察者跳出自身的“母体文化”的囿范,用客观求实和平等的态度看待其他的文化和民族,不管是何民族或种族,也不管他们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状况与程度,都不带任何偏见地平等对待,找寻其中的异同以及文化的通则(nomothetic ),
这种称做“跨文化比较方法”(cross —cultural comparison method)是当代人类学文化观的一大特点。这种文化观和研究方法主要是体质人类学家们通过人类进化的大量研究所提供的理论依据,即基于世界各种族、各民族在体质、智力和创造性等方面,具有人的本质上的一致,没有优劣之分。因此,我们的任何观察研究,必须毫不犹豫地全面彻底地清除一切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
文化人类学家倾向于认为,人类的行为模式是由许多风俗习惯形成的,而社会人类学家则倾向于由众多的人际关系所组成。文化人类学比较注意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如何形成又如何传递给下一代;不同的民族或群体如何进行不同人群关系的整合;人们是如何产生众多的超自然的观念和信仰来希求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从这些不同民族行为模式的比较研究当中,我们发现,每一个文化环境和社会历史背景不同的民族,早就各自形成了一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每个民族都有价值选择的方向,即“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 作为各自行为取舍之标准。因为标准不同,行为才各异。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几乎都是一个自成系统的文化整合的丛体,而每个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多是非常看重的,也是属于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当中最为重要的东西,所以欲了解和说明一个民族的文化和行为,只有用该民族自身的观点和价值取向去观察了解才有意义,如果轻易采用别人的或其他民族的观点和标准去观察了解,就不可避免地经常会产生许多的偏见或误解,这就是文化人类学家说的“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的观点。
当代人类学家已认识到,每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完整系统,在我们自己的文化系统之外,世界上还存在着众多的文化系统。我们可以讲习惯于哪一种文化不习惯于哪一种文化,但不可以说我们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他人的文化是最不好的。我们不应该根据自己文化的好坏标准来评判他人的文化。文化都是从各自的环境、传统和深厚的生活土壤里世代生长出来的,它们适用于本民族的生活。因此,在不了解他人文化发生的背景条件及其文化本质的情况下,硬要把自己文化的一套东西作为“先进的”、“优秀的”强加在他人的文化之上,这是相当危险的,值得深思。对于各民族文化采取科学的客观的平等态度,这是当代人类学提供的和异族异文化相处之道的基本观点,被视为是对于文化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文化的差异古来有之,是客观的存在。当代人类学提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不断增进对于全人类文化和行为的异同的了解过程中,既要了解他人的文化也要了解自己的文化,通过知己知彼的比较方法,懂得了别人的和自己的文化,才具备对异民族异文化进行阐释的资格。此点对于影视人类学的理论建设尤为重要。
当代人类学正处在一个充满了文化撞击和文化震荡与变迁的世界性潮流之中,文化上的共同性在逐渐增多和加强。这一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已愈加地明显。二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断分化又不断重新组合的世界,原始社会的遗存几乎荡然殆尽;西方的殖民地正在全面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先后出现了一系列新独立的国家和民族;前资本主义的民族与社会纷纷进入发展中的阶段,皆以不同的方式从传统型社会朝现代化的目标前进,往日传统社会的关系正被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关系所取代;民族意识的成长,不断出现为自身的权益而采取激烈的独立化运动,备受歧视的种族、民族、阶层和妇女,成为这类独立平等运动中的一部分。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处在重新调整当中。面对着如此剧烈变动的时代,人类学的传统理论已经愈加显得不能适应了。人类学究竟应该怎样地去观察、描述和分析日益混杂不清的文化?怎样对待那些业已散碎变异了的理论呢?一些学者们提出,需要立足于当代和未来,创立新的观念模式,重新认识和估计现今变化着的世界,人类学的研究需要有一个全新的见解,呼唤一种新型的能够反映当前不断变化着的世界的民族志的描述,这就产生了一种构建当前人类学的尝试,这个问题至少在本世纪70年代就被提出来了。我们认为,跨世纪的人类学既需要发展,也需要继承。影视人类学的建设与发展和人类学的趋势汲汲相关。我们需要关注当代人类学的各种探讨及其发展动向,并且通过影视人类学的实践从一个方面来帮助推动当代人类学的前进。
二
本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影视人类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人类学影视片摄制的理论、方法和技巧;影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人类学影视资料的价值和文化保存、再现及传播;影视人类学和公众生活及教育;影视人类学向“分享人类学”(shared anthropology)迈进等。 在摄制的理论与实践方向,以科学性和艺术性的争论最为突出,反映了当代人类学的科学性和影视学的艺术性之间的矛盾或冲突。
迄今人类学影视片的摄制大大超过了其理论研究,致使人们怀疑影视人类学是否称得上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少学者认为,人类学影视片仅是一个内容独特的片种,或是包含有大量的人类学、民族学信息的影视片。他们历来只习惯于用文学符号来建立学科,表现其研究的成果,对于电影摄影机、声像同步的摄像机等新科技产品的使用,多不精通,对此往往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
对于影视专业人员,通常皆强调运用视觉艺术的特点,通过“影视形象”和“影视语言”说话,认为影视片必须有个人的艺术风格,他们特别注重于艺术上的构思和表现手法。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和影视工作者这两种不同职业或专业的人一起合作,多以各自所熟悉和习惯了的思维方式来对待处理人类学影视片的摄制,在科学性与艺术性的问题上,常会发生明显的矛盾。从事于科学研究的人,总是通过具体的事象进行综合、归纳、概括,偏重于逻辑思维或推理,习惯于运用抽象的概念、术语及文字符号来严密地表述事物的逻辑过程。而从事于影视艺术创作的人,常是受到具体形象与情绪的感染和激发,注重于形象的艺术塑造和情感的抒发,侧重于运用形象来思维。这是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和矛盾。
在影视人类学当中,强调科学性是主导。艺术为科学服务的意见认为,影视人类学存在着观察和理解事物的两种不同方式,这就是科学研究与审美意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影视民族学中,影片只是工具,民族学研究才是目的。”“必须首先并且要不断地强调民族学性一定要优先于电影摄影的艺术性,当民族学的要求与电影摄影的要求发生冲突时,必须以民族学的要求为主。”指出:“影视民族学最重要的属性在于影片具有民族学活力”。(注:海德,K·G·著 田广等译:《影视民族学》,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5页。) 持此看法的美国影视人类学家K·G ·海德(Heider)还认为, 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矛盾是人类因素造成的,主张“影视工作者要从民族学角度,即从科学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民族学工作者则必须从影视的角度,即形象的角度考虑问题。”(注:Rouch,Jean:"The Camera and Man",See pautHockings Editor:"Principles of risaul Anthropology",Secongedition Mouton de Gruyter 1955.P.97:P.16。)双方互相渗透、互为对方增添光彩。持类似观点的J·茹比(Ruby)(注:Ruby,Jay:《 ls an Ethnographic Film a Filmic Ethnography?》 See:《Studie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Visaul Communication》2(2):P104~111。)也主张民族学影片要尽量符合科学的民族学标准, 认为,无论在方法上及资料的搜集分析上,都要具备科学的逻辑和理论的涵意。影片作为沟通的媒介与技术,必须将科学的论述传达出来。他觉得大多数民族学电影均未能达到这种标准和效果,虽然这类影片都可供人类学研究分析,但不应随意地为它们冠上“民族学电影”之名。
持相反观点者首先对于“科学性”提出了质疑。本世纪80年代西方人类学界掀起了对书写民族志的文学性风格的推崇的浪潮,认为民族志是一种作品,首先值得提倡的应是它的文学性或美学的价值,而不是所谓的科学性。这一思潮认为,人类学作品应该以文学作品的美学情趣或审美标准来要求,不应该以是否合乎科学标准来评价,因为所谓科学性标准在他们看来往往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指出科学所要求的客观,总是尽可能压制作者和研究者的情感流露,使这种个人的情感不得不深藏起来,而人类学家于田野作业中所产生的丰富而生动的经历、经验,多半只能写进不一定就能公开发表的他们的调查日志当中,绝对不能写入民族志里面。C·格尔茨(Geertz )曾检视了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诸如B·马林诺斯基、埃文斯—普里特查、R·本尼迪格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民族志后认为,这些著作中的理论力量如今已经消失,但人们依然乐于阅读它们,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学风格,令人难以忘怀。因此,他认为民族志的文学性格和人类学家的作家角色是不容忽视的。(注:Geertz,clifford:《Works and Lives:the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California:Stanfofrd universityPress.)我们认为, 民族志当中确乎存在着文学性和美学的因素, 这些因素原本寓于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之中,产生于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这是事实,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对此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深刻感受和激扬的情绪。问题在于民族志究竟是以科学的描述为主抑或是以文学的描写为主?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是以科学家的角色出现抑或是以文学家的角色出现?如果二者兼得,当然极佳;如果只是强调应以后者为主,那么,人类学、民族学和文学及其二者的作品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上述思潮还涉及到民族志的写作究竟是给谁看的问题。在殖民主义时代,人类学家以西方学术界所关心的理论问题带到殖民地的田野去印证,出版的民族志主要限于学术界阅读和讨论。C·格尔茨认为, 现今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民族志的研究者、被研究者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应有所改变,被研究者不只是被描述的对象,读者也不只是被动地被告知,今天的民族志应该使得三者之间能够有所对话和交流。形成于殖民主义时代的人类学理论在后殖民地时代已经不再适合了,民族志的写作要注重风格和美学,把一个群体的意识切适地传给其他人群。(注:Geertz.Clifford:《Works and Lives:the Anthropologistas Author》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see.) 在民族志写作的革命浪潮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写法, 尝试用更自由、更合乎人性和更具艺术的审美价值和风格情趣的书写方式来著述出版新的民族志,以摆脱所谓的“科学”紧箍咒的束缚。
书写民族志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对于影视人类学不无直接的影响。本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出现了反对人类影视片以科学为优先考虑的主张,要求摆脱科学性对民族志的桎梏,从以往的科学性的规格中解放出来,使人类学影视片成为一种“分享的人类学”、“人性的人类学”的理论。(注:胡台丽:《民族志电影之投影——兼述台湾人类学影像实验》,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71期,1991年。)
这方面有一定代表性意见的如I·C·贾维(Jarvie),他说:“我对于以电影作为科学性人类学传达工具之价值甚表怀疑。”他明确地反对把电影作为表现某种理论的需要的工具来看待,认为人类学的知识如果是为了顺应某种理论的需要而展现真实(reality)的话,那么, 影片的表现势必要受制于理论与思想观念的束缚,在这种条件下的表现是难以获得长足进展的。他指出,人类学影视片的摄制者与人类学家的目标可能不同,前者主要是处理具有想象力的视象,后者则以审慎和精确科学态度从事,二者如果勉强凑合在一起,双方都不会满意,这在实际上对于民族志没有什么贡献。(注:Jarvie,I·C·:《The Problemof the Ethnographic Read》See:《Current Anthropology》24(3):313~325,1983。)
人类学影视史显示,同人类学电影一起成长的纪录影片,7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大大超过人类学电影。本世纪50年代以后,一些人类学电影有意识地将纪录片的美学原则和文学观念吸收到自己的影片中,出现了新的风格和创新,促进了人类学电影的发展,其中以法国民族志电影摄制者J·尧奇(Rouch)的影片为代表。他采用不同的标准和方式来处理或表现书写民族志和民族志电影。对于书写民族志,他采取了严谨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而对于民族志电影,则采用大胆的文学性的个人情感的抒发。显然,这种分别对待的做法,并没有真正解决人类学影视片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互相协调的问题,因此,有关二者的关系和标准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三
有关人类学影视片的摄制标准,可能至少存在着三种,主要取决于它们的用途和观众。一是用于学术研究和教学,其科学性占首位,多数是非商业性质的人类学和民族志影视片;二是供大众观赏娱乐,其艺术性占首位,多数是商业性质的风情旅游影视片;三是用于社会文化教育或政令宣传,以规范人们的行为。我们认为,对于第一种标准的影视片,即所谓正统的人类学、民族学影视片,应注意改进那种一味地强调科学性或学术性而忽视影视艺术特点的偏向,克服那种单调乏味地平铺直叙、降低可视性程度,或者生硬刻板地搬弄、印证某种理论观点,甚至不惜削足适履地框套于无所关联的现实生活;对于第二种标准的影视片,不宜以过分地强调艺术风格和个人情怀的主观抒发而不顾及基本事实,造成对现实的歪曲或损伤,因为艺术上的过于渲染,经常会偏离了事物的原貌或属性,造成误导或变质;对于第三种标准的影视片,也需要考虑到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方法,恰当地予以应用。不管是哪一种摄制标准或方法,纪实性和求实风格应是人类学影视片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现今的世界与社会确有许多从未有过的现象和课题正等待着我们去观察纪录和深入研究,影视人类学和当代人类学一样任重而道远。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人类学、民族学学者来说,能够具备既精通本学科原理又谙练影视技术修养的人是不多的,而影视片摄制者又多是只熟知影视艺术和拍摄技巧,却缺乏人类学、民族学的知识,所以双方的经常合作势在必行。
影视人类学和人类学影视片对于多数人还是个比较陌生的学科和片种。人类学影视片除了纪录保存民族的传统生活样式及文化知识用于教学与研究之外,应该尽可能地深入生活、发掘题材,选择和运用各类素材与拍摄方法来不断拓展它的生命的活力,让社会上更多的观众参与进来,关注人类的行为和文化的命运。人类学影视片综合和积累了人类传统的知识与感情,我们需要把这种知识和感情融为一体,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开去,努力做到雅俗共赏,让不同的观众能够通过这类影视片找到各自关心的东西,包括已经失去了的和能予寄托的,用以启发今后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