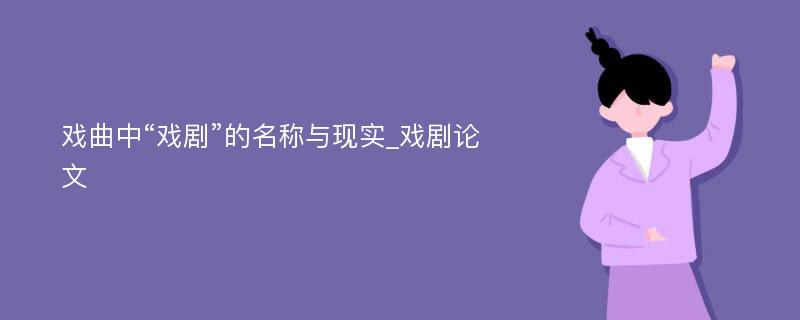
戏曲“剧种”的名与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种论文,戏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2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549(2015)04-0059-12 一、问题的缘起 中国戏剧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还有多元的形态。“剧种”是当下人们用以区分戏曲内部形态差异的主要范畴,按“剧种”的区分,通常认为戏曲可以区分为300多个剧种。戏曲之所以被区分为如此之多的“剧种”,实由于“剧种”这个20世纪才出现的戏曲分类学术语被普遍运用,而“剧种”这一称谓是何时出现以及如何出现的,迄今我们还不能从任何研究文献中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刘文峰先生在《关于认定剧种标准的意见和建议》中认为,“剧种”这种称谓被普遍运用,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在戏班登记时,登记表中设了‘剧种’这样一个栏目,于是各地戏班给自己演唱的戏曲起名为‘某某剧’”,[1]这一观点应该援引自我在戏曲档案中发现当年的“剧团登记表”时所产生的误解。[2]我提出这一看法时,主旨是为了追溯“剧种”一词的出现与剧团国家化的关系,因而对“剧种”的称谓来源未做细致考察。实际上用“剧种”作为各地流行的地方戏的称谓,要远远早于剧团登记。举例来说,1950年初创办的《新戏曲》杂志,从一开始就是用剧种来称呼地方戏的,这一点已经和今天没有任何区别;而上海市举办的戏曲改进运动春节演唱竞赛的获奖名单上,也明确标示着京剧、越剧、绍兴大班、沪剧、江淮戏、维扬戏、甬剧、常锡戏、滑稽剧等,虽然“江淮戏”等具体名称与现行通称有异,但其中体现的剧种意识已经非常之清晰。从1950年8月开始,《新戏曲》开辟专门的栏目介绍地方戏,从10月20日出版的第三卷第五期开始,特别给这个栏目加上了“各地剧种介绍”的名称。田汉在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代表文化部作的报告《为爱国主义的人民新戏曲而奋斗》中提及各地包括“地方大戏”、“民间小戏”在内的地方戏后,明确指出,中央决定“各地戏改工作以对于各地群众影响最大的剧种为主要改革对象”。这些材料都充分说明,“剧种”这个范畴术语,1950年左右在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和文化部门正式文件里,已经被普遍使用。而大规模的剧团登记,要迟至1953年才开始。文化部在1953年1月29日发布了《文化部关于整顿和加强全国剧团工作的指示》,开始全面部署并强化全国性的剧团登记和整编,随后于5月13日颁发《文化部关于全国剧团整编工作的几项通知》,12月12日发布《文化部关于私营剧团登记和奖励工作的指示》,次年10月14日发布《文化部关于民间职业剧团的登记管理工作的指示》,1955年6月17日下发《文化部关于民间职业剧团登记工作的补充通知》。在此之前,或已有部分省份提前开展的剧团登记工作,但不会早于1950年。所以,剧团登记表上出现“剧种”这一栏目,固然对相当多地区的艺人命名自己所演唱的戏曲样式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在此之前,“剧种”一词在政府文化部门的使用已经很普遍,登记表的设计只能是其结果,而非其原因。 总之,“剧种”作为一种区分各地方戏曲的称谓方式,它的出现以及流行的过程并不单纯。我们只知道它并非戏曲诞生以来就有的词汇,如果能够对这样一个重要的用语的来源做一番考原求证的工作,或许能够深化我们对戏曲的历史与发展演进的认识。 戏曲历史悠久,分类及命名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南戏、北曲是基于所诞生区域的区分,杂剧、传奇是基于文本形态的区分,雅部、花部是基于美学取向的区分,但相对于丰富复杂的戏曲,这些区分方法终究过于笼统。而随着戏曲在各地广泛传播,音乐与方言语音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支配的关系逐渐上升,最终导致各地方戏曲在形态与性状上呈现出诸多的差异,戏曲的地方化特征才得以充分显现。正因为这些地方特征多半与地方语音的腔调相关,所以基于腔调区分和命名各地的地方戏曲,就逐渐成为新的习惯,祝允明《猥谈》和徐渭《南词叙录》等早期文献里,这种区分和命名方式就已出现。 因此,从戏曲开始呈现出地方差异的明初时期起,各地方戏曲就是主要以腔调为分类依据的,明代的“四大声腔”和清代文献中所称的高腔、梆子、乱弹等,都是在强调彼此间声腔的差异(其中“乱弹”之名,看似与声腔无关,但是它所指称的也是音乐的性状特征,且因音乐上特征明显,具有很强的可辨识性)。昆曲或曰昆腔就是最好的例子,“昆”虽然本为地名,但因为它在全国各地得到最广泛的流传,与它的原生地昆山的地方文化的归属关系早就模糊了,“昆”作为地名的意义远不如它作为声腔的意义那么重要,对“昆”的辨识,主要是对音乐性状和声韵的辨识而非其他。 在戏曲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梆子、乱弹等民间性很强的声腔广泛传播,一方面戏曲的音乐与地方的方言之腔调相表里的特征日益重要,这些俗文化范畴内的声腔,又不像昆曲那样有严格规范,所以同一声腔在不同地区难免出现其或大或小的流变。高腔、梆子和乱弹的流传区域都十分广泛,在漫长的时间内,在不同地区均逐渐出现、形成了不同的表达形式和不同的风格。同样都是高腔、梆子或乱弹,相互间的差异可以很大,因而加剧了戏曲内部构成的复杂化,并且经常出现同名异腔的现象。所以,习惯上人们也会在声腔的基础上冠以地名,用以区分各地的地方戏曲,如“梆子”有上党梆子、山陕梆子等,高腔、乱弹无不如此。至于花灯、采茶、花鼓、道情、秧歌等小戏,其音乐表达原本就相对简单,各地相类似的表演更不可能太受其内在的规定性的制约,也就更加容易产生地域性的差异。这既是地方戏出现的原因,同时也正是戏曲史上出现以地域名称为地方戏命名的缘由。当然,戏曲声腔内在关系复杂,同名异实、异名同实的现象时有发生,无论是业内还是社会各界,包括文人学者,历史上从未有人按声腔为戏曲的地方戏做过全面而精细的分类与命名,这也是事实。 总之,用声腔为地方戏曲命名的方法,其出现与流行可以远追至明初,而用地域为地方戏曲命名的方法,或者在声腔前面冠以地名的命名方法,在清代已经多有出现。这些称谓都是自然形成的,或能得到伶人和各地戏曲观众认可,但多无规范可言。所以我们看清代的文献,例如“乱弹”这样的称谓,所指称的对象之错综复杂,莫衷一是。 二、地方戏命名方式的新变化 晚清时,有关地方戏的命名出现了新的趋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京剧称谓的变化。 晚清时,京剧业内人士多自称为“皮黄”。这样的命名,是因为它在声腔上具备以西皮、二黄为主的音乐属性,这是其区别于其他地方戏的最重要特征。但是我们同时看到,“京戏”和“京剧”之名,在媒体上很早就大量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的《申报》等大众媒体上,“京剧”或“京戏”的称谓被大量地交替使用,在新兴的杂志类媒体上,这种称谓非常多见。随手摘抄几条:1904年创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的文章里大量使用“京剧”的称谓,1913年创办的《游戏杂志》,几乎每期都设有“京剧”专栏,介绍京剧的重要剧目或伶人;1906年出版的《通学报》第二期介绍社会上的冤事,称“京戏有《九件衣》一出”,1913年《滑稽杂志》第一期刊有诗丐撰写的《京戏名对》,1914年出版的《俳优杂志》第一期刊有《京戏术语》一文(不署著者),等等;清末上海剧评家郑正秋写的文章里,“京剧”一词也很常见。而使用“皮黄”者,越来越限于业内人士或所谓“行家”。 民国中期,仿照“京戏”、“京剧”的称谓方法,用地名冠以“戏”或“剧”的方式为地方戏曲命名,有逐渐普及的迹象。如“粤剧”的称谓,可查到1919年《益世杂志》上的剧本《书生忧国》,前面署有“粤剧碎锦”的题名;1922年《游戏世界》杂志上刊登过刘豁公和人合写的《粤剧杂谈》,如果我们再翻检同时代的其他报刊,不难找到很多文章使用“粤剧”这一名称。至迟到20世纪的20年代末,这个称谓在各报刊上已经非常通用。再看其他地区的地方戏曲,1929年第10期《戏剧月刊》载有署名夏晓东所著《汉剧现状》,1932年《剧学月刊》连载杨铎著的《汉剧十门脚色及各项伶工》,1935年出版的《蹦蹦戏考》的印行者署名为“评剧研究社”,1939年《十日戏剧》杂志连载邹少和著的《豫剧考略》,这些作者使用的剧种名称,都已经与今人无异。除了秦腔偶有人称之为“秦剧”,并未普及之外,“川剧”、“粤剧”等名称,都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报刊中的常用词汇,而“豫剧”、“越剧”之类名称,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也基本上已经为大众媒体所经常使用。无论是1937年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还是1944年在桂林举办的“西南剧展”,各地方戏曲的名称,都逐渐开始流行后来最多见的“地名+剧”模式的称谓。 当然,在民国中后期,虽然在地方戏曲中冠以地名的现象急剧增加,然而“地名+剧”的命名方式,仍然只是地方戏曲若干种命名方式中之一种。以广西地区清代开始流行的弹腔为例,20世纪30年代曾经有“桂戏”的称呼,欧阳予倩和田汉主办“西南剧展”并为之创作新剧目时用的是“桂剧”,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桂戏”和“桂剧”两种称呼仍然同时并存,在《戏曲报》第三卷第七期发表的方非的长篇介绍文章《关于桂戏》,题目中用的就是“桂戏”而非“桂剧”。 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地方戏曲的称谓的形成,发生了一个可以称之为从“内命名”向“外命名”转变的过程。其中关键性的变化,就是地方戏的命名原则,从其艺术属性的界定,逐渐转为与其艺术属性关系不大(至少从表面上看)的地域化的界定。地方戏的分类方法从内命名向外命名的转变的结果是,原来地方戏最核心的辨识标志是声腔之不同,此时却变为地域代之以成为其主要的辨识标志。这一变化之所以出现,之所以可以称之为从内命名向外命名的变化,还因为导致这一处于核心地位的辨识标志的替换,其动力显然源于梨园行外,它的命名主体是戏剧界之外,尤其是大众媒体,又尤其是异地的大众媒体。简单地说,命名主体从内行变成了外行,从本地人变成了外地人。正因为此,相对于地方戏的声腔音乐而言,地名显然是更容易为大众(尤其是异地的)媒体的编辑、记者和读者们认知把握,也更容易辨识的元素。面对更多元的观众,冠以地名是更容易普及的称呼,基于更大范围的传播,地名作为辨识指标的作用也更显著。因而,它放弃了对地方戏曲的形态与性状、尤其是在艺术上具有特殊意义的音乐和声腔的特点的界定,换取的是更广阔的地域的更多人、尤其是“外行”的接纳。其实从几个细节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变化与命名主体的关系。“京剧”一词首先出现在上海而不是北京,1875年后,《申报》上“京剧”和“京戏”的名称大量出现,北京的《顺天时报》和天津的《大公报》上同样有大量京剧消息,却迟迟看不到这样的称呼。民国时期,在戏剧类专业杂志上,“皮黄”这个称谓比起一般的大众媒体而言更为多见,相对于后者通常更多使用京剧、京戏(或北京改称“北平”之后更通用的“平剧”)这些词汇,当然是由于戏剧专业期刊上撰文的作者和读者中更多剧界人士,他们对声腔更为敏感,也不愿意追随大众媒体,使用虽然通俗却忽略了更重要的声腔音乐之特征的“地名+剧”这样的称谓。 尽管从晚清到民国,在各地方戏的称谓上冠以地名逐渐成为通例,但这种命名方法毕竟有无法解决的困难。问题在于地方戏曲的流播以声腔为基础,而声腔不仅仅意味着音乐旋律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文本的差异,进而意味着剧目的差异,甚至导致表演手法的差异。在戏曲发展过程中,每种声腔都形成了它自己特有的代表性剧目,形成了某些特有的表演技巧与手法,自成系统。而声腔的流传区域更不可能完全与行政区域完全重合,不同声腔流传的地区往往犬牙交错,且同一地区往往流传着不同声腔。以西南地区为例,从民国初年起,这一带流传的地方戏通称为“川剧”,但它实际包含了高腔、胡琴、弹戏、灯戏等几大声腔系统,还保留有部分昆曲剧目。虽然民初就有人仿照“五族共和”之意提倡“五腔共和”,普通民众也早就习惯于使用“川剧”或“川戏”的统称,但是具体到那些重要的保留剧目,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艺人们仍一直坚持要明确界定各自所属的声腔。对不熟悉川剧的普通观众,或者对那些不了解川剧声腔的复杂性的学者来说,川剧就是川剧,然而对川剧艺人和资深的川剧观众而言,不同的声腔具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形态,是无法满足于只使用笼统的“川剧”这一个概念描述的。 川剧遇到的麻烦还不止于此。如前所述,声腔的流布与方言区高度相关,四川和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因属于同一个方言区,所以三省都是川剧流行区域。但云南另外还有滇剧,贵州另外还有黔剧,为什么云贵地区流传的多声腔的川剧要叫“川剧”,而不是和那里的地方戏并称为“滇剧”和“黔剧”?川剧只不过是用地域命名剧种时遇上麻烦的中国无数地方戏的代表。声腔的差异与方言语音的差异相关,而行政区域的划分与方言区不可能完全一致,基于声腔命名剧种和基于行政区域命名剧种,一定会出现矛盾。这就是漠视声腔等内在的艺术特质的差异,而简单化地依赖分布区域命名地方戏曲的方法的局限。但是,在晚清民国的大众媒体推波助澜之下出现的地方戏新的命名方法逐渐普及之时,人们还意识不到这一缺失将对戏曲的发展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三、“剧种”与地方戏研究 对地方戏曲的重视与认知,必然引向对各地的戏曲之内在差异的认知。大约民国中期,学术界对戏曲的关注中心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地方戏曲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且已经开始有学者尝试着勾勒地方戏曲的全貌,而一旦这样的学术努力初露端倪,立刻就会意识到在中国的广袤地区流传的地方戏曲有多么丰富。民国年间著名的戏剧学者佟晶心可能是最早试图全面研究地方戏的学者,他在《八百年来地方剧的鸟瞰》一文中这样写道: 设如以汉口为中心,就有湖北的汉调,湖南的祁阳戏,再往南就有广东、广西的梆子。往西就有四川戏。往东南就有闽剧。往北就有河南梆子。往西北有山西、陕西和甘肃的秦腔。往东北有安徽、河北、山东的梆子,北平的皮黄。往东三省就有奉天落子。还有其他不甚显著的地方小戏……① 在戏曲和曲艺领域的学术与创作兴趣十分广泛的佟晶心,只是开启了这项研究的大门。“剧种”这一范畴出现以及民国期间的地方戏研究,与马彦祥有密切关联。他是该时期在地方戏曲研究中最突出的学者,这不是由于他1932年就在《燕京学报》发表了长篇论文《秦腔考》(类似的对秦腔这单一剧种的性状的研究,即使限于“花部”,也早有波多野乾一的《京剧二百年历史》等更重要的著作),他的贡献在于,他可能是第一个注意到地方戏曲在全国各地的分布规律以及地方戏曲不同特色之形成原因的学者,而这正是其他所有学者远远不及的学术认识。他在1943年对全国各地方戏剧的分布的全面叙述,比佟晶心的上述概括又有新的推进。马彦祥指出: 就目前所存的地方剧而言,名称之多,范围之广,殆难尽述。只用的方言不同,遂使其流行的地域各受了很大的限制,例如潮州的潮州戏,宁波的四明文戏,绍兴的越剧,因方音过于特殊,其流行区域即不出潮州宁绍一带(今泰国曼谷就盛行潮州戏,亦无非因该地华侨多系潮州籍之故);有的虽也用的方言,但其方音的特殊性较少,其流行区域便较为广大,例如四川的川剧,湖南的湘剧,湖北的楚剧,广东的粤剧,福建的闽剧,安徽的徽剧,东三省的蹦蹦戏,以至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各省的梆子等,则无异已成为某一省的戏剧。其中尤以皮黄剧(即京剧)最为普遍。② 这里所涉及的地方戏虽然还未尽其详,但已经遍及全国。马彦祥对地方戏曲的研究兴趣,还因为与焦菊隐的一场争论而被强化,焦菊隐坚持认为中国“有地方调,但是没有地方戏”③,认为各地方戏的差异仅在或主要在音乐上,而在故事、人物以及表演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异,这使得马彦祥探究各地方戏之间的差异的学术努力,有了更多的针对性;并且由此触动了全面了解与统计全国各地的戏曲究竟有多少“种类”的设想。他甚至通过报纸公开发布告示,征求各地学者和有识之士的协助,希望他们提供各地方戏曲历史与现状的信息资料,达到普查全国地方戏曲“种类”的目标。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学者希望通过详尽和客观的调查,全面掌握“剧种”的数量。 如果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在马彦祥前后,欧阳予倩、周贻白、黄芝冈、杜颖陶等学者都陆续有对地方戏的精彩研究,他们的研究,成为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会演之后,中国戏曲研究院凝聚全国各地学者对地方戏开展全面研究的极其重要的基础。而马彦祥对地方戏的研究并没有止步于此,因为要证明焦菊隐否认“地方戏”存在的观点的错误,前提是能清晰地指出各地方戏曲在性状上的质的差异。他们当年的争论无法深入,就是由于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与语境中,各地方戏曲之间所具备的共性或许与它们的个性相比更有研究的价值,所以无论是焦菊隐还是当年的马彦祥,都受制于地方戏研究十分薄弱的现实。尽管进入民国之后,戏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但多数学者的兴趣点仍然限于文学领域,甚至连古代戏曲学者所关注的音律的研究也渐成绝响,更遑论对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的全面概括、描述与研究。而没有对各地流行的地方戏曲的深入研究,当然无法把握戏曲的全貌。 因此,“剧种”命名并不只是在一幅绘制完成了的地图上,给不同区块找一个合适的称谓。这样的命名需要建立在对各地流传范围很不规则的地方戏曲的辨识基础上,而辨识就需要找到足以区分不同地方戏曲种类的依据。只有找到这样的依据,我们才有足够的理由,把上海的京剧和大连的京剧都称为“京剧”,而且不会因为其都是在武汉流传的地方戏,就把汉剧和楚剧混为一谈。这就是马彦祥和一般的大众媒体记者编辑的不同之处,他不满足于只是给某地的地方戏曲安上一个地名,他知道只有通过研究才可能厘清地方戏的“种类”,进而知道中国戏曲有多少“种”。命名是统计的前提,但是,对象性状的认识与把握则是命名的基础。 四、“戏改”与地方戏的命名 马彦祥的设想在当年没有成为现实,是因为严肃的“剧种”调查,必然要以有学术内涵的研究为基础。他可能是最早清晰地认识到这一学术路径的学者,幸运的是,他这一理想在20世纪50年代居然得以实现。 完整地统计地方戏曲的种类,首先是辨识,然后才是命名。这是马彦祥当年早就形成了的清晰认识,但很难说历史是不是真的按照他绘制的路线图运行。20世纪50年代的“戏改”运动中,各地方戏曲才第一次得到完整的统计,因此有了戏曲种类——剧种——数量最初的数据。在全国范围内的“戏改”全面展开之前,马彦祥就是作为其前奏的华北地区“戏改”的主持者,在他担任主任委员的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成立之际,《人民日报》配发的专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特别指出: 在华北解放区,据初步调查,有平剧、河北梆子、评戏、各路山西梆子、秦腔、秧歌、柳子调、老调、丝弦、高调、道情等二十余种……④ 联想到马彦祥曾经向全国各地的同道征求地方戏曲情况,尤其是前引他1943年的文章所表述的观念,这样的调查正是马彦祥早就想开展的,适逢担任“戏改”机构的领导人,使这项对地方戏曲而言极为重要的工作的推进获得了最好的机遇。1951年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著名的“五·五指示”,进一步让“剧种”这个范畴进入了戏剧主管部门的视野。文件称: 中国戏曲各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今后各地戏曲改进工作应以对当地群众影响最大的剧种为主要改革与发展对象。⑤ 几个月前,这段话曾经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回复东北人民政府戏曲改进处的函件里,当时戏曲改进局的局长是田汉,马彦祥担任副局长。其中涉及的“剧种”的概念和文件的措辞,都与马彦祥此前的研究相吻合。 而无论20世纪50年代初遍及全国的地方剧种统计与命名潮是否按马彦祥的理念而展开,我们都看到,有各地的文化部门与戏剧爱好者积极参与,加上报刊尤其是戏剧专业杂志推波助澜,地方戏出现五花八门的称谓实难以避免。《戏曲报》1950年7月刊登的一篇文章最为典型地表现出处于过渡时期的戏曲称谓的混乱,这篇题为《锡剧在无锡的活跃》的文章,署名是“常锡戏工作者”陈梅森,文中称无锡大众剧团的新剧目演出受到当地政府很高的评价,且称这“一个剧团的成功也就是我们整个常锡剧的成功”⑥;同样的对象,标题、署名与内文,原来的“常锡文戏”已经有四种称谓。而混乱还不止于此,文中提及,到1951年初,“常州和上海已经统称为‘常锡剧’,苏州叫‘苏锡文戏’,无锡叫‘无锡文戏’(现已改名‘锡剧’)。”⑦短短一篇几百字的文章,为这个剧种提供了多达6种称呼。现在我们已经很难还原“锡剧”是何时被当地文化部门接受的(至于艺人与观众是否接受,在这个过程中大约很少有人虑及),也不知道原本一直在“常锡文戏”前面的“常”字何时突然消失。无法知道是什么人定下了这个名称,尤其是定名时常州文化部门为什么没有坚持要保留一直有的“常”字,“常锡文戏”为什么要改称为“锡剧”而不是“常剧”。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过程中,除行政部门的主导外,恐怕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让“锡剧”的定名一锤定音。 假如完整全面地统计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地方戏曲的种类,确实是马彦祥的初衷,这项当年几乎完全无望实现的浩大工程,现在只需短短几年就成为了现实。戏改局一经部署,行政体系从上至下的高效率得到充分发挥,充分证明了只有公权力的实施,才是剧种调查、统计,尤其是命名最为干净利落的手段。然而统计及命名的难度,以及通过行政命令实施的剧种统计和命名可能带来的复杂影响,是当时包括马彦祥在内的戏剧主管部门没有意识到且不可能意识到的。困难并不在于许多地区的地方戏定位不清晰,或者没有合适的名称。地方戏的定位不够清晰的现象确实存在,它们原有的命名也未必准确或合适,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身居文化部戏改局负责人位置的马彦祥固然可以调动全国各地的力量,在短时期内迅速完成剧种统计,但他所能够借用的力量,只能是各地的戏改干部而不是艺人。 20世纪50年代的地方戏曲剧种的统计和与之相关的命名,主导者只能是各地政府部门。尤其因各地政府重点支持的民营公助剧团,无不是在戏改部门指导帮助下组建成立的,剧团的命名权自然就掌握在戏改部门及其干部手中,地方戏命名时“外命名”的现象比起当年媒体主导时更甚。各地戏改干部身份复杂,对戏曲的了解程度参差不齐,更致命的是他们往往有太过强烈的主体意识。从参与戏改工作时起,这个群体的多数人就不甘心于做一位被动的记录者,而更喜欢以这个行业主人的身份出现;然而相当大比例的戏改干部对戏曲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更谈不上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敬畏。这样的心态,最典型地体现在剧种的统计和与之相关的命名过程中。很多地区在为地方戏曲命名时,并不愿意简捷明了地沿用地方戏原有的、早就为艺人和观众所熟悉的名称,而喜欢按自己的意念为之重新命名;对他们而言,选择用地名作为剧种命名的工具,显然比起揭示各剧种艺术上的特质更为方便,也更契合于他们的工作性质与喜好。 从大众媒体的介入到政府戏改部门的掌控,剧种名实分离的现象越来越多见。首先,由于戏改干部归属于政府部门,且干部派驻是依行政区划安排的,按照行政区划人为地割裂地方戏的现象时有出现,尤其是那些跨行政区域流传的声腔剧种,很容易因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而被分割成不同的剧种;更粗疏的现象,是将本地流行的不同声腔的戏曲种类归为一个剧种,尽管这与“五·五指示”要求各地选择一个重点改革发展的剧种的思路相关,然而不加区别地把流传在同一地区的多种声腔划到一个剧种里,模糊了地方戏曲的内在属性,导致“剧种”这个概念越来越远离描述戏曲艺术内在差异的功能,也很难起到艺术层面的辨识作用。 江西地方戏曲“赣剧”的命名,是我们探讨剧种称谓出现时可以作为典范的极好例子,从中可以看到政府文化部门在剧种命名过程中有可能发挥怎样的特殊作用。《戏曲报》1950年刊登的一篇介绍文章,让我们很清楚地了解了“赣剧”这个新称谓的来源: 赣剧原名乐平戏,又叫饶河戏,原来是流行在赣东北旧属饶州、广信两府(今浮乐、上饶分区)的一种地方戏,由于它流传历史的悠久,戏曲内容的丰富,民间基础的深厚,加上它还是江西最古远的民间音乐——弋阳腔的保存者,所以最近江西省文联决定把它改称为“赣剧”,作为江西地方戏的代表。⑧ 这段叙述除了告诉后人“赣剧”这个称谓,是20世纪50年代江西省文联人为创造出来的以外,满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漏洞。这个“剧种”实为唱乱弹为主的饶河戏和唱高腔的乐平班按行政部门的意志两相撮合的结果。在1950年之前,所谓“赣剧”从来就不存在,更没有作为一个单一、独立的“剧种”的历史,有的只是数百个饶河戏班所承载的饶河戏的历史和硕果仅存、奄奄一息的一个乐平戏班所承载的乐平腔的历史。只因为地方文化部门希望让弋阳腔这个江西戏剧引以为自豪的声腔继续存在,并且用它作为江西的地方戏的代表并给予重视和扶持,因此就将这两种分布地域虽然接近,其声腔却毫不相干的地方戏,人为地捏合成一个“剧种”,并且用江西省的简称“赣”命名,成了江西地方戏曲的代表。 “赣剧”的出现与命名是20世纪50年代剧种命名与统计过程的缩影。同样可议的还有浙江金华地区的婺剧。金华地区虽然原有“金华戏”之称,通常只用以指称徽戏。该地区的戏班多同时表演几个声腔的剧目,如“三合班”的演出包括高腔、昆腔、乱弹剧目,“两合半”班的演出包括乱弹、徽戏和部分昆腔剧目,还有专门的乱弹班、徽班和昆班。20世纪50年代初,该地区流行的戏曲全部被笼统地归为“婺剧”,于是这个戏曲声腔十分丰富的地区,就像四川一样,只剩下了一个“多声腔剧种”⑨。 如同我们在江西和金华所看到的那样,剧种命名与政府部门戏改工作的关联过于密切,在这一领域留下许多后遗症,为完整准确地把握全国各地的地方戏流布与发展带来很多混乱。几乎同样的现象在近年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又一次露面,可见我们对当年剧种统计与命名过程中过多的行政参与的消极作用,实在缺乏理性的分析,未能吸取历史的教训。 五、剧团登记与剧种定名 现在我们要回到文章开头的讨论,客观地估计与评价“剧团登记表”在剧种定名中的作用。诚然,现在我们经常使用的各地方剧种的称谓,很大部分是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经历了一个地方戏称谓如锡剧那样十分混乱的阶段之后,“剧团登记表”或许恰好是一个契机,让各地的文化主管部门果断迅速地结束各种不同称谓并存的现象,将地方戏的名称定于一统。因此,剧团登记过程,至少在剧种称谓的固定化(这里大约也可以使用更具褒义的词汇,叫“规范化”)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地方戏曲均以“地方+剧”的方式被命名,尤其是许多民间一直流传的传统称谓,包括艺人们以声腔为基础的称谓不再被使用,关键原因还在对于命名最具决定权的,并不是熟悉地方戏的观众和以此为生的艺人。 所以,用流播区域的地名取代声腔的差异命名“剧种”的现象,从晚清到民国年间已经因大众媒体的介入而出现,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戏改”过程中,这个过程才真正完成。正因为经历这个普遍命名的过程,我们今天才有可能拥有把握和表述复杂多样的地方戏曲有效的工具。我们要用面对现实的心态,看待半个多世纪前剧种命名过程中多少有些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带来的后果,经历数十年的演变,那些当年被强行划归同一剧种的不同声腔,不是没有融合的可能;同一声腔被划分为不同的剧种后,相互之间原本可能只是很微小的差异,也有可能逐渐放大。更无奈的是,当年以行政方式划分剧种的结果,多数已经无法更改,也无须更改。但如果剧种统计有机会重来,20世纪50年代初因过于依赖行政权力而留下的那些遗憾,是否有可能得到弥补,对中国戏曲的种类的区分、归纳与描述,是否可能有更合理、更符合艺术内在规律的方法? 注释: ①佟晶心:《八百年来地方剧的鸟瞰》,《剧学月刊》,第3卷第9期,1934年。 ②马彦祥:《论地方剧——中国地方剧史之一》,《文艺先锋》第2卷第4期,1943年。 ③焦菊隐:《桂剧之整理与改进》,《建设研究》第2卷第5期,1939年出版。据马彦祥转述,焦菊隐先后还在多篇文章中强调了“中国没有地方戏”的观点,这也是他撰写长达21页的《论地方剧》的动机之一。 ④《人民日报》1948年11月13日第1版。多年来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是通过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吉林省戏剧创作评论室评论辅导部合编的《戏剧工作文献资料汇编》引用这篇文献的。受汇编者误导,认为它的发表日期是“1948年11月23日”,且都称其为《人民日报》社论,事实上它发表在13日,原报上这篇文章也没有标示“社论”,只是称“专论”。但是这大约不是汇编者的失误,我偶然发现,这篇文献发表日期的错误居然可以追溯到1951年的引用者。而真正让人感到遗憾的还不是当年引述者的错误,而是60多年来,这个错误居然没有得到纠正。 ⑤《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1951年5月5日。 ⑥《戏曲报》第2卷第10期,1950年7月22日。 ⑦倪鑫森:《关于常锡剧》,《戏曲报》第3卷第10期,1951年1月5日。 ⑧聿人:《江西的赣剧》,《戏曲报》第3卷第5期,1950年10月20日。 ⑨有关“婺剧”这个称谓的来源,一度有过不同的说法。这个称谓最初见之于正式文献,是1950年金华专署文工团演出队参加浙江省文工团调演时第一次使用的;但有当事者在数十年后指出,他们早在1949年就组织过业余性质的“婺剧社”。详细的讨论可参看拙文:《婺剧:腔调与剧种》,《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