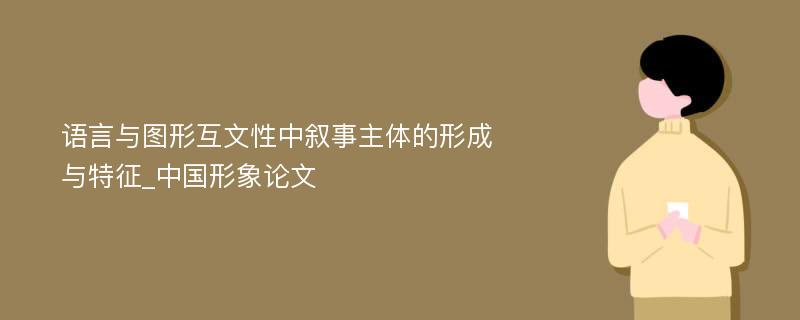
“语-图”互文之中叙述主体的生成及其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4)01-0107-05
“叙述者”是西方叙事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研究特点在于把“叙述者”与传统中的“作家”研究划清界限,重点从叙述文本内部研究“叙述者”所具有的叙述特征、种类及其叙述风格等等方面的问题,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然而,西方叙事理论的缺点也就在于其研究文本的封闭性和把“叙述者”作为一种抽象性的叙述机制方面。我们知道,如果“叙述者”完全封闭于“文本”之中,那么除了明显的语言标示之外,“叙述者”又怎样表现“自己”,又怎样表现与语言文本的关系呢?既然“叙述者”是叙述本身塑造的特殊形象,那么,“它”又怎能左右其所“身处”的语言呢?这些难题实质上表现了人类叙述行为所具有的深层矛盾,也影响了有关“叙述者”问题研究的深入。有鉴于此,本文把“叙述者”范畴扩大为“叙述主体”。一方面,“叙述主体”融合了“叙述者”与“作者”这两个范畴,尤其注重类型化“作者”的文化心态、叙述观念及其叙述风尚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结合本文论题,我们把“抒情人”也作为“叙述主体”的重要类别之一,由此深入探讨“抒情人”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审美价值。由此,“叙述主体”成为我们连接图像叙述内、外部研究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成为我们全面探讨中西叙述特征与奥秘的一个新的契入点。
一
在口传叙述传统中,“面对面”是叙述交流的必要条件,表示着叙述主体与接受主体双方的“在场”。因此,在口传叙述中,无论“在场”的叙述主体以何种“人称”出现,叙述信息交流的本质都是“我”对“你”讲。“口传叙事一律展示出一个权威的和真实的叙述者,他具有能力观察来自各个方面的动作和告知一个人内心的秘密”[1](P51),叙述主体以“我”的身份控制着叙述语言,要么作为“故事层”的参与者或见证人(“我”说着“过去的我”所遇到的“故事”);要么成为“叙述层”的叙述者(“我”说着“我”现在的叙述行为)。(注:“故事”与“叙事”是西方现代叙事理论中的一对重要概念,虽然对其含义略有分歧,但是,一般认为“故事”指未经任何特定视点和表述歪曲的客观事件结构;“叙事”是指被叙述出来的“故事”。其中涉及到叙事文本的分层问题。参见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版,第125-126页。)其中尤其是后者具有很强的“元叙述”特征。同时,在口传叙述中,叙述主体的形象、语调、表情、姿势等因素虽然外在于所叙“故事”,但是这些因素左右着“故事”的种种感情表达,具有极强的“视听”可感性,无疑是叙述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字叙述中,口传叙述的“在场”特征遭到破坏,叙述主体众多可感因素都“消融”到文字中,“叙述主体”蜕化为“不在场”的抽象叙述主体,“叙述主体”由此变成了一个文字逆推出来的“虚拟形象”,一个永远无法复归“原形”的主体“投影”。这样,叙述主体身份及其叙述行为变得异常复杂起来,由此也强化了叙述行为的一些本质特征:(1)叙述主体是可以“分裂”的:叙述主体(“叙述层”中承担叙述行为的“本质的我”);叙述者(“故事层”中“叙述的我”);行动主体(“故事层”中“参与事件的我”)。三个分裂的“我”本质上是无法复合的,尤其是叙述主体(叙述层中叙述行为“本质的我”)已经“抽象”为一种叙述机制,无法具体表征。而叙述者(“故事层”中“叙述的我”)和行动主体(“故事层”中“参与事件的我”)只是叙述主体语言叙述行为中的“面具”人物,表示着叙述主体“具象化”的不同形态[2](P34)。(2)叙述主体的多重分裂,产生了叙述主体与行动主体之间叙述行为的“时间差”问题,深刻揭示了叙述行为的“时间”差异特征。我们知道,叙述的本质在于讲述接受主体未曾经历的事情,也就是说,叙述主体本质上是在叙述过去的事件或未来的虚拟事件,而很难叙述“现在时”的事件。叙述的“现在时”事件是正在目击的事件或叙述行为本身,叙述主体对正在目击的事件“边看边说”并非不可能,然而如果接受主体“不在场”,这一叙述行为也就失去了价值;叙述行为本身是一般属于“元叙述层”,本身也是几乎“不可自说”的,就像“观看者”一样几乎无法“看到”自己(照镜子应该是人的一种特殊的“看”)。现代广播、电视叙述的“现场直播”似乎解决了这一问题。然而,其中的“报道者(主持人)”充其量只是“叙述者”(“故事层”中“叙述的我”),真正的叙述主体还是摄像机背后的“眼睛”及其几乎机械化的叙述主体机制。一旦图像叙述“直播”的主要场面完全展开时,所谓的现场“报道者(主持人)”就会被摄像机、声讯传播设备等组构的传播机制“抽象”而去,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主体之间无法弥合的裂痕。(3)叙述主体的身份分裂,导致不同叙述主体之间的肯定、否定、怀疑、讥讽等多种情感关系,进而形成叙述主体不同叙述语调和叙述风格,成为语言修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我们总结了“口传叙述”与“文字叙述”之中“叙述主体”的不同特征。我们发现,“叙述主体”的这些不同特征主要基于西方叙事学的理论概括,也就是说是基于史诗、故事、小说之中的“叙事”分析而得来。那么,这一“叙述主体”特征是不是具有“普适性”呢,也就是说,这一基于“叙事”的“叙述者”特征是不是也适用于“抒情”之中的“抒情人”呢?施塔格尔认为:“叙事是‘面对面’,即把过去的事情放在眼前(呈现);抒情式的诗走进过去或现在发生的事情里并与之融合,即是说,他‘召之入内’。诗是‘回忆’,应当是表示主体与客体之间没有间隔距离,表示抒情式的‘互在其中’”[3](P52),这段论述表明了叙述主体在“叙事”和“抒情”中的不同状态。在“叙事”中,叙述主体要确立自己的身份“位置”,要确立“他”所讲述的“客体”,同时,还要关注“他”所面临的接受者,可以说,围绕着叙述主体所形成的这三重关系表现了人类初期叙述的基本状态。“叙事是‘面对面’,即把过去的事情放在眼前(呈现)”,就表明叙述主体是外在于叙述的“客体”和“接受者”的,这种叙述的“距离”给叙述主体营造了讲述、见证和发表见解的“空间”。可以说,“面对面”在叙述中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也就是文字叙述“破坏”了口传叙述的“在场”特征之后,依然努力营造叙述“拟在场”的根本原因。
二
相比较而言,由于图像叙述主体无法以“我”的身份进入图像之中,同时又让这个“我”承担起叙述的功能,因此,图像叙述主体显得更为“抽象”,图像叙述的直接抒情也显得十分困难。在主体的体验状态中,自然的主体化比较容易,然而,要把这一主体体验的自然“物象化”并叙述出来却有一定的困难。图像叙述是具象性的,“自然”与“叙述主体”之间“物我”的形体差别难以混同,图像叙述的自然形象描绘得越“逼真”,与叙述主体的“距离”就越大,因此,自然物象融合主体情感,除了需要语言叙述及其意义阐释模式“帮助”之外,还有两个呈现途径,一是由画幅逆推出来的叙述主体具有特殊的情态特征;一是叙述主体改变物象的逼真形态,对自然物象进行变形,变形程度可以组成一个从小到大的谱系,一般来讲,图像叙述的图形变形程度越大,其表现的叙述主体意图就会越明显。
一般来讲,图像叙述主体只能表现在“他”看的方式之中,由此形成图像叙述主体的三个文本确立因素:视点、位置与方向。“视点”是虚拟于画幅之中的叙述主体的视觉集中点,“视点”一旦形成,就暗示着“叙述主体”站立的“位置”及其无形的目光,这样,图像叙述主体是“可感的”,“他”是一个“观者”;另一方面,图像叙述主体又是“无形的”,因为“他”只能“站在”画幅前面,无法像面对镜子一样反观自己,而一旦图像中出现了“叙述主体”的真实形象,那么,“叙述主体”的身份就发生了分裂,图像之中的“叙述主体”就蜕变为一位被画外“叙述主体”观看的特殊对象。其原有的叙述主体身份之中的叙述功能肯定相当弱化甚至消失(注:对于所谓的“自画像”,除了直接描绘挥毫作画的画家外(中西画史中这样的画家形象并不多),叙述主体的自我身份一般需要语言提示,如《自画像》等,或者需要另外一个图像与语言叙述来印证。)。现代运动图像并未改变图像叙述主体的“隐身”特征。在叙事性的运动图像叙述中,“叙述主体”如果以“我”的口吻讲述故事,那么,除了语言叙述外,这个“我”必须是”隐形的”;而一旦这个“我”在故事中现身,那么“我”就蜕变为一个“人物”或“行动者”,而丧失了其作为“叙述主体”的叙述功能。摄像之中的“引导人”和电视直播中的“主持人”也许是图像叙述主体直接现身的最为极端的例子。然而,即使是在“现场主持人”手持话筒“面对面”的讲述中,“现场主持人”的声画形象仍是通过“无形”的摄像机及其叙述系统来展现,而一旦“现场主持人”向接受者呈现他所目击与见证的事件,那么,他就会“隐身”于呈现的图像之外,充其量只能用“画外音”叙述图像的叙述流程。因此,从图像空间中所逆推出来的“叙述主体”一般是单一的、非性格化的,表明着“观看的”一种逻辑机制,与语言叙述主体的抽象本质一样,是一个阅读(看)行为逆推出来的“特殊形象”。然而,图像叙述主体与语言叙主体之间又有着深刻的不同。(1)语言叙述主体根植于口头叙述主体,虽然“它”丧失了现实的“在场性”,可是“它”在文本叙述中仍试图建立一个“我—你”的交流系统,这一点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以“说书人—看官”的模式化形式体现得极为典型。一些学者认为图像叙述是“呈现的”而非“叙述”的,那么其中是不是就不存在叙述主体呢?对于这一争论较多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图像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叙述行为,其中必然存在着叙述主体。图像叙述主体的特殊性在于其叙述是“隐性的”,其叙述是一个限制“范围、内容、角度和清晰度”等方面的“看”的过程,一旦某人“看”一幅图像,某人就代替了“叙述主体”的叙述位置。因此,图像叙述及其接受就具有一定的自为性和自在性,“看画”就成为接受者与图像之间的双向交流过程。因此,图画像叙述的接受是一个“观看”的替代过程,很难形成类似于语言叙述明晰的“叙述主体—接受者”的交流语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图像叙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把语言叙述的“你听”转化为“我看”。(2)由于图像叙述主体与接受主体的“阅读位置”趋同,叙述似乎是“无中介”的,叙述接受者就更容易接受图像所“呈现”的物象;然而,也是由于“无人引导”,叙述接受者意欲看出其中的物象“意义”就又显得相对困难。同时,也由于上述原因,叙述接受者的“目光视域”就大于画中的任何人物。语言叙述中的“视角人物”及其“视线”消失了,接受(看)的目光就是图像叙述主体的“全知”视角。(3)语言叙述中“视角人物”是丰富叙述“多调性”或增强抒情真实性的一种重要途径。然而,在图像叙述中,“视角人物”的诸多叙述功能都有所减弱,这是图像叙述的叙述方法与抒情变得相对“单调”甚至困难重要原因之一。
三
西方图像叙述的“定点透视方法”在画幅中标出了一个虚拟的“聚焦点”,由此,表明了叙述主体观看景物的某一最佳位置,表明着“叙述主体”的“在场”。“叙述主体”成了叙述的“见证人”,从而迎合了追求科学、客观真实地反映世界的文艺复兴时尚。这样看来,“定点透视法”只是确立图像叙述主体功能的一种极端形式而已。贡布里希认为“透视法”的发明和使用基于西方的“见证原则”[4](P63),体现了艺术逼真摹仿现实的叙述原则。的确,现代摄影与摄像技术的发明证明了“眼见为实”及其对这一视觉实境摹仿再现的可能性。因此,“定点透视法”成为西方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对西方摹仿型再现艺术传统的成熟与发展意义非同寻常[4](P85)。“定点透视法”不仅强调科学地看,而且要求把所看到的物象“逼真地”描绘出来,这其中既包含着叙述技巧的新的革新和叙述接受的新的要求,也包含着叙述观念的新的变化,图像叙述主体基于视觉现实的聚焦点、明确的定点位置、理性思考等概念就成为西方近现代图像叙述的“关键词”。“定点透视法”对文学叙述的影响在于,它增强了西方几乎整个19世纪文学叙述主体摹仿现实的信心,培养出全知全能的自信的语言叙述主体。叙述主体可以对环境进行目击般的细致描写,时时提炼着语言叙述的中心(聚焦点),并以“见证者”的自信身份对现实进行客观理性的思考评论。可以说,从文艺复兴时期薄加丘的《十日谈》开始,西方叙事文学(小说、戏剧)就与同时发明的“透视法”一起,促发了整个西方叙述方式的巨大转型。中世纪基督教的镶嵌画与叙事文学表现出多重人物、多个视点和多起事件,至文艺复兴则转化为单个人物、单一地点和单一场面,时间变成了线性的序列,事件沿着因果的、先后的情节线索发展。在此背景中,语言叙述与图像叙述表现了叙事观念的一致性,也突出了二者在叙述媒介方面仍然无法调和的叙述矛盾[5](P344-348)。19世纪雨果、巴尔扎克、左拉等作家所代表的欧洲文学叙述更是“定点透视法”及其自信叙述主体的成熟表现,而在20世纪罗伯—格里叶“新小说”的创作中,“定点透视法”的运用可谓发展到了几具反讽性的顶点,其叙述主体趋于客观化,更接近于叙述主体的机制特征。总之,西方“定点透视法”所培育的叙述主体,无论“他”是全知自信的“讲述者”,还是客观默然的“观看者”,都彰示着叙述主体与所叙(看)对象之间无法弥合的距离与差别。西方的叙述主体是外在于、高于其叙述对象的,像达芬奇所谓的“绘画与自然争胜,并超越自然”的观念不仅是图像叙述由科学技术所确立的信条,也成为其它艺术描写现实、再现自然的自信原则。
四
汉诗的语言叙述“借景抒情”异常便捷,虽然中国第一首纯咏物诗出自曹操,但是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众多“以景比兴”、“融情于景”的佳句。王国维论“境界”时分析出汉诗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并认为“无我之境”高妙于“有我之境”(王国维《人间词话》)。实际上,无论是“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本质上都是“有我之境”,因为在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中,我们还是能够明显地感知到“隐形的”抒情主体。以张继《枫桥夜泊》诗为例: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从表面上看,这首诗十分符合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即诗句纯以景出。然而,细品此诗,我们还是时时感知着那个“感知—呈现”的“隐形”抒情主体的存在,换言之,诗中“物象”都由抒情主体“视听”而得,其中的一个“愁”字更是以浓郁的情感强度“点明了”抒情主体的抒情指向,成为统一众意象的情感“凝聚点”,并由此形成全诗幽渺孤寂的“乡愁”意境。因此,王国维所分析的抒情的“有我”与“无我”之境实质上只是表明了抒情主体“显”与“隐”的不同状态,并不能说明抒情主体的“有”与“无”。在“抒情”之中,“感知之我”与“抒情之我”表明着抒情主体所处的两个阶段或两种状态。在“叙事”之中,叙事主体一方面要面临“客体”,另一方面要面对“接受者”,这就要求叙事主体必须尽量“还原”客体形态与时间过程,保证叙述交流的正常进行,此时,叙事主体的权威化或见证人式的身份特征十分明显。与西方古代史诗中的“非角色化”叙述主体不同,汉诗语言叙述的抒情优越性在于抒情主体的“自我”特征异常显著。由于历代类型化文人的锤炼,这个抒情主体逐渐成为抒情中具有共同品位与认同感的“大我”,这个“大我”的抒情“直接性、交融性、在场性”强,在本质视域中可以灵活地转变身份。这正是中国古代“语-图”互文中“文人”形象性格塑造呈现的基础。同时,中国古代诗歌强调抒情的“经验性、当下性、即时性”特征,尤其是格律诗,篇幅短小,文人的抒情常常是当场脱口而出,抒情自我由此融入当下的情景之中,我行我事,我抒我情,抒情自我始终保持着反思之前的本真特征与高度的统一性(注:西方的叙事主体(尤其是自传中的叙述主体)那样,“反思之我”、“行动之我”与“叙述之我”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叙述主体”把“行动之我”和“反思之我”叙述客观化,并以严格的时态标示出来。)。
叙述主体的本质具有一定的抽象特征,西方的叙事学理论家从人物行动代码、叙述机制等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当然不会认为这一抽象特性是由传统的“形而上”理论决定的。然而返观中国叙述,我们确实发现中国古代叙述主体与“形而上”的“道”之间的亲密关系。中国古代叙述主体体验“道象”、描绘“道象”,都努力地融入万物自然之中,“自我”以一种原初的、自然的状态感受“道象”的运行之理。先秦的“象说”之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其实都在泯灭“小我”而追求“大我”,然而,中国古代体验主体和实践(叙述)主体的“自我”本质并不是西方“理性、意志、机体”所组成的生理的、心理的或目的论的“自我”,而是一种“焦点—区域式自我”,这个“区域”是由特殊的体验状态、家庭关系或社会政治秩序所规定的各种特定的环境构成,其焦点聚集于个人,区域影响、塑造个人,又使个人融为集体。这个“自我”的本质决定了体验主体的开放性、灵活性和趋向“道”的顺从性与实践性等诸多特征[6](P27、44、52),这些特征都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叙述主体的形成,并构成“类型化”叙述主体的基础。中国古代“类型化”叙述主体具有一定的群体化特征,在语言叙事中形成“记言者”和“说书人”两大叙述主体类型,二者分别源于先秦史官和唐宋民间“说书人”,都具有非角色化叙事主体的全知、自信和隐形特征。“记言人”和“说书人”一般极少在叙述中自称,而是自觉归从于其身份所规定的“笔录”与“演说”的严格功能界定。中国自古浩瀚的史书和通俗叙述作品中,一直通行的是这两类“类型化”特征极强的叙述主体。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抒情主体也十分成熟,一般来看,中国古代抒情主体的“自我”特征较为明显。然而仔细探究,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这一抒情叙述主体本质上也是群体“类型化”的,这就是我们上文已经简单论述的“文人化”特征。这一“文人化”抒情主体与社会的关系密切,可进而分为“出世者”和“入世者”两大类型,“他们”独善其身也好,兼济天下也好,都体现了鲜明的基于儒道理想的“士”的类型特征。相对于中国古代图像叙述主体而言,人物画与故事画一般在政教阐释背景中展开,在明晰化的叙述交流中主要表现一种“叙事性”。其叙述主体类似于语言叙述的“记言者”,“它们”旨在还原事件的原貌或强调事件之中的意义,十分近于语言叙述的“史官”和“说书人”的身份,类型化特征十分明显。山水画和花鸟画之中的叙述主体则类似于语言叙述中的抒情主体,“他们”完全借“形象”来抒情,并通过“类型化”的阐释规范使其抒情富有韵味效果。宋元“文人画”出,其图像叙述主体直接追慕老庄“道象”,“道象”特征进一步培育出图像叙述主体独特的审美品格。六朝时期,宗炳、王微等人澄怀味象、卧游畅神,善画山水的萧贲等人则“学不为人,自娱而已”,这些都说明具有类型化特征的文人叙述主体的形成。类型化特征的文人叙述主体强调文人叙述主体的“体道乐感”和自我美感形象的表达,其呈现的是“抒情性”。类型化特征的文人叙述主体的成熟也催生了中国山水画和花鸟画的成熟,人物、花鸟、屋室等古老题材表现出新的叙述观念和叙述美感。而从图像叙述的实践看,这一类型化的文人主体通过诗书印画的文本互融而完美定型,成为中国古代叙述最具特色的叙述主体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