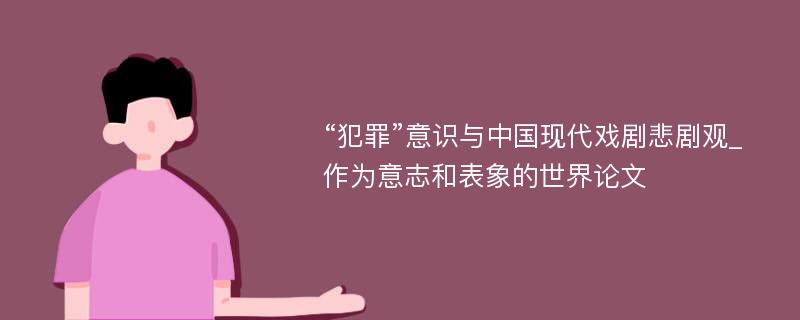
“罪”意识与中国现代戏剧悲剧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戏剧论文,悲剧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外来文化影响而言,精神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化,是一部分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文化资源 之一。尽管它不像传统的儒、道和佛教思想深深潜入作家们的心底,却也诱发了一部分现代 批评家、作家,尤其是剧作家,在悲剧意识方面的转化。
一、“罪”意识与中国近现代悲剧观念的蜕变、发展
中国近、现代戏剧中的悲剧观念,指的是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剧作家、理论家在悲剧作 品、批评文章、理论著作里,表现出来的对戏剧中悲剧的种种认识或看法。主要有:何为戏 剧中的悲剧,如何构置戏剧悲剧的冲突,如何把握戏剧悲剧中的悲剧性格等。
“罪”意识指的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从“原罪”及其“本罪”概念体现出的人性恶,罪 恶感等观念。“罪”意识对西方文化发展具有某种引导性。这不仅表现在中世纪前后的西方 哲学、文学中,也表现在19世纪以后的哲学、文学中。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较大的西方学 者、作家,如叔本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身上,都很容易看到这些影响与表现 。
进入20世纪,中国社会不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悲剧观念也处在不 断变化之中。王国维、鲁迅、朱光潜的著述,在中国悲剧观念的蜕变、发展的过程中,可以 说具有座标与基石的意义。而他们,多少都受到过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其中王国维、朱光潜 更 为典型。
王国维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并且运用到自己所研究学科中的学者。在初 刊 于1904年《教育世界》的《<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论述的三个问题:什么是悲剧、第 三种悲剧、彻头彻尾之悲剧,对中国近现代悲剧意识的蜕变、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王国维认为,人的出生、生存本身就是痛苦,就是悲剧。他借用老子的话说:“人之大患 ,在我自身。”(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见张正吾等选注《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文论卷》
,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313、325、320页,第322页至323页。)但是,“王氏意不在老庄,不过借以旁证叔氏所宣扬的那个‘原罪’说而 己”。(注: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55页。)王国维阐述道:“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实由吾人类之祖先一时之误谬。”“夫人 之有生,既为鼻祖之误谬矣”,“则鼻祖之罪,终无时而赎,而一时之误谬,反复至数千年 而未有已也。”(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见张正吾等选注《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文论卷》
,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313、325、320页,第322页至323页。)
可见,王国维所说悲剧的起源与他所谓的“欲”,明显通着叔本华的原罪 ,也即基督教文化中的“原罪”。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写道:“悲剧的真 正意义是一种深刻的认识,认识到(悲剧)主角所赎的不是他个人特有的罪,而是原罪,亦即 生存本身之罪。”他还引用西班牙剧作家加尔德隆的话说:“人的最大罪恶就是:他诞生了 。”(注: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2至353
王国维深受叔本华这种悲观主义理论的影响,认为:在罪的“轮回”中,个体求得解脱之 法,只有拒绝意志、拒绝一切生活之欲。即“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因为 ,“出世”与“在世”相对,意味着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自杀的结果“去世”,与“来世” 相对。“去世”之后,一经轮回,又会依然“在世”。《红楼梦》的伟大,就在于既将“人 人所有之苦痛”,“掇拾而发挥之”; (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见张正吾等选注《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文论卷》
,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313、325、320页,第322页至323页。)
又通过“出家”,展示了一条正确的解脱之道—— 中国式的出“欲”之道。
王国维将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 第 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 必须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在这三种悲剧之中,王国维认为第三种悲剧“贤于 前二者远胜,最为感人”。因为,它所描写的是生活中“普通之人物”,在“普遍之境遇” 中,“逼之不得不如是”。揭示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 (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见张正吾等选注《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文论卷》
,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12、313、325、320页,第322页至323页。)
。王国维的第三种悲剧论,同样来源于叔本华的悲剧说。叔本华曾将悲剧,划为“三个类 型”:其一,“造成巨大不幸的原因可以是某一剧中人异乎寻常的,发挥尽致的恶毒”。其 二,“还可以是盲目的命运,也即是偶然的错误。”其三,“也可以仅仅是由于剧中人彼此 的地位不同,由于他们的关系造成的”。“道德上平平常常的人们”,“在经常发生的情况 下”,“处于互相对立的地位,他们为这种地位所迫”,“互为对方制造灾祸,同时还不能 说 单是哪一方面不对。我觉得最后这一类(悲剧)比前面两类更为可取,因为这一类不是把不 幸当作一个例外指给我们看”,“而是当作一种轻易而发的,从人的行为和性格中产生的东 西,几乎是当作(人的)本质上要产生的东西,这就是不幸也和我们接近到可怕的程度了。” (注: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52至353 页。)叔本华的悲剧类型说,在美学上有一定的意义。但是,从根源上看,显然又是来自基督教 思想中的原罪说,是“‘人生即是悲剧的诞生’的论点的一种反映。”从社会效果看,可能 会使人认为“苦难是与生俱来的”,“作为受苦受难的悲剧之人,只须一心一意赎他的‘原 罪’就行”,而“对世上的邪恶、非正义和不公平不要有任何的抱怨和斗争”(注: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332页。)。
就这样,王国维没有主动靠拢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中的一些重要因素,尤其是‘罪’ 意识,却通过王国维所接受的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也通过王国维所阐述的悲剧观念,在中国 近现代悲剧意识的蜕变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影响。
朱光潜是中国现代时期,“把文学批评的理论上升到实用美学的高度来研究”的学者(注: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49、251 、252页、第250页,第249至250页。)。 他在《悲剧心理学》中,对悲剧学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悲剧表现 的是受难与反抗。
论及其理论源头时,多认为朱光潜与克罗齐美学关系密切。“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 作为朱光潜美学理论的起点是叔本华。可以说,比起其它外国的哲学美学家来,叔本华给予 朱光潜的影响更是根本性的。朱光潜几乎同他所赞赏的美学前驱者王国维一样,在人生观上 也倾向过叔本华,从而一开始就以叔本华的文艺‘解脱说’作为自己美学观与文艺观的第一 块基石。”(注: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49、251 、252页、第250页,第249至250页。)
朱光潜在继承与批判黑格尔与叔本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过,就悲剧理论 而言,他对黑格尔的批判似乎多过继承。他批评“黑格尔像讨论过悲剧的大多数哲学家一样 , 采用一种很不好的方法,即从一个预想的玄学体系中先验地推演出一套悲剧理论来,而不是 把悲剧理论建立在仔细分析古代和近代悲剧杰作的基础之上”。他认为:“黑格尔很少谈论 悲剧中的受难。然而叔本华却把这一点变成唯一重要的因素。”“对于悲剧来说,只有表 现大不幸才是重要的”。并说:“叔本华也许比黑格尔更接近真理。……他对于我们认识悲 剧至少作出了两大贡献。一是他比别人更能使我们生动地感受到悲剧悲观的一面。……强调 悲剧中的受难,就填补了黑格尔留下来的一个空白。”在此基础上,他也批评了叔本华,并 形成、提出自己的看法:“严格来说,叔本华说‘只有表现巨大的痛苦才是悲剧’,并不符 合实际情形。……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对悲剧来说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是 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 。”“悲剧正是描写悲剧英雄甚至在被可怕的灾难毁灭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自己的活力与 尊严,向我们揭示出人的价值。”(注: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118页、第119页、第12 1页、第121页、第138页、第140页、第206页、第122页,第207页、第218页、第221页。)在对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有所继承、批评的基础上, 朱光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悲剧不仅表现受难,还应表现反抗,悲剧表现的是受难与反抗。
朱光潜和王国维、鲁迅一样,严厉批评中国传统的“大团圆”方式。他认为大悲痛和大灾 难,在一切伟大的悲剧中是不可避免的。他借用尼柯尔的话说:“悲剧认定死亡是不可避免 的”,并发挥道:“人非到遭逢大悲痛和大灾难的时候,不会显露自己的内心深处,而一旦 到了那种时刻,他心灵的伟大就随痛苦而增长,他会变得比平常伟大得多。”但是,在中国 “戏剧情境当然穿插着不幸事件,但结尾总是大团圆”。他认为,没有了大悲痛和大灾难的 结尾,等于就没有了悲剧。“中国文学在其他方面都灿烂丰富,唯独在悲剧这种形式上显得 十 分贫乏。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论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时,他倾 向于批判剧作家的“道德感”。认为是“他们强烈的道德感使他们不愿承认人生的悲剧面 ” (注: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118页、第119页、第12 1页、第121页、第138页、第140页、第206页、第122页,第207页、第218页、第221页。)。
朱光潜关于悲剧的这些观点,以及他研究悲剧的思路与方法,在现代悲剧理论的发展中, 具有积极的意义。如温儒敏说:“当时很少有人像朱光潜这样认真地把批评原理的研究提升 为一种实用美学,也少有人用科学的方法分析文艺创造和欣赏心理的事实,并以此探讨批评 的本质” (注: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49、251 、252页、第250页,第249至250页。)。朱光潜关于中国“在悲剧这种形式上显得十分贫乏”的说法,已经引起过不 少的争论,且还有待争论。但他对中国传统的“大团圆”方式严厉批评,是醒目与有益的。 他 的“受难”—“反抗”说,对王国维的“苦难”—“出世”说,是一种修正;对鲁迅的“ 愚昧”“毁灭”说,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从王国维经鲁迅到朱光潜,中国悲剧观念有了极大的变化。它既标志着中国悲剧观念时代 性的转换,也影响、制约和呼应着中国现代戏剧悲剧观念的多向流变。
二、“罪”意识与中国现代戏剧悲剧观念的转化过程
西方戏剧在我国演出,最早从教会学校演出宗教剧开始。中国早期话剧,由此受到基督教 文化艺术的重要启迪与影响。但是,其对中国早期话剧的影响,只限于话剧形式——只说不 唱的演法;话剧观念——追求真实的、生活化的表演观念两个方面。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影响,比较广泛、深入。中国现代话剧,经历了演西方剧本 、模仿西方剧本、写自己的剧本三段历程。通过五部剧作,可以对这个三段式,以及“罪” 意识与中国现代戏剧悲剧观念的转化过程看得较为清楚。
1.作为替代性“标志物”的《莎乐美》。
本世纪20年代初,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开创期。由于缺乏现代戏剧悲剧的创作经验与现代戏 剧中悲剧意识的“标志物”,中国现代剧作家们把眼光放在了西方。直到“找到”《莎乐美 》这部西方戏剧悲剧,才算找到一个他们所寻求的“标志物”的外来“替代物”。
《莎乐美》为中国话剧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悲剧意识。首先,悲剧人物性格极端复杂,而且 “善”、“恶”交织。其次,悲剧表现受难,更应表现反抗;而且,是主动选择的反抗,以 死为代价的反抗。
《莎乐美》是一部翻译剧,严格来说,它只是向现代中国展示了一种全新的现代西方的悲 剧意识。尽管如此,田汉翻译《莎乐美》,在中国现代悲剧意识的转换途中,还是极具意义 。首先,它的发表时机,恰好在中国现代剧作家,急待转换悲剧意识,而又缺乏明确的“实 例”导引之时,《莎乐美》译作的出现,客观上给了中国现代剧作家,一个他们所寻求的“ 标志物”的“替代物”,而且,是一个极“现代”、高水准的“替代物”。其次,《莎乐美 》与中国古典戏剧悲剧的“悲喜交集、苦乐相错”的传统大相径庭。田汉的引进,是有选择 性与创造性的。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戏剧家,在观念上发生了变化后的选择。
2.试图摹仿“替代物”的《暗嫩》。
中国现代剧作家,一方面以《莎乐美》这部西方戏剧悲剧,作为他们所寻求的“标志物” 的“替代物”;另一方面,也在试图尝试以摹仿“替代物”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标志物” 。向培良的《暗嫩》,就是这种探索途中的一次没有成功却值得注意的尝试。
向培良学习王尔德,到《圣经》中寻找题材。从作品的整体构成看,向培良并没有像王尔 德那样,取材圣经、背离圣道;也没有像王尔德那样,通过“断章取义”,变更矛盾的中心 ,使戏剧的主题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作者的悲剧意识也比较模糊。首先,暗嫩以害人起,到害己终,主导方面始终是恶,并非 王尔德所说的“善”“恶”交织。以暗嫩作为悲剧主角,也显示出作者对悲剧的本质,缺乏 深入认识。其二,《暗嫩》中,所谓“理想”的幻灭、“热情”的消逝,都无法作为“悲剧 ”的毁灭性事件。事实上,是强者毁灭了弱者,作者却把弱者放在一边。
向培良在《暗嫩》中的尝试,是现代剧作家试图通过“摹仿”,建立“新悲剧”的一次“ 投石问路”。其中悲剧意识的混乱,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现代悲剧意识,在蜕变、转换 过程中的一种迷惑与阵痛。
3.在摹仿中转变观念的《潘金莲》。
当向培良注重对“替代物”的形式进行摹仿时,欧阳予情注重的是对“替代物”的精神进 行摹仿。他创作的“翻案剧”《潘金莲》,在中国现代戏剧悲剧意识建立过程中,是通过摹 仿、转变观念的一次较为成功的尝试。
欧阳予倩借用王尔德的“变形”精神后,即转向解构中国文学的“经典”——《水浒传》 。在《莎乐美》为中国话剧,展现了一种全新的西方悲剧意识之后,《潘金莲》继以创作的 成果,摹仿、实践、张扬了这一全新的悲剧意识。
首先,欧阳予倩借鉴了王尔德对悲剧人物的认同与表现方式:悲剧人物性格极端复杂,大 “善”与大“恶”交织。中国古典悲剧中,悲剧性格的善与恶非常分明。美与丑、善与恶, 分别被设置在矛盾冲突的两个互相对立的方向。潘金莲作为主要悲剧人物,她的“美与善” 被“夸大”;她的“恶与丑”没有被“删节”,也没有被缩小。因而,她是一个性格极端复 杂,带有全新意味的中国戏剧中的悲剧人物。
其次,欧阳予倩借鉴了王尔德对悲剧毁灭性事件的理解:悲剧表现以死为代价的大苦大难 ,更应表现受难者以死为代价的反抗。《潘金莲》强调悲剧人物对生存环境的顽强拼搏,强 调“受难”之前“壮快淋漓”的反抗。
如果说,田汉翻译《莎乐美》,客观上显现出中国现代剧作家悲剧意识演进的话;那么, 《 潘金莲》作为中国现代剧作家创作的戏剧悲剧,意义与影响都大不相同了。它不仅表现出中 国现代剧作家在悲剧观念方面至关重要的转换性的变化;而且,在整个中国现代悲剧意识转 换的过程中,还“扮演”着以“摹仿物”真正替代“替代物”的“角色”。
4.显示“自我身份”的《雷雨》与《原野》。
到了曹禺的《雷雨》与《日出》,受到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中国现代戏剧中的悲剧意识,便 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历程——由翻译、经摹仿、到转换——再到此时的,进入高峰与成熟 。
曹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剧作家,在经过一段主要接受以挑战、颠覆为特征的西方反 基督教文化之后,又出现了另一种接受方式:注视、解读并有选择的接受一个自成体系的基 督教文化,以悲悯的心态看待悲剧作品中的所有人物。曹禺说:“我曾经找过民主”,“甚 至对基督教、天主教,我都想在里边找出一条路来”(注: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北京作家谈创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6月版。)。在基督教文化中,找社会的出路 、 个人的出路,也许只是作家的一段历程,但它宣示着基督教文化中一些重要的观念、意识, 有了潜入中国戏剧作家意识的可能。中国现代戏剧悲剧观念的转化过程,也揭示了这种可能 。
《雷雨》的整体架构,以及作者对整体架构的说法,便透露着这种讯息。在“序幕”与“ 尾声”中,周朴园“衰老”了、变化了;性情变得“沉静而忧郁”,外貌变得“可怜与窘困 ”。言行透露出愧疚与悔意。这时的周朴园,对侍萍更愧疚;他的关心,更多放在侍萍身上 。对周朴园的这种变化,曹禺后来在作“自我批判”时,有过“实证”:“旧本《雷雨》的 序幕和尾声中周朴园衰老了,后悔了,挺可怜的,进了天主教堂了。”(注: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曹禺研究专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上 册,第107页。)可见,这个“完 整的戏剧构架”,以环境的外在变化,透露着一种宗教气息;以人物的内在变化,透露着作 者对悲剧中包括周朴园在内的每一个人的悲悯。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超乎阶级意识的具有基 督教“泛爱”色彩的悲悯。
在《雷雨》的“躯干”部分,作者同样显现出对人物的这种悲悯。作者写足了周朴园,作 为一个“坏人”之坏。接着,作者也以悲悯之心,写出了周朴园作为一个稍有“忏悔”之意 的“罪人”,“认罪”的开始。由于特定的阶级立场与观念,周朴园对许多罪,并不认为是 罪,也没有“悔”。但是,对侍萍的悲剧,他已开始“认罪”,走向“忏悔”。
曹禺领会着欧阳予倩对悲剧人物的看法。但是,他将“悲剧人物性格极端复杂”,改为悲 剧中人物性格极端复杂;将人物性格外显式的“大‘善’与大‘恶’”,内化为人物内心世 界的“善”、“恶”交织、“善”、“恶”冲突。曹禺也体会着欧阳予倩曾借鉴、“摹仿” ,来自王尔德悲剧中的“毁灭意识”与安排“毁灭”的基本构思。但是,他不仅消融了反抗 中的“唯美”色彩,还更加注重对“毁灭性事件”中反抗的发挥。他把悲剧性人物的反抗, 从“‘受难’之前‘壮快淋漓’的反抗”,“拉长”成一个曲折、复杂、无奈的反抗过程; 把一个以“受难”为“舞台”,以“壮快淋漓”地展示某种“思想”、“主义”为目的突出 型反抗;改变为悲剧性人物,不断反抗“受难”、挑战“受难”,最后,在走投无路中被迫 陷入“受难”的挣扎型反抗。
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悲剧,相互碰撞的路径来看,《雷雨》、《原野》的出现,标志 着30年代中国现代悲剧意识,也从“另一种路子”走向了高峰;标志着中国现代剧作家走出 了对西方现代悲剧意识的“摹仿”,开始以自我的身份,确立起了自己的“标志物”。
三、“罪”意识与中国现代戏剧中悲剧观念的新特点
在基督教文化曲折、迂回、复杂的影响之下,中国现代戏剧中的悲剧意识,立足于中国现 代社会,汲取着西方文化与艺术的智慧,从而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
其一,悲剧的起源论——打上了社会性与时代性烙印的欲望或追求。
自王国维从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中,以“欲”为纽带触及基督教的原罪说,一种新的悲剧起 源说,便被介绍到了中国:即将人的欲望与人的生存相连,作为生活的本质与悲剧的起源。 运 用这个理论,王国维分析了《红楼梦》并取得了较大成功。当时的话剧家,虽未主动认同这 一理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王国维的悲剧理论,作为一种观点依然存在着。由于《莎 乐美》的示范效应,以及曹禺的成功,悲剧起源于追求或欲望的意识逐步形成。从《莎乐美 》中的莎乐美、《潘金莲》中的潘金莲、《暗嫩》中的暗嫩,到《雷雨》中的繁漪、《原野 》中的仇虎,都可以看出:他们的悲剧,既不是生存竞争中的悲剧,也不是政治斗争中的悲 剧,而是在于他们拥有一种曾经是非常执著的追求与欲望,或为爱情、婚姻、自由,或为感 官享受,或为复仇。这些追求与欲望,既是体现着社会性与时代性特征的思想意识,也是打 上了社会性与时代性烙印的作为个体的人的追求与欲望。如果没有这些追求与欲望,莎乐美 、潘金莲、繁漪们会在她们的位置,生活得很好。在她们的社会中与时代中,有许多人就这 样不思不虑地活着。她们的生存处境,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郭沫若笔下的屈原——连 基本的生活保障与人身安全都丧失殆尽。复仇之后的仇虎,若不是为自己的“心魔”所困扰 ,也不会迷失在从小就生长在此的树林中。
其二,悲剧性冲突——既是悲剧人物与社会的冲突,又是悲剧人物自身性格的冲突。
由于将悲剧视作具有时代意义的追求与欲望遭受毁灭的悲剧,视作人性在愚昧中觉醒即遭 毁灭的悲剧;中国现代悲剧意识,对悲剧性冲突的理解有所扩展:悲剧性冲突,既可是悲剧 人 物与社会的冲突,也可是悲剧人物自身性格的冲突,更可以是两种冲突的纠缠、交织。戏剧 中悲剧冲突的逼迫与毁灭性力量,既可能来自社会,也更可能来自内心。就悲剧主人公的毁 灭而言,有时来自内心的逼迫,更甚于来自外在的逼迫。莎乐美、潘金莲、繁漪,因为有了 追求与欲望,才从愚昧与平凡中挣脱出来。但是,很快就因为她们的追求、欲望与社会、环 境发生激烈冲突,而走向毁灭。《原野》的悲剧性冲突,较为典型地体现着悲剧性冲突的两 重性:既是悲剧人物与社会的冲突,也是悲剧人物自身性格的冲突。复仇时的仇虎,冲突的 对象显然是整个黑暗的社会。他坚定不移地活下来,就是为了血债血偿、命命相抵。就此而 言,他的目的达到了,起码是部分地达到了。复仇后的仇虎,冲突主要发生在自己的内心— —手刃了好友、客观上造成了小黑子的惨死之后,心灵的自责——强烈的自我谴责。尽管当 时许多批评者,对此提出了批评,但《原野》展现出的新的悲剧意识,与批评者对新的悲剧 意识的批评,共同为中国现代悲剧意识增添了新的内容。
其三,悲剧人物性格——既非全善、也非全恶,而是善恶兼备、善恶交织。
中国传统的悲剧理论,有关“英雄”与“恶人”的说法就比较简单:“英雄”与“恶人” 的“道德实体”,是统一的。“英雄”的“道德实体”,统一于良善、纯洁、忠诚、崇高; “恶人”的“道德实体”,统一于邪恶、卑鄙、奸狡、低劣。
王国维推崇叔本华并引入西方悲剧人物性格论时,实质上便已经引入了悲剧人物——既非 全善、也非全恶,而是善恶兼备、善恶交织的观念。待到以王尔德的《莎乐美》进行实例“ 示范”时,对悲剧人物性格构成要素的理解要激进得多:“道德实体”的“分割”、“冲突 ”,成为了大“分割”、“大冲突”,而不是一般意义的“分割”、“冲突”。所以,莎乐 美之后,还出现了潘金莲这样大善与大恶交织的悲剧人物性格。曹禺对基督教文化有较深入 认识,写剧时又怀有深厚的“怜悯”之心。他的悲剧作品显示出的悲剧人物性格构成要素, 更吻合亚里土多德以来的西方主流性悲剧性格理论——悲剧主人公必须是与我们十分类似的 中等人——悲剧主人公的性格存在着“道德实体”的“分割”:“冲突”,即既非全善、也 非全恶,而是善恶兼备、善恶交织。曹禺的“怜悯”,使他对“恶人”周朴园的性格描写, 也出现了“道德实体”的“分割”、“冲突”现象。周朴园成为了中国现代戏剧悲剧中,为 数不多的在“道德实体”方面有所“分割”、“冲突”的“恶人”,“身上仍然找得到人性 ”的“恶人”。如此一来,在基督教文化影响下,中国现代戏剧中的悲剧,对所谓悲剧英雄 与悲剧中的恶人,都有了不同于以前的阐释方式与构建方式。
就这样,在基督教“罪”意识曲折、迂回、复杂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悲剧意识在起源说、 冲突论、性格塑造等观念方面,都具备了新的特色与变化。
标签: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论文; 戏剧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潘金莲论文; 读书论文; 雷雨论文; 朱光潜论文; 基督教文化论文; 叔本华论文; 曹禺论文; 王国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