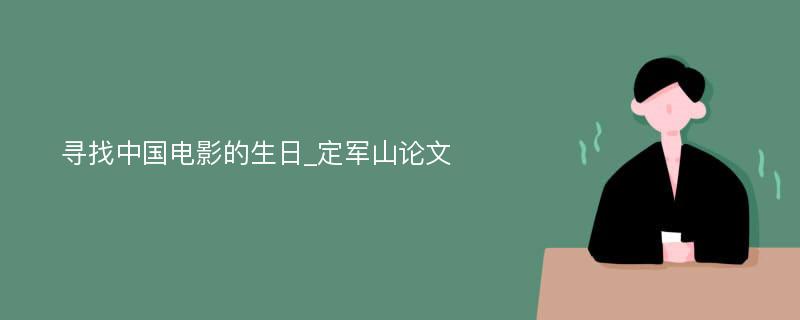
寻找中国电影的生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电影论文,生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定军山》之谜
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地下室售票放映了 《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拆墙》、《火车到站》、《婴儿午餐》、《水浇园丁》等 影片,被认为是世界电影的诞生。1995年,世界范围的电影百年庆祝活动,也都围绕着 12月28日这一天来进行。
10年后的1905年中国电影诞生。然而当我们庆祝中国电影百年的时候,同样的问题摆 在我们面前:只有知道《定军山》什么时候拍摄的,或者什么时候放映的,我们才能围 绕着这个“生日”展开庆祝。
但现有的所有资料,都无法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影片“前后拍了3天”,但 就是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天拍的,甚至连哪个季节拍摄的都不知道。《定军山》是在春夏 之交还是秋天拍摄的,是电影史学界讨论的焦点。
疑问不止于此。1988年北京两家媒体《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相继发表报道,提 到大观楼初建时间为“1913年”。大观楼是传说中《定军山》放映的地方,但1913年建 成的大观楼如何在1905年放映《定军山》的呢?
《定军山》拷贝早已失传。这个失传意味着什么?是失落民间还是毁于大火?“失传” 的影片为什么会单独留下一张剧照?
我们知道拍摄《定军山》所使用的摄影机,是从“德国洋行买回来的法国货”,但从 来不知道这个法国货是什么牌子,有什么样的技术规格;我们知道《定军山》“有万人 空巷来观之势”,却不知道这部影片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放映的,当然也就更不知道是否 售票以及票价几何了。
大观楼和丰泰照相馆分别是什么时候建立、什么时候遭到火灾的?任庆泰和刘仲伦分别 是什么人物,他们究竟又是什么关系?影片究竟拍了些什么?又有谁看过影片?又是谁第 一个告诉世人,《定军山》是1905年所拍摄的,中国第一部电影……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开始了寻找中国电影“生日”的调查,希望能够梳理出电影史学 界多年来研究的成果,为一段模糊的历史增添一些明晰的证据。
“当时我拍《西洋镜》的时候没想到过几年就是中国电影100年,想到的话当时就该多 等几年”。《西洋镜》的导演胡安正在考虑重新出版音像制品,让“发行公司也能在纪 念中国电影百年上有些提议”。
“《西洋镜》是第一次讲述中国人最早的电影拍摄的影片,没想到这段历史一直没有 后续的新作。”谈起自己的处女作,胡安有些得意。
虽然,在以“中国电影100年”的名义,从媒体到职业导演都纷纷来赶“续新作”的热 潮,甚至连“重现《定军山》”的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胡安和《西洋镜》“第 一次”的位置仍然坐得牢牢的。可能她惟一的麻烦就是《西洋镜》的编剧之一黄丹。
“你去看我的《定军山》剧本,我从来没敢写‘谭小凌’(《西洋镜》中京剧名角‘谭 林培’的养女),更没有安排她跟人私奔,我对谭老先生还是很敬佩的,也是有禁忌的 。这都是胡安自己改的。”黄丹说。黄丹当初写成的剧本,名字是《定军山》,胡安基 本上推翻了这个剧本,重新编写了故事,另取了片名,拍成《西洋镜》。
“不知道的人以为是我乱编,其实是胡安篡改了我的剧本,她非要从外国人的视角来 看待我们中国电影文明,那是一个殖民者的文化态度。”目前,黄丹正在搜集文章,连 同《定军山》的剧本,一起出成书,书名暂定《从<定军山>到<西洋镜>——电影文化的 一次历险》,作为北京电影学院今年被审核下来的第一个科研项目,定于今年11月底出 版,“也算是给中国电影百年的献礼”。
面对黄丹五年如一日的指责,胡安的反驳已经轻车熟路了:“我拍的是故事片不是纪 录片,而且现在这段历史也无从考证,在没有办法还原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虚构。黄丹 的剧本都是高大全的人物,你不能让影片中的小人物全都有雄心大志。”
胡安和黄丹在看法、剧本立场、艺术观点、署名几乎所有方面都有很大分歧,只在一 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有关《定军山》的历史资料太少了,几乎没有。
《定军山》有几个生日?
谁都没有见过那个电影,所以没有人能肯定那是影片的剧照。这张被广泛拿来当成中 国电影百年起源的图片,实际上也是一个不解之谜。
“几乎没有”的意思是:有,但是非常少。
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2月出版、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以下简称《发展 史》),是1949年后第一本电影史著作,也是“中国电影源于1905年的《定军山》”论 断的源头。
《发展史》主编程季华表示:“后面的人关于《定军山》的说法,都是根据《发展史 》来的。”
40多年来,电影史学界一直在对这个“源头”进行补充和修正。
《发展史》在插页上提供了一张“谭鑫培《定军山》剧照(1905年由北京丰泰照相馆拍 成戏曲片片断)”,这张照片也与文字一样,被之后大大小小讲述中国电影历史的书籍 所引用。
《定军山》的胶片早已丢失,最流行的说法是在大火中被烧毁。丰泰照相馆和大观楼 都着过火,《定军山》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被烧的,这依旧是个谜团。胶片烧 毁了,为什么有“剧照”流传下来,又是谁第一个告诉人们,这就是《定军山》的剧照 ?
“照片是从戏曲研究所拿的。”《发展史》编写者李少白告诉记者。
“我亲口问过程季华,他说那个是戏装照,没错。当时我还说,‘是戏装照就不能够 说是剧照,你把那说成是剧照,大家都以为那是真的。’他也没吭声。”中国电影艺术 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博士生导师郦素元则十分肯定地告诉记者。
至于电影史“剧照”的来源,程季华说谁找到的不记得了,但“肯定是从丰泰照相馆 拿来的”,因为无论是剧照还是戏装照,谭鑫培的照片“不可能从其他的地方拿来”。
“剧照和戏装照是可以划等号的。拍《定军山》的时候,他穿着戏装,他也可以是拍 的戏装照,也可以是电影剧照,现在我们的电影剧照也有用照相机拍的,这是一样的。 ”当年负责管理电影史1000多张原始照片的程季华试图淡化剧照和戏装照的差别。
现任央视电影频道节目部主任的陆红实在新书《中国电影史1905—1949》中,使用了 谭鑫培另外一张《定军山》“造型图片”,照片从谭鑫培的服装、造型,以及画画的构 图,没有任何差别,惟一不同的是,这张照片是从谭鑫培左侧拍的。
“我当时一看,啊!《定军山》!我问他们是不是《定军山》?他们说是。这是第二张《 定军山》。之前从来没有人拿出第二张《定军山》照片!”陆红实的经历也发生在中国 戏剧研究院戏曲研究所里,当时他到那里翻拍资料。翻拍过程之中,他“在角落的垃圾 筐里无意发现了这张照片”,相片上面还有水渍,看上去也是翻拍的,“不然我也拿不 出来了”。
“我个人感觉照片不会是在拍电影的过程当中别人给拍下来的。”陆红实一直希望从 《定军山》两张“剧照”的本身画面里找到更多线索,“电影肯定不是在照相馆里面拍 的,需要日光,但如果是日光的话,室外不会那么干净,你看他的背景,他的头上他的 脚下就不会那么干净”。
陆红实在《定军山》考源方面更大的成果是对影片拍摄时间的考证。“我觉得《定军 山》应该是春夏之交拍的,而不是《发展史》所说的秋天。”陆红实说。就职电影频道 之前,陆红实一直在进行《中国电影艺术史》的编纂工作,他所负责的部分就是1905年 至1949年之间中国电影的研究。“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执笔者许姬传回忆说,《 定军山》的拍摄‘大约是一个秋季’”,但《发展史》中提到,“谭鑫培参加拍摄影片 这一年,正是他的六十诞辰”,谭鑫培的生日是农历三月初九,也就是春末夏初的时间 ,“许姬传是根据其友吴镇修亲睹此片来记述的,很可能是目击者记忆中春末夏初的季 节特点跟秋天十分相似的原因”。
“我一直不敢提庆祝谭鑫培60大寿,谭鑫培是出生在1847年,1905年的时候他应该是5 8岁,为什么会在58岁的时候拍一部纪念自己60大寿的电影?”参加过《北京市电影发行 放映单位史》编写的吴凡,跟记者说了心中一直以来的疑问。“旧时老人过生日往往逢 九过十”,所以会把过59岁当作过60岁,但58岁又作何解释?
目前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展品征集办公室工作的王大正认为:“以前人们都是算虚岁, 上半年生的人虚一岁,下半年生的人虚两岁,谭鑫培是上半年生的,虚一岁,1905年可 以算是他虚岁59岁。”所以在1905年庆祝谭鑫培“60大寿”,“也能说得过去”。
“有两个人,他们可能不能够推算出1905年,但是他们能够印证影片在1905年拍摄。 一个是王越先生,一个是邢祖文先生。但这两个人都过世了。”陆红实对此颇为遗憾。
王越是《发展史》的工作人员,邢祖文是《发展史》三位编著者之一。《发展史》中 关于《定军山》的章节,由王越搜集资料,邢祖文执笔撰写。
1988年,王越在《影视文化》第1辑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电影的摇篮——北京丰 泰照相馆拍摄电影访问追记》(以下简称《追记》)。《追记》回忆了他在1959年采访当 时丰泰照相馆摄影师刘仲伦的“堂族弟弟”刘仲明的内容,这实际上是现存惟一支撑“ 《定军山》摄于1905年”论点的史料。
1934年,谷剑尘为《中国电影年鉴》所写的《中国电影发达史》中,对“自摄影片的 发端与起续”的讲述,开篇便是从“中国第一个摄制影片的公司”开始讲起,并未提及 《定军山》。1949年前,中国电影的史学研究著作包括《中国电影发达史》和郑君里《 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这两本著作中都以1913年的《难夫难妻》为中国电影的开端。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颇有影响的电影编导程步高曾在1983年出版的《影坛忆旧》中谈到 《定军山》:“一九零六年,即电影到中国后七年,有个法国人到北京拍风景片……人 地生疏,邀和平门外琉璃厂里那里一家叫丰泰照相馆帮忙……到一九零八年,仍由该馆 出面接洽,商得当时北京著名京剧名角小叫天(谭鑫培)的同意,及戏院的协助,在一块 空地上,搭露天棚,棚内置舞台布景,利用日光(当时本无灯光),与普通拍照相同,拍 摄谭鑫培的《定军山》。当然是无声片,故唱功场面均删,只抽《请缨》、《舞刀》、 《交锋》等几个舞蹈武功动作场面,拍成电影。这是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亦是中国 最早的一部京戏纪录片。谭鑫培乃成为中国第一位献身银幕的艺人。”这段文字,起码 有两个跟《发展史》截然不同地方:《定军山》的拍摄时间为1907年,拍摄者是法国人 ,而非刘仲伦和丰泰照相馆。
1938年12月出版的《电影周刊》上,《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一文专门讲述《 定军山》,后来包括《发展史》在内,对《定军山》上映时“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的 描写,应该都出自这里。不过这篇文章并没有署名,在讲述《定军山》的开头,也使用 了“某剧作家言”,表示内容也是听来的。
程季华本人在主编《发展史》之前,于1956年10月28日出版的《中国电影》杂志上, 发表《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所提到的《定军山》拍摄时间为“一九零八年”。
“中国电影第一厅”
粘好之后的碑文拓样,是“大观楼电影院开业于公元一九零三年”——2004年12月前 ,同样的位置,写着“大观楼电影院开业于公元一九一三年”
1988年,北京两份报纸相继发表报道,提到大观楼初建时间为“1913年”。这个说法 在媒体流传很广,很自然就带出了一个问题:建立于1913年的大观楼怎么可能在1905年 放映《定军山》?
“这不是很严谨的做法。”大观楼电影院现任经理王占友这样说。他口中的“不严谨 ”,指的是把大观楼诞生定在1913年。
1988年,《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发表大观楼1976年失火、1988年重开的文章 ,是大观楼提供的资料,将“初建于1913年”写进文章。大观楼提供的资料是一扇名为 《重建大观楼记》的碑文。碑文由建筑师萧启益撰文,刘炳森书写,在1987年10月刻下 。
“无论是你还是我还是建筑师,他都不是历史上考证得那么具体,那么深,也不是随 便哪一个人来说1913年建了,就是把它当作是1913年诞生。”
“我们有一种文字性的史证在那里,这么多年,都确定《定军山》是1905年在大观楼 放的没有问题。谁能提出来1905年不是在这里放的吗?在那个论证会上,谁也提不出来 中国的第一部电影是另外一部,是在别的地方放的。提不出来也就反证了是1905年在大 观楼放的。”
王占友所说的“文字性的史证”,是1963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以及《北京电 影业史迹》和《北京市电影发行放映单位史》。
《北京电影业史迹》是在1907年这个时间段中提到“大观楼”的,“一九零七年开始 ……随后,前门大栅栏的大亨轩后改名为大观楼,电影每晚上座常满。但所放影片尺寸 甚短,除滑稽片外,仅有戏法与外洋风景”;《北京市电影发行放映单位史》对大观楼 的描写是“最早的大观楼影院名字叫马思远茶楼,1905年改称大观楼,是南城最早的放 映电影场所之一、1907年12月改为大观楼影戏园。”那么大观楼究竟是1905年还是1907 年改叫“大观楼”的?大观楼的前身究竟是“马思远茶楼”还是“大亨轩”?
记者在国家图书馆查阅过《顺天时报》,该馆现存的最早一份是1905年3月5日的报纸 ,一直查到1909年12月31日,没有任何讲述大观楼的前身是马思远茶楼或是大亨轩茶楼 的报道。记者查到1908年4月15日出版的《顺天时报》上,有一篇《记大观楼改良文明 新茶社》的文章:“自从首善第一楼失火后,喝茶的人都到了宾宴楼上去。大观楼经理 人,因此触动商业竞争的思想,在原有小蓬莱茶社大加改良。”大观楼前身的竞争者行 列中增添了“小蓬莱茶社”的身影。
“大观楼其实从1902年就开业了,直到1912年一直开业,很多资料说大观楼是1909年 烧的,都是错的,是1908年烧的,这是白纸黑字。”为年底开馆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做资 料搜集的王大正言之凿凿地告诉记者,他通过从故宫、北京档案馆等处搜集到的资料中 ,发现了大观楼真正的起止日期,包括失火记录。
王大正和电影博物馆负责人朱天纬决定在年底电影博物馆成立的时候首发这些资料。 如果这个1902年能拿出确凿的证据,那将是首次对大观楼进行的肯定描述。
学术界关于大观楼成立、失火时间的考证还没有取得共识,精明的商家已经充分利用 上时间的模糊。
大观楼影院位于前门外大街斜街深处,前门外大街有不下十处类似的斜街,而且这里 有近70余家百年老字号,但指路的人们还是能用简洁而肯定的言语,让你能在最短的时 间里达到。今天的大观楼影院,虽然门口依然跟“美容美发”脱不了干系,但是已经没 有了十年之前“大观市场俄罗斯商品专柜”的景象。
今年之前,大观楼是“新影联”属下的二线影院,类似《终结者3》这类大片只有在首 映10天之后才会到这里放映。大观楼的转机是获得“中国电影诞生地”的称号。
“你看这个‘零’,是不是要比其他的字颜色浅啊?你再仔细看看,这个‘零’是不是 圆的啊?”大观楼的一个工作人员将记者带到影院会议室,指着墙上一个拓下来的碑文 说:“这是复印之后粘上去的,用的就是后面碑文里那个‘一九六零改进成北京’的‘ 零’。”他凑到装裱碑文的玻璃前又看了看,说:“粘得还挺好的,幸亏下面那个是‘ 一’,笔画简单,粘上去不太看得出来。”
粘好之后的碑文拓样,正是“大观楼电影院开业于公元一九零三年”——就在2004年1 2月之前,同样的位置,写着“大观楼电影院开业于公元一九一三年”。
大观楼已经前后换了12任经理,2004年12月,王占友的上任,可以被看成利用中国电 影百年的契机,将大观楼影院扭亏为盈。他为了让大观楼成为“中国电影诞生地”,在 “中国电影专家论证会”上“据理力争”,虽然一部分专家认为丰泰照相馆是可知的《 定军山》诞生的地方,但专家会最后还是“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诞生地在大观 楼”。
大观楼被确认为“中国电影诞生地”后,的确显出了扭亏为盈的架势。
“牌匾立起来,到时我们就叫中国电影诞生地了。”王占友对大观楼的前景充满信心 和设想,到时候大观楼要“立一个中国电影诞生地的纪念碑”,“搞一个诞生地地标” ,“树一座中国电影第一人任景丰的塑像”。
虽然这个任景丰的塑像“估计不便宜”,但“中国城市影院发展协会将给塑像进行捐 资工作”。改造大观楼包括修建3个影厅,费用可能也“不在几百万之下”,王占友表 示,北京市政府、宣武区政府都把这当成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在做,“配合‘中国电影诞 生地’的牌匾揭匾,我们也搞一系列的活动,包括中国电影周、电影论坛等等,都在大 观楼这里办,所以要对大观楼进行一些改造。”
大观楼将在南面开一个大门,任庆泰的塑像就会被放在大门前的小广场上,改造之后 原来单厅影院的大观楼将多建3个电影小厅,“一个是数字的;一个我们管它叫‘中国 电影第一厅’;还有一个我们管它叫VIP豪华厅。我们想把大厅改造成搞庆祝会议的场 所。”王占友经理对于未来的规划成竹在胸。
目前,据说还在准备拍摄阶段的《定军山》,已经计划在大观楼首映。
“惊人的记忆力”
王越在1959年对刘仲明进行访问,将近30年后,他在几乎没有任何文字材料的情况下 ,完全凭记忆写出了7页的回忆文章……
围绕《定军山》的所有考证都无法绕开一个人——王越。
陆红实在《任庆泰与首批国产片考评》一文中,有不下五处引述了王越在1988年所写 的《追记》。他在介绍这篇《追记》的创作经过时,使用了这样的说法:“以他惊人的 记忆力”。这个“惊人的记忆力”的含义是:王越在1959年对刘仲明进行访问,将近30 年后,他在几乎没有任何文字材料的情况下,完全凭记忆写出了7页的回忆文章。
这篇“凭惊人记忆力”记录下来的追记中,王越提到了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著名 北京掌故专家张慈溪”,“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他写的关于早期北京拍电影的文章,邀他 来详谈的”,通过他的介绍,王越找到了当时住在牛街、年近七旬的刘仲明。这个刘仲 明“说他十三四岁便在丰泰照相馆当小伙计。他们哥儿仨都在丰泰,两个堂族兄刘仲昆 和刘仲伦在馆里学照相技术,刘仲明当时年纪太小,就当店里的小跑。丰泰创办人任景 丰见他机灵,就拿他当了亲信,一些重要的事,常常让他去办。”
曾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的首任理事的孙建三给记 者打来了电话“我说1937年卢沟桥上我拿大刀砍死了100多个日本鬼子,讲得详细极了 、精彩极了,你只要问我把身份证给你看看,看看是哪一年生的,就知道那时候没我。 不管我讲得多么精彩多么多么丰富,那时候没我啊!”孙建三对《追记》中刘仲明提到 的1905年电影机器和胶片提出了质疑。
孙建三告诉记者,当年撰写《中国电影发达史》的谷剑尘曾经因为听说谭鑫培拍了《 定军山》,给蔡元培去了一封信,希望通过他在北大当这校长的关系“让北大的学者查 一查谭鑫培拍电影这个事”,“北大的学者核查完了以后,就给蔡先生回了一封信,我 父亲拿相机拍了这封信,有这个照片!说没这档子事。”后来谷剑尘不死心,觉得好多 人都说过这个事情,不可能全部是空穴来风吧。于是又找到北京师范大学的代校长,委 托北师大的学者来核查此事,“结果信回了,也是没这档子事,我爸爸也拍了照片,所 以我见过”。而孙健三现在无法拿出信件的翻拍照片,原因与王越当年收集的资料遗失 的原因相同——“‘文化大革命’被拿走了”。
“现在照片被人拿走了,我也不能口说无凭,但是王越的这篇文章,我能指出很多技 术上的错误。”
对王越这篇带有随笔性质的追记,孙建三从技术上指出其中的“失实”之处:1905年 的电影机不可能是“大木箱”;胶片不可能有100英尺的胶片;胶片的保质期很短,必 须提前订货,不可能随到随买;忘记摇动摄影机,不可能导致胶片报废。
“1905年最长的胶片是50尺,比如说你看到的最早的电影《火车进站》、《水浇园丁 》、《工厂大门》,都是55秒不到一分钟的片子”,“50尺的胶片卷起来也就这么一卷 ,放在电影机里面就很小,再加上一个镜头、一个抓片器、一个压片机构、一个输片机 构,所以它的体积就可能这么大”。
孙建三的“这么大”,是相比当时的照相机大小而言的,“他是在照相馆工作的人, 如果他买了一个比照相机大的东西他可以说大木箱,他买了一个比照相机小得多的东西 ,那个东西多大呢?30多公分高,20多公分宽,不到20公分厚,你说这么个东西,他怎 么能够认为是一个大木箱呢?”
就此,记者向北京电影学院李念芦求证。她表示有关于摄影机尺寸的问题,最好到美 国和法国的摄影网站看图片实例,或者看一下当年的《西洋镜》。《西洋镜》导演胡安 对于自己让“刘京伦”使用的一个尺度较大的摄影机,表示只是想“摄影机大一些,更 有利于在画面上的表达”,“并非还原当时的摄影机原貌”。
孙建三对于胶片的疑问还产生在刘仲明对胶片的购买上,“胶片上面的感光层是化学 的东西,这个东西有两大特点,从做成那一秒钟开始它的感兴度就在下降,挥发度就在 增加。所以老胶卷拍的照片都是灰蒙蒙的。当时胶片的有效期是三个月,所以从买胶片 的时候,如果看到这个胶片已经从出厂日期过了两个月了,我就绝对不会买,一定要用 刚出厂的胶片。那时国外的摄影师是怎么做的呢?他会根据自己的拍摄计划,我这个月 需要多少胶片,下个月需要多少胶片。比方说那个法国人1906年来的到1908年拍完走了 ,这两年当中,你每个月给我发一次货。如果说我把两年的胶片都带去,那么这些胶片 肯定都不能用了。”孙建三质疑的是,刘仲明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那么轻松买到 胶片,而且之后“刘仲伦只顾看戏,忘了摇机,报废了2卷片子”,任景丰又赶紧让刘 仲明到祈罗孚洋行,一下子又买到了10卷胶片。
“忘了摇机,为什么会报废片子呢?你没按快门,也没打开后盖,停在那里怎么可能把 胶片给报废了呢?”
李念芦确认,“机器不动胶片就不会曝光”。
“不管孙建三说的有没有道理,从电影史研究的角度,我觉得应该提出质疑。当然我 不是否定,因为我也没有否定的依据,但是我只能说把它成为一段历史材料远远不够, 就是没有充分的材料和证据来证明这段历史是真实的。”郦素元说。他认为,这段历史 是根据王越的采访而来的,店是任景丰的,拍的是刘仲伦,被拍的是谭鑫培,王越采访 的却是刘仲明。刘仲明不是“当时真正的直接的当事者”,而且他是在回忆,1959年的 时候回忆1905年的事情,“那又是50多年前的事”。所以,对这段史料的质疑可以概括 为:刘仲明的叙述是不是准确?王越当时对刘仲明的叙述记录是不是准确?
“但这些只能是疑问,你不能说有疑问就能推翻它,只能是存疑。”陆红实一再强调 :没有任何证据推翻《定军山》的存在,也没有证据能推翻1905年拍了《定军山》,所 以“只能承认它,除非能证明它不存在”。
“即使证明了刘仲明的话不属实,或者王越的文章不属实,也没有办法证明《定军山 》不存在。”陈山和李少白、陆红实、朱天纬在这点上都持有相同观点。
《定军山》的“野史”
王越甚至提到了1959年下半年去大观楼电影院时,遇到3个看过电影《定军山》的老人 ,却对找到丰泰照相馆账本的事情,没有提到一个字……
关于中国电影的起源,“定军山说”是确认“正史”,但电影史学界的探讨一直没有 停止过。
谷剑尘和程步高都已过世,惟一可以请教资料来源的便是程季华:“1956年的时候我 们还没有把它弄清楚,这个1908年也是有根据的,为什么肯定是1905年呢?片子是1905 年拍的、放的,之后也在演,我们先看到后面的文章,再看到前面的文章,所以还是以 之后的文章为准。”
是什么材料让《定军山》从1908年又提前到了1905年呢?“主要是账簿,还有报纸。”
《发展史》编撰的时候,王越曾经找到过丰泰照相馆的账簿,这几乎是《发展史》出 版以来第一次听说的资料文献。据程季华介绍,这本账簿是从丰泰照相馆拿来的。程季 华那篇文章写于1956年,《发展史》出版于1963年,可以肯定,账本一定是在这期间得 到的。程季华可以肯定,王越和另外的工作人员到了丰泰照相馆,照相馆的人将旧账本 给他们看了。程季华最后悔的是“没有把账本要回来”,因此没有亲眼看到账本。工作 人员回来后就向程季华“汇报”过了,所以程季华脑子对此事有个印象。除了账本之外 ,程季华印象中另一个资料是在当年的旧报纸上查到的《定军山》的放映记录。
王越在《追记》中,甚至提到了1959年下半年去大观楼电影院时,遇到3个看过电影《 定军山》的老人,包括他们对影片的内容和画面的回忆,却对曾经找到过丰泰照相馆账 本的一事,只字未提。
作为《发展史》3位编撰者之一,李少白回想了很久,表示“根本就是头次听说,我完 全不记得还有账本”。
至于账本的下落,程季华回忆说,是在“丰泰照相馆失火烧毁的”,后来意识到价值 时已经晚了。
程季华还提到,当时的报纸对《定军山》的放映有所报道。记者在国家图书馆查阅了1 909年之前的《顺天时报》。虽然这份报纸创刊于1900年,但国家图书馆现存最早的《 顺天时报》开始于1905年3月5日,接下来保存的《顺天时报》就到了3月12日,谭鑫培 生日附近的这两份报纸上都没有关于《定军山》的任何消息。现存1905年的《顺天时报 》只有十余天,也没有任何关于《定军山》的报道,惟一跟电影有关的,就是放映电影 时,出现故障,炸伤了人。1906年的《顺天时报》也不齐全,直到1907年,才开始每天 都有。一路查下去,直到1908年1月3日,才看见第一个电影广告,即“大栅栏三庆园开 明电影,全球第一举国无双”,广告里不但有电影内容的渲染文字,还有四等票价和男 女分座,将戏票交还账房可以获得赠品等内容。这个广告一登就是一年多,其间并无其 他电影广告。
国家图书馆馆藏中没有1905年之前的中文报纸。上海《申报》1905年3月1日至6月11目 的报纸除了茶园戏曲广告,还有一则外国戏到上海放映的广告,跟《顺天时报》相比, 《申报》的戏曲文化部分要少得多。另外记者还翻阅了《华字汇报》,但也只从1905年 6月开始,其中缺损的地方很多。当然这份刊有“美人鱼消息”报道的早期八卦报纸, 也没有提供任何《定军山》的消息。
北京大学艺术学系研究中国电影史的李道新曾带研究生查过这个时段的上海《申报》 :“北京方面1905年前后关于这个的内容很少,即使《定军山》打出广告,《申报》上 也不可能查到广告。”
谁还在研究电影史?
1999年我离开艺术研究院的时候,每个月所有的钱加起来只有500元。当时猪肉的价格 是每斤6.5元左右。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李少白组织陆红实、王越等5人编撰《中国电影艺术史》。“ 当时国家给了5万元的研究经赞,光买资料就花了3万多元。”当时,编撰者的工资在10 0元钱左右,只能靠稿费养家,“你如果完全把精力都放在制史上,你每个月工资就是1 00多元,其他一分钱都没有。你要养家,就必须写点别的东西,大概也能挣到100多元 的样子。”
这本书第一卷出来的时候,因为有些说法和《中国电影发展史》不一样,所以“在当 时电影界是很轰动的”,《定军山》是春夏之交拍的还是秋天拍的,就是在当时研究中 提出的。但由于待遇等问题,这本书做完第一卷之后再也做不下去了。
“1999年我离开艺术研究所的时候,每个月所有的钱加起来只有500元。当时猪肉的价 格是每斤6.5元左右。”陆红实最终选择了离开,6月份办的调转关系,7月份领到北京 电影学院第一个月的工资,那时已经是暑假了,工资条上写的是1500元,陆红实说当时 自己吓了一跳,“我说我真应该调出来”。
即使是在庆祝世界电影100周年、中国电影90周年之后,研究电影也并不会被认为是多 么重要的事情。目前在帮中国电影博物馆做资料搜集工作的王大正告诉记者,1999年金 鸡百花电影节在沈阳举行,沈阳市文化局希望把电影第一人任庆泰介绍一下,并设立电 影纪念日。“中国电影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电影日。我接受的任务就是调查‘第一人’ 。领导给我一周的时间,让我到北京和天津两个地方调查。我是白手起家,5天让我到 两个地方调查。星期天我到了天津,抢了一天,找到天津文化局,还有我在天津的老同 学老朋友,整个溜达跑了一天,跑了5个地方。星期二早上4点的火车跑到北京来,星期 三和朱天纬见了面,然后就回去了。调查的时间有限,我只能把人们前期调查的成果东 抄一点西抄一点。回到沈阳之后才开始真正做调查。当时没有时间,实际上是在心疼调 查费,说不用那么认真调查。”后来因为这段经历,王大正被当成了这方面研究的专家 。“其实就那么一点时间,我能知道什么?后来有人找我谈谈,我也谈了、写了、说了 ,但现在跟你讲,那全是错的。”
目前,王大正跟中国电影资料馆签订了3个月的合同,专门负责资料搜集,特别是《定 军山》前前后后的调查。今年12月,官方将对中国电影诞生百年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包 括建立中国电影博物馆、确定电影诞生地、发行电影百年纪念邮票……“故宫、档案馆 ,还有沈阳、天津,我们都在陆续查,只能一点点把任庆泰、丰泰照相馆、《定军山》 的东西拼起来”,现在朱天纬还在一点点搜集资料,“反正建电影博物馆是绰绰有余了 ,我想的是把《定军山》这个事情搞得更清楚一些”。
《定军山》正史
《中国电影发展史》对“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描述包括:丰泰照相馆和任 庆泰的生平简介、谭鑫培拍摄《定军山》的情况,以及此后紧接着拍摄的戏曲电影。
“中国人尝试拍摄影片,是在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的秋天,由开设在北京琉璃厂 土地祠(即今南新华街小学原址)的丰泰照相馆摄制的……《定军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 戏曲片,也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我国第一次尝试摄制电影”。
《发展史》这段“北京丰泰照相馆与谭鑫培等的戏曲纪录短片”中介绍,任庆泰开设 的丰泰照相馆“是当时绝无仅有的第一家”,同时他还经营了“好几家药房、中药铺、 桌椅店和汽水厂”;任庆泰拍片的原因是“感于当时在中国放映的都是外国影片,而且 片源缺乏,于是产生了摄制中国影片的念头”;拍摄的器材是在德国洋行祈罗孚买到“ 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一架及胶片十四卷”;拍摄是由丰泰照相馆最熟练的摄影师 刘仲伦掌机;拍摄地点在丰泰照相馆“中院的露天广场上”,“前后拍摄了三天,共成 影片三本”;之所以参加拍摄的是谭鑫培而不是其他梨园泰斗,是因为“谭鑫培参加拍 摄影片这一年,正是他的六十诞辰”;影片拍完后,对放映情况的相关说明是:“先后 都在北京大栅栏的大观楼影戏园和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放映过,‘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 ’,可见观众对我国自制影片的热烈欢迎。除北京外,这些影片还曾运往江苏、福建等 地放过。”
他掌握着《定军山》的孤证
“王越的确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李少白说,“《发展史》就是根据王越采访记 录的稿子压缩,由邢祖文执笔写的。”李少白概括了王越当时工作的性质。程季华也能 映证这点:“王越那时在电影家协会,是电影史研究工作人员之一。派他出去写研究调 查报告回来,后来文章就是根据当年的调查追忆的。”
“20多岁的小伙子,每晚都睡不着觉,一度患上了严重神经官能症,到了不能思考的 程度,”王越的儿子王旭说,“我父亲为了电影史,牺牲了青春、健康、家庭幸福,甚 至走向了人生厄运。”但翻看《发展史》,只有“主编程季华,编著程季华、李少白、 邢祖文”的名字,并没有一处提到王越。
李少白和陆红实都跟王越共事过,他们共同的评价也是“这个人身世十分坎坷”。王 越是2003年去世的。
王越是电影编剧艺术研究班第一期学员,“同时期很多人不是名导演就是名编剧”, 但王越因为工作需要,从1958年开始在中国电影家协会工作,参加编写《发展史》。“ 那是解放后第一次系统地整理电影资料,那时候很多电影拷贝上面都贴着封条放在仓库 里。我爸爸经常把自己关在昏暗的房子里,用小型放映机看拷贝,从中选取有价值的画 面翻拍,再到暗房冲洗。”
“我爸爸工作有多忙,我跟你说,那时他跟我母亲在谈恋爱,母亲在外地复习高考, 好不容易来北京看他,他让母亲到北海公园先等他,自己忙着在北京图书馆查资料,一 天都没有出来。”
由于整日看不到阳光,拷贝里面含有挥发性物质,对身体有很大损害,加上王越工作 过于投入,以至于病倒了,最后在小汤山康复了2个月才又回来参加电影史编写的。现 在没有人能记得王越是在生病之前采访的刘仲明还是生病之后,主编程季华回忆说:“ 王越作为工作人员之一,我派他去调查过丰泰照相馆,也不能说只有他一个,但这个任 务我现在回想起来是让他去调查的。”
在王越的平反决定上,明确写到他1958年到1962年参加编写《发展史》,但《发展史 》上没有一处提到王越的名字。如果不是他写了篇追记,如果陆红实没有在多篇文章中 引述了王越的《追记》,恐怕没有会知道他的存在。
“他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参加完电影史的编写就退出了”,程季华这样解释,“王越 有没有参加编写,现在也必须查档案才知道。”
“不但没有名字,据说《发展史》的稿费发了8000多元,那个时候是一笔巨款啊。程 季华拿了4000元,李少白和刑祖文各拿2000元,我爸爸一分钱没有。后来李少白和刑祖 文为我爸爸抱不平,还说从自己拿的稿费里分一部分给他,我爸爸没要。本来说在发展 史后面加上‘全书资料搜集:王越’,最终也没有加上。”王旭的说法得到了李少白的 印证。
王越是在2003年10月去世的,在去世之前,他接受了李少白的邀请,参加《中国电影 艺术发展史》编写,那篇对丰泰照相馆的《追记》,也是李少白和陆红实力劝他写出来 作为今后论证这段历史资料才写成的。
刘仲明回忆的《定军山》
为了这件事,我们任老板可没少动脑筋,记得有一次他曾问过仲昆、仲伦,还有一个 姓孙的照相技师,问他们对当时演的那些洋影片看得懂吗?他们都说看不懂,并说看来 看去就是亲嘴、踢屁股那点玩意。任老板又说,咱们自个儿弄点新戏怎么样?那个姓孙 的技师说,那洋玩意,咱们怕不会弄。任老板说,别让洋东西唬住,没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活动照相吗!那时,在东交民巷,有个德国商人,开了个祈罗孚洋行,专卖照相 器材,任老板天天派我去跑。先在那里买来了一个大木箱,我们都管它叫“活动木箱” ,前面有个照相机镜头,还有个手摇把,一摇里面还‘吱嘎吱嘎’的响,别看这么个玩 意,竟是个法国货,底下还带四根腿,像个板凳,把那木箱放在腿上,再安装上胶卷, 就可用了。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也就是谭老板大寿整六十的那年,上半年的一 天,任老板让我赶紧去祈罗孚洋行买四卷胶卷,好给谭鑫培老板拍电影。
就是在这个中院里,廊子下借着两根大红圆柱,挂上一块白色布幔。屋内成了谭老板 临时起居的地方,他的跟包、琴师都来了。屋内院子里,把那架号称“活动箱子”的摄 影机,摆在了靠前院后墙边。由照相技师刘仲伦担任拍照,他是“丰泰”最好的照相技 师了。虽然前几天练过几回,但真的上阵,仍显得有些紧张。一通锣鼓过后,布幔后闪 出一个戴髯口、持大刀的古代武将来,这就是谭鑫培最拿手的《定军山》里的老黄忠, 只见他配合着锣鼓点儿,一甩髯口,把刀一横,立成……就听见旁边有人喊:‘快摇’,刘仲伦便使劲摇了起来,那时的胶片只有200尺一卷,很快就摇完了,算告一个段落。然后便是吃茶,卸装。而刘仲伦却摇出了一身大汗,大家忙着给他拧毛巾。第二天,仍在原地,拍黄忠舞刀,那真精彩极了,之间刀光闪闪,把人都看呆了;刘仲伦也只顾看戏,忘了摇机,结果报废了两卷片子。任景丰一听急了,就叫刘仲明赶快到祈罗孚洋行,一下子买了十卷胶片,以防万一。那时拍影戏,受限制很大,因是利用太阳光拍的,一早一晚,刮风下雨都不能拍。所以每天只能拍很短一段时间;就这样断断续续拍了三天,拍下了《定军山》里的“请缨”、“舞刀”、“交锋”等三个场面。刘仲明谈得有些兴奋。稍稍休息后,我又问他,剩下的胶片呢?他说,全都拍戏用了。
——摘自《中国电影的摇篮——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电影访问追记》(王越,原文发表 于1988年《影视文化》第一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