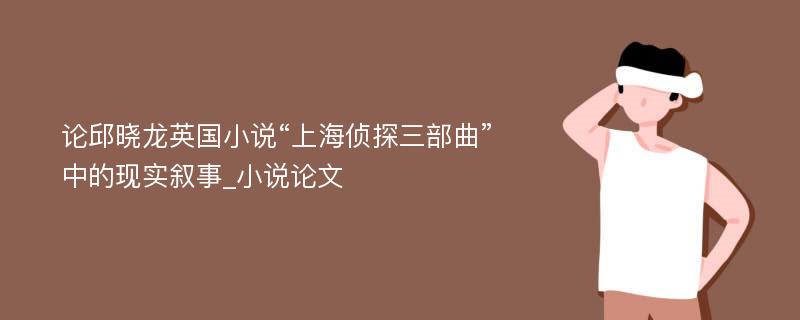
评裘小龙英语小说“上海侦探三部曲”里的现实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语论文,小龙论文,上海论文,侦探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后期的美国文坛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族裔文学得到空前发展,其中华裔文学更是群星璀璨。自1976年汤亭亭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1975)获得国家图书批评家奖,以及1981年《中国佬》(China Men,1980)获得国家图书奖及普利策图书奖第二名后,黄哲龙、谭恩美、伍惠明、任碧莲、雷祖威、李健孙连连登台,老一辈作家赵建秀、徐忠雄、陈耀光也新作不断,美国华裔文学在连续20多年的时间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既而,到21世纪之交,美国文坛上的华裔写作又涌现出另一股新生力量。1999年,大陆留学生作家哈金的小说《等待》(Waiting,2000)一举获得国家图书小说奖;2000年,大陆留学生作家裘小龙的首部英文小说《红英之死》(Death of a Red Heroine,2000)先后入围爱伦·坡推理小说奖和白芮推理小说奖,而后获得安托尼小说奖,即第32届世界推理小说奖,并很快被翻译成七种语言出版。自此,美国华裔文学的版图发生了变化,以大陆留学生构成的新的华裔英语写作群开始崛起。这批作家具备中文、英文两种语言文化背景,他们了解中国,了解世界,并对自己写作的美学格调保持清醒的意识。因此,他们的写作起点不仅超越了先前大陆留学生的“海外文革伤痕文学”,而且也超越了美国本土华裔写作主流的“族裔主题文学”。然而,近几年在海外影响较大的这些大陆留学生作家及作品在国内学界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有关哈金的研究论文已有不少(多数论文作者系海外学者),但相比较起来国内对裘小龙作品的研究几乎仍是空白。①本文拟以裘小龙的三部小说——《红英之死》、《外滩花园》(A Loyal Character Dancer,2002)和《石库门骊歌》(When Red Is Black,2004)为分析文本,②讨论小说中记忆与现实的关系,说明小说的现实叙事蕴涵着对于历史和记忆的揭示与反思这一主旨。
裘小龙博士属于20世纪50年代出生、70年代经历文革、80年代读书的那一代人。他师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诗人学者卞之琳,在1988年赴美前,曾是中国作协成员,其诗歌翻译和写作在国内已有一定影响。他在美国的英语创作开始于1989年,历经10年的磨炼,他的第一部小说《红英之死》于2000年获得世界推理小说年度最高奖。此后他以每两年诞生一部新作的速度不断引起西方英语读者的关注。③由于其小说的题材及类型的独特性,他的作品受众广泛、影响较大,仅其第一部小说《红英之死》,“销售至今,在美国、法国、德国都已经发行了五、六万本,在德国,精装版就印了5版。”④
裘小龙的上述三部小说均以改革开放后的上海为背景,小说的情节以谋杀、破案为主线。主人公陈超及其同事、亲友作为主要人物贯穿始终,构成了“诗人警长陈超”的小说系列。《红英之死》和《石库门骊歌》的谋杀案素材均取自发生在上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轰动一时的刑事案件。小说《红英之死》的故事时间是1990年,红极一时的上海第一百货大厦的女劳模关红英被人奸杀,抛尸远郊河底。侦破过程锁定的凶手是市宣传部长的儿子吴晓明,但在调查取证及定案的过程中,负责此案的公安局特警队队长陈超和他的伙伴于光明却遇到种种恐吓、利诱和阻挠。多亏了陈超前女友从中相助才打破僵局。然而,此案的判决结果却令人愕然——吴晓明未经公诉被匆匆处决,另一名涉案同伙也同时被判了死刑。⑤而在另一部作品《石库门骊歌》中,小说被害者是住在“石库门”(两层石材质小楼)亭子间的中年女作家尹骊歌。在“石库门”展开的调查涉及每家住户,退休工人万前胜投案自首,文学爱好者于光明的妻子佩青由尹骊歌的小说追查出尹在“文革”时的大学教授男友杨彬的英文书稿,从而牵出了真正的罪犯——杨彬的乡下外甥包国华。此案的事实真相是包国华为争版税而失手杀人。在裘小龙系列中,《石库门骊歌》的写作手法最为娴熟。小说故事情节紧凑,布局合理,人物描写较多,细节生动。这本小说的重心并非谋杀案本身,而是改革开放后上海的变迁及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小说《外滩花园》的故事情节似乎完全出自作者的想象。故事描写了中美警方联手打击偷渡的一次跨国行动,主人公陈超负责协助前来中国的美国女警官凯萨琳寻找引渡蛇头案件重要证人的妻子温丽萍,并在开庭前将她带去美国。这本书几乎汇聚了电影《007》的所有元素:美女、陷阱、追杀、枪战、破案线索的出人预料(小说中,陈超是从一本诗集里发现了温丽萍藏身何处的线索)。书中的两名女主角构成了两条叙述主线:凯萨琳在陈超的陪伴下遍游沪杭风景名胜,品尝中国美食,充分显示了中国文化的雅致情趣;温丽萍的经历则展现了一个原上海女知青不幸的人生遭遇。
事实上,裘小龙小说所显示的社会关注超越了一般概念的侦探小说,因此把他的小说定型为“侦探小说”似有屈就之嫌。在西方当代文学中,许多著名小说如《洛丽塔》(Lolita,1955)、《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1984)以及新近的《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2003)等,在类型划分上都很难用“侦探小说”或“犯罪小说”分辨清楚。美国书评界对裘小龙小说的类别也有不同看法,《亚裔书评》的编辑彼得·戈登(Peter Gordon)指出,裘小龙“不仅仅是在写犯罪小说,他的书也是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饮食的评介……”(Gordon);《洛基山新闻》的书评提到:“裘小龙书中对中国的见解为‘悬疑小说’带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文化路向,这正是他小说独特并值得阅读的地方”(The Rocky Mountain News)。这情形就像当年汤亭亭的《女勇士》出版时所遇到的情况一样。1976年,《女勇士》乍一问世,竟然连出版社都不知该如何分类,权作“自传”。多年之后,这部打破类型界限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开始被出版商认可之后,才被出版界和评论家们称作“小说”,尽管仍带有一个“自传体”的修饰语。
无论怎样衡量,裘小龙小说的写作格调、思想范围与通常概念上的侦探小说不同。首先,小说主人公陈超这个人物精通中英两种语言,对西方当代诗歌的研究颇有心得,在小说里成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导引者。主人公与作者本人有相似经历——经历过文革、学外语出身、从事译诗、尝试写诗……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将陈超这个充满矛盾、性格复杂的人物写得生动饱满:他既能破案、吟诗;也能在官场和社交圈中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但同时不忘“父训”——儒家的道德信仰。“陈超”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小说的叙述主体具有一般侦探小说难以企及的文化内涵与自省意识。
其次,裘小龙的小说蕴涵了大量的中国文化信息。在此之前,虽有不少海外发表的华人英语小说涉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但尚未有人直接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状作为主题写进小说。裘小龙的小说内容涉及各种空间地点,这其中包括:上海公安局、里弄居委会、餐馆、夜总会、北京图书馆、广州夜市、发廊、苏州园林、福建乡村……小说里描写的人物林林总总,包括公安干警、高干权贵、作家文人、商界新富、妓女、黑帮,以及众多各类普通人……
裘小龙的小说令人兴趣盎然、不忍释卷。他的小说除了情节巧妙和人物逼真之外,小说人物的所思所虑也与我们身处的现实十分接近。“陈超”在小说中有不少若隐若现的自省式诘问,⑥如:“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许多问题我无法解答,……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Qiu Xiaolong 2002:223),这何尝不是现实生活中同样困扰我们自己的问题?经济改革使中国发生了巨变,但市场经济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如两极分化、“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等。怎样认识和正确阐释我们所处的社会现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
裘小龙的小说在描写复杂多样的当代中国社会图景时,以一种清晰可辨的叙事,展示了作者对于现实的一种多向度认知。这对我们不无启示。
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在论证历史是虚构与阐释的结果这一观点时说道:“人们过去区别虚构与历史的做法是把虚构看成是想象力的表述,把历史当作事实的表述。但是这种看法必须得到改变,我们只能把事实与想象相对立或者观察二者的相似性才能了解事实”(海登·怀特177)。在怀特看来,只有当事实与想象构成叙事时,我们才能把握事实。按照佛家的说法,现实世界不过是幻象的投射,因此现实本身不可能具备自我阐释的功能。所谓“三世因缘”实为佛家阐释事物的历史辩证法门,一物一人,前因后果而已。有趣的是,在裘小龙的小说世界里,现实与历史、现实与记忆是相通和互动的。作者使用相互折射的视角手法,描述现实中的景观和人物,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反思式叙事。
在弗雷得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后现代主义的阐述中,建筑作为具有完成多国资本主义“新世界空间里的政治艺术的使命”的功用而被大量引证。(弗雷得里克·詹姆逊99-134)在詹姆逊那里,后现代主义的建筑体现了去意识形态和去乌托邦的“美学上的民众主义”,直接参与了后现代主义的叙事。(152-212)在裘小龙的小说里,中国建筑、中国美食、中国诗歌等作为构建小说心理文化空间的要素,都参与了小说的“现实”叙事。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讨论裘小龙小说的中国诗歌部分。
裘小龙小说语言的汉语使用堪称奇观。裘小龙的小说大量运用当代中国“活的语言”。在他的小说里,中国人口头上的惯用语和流行语比比皆是。例如,“向钱看”(Qiu Xiaolong 2000:317);“第三者”(285);“十年河东,十年河西”(191);“热脸碰到冷屁股”(85);“说你胖,你就喘”(Qiu Xiaolong 2002:78);“夹着尾巴做人”(200);“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171);“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139);“僧多粥少”(323);“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Qiu Xiaolong 2004:16)等等,不胜枚举。美国纽约圣·约翰大学当代中国学教授杰弗里·肯克雷(Jeffrey C.Kinkley,1948-)在一次访谈中说,“西方读者和批评家对于哈金和裘小龙小说中英语的喜爱程度,是任何从中文翻译过来的英译作品所无法比拟的。然而,他们小说里的语言形象几乎直接出自中国普通话口语。这倒颇为奇怪”(Kinkley)。
裘小龙的小说除了大量使用中国当代的“活语言”,还引用了不少中国诗歌。事实上,这两点也正是裘小龙小说的语言特色所在,其中尤以诗歌的引用受人瞩目。在裘小龙的三部系列小说中,作者常常借主人公陈超的诗人身份引用中国古典诗歌名句。小说先后引用了十多位中国古代诗人词人——李白、李煜、李商隐、王维、杜甫、苏东坡、柳永、陆游、李清照等以及现代诗人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诗句。此外,小说中以陈超和杨彬的名义创作的诗歌(即作者本人的创作)也频频出现。
裘小龙小说里引用的中国诗歌不仅有助于主人公陈超的人物塑造;更加重要的是,中国诗歌的美学意境给小说里的当代中国增添了浓郁的文化与历史氛围。在小说中,诗歌的引用与故事情节之间有着有机的结合,作者往往借主人公陈超的触景生情使诗歌的语境和引申得到交代,并用借古论今的方式点明诗歌与小说人物的意义关联。
以下试就裘小龙小说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引用类型及意义关联举例说明:
1) 点睛式引用/中国哲理。例如,在《红英之死》一书的结尾,陈超成功办案后回家看望母亲,发现母亲对他从事警察职业的看法有所改变,开始理解和支持他的工作。陈超离家时踌躇满志,决心努力工作,他想起了小时候父亲教他的一首诗,诗里说,儿子对母亲的爱是永远报答不尽的,同样,一个人对国家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此,作者引出孟郊《游子吟》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Qiu Xiaolong 2000:464)作为全书的结束语。作者通过引用这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唐诗,突出了主人公陈超的精神追求,诠释了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中国人“内在自我”的塑造作用。
2) 介绍性引用/借古喻今。例如,陈超的女友王枫决定去日本定居,陈超夜不能寐,想起宋代词人柳永的词句:“今夜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紧跟着,作者借陈超的思绪,引出了一段柳永的生平介绍:“陈超和柳永的处境正好相反。在诗里,告别情人的是柳永,但眼下却是王枫要离开陈超。柳永是中国古典文学历史中受人尊敬的词人,但他一生贫困潦倒、饮酒作乐、耽于幻想,最好的年华都在烟花巷里消磨掉了。据说,正是他写的那些浪漫诗歌害苦了他。柳永被他同代的文人所鄙视。他们站在正统的立场,谴责他玷污了儒学的尊严。他临死前一文不名,只有一个喜欢他诗歌的穷妓女守在身旁。这个说法也可能是后人的编造。人们给装满苦味的杯子里加块糖,聊以慰藉而已”(348)。此处,作者借用柳永的《雨霖铃》描写陈超与女友分离时的感情痛苦。作者将柳永生平的叙述角度放在诗人为情和爱耗尽生命,却最终落得孤家寡人这一点上,表现了小说中主人公陈超对自己的爱情婚姻的自嘲——人到中年,仍未成家,自己喜欢的女友又要离他而去,远走他乡。
3) 联想式引用/意境融合。例如,陈超前往广州寻找证人,遇到一个喜爱诗歌的当地小老板欧阳,他努力帮助陈超办案,还热情地尽地主之谊,邀请陈超到珠江边上的夜市品尝美食。女服务员的殷勤和欧阳的崇拜使陈超醉眼蒙眬,发现“缺乏浪漫气息的广州夜晚竟如此的醉人”(263)。“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陈超念出韦庄的《忆江南》,大发议论:“我真觉得韦庄写的就是广州的情景,诗里说的那个地点恐怕就离这儿不远。……中国古代有不少描写街边食肆的诗歌,最初可能源自汉代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在他们人生最困难的时期,这对情人就在街边摆摊卖酒”。“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呀!”欧阳叫道,“对了,我看过一出广东戏,讲他们的浪漫故事。相如是个大诗人,文君跟他私奔了”(263)。作者在这里采用的是散发式的联想方式:年轻女招待→韦庄的《忆江南》→街边食肆→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巧妙地将古诗里的人与物和现实中的人与物融合起来,历史与现实虚实难分,有效地衬托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
4) 优美的英语翻译。毋庸置疑,裘小龙小说中诗歌的优美翻译是诗歌的美学意境得到充分表达的重要原因。例如,在《红英之死》中,当于光明在谈话中提到“桃花运”和即将远赴日本的陈超女友王枫的名字后,陈超不禁随口念出两句唐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并向于光明解释说,“‘桃花运’一词不一定出自这首诗,但写诗的人肯定有过亲身的经历。唐朝诗人崔护金榜题名,重返故地寻觅心上人,却再也见不到她的面,因而伤心欲绝”(238)。这首诗的英语译文非常简练,节奏分明,语义连绵,意象独特,其间的“留白”传神地表达了原诗的含蓄、伤感的韵味:
This door,this day
——Last year,your blushing face,
And the blushing faces
Of the peach blossoms reflecting
Yours.This door,this day
——this year,where are you,
You,in the peach blossoms?
The peach blossoms still
here,giggling
At the spring breeze.(238)
裘小龙在小说中通过引述中国诗歌,尤其是那些代表中国古典文学巅峰的唐宋诗歌,生动地表现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心理积淀。中国诗歌在裘小龙小说里的成功引用,不仅得益于作者点睛之笔的评介,也得益于作者优美的英语翻译。裘小龙小说中的诗歌引用与小说情节保持关联,这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所崇尚的情智提供了一个感性的认知语境。⑦
裘小龙小说的另一美学成就是其小说里的人物刻画。在他的三部小说中,先后出现的人物多达数十名,其中贯穿全部系列的就有十余人,如陈超的母亲、女友凌和王枫、中学同学卢华侨和妻子、单位领导李书记、搭档于光明一家(父亲“老猎手”、妻子佩青、儿子青青)以及同事夏医生和司机小周等。裘小龙系列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几乎涵盖了当代中国城市的各个社会层面——从法律机构到黑社会;从白领丽人到暗娼;从中央上层到城市居委会;从富豪到普通市民……虽然他们的社会角色千差万别,但在小说中都有着各自鲜明的人物特色。《石库门骊歌》的人物描写在三部小说中尤为成功,它以开阔的视野展现了一幅当代上海的社会图景。这部小说人物众多,细节生动,刻画了住在“石库门”里的十多户普通居民的生活状况。那里有细心的居委会老伯、警惕性高的民警老梁、靠剥虾为生的“虾姑”、快嘴好事的兰兰、“节俭的美食家”任老先生、退休工人万前胜、小食摊主雷学光、无业者蔡勇及妻子秀珍、岳母林娣……小说还描写了石库门外的另一些人——如“石库门总汇”的开发商顾先生、在夜总会打工的复旦学生白云、前干校领导乔明、周教授等等。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一本书,都以各自不同的人生故事演绎和诠释着当代中国的现实。
美国已故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1916-1962)在他著名的《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1959)一书中,对社会人文学科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法”奉为“学术的共同尺度”的趋向提出质疑,他把“社会学的想象力”作为人文社会学者、艺术家和科学家能否具备把握和解释社会问题或个体困扰的核心智识品质。米尔斯认为:个人环境的变化很多时候都是由“社会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应重视传记与历史解读的关系,因为“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人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能看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个人常常是怎样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在这样的杂乱无章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社会的架构,在这个架构中,我们可以阐明男女众生的种种心理状态”(C·赖特·米尔斯3)。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即赖特心目中的正确研究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赖特那里,“现象”包括纷繁的社会现象与个体的生存状态;“本质”则指社会结构性的变化,即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或社会动荡。在赖特看来,一个人一旦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就能够把握正确的阐释社会的能力。
反观裘小龙小说的人物描写,我们发现小说中的主要情节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1966-1976年间的“文革”。小说通过各种不同的人物故事讲述了那段历史带给人们的精神阴影以及给人们现实生活所造成的不可弥补的创伤。裘小龙小说的人物描写旨在揭示“文革”这一“社会结构性的变化”对于个体命运的影响以及个人在社会变故中所遭受的伤害。在裘小龙的小说中,人物故事似乎具有某种主题叙事的功能。
为方便讨论,我们将三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大致划分为以下几类:1)中年一代:如陈超、于光明夫妇、卢华侨、开发商顾先生等。他们紧跟时代发展,接受多元价值观,但多数仍在内心保持理想主义;2)老一代:如“老猎手”、市局李书记、调研员张政委、前工宣队代表万前胜等。他们或正直,或圆滑,或正统,或极左,但都坚守自己固有的意识形态立场;3)新生代:如王枫、白云等。他们是“文革”后出生、在市场经济时代成长的一代人,聪明能干、自我意识强、注重物质享受、淡漠意识形态;4)小说案件中的主要受害人:关红英、温丽萍、尹骊歌。她们属于“文革”的直接受害者,她们的人生或在精神上、或在肉体上成了“文革”的牺牲品。上述人物中,除了新生代的王枫和白云之外,几乎其他所有的人都遭受到“文革”的影响,不同程度地为那段“十年浩劫”的历史付出了代价。以下,笔者将把小说案件中的三名受害人作为主要讨论对象,分析这类人物形象与小说总体叙事的关系。
在《红英之死》中,关红英这个人物的刻画非常出色。她人虽未在书中真正出现,但却像《蝴蝶梦》电影中的丽贝卡,成为全书的真正主角。关红英在书中从头至尾牵动着读者,悬念不断——读者先是发现了她令人震惊的另一面;后是担心杀害她的凶手是否能被依法惩治。小说中的关红英年轻、漂亮,遇害时才31岁。她出生在50年代末,20岁参加工作,被害前是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化妆品部的领导,赫赫有名的全国女劳模,媒体明星,她的工作表现在领导和同事的眼里无可挑剔。百货公司的总经理认为“她在各方面都是一个标准的劳模”(Qiu Xiaolong 2000:63);同事说:“在政治上她积极参加每次运动,从不犯错;诚恳、忠实、热情。作为部门领导,她责任心强,工作兢兢业业,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71)。然而,随着案情一步步地展开,读者震惊地发现这位公众眼里事业成功的群众楷模,竟然有着另外一面完全不为人知的个人世界。她几乎没有朋友,没有恋人。唯一的亲人——母亲——也因患老年痴呆症常年住在安康院,很少与她交流。关红英从不对别人谈论和自己有关的事情(71);也没有任何工作之外的社会交往。在别人眼里,她高不可攀:同事觉得她“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但她还能怎么做呢?政治上有了名气么。”(71);邻居则认为“她是名人,不愿意和我们搅在一起。我们也犯不着热脸去碰冷屁股”(85)。但是,恰恰是这位朴素得体、无暇顾及个人生活的公众楷模,却被人听到“深夜独自伤心地哭泣”(90);在衣柜的里层摆放着许多从未露面的名牌时装、性感内衣、名牌化妆品;(81)在挂画背后藏匿着她的裸体乱交照片。(411)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社会环境已有了很大的改变,人们开始接受并追求物质享受。爱美是人的天性,何况像关红英这样漂亮能干的年轻女人,她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像其他人一样,打扮自己,寻找个人的幸福。但关红英在她的人生舞台上,强迫自己扮演另一个“她”——劳模。就像关红英的一位邻居——一位退了休的模范教师所说:“你一旦当了劳模,那就得永远按劳模的样子去做。……它就像个神奇的面具,你一旦戴上这副面具,面具也就成了你”(89)。为了扮演“劳模”,关红英变成了一个有着双重人格的怪物。“文革”时期的政治充斥着虚假的宣传,当时的英雄形象被拔高到了非人性的地步。小说曾在几个不同的地方,把“英雄人物”关红英的虚伪处境同“雷锋”、“阿庆嫂”和“妙玉”相比较。例如,曾经感动全国的“无私奉献”的“雷锋模范神话”(55)到了80年代“穿了帮”,《雷锋日记》原来是专业作家的集体创作;(117)“文革”时期的样板戏里没有夫妻,不要家庭,《沙家浜》的阿庆嫂虽有丈夫却出了远门,(71)因为浪漫的爱情会妨碍英雄人物的革命事业;《红楼梦》里那位远离尘世、外表高洁的妙玉,深夜在道观性欲难以排遣,走火入魔,结果被强人奸杀。(150)事实上,小说作者通过上述三个人物,从不同侧面谴责了那个时代所谓英雄“无私、无小家、无欲”的虚伪性和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假、大、空”的恶劣倾向。关红英的人生悲剧在于她接纳了虚伪,并让面具吞噬了本性与自我。由于面具的需要,她失去了人生的第一次爱情与可能的婚姻。(189)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她的七情六欲无法得到正常表达,她的命运和“妙玉”一样,最终落到遭人玩弄,被人杀害的结局。《红楼梦》里的“妙玉”被其“心魔”所毁;(150)而小说中的关红英则成为虚假面具的牺牲品。
在裘小龙三部小说的女受害者中,作者对关红英这个人物的描写侧重于人性扭曲这一方面,进而揭示出“十年浩劫”对于个体的精神危害。而在温丽萍与尹骊歌这两名人物身上,小说则从“身体”的角度,描写了“文革”对于个体人生的摧残。在《外滩花园》里,温丽萍虽遭黑社会追杀,但并未被杀害。小说的结尾预示她得到各方帮助,有可能走向新的生活。她是三名受害者中的幸运者。然而,在三名受害者的故事中,温丽萍的个人经历却最为凄惨,也最令人同情。温丽萍属于“文革”中荒废了青春、耗尽了狂热革命理想的“老三届”。少年时代的温丽萍是领跳“忠字舞”的红卫兵,更是男同学的“梦中情人”。70年代初,作为“知青”,她离开上海,孤身投靠福建长乐的一个远方亲戚,在那儿插队落户,但不到一年,这个美丽的上海知青在威逼之下,和一个比她大15岁、时任“公社革委会主任”、靠“打、砸、抢”发迹的本地农民结了婚。婚后温丽萍终日沉默寡言,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往来(除父亲去世时回过一次上海)。“文革”后她丈夫与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对温丽萍更是经常打骂,后来她唯一的儿子也因车祸丧生……在小说的开始,温丽萍的照片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没有人会把这个可怜的村妇同当年美丽的上海知青联系在一起。(Qiu Xiaolong 2002:26)在任何正常的社会里,人们很难相信一个人的命运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如此突然的变故,但对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这样的人生变故很平常。温丽萍的悲剧在于她的无辜与无奈,她像当时无数其他无辜个体一样,人生在政治潮流的裹挟下,遭到灭顶之灾。在小说《石库门骊歌》中,尹骊歌的故事是警方从她的邻居、同事和出版社编辑那里听来的,断断续续、支离破碎,就像她割裂、封闭的人生一样。“文革”开始时,在大学当政治辅导员的尹骊歌加入红卫兵组织,担任造反派领导,后被送进“五七”干校,在那里因和杨彬教授发生爱情受到迫害,并亲历了杨彬的死。“文革”后,尹骊歌发表小说《教授之死》,成了著名作家,但她从不与人交往,独往独来。她自杨彬死后便开始自闭:“从那一刻起,她无论活着或死去,都只是为了他”(Qiu Xiaolong 2004:114)。小说中除了得到过她帮助的个体食摊主雷学光和“虾姑”之外,没有人理解她,更没有人喜欢她;(106,160)“……她像只关闭的蚌,躲藏在过去的记忆中,一缕光线也照不进”(67)。小说中的尹骊歌如同“行尸走肉”,人虽活着,心却早已死去。她是一个活在“过去”,从未走出“文革”阴影的人。
裘小龙小说中的三名受害者使我们看到三种毁灭的人生与历史之间的种种关联。《红英之死》里的关红英被“面具”消解了本性与自我。《外滩花园》里的温丽萍以触目惊心的个人悲剧演绎了“文革”时代的荒诞。在《石库门骊歌》中,现实对她的伤害不仅体现在尹骊歌自闭的人生态度上,还反映在人们的看法与偏见之上,例如同事说她的悲剧是她应得的“报应”,因她当年“对别人可没有半点怜悯之心”(160)。如果说在《外滩花园》中,我们还可以为受害人温丽萍追索出某个具体加害者(如前公社革委会主任的丈夫),那么在《石库门骊歌》里,正如小说开始所叙述的那样,所有的邻居都有作案的嫌疑,也就是说,“文革”的影响殃及我们每一个人——“这里的人似乎仍然笼罩在过去的尘埃中,……确切地说,他们仍未走出文革的阴影”(125),偏见难以消除,对他人缺乏宽容。(144)在《外滩花园》中,有这样一句哲理性的话,“现实总是在改变着过去,但过去也在改变着现实”(Qiu Xiaolong 2002:31)。我们对过去有清醒的认识吗?
人们只有通过客观的回忆,才能真正面对记忆的创伤。(帕特森·法拉4)在裘小龙的小说里,客观的回忆就是从历史的记忆中寻求现实的意义。裘小龙文本所呈现的“现实”是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折射,是文化记忆和社会历史多重角度投射下的聚合体。作者通过中国诗歌表现历史与文化的源远流长;通过人物描写表现了历史与现实的不可割裂。作者试图提醒人们应时时对历史和记忆保持敏感,并对社会变革中的个体命运给予关注。“小说家的严肃著作体现了对人类现实的最广为人知的界定,他们通常具备这种想象力,……通过它,人们发现了历史与现实间的走向。……它似乎能戏剧性地让我们理解我们周围的现实与更宏观的社会现实间的联系”(C·赖特·米尔斯13)。
这也许就是裘小龙小说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自2000至2008年,由中国期刊网收录的有关哈金的论文近30篇,有关裘小龙的文章仅4篇。
②Qiu Xiaolong,Death of a Red Heroine,New York:Soho Press,Inc.2000; A Loyal Character Dancer,New York:Soho Press,Inc.2002; When Red Is Black,New York:Soho Press,Inc.2004.这3本英语小说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汉译本:《红英之死》(俞雷译,2003)、《外滩花园》(匡咏梅译,2005)和《石库门骊歌》(叶旭军译,2005)。本文所使用的书名、地名和人名均沿用汉译本名称,但小说内容的讨论及相关引文则依据英文原版小说。
③裘小龙新发表的小说有:《双城案》(A Case of Two Cities,2006)、《红旗袍》(Red Mandarin Dress,2007),均由纽约St.Martin's Minotaur出版公司出版。
④该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即2005年作者接受中文报刊采访的访谈录。原文为,(裘):“……这三本书在国内的发行量都是一万多,国外要多一些,尤其是第一本《红英之死》(2000年出版),销售至今,在美国、法国、德国都已经发行了五、六万本吧。在德国,精装版就印了五版。最近,英国的出版社还要推出这三本小说的英国版”。
⑤该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Author Interview(or Q & A):Qiu Xiaolong by Jeffrey Kinkley”。裘小龙在这次访谈中说道,这部小说的素材来自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真实事件,并无命案缠身的高干子弟与其随从被判死刑。
⑥小说中,陈超欢迎市场经济带给人们生活的变化,但却担忧市场经济背后的思想会导致人们过分崇尚物质生活。(见Qiu Xiaolong.Death of a Red Heroine.New York:Soho,2002年版,第222页。)
⑦参见〈http://www.howardwfrench.com/cgi-bin/mt/mt-tb.cgi/1478〉,Interview by Dr.Jamieson Spencer.在这次访谈中,裘小龙说他在写《红英之死》时曾翻译过一些中国爱情诗加进书里,受到外国读者的喜欢,因此他又继续翻译了一些中国古典诗歌,后收集在《中国爱情诗精选》(A Treasury of Chinese Love Poems,2003)中在美国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