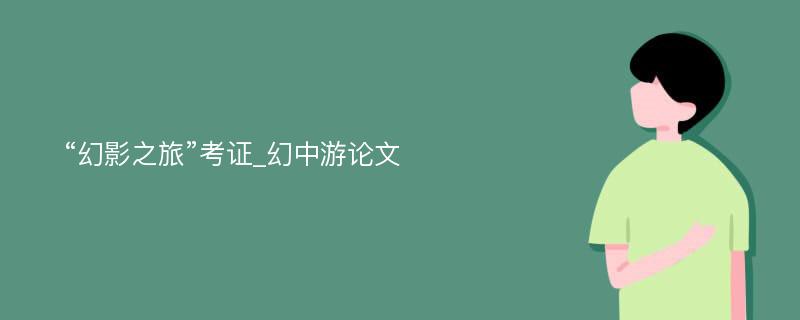
《幻中游》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207.42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425(2000)04—0043—05
《幻中游》国内不见藏本。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四明清小说部乙著录:
幻中游 十八回
存□坊刻本。卷一题《新刊小说幻中游醒世奇观》[日本东京帝大文学部研究室]清无名氏撰。题步月斋主人编次。封面题烟霞主人编述。
1988年3月,北京图书馆的薛英访问日本东京, 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协力部副部长松泽隆夫的协助下得《幻中游》,此后,将其交付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使我们得以窥见全貌,其版本情况如下:
小说封题《幻中游》,其右上角题“烟霞主人编述”,左下角题“本衙藏板”,内题“新刻小说幻中游醒世奇观”、“步月斋主人编次”。著录为18回,不分卷,但正文又分4卷,1至5回为卷1,6至9 回为卷2,10至13回为卷3,14至18回为卷4。回目前题“新刻小说幻中游醒世奇观”,书后刻“大清乾隆三十二年菊月新编”(以下简称该版本为乾隆本)。该本白口、四周单边。版心有单鱼尾,其上书《幻中游》,其下为回目及页码。半叶11行,行28字。
其实,乾隆本的《幻中游》就是孙先生所见的版本。因为两个版本的来源同出一处。显然是孙先生将“新刻”误为“新刊”了。
从版本的情况看,我们可以肯定乾隆本的《幻中游》不是初写本或初刻本。其理由如下:其一,封题“烟霞主人编述”,虽表明著作权,但内题“步月斋主人编次”则表明《幻中游》早有写本,依稀地透露出乾隆本不是初写本或初刻本的蛛丝马迹。
其二,内题“新刻小说幻中游醒世奇观”,虽然旨在传达乾隆本就是初刻本的消息,甚至,刻书者还不忘在书后刻上“大清乾隆三十二年菊月新编”的字样。但恰恰是这个“新编”推翻了给人留下的“新刻”即初刻的意向。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看,明清小说凡是带有“新编”的一般都不是初刻本。
其三,乾隆本是坊刻本,一般来说,坊刻本的书多以重刻为主,是书商追求商业利润的产物。
其四,从小说回目看,《幻中游》的回目皆为单句,这无疑是在宣称该小说有较长的流传时间,即它不应该出现在小说回目工整对仗的乾隆时期。因为从通俗长篇或中篇小说回目发展的规律来看,总是先有单句,然后才有比较工整对仗的句式。如明末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平山冷燕》的回目皆为单句。换言之,从回目的句式来看,乾隆本的《幻中游》不可能是初刻本。因为乾隆时期是古典小说的成熟期,其回目不再是单句,这时,小说的回目大都是较为工整的对仗句式。
其五,《幻中游》回目明显地经过修改,这一修改应该在乾隆本中完成。薛英曾就《幻中游》的回目问题作过这样的论述:“如果把每两回回目文字合起来看,便是我们常见的对仗比较工整的对句回目文字了。”[1] 薛英的论述是有一定道理的,它表明《幻中游》在产生之后,其回目曾有过修改,有将两回合为一回的企图。这就使我们想起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版本的情况,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嘉靖本为240则, 回目虽相对整齐但并不工整对仗,清初以后,该书才以120回的面貌出现,是时,回目的句式才工整对仗。这就告诉我们,《幻中游》在坊刻之前,似乎有过将两回的回目合为1回的考虑,很可能是因为合并后9回的回目在视觉上的效果不如原来的18回好看,故此作罢。尽管如此,《幻中游》的回目在书坊刻印时却作了修改。我们以为,对其进行修改的肯定不是原作者,很可能是“步月斋主人编次”时进行的。为了充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再分析一下与“步月斋主人”相关的“烟霞主人”的情况。在另一部由“烟霞主人编次”的小说《跻云楼》里,我们发现,十四回的小说《跻云楼》也是单句回目,也有将两回回目文字合在一起为对仗句式的痕迹。同时,这部小说也是“本衙藏板”,其刻书年代是乾隆三十三年二月,与《幻中游》同刻于一个书坊。略有不同的是,这部小说刻印的时间比《幻中游》迟5个月。另外,《跻云楼》是由“自得主人编次”的。这样,我们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书商在得到了烟霞主人编述的《幻中游》和《跻云楼》的抄本或初刻本后,以为这两部小说有一定的商业价值,因此找来了步月斋主人、自得主人对其进行“编次”,并向他们提出了统一格式的要求。当然,如果步月斋主人就是自得主人的话,其笔法和风格自然会一致。事实上,这两部小说的乾隆本回目的编撰风格也较为一致。故只能有这样的解释,就是书商提出了划一的标准,让步月斋主人或自得主人贯彻其意图。另外存在的可能性是,步月斋主人就是自得主人。
其六,对两部小说回目的修改工作不可能在乾隆本诞生以前较早的时间进行,因为如果没有再版或新刻的契机,一部小说是不会专门去进行回目的修改的,就是说小说回目的修改只能是在决定重新翻刻时进行的。换言之,修改回目的工作是在乾隆三十年前后完成的,即对《幻中游》的修改是在此间完成的。
以上六点我们论证了乾隆本不是《幻中游》的初本,其理由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的。
那么,《幻中游》题材来源的依据是什么呢?它的作者应生活在什么时代呢?我以为其题材的来源应与李清的《梼杌闲评》相关,写作时间的上限应略迟于蒲松龄写作《聊斋志异·小谢秋容》的年代。其具体理由为:
第一,《幻中游》是围绕明末宦官魏忠贤专权、陷害忠良来结构全篇的。众所周知,魏忠贤之事是明末清初诗文戏曲最关心的内容,也是清初小说最关心的题材之一,这一时期曾出现过李清的《梼杌闲评》。欧阳健在《梼杌闲评作者为李清考》一文中,详细论证了《梼杌闲评》的作者为由明入清的李清[2]。 李清的《梼杌闲评》在结构章法上与《幻中游》有着明显的接近之处,一是它们均以魏忠贤之事结构全篇,以此来揭露现实政治的丑恶,并进行社会批判;二是它们都把“奇”、“幻”视为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唯远为源。可以说是李清的《梼杌闲评》在启示着《幻中游》作者对这一题材的关注,进而写下了这部“似近荒唐,详考确有实据”(《幻中游》第1回)的小说。
第二,我们说《幻中游》的写作时间是在蒲松龄写作《小谢秋容》之后,这是因为《幻中游》中石茂兰设帐收鬼徒的情节明显地因袭了《小谢秋容》的内容,只不过《幻中游》的情节更丰富复杂一些,按照小说史发展的规律,故事形态的丰富一般是由简到繁。因此,《幻中游》原则上说产生在《聊斋志异·小谢秋容》之后,其作者的生卒年代也自然略迟于蒲松龄,最多与蒲松龄同一时代,但绝不会早于蒲松龄。
那么,《幻中游》应产生于何时呢?
我们认为应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以后,是时,《聊斋志异》开始有朱湘抄本流传。《幻中游》的作者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或略迟几年见到《聊斋志异》,然后才开始创作《幻中游》,其时间大约在康熙四十年左右。换言之,《幻中游》应产生在康熙四十年左右。之所以不会再迟,是因为自明末出现《魏忠贤小说斥奸书》、《魏忠贤轶事》以后,清初则出现了写作魏忠贤事的高潮,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李清的《梼杌闲评》。在时效热的驱动下,《幻中游》有可能产生于此时。
至于作者烟霞主人究竟为何人?《幻中游》的修改者步月斋主人究竟为何人?由于资料贫乏,一时无法考定。
《幻中游》主要叙述了明万历、天启、崇祯年间黄州罗田县石峨、石茂兰父子两代因忤宦官魏忠贤屡受迫害而家破人亡,以及魏忠贤事发后石茂兰登科为官故事。从故事情节来看,《幻中游》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
首先,作品有意识地把故事的背景放在魏忠贤专权的年代,紧紧地扣住这一社会背景来写人物命运的沉浮及其悲欢离合,这样就深刻地揭示了晚明政治腐败、宦官专政的黑暗政治现实,进而为我们提供了一幅难忘的生动的历史画卷。众所周知,魏忠贤是明代后期的宦官,明熹宗时得到宠幸,朝廷士大夫深受他的荼毒,在魏忠贤的网罗下,朝廷内外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阉党势力。《明史·魏忠贤传》云:“初,朝臣争三案。及辛亥、癸亥两京察与熊廷弼狱事,……其党欲藉忠贤力倾诸正人,遂相率归忠贤,称义儿,且云:‘东林将害翁’。以故,……御史梁梦环复兴汪文言狱,下镇抚司拷死。许显纯具爰书,词连赵南星、杨涟等20余人,削籍遣戍有差。逮涟及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6人,至牵人熊廷弼案中,掠治死于狱。又杀廷弼, 而杖其姻御史吴裕中至死。又削逐尚书李宗延、张问达、侍郎公鼐等50余人,朝署一空。……于是忠贤之党遍要津矣。”又云:“凡忠贤所宿恨,……虽已去,必削籍,重或充军,死必追赃破其家。或忠贤偶忘之,其党必追论前事,激忠贤怒。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作品紧紧地扣住这一现实,一笔并写两面,一是正面描写魏忠贤及其阉党对朝廷士大夫的无情迫害;一是在这一广阔的背景下写百姓流离失所深受盘剥与压榨的痛苦。
为了深化这一主题,作者把笔墨重点放在石峨、石茂兰父子两代人经历的事件上。如写石峨抗魏氏放银盘剥百姓之后,尽管魏忠贤出于顾虑而暂时停止了对石峨的迫害,但却唆使其党羽屡屡加害于石家父子。虽然石峨死去,他们依旧不放过对石茂兰的迫害,如在榨干石茂兰的家产后,他们又将石茂兰拘役河役3年(第6回)。此后,在石茂兰流落异乡之时,魏忠贤的密探还暗察石茂兰的过失。如第9 回写石茂兰有感于身世飘零,在画上题诗道:“安邦自古赖贤豪,群奸杂登列满朝。幸得手持三尺剑,愿为当代锄草茅。”魏忠贤的党羽不但立即将此诗抄录给魏忠贤,还提醒魏忠贤斩草除根。于是,石茂兰又遭迫害并身陷囹圄。作品就是这样通过魏忠贤对石家父子的迫害真实地反映了魏忠贤专权,满朝文武仰其鼻息,内外勾结,大干伤天害理之事的罪行。故作者在第1回写道:“乍看似近荒唐,详考确有实据。 ”将此情节与《明史》印证便知作品对魏忠贤及其党徒的批判是十分有力的。由于作者精心构思了石峨弃官的前因系反对魏忠贤鱼肉百姓而辞官,这样,就使得魏忠贤及党徒加害石氏父子的做法更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意义。
其次,《幻中游》对社会的批判是围绕“忠”、“奸”这样的理念来进行的。“只因朝纲不振,权奸当道,立意家居, 无心宦途”(第1回),清官石峨的这番感慨是针对黑暗的现实而发的。如何把这样的理念化为生动可感的艺术情境呢?作者遵循艺术的规律,通过塑造形象,在生动而鲜明的对比之中揭示人物的风貌和特质。故事从石峨任广西柳州府知府,拒绝为魏忠贤放银盘剥百姓写起,与此同时,卖身投靠魏忠贤的广西巡抚见石峨拒绝放银,遂以“东厂大人的钧旨,谁敢抗违”进行威胁。面对威胁石峨大义凛然,公然对巡抚宣称:“吾人出仕,原以行义,非图固宠。卑职自幼读书,颇有志气。昔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吾宁为五马荣挫志乎?大人既不肯为万民作主,卑职断不给太监放债。”当巡抚见威胁不行又以仕途前程为利诱时,石峨回答道:“与其待大人提免,何如卑职先自行引退。”这是小说展开的引子,可以说是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来塑造石峨刚正不阿的艺术形象的,作为小说的引子,它既展现了石峨这一艺术形象的魅力,同时也为下面故事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伏线。
“忠”、“奸”之争是一种理念,如何使这一理念化为生动可感的艺术情境呢?作者表现出勇于探索的艺术精神,为了使小说成功地担负起深厚的社会批判内容,作者别具匠心地把故事的重点放在魏忠贤及其党徒对石峨及后人所施加的迫害方面。如巡抚在石峨离职后依旧不忘写密信给魏忠贤告石峨的黑状。又如一帮拜在魏忠贤门下的贪官污吏沆瀣一气、相互勾结,连连不断地把厄运降临到石峨、石茂兰一家的身上。再如西安知府范承颜为讨好魏忠贤竭力地网罗罪名,将石峨前任开挖的引河淤平之事移栽到石峨的身上。由于石峨这时已经去世,范承颜又把淫威发泄到石峨之子石茂兰的身上,致使石茂兰家破人亡(第5回)。 所有这些故事的延伸都在提高着“忠”、“奸”之争的艺术质量。反过来说,如果小说没有这些情节的楔入,其社会批判的力量将会大打折扣,而且也将不会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可以说这部小说之所以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就在于它对人物命运的揭示是在理念与生动可感艺术形象的结合中完成的。
其三,作品在描绘世情方面,为加大社会批判的力度,还有意识地加入了“奇”、“幻”的笔墨。如石茂兰身陷囹圄之后,作者精心构造了两个场景:一个是女弟子秋英将石茂兰的冤情投诉到了城隍台(第9回),按理说,阴间的城隍爷该明察秋毫了吧,偏偏秋英遇到了垂涎其貌美的肖判官,肖判官不但不准其告状,反而要强占秋英为妾。秋英不从,肖判官便将其锁入家门,每日肆意拷打以逼其应允。另一场景是,弟子馗儿投状于阳间的抚院衙门(第10回),抚院不但不准其状,反而不问青红皂白任意拷打馗儿,仅此还不算,抚院还把馗儿关押进监。作者精心构思的这两个场面是很有匠心的。如果说魏忠贤及党羽在阳间的横行是因为形成了一个个层层庇护、相互勾结的网络,那么,阴间地府的黑暗无疑是对前者的补充和发挥,可以说这两个情节的楔入是作者企图在更深广的范围内加强对现实批判的力量。诚然,一个魏忠贤并不可怕,但是当他网罗党羽形成一股强大的邪恶势力的时候,这种邪恶势力使正义得不到伸张,这样,给人带来的心灵创伤无疑是巨大的,同时也是无法用言辞来表达的。
必须指出的是,作者对魏忠贤进行社会批判时的艺术把握水平是十分高超的。在暴露魏忠贤罪恶时,作者关注的目标并不是让魏忠贤参与到每一个具体事件的全过程,而只是让他或发狠或含而不露地说上几句,仅此而已,其爪牙们便心领神会地去做无法无天的事情,而且就足以使善良的人家破人亡,冤情得不到伸张和昭雪。对官场黑暗内幕的揭露,使这部小说的社会批判力量更为厚重。所以,秋英阴间地府告状的失败与馗儿阳间抚院告状的失败如同社会批判的两把匕首,在更高的层次上诉说着官府的黑暗,官府是魑魅魍魉横行、见不得人的地方。
作品对现实的批判是有力的同时也是极为深广的。石茂兰被迫变卖家产抵父债以后,官宦子弟王诠因慕石茂兰妻子房翠容美貌便顿起歹心。在石茂兰行役三年期间,王诠为了达到霸占房翠容的目的,不惜造假文书冒充石茂兰之名说同意房翠容再嫁,此为房翠容识破以后,又买通贼人杀了房翠容的母亲,使其失去生活的依靠,随后又散布石茂兰死去的假消息来迫使房翠容就范(第6回)。从表层看, 这一情节似乎是告诫人们交友要慎重,就是说,如果当初石茂兰不与王诠相交断然不会引狼入室,断然不会造成个人的家庭和婚姻的悲剧。其实不然,由于作品注意将个人生活的悲剧置于社会黑暗、官场乌烟瘴气草菅人命的大背景下来写,因此,这一内容的出现其实质是在官绅相互勾结的背景之下,以更深广的范围来加强作品批判现实的色泽。诚如作品题目上所题的那样,《幻中游》是一部“醒世奇观”。
那么,作者是如何构思《幻中游》的呢?在第一回有一类似序言的短文,尤其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原文不长,移录如下:
天下事之所有,必非理之所无;而理之所无,恒为事之所有。此以知胶柱之见不可存,而观变之所应裕也。即如鬼神一说,过溺则邻于惑,太忽则涉于侮。《鲁论》云:“敬鬼神而远之。”斯言至矣。然依古以来,往往有生平不信鬼神,而实默受其策遣而莫觉者。亦有明与鬼神相交而卒收其俾益于无穷者。奇奇幻幻,出人意表。岂第如黄熊入梦,大历坏寝,纯在恍惚不可为象之间哉!这部小说,单道有明一桩故事,乍看近荒唐,详考确有实据。其中忠臣孝子、烈女节妇、良师信友、义仆贤妓,无不悉备。俾看官有以启其善念,遏其邪心。较之才子佳人,花前月下,徒以偷香窃玉之态,闺阁床第之言,长人淫欲,贻害幼学者,似为不无较异云。
这里明确地交待了《幻中游》的创作思想是“启其善念,遏其邪心”。就这一思想而言,《幻中游》的立意并不出奇,但由于作品借鬼神之事贯穿了“似近荒唐,详考确有实据”,注意将笔墨集中在揭示现实生活的矛盾方面,故作品依旧显得楚楚动人,特别是作品的上半部分。
作品的奇幻笔墨尤其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从小说的内容来看,《幻中游》主要写世情,然而,它又强调了“幻”,并且把“幻”的内容贯穿于小说的始终。正因为这样,作品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是独特的,也是耐人寻味的,如石茂兰设帐收鬼徒读书的情节(第7 回)便可与《聊斋志异》中的篇什《小谢秋容》相比美,当胡员外把落难之中的石茂兰让进家门时,二女鬼秋英、春芳来到石生的书房,提出读书的要求——
二载有余,这石生在外鳏居已久,见二女又是绝色美貌,未免有些欣羡之意,时以戏言挑之。二女子厉色相拒道:“你我现系师徒,师徒犹父子也。遽萌苟且之心,岂不有忝名教,自误前程,劝先生断勿再起妄念。”石生见其词义正,游戏之言从此不敢说了。
这一情节极为感人,它既塑造了天真无邪的秋英与春芳的形象,以她们的读书过目不忘显示着她们的聪明过人,而拒绝与石生的苟合又见其品质。至此,作者并没有停下笔来而是继续深化她们的性格,塑造其感人的艺术形象。围绕着石茂兰遭陷害进监事件的发生,二女鬼以及馗儿展开了营救的活动。围绕着探监、告状阴间地府、抚院等一系列事件,二女鬼及馗儿的形象都显示出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就其故事的基本元素而言,这虽与《聊斋志异》中的《小谢秋容》相似,但由于《幻中游》把握的是一重大社会题材,所以石生与鬼徒间的故事,较之《小谢秋容》就显得更为激动人心。因此,这一笔虽“奇”虽“幻”,但借鬼神之事来批判现实的丑恶,无疑是别开生面发人深省的。
平心而论,《幻中游》的确是有不少糟粕,如写石峨登科是因魁星帝君向玉帝进献的缘故;写石茂兰命运多蹇,后来官运亨通则是因太白金星化为曹半仙为其算定的结果,而房翠容逃脱王诠的魔掌则是因为有观音菩萨的相救,秋英能协助石茂兰大败苗王则是因为有碧霞宫神女传授三卷天书,等等。这些都刻意地宣扬了神的力量和神的无所不在。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作者在安排人物命运时强调了神的旨意,但其中又确实不乏精彩场面。如石峨赴任长安县,衙役因官衙闹鬼想把石峨安排到民宅,但石峨坚持住进官衙。“是晚,更夫巡夜,闻有鬼说道:‘石青天在此居官,吾等暂且回避。’从此官衙内安静无事了。”(第3 回)显然,这鬼,已不是一般的鬼,而是具有象征意义。就是说,鬼魅在官衙中作崇是因为政治不修明,是因为有贪官污吏。那么,作者是无神论者吗?但他又分明写下“有生平不信鬼神,而实默受其策遣而莫觉者。亦有明与鬼神相交而卒收其俾益于无穷者”之语。此外,作品还有意识地宣扬了因果报应、前世已定的宿命思想。如石茂兰屡遭磨难以及与二女鬼秋英、春芳的婚姻均为前世已定,又如王诠恶贯满盈遭恶报以及石茂兰不计前嫌赠金给王诠妻,乃至王诠的鬼魂解石茂兰之厄,等等。令人眼花缭乱,难以窥透作者对鬼神之事的态度。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作者在题旨中所宣扬的——劝善惩恶。在这种动机的支配下,作者故意以“奇奇幻幻,出人意表”的情节来迎合读者,来打动读者。
总之,《幻中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世情小说,因为它在写世情时,始终用鬼神之事造成的氛围笼罩全篇,在写鬼神之事时又夹杂着兵革之事,如石茂兰化装成算卦先生私探贼穴(第15回),秋英得天书助石茂兰大战苗王。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幻中游》并不能归入“烟粉”一类(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是这样归类的),它应该是一部以写世情为主的杂糅小说,反映了作者敢于突破旧有的小说题材模式,努力探索新的创作道路的意图。因此,小说虽有一些败笔,如作品的后半部分不如前半部分紧凑,有故意拉长之嫌,又如过分地宣扬因果报应等,但整个作品还是有一定审美认识价值的,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作品。
[收稿日期]2000—0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