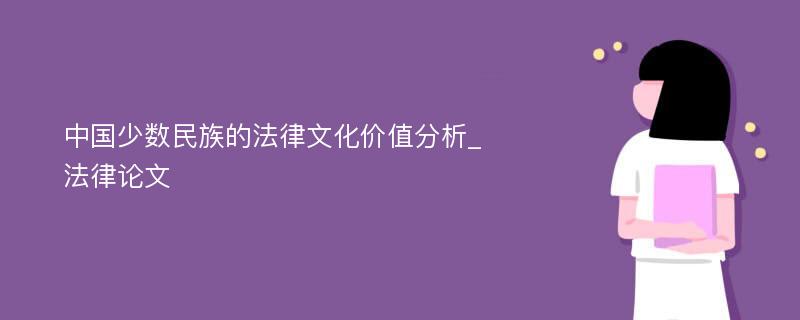
中国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价值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少数民族论文,中国论文,价值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09、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07)12—128—133
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为我们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中华法系乃至传统法文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1](P3) 各民族的许多精神智慧、价值因素长期存活在他们的法律生活中,甚至至今还发挥着调整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对少数民族法文化田野调查中,我们接触过、感受过富有生命力的原创智慧,这些智慧因子是中华法苑中的奇葩,值得我们去赞赏,也需要我们去认识、了解、研究。
一、宽容、妥协、和解的精神智慧
一般说来,各少数民族对偷盗、杀人等严重违反刑事习惯性规范的行为,以及社会内部产生的纠纷都较为详尽地规定了解决、处理的原则、机构人员、程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纠纷解决的最终目的并非简单的权利义务再分配,而是避免双方矛盾冲突的激化,使一时异常的秩序回复到有序状态。另一方面,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经济制裁方式占了很大比例,始终贯穿着以赔为主、以刑为辅的特点,实行“以赔代刑”的方法。这些特点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法文化中的宽容、妥协、和解因子,集中表现在尚存于许多少数民族法律生活中的“赔命价”(costoflife)制度和调解制度上。
(一)“赔命价”制度
所谓“赔命价”,指的是杀人者按照被害者的身份,支付给死者家属一定数额的金钱或实物作为补偿,而被害者家属则放弃报仇,从此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命价”在此可以理解为是与被害人性命价值相当的等价钱财,其目的在于用财产使受害方恢复到未受害时的状态。人类学家普遍认为,“赔命价”是人类社会从对复仇的公开支持走向否定的标志,它具有减少仇杀、避免世代冤冤相报的积极意义,有助于维护少数民族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据二十四史》记载,我国古代社会北方游牧民族习惯法中多有类似的规定。例如,以鲜卑族拓跋部为政权主体的北魏王朝就沿用了鲜卑拓跋部族的传统习惯,在立朝之初就有“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者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责五,私则责十”(《魏书·刑罚志》)的规定。此外,建立金王朝的女真族习惯法中也有“杀人偿马牛三十”的法条(《金史·刑法志》),西夏党项族也奉行“杀人者,纳命价钱百二十千”(《辽史》卷115)。《清会典》记载:“国初,凡过失杀伤人者,鞭一百,赔人一口”。
在南方山地少数民族中,“赔命价”在历史上曾一度适应这一地区特有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对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景颇族的习惯法认为,杀人本来已不是好事,再把活着的人处死那就更不好了。因此,按其习惯法的规定,凶手必须赔给死者家属若干头牛。此外,还要象征性的实行同态赔偿,即头颅要赔葫芦一个、眼睛要赔宝石两颗、牙齿要赔斧头一把等等。傈僳族在械斗结束后,如果一方死亡的人太多,另一方必须付给偿命金,赔偿的财物归集体分摊,当事人及近亲属要多负担一些。对方得到的偿命金也大家分享,被害者家属可多得一些。傣族还规定赔命价的人,还应出绳子银三两三钱,刽子手的刀银三两三钱,拴绳子的银五厘。藏族“赔命价”习惯法源于松赞干布时期的《法律二十条》,它以藏传佛教戒律为指导,规定“杀人者以大小论抵”。到17世纪五世达赖时期的《十三法》与《十六法》,都在第四、第七两部法律中规定杀人为“重罪”应“赔命价”。藏族的“赔命价”习惯法不但历史十分悠久,而且内容相当完整,逐渐成为整个藏区包括西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藏族居住地的藏族部落之间、个人之间处理杀人、伤害等纠纷的一种习惯法。过去有藏区无“大辟”的说法,主要就是因为藏区大都采取“赔命价”来处理人命纠纷,而不宣判死刑。
“赔命价”作为一种“以罚代刑”的解决纠纷方式,实际上是通过一种交易方式解决极端矛盾的过程,它便于调节和削弱竞争、对抗中出现的人际紧张关系,使人们更为注重道德的谴责和经济赔偿。在这一过程里,普遍追求的目的并不是诸如惩罚、改造、预防犯罪之类的正统刑罚目的,而是追求通过有效的赔偿、补偿在侵害与受害双方之间避免复仇,实现“永不反悔”的和解。因此,“赔命价”制度实质上折射出“宽容”、“妥协”的精神,人们通过如此方法化解矛盾,继续保持共同生活与繁衍。另一方面,“赔命价”也与当代刑事司法改革的某些趋势暗合。现在,社会已经公认人类社会最终会废除死刑,而“赔命价”制度在价值选择上既是对复仇的否定,也是对死刑的否定。以人为本,保全人命,温和了活着的人们的欲念,消除怨冤,正代表了人类社会废除死刑的进步方向。
(二)调解制度
在西藏调查时,自治区司法厅的同志告诉我们,2002年全区大约发生5900余件民事纠纷,90%以上都是通过民间和解处理的。换言之,民事纠纷案件基本上是通过民间传统习惯和解了的,而且和解之后没有一件反悔。例如,被当地百姓称为“高原之鹰”的饶赛居委会调解员群培就处理过很多棘手的民间纠纷。群培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熟悉藏族传统的习惯规则,又了解国家法律的规定,还具备藏传佛教的基本知识。他说,调处好一件纠纷,常常要综合运用习惯法、国家法、宗教法三种知识,形成一种化解矛盾的合力。藏谚云,“两只豹子打架也不会撕破豹皮”,意思是说,即使有矛盾也要互留情面,留有余地。《萨迦格言》也说,“强求一致是闹纠纷的根源”,这些都反映出藏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妥协、宽容、和解精神,这与儒家法文化中“息讼”、“无讼”、“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和合精神是多么相似!
生活在云南剑川地区的白族,把民间的调解称为“议话”(羌族也是如此),就是讲道理的意思。若双方发生殴打,则由其中一方准备酒菜,要求本村有威信的老人、知识分子或旧时的保甲长到家评理。双方到齐后,先由当事人分别叙述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经过,然后由其他人评理。对盗窃、通奸等违反习惯法的行为,一般也是请人议话,不对的一方即为输理,要赔偿损失并罚款。类似的民间调解方式还有毛南族的“匠讲”,主持人是村老、排头、学董、文武相公等;[2](P142—143) 瑶族的“交码”,当村子里发生争端需要请头人处理。判案时,以禾秆为筹。当事人申述发生争端的原委,每讲一条道理头人就折一节三寸长的禾秆放在桌上,有多少条道理就有多少根禾秆。甲方申述完了,头人把禾秆收起来带到乙方去摆禾秆,把甲方的理由重复一遍。乙方如果不同意,又向头人申述理由。这样往返数次,直到双方的理由都摆透了,头人再根据双方的陈述判案。[3](P68—70)
又如,历史上凉山彝族不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都由专职的“德古”依照习惯法解决,且这种纠纷解决的机制在今天还被民间广泛采用。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1982年,男方姓吉达,女方姓曲木的二人从小订下娃娃亲。后曲木与男方行了婚礼,但未落户夫家(彝族风俗,双方举行婚礼后,女方要隔2—3年方落户夫家)。后来曲木认为吉达人才不如她,遂提出离婚,在财产返还方面发生争执,在“德古”的调解下,曲木家用“依查”仪式即热烫钱,杀一头牛请吉达家吃,意为向吉达家表示歉意,并退还男方婚事费用共5000元钱。案结后,举行了“西过则”仪式,即捏死一只鸡,并说:“今天是猴年马月猪日,你们两家的这桩离婚纠纷在‘德古’的处理下,已经说清楚。将来如果哪一方反悔,就如这只鸡一样死去”。此纠纷得以妥善解决。
该种纠纷解决的“方案”对法律界人士来说,多半是陌生的,因为这一争议本应到法庭上“讨个说法”,于是接下来的程序便是起诉、传唤当事人到庭、举证、质证、裁判、执行,然而彝族人民并未这样做,他们选择了让“德古”、“毕摩”们当“法官”,用他们的“土办法”,在两三天或一个星期内便成功解决了,用现代的话说“诉讼效率不可谓不高”,而这不正是现代法治孜孜以求的目标吗?用法律专家的眼光来看,他们的这种做法也许是“不懂法”、“法律意识淡薄”,但在彝区人民看来,他们的祖宗之法——习惯法便是解决争议的最佳方法。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许多按照制定法解决的争议,尽管当事人获得了一纸裁定,却并未获得实质上的解决,于是只好又请“德古”们出来解决,而经“德古”们的处理,纠纷还真的获得了“实质正义”。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法文化中的“赔命价”制度和调解制度,确实包含着深刻的原创智慧,它不仅可以为当代法制提供根基性的文化资源,而且还包括技术性的知识。
重视司法程序之外的调解,研究和总结民间解决纠纷时重妥协、重宽容的经验,已成为当今世界特别是欧美法治国家司法改革的重点。目前,世界各国普遍确立了不同程度、不同模式的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机制,对于已经出现“诉讼爆炸”现象的国家,极大缓解了司法和社会的压力;对于职权主义程度较高的司法体系,带来了司法民主化的气氛;对于特殊类型或复杂的案件,提供了符合情理、追求实质正义的个别平衡。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中宽容、妥协、和解的精神对于当代法治的重大意义。
二、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因素
少数民族法文化中包含有现代社会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因素,其中蕴含着人类社会早期的原创性智慧。摩尔根、恩格斯都曾赞美过原始社会制度的自由、民主、平等,在这种制度下,“人民是自由的,政治的精神是民主的”。[4](P248) 一般而言,族长、寨老等社会组织首领的产生并非世袭或由特定权威指定,而多以个人的才德、威望以及受到全体成员信任和拥戴的程度自然形成的。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的活动一般以会议的形式进行,族群中的内外大小事务由与会者共同商议、表决,最后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形成决议,首领只起到召集、主持和宣布决议的作用,社会组织的权力还是来源于大多数人的合意。例如,在北方游牧部落中,通过盟誓,部落或部落联盟内部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权利义务较为稳固的关系,来维持、推动内部秩序的正常运转;通过议事会制度,部落中的重大事件,如战争、打冤家、对外交涉、调整草场、制定习惯法等,多由部落头人和民众推选的代表联合召开部落议事会,甚至是举行部落全体成员大会讨论解决,以维护族群成员的共同利益。
西盟佤族社会也存在类似的原始议事制度。窝朗、头人、魔巴、朗巧中的任何人,即使权威再高,也不得独断专行。他们行使职权时必须符合阿佤理,有关部落或村寨的大事,必须召开头人会议协商解决,有时还得召开全体成员大会,许多佤族寨子至今还有类似“民主广场”那样的一块坝子,供村民协商、议事之用。除了民主议事制度外,西盟佤族的权威者也不能享有种种特权,他们的言行也处处体现佤族原始部落社会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精神。例如:
1955年8月,原小马散寨大头人岩瑞约了5个人去偷西盟粮库的存米,结果被发现,该寨群众认为他丢了寨子的脸,根据阿佤理抄了他的家,拆了他的房屋,把他的猪也杀了分吃掉。此后其兄弟盖房都不找他帮忙,以示断绝关系。岩瑞在寨子里住不下去了,就跑到果果寨去住。1956年9月才回到小马散,而寨里人已不再承认他是头人了。再如,窝努寨魔巴岩扫之长子与已订婚的女子结婚,该女子的未婚夫即根据阿佤理抄了岩扫魔巴的家。
这说明佤族的头人、魔巴一般是受群众信任的,但如果违犯阿佤理,同样要受到制裁,这是原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在原始状态里,全体成员的关系都是直接的,他们共同消费非常缺乏的社会必需品,利益是共同的,基本的社会秩序也是通过原始的社会控制手段来维护,原始人几乎很少意识到存在一种超越族群之上的权力。尽管这种观念与现代法治社会宣扬的“主权在民”、“人人平等”有本质的区别,但它却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我们真正树立并实现这些观念的起点和基础。
苗族议榔制、侗族款约制也充分体现了人人参与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智慧因子。在制定“榔规榔约”、“款约”时,每户都要去一个当家人,凡参加之人都有平等发表见解的机会和权利。会议由德高望重、为人正派的头人主持,他们大多不经过民主选举,也不受财产多寡的限制,而是凭借公众的信任、树立威望而自然形成。所立之约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类似于法律的强制执行力。例如,清水江下游沿岸苗、侗社会出现的议约化倾向,就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苗侗民族社会原始民主制的特点,多少也折射出公意的味道。
凉山彝族调解纠纷的“德古”一词本身就富有民主特色。“德”是指“重、稳重”,“古”是指“圆、圆圈”,“德古”是指“一个稳定的圈子”,可见,“德古”一词强调的是环境、场所,也就是说,调解案件的法官们的位置不分高低,人不分贵贱、男女、甚至老少,大家围坐成圆形的“德古”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可以充分发表各自的意见。这种座位方式正是与“德古”的自然产生和民主公平制度相一致的,是彝族最古老的“圆桌会议”形式。[5](P66—67) 圆桌会议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稍有不公,即曝光于社会,“德古”便丧失人心,声誉也自然消失。正如彝谚所讲:“德古儿子无能则当马夫,骏马之仔无能抵债务”。这种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闪烁着彝族法文化的魅力,赢得了彝族民众的热爱。
瑶族在对待异民族的关系上,也采取平等原则,更表现出一种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精神。例如,广西大瑶山习惯法规定,不论是否加入石牌,也不论汉壮商人宾客,只要他生活在石牌管辖区内,都得受石牌法约束,同时也受石牌法保护。大瑶山曾经发生帮助汉人客商追回损失的案例就是明证。此外,瑶族还比较尊重社会成员的意志,离婚大多比较自由。离婚时,只要备一斤酒到中人家并向中人说明离婚理由和条件,中人了解有关情况后,经过一些简易仪式即告离婚。
三、公正、秩序、和谐的目标追求
人类学家布朗在解读社会习俗的“功能”时,特别强调它在整个社会体系运转时对社会生活的贡献——有利于社会实现公正、秩序、和谐[6](P204—205)。事实上,公正、秩序、和谐是东西方文化共同的价值诉求,三者间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在荷马史诗中,表达正义、公正之意的词语,原本就预示着一种基本的和谐的秩序,这种秩序既是自然性的,也是社会性的,同时也是人格化的。亚里士多德把正义、公正看作是最高的自然秩序,同时也说,虽然正义对不同社会角色的公民要求不同,但它对所有公民来说都是一种必备美德。我们无法想象,一个脱离了公平正义,只留下强者说了算的社会,如何能够建立起运转自如的社会和谐秩序。
少数民族的先民们虽然不了解希腊人的哲学智慧,但数千年来,他们从民族的演变史和社会生活中,通过切身经验,感受到社会公正、秩序与和谐的重要性,认识到实现正义、创建秩序与和谐的环境就必须要有规则。各少数民族在这一方面都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
(一)公正
少数民族法文化的公正性集中体现在调解案件的仲裁者身上。如前所述,这些仲裁者不是国家行政权力指派的,也不是由民众投票选举产生的,而是民众法律生活中自然地涌现出来的。例如,闻名凉山彝族的“德古阿莫”都是一些大智大勇、大仁大义的人,彝人民众几乎视他们为公正的化身。凉山越西县有一位健在的盲人德古海乃,在凉山州的越西、昭觉、美姑等相邻三县交界的十余个行政区范围内很有名,人们牵着马去接他调解纠纷,甚至政府解决不了的案件都由他处理好了。他们在家支与冤家之间、不同等级之间、不同民族之间表现出的公正、无私和宽宏大度,常常使我们感到惊奇。
(二)秩序
一方面,公正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后果。秩序安排如果能带来社会公正,那它就是和谐的。在少数民族地区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上都存在这样一种秩序精神。例如,在清代人工林业发达的贵州苗族文斗寨,契约活动蔓延得极其广远和长久,村民们在寨内和寨外都有着各种契约关系。当时,山林租佃和山林买卖活动几乎把绝大多数文斗家庭都卷入到契约关系中,普通民众的社会经济行为也受到契约的影响和制约,契约规范成为这个小型区域社会法秩序的主体部分。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发现,清代这一地区秩序的产生主要不是靠规范与规范之间的互动,而是需要靠规范与社会诸因素之间的互动。人们为了谋求经济或安全等方面的保障,不得不与他人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于是契约这一形式被广泛采用,不仅规范了经济活动,还被引入到纠纷调解、订立禁约等方面,而且一些社会生活也依靠契约关系来支撑并通过“约”的形式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清代基层社会生活已呈现出议约化的现象。契约本身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以契约为形式订立特定的禁约,这意味着禁约对缔约人的约束也是一种契约的义务。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习惯法也重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治盗防匪,对于违反有关规定的处罚也较重。例如,贵州马黑寨为清代永丰州与册亨州之分界,地处要冲,有盘江航运之利,社会治安尤为重要,布依族人充分运用乡规民约习惯法的作用,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广西龙胜龙脊十三寨道光初年的《会议禁约》是一典型例证,条款订得细密,规定:盗窃猪牛者罚钱X千,如违送官究治;盗偷布帛鹅羊者罚钱X千,如违处置。融水苗寨“依直”(埋岩会议)规定:谁偷了别人家东西,一经发现,就要他捉自己家里最大的一头猪来杀,然后切成一两左右的扁方肉片,用竹条串起来,并边敲锣边说“我错了,以后我改,你们千万不要学我呵,”[7](P183) 这样谁也不敢小偷小摸了。由此可见,少数民族地区在运用习惯法过程中创造了一种社会治安综合管理的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和谐
和谐是众多元素的完善统一,各少数民族法文化中蕴含着丰富而有益的和谐因子,而且在历史中已被实践所证实。
少数民族普遍信仰万物皆有灵,神灵无处不在。如果人类过度贪婪,打破人与自然共生的和谐状态,万物必显灵,使人生出病痛、遇上灾祸。正因如此,各种保护自然的习惯性规范形成了。羌族习惯法规定森林由专人看护,禁猎季节切勿打猎,如若违反则罚款,情节严重的施以重罚。纳西族地区神山中的大栗树不得任意砍伐和践踏,据说只要动它的一片叶子都会招来莫大的灾难。傣族禁约规定“禁止射猎飞入村寨的鸟类,用枪去打停在别人谷堆上的鸟,罚银四两八钱四分;用枪去打停落在已割的稻谷上的鸟,罚银三两六钱三分;用枪去打停落在别人屋顶上的鸟,罚银三两六钱三分。”[8] 苗族传统“理词”中说:山林常青獐鹿多,江河长流鱼儿多;不准打别人河里的鱼圈、毁别人坡上的捕雀山。[8] 云南白族长期保存着保护动物的习俗。鹤庆县曾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由县长亲自颁布六禁,并勒石成碑,立于县城。其六禁是:“禁宰耕牛、禁烹家犬、禁卖鳅鳝、禁毒鱼虾、禁打春鸟、禁采树尖。”[8] 这些规范在主观上表达出人们害怕自然惩罚的恐惧以及善待自然的愿望,在客观上实现了人与自然互惠互利、和睦相处,达到保护自然资源多样性与保持生态环境平衡的效果。这种古朴的自然意识,也凸现了民族法文化的优秀层面。
许多少数民族习惯性规范对人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都予以全面而周到的关照,这些规范协调个人与集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等各种社会关系,指导人们的行动,稳定民族的生活秩序,促使社会安定和发展。例如,羌族在议话坪共同讨论、决定社会事务的习惯由来已久,并逐渐形成一套具有约束力的制度。一些小的纠纷一般通过家族内部协调解决,但杀人、放火、偷盗、重伤、村寨之间的纠纷、械斗以及触犯习惯法的其他严重行为都要在议话坪上通过公众讨论决定如何处理,并在此执行。苗族的议榔会议、彝族的家支大会与其性质与作用都有类似之处。苗族村寨至今还沿用着一种叫“罚3个100”的处罚方式,对维护地方治安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具体内容视不同情况而定,一般是罚肉100斤、米100斤、酒100斤,也有的各增加20,罚为120斤肉、120斤米、120斤酒,还有“罚4个120”的,即罚120斤酒、120元现金、120斤糯米和120响的鞭炮,用于请全村老小会餐一顿,以表示对该行为予以足够的惩罚以及表达行为人悔改的决心。
另外,各少数民族法文化所体现出来的群体性,决定了其对社会保障事业、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的关照,以及对修桥筑路等公共、公益事业的提倡。布依族素来有济困扶贫的传统,对鳏寡孤独、老弱病残以及丧失劳动力者特别关心,寨内村民乐于捐资、捐物或轮流扶养,并已形成制度化,即有房归房,无房归族,无族归众。苗族有一种叫“合会”的民间借贷形式,也体现村民互助的精神:合会由困难户发起,担任会首,邀数十人参加,每人每次出一定数额的会款,第一次会款归会首所得,以后每隔一段时间集款一次,获得会款的秩序,由大家商量决定,也会适当考虑各户的经济状况。“合会”既具有借贷的特征,又含有社会保障的意义,其中具体实施细则由参加人协商合意决定,执行起来比较容易。
四、余论
少数民族法文化中保留了许多人类本真的东西。例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在贵州册亨县者冲乡岩洞寨大路边立的乡规民约碑,内容主要涉及社会风尚,提倡良风美俗、济困扶贫、互相帮助、友善待人、防盗防匪、禁赌禁奸等。该民约以“五伦”人道为首款,把儒家宗法人伦之道演变为具体的行为规范,这是布依族人的创造,在这里,儒家精神融合在乡土社会的行为规范之中,民约不仅惩恶,而且扬善,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诚信、尊重、宽容,凸显了布依族人对和谐有序社会和安居乐业生活的追求。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背景,造成布依族人原始民主精神的存留,这恰恰沟通了布依族人同儒家原创文化的自然关系,折射出强烈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和人文关怀。
今天,许多学者热衷于讨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其实,我们只要出去走一走(社会调查),就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认识。所以,我们研究中国法律传统时,“不应仅仅停留于古代经典,还需要学习人类学学者,‘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出书斋,做艰苦的田野工作,去发现远古时代传承下来,尚存活在人们心中的原创智慧和原创文化因素。”[9] 因为少数民族法文化是人类法制文明的活化石,保留了许多“原始经验”、“原始智慧”的特征,而建构法治社会所需的一些原则、规则都能从这些经验、智慧和本真中获得一定的启发。解读少数民族法文化中的原创性智慧,将帮助我们看清现代法治构建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异化现象,寻找到人类本真和原创的智慧因子,进而思考现代法治进路的多元性和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