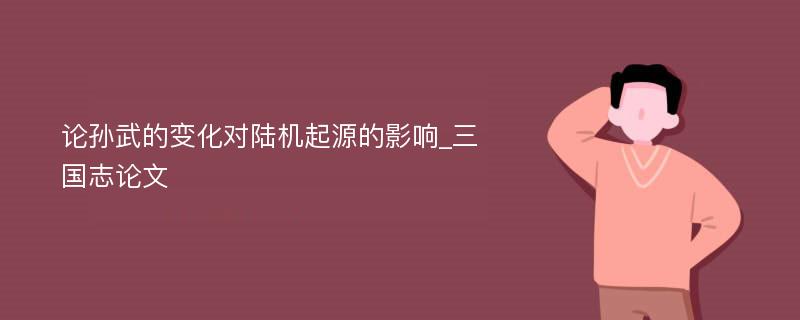
论孙吴士风的变迁对陆机出处之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孙吴论文,处之论文,陆机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太康末年起,陆机在十余年的仕晋生涯中,先是因与贾谧亲善,而为世人所讥;在八王 之乱中,赵王伦篡位时,他参与劝进事宜;其后他又驱驰于成都王麾下,因谮而死。当其时 , 张翰、顾荣等江东士人大多不约而同地南归吴会。他们还曾试图劝说陆机与之同归故里,但 “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1]。陆机被害后,孙惠与朱诞书曰:“马援择君 ,凡人所闻,不意三陆相携暴朝,杀身伤名,可为悼叹。”[2]点明了陆机与其它江东士人 在出处问题上的分歧,“杀身伤名”一语,则表达了孙惠对陆机的生命殒灭和名节蒙尘的双 重惋惜。陆机在乱世不能激流勇退,先后投靠佞臣贼党,可见其仕进求名之念甚切,而固节守操之 心几无。其原因在于陆机从变化了的孙吴士风中接受了一些新观念的熏陶,而入洛以后,更 沾染了当时对于功名时势的流行观念。
一、厉俗明教:江东士人好议论、重名节的传统
东汉以来,清议之风盛行,桓灵之间,尤以品评人物著名者为郭泰、许劭。史称郭泰“性 明知人,好奖训士类”[3],又许劭与许靖“好共覈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 俗有月旦评焉”(《后汉书》本传)。在汉末清议风气的影响下,孙吴士人亦好为议论。陆机 《辩亡论》曰:“奇伟则虞翻、陆绩、张温、张惇以讽议举正。”[4]虞、张、陆等人均出 自江东世家大族,诸人均好为议论,以正时俗。虞翻曾斥糜芳“失忠与信,何以事君?”(《 三国志》本传)陆绩与荆州庞统友善,并曾与统相约:天下太平之后,与庞统共料四海之士 。可见其对于人物品评的兴趣。他曾反对“今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惟尚武”(《三国 志 》本传),正可窥见其以儒家正统议论时弊的特点。张温更是以“亢臧否之谭,效褒贬之义 ”(《三国志》本传)著名。
在品评人物的风气大为盛行的同时,名士奖拔后进、交游结党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如顾劭 之拔举丁谞、张秉、吴粲、殷礼诸人于幽贱,又史称顾劭广交四海名士:“自州郡庶几及 四方人士,往来相见,或言议而去,或结厚而别”(《三国志》本传),因此世以劭为知人。 又虞翻曾拔举丁览、徐陵等人,其子忠、耸皆好识人物。这种风气之甚之烈,甚至成为风俗 。《晋书·虞预传》称:“余姚风俗,各有朋党。宗人共荐(虞)预为县功曹,欲使沙汰秽浊 。”葛洪指出“汉之末年,吴之季世……举士也必附己者为前,取人也必多党者为决”[5] ,议论交游之风,如果不能保证公正的品评标准,势必产生党同伐异之弊,他是从反面揭示 了 孙吴交游风气之盛。
与清议精神生息相关的,是士人的操行节义观念。如许劭之简别清浊,与其自身之崇尚名 节是互为表里的。而其议论,又无疑能敦促士人改操饰行。清议精神在孙吴也同样起到了砥 砺士节的作用。
分析孙吴士人的名节观念,必须首先回顾吴地士风之传统。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说,吴有 太伯之三让:据《史记》[6],吴太伯、弟仲雍为周太王之子,王季历之兄。季历贤,有圣 子昌,太王欲立季历和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以避季历。太伯三让的文化积淀 ,势必对士人的观念产生深刻影响,使得以隐逸节义相尚,成为吴地士风的重要特色。如陆 机《吴趋行》也以“泰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陆机集》卷六)为吴地文化传统之源头所 在。又如虞翻在与王朗论及会稽英贤时,认为“昔越王翳让位,逃于巫山之穴,越人熏而出 之,斯非太伯之俦邪?”(《三国志·虞翻传》裴注引《会稽典录》)可见,吴越传统文化中 崇尚名节廉让的观念对于士人有着深刻影响。
孙吴初年士人对汉末清议精神的张扬,又进一步强化了士人的节操观念。清议人士的节义 风概往往表现为家风闾德。如张温姐妹以节烈著称:“温姊妹三人皆有节行,为温事,已嫁 者皆见录夺。其中妹先适顾承,官以许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饮药而死。吴朝嘉叹,乡人图 画 ,为之赞颂云。”(《三国志·张温传》裴注引《文士传》)又如陆绩之女郁生适张温弟白, 张白迁死异邦后,郁生“抗声昭节,义形于色,冠盖交横,誓而不许”(《三国志·张温传 》裴注引《姚信集》)。又据史,“故吴之风俗相驱以急,言论弹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 之丧者,往往致毁以死。”[7]这既表明了清议与名节之关系,又反映出孙吴崇尚名节的激 烈 程度。这种砥砺操行的风气,甚至到了晋代以后仍然可见其流风余韵。如东晋苏峻之乱中, 江东士人或如陆晔之“随帝在石头,举动方正,不以凶威变节”(《晋书》本传),丁潭之“ 及侍中钟雅、刘超等随从不离帝侧”(《晋书》本传),忠心护驾,或如孔坦、陶回等谋议出 兵以保帝室。此时中原士人能不改节操者寥寥无几,江东士人却“并能保全名节,善始令终 ”(《晋书·孔愉丁潭传论》),可见孙吴崇尚士节观念之影响深远。
二、扬郭抑许:陆氏家族与江东新兴士风的萌芽
(一)扬郭抑许之论的产生
孙吴士风就其整体而言,继承了东汉经明行修的传统,是故较中原文化为保守,[8]但随着 时代的发展,士人的行为模式、立身准则等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在孙吴士风的变迁中,暨艳事件的发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暨艳由张温引致而为尚书, 其人“性狷厉,好为清议,见时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三国志》本传) ,于是弹射百僚,贬高就下,因为树敌太多,反遭当事人诽谤,最终导致暨艳及选曹郎徐彪 之自杀,张温亦因平素与艳、彪观点相同,书信往来频繁,而获罪被废。张温之被废,固然 一方面因为孙权嫌其声名太盛,恐终不为己用,但另一方面他与暨艳共为清议,沙汰清浊, 是 一重要因素。正如诸葛亮分析张温获罪原因云:“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 。”(《三国志·张温传》裴注引《会稽典录》)
暨艳事件的发生,透露了臧否人物的清议风气开始受到抑制的消息。清议本应识别清浊, 对人物的品评包括褒赞和非难两方面的内容,然而暨艳等人因好为清议,揭发他人过失而获 罪 ,表明当时对于人物品评,有要求扬人之善,反对贬人之恶的倾向。从孙吴士人对暨艳事件 的评论,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士人开始对汉末清议之风进行反思。
史载,因为尚书暨艳盛明臧否,扬人之失,陆机从祖陆瑁致书暨艳曰:“若令善恶异流, 贵 汝颍月旦之评,诚可以厉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远模仲尼之泛爱,中则郭泰之弘济,近 有益于大道也。”(《三国志·陆瑁传》)
陆瑁对于暨艳的劝告,反映出孙吴社会思潮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新动向:将好为人物品评的 许、郭两人分而论之,反对许劭的月旦之评,却提倡郭泰之弘济。若论许、郭之别,《续谈 助》卷四殷芸《小说》引《许劭列传》曰:“自汉中叶以来,其状人取士,援引扶持,进导 招致,则有郭林宗。若其看形色,目童龀,断冤滞,摘虚名,诚未有如劭之懿也。尝以简别 清浊为务。”[9]则许劭主简别清浊,而郭泰则重扶持士人。孙吴士人在取则郭泰这一点上 ,并无异议。与郭泰风概类似者,如吴郡顾劭,颍川周昭称其“《论语》言‘夫子恂恂然善 诱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顾)豫章有之矣……是以人无幽滞而风俗厚焉” (《三国志·张顾诸葛步传论》)。他指出顾劭是以赞誉人物的方式施行教化。周昭还论及当 时士人致祸之由曰:“古今贤士大夫所以失名丧身倾家害国者……急论议一也……急论议则 伤人。”周昭重视顾劭之奖拔人物而非议“急论议者”,可知他同样将许郭分而论之,并且 伸郭屈许。
对于许郭有所轩轾的说法,又可见于陆机祖父陆逊与诸葛恪的讨论中。据史,“初,暨艳 造营府之论,逊谏戒之,以为必祸。又谓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 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于上,意藏于下,非安德之基也”(《三国志·陆逊传》),由此不难 看出,陆逊亦倡郭泰弘济之风。诸葛恪知陆逊不满于自己的沙汰清浊,因此他与陆逊书,责 难清议之风,所发者实为陆逊之观点:“自汉末以来,中国士大夫如许子将辈,所以更相谤 汕,或至于祸,原其本起,非为大仇,惟坐克己不能尽如礼,而责人专以正义。”(《三国 志·诸葛恪传》)这里对许子将的批评恰与陆逊之扶持士人之说相辅相成,在扬郭抑许这一 点上,陆逊之观点与陆瑁等人如出一辙。
伸郭屈许的观点之产生,是以“弃瑕录用”的现实为背景的。当汉末群雄纷争之际,世好 纵横,弃瑕录用的现象较具普遍性。以襄阳庞统而言,统“性好人伦,勤于长养。每所称述 ,多过其才,时人怪而问之,统答曰:‘当今天下大乱,雅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方欲 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谭即声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为善者少矣。”(《三国志》本传) 可见对于士人以奖掖为急、不求全责备的做法,并非孙吴独有。孙吴士人也正是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伸郭屈许的理论。如陆瑁以为:“今王业始建,将一大统,此乃汉高弃瑕录用之时也 。”(《三国志》本传)诸葛恪与丞相陆逊书亦云:“杨敬叔传述清论,以为方今人物凋尽, 守 德业者不能复几,宜相左右,更为辅车,上熙国事,下相珍惜。”可见世积乱离、人才寥落 是陆逊等人重郭泰风概的原因。朱据反对举清厉浊,也是由于“天下未安,宜以功覆过,弃 瑕举用”(《三国志》本传)。
“弃瑕举用”的说法,提示了伸郭屈许的社会思潮对士人的名节观念可能产生的影响。因 为弃瑕录用之说,近于曹操著名的“唯才是举”令。其建安十五年诏指出:“今天下尚未定 ,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三国志·武帝纪》)十九年令又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进取,进 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而陈平定汉业。”(《三国志·武帝纪》)陈平一事, 可作汉高弃瑕录用之佳例。这正说明了伸郭屈许的社会思潮在孙吴的产生,是沾染了曹魏新 兴思潮的结果。当然,孙吴士人重“弃瑕录用”,并没有曹魏走得那么远,他们在时势论之 外,又援引孔子等儒家先贤之说进行论证,如陆瑁曰:“夫圣人嘉善矜愚,忘过记功……宜 远模仲尼之泛爱。”(《三国志》本传)又诸葛恪认为:“仲尼不以数子之不备而引以为友, 不以人所短弃人所人也。”(《三国志》本传)可见伸郭屈许,并没有导致儒家道德原则的全 面崩溃。
(二)孙吴士风的变化
对于汉末清议精神的反拨,还是多多少少地带来了孙吴士风的变化。以陆氏为代表的孙吴 士人伸郭屈许,为与清议密切相关的士节观念的变化打开了一个缺口。不仅如此,重郭轻许 ,势必导致士人热衷于求名逐誉而忽视砥砺节操,必将使得“道德名望”与“立功立事”这 两项本应并行不悖的品质,在不同的士人身上发生分化。对一部分士人来说,功名进取之心 将日益强烈,道德操行观念则有可能相对趋于淡漠。
吴末晋初江东士人对功名进取的热衷,可以从当时思想界的一些争论中看出。关于君臣遇 合的讨论即是其一。太康中,扬州别驾陈总为华谭饯行,因问曰:“思贤之主以求才为务, 进取之士以功名为先,何仲舒不仕武帝之朝,贾谊失分汉文之时?此吴晋之滞论,可辩此理 而后别。”(《晋书·华谭传》)这一论题,讨论士人何以不被君王赏识任用,而被称为“吴 晋之滞论”,可见它已成为当时士人所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又如,丹阳纪瞻举秀才,尚书 郎 陆机策试之,其中一策即为:“夫成功之君勤于求才,立名之士急于招世,理无世不对,而 事千载恒背。古之兴王何道而如彼,后之衰世何阙而如此?”(《晋书·纪瞻传》)足证此类 君臣遇合的问题,确实为士人所密切关注。这样的问题成为热点,其中的原因之一,当为士 人求进之心驱使所致。而华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更清楚地表明吴士对儒家成说的突破。华 以为“承统之王,或是中才,或复凡人……虽有求才之名而无求才之实。”如此客观理性地 分析君王的才能,以为历世不乏才能凡庸之主,其逻辑归宿必然是对忠君观念的动摇。在作 为士人立身准则的儒家道德观念的系统中,任何一环的突破都有可能导致整个体系的动摇。 君臣之节的恪守如果被附加了条件,那么去就大义等等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三、立功立事:陆氏家风的分化与陆机的选择
从孙吴士风的总体特征来看,新兴士风的萌芽并未充分成长起来,士人功名进取之心的增 强,也并未改变德行节操的基本框架。但对具体的士人如陆机而言,这种影响却可能决定其 整个价值体系。
陆氏家族向来被视为忠义之门。陆机之七世祖陆续因节操卓著而名列《后汉书·独行 列传》,其主要事迹为:会稽太守尹兴名列谋反名单,陆续与诸郡吏诣洛阳狱就考,续肌肉 消烂 ,终无异辞,最终尹兴一案得以昭雪。陆续极重砥砺操行,反映出陆机家风中的东汉士人风 操传统的积淀,是较为深厚的。这样的家风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代代相传下去了。陆绩之立 身处世,正可鲜明地看出乃祖节操的影响。即便是主伸郭屈许之论的陆逊,也未尝没有奉守 儒教的气息。如其时曹魏流行刑名法治思潮,丁仪、刘廙等人有刑礼之论,陆逊斥责曰: “礼之长于刑久矣,廙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皆非也。”他对当时流行思潮之背离先 圣教导,颇为不满。直至东晋之世,陆机之从弟晔被誉为“清操忠贞,历职显允,且其兄弟 事君如父,忧国如家,岁寒不凋,体自门风”(《晋书》本传)。可以说,陆氏家风就其主流 而言 ,可谓清操忠贞。
但是暨艳事件发生后,反对其简别清浊之举,提出扬郭抑许之论者,陆氏家族有陆逊、陆 瑁两人。变化了的时代思潮还是在陆氏家风中留下了烙印。这一点,从陆抗、陆喜的人格特 征的区别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据《晋书·吾彦传》,吴郡吾彦出身寒微,初为小将,跟 随吴大司马陆抗,抗奇其勇略,遂设法拔用之。然吾彦仕晋后,武帝问彦:“陆喜、陆抗 二人谁多也?”彦对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此答颇令陆机兄 弟恚怒。吾彦对陆抗、陆喜二人之评价虽然触怒了陆机兄弟,但其议论本身,似不无根据。 这一说法揭示了陆氏家风的复杂性。按照儒家的人格理想,立功立事与道德名望应该是合二 而一的,然而吾彦认为抗、喜二人各有偏长,便暗示了陆氏家风中可能存在着多元的道德观 念和价值取向。陆机之父陆抗确实功名业绩显著,而道德名望稍逊。观其立身行迹,如“抗 之克步阐也,诛及婴孩,识道者尤之曰:后世必受其殃”(《三国志·陆逊传》裴注引《机 云别传》)。陆抗克平步阐,诚为巨勋;诛及婴孩,则于儒家仁义有亏。而陆抗之从兄弟陆 喜,却以道德名望著称。陆喜其人好为清议,作《西州清论》传于世,其中之《较论品格篇 》认为薛莹有愧于第一国士之称,其根据为当时孙皓政权暴虐无道,有识之士大多高蹈出世 ,薛莹却身仕乱朝而显名,故其品必不能高。对于薛莹之出处,三国史臣亦讥其“于暴酷之 朝,屡登显列,君子殆诸”(《三国志·薛莹传论》)儒家传统思想有关士人出处去就的原则 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泰伯》)陆喜是反对显名于乱世的,他对薛莹的评价不高,也正因为薛的行为违悖 了这一传统人格标准。事实上对是否出仕乱朝的选择,正表明了士人对功名进取和道德名望 孰轻孰重的看法。陆喜、陆抗二人对道德名望和立功立事的各有所重,正显示了孙吴伸郭抑 许之风对陆抗的价值观念的影响。
陆机在去就问题上所作的选择,与其从父陆喜的观念恰恰相反,而接近于其父陆抗。在兼 容了重视功名和砥砺操行的多元取向的家风中,陆机更多地关注立功立事的追求,而在一定 程度上忽略了对道德节操的涵养。从陆机入洛以后的立身行事中,已经很难看到东汉士人的 廉退之节了。从其作品来看,他除了在诗文中反复地吟咏“行矣勉良图,使尔修名立”(《 遨游出西城》,《陆机集》卷五)的志向以外,其怀念入侍东宫生涯时云:“玄冕无丑士, 冶 服使我妍。”(《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陆机集》卷五)较为独特地刻划了其仕进之喜悦 。他在《五等论》中力主五等制,反对郡县制的一个重要依据即为:“盖企及进取,仕子之 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进取之情锐,而安民之誉迟。”(《陆机集》卷十)在认 同了士人的功名之心的前提下,他甚至已经承认了仕子之进取心甚于安民心的合理性。
四、乘时借势:陆机对西晋士风的沾染
陆机兄弟入洛以后,热心学习包括玄学在内的中原文化,乃至有陆云夜遇王弼之精魂,与 之共谈《老子》,因而谈《老》殊进之传说。[10]可以想见,西晋士人的立身原则、价值观 念,必然对陆机兄弟的思想产生冲击。
西晋政权的建立,是司马氏违背儒家礼教,篡夺曹魏政权的结果。统治者在忠义道德上的 尴尬处境,不仅使得政权本身邪正不分,而且导致全社会缺乏弘扬儒家忠义观念的政治基础 ,士人的德行节操便由此颓坏。[11]西晋之初,世务荣进。庾峻因此上疏抗论“普天之下, 先竞而后让;举世之士,有进而无退”(《晋书·庾峻传》)的社会现象。刘寔亦因世多进 趣而作《崇让论》。贾谧之“二十四友”,可以说是进竞士风的最集中的体现。史称“(贾 谧)开阁延宾,海内辐凑,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晋书·贾谧传》)。这 是一个热衷于功名利禄的文人团体。身居其中的潘岳即认为“顾常以为士之生也,非至圣无 轨微妙玄通者,则必立功立事”(《晋书》本传),史又称其性轻躁趋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 ,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则潘岳其人求进之心甚切,廉让气节全无。正因为陆机的价 值观念中已经打下了重功名轻士节的基础,他入洛后不久,便投身于这样一个为世所讥的圈 子。这些文人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必然进一步地强化了陆机的功名之心,而淡化了他的节 操 观念。
在功名仕进之心的推动下,促使陆机不避危祸而效力于诸王的一个观念上的原因,是陆机 对所谓时势的看法。其《豪士赋序》曰:“是故苟时启于天,理尽于人,庸夫可以济圣贤之 功 ,斗筲可以定烈士之业。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盖得之于时世也。”(《陆机集 》卷一)陆机作《豪士赋》的本意是讥刺齐王冏之骄纵,但是他在分析齐王得势原因的过程 中,却提出了乘时得势对于建功立名的意义。这种乘时论的形成,亦与陆机所受的西晋社会 思潮的影响密不可分。
西晋时期,门阀制度逐步形成,孤寒有才之士进取无门,因此多有作不平之鸣者。如张载 《榷论》、王沈《释时论》、蔡洪《孤奋论》等文,其主旨均在抨击门阀制度之埋没人 才。如王沈《释时论》反对“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晋书》本传),张载《榷论》则痛斥 “今士循常习故,规行矩步,积阶级,累阀阅,碌碌然以取世资”(《晋书》本传)的现象。 当世重阀阅,使得寒士体会到于守平之时建功立业的艰难,由此滋生出对纵横之世的向往。 ①从对门阀制度的思考、批判出发,士人对时势与仕进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张载《 榷论》开宗明义曰:“夫贤人君子将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时,曷由致之哉!” 这一看法,与陆机之“得之于时势”的观点,可谓如出一辙。张载又进一步指出:“时平则 才伏,乱世则奇用……有事之世易为功,无为之时难为名也。”王沈《释时论》也同样指出 才士建功于乱世的规律:“英奇奋于纵横之世,贤智显于霸王之初。”
这些抨击门阀制度的理论,自然地导出了功名建立于时运之上的观点,并且更进一步地推 出寒士只有在乱世才能驰骋一己之才的结论。张载等人作出了这样的分析,然而他们本身并 没有躬行之。如王沈因当时王政陵迟,君子多退而穷处,遂终于里闾。张载亦因世乱而称疾 归家。这种思潮却深刻地影响了陆机之立身行事。②陆机不仅从理论上认识到了乘时借势以 建 功立业的重要,而且在实践中贯彻其凭藉乱世以驰骋才智的思想。他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及 时 抽身的机会:赵王伦败后,齐王冏收陆机等人付延尉,赖成都王颖、吴王晏之救理而免祸 ,是时南士顾荣等人劝机还吴,陆机未从;太安二年,司马颖、颙讨长沙王乂,颖任用陆 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陆机此时已深知羁旅入宦的艰难,乡人孙惠亦劝其让都督于王粹 ,然而陆机踌躇再三,终于还是赴命了。
很多学者注意到江东儒学传统和中原新兴玄风都对陆机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产生了影响 。③本文试图从江东士风的变迁中找到陆机接受北方新思潮的依据,并解释何以新兴思想的 萌 芽未能改变江东士风的基本特征,即使是陆机的立身处事异于其他江东士人。本文通过追溯 陆机关于出处去就观念的家族渊源,发现孙吴数十年间,经明行修的江东学风还是或多或少 地受到了新兴思潮的影响,陆氏家族中陆瑁、陆逊等人在孙吴士风的变革中得风气之先,陆 氏家风遂产生了陆喜尚道德名望和陆抗重立功立事的分化,陆机秉承了乃父之风而重视功名 进取。家族文化的多重机缘,决定了孙吴士风的转变最集中地体现在陆机身上,使得陆机很 快接受了中原新兴士风的影响,陆机趋利求进的行为方式遂成为江东士人中的一个较为独特 的现象。
①西汉士人早已有类似的观念,如东方朔《答客难》云:“(今)圣帝德流,天下震慴,诸 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与 不肖,何以异哉?”(《文选》卷四十五)西晋士人之所以与汉人有类似的感慨,不仅因为西 晋天下一统的局势与西汉相同,更因为西晋门阀制度对有才寒士的压抑。
②这不仅由于时势之论与陆机的功名之心非常契合,还与西晋吴士在门阀社会中的地位有 关 。史称永康初,州举丹阳纪瞻为寒素。据《晋书·李重传》,西晋寒素的定义为:“寒素者 ,当为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纪瞻祖亮为吴尚书令,父陟为光禄大夫,父祖并官位显赫 , 但纪瞻在西晋却成为“无世祚之资”的寒素,前述吴郡蔡洪《孤奋论》(已佚)之作,很可 能即为失去了祖荫门资的江东士人而发。又《世说新语·言语》记蔡洪赴洛,洛中人讥其为 “亡国之余”,蔡洪反唇相讥,可知蔡洪亦身历亡国失路、为北人压抑之痛苦。中原寒士对 门阀制度的不满,与江东士族沦为寒门孤士的失落之间便产生了共鸣。亡国以后陆机的社会 政 治境遇,是陆机接受时势论的现实基础。
③关于陆机《文赋》的产生与洛下“言意之辩”的关系,请参看周勋初师《<文赋>写作年 代初探》,载《文史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