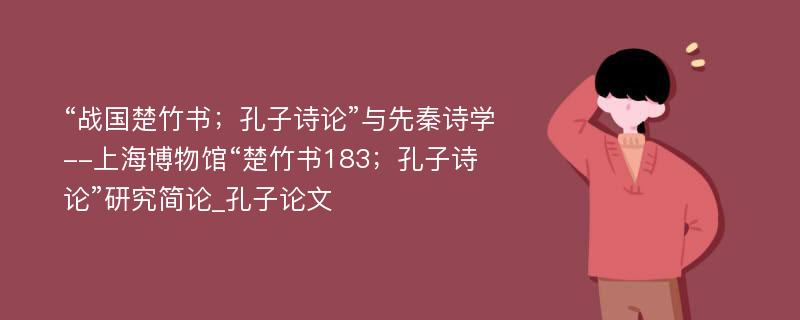
《战国楚竹书#183;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183;孔子诗论》研究浅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战国论文,浅见论文,诗学论文,诗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出版(注: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版。),在中外文史哲研究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这种震撼,随着研究的深入,只会越来越大。我们感谢这批楚简的收购者,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一睹这些国宝;我们也感谢简文的整理者,他们的创造性工作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在楚简《诗论》“热”起来之时,我觉得还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的研究者注意。
首先,要从形制上进行正确的编联。《诗论》29支竹简的编联,除了马承源先生一种外,还有好几种不同的编联(注:见《简帛研究》网站2002年1月所刊释文。)。这些编连,虽然各有所长,但共同点都是注意了文义的联系,而忽视了形制的区别。整理竹简,形制是第一位的,而文义应该是第二位的。只有在一定的形制内,才能按文义将竹简系联。《诗论》简有所谓“满写简”和“留空简”之别,我们应该“满写简”归“满写简”,“留空间”归“留空简”,才能把不同的文献区别开。不顾这一点,追求《诗序》、《讼》、《大夏》、《小夏》、《邦风》之别,只会治丝而愈棼。我认为,属于“满写简”的简1、简8至简29,全部应归诸《子羔》篇。而属于“留空简”的简2至简7,应属另一篇。两者虽同为《诗》论,记载相近,但各有不同的来源。
其次,要科学地确定《诗论》的作者。马承源先生将《诗论》全部29简命名为《孔子诗论》,实质上已认为《诗论》全部29简皆为孔子之语。其实,细加分析,《诗论》简并非全为孔子论《诗》之语。如“满写简”的如下一段:
“《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何?曰:重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10……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14[喻求女之]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樛木》福斯在君子,不[亦能时乎]?12[《汉广》不求不]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智恒乎?《鹊巢》出以百辆,不亦有离乎?《甘13[棠]思》及其人,敬爱其树,其报厚矣。甘棠之爱,以召公[所茇也。《绿衣》]囗囗囗15……[《燕燕》]……情爱也。《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樛木》之时,则以其禄也。《汉广》之智,则知不可得也。《鹊巢》之归,则离诸11[父母也。《甘棠》之报,敬]召公也。《绿衣》之忧,思故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独也(注:释文简号注于简末。缺字能补出的,用[]号表示;不能补出而可数的,用囗表示;不能补出又不可确数的,用……号表示。脱简缺文亦用[]表示。具体考释可见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
这一段是典型的解经形式。主名并不清楚。如果以简文“何”后之语为孔子的解说,“《关雎》之改”云云就是孔子解说的对象,是较孔子更为权威的《诗》说。如果以简文“何”后之语为孔子后学之语,“《关雎》之改”云云就有可能是孔子之说。比较之下,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因为在《诗论》的29简里,是孔子语都冠以“孔子曰”,此只称“曰”而不称“孔子”,应该非孔子之语。而“《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与下文简27、简29、简26的“孔子曰:《蟋蟀》知难,《螽斯》君子,《北风》不绝,人之怨子,泣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卷耳》不知人,《涉溱》其绝,《著而》士,《角枕》妇,《河水》智,……忠,《邶·柏舟》闷,《谷风》怌”形式相近(注:释文简号注于简末。缺字能补出的,用[]号表示;不能补出而可数的,用囗表示;不能补出又不可确数的,用……号表示。脱简缺文亦用[]表示。具体考释可见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颇有“一言以蔽之”的风格。正因是孔子的论断,简文才“一唱三叹”,反复阐释。所以,这一段《诗》论虽然也引证和阐释了孔子《诗》说,但其主体应是孔子弟子之说。不得称为“孔子《诗》论”。
再来看“留空简”的第一段:
口口[问于孔子]曰:“诗其犹广闻欤?善民而裕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慼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04[曰:“《小雅》是也。”“……者将何如?”曰:“《大雅》]是也。”“侑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肃雍05[显相”,以为其]……(注:释文简号注于简末。缺字能补出的,用[]号表示;不能补出而可数的,用囗表示;不能补出又不可确数的,用……号表示。脱简缺文亦用[]表示。具体考释可见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
这一段“清庙”以前是问答体,问的是孔子弟子,答的方是孔子。自“清庙”起,当是另起一段。主名有可能是孔子,也有可能是别人,尚难确定。
又如“留空简”的第三段:
……[“帝谓文王,予]怀尔明德”,何?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何]诚命之也;信矣!孔子曰:此命民夫!文王虽欲也,得乎?此命也,07志也,文王受命矣。《颂》,旁德也,多言厚,其乐安而迟,其歌伸而引,其思深而远,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02[……《小雅》]口[德]也,多言难而怨湛者也,衰也,小矣。《邦风》其纳物也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孔子曰:虽能夫03……
这一段简文先是引《诗》,然后在“何”之后解经(注:“‘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句,“诚”前抄漏了“何”字。)。解经时引孔子论《诗)之语为证,与《公羊传》、《谷梁传》解经十分相似。问题是简文引孔子语是到“文王受命矣”还是到“其声善”。如果到“其声善”,那主体就接近是孔子了;如到“文王受命矣”(注:见李零《上博楚简校读记(之一)——〈子羔〉篇“孔子诗论”部分》,《简帛研究》网站2002年1月4日。),主体则还是孔子的弟子。我比较赞成引孔子语是到“文王受命矣”为止。这样,这一段简文则是孔子的弟子解《诗》,屡引孔子《诗》论为说。
由此可知,除了孔子《诗》论外,无论是“满写简”还是“留空简”,都有非孔子《诗》论的存在,其人可能是孔子弟子,也可能是再传弟子。记载这些《诗》论的,又当是他们的后学了。因此,将这些《诗》论全部称为“孔子《诗》论”,并不十分妥当。我们在研究时,必须分清哪些是孔子《诗》论,哪些非孔子《诗》论,不然,差之毫厘,就会失之千里。
第三,要正确地释读简文。《诗论》简称《国风》为《邦风》,整理者认为《国风》原为《邦风》,是汉人避刘邦讳,改“邦”为“国”(注: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第129页。)。这是正确的。但据上引“留空简”的第三段,能不能说明《诗经》原本是《颂》、《雅》、《风》而非《风》、《雅》、《颂》呢?我以为不能。这从上引“留空简”的第一段可以证明。这一段先问“诗其犹广闻欤?善民而裕之,其用心也,将何如?”孔子答曰:“《邦风》是也。”又问:“民之有慼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其下虽有脱简,但据上下文义,我们可以补出“曰:‘《小雅》是也。’‘……者将何如?’曰:‘《大雅》”等,接上“是也。’‘侑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就可知道,孔子与弟子问对,是从《邦风》到《小雅》,再到《大雅》,再到《颂》,与今本《诗经》之序全同。但上引“留空简”的第三段又如何解释呢?我认为这是倒数。数数可以说1、2、3、4、5、6、7、8、9,也可以9、8、7、6、5、4、3、2、1,可以由小到大,也可由大到小。比如《周易·彖传》:“晋,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晋卦下坤上离。“明出地上”,释上下经卦之象,由上到下。明,指上离为火、为日;地,指下坤。“顺而丽乎大明”,释上下经卦之德,由下到上。“顺”,指下坤之性;“丽乎大明”,指上离之性。又如:“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卦下坎上震。“险以动”,是说解卦下坎有险性,上震有动性,这是由下到上。“动而免乎险”,则是由上到下了。《说卦》也是如此,既可顺数,也可逆推。其第三章是顺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水火相射,雷风相薄。”第四章则是逆推:“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注:说详廖名春《〈周易·说卦传〉错简说新考》,《文史》第51辑,中华书局2000年7月版。)所以,《风》、《雅》、《颂》既可顺数,也可倒数,不能一看到简文有倒数《颂》、《雅》、《风》就说《风》、《雅》、《颂》之序错了。
简文的《角幡》、《河水》、《墙又荠》几篇不见于今本《诗经》(注:“墙”字右旁原从章。),整理者以为佚诗。其实,《墙又荠》即今本《诗经·鄘风》的《墙有茨》,是文字假借的问题(注:在2000年9月2日召开的清华大学简帛讲读班第10次研讨会上我就曾指出过,参余瑾《清华大学简帛讲读班第10次研讨会综述》,《简帛研究》网站。)。《河水》当是《伐檀》的别名,因“河水清且涟猗”等句得名。而韦昭《国语》注以《河水》为《沔水》之误,杜预《左传》注以《河水》为佚《诗》,都是错误的。《角幡》当读为《角枕》,即《唐风·葛生》,因“角枕粲兮”一句得名。
一些人风闻《诗论》简的片言只语,并没有经过详细的考察,就匆忙地以《诗论》简为据,大作毛《序》的文章。而简文论《诗》重神,而毛《序》说《诗》重形;简文论《诗》重意,而毛《序》说《诗》重史,两者显然是两种说《诗》的风格。比如其论《甘棠》7篇,《诗论》简尽管与毛《序》论《诗》都强调礼义教化,其论《关雎》、《甘棠》、《燕燕》之义或相同,或相合。但论《樛木》、《汉广》、《鹊巢》、《绿衣》却各不相同,特别是毛《序》总是具体指出每首诗的背景、所涉及的人和事,如于《关雎》、《樛木》则称“后妃”,于《绿衣》、《燕燕》则言“卫庄姜”,于《汉广》则说“文王之道”,于《樛木》则曰“夫人”,而简文除《甘棠》一诗称举“召公”与毛《序》同外,其余则只言诗义,不说所关涉的人和事,与毛《序》有明显的不同。以此来解决毛《序》的作年,又有多少说服力呢?
因此,《诗论》简研究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文献学方面存在的问题,只有在竹简的编联、文字的隶定、字词的释读、作者和作年的探讨等基础性问题解决之后,才能进行学术史的深入发掘,才能进行义理的探讨。绕开这些问题,我们就将是把七宝楼台建立在沙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