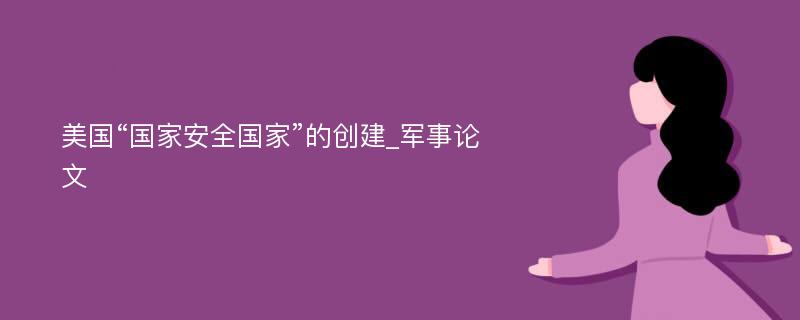
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国家安全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01-0063-28
作为持续半个世纪的世界历史事态,冷战不只在“国际政治”或者说“国家间政治”层面上发生,不只涉及外交、“热战”和危机事件,不只涉及敌对双方在政策、战略上的互动和高层人物的决策活动;冷战有其作为国内进程的内容,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参与国家的内部生存性状和政治经济发展态势,因此冷战也是一个“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过程。这就是说,冷战的政策和战略有面向国内的方面和层面。
冷战时期美国国内变化的诸多方面均可置于“国家安全国家”①概念之下加以认知和讨论。“国家安全国家”是伴随冷战而出现的美国历史上全新的事态。在冷战爆发和演进的同时,经过战后初期关于国家安全组织体制的大讨论和持续进行的政府机构的重组,美国的政府组织体制,乃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的“国家安全”理念之下,美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扩张政府对外事务和军事部门的规模并提升其重要性,在政府组织体制和政策制定程序上达成政治、军事、外交、内政、经济、情报等各职能领域和部门之间的集中统筹和全面协调,并对国内的人力、经济、意识形态和智力资源实施充分动员。内在于“国家安全国家”的范畴,或者与其相连带的还有其他一些重要趋势,包括行政部门特别是总统在对外事务上的权力扩张(所谓“帝王式总统”),常规外交职能部门(国务院)和专业外交官实际影响力的下降,军事部门和情报部门的规模扩大、影响力上升,以及政策事务中保密规则的强化等等。“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和扩张,为美国制定和推行冷战政策创造了基本的国内政治条件和制度框架,也是美国在全球主义对外战略和政策之外对冷战做出反应的基本方面和基本内容。进而可以说,对内部组织体制和动员机制的变革和建设,是美国冷战“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更广阔的美国历史长期运动看,“国家安全国家”与“福利国家”和“管理型国家”共同形成20世纪美国以“大政府”为方向的“国家构建”长期运动的三个基本向度。
一 冷战与美国的“国家构建”:相关学术史考察
长期以来,在专业性“常规智慧”支配下,美国历史学各分支中被认为最具“兰克式史学”特性的外交史研究在对冷战的考察中,对冷战的国内方面和层面缺乏与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性相称的重视。特别是作为外交史主流的现实主义的正统派,习惯于把冷战视为敌对双方在战略和政策上的决策活动和往还互动,对政策、战略、事件和人物背后的国内政治和制度因素缺乏追究探讨。②正学派一般说来更重视国内利益集团和阶级结构对对外政策的影响,但其特有的某种经济决定论倾向又导致其容易忽视政府制度、官僚政治和国家问题。③这是长期以来冷战史与“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或者state-making)问题缺乏必要关联,历史学领域里对美国“冷战国家”(Cold War State)研究不足的基本原因。
但是,另一方面,外交史以外各领域颇有一些研究,可以为“国家安全国家”的研究提供启发性的思想素材和问题意识。自马克斯·韦伯以来,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一向有注重战争和军事因素对民族国家的生成和塑造作用的研究传统,尤其是研究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查尔斯·蒂利,他着眼于战争的制造、准备和动员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各项中心制度的塑造作用,提出了“战争塑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的著名论说④,自然可有效地引申到对“冷战塑造国家”的思考中去。威廉·麦克尼尔纵论西方历史上军事技术因素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塑造和影响,在题旨上与蒂利有相通之处。⑤政治学家法里德·扎卡利亚考察了从内战后到20世纪初这段时期内美国是如何强化其将国内经济资源转化成用于对外扩张的国家力量的机制,促使研究者注意政府体制与对外政策行为相互适应的问题。⑥
在更具体、直接的方面,政治学和社会学更有不少研究可为考察“国家安全国家”提供经验研究的素材和思路。“国家安全国家”有两方面的基本问题:一是政府组织的政治学问题,即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的官僚体制、决策程序和国内政治环境的问题,主要涉及美国联邦政府中与外交、军事、情报等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机构部门;二是政治社会学问题,即“冷战国家”对国内人力、经济、智力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资源实施动员的相关问题,也就是“冷战国家”和国内社会的联结方式的问题。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政治学中有所谓“对外政策的政治学”⑦,可为历史学相关研究直接借鉴、吸收。冷战时期,一些学者(往往有政府背景)持续关注总统权和国家安全机构(特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织合理化和决策程序的效率问题,产生了大量“政策导向”的研究。⑧1950年代末,美国国会组建专门研究国家安全组织的小组委员会(杰克逊小组委员会),组织了大规模研究,留下卷帙浩繁的文献。⑨对历史的回溯性讨论往往是这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第二个方面而言,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具有政治社会学取向的一些研究注意到为冷战而进行的战争准备和动员给美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带来的剧烈变化,尤其关注“公民防务”(Civil Defense)和“国内战线”(Home Front)等问题,其研究同时触及国家机构和基层社会两个层面及其互动关系。⑩
在不同程度上脱离常规外交史研究套路的历史学研究中亦有切近“国家安全国家”主题的研究。在越南战争引发的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反思和批判中,一些人开始追究冷战启动以来美国政府制度层面上发生的变化,着重指出总统和行政部门(相对于立法部门)的权力过度膨胀,乃至于整个对外政策机制的隐秘、过度军事化和非民主特性,“国家安全国家”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开始出现。(11)丹尼尔·耶尔金在外交史之政策研究中,意识到并讨论了冷战中创生的“国家安全国家”及其背后的观念,使这个概念首次正式进入外交史研究。(12)施莱辛格开发了“帝王式总统权”(imperial presidency)这一概念,探究总统和行政部门的权力扩张与冷战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13)后文将显示,“帝王式总统权”问题与“国家安全国家”密切相关。此外,历史学家厄内斯特·梅很早就留意对外政策制定的官僚体制,曾考察二战前的总统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咨议程序,又曾直截了当地提出当代美国政府是“冷战的产物”的命题。(14)
在“国家安全国家”问题上建立更自觉清晰的问题意识并开展专门、系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1990年代以后的“新冷战史”运动为背景和条件的。“新冷战史”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在“总体冷战”(Total Cold War)观念下强化多因素综合的研究旨趣,在“外交史”和“美国史”之间、常规外交史议题与国内问题之间、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之间实现更大程度的交往互动,形成“超越外交史的冷战史”的态势。(15)“新冷战史”固然呈现出“国际史”特性(强调塑造对外政策的国际动力并注重多国档案研究)强化的趋势,但同时其中也有一些研究以各种方式指向了冷战的国内层面和方面。就此而言,最为突出的是“合作主义”(corporatism,associationalism,corporatist synthesis),该流派一方面承袭进步主义史学传统,面向国内因素,注重分析国内阶级状况、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因素对对外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较之老的修正学派在解释框架和理路上更为开放,更强调多因素综合观点。它又呼应1980年代以来比较政治学和历史社会学等领域“重新探究国家”(16)的主张,更着力于分析国家本身,将国内阶级、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政治文化与国家构建和体制变迁的问题结合起来。(17)最能体现“合作主义”流派当前学术取向的,正是其领军人物迈克尔·霍根关于杜鲁门时期的“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的巨著,它将冷战史与“国家构建”问题密切关联,有力地申述了“冷战塑造现代美国国家”的主题,使“国家安全国家”这一概念获得充实的学术内涵和理论价值。(18)当前流派纷呈、议题众多的冷战史研究中,“国家安全国家”不仅成为一个常见的术语标签,而且也成为继续被加以深入探究的主题。(19)
在对“国家安全国家”的专门研究之外,“新冷战史”中尚有众多成果可用以支撑和丰富对“国家安全国家”的深入理解和研究。比如,梅尔文·莱夫勒的冷战史巨著大体上关注对外政策问题而非内部体制问题,但其以“国家安全”概念为核心的解释框架及其研究理路上的综合性旨趣与霍根的研究多有相通之处,对理解“国家安全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深层机理当有助益。(20)此外,特别需要留意的是作为近年来冷战史研究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之一“冷战的科学史”,这些研究带有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以及意识形态史研究的问题意识,集中关注国家基于冷战目标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动员、利用和塑造,开掘了考察“国家安全国家”的一个重要维度。(21)
通过上述学术史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安全国家”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本身,而且在于它对冷战史的其他诸多问题有钩沉连带的意义,从而提供一个认识冷战的诸多面向、深化对“总体冷战”的理解和认识的重要途径。
二 二战的制度遗产与“国家安全国家”的蓝图——《埃伯斯塔特报告》
“国家安全国家”的建立,是美国历史上的全新事态,是对其自身政治传统的重大背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大部分时候,美国政治生活中居于统御地位的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观念模式:美国式“反国家主义”,旨在限制中央政府规模和权力,抑制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和官僚机构扩张;美国式“反军国主义”,戒惧和防范军队规模和势力坐大,反对在和平时期保持常备军,相应的严格奉行“文官控制军队”原则;对外政策方面的“孤立主义”,力求避免在海外卷入国际冲突,避免卷入战争。在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构建的机理和军事因素在国家构建中的作用上,历史上的美国堪称“例外”。整个19世纪美国扩张主义间歇性发作,到威尔逊时期,“国际主义”作为“孤立主义”的对立物登台亮相,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一战结束后,美国仍旧迅速退回到孤立主义。与此相应,在19世纪晚期美国经济力量迅速壮大的同时,其“nation强大,state虚弱”的局面未根本改观,仍维持着“一个因过于虚弱而不能持续汲取国内资源,同时因过于分散而不能以系统连贯的方式采取行动的国家(state)”(22)。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内部和军事部门曾有过多次创议和努力,旨在强化军种之间、外交和军事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提高动员国内资源的制度能力,但均收效不彰或归于失败,未引发国家体制的重大改观。正如厄内斯特·梅所说,直到1930年代中期,美国联邦政府的设计仍然大体上面向内部事务,掌管对外事务和军事事务的机构规模小,地位边缘。那时的华盛顿不过是个“和辛辛那提城一般的首都”(Cincinnatian capital),当然也远没有后来那般威武壮观的帝国中枢气象。(23)
美国建立“国家安全国家”的实实在在的努力,首先是作为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应而开始的。如果说战争从来就不局限于军事,那么二战比以往的任何战争都更多地涉及军事以外的内容,更多地涉及军事和非军事领域之间广泛、深刻、复杂的互动。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使美国人领略了现代总体战(Total War)的酷烈和复杂,那么二战才最终迫使美国人认真面对这一新的世界历史因素,使其在对当代世界的认知中融入了对外部威胁空前强烈的恐惧感和危机感。美国赢得了战争,但战争中暴露出美国军事指挥体制、政府决策体制和动员体制上的种种缺陷,使得美国人做出必须为因应总体战而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改变自身、重建国家体制的决断。《埃伯斯塔特报告》就是美国构筑“国家安全国家”的蓝图和纲领。
自美国加入二战以来,美国政府和军队为适应战争需要而在机构和程序上做出了诸多临时性的变更和安排,其目标和方向已经显示了其后“国家安全国家”的特性,成为战后国家制度建设的基本遗产。首先,克服组织上的本位主义,强化军种之间、军事和非军事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以提高决策和行动的效率,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陆军—海军协调委员会”(SWNCC)。其中前者是战后军队体制的最高层级的制度设施,后者则可在一定意义上视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身。其次,建立和深化对产业和人力资源实施战争动员的体制,设立了战争动员办公室(Office of War Mobilization,后更名为Office of War Mobilization and Reconversion)、战争生产委员会(WPB)、陆海军装备委员会(ANMB)等机构。此外,战争还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制度遗产,即战略情报局(OS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和其他各情报机关的建立或壮大,而现代“情报共同体”(Intelligence Community)的形成反映了情报和秘密行动的重要性增强,以及综合性战略情报相对于战场战术情报的重要性上升的趋势。(24)
在战争期间进行制度变更和制度创设的同时,美国军队和政府中展开了关于国防体制的大辩论,其内容涉及:如何看待、总结美国在二战中决策和指挥体制上的基本经验教训,如何对军事体制进行改组,乃至于战后应建立何种全面协调军事和文职部门的组织体制。这场辩论在很大程度上以1943年以后的所谓“军种战争”(service war)为表现形式,在战争后期趋于白热化。海、陆军之间为了在战后军事体制和资源分配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争相提出各自的军事体制改组方案。陆军主张合并陆、海军,建立统一的国防部和单一的军事指挥体制,对美国武装力量实施“一体化”(unification)改组;海军则主张继承二战的主要制度遗产,通过跨部门机构强化联系协调的机制,同时维持海、陆军的分立。(25)为了对抗陆军方面的改组计划,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James Forrestal)在1945年6月任命他早年的公司合伙人、老友和私人顾问费迪南德·埃伯斯塔特(Ferdinand Eberstadt),就军事和国家安全体制的改组提出规划和建议。埃伯斯塔特在战争期间曾担任陆海军装备委员会主席和战争生产委员会副主席,对军队和国家体制已有诸多定见和设想。他召集了一个研究小组,其成员多兼有广泛的商界或学界背景以及战争期间参加政府工作的经验。(26)在进行了3个月的研究、讨论、广泛的咨询之后,9月25日,埃伯斯塔特向福莱斯特尔提交了最终报告全文。10月18日,报告送呈杜鲁门总统;10月22日,由参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印发(12月17日解密)。(27)
《埃伯斯塔特报告》的内容远远超越了海军方面维护自身地位、阻止陆军改组方案的初衷。它本着“为总体战而进行总体组织”(total organization for total war)的精神,不限于军事组织体制,而是通盘考虑军队和文职部门、政府机构和私人部门,全面规划设计战后整体的国家安全组织体制以及永久性战争准备和动员体制。报告对美国在战前、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英、德等国的组织体制,予以分析和总结,申述了战后国家机构改组的必要性和基本方略。《报告》认为,自一战以来,美国在军事、外交的组织体制上基本上是失败的,其中最大的弊端在于部门和职能之间缺乏统筹协调。《报告》要求在“国务院和各军事部门之间,在军事部门和负责产业和人力资源动员的规划和执行的部门之间,以及在信息和情报的收集及其分发和使用之间,在科学研究的成果及其军事运用之间”建立制度性纽带,实现统筹协调。(28)
《报告》提出十二项具体建议:(1)将军事部门组织为三个相互协调的部,成立单独的空军;(2)建立总统亲自担任主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作为国家安全组织结构的“基石”(keystone),全面协调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的制订和执行;(3)对二战中建立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予以保留,以达成军种间的协调和协同,并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军事问题提出咨询和建议;(4)建立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Resources Board,NSRB),负责平时和战时的工业和其他民间部门的军事动员计划,并在NSRB下设一个顾问委员会,由商业界、产业界、劳工和农业组织的代表组成,以保持军事部门和民用经济部门之间的密切联系;(5)建立军备委员会(Military Munitions Board),掌管军事订货和后勤;(6)对现有的跨部门机构进行研究,以就其重组、合并和解散做出决定;(7)在科学研究和发展方面采取“积极措施”,统筹军队、学术界和产业界的科技研发活动;(8)设立军事教育和训练委员会及附属的由教育界人士参加的顾问委员会;(9)设立中央情报局,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其他部门提供所需的情报,并在各情报部门间居中统筹协调;(10)“在相互协调的各军事部的组织结构上实现最大限度的平衡”,增强军种间在行政管理、采购和后勤方面的协调;(11)在行政部门(特别是NSC和NSRB)与国会之间保持密切联系,加强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诸领域的连续性和统一性;(12)由总统或国会或者两者联合任命一个委员会,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整体研究。(29)
《埃伯斯塔特报告》的意义和重要性是多方面的。第一,《报告》以有力的方式阐述了战后美国的一个基本国家目标,即美国必须进行前所未有的“面向总体战的永久性战争准备”,为此又必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军事和外交机构实施扩张和集中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强度对国内资源在和平时期实施动员。而国家的动员和组织体制的这一根本性变化,也是美国对外政策体系完成由孤立主义向全球主义转型的一个基础和组成部分。如果不把面向国内的方面和内容排除在“战略”的概念之外的话,则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也是战后美国“大战略”的基本方面和内容。第二,《报告》以清晰具体的方式阐述了联邦政府中与对外事务相关的组织体制的基本原则,也设定了“国家安全国家”的一些主要的制度要件,如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央情报局以及NSRB等承担国内动员功能的机构,均在冷战进程中延续下来并持续演变强化,成为冷战政策运行的组织框架和制度平台。第三,《报告》申述和体现了“国家安全国家”运作方式和实践风格中的一些基本特点,强调在战争准备和动员中强化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提倡在两者之间建立沟通联系的渠道和咨议制度,吸纳包括学术界、产业界等各领域的专家及其知识资源,凸显了美国式的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凸显了对组织效率、组织技术的强调。所有这些因素均是冷战中美国动员经济、人力和智力资源的机制的重要因素,标示着美国“国家安全国家”自身的特性,也昭示了美国形态的政商关系、政学关系的特性。第四,《报告》在原则和论说上致力于维护美国的民主认同,其制度设计力求使新的国家安全组织与美国权力分割和“文官控制军队”原则相符合,并就防止战争压力下权力的过度集中和“马背上的人”控制国家的倾向提出警告。(39)就此而言,它标示了新生的“国家安全国家”与美国政治传统之间的连续性,也体现了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构造和当时的基本政治生态。
《埃伯斯塔特报告》更深远的意义可以表述为:它是申述对美国主导性政治传统构成重大偏离和震荡的“国家安全”观念的第一个、也是冷战早期最重要的纲领性文本,为美国“国家安全国家”奠定了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埃伯斯塔特报告》不只是一个方案,而且是一个论说的文本,它以大量的篇幅投入对原理和原则的讨论,而且“将原则牢固地建立在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眼光长远而广阔,思虑深入而周详。(31)特别是《报告》的分析和研究部分,可以说综合和申述了一战以来形成和壮大起来的、秉持国际主义和“自由合作主义”观点的“国家安全精英”中的共识。《埃伯斯塔特报告》的出现先于通常所认为的冷战爆发的时间,甚至先于美国对苏联的意图和性质、美苏关系的全面对抗格局做出明确判断和公开宣示,这一事实表明:无论是作为美国冷战努力的基础工程,还是作为冷战“大战略”的一个方面,《埃伯斯塔特报告》都完全有资格列入最重要的冷战史文献之中。
三 1947年《国家安全法》和1949年国防重组
战后初期,美国对其军事和对外政策组织体制予以改造,已是势在必行。这个目标和方向在国家精英阶层有着高度共识,有分歧和争议的是改造的方式和范围。《埃伯斯塔特报告》只是当时国防和政府体制问题大讨论中涌现出的各种报告和方案中的一个,而相关争议在《报告》问世后也远未结束。
当时,杜鲁门总统基于对军事指挥体制的效率、军事计划和预算的统筹管理等方面的考虑,倾向于陆军“一体化”方案,主张建立统一的国防部,与《埃伯斯塔特报告》意见相左。1945年12月19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方案,将武装力量统一到一个单一的军事建制之下,设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但是,该方案局限于军事体制,并不包括关于设置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容。(32)这个方案遭到海军方面的强烈抵制。福莱斯特尔和埃伯斯塔特进行了密集的国会游说和广泛的“公共教育”活动,力争在政府内部、国会和社会各界取得广泛支持,对总统和陆军的主张形成强有力的阻截。(33)
1946年4月到7月,国会就国家安全组织体制连续举行听证会,海军方面取得明显优势。5月13日,总统在白宫召集陆、海军部长和主要军事将领参加的会议,总统从原来坚持设立总参谋部的立场上有所退却,以图促成海、陆军做出妥协。在总统的敦促、协调之下,5月底,海、陆军部长向总统呈交一份联合报告,就双方分歧和共识予以申述。此后,总统,海、陆军部以及国会各方的协商讨论继续进行,所议范围扩展到军事体制和军种关系问题之外,各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科学研究和工业动员的组织和机制等内容上逐渐达成协议。1947年1月中旬,福莱斯特尔和陆军部长帕特森达成最终协议,总统旋即于2月26日将数易其稿后的法律草案提请国会审议,之后改组方案进入第80届国会立法程序。1947年7月26日国会通过《国家安全法》。
从《埃伯斯塔特报告》问世到1947年《国家安全法》通过,是涉及总统、各军种、各政府部门以及国会等各种制度主体的争论、游说和妥协的过程,也是改组方案的内容和范围发生扩张的过程——由军事机构的组织问题扩张为联邦政府的全面改组。《埃伯斯塔特报告》最终在各种方案中胜出,实际上被国会接受为立法蓝本。两相对照,《埃伯斯塔特报告》中的建议绝大部分被《国家安全法》采纳,以至于《国家安全法》被视为“埃伯斯塔特计划的修订版”(34)。
对照后来的诸项发展可以看出,1947年《国家安全法》(35)的确构造了“国家安全国家”的基本框架。也可以说,“国家安全国家”的诞生的确切时间可以标定为1947年《国家安全法》通过的时间。
1947年《国家安全法》最重要的产物是5个机构,分别体现了“国家安全国家”的诸项基本功能目标:集中体现国家安全事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空前的、绝对的重要性,以及体现“国家安全国家”组织制度之综合特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体现武装力量的一体化理念、成为国防部前身的“国家军事机构”(National Military Establishment);体现军队指挥系统的集中化、作为军队最高组织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承担国家和平时期对国内资源予以动员的目标和职能的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以及体现情报在国家决策体系中空前重要性,对各部门来源的情报进行汇总处理、向高层决策提供情报支持的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47年《国家安全法》最重要的产物,它由总统、国务卿、防务首长、三军部长和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主席作为法定成员组成,其职责是“就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的统筹向总统提出建议,以使各军种和政府各部门机构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事务上更有效地协作”,成为“国家安全国家”的中枢机构。在国防机构的设置上,《国家安全法》确立了空军的独立地位,并设立一个文职的“防务首长”(36)(Secretary of Defense,福莱斯特尔首任该职),统领松散的“国家军事机构”,协调具有内阁部地位的陆、海、空三个军种部,同时在防务首长办公室下使二战当中建立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继续存在,以强化军种间的协调。(37)中央情报局则接续了二战中战略情报局和战后最初的中央情报组(National Intelligence Group)的遗产(38),承担统筹、协调各部门情报活动,并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情报和建议。至于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虽然因《国家安全法》对其职责界定不清导致成立后运作乏力,旋于1950年解体,但它作为一个高级别机构,代表了国家在平时和战时动员国内经济资源为战争做永久性准备的制度目标,具有不限于其自身的方向性、标志性意义,亦足为“国家安全国家”的制度和理念遗产。
经《国家安全法》的通过和实施,美国“国家安全国家”已经具备基本形制和架构,成为确定的历史趋势,但制度变迁的历史并没有在1947年终止。此后,围绕宪法原则的贯彻以及机构设置的合理化的争论和斗争也仍然在继续,多个具体机构的组织和程序、地位和作用仍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中最初几年关于“国家军事机构”的地位和功能争议最为激烈。(39)1949年年初,前总统胡佛领导的一个国会专门委员会(40)即对国家安全组织体制予以首次全面评估,强烈申述当下“军国主义”的危险性,强调“文官控制军队”的原则,对1947年体制多有指责。(41)同时,杜鲁门总统则在体制变动的过程中致力于维护总统特权,继续推动军事体制的一体化,力主削弱军种的独立性和地位。3月,杜鲁门向国会提出修改《国家安全法》的要求。经过新一轮的争议和妥协,当年8月,《国家安全法》修正案(P.L.81~216)通过,取消了三个军种部的内阁部地位及其部长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法定成员资格,将国家军事机构转换为更具实权的国防部,并将之作为唯一的内阁部级军事部门,相应的建立了统一的军事预算体系。同时设置了在军种间承担协调职责、但没有军事指挥权力和在参联内部的否决权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修正案又赋予副总统以国家安全委员会法定成员资格,并将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厅置于总统行政办公室之下。经过1949年国防重组,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基干组织设置大体稳定,以后的制度变更大多属于在各主要机构内部的细微调整,而很少以国会立法变更的方式进行。
“国家安全国家”的初创过程是在尖锐、激烈的官僚机构的冲突和更大范围内的政治争议中进行的。第一,官僚机构和军队的部门利益、部门观点和本位主义,特别是海、陆军之间的“军种战争”,军事部门和文职部门的权力争夺,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二,作为战后美国高层政治中一个突出的情况,总统权和官僚机构部门的龃龉争执也以或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展开,“国家安全国家”的扩张和总统权的扩张呈现出复杂的张力关系。第三,美国政治传统中的反国家主义、反军国主义势力也与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和“国家安全国家”扩张的主张和趋势多有抵牾,并对其构成有效限制。第四,在政治体制(特别是总统权)中的非个人化和个人化因素之间,官僚机构的常规化、制度化律令和主要政府官员的个人立场和问政风格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凡此诸端,造成“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和以后的演进只能是在无休止的谈判和妥协过程中进行,更造成其达成的方案在文本上往往是掩盖分歧以求取暂时妥协,而多有含糊不清的用语,对诸多机构的职能和运行程序以及部门间的相互关系未能加以更为清晰的厘定,以至于为无休止的细微制度变动和非正式安排和行为留下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国家安全国家”的演进和扩张是与冷战酝酿和展开的过程相伴随的。《埃伯斯塔特报告》形成时,美国尚未对苏联的意图和性质、美苏关系的全面对抗格局做出明确判断和公开宣示,核武器因素对战略格局的重大影响尚未充分显现,冷战尚未正式启动。《报告》力求使战后国家体制与美国以权力分割为中心的政治传统之间保持更多的连续性,偏重“协调”而不是“集中”。它肯定永久性战争准备和动员造成的集中化趋势,但对其程度估计仍有不足。从“协调”原则立场出发的一些考虑和制度设计,在以后冷战危机不断出现、外部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被证明或多或少不合“时宜”。《埃伯斯塔特报告》之后,1947年发生了希腊和土耳其的危机,“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凯南的遏制理论出台;1948年发生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和柏林危机,1949年中国最终被“丢失”,苏联爆炸了其第一颗原子弹,1950年则爆发了冷战中的第一场“热战”——朝鲜战争,这一系列事件和事态持续提升冷战的强度,造成紧迫的危机态势和威胁感,为“国家安全国家”的扩张及其内部构造的进一步的集中化提供了国内政治氛围和直接的动力。
四 “国家安全”理念
“国家安全”理念是二战后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理念中的一个新的要素,是“国家安全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基础。“国家安全”观念内涵的扩张,是“国家安全国家”本身之扩张的动因和表现。“国家安全”理念的特性是对外部威胁的强烈感知和强调,对“安全”和“利益”含义的广泛的、高度综合性的界定方式,对行政权力扩张的强烈偏好,以及对组织协调和一体化的强调。
在反国家主义—反军国主义—孤立主义的三位一体模式占据美国政治生活主导地位的时代里,“安全”观念大大异于后来的冷战时代。一般而言,民族国家共同体一经出现,则其“安全”作为现实问题和主观理念也将出现。“安全”(security,safety,或者tranquility)的概念和用语在美国当然也还是有的,如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就有“免于外部危险的安全”(safety from external dangers,或者security against foreigndanger)之类的表述。(42)但长期以来美国人很少把“国家”(national)和“安全”(security)放在一起,使用“国家安全”这个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内曾有人倡议建立协调国防和对外政策的机构,1916年通过《国防法》(The National Defense Act),设国防委员会(Council of National Defense,有人认为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某种前身),亦不取“国家安全”一语。(43)
据耶尔金的语源学考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才有一些学者开始使用“国家安全”这个概念(44),但在1944年春关于军事体制问题的讨论和国会听证中,这个词还很少出现。到1945年1月间,埃伯斯塔特本人在其构想中使用的仍然是“国防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Council),而1946年4月的一个国会方案也曾提议使用“共同防御委员会”(Council of Common Defense)一语。(45)然而,到了1946年晚些时候,“国家安全”一词却广泛流行起来,而且往往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而使用的。(46)在1947年《国家安全法》问世时,“国家安全”已成为一个统御性用语,而且被嵌入该法名称本身和两个主要机构(NSC和NSRB)的名称中。
特定语词的使用和流通背后是大有意味的。正如扎卡利亚所指出的,“安全是一个伸缩性极强的概念……几乎所有对外政策行为,从为了生存而采取的小心翼翼的措施,到意在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勃勃的步骤,都可以(也的确)被说成是为了寻求安全”(47)。厄内斯特·梅的考察显示,“安全”概念的内涵在美国历史上是有一个流变过程的。从美国立国到大约19世纪晚期,历任总统大体上是从两个方面——即边界安全和确保合众国的统一——来界定“安全”的内涵的;19世纪后期,又开始加入西半球各共和国的独立和国内秩序的稳定的内容。到了冷战时期,“安全”变成了“国家安全”,用以指涉在全球范围内使“自由世界”各个国家保持独立和自由,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繁荣和健康。在此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安全”这个概念在各个阶段的共同点是,它一向被理解为既有对外成分又有面向内部的成分,尽管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时被认为是互惠的,有时被认为是相互冲突的;(48)第二,与其对“国家利益”一词的使用一样,“安全”概念被赋予越来越多的内容,有一种内涵扩张的趋势,而“国家安全”一词在1940年代中期以后的出现和广泛流行,显然是这种扩张最剧烈的一段时间;第三,在冷战以前的时代里,“安全”这个概念显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成为政策、制度体制和理念上的一个重要的统御性名号,政府机构名称中也没有出现过“安全”一词。
对“国家安全国家”的机理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要以对“国家安全”理念的理解为基础,而理解“国家安全”这个词的关键在于其综合性特征。一向以来,“安全”一词因其包含了面向国内的内容而具有比传统的“外交”、“对外政策”、“国防”等概念更广泛和更综合的特性。而“国家安全”这个新词不仅要融通外交和内政,还意味着:以往的政策理念和政府体制中惯常的各个面向的功能性划分的界限都要被打破,并加以综合统揽,如外交和军事,平时和战时,军队和文职部门,政治、经济和军事,政府—公共部门和社会—民间。这个词的这种综合特性,正与美国的政治精英在对战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认知、对美国的政府组织体制的设计以及“大战略”的规划上的基本共识相一致。《埃伯斯塔特报告》正是从“‘国家安全’这一语汇变化了的内容和范围”(49)来讨论问题的,其全部思想均指向“国家安全”作为一个认知框架的综合性特征。着力推广这个概念的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在1945年说:“我们的国家安全只有在一个十分全面和综合的范围里才能得到保障。我在这里要一以贯之地使用的是‘安全’这个词,而不是‘防务’(defense)。”(50)1946年9月,福莱斯特尔在致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的信中说:“外交和军事力量纠结在一起,划不出黑白分明的界限……一体化不仅仅是陆、海、空三军的事——它是我们的国家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政治的力量的整体综合。”(51)曾任国家安全委员会首任行政秘书的西德尼·索尔斯(Sidney Souers)在1949年提出这样的理解:“‘国家安全’也许最好被理解为一种观点,而不是政府职责的一个具体领域。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整体国家政策有三个维度,即对内政策、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就此而言,国家安全的内涵在和平时期小于作为整体的国家政策,而在战争情况下,它可以扩展到等同于全部国家政策的程度。”(52)
“国家安全”理念是在二战后期以来的“军种战争”和关于国防体制的大讨论中被促生的,《埃伯斯塔特报告》在这个理念的塑造和传播中作用突出。在此之后,随着有关苏联的意图和政策的更清晰的战略判断的做出,特别是经过凯南的遏制理论和“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国家安全”成为一种“统御性理念”(commanding idea),一种“教义”(doctrine)和“符咒”(gospel);(53)或者如霍根所说,成为一种“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作为理念和意识形态,“国家安全”有其认知的基础,即对现实的映射、认识和判断。
在战后初期,“国家安全”理念的认知基础是对“总体战”的认知。自二战爆发以来,美国军界、政府、学界和新闻界都出现了大量的对总体战的讨论,将其作为影响美国生存状态、改变美国和世界关系的重大事态。它们看到了现代总体战的军事技术特性,即“战争的机械化”或者“战争的工业化”条件下军事力量快速、远程的投放能力和空前巨大的杀伤力、破坏力。(54)核武器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国家安全精英”对总体战的认知和危机感。《埃伯斯塔特报告》的论证正是基于对“总体战”的认知,基于对其“速度和破坏力的革命性因素”的认知。它强调“美国的战后体制必须认识和反映变化了的条件”,而这种“变化了的条件”,一言以蔽之,就是“总体战”:“现代战争将交战国全部的资源投入冲突之中,陆、海、空军只不过处于国家力量的金字塔的顶端。它的物质基础在于其农田、森林和矿山,在于工厂、发电站和交通运输系统,在于管理、技术和劳动的能力。”“总体战”“要求与我们对人力、物质和精神资源的全部力量的统御相适应的组织形式”。(55)这样,现代战争的“总体战”特性决定了“国家安全”理念的综合性特征,而“国家安全”理念的综合性特征决定并反映了“国家安全国家”之组织集中化和全面动员的特性和机理。在冷战尚未展开之时,在美国尚未最终明确谁将是未来“总体战”中的对手之时,美国已经依据在二战中获得的对“总体战”的认知来考量和决定其基本国策了。或者说,以“全球遏制”为核心的冷战“大战略”中一个关键部分即关于内部体制的部分已经初告形成。
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安全”理念有了进一步的演化和扩充,而这一“演进和扩充”是与冷战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关联在一起的。在以《埃伯斯塔特报告》为代表的早期“国家安全”理念中,着眼点是为未来战争做准备,基本逻辑是一种从“总体战”的军事技术的和物质的特性出发,从军事上的迫切需要推展到非军事领域的逻辑。在冷战初期,美国人对与苏联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估计很高,这也强化着这个逻辑,1950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 68)就突出反映了这种情况。随着冷战的加剧和欧亚大陆战略平衡局面的形成,以及核武器对战争意愿的抑制作用的凸显和增强,对美苏之间全面战争的准备不再是美国冷战战略思维的唯一内容,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冷战的最终结果将取决于美苏之间在社会体制的优越性上的竞争。由此,冷战的非军事的和意识形态的特性被进一步突出和强化,冷战的文化和社会的内容也越来越多。抑或可以说,正因为冷战是“冷”的,这场冲突和竞争中的非军事方面的重要性更被加强了,“总体冷战”呈现出不同于“总体战”的、超越“总体战”的特性。这个过程也就是“国家安全”理念的内涵不断扩充的过程,美国人愈来愈倾向于超越“实体安全”(physical security),以维护美国的“核心价值”(core values)来界定其“国家安全”。(56)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表现是,“政治战”和“心理战”之类的“非军事战争形态”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意识形态的斗争即“争取心灵和头脑的竞争”走向冷战“战场”的中心地带。(57)到1960年代中期,对美国国家安全组织体制予以全面考察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已经可以提出对“总体冷战”的一个完备表述:“这场竞争是总体的——它是军事的、经济的、科学的、政治的、外交的、文化的和道德的”。(58)
“国家安全”在冷战扩张和深化的过程中成了一个概念箩筐。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在国内冷战恐慌的气氛下,“内部安全”(internal security)观念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出现;(59)而在美国构筑冷战国际同盟体系、实施对外军事援助的过程中,“共同安全”(mutual security)也在1950年代初成了一个新的政策和制度标签。由此“国家安全”观念又有了两个新的附属物。
1950年代末以后,随着美国政策体系中“全球主义”或者说“自由国际主义”的性格的彰显,(60)随着冷战剧烈地向第三世界扩散以至于达成真正的“全球冷战”局面,(61)第三世界在冷战中的地位有了突出上升,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被判定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内部发展的方向和性状成为关乎美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事项。到肯尼迪时期,“发展”和“现代化”成为与“国家安全”理念有密切关联的政策目标和政策理念,援助和发展政策更成为冷战战略的新重点。在这里,“全球冷战”的逻辑强化着“总体冷战”的逻辑;全球主义逻辑强化和扩充着“国家安全”理念,“自由国际主义”——“使民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安全”(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成为对“总体战”的认知之外的另一个塑造和扩充“国家安全”理念的基本要素。
五 冷战初期“国家安全国家”的扩张
“国家安全国家”的扩张涉及政府体制的变更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两个基本面向。就前者而言,有必要指出,“国家安全国家”的扩张是一种政府职权和业务的总体扩张,不仅涉及新的组织创制,而且包括对传统制度和职能的吸纳和改造。虽然“国家安全国家”的最主要、最明显的制度要件是联邦政府内与外交、国防、情报等相关的职能部门,但“国家安全国家”的组织活动和运行机理却不只涉及这些部门,许多在传统的、常规的原则下看似与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无关的部门也或多或少被牵涉到“国家安全”标号下的政府活动中。所以,把“国家安全国家”看做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的总合的观点是不足取的。就后者而言,“国家安全国家”不仅涉及政府组织制度的创制和变更,而且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重建。“总体冷战”观念不断深化、“国家安全”理念和国家战略目标不断扩张的过程,也是“国家安全国家”创制向政府和公共部门以外的私人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的权力渗透过程,是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建立广泛的连接纽带、以达成更大程度的嵌入性(embeddedness)的过程。
用阿隆·弗雷德伯格的概念来说,“国家安全国家”需要有相应的“权力创制”(power-creating)机制,包括旨在提高国家对国内财政资源的提取能力,动员人力以获得兵源和政府公职人员、动员产业资源以满足军备需要的政策和制度;此外还有与知识界建立广泛的制度和非制度纽带,动员和利用知识和意识形态资源,以满足“总体冷战”斗争的多方面需要。(62)“权力创制”的需要造成国家组织体制方面的变动和新设机构的产生,扩大了政府机构对非政府部门施加行政权力的能力,同时也促使政府与非政府部门建立各种制度的甚至非正式的纽带。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到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和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牵制,“国家安全国家”的演进并不是一个无限制扩张的过程,其间也有波动起伏。在具有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和竞争性民主制度的国内政治条件下,内部的政治、经济条件会对战争动员的努力构成重大障碍,来自社会的制衡力量会对政府“权力创制”的冲动构成持续的抑制。这样,正如弗雷德伯格所指出的,受到掣肘的美国宪政国家只能在诸多限制性因素之下制定有限的、其扩张性被大打折扣的“权力创制”机制。
二战以前美国动员国内产业资源以满足军事需要的能力相对薄弱,《埃伯斯塔特报告》和1947年《国家安全法》确立经济动员体制由文职部门控制和多部门协调的原则,建立了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负责政府产业动员政策的协调统筹。但该机构职权界定不清,仅有协调功能而无行政权力,且被总统担心损害其特权,导致运作低效乏力,终于在1950年解体,其权力被划归新成立的“国防动员办公室”(Office of Defense Mobilization)。(63)朝鲜战争以前,产业动员的机制停留于纸面作业,并没有建立起来。朝鲜战争扭转了二战结束以来的“复原”(demobilization)状态,加速了美国军事部署和军备建设的努力,并导致国内民意对高军费开支的总体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动员的目标和方式也发生重大转变,即从起初的主要针对克服军事物资供应的短缺瓶颈,在可能爆发战争的短期预期下为军队提供武器和装备,转变为一种超越单纯的军事后勤观念的、更具长期性的、更广泛的目标,力求从根本上扩张美国工业生产的能力,以便为美国的武装力量奠定充实的经济物质基础。为此国防动员办公室曾一度设立产业计划体制,对200多个行业确立生产指标体系,并设定相应的税收鼓励措施,以促进私人企业对薄弱生产领域的投资和生产,这一做法一直持续到杜鲁门政府任期结束。艾森豪威尔基于其自由企业理念而不断试图削弱杜鲁门时期对经济的政府干预水平,在其任期内逐步取消了大部分产业动员计划,由此至1950年代末,美国终止了一度曾经尝试建立的集中化的产业动员机制,同时放弃了战前少量的军队下属的军工企业。(64)但尽管如此,在战后高位军费和大强度军备建设的情况下,形成了以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的合同体制为主要制度工具,以非集中化为特点的产业经济动员体制。而在巨大的军备建设中生成了美国历史上全新的事物——非正式但影响力巨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65)
为冷战征集人力资源、并创造冷战的国内政治条件的努力集中于冷战初期与“普遍军事训练体制”(Universal Military Training,UMT)、“公民防务”(Civil Defense)和“国内战线”(Home Front)相关的制度和机制之上。
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和平时期不保持大规模常备军而仅维持一支小规模的职业军队的传统受到挑战,国内出现了建立普遍军训制度、以此为未来“总体战”提供兵源储备的主张和呼声(66),杜鲁门、马歇尔等政治家和军界领袖都是普遍军训制度的支持者。1947年6月,杜鲁门总统委派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提交了一个报告,力主将普训制纳入国家安全规划体系之内,基本内容是要求所有合格的男性公民都要接受为期不少于6个月的军事训练,以备战争来临时大规模征兵之需。(67)虽然冷战前十年间民间舆论对UMT支持率很高,但来自劳工组织、农业、教育界、教会和和平主义团体的社会力量始终保持了对UMT的强大反对,国会始终拖延或者回避就此举行投票,终于使UMT计划消失于无形之中。艾森豪威尔政府推出“新视野”(New Look)(68)战略之后,美国确立了倚重核武器的战略原则,对人力资源需求的迫切性一时大大下降,UMT争议走向终结。其后美国实行选择性兵役制,其军队兵源由志愿兵和义务兵共同组成。
通过实施“公民防务”计划而构筑冷战的“国内战线”,是美国为冷战而对国内基层社会实施政治动员的氛围的一项重大而持久的努力,较之于军事训练和兵役制度,这方面发展趋势似乎对美国国内社会构成更广泛深刻的影响。如何在一个具有反军国主义政治传统、军事化程度很低的国家实施对基层社会的动员,实现“深度国防”(defense in Depth),(69)是战后初期美国国家安全精英费心劳力的任务。而在原子武器这一新的强化“总体战”强度的因素日益突出的冷战初期,通过国民教育使美国公众不至于因恐惧核武器而退回孤立主义,获得公众对冷战政策的支持,同时要动员、训练、教育公众,既为核战争做准备,又为“公民防务”增加了新的目标和内容。二战期间美国已经开始建立国内社会动员的组织机制,如“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OWI)和“公民防务办公室”(Office of Civil Defense,OCD)等机构,战后的短暂复原中没有解散“信息管理”和“公民教育”等方面的相关机制。(70)1947年《国家安全法》对二战期间创建的制度加以改造,开始强化“紧急状态管理”和“国内战线的充分准备”的体制,在“防务首长办公室”下设“公民防务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Civil Defense Planning,OCDP,后于1950年3月转入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下)。作为对1949~1950年的危机气氛的反映,国会通过了《公民防务法》(Civil Defense Act of 1950,P1 81~920),创设了单独的联邦公民防务管理局(Federal Civil Defense Administration,FCDA)。该机构在1951年开始正式运作,大幅度增扩了前公民防务办公室的职责,全面掌管公民防务相关的信息管理、专业训练和公民教育计划。(71)该机构还精心构造与社会科学界、媒体乃至于好莱坞的关系,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公民国防的公众教育。它于1952年开始实施“警惕美国”运动(The "Alert America" Campaign),致力于冷战爱国主义和公民责任观念的灌输,并有意识地传播核武器的后果可以控制的思想。又实施“东河计划”(Project East River),动员研究型大学里的社会科学力量(特别是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对“恐惧管理”、“恐慌预防”和“士气监管”的手段予以研究,是当时最全面的全国性民防研究,其“恐惧管理”的理论又被整合到“警惕美国”运动之中。(72)公民防务计划由联邦政府向下延伸,到1951年各州政府内都建立了相应的常设民防管理机构,有些州(如田纳西)还通过了关于公民防务的州立法。政府部门更着力将民防机制延伸到社区层面,到1950年代前期,FCDA成功地通过社区层面的民防机构对人口中的相当大的部分(特别是都市郊区的中产阶级居民)实施了动员。(73)此外,作为推行公民防务的一个部分,联邦政府还积极推动公立教育机构以制度化方式开展国防教育,最终在1958年促成《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的通过。(74)
如果说“公民防务”和“国内阵线”意味着冷战的非军事内容在国内的体现,那么“心理战”和“政治战”就代表了心理、精神和观念的冷战在美国境外的实施。而这两方面在理念和制度上也经常是重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美国出现了诸多用以指称超越单纯军事意义的,与人类精神、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相关的“战争”形式的术语,如“观念战争”(the war of ideas)、“争取心灵和头脑的战斗”(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争取人类精神和意愿的斗争”(struggle for the minds and wills of men)、“思想战争”(thought war)、“意识形态战争”(ideological warfare)、“神经战”(nerve warfare)、“真理运动”(campaign of truth)、“教义战争”(doctrinal warfare)、语词战争(war of words)等等,最终,“心理战”(psychological warfare)和“政治战”(political warfare)两个术语成为更强势的术语标签。(75)“心理战”的实质含义与“宣传”略同,但美国人忌讳这个已经与纳粹和“共产党极权主义”联系起来的词,而多取“信息”(information)和“传播”(communication)之义。最初,冷战斗争的各种非军事手段,包括秘密行动、贸易和经济援助、武力威胁、文化和教育交流项目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被置于“心理战”的概念下加以考虑。(76)与“心理战”的综合性特征密切相关,杜鲁门时期“心理战”的制度安排也体现出多机构参与的特征,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新闻署(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IIA)、技术合作署、共同安全署、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均介入其中。1951年春,杜鲁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由副国务卿、副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长组成,并设一个全职的主任和工作班子,专门负责心理战略的开发和协调,成为“一种规划和监督冷战的总参谋部”。心理战略委员会主任列席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显示了“心理战”的重要性。(77)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初期,对心理战略的重视有增无减。1953年9月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建立“行动协调委员会”(Operation Coordinating Board),以取代先前的心理战略委员会,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心理战”相关政策和行动的协调,将“心理[战]因素注入[美国政府]的所有行动领域”。同年设立美国新闻署(U.S.Information Agencv, USIA),将杜鲁门时期存在于各机构的对外宣传业务纳入其中。(78)为避免“information agency”的称谓在海外引发该组织和情报机构的联想,其在海外的机构被冠名为“美国新闻服务局”(U.S.Information Service,USIS)。(79)
有系统的对外援助也是战后美国在“国家安全”理念下新生的政策领域,为此联邦行政机构进行了相应的制度建设。外援机构设置的沿革变迁十分复杂,显示了外援政策多重目标之间的冲突和平衡。(80)1947年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以及马歇尔计划开启了战后经济援助的政策实践,1948年《欧洲经济合作法》(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ve Act)把此前分散管理、临时性的对外援助计划纳入该法案下新成立的经济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gency)的统一管辖之下,加强了美国对外援助活动的系统性和制度化程度。1949年10月通过的《共同防御援助法》(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Act,又称《军援法》),授权国务院指导军援计划的实施并掌握经费的分配,同时成立了一个由国务院、国防部和经济合作署首长组成的外援政策协调委员会,以协调外交政策和援助政策以及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81)1950年6月,关于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援助的《国际开发法》(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ct)通过,10月又据该法在国务院内成立了技术合作署(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负责对发展中国家(最初以拉美为主)提供技术援助。作为进一步强化军事援助和加强援助计划间的协调的步骤,1951年10月通过了《共同安全法》(Mutual Security Act of 1951),设共同安全署(Mutual Security Agency)取代经济合作署,以统一管理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其中军事援助与国防部共管)。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很快对援助机构进行改组,于1953年8月将共同安全署和技术合作署合并为独立于国务院的对外业务署(Foreign Operation Administration),1954年又将对外业务署改组为国务院属下的国际合作署(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此后外援机构设置相对稳定,直至1961年《国际发展法》(Ac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设立国际发展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82)
对知识和学术资源予以深入广泛的动员和利用,是自二战以来愈来愈受重视的政策和制度目标。二战前美国缺乏国家赞助科学研究的制度体制,联邦政府对科学的投入很少,而且大多集中于农业领域。科学共同体维持着相对于政府的独立自持的状态。二战期间科学界在参与各项战争努力的过程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特别是原子科学和电讯科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和威望,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此前基本上处于分立状态的关系,开启了“科学的政治化”进程。(83)当时的科学研究和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OSRD)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二战后至1950年,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Navy Research,ONR)在政府与科学的关系中占有特殊地位,一度成为“联邦政府赞助学院科学研究的主要机构”。联邦政府通过于ONR渠道大规模地资助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既帮助“纯粹为了增长知识”的研究工作,又帮助“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项目。更重要的是,通过ONR的运作,联邦政府形成了一套赞助大学研究的管理机制,延续至整个冷战时期。与此同时,杜鲁门政府建立了科学技术动员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Mobilization),掌管基础科学研究项目。1950年,ONR的研究转向军事技术方面,新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开始接管资助基础研究的任务。(84)NSF并不拥有明确的职权和专职人员配备,并没有制订统一的关于国家科学发展的全面规划。政府流向工业和大学的基金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机构和机制来运行的,以“多元并立和松散协调型”或者是“分散多元型”为特征。(85)其中1947年1月正式成立的原子能委员会(U.S.Atomic Energy Commission)主持下建立的国家实验室(national laboratory)体系尤为重要,它为冷战时代美国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制度平台。(86)经过战后初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实践活动,国家安全国家向科学提供“财政的、制度的、政治的和道义的支持”,科学和国家之间出现了庞大坚实的“灰色地带”,“冷战政治成为决定科学的内容、方法和意义的一个因素”。(87)另外一个反映冷战国家对科学的巨大影响的事项的,是作为战后美国科学的主要潮流之一的“大科学”(Big Science)的制度和运作模式;对于它的兴起,如果离开“国家安全国家”的因素,就无法得到理解。(88)
冷战深刻影响了知识生产方式和知识形态,“国家安全国家”与学院学术之间产生巨大的“灰色地带”——就此而言,社会科学绝不亚于自然科学。“国家安全国家”创生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专业化社会科学知识渗入国家政治领域,“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观念在军事和对外政策领域里发挥作用的过程。本节所述产业动员、心理战、公民防务、对外援助等方面,均有社会科学家的参与和影响。二战以前,德国“纯粹科学”(pure science)观念对美国社会科学有深刻影响,在社会统计、经济学和农村社会学以外,政府和大学联合推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况很少。战争期间,社会科学家(特别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大批加入情报部门,以从事敌情研究为参与战争的主要方式。(89)战后,与国家动员产业界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制度方式一样,社会科学领域也没有建立集中化的、自上而下的组织体制,而是主要通过政府合同体制对大学和民间智库注入资金,对社会科学予以动员和利用,在此基础上迅速形成大型社会科学研究经费大部分来自政府机构的局面。与此同时,大学、基金会、民间智库和政府(及其下属研究机构)之间形成了广泛复杂的沟通合作网络和频繁的人员交流机制。“国家安全国家”对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社会科学的“制度建设、文本、方法论和知识体系这些被认为是学术事业的基本要素的东西”均为冷战的国家目标所深刻塑造。(90)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三大潮流,即行为主义(“行为科学”)的蔓延、发展(现代化)研究的兴起、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和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学术体制的确立,均与“国家安全国家”密切相关。(91)一些重要的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均因来自国家的资金支持而得以建立和发展。例如,美国最早的从事“政策相关研究”(policy-related research)的大学国际研究机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中心,就是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心理战研究项目“特洛伊计划”(Project Troy)的直接产物。(92)
曾有人称:“如果说一战可以被认为是化学家的战争,二战是物理学家的战争……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大有理由被看成社会科学家的战争。”这话不无道理。在冷战的启动和行进中,美国如何做出对世界形势和自身历史使命的基本判断,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如何制定和实施冷战的“大战略”和局部政策,如何在冷战政治中动员和吸纳知识和意识形态的资源,如何达成符合冷战需要的国内政治气氛和全民共识,美国冷战的这些方方面面,如果脱离开从事“政策导向的研究”、为“国家安全国家”提供政策思想和建议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法理解的。“军事—学术复合体”(military-intellectual complex)成为“国家安全国家”的连体物。(93)国家动员社会科学的机制又改变着“国家安全国家”自身的人员构成。1950年代中期以后,先前“国家安全精英”主要来自具有商界背景的人员的情况有了重大改变,“在学界和政府之间进进出出的人”成为“国家安全国家”的基干力量。这些人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学术史的主体,他们还进入了冷战的政治史;而美国的冷战史不仅是一部由政治家、军人和外交官主导的外交史和政治史,也是一部知识史或者思想史——学术精英和社会科学家是其中的要角。
六 “国家安全国家”与“帝王式总统权”——国家安全委员会初期的演变
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意义,《埃伯斯塔特报告》将其设计为国家安全组织结构的“基石”,研究对外政策决策体制的学者称其为“有史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在内阁层级上为政策协调而进行的最为雄心勃勃的努力”、“美国政府外交和安全政策制定最为重要的正式制度”。(94)而首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卡特勒则在1956年称:“位于政府顶端这个新机构的稳固建立和有效运作是美国政治经济的一个当代现象。”(95)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家安全国家”的庞大工程群组中的核心设施,或者说是它最明显的标志性建筑。它标示了战后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即“国家安全”成为一种“高位政治”(high politics)(96),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了首要的、中心的、统御的地位。它也最集中、最全面地体现了“总体冷战”的律令,体现了“国家安全国家”自身的集中化和综合特性,体现了为因应“总体冷战”而“在政府的最高层级上对部门观点予以协调和整合的某种正式机制的必要性”(97)。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只是一个机构,而且也是一个枢纽性体制,是一组勾连了联邦政府各个分支机构和多个政策领域的组织机制。
然而,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细致考察显示,即使我们可以把国家安全委员会看做“国家安全国家”的中枢,却并不能把它理解为“国家安全国家”的顶端——而这是一个通常容易产生的误解,其原因往往在于高估美国政府高层的制度化程度。“国家安全国家”的顶端并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而是在冷战时期迅速扩张、具有内在的非制度化因素和高度个人化特性的总统权。毋宁说它是总统权自身在国家安全领域运行的一个机制,或者说是总统权控制“国家安全国家”的一个制度工具。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历史与“帝王式总统权”的演进是纠结在一起的。
《埃伯斯塔特报告》出台后,对于通过这样一个机构达成外交和军事决策过程和行动的有效协调,并没有明显的争议。但是,就它在决策程序中的性质和具体作用及其与总统权的关系,在总统及其幕僚班底、军事部门、国务院等行政机构以及国会之间,却存在巨大的认识差异。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初的运作中,总统权与实力暴然增长的军事机构的竞争是一个突出的因素。杜鲁门后来在回忆录中称:“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的初期,有一两个成员曾经想按照英国的式样把它变为高级执行内阁。福莱斯特尔和约翰逊部长就试图对行政秘书施加压力。他们要它僭取监督政府其他部门的大权,并且监督委员会将所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98)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之初,对总统而言不啻为一匹有待驯服的烈马。
对这个机构最主要的倡导者福莱斯特尔和埃伯斯塔特来说,基于对罗斯福时期总统在外交和国防决策上绕过正式制度程序而导致严重的“行政混乱”的不满,以正式的、制度化的组织程序框定总统决策行为,以某种决策集体化机制限制总统权,是一个隐含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创意当中的目标。由是之故,国家安全委员会曾被谑称为“福莱斯特尔的报复”——强调程序化、制度化的官僚机构对专擅的总统权的报复。(99)在福莱斯特尔等人关于NSC的概念中,英国战时内阁体制即“帝国国防委员会”(British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se)是一个范本,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某种战争内阁。(100)《埃伯斯塔特报告》中对NSC职责的用语是“制定和协调政治和军事领域里的总体政策”(101),暗含总统的权责要归于这个机构或者与这个机构分享的意味。杜鲁门是因前任突然亡故而上台的,对于这样一个“事故总统”(accidental President)缺乏对外政策经验的担心,以及那些“有经验的人”分享更多的决策权力的企图,也是促使福莱斯特尔等属意于推动设立NSC的一个动机。所以不难理解,对维护总统权力极为敏感的杜鲁门总统起初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置并不热心,甚至疑虑重重。他在1945年12月19日向国会提交的改组方案中,并不包含《埃伯斯塔特报告》中强烈提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当时作为总统班底的预算局(Bureau of Budget)以及国务卿马歇尔等人也对NSC持怀疑态度,担心如赋予其法定政策权力,则势必削弱总统在决策程序中的地位。在此后《国家安全法》的起草过程中,有关NSC的内容和军事机构的问题一样,也充满争议和妥协。杜鲁门最后接受NSC,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换取海军方面支持武装力量更大程度的一体化而做出的一个妥协。总统及其班底想让它成为一个纯粹的咨议机构,没有法定权威性职能,其附属办事机构由总统任命。结果,在最终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文本中,并没有规定其为决策机构,而是突出咨议性职能。除了对其法定成员的明确规定外,关于NSC的地位和职责的用语相当含糊(102),而这显然是反映了白宫方面要求的刻意之举。(103)NSC与国会的关系是独特的:与总统行政办公室的其他机构不同,它不向国会报告,其班底完全由总统任命而不需国会批准。
《国家安全法》难以消弭关于NSC性质和功能的认识分歧,总统和国防官僚集团之间的竞争在NSC运行的初期就展开了。向来作风高调强势、于1947年就任防务首长的福莱斯特尔力求使军事部门在NSC内掌握更多的权力,意图把NSC与“国家军事机构”在实际上混同起来,使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厅(NSC Staff)尽可能与防务首长办公室合为一体。他还主张总统不必经常出席NSC会议,而由防务首长主持其日常运行。但在另一方面,总统和预算局则力求将NSC定位于一种咨议性角色,防止其演变为一个掌握实际决策和执行权力的“运作实体”,建议在总统缺席时由国务卿主持NSC会议。双方的竞争还表现在NSC的办公地点上,福莱斯特尔想把NSC的办公地点放在五角大楼,以便于使NSC体制与国防体制合而为一。而代表总统意愿的预算局和白宫办公厅则成功地排除干扰,最终将其置于白宫旁侧的老国务院大楼内,与总统行政办公室的其他部分连为一体。此中防止军事部门对NSC影响力过大的意图昭然可见。(104)
杜鲁门维护其总统特权的决心及其个人性格在对NSC运作方式的塑造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在1947年9月2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杜鲁门就告诫与会者:这是“我的委员会”,每一个成员都不要在其中有任何充当“首席女高音”的做法,迫使福莱斯特尔当场表示他理解NSC是属于总统的咨议机构。(105)总统控制NSC的另外一个办法是抑制NSC的作用,包括少举行会议,他本人尽量少出席NSC会议,以此造成决策出自总统而非NSC的例规。在1947年9月26日第一次NSC会议之后10个月里,他再也没有出席第二次;而此后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在56次NSC会议中他只参加了其中的11次。(106)而NSC会议最初均安排在白宫的内阁会议室(Cabinet Room)举行。杜鲁门还通过在NSC内厚此薄彼的方式确保NSC按照自己的意愿运作。在1949年8月副总统加入NSC前,杜鲁门通常委托深为其信任和倚重的国务卿马歇尔主持NSC会议,使后者成为NSC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同时由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承担对外政策长期计划和起草NSC主要文件的职责,政策计划室主任凯南挂名NSC顾问,以此作为压制与总统多有抵牾的福莱斯特尔和军事部门的影响力的安排。(107)
总统驾驭NSC的一个更重要途径是将NSC办公厅作为总统行政办公室的一部分,使之成为不折不扣的“国王的人马”。杜鲁门选用的首任行政秘书西德尼·索尔斯忠实地履行了维护总统权力的使命,对以后NSC的工作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索尔斯将自己的职责定位为总统的“亲信”和“仆从”,以及NSC和各部门之间的中立协调者,承担秘书和管理性质的工作,着意于不让NSC内来自个人和部门的意见和压力干扰总统。他和NSC办公厅其他成员一方面主导NSC工作文件的流程,另一方面又尽力确保NSC仅有咨议职能而无决策权力,仅行使协调功能而不负责执行。(108)由此NSC的办公厅实际上成为总统直接掌握下的负责对外政策的工作班底。
1949年年初国会负责审查国家安全组织的胡佛委员会也指出总统对外政策决策体系“以许多缺陷为标记”,要求总统在执行政策之前应该更多地在行政部门内以正式渠道寻求建议。但当年夏天以胡佛委员会建议为基础的国防重组对NSC影响不大,只是改变了NSC法定成员的构成——三军部长退出,而副总统进入;同时将NSC办公厅从属于总统行政办公室的既成事实予以确认,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总统的咨议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的地位。为了协助NSC处理具体问题,开始建立某些专门常设委员会,如跨部情报会议和内部安全跨部委员会。(109)
朝鲜战争爆发前,杜鲁门着意抑制NSC机制,并非由于他认为这个机构没有用,(110)而是因为他要防止这个新的官僚机构对自己构成掣肘。既然经过一段时间后,杜鲁门已经将NSC变成自己掌握下的一个方便顺手的工具,他就会更多地利用它,提升它在决策体系中的地位。1949年发生“中国事变”和苏联的原子弹试爆,使得杜鲁门感到迫切需要考虑长期政策规划问题,于是指派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组成特别委员会,考察政策目标和战略计划问题,其产物作为“NSC68号”文件于1950年4月提交给总统。为了保障NSC68的执行,NSC办公厅的地位的又有所加强,规模也有所扩大。(111)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更导致NSC在决策体系中作用提升。1950年7月19日,杜鲁门给NSC各位成员发出训令,表示鉴于目前的国际形势,他希望在NSC中讨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各项政策,要求所有重大的国家安全政策都要通过NSC机制上达总统,NSC会议增加为每周一次,而且总统亲自出席。从1950年6月28日到1953年年初其任期结束,国家安全委员会共举行71次会议,而总统参加了其中的62次。(112)为了提高NSC会议的效率和影响力,杜鲁门明确规定了NSC会议的参会人员,包括五位法定成员加上财政部长、参联主席、中央情报局长,以及作为总统特别助理或者顾问的哈里曼(W.Averell Harriman)和索尔斯。杜鲁门还重新组织了NSC办公厅,建立了由来自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的派驻代表(一般是助理部长以上的官员)组成的高级办公机构(Senior Staff),由NSC行政秘书统领其工作。根据冷战形势和政策演进的需要,NSC机制继续扩张。1951年的《共同安全法》设共同安全署,其署长成为NSC法定成员。1951年春,NSC下建立心理战略委员会。(113)
1947年《国家安全法》并没有设置后来“国家安全顾问”的职位,但总统仍致力于在NSC的机制中制造出脱离常规官僚机构的、作为“国王的人马”的对外政策顾问。首任行政秘书索尔斯实际上就部分地履行后世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角色,尽管他是以很低的姿态和高度“中立”的方式履行一种“管理性”(程序性)的职责,而不介入实际政策制定。1950年索尔斯行政秘书任职结束后,旋即被总统任命为军事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特别顾问”。在1946~1950年间,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向总统提供国家安全事务咨询的还有身份属于白宫顾问系统的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设置更正式也有影响力的国家安全助理职位的进程又向前迈了一步。1950年6月,总统任命哈里曼为新的总统特别助理,其职责没有清晰界定,但在朝鲜战争事务以及代表总统协调国防部长和国务卿的活动方面发挥特别作用。所有这些安排,共同构成了肯尼迪以后在决策体系中地位显要的国家安全顾问一职的制度起源。(114)
杜鲁门任期结束时,这个本与总统权大有龃龉的新生官僚机构可以说已经被总统权“驯服”了,其基本制度地位和运作模式已然被确定。但在美国历史上,每一个总统都以自己的方式和偏好或多或少地重新塑造总统权,这同样表现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利用NSC的方式上。出身职业军人、讲究组织规程的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期间就公开批评杜鲁门政府NSC运作,表示要赋予这个机构以关键的重要性,将其用作帮助总统在“高层政策”和机密政策的制定上的主要机制。(115)入主白宫后,艾森豪威尔立即着手改造NSC,基本方向是强化组织规范性,并大幅度扩展其业务范围。为此艾森豪威尔在NSC内新设了两项机制:“计划委员会”(Planning Board,PB)和“行动协调委员会”(Operation Coordination Board,OCB)。前者对杜鲁门后期“高级办事机构”的模式有所承续,由在NSC法定成员代表资格和列席会议资格的各部门的助理部长一级的官员组成,负责为NSC起草重要的对外政策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新设的名为“基本国家安全政策”(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的年度评估报告,旨在为国家安全政策提供纲领和宏观指导。OCB则由杜鲁门建立的心理战略委员会脱胎而来,成员包括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CIA局长等,其目的在于监督推动各部门执行已经制定好的政策。首任国家安全顾问卡特勒曾打过一个比方来形容艾森豪威尔时期有条不紊的决策过程:如果把国家安全政策制定程序看做一座山峰,则国家安全委员会居于顶端,在其中的一个政策创议通过PB向上流动;如果总统接受了一个政策建议,则政策要顺着OCB的一侧向下流到个部门机构,由后者负责制定具体计划和执行。(116)
艾森豪威尔初期NSC有五个法定成员: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防动员办公室(ODM)主任。但他在法定成员之外又经常召集下列众多官员参加NSC会议:财政部长、预算局长、对外行动署署长、裁军事务特别助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央情报局长、对外经济政策特别助理、美国新闻署署长、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及其助手,以及NSC办公厅行政秘书及其助手。除了以上官员,艾森豪威尔还会根据会议的特定议题召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作为特别与会者参加NSC会议,包括与核武器相关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和与内部安全相关的司法部长,以及联邦民防管理局局长、三个军种部长和军种最高将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乃至于商务部长。(117)自然,与杜鲁门时期相比,艾森豪威尔时期NSC以更多的会议(118)、更活跃的政策讨论、种类和数量更多的政策文件、更正式和制度化的工作程序、更广泛的与其他政府机构的联系机制为特点,在咨议职能之外具有更强的正式决策和执行功能,由此似乎使总统在对外政策上的决策权被融入NSC正式的、规范化的机制当中。
但是,事后看得更清楚的是,“站在政策山峰之巅”的是艾森豪威尔,而不是NSC(119),尽管NSC构成了这座山的上部。在杜鲁门奠定的基础上,NSC已不对总统权构成限制和竞争关系。而在这种情况下强化NSC就是强化总统权,而且总统权对常规官僚机构的抑制和规训并非荡然无存。艾森豪威尔曾向NSC成员表示,他把NSC看成是一个“法人团体”,由那些以自己的身份、而不是作为各自部门负责人的身份向总统提出建议的人组成。他希望委员会成员“带着自己的背景和经验,对国家安全问题给出最具政治家气度的答案,而不是寻求仅仅代表部门立场妥协的办法”(120)。在NSC内他也总是尽力使官僚机构服从于自己的意志,采用的手段包括让官僚机构(特别是国务院和国防部)在NSC机制内相互竞争,而自己居中实施“分而治之”和最终裁决。NSC并没有主宰或者消解总统的决策和咨议体系,其职责偏重于长期政策的研讨和规划,而对外政策的日常运作却牢牢掌握在总统的手中。实际上,和战后所有总统一样,NSC并不是总统咨议体系的全部,艾森豪威尔也有自己在NSC之外的非正式的咨议渠道。(121)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研究者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以“从白宫伸出的一只幕后之手”在运作国家安全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办公厅只是这只手的两个手指而已。(122)
而作为使NSC办公厅这个手指更强有力的措施之一,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就任伊始就设置了履行跨部门政策计划职能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123)一职。它也被授权执掌计划委员会(PB)的工作。艾森豪将国家安全顾问作为政治性任命,为的是赋予其在与政府各机构官员打交道时拥有更大的权威。虽然这个不需通过国会确认的职位当时并不十分显要(124),但此后却成为一个势力不断增长,最终在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时期成为一个凌越首席外交官即国务卿的职位。而NSC办公厅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基础上,在肯尼迪时期成为积极介入决策过程的“小国务院”,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国务院。(125)就此而言,艾森豪威尔时期也处在战后总统权扩张连续性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上。
就制度创设的动机以及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实际的历史过程来看,NSC这一机构内在地具有三方面的潜在功能:即作为咨议体系和政策讨论平台的功能、作为正式政策制定程序的功能以及向总统提供对外政策班底的功能。(126)在1950年以前,前两项功能在总体上受到抑制,而1950年以后特别是在艾森豪威尔时期虽一度得到有限度的发育,但始终没有使NSC成为以总统为首的国家安全政策机制的全部。相反,后一项功能则处于稳定的、连续的强化过程之中。而从后来的历史事实来看,作为正式咨议机制和决策机制的功能在艾森豪威尔时期达到顶峰后便趋于弱化,而第三项功能成为整个NSC最为重要、且处于不断强化中的功能。NSC办公厅存在的事实,其意义恐怕远远超过了NSC成员的构成。NSC办公厅和国家安全顾问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时期虽尚未如后来那样耀眼,但这些年也为以后的发展趋势奠定了一个足够坚实的基础。就此而言,杜鲁门在第一次NSC会议上发出的“这是我的委员会”的声音,为以后NSC的发展制定了基调。NSC不仅是“国家安全国家”的一个中枢制度,也成为总统权扩张的一个工具,由此成为“国家安全国家”和“帝王式总统权”的共同环节。
新政和二战以来美国政治的突出趋势之一是强势总统权的演进,小亚瑟·施莱辛格将其命名为“帝王式总统权”。他认为,这种对美国分权的宪政传统构成冲击和偏离的“帝王式总统权”的主要动力来自对外政策和战争,是一个伴随着冷战的现象。(127)小施莱辛格的讨论也揭示出,作为“国家安全国家”的观念基础的“国家安全”理念,实际上也是“帝王式总统权”的基本机理——“为了各种目标而动用‘国家安全’的符咒……意味着帝王式总统权从对外事务向内部事务扩张”(128)。小施莱辛格主要是从国会和总统在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权力分配和制衡的角度考察“帝王式总统权”,而对NSC的考察显示,总统权对常规官僚机构的驾驭和“驯服”也是冷战时期总统权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情况与美国总统权的内在特性有关,即它是一个“特别个人化的制度”,而且在美国是实际上的总统负责制而不是英国式的内阁负责制。(129)从更广泛的观点看,在冷战使得决策系统的集中统筹成为必然律令的历史条件下,讲究综合性、全局性的“高层政治”对纯粹的“技术治理”原则构成凌驾之势,国家政治体系顶端的总统权享有对部门的、局部的、专业化的官僚部门的内在优势。冷战同时造成了总统权在外交军事领域扩张的政治舆论氛围,具有“反总统权”秉性的国会因素和共和党因素也都在总体上顺应了这种趋势。(130)在这种大势之下,军事部门在二战和冷战初期迅速扩张的势力被抑制在一定限度之内,而在外交政策重要性提升的背景下常规外交部门的势力和影响却趋于长期下降,也都是“帝王式总统权”的题中应有之意。
七 美国国家构建长期趋势中的“国家安全国家”
(一)“国家安全国家”与19世纪末以来美国国家构建之趋向
“国家安全国家”须被置于19世纪末以来美国国家构建的长期趋向中才能得到理解。
独立以来到二战之前,欧洲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作用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和战争压力对美国而言几乎不存在,其经历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战争是内战,非因外部威胁而起。对美国来说,战争、军事和军人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弱于欧洲那些更“典型”的民族国家。孙子所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古训,马克斯·韦伯和查尔斯·蒂利等人关于暴力和战争促成国家体制的集权化趋势、“战争塑造国家”的现代社会科学论说,如用以看待20世纪中叶以前的美国历史,均不切合。20世纪以前,美国大概可以说是西方大国中最不尚武、也最少武人政治的一个国家。美国政治传统中对军队和军人政治的不信任与其承自英国的传统有关;而在后来历史演进中,这种思想因素在美国起作用的程度明显超过了英国。(131)可以说,在美国人的民主信念和维护民主政治的方法原则中,防止军队规模和军人权力过大是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就是美国的所谓反军国主义传统。(132)这是美国国父们着力加以申述的一个主题,尤其是华盛顿和杰斐逊。(133)
美国政治传统的另一个基本要素是美国式的反国家主义。这一政治传统强调公民自治和基层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刻意限制中央政府规模和权力,抑制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和官僚机构扩张,而且在联邦政府内部与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两个层面上强调权力分割。(134)又有论者以“明显的国家缺位状态”来形容美国早期政治文化的这种独特性状。(135)显然,这种反国家主义与反军国主义构成相辅相成的关系。与此相关,美国国家构建和政治发展所经历的是一种不同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次序关系,即美国的民主化过程先于国家机器的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这造成“国家权威、官僚机构及其公职人员并不享有强势地位”的总体状况。(136)
而对外政策思想上的孤立主义同时支撑着反军国主义和反国家主义。孤立主义的背后是一个把民主与和平联系起来的逻辑,就是说平民的、和平的国家最有利于维护国内的民主制度,反过来,民主国家有反对战争的内在倾向。这就是所谓“民主和平论”。
反军国主义、反国家主义和孤立主义的三位一体构成美国的基本政治传统,造就了美国国家构建进程的独特性。但美国政治思想史的图景不是单色的。美国立国以来就有所谓汉密尔顿主义传统,呼吁造就强大、积极的政府,也主张建立训练有素的职业化军队和统一国防。但联邦党人也体会到外部压力对民主造成威胁的机理,而且也反对大规模常备军,尊奉文官控制军队的原则。(137)总体上,汉密尔顿主义毋宁应当被看做一种“抗衡力量”,即对主导性力量构成制约、平衡和矫正的非主导性力量。在19世纪末以后曾一度出现空前高涨的扩张主义和尚武精神,以及相应扩张政府和军队的呼声,以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和马汉(Alfred T.Mahan)等人为代表。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更有了扩张国防和外交机构的动议和努力。但一战结束后,美国迅速退回到孤立主义立场,反国家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舆论氛围也继续维持。战争期间的制度变更努力或废止或消退,大多没有延续下来。当时美国社会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加入一战是个大错误,是军火商和银行家为了私利而用欺诈手段把美国拖入了战争。此中清晰可见的仍是那种把对外战争和国内民主对立起来的杰斐逊式逻辑。在这种情况下,战后军事力量规模迅速收缩,小政府模式得以延续。1934年,参议院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奈委员会,Nye Committee)调查军火工业和一战的牵连,特别委员会在次年做出的结论就持这种看法,这直接促成以中立法为代表的孤立主义新高潮。(138)
但是,现代工业主义却在销蚀着反国家主义的历史条件。作为对19世纪晚期的工业化高潮及其引起的社会失序的一种反应,“技术治理”思潮伴随着进步主义运动蔚然兴起。(139)它的指向是用理性化、技术化和专业化原则管理和控制社会生活,提升技术官僚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反映了现代工业主义的技术本质及其对国家政治产生的必然效应。在新历史条件下,管理主义和技术治理原则由经济和社会领域向国家政治领域扩展,造成官僚化扩展的趋势,此中也暗含了政府行政部门力量扩张和地位提升的趋势。由此美国展开了“管理型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或者managerialstate)——这是现代美国官僚制国家(bureaucratic state)的别称——的建构进程。进步主义致力于填补“国家缺位状态”,主张扩大政府在公民福利和社会经济事务中的责任和权力,对反国家主义传统构成背离,发出了建设“新美利坚国家”(New American State)和美国式“福利国家”的先声。但是直到1930年代,美国国家构建的进程是一个平缓渐进的过程,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舆论氛围并未根本改观。
历史上重大制度变迁的发生和加速往往以大型危机为条件。大萧条就是这样的危机。作为对大萧条危机的反应,罗斯福新政和现代民主党自由主义压倒了美国式的反国家主义。而珍珠港事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这样的危机,它决定性地终结了孤立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开启之时,反国家主义—反军国主义—孤立主义的三位一体模式已经无力继续主宰美国人的政治生活和国家意识形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强劲的国家构建的历史运动:“管理型国家”、“福利国家”和“国家安全国家”构成了它的三个基本面向和基本内容。新政以后的现代美国民主党自由主义在这三个方面均鲜明地代表了国家构建的基本趋向。虽然“国家安全国家”与“福利国家”之间会由于“黄油和大炮”的竞争关系而形成一些冲突,但从美国历史的长期趋势看,三者的关系大体上是相辅相成、趋于一致的,三者共同促成战后美国的“大政府”趋势。(140)
(二)“国家安全国家”与美国政治传统:偏离,还是决裂?
“国家安全”理念和“国家安全国家”是对美国政治传统的重大偏离,但也难说是决裂。“反国家主义—反军国主义—孤立主义”的三位一体模式让位于“国家安全”理念和全球主义战略,但前者仍作为美国政治传统的延续性因素,或者说作为对“国家安全”理念构成制约、平衡和矫正作用的“抗衡力量”,以或直接鲜明、或曲折隐晦的方式发挥着作用。观察“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和扩张的一种方式,就是把它看成这两种力量相互竞争和相互妥协的过程。大体而言,“国家安全”理念和全球主义的载体是新政以来形成的致力于推动美国走向“福利国家”和“大政府”的政治和思想联盟,主要是东部和西部沿海各州的民主党人。“福利国家”和“国家安全国家”的支持者两者有一定程度的重合。而代表传统和延续性因素的则是来自中西部和平原州、山地州的共和党人,以及老共和党进步派、南部的民主党保守派,它们杂糅洛克主义传统、杰斐逊共和主义传统和孤立主义传统,组成反对新政、反对“大政府”的右翼保守派阵营。这两种力量不仅在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问题上分营对垒,而且在对外政策和国防体制上也有诸多矛盾。(141)
在战后初期关于国防问题的大辩论中出现的“堡垒国家”(Garrison State)论说就体现了当时“国家安全”理念与美国政治传统之间的冲突。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哈罗德·拉斯维尔在二战爆发前著文指出,现代战争的“总体战”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永久性战争准备的压力,将导致民主国家的精英构成和权力结构发生重大深刻的变化,“暴力的专家”即军人将取代“谈判的专家”即工商业者而占据社会权威的中心;安全的紧迫性将挤压自由的空间,政治生活的形态朝向更具“专制、政府主导、集中化和整体化”的方向发展;军事和非军事领域的界限将被彻底打破,政府和军队对人力和经济资源分配的权威将大幅度增长;国家结构中那些不适应战争动员的部分将消亡或者至少处于屈从和边缘地位,公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观念将趋于崩溃。总之,美国面临将自己转变为适应“总体战”需要、但严重削弱自身民主传统的“堡垒国家”的巨大压力。(142)
“堡垒国家”的论说实际上确认了为“总体战”而使国家体制向着扩张和集中化方向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更引人注意的,是它指出权力分割、文官控制军队、保护私人领域等美国传统政治原则的所面临的压力和威胁,是对美国反国家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传统的一种曲折但有力的申述。在战后初期关于“复原”、政府改组、财政预算、兵役和普遍军训制(UMT)等诸多议题的政治争论中,保守阵营均时常引入“堡垒国家”论说,使之与哈耶克关于“集体主义”和福利国家导致“极权主义”和“奴役”制度的论说(143)一道,成为对抗扩张和集中化的国家构建路线的思想和话语资源。一时之间,“堡垒国家”成为“标号语”(catchword),广为流传。(144)政客、学者和民意领袖(特别是其中的保守派)都在议论“堡垒国家”在冷战初期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的国际情势下,美国人是不是必须在“堡垒国家”之下生存,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真实而迫近的问题。可以说,美国人不仅生活在对核战争的恐怖想象之中,而且他们的思虑和行动还实实在在地笼罩在“堡垒国家的阴影”之下。比如,当时还有人以“宪政独裁”(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来表达这种焦虑,认为美国建立“某种形式的行政一军事独裁”的前景已无可避免,只能退而求取两个目标:在制度上,“让独裁更有效同时更负责”,在哲学上创造一组“民主生存的价值”,尽可能使独裁被置于宪政民主的总体架构之下。(145)
艾森豪威尔关于“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说法实际上也是对“堡垒国家”论说的一种呼应。1961年1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离任告别演说中郑重告诫美国人,“庞大的军事权势集团和巨型的军工产业”在美国历史上取得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乃至于精神上的”影响力,“其不正当权力灾难性扩大的潜在可能性”已经并将持续存在,对此必须予以警惕和防范。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在缔造“国家安全国家”的过程中,美国历史上惯常出现的妥协和中和的机理也在起作用。这也体现在《埃伯斯塔特报告》中。在某种程度上与拉斯维尔一样,埃伯斯塔特这些“国家安全国家”的缔造者们也看到国家安全组织有可能颠覆美国政府的基本原则,总体战需要下的“国家安全国家”有和民主原则相抵牾的方面。《报告》明确宣称维护美国民主政治的认同,并尽力在“国家安全”理念与美国的政治传统之间寻求折中。从《埃伯斯塔特报告》开始的整个“国家安全国家”的建立和扩张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争议、妥协和折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传统政治价值以及体现这些价值的“堡垒国家”论说成为激进的“国家安全”理念的一个滞碍因素,逼使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做出让步和妥协,起到制约、平衡和矫正作用,而这种作用总的效应在于抑制集中化、军事化和战争动员的强度,确保限制和分割政府权力、文职控制军队、预算平衡和限制公共开支、保护私人—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的自主性等原则的存续。(146)
同时,正如孤立主义和反国家主义本身在20世纪的演进中总体上趋向弱化并实现某种转型,新政派的干预主义和国家主义立场自1930年代末以来也趋于温和化,由此又有20世纪中期美国政治思想两大阵营走向中间立场和趋同的趋势。而这种趋同趋势不仅体现在党派政治和总统政治上,也体现在塑造、掌握和运作“国家安全国家”的精英群体的身上。
(三)“国家安全精英”与“自由合作主义”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企业家和律师越来越多地介入政府、军队和对外政策事务,他们大多来自沿海都市地区,有国际商业经验和国际视野,成为推动美国走向国际主义的主要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些人更是成群结队地加入美国的战争努力,其中有不少在军需生产和产业动员各机构中任职,充当政府和私人经济部门的沟通桥梁,其势力和影响力急剧上升。从最初的作为开创型人物的伊莱休·鲁特开始,列数战后初期担任外交、国防、情报部门要职的人物,我们可以为这一群体开列一长串名单。一个很值得重视和进一步考察的情况是,正是这批人构成战后初期的“国家安全精英”或者说“国家安全当家人”(national security managers)的基本力量。战前拉斯维尔预见到军人地位和势力的上升的不可避免,冷战初期赖特·米尔斯也观察到军方的影响力空前强化,在对外政策方面有挤压外交官的地盘的趋势(147),但实际上职业军人并没有像米尔斯说的那样,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权势集团的“嫡长兄”,其总体的政治影响力显然不及上述有商界背景和文职身份的“国家安全精英”群体。与此相关,美国没有把自己变成一个“堡垒国家”,或者可以说,它大体上是拉斯维尔所称的“公民型堡垒国家”,而不是“军队型堡垒国家”。(148)
在国际观上,这批“国家安全精英”一般都兼具国际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观念,主张美国积极介入海外事务并维持强大的军力。他们当中许多人具有管理主义和技术治理论倾向,同时在党派和意识形态方面具有中间色彩,一般持温和的干预主义和改革理念,既接受和包容了进步主义和新政的一些思想要素,又遵奉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和传统的民主价值观。进一步说,他们所秉持的是一种美国版的(当然是不同于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合作主义(149)“原型”的,但也对其有所吸收)合作主义,或者说是“自由合作主义”(liberal corporatism或corporate liberalism),主张塑造团结的、有共识的和有秩序的美国社会和“新美利坚国家”。他们强调管理效率和组织技术的重要性,其中有人特别着力于推动政府部门充分利用商业界的管理和组织技术;他们呼吁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在政府、企业和工会之间建立有效、充分的合作;他们主张建立各种(包括半官方的和非正式的)沟通机制和咨询机构,促进政府对社会各领域的人员和智力资源的吸纳和利用,促成政府和商界、学界之间“进进出出的人”(in-and-outers)的大批涌现。(150)具有典型和代表意义的正是福莱斯特尔和埃伯斯塔特,前者是民主党保守派,后者则是共和党自由派,他们之间的合作正是以这种“自由合作主义”共识为基础。
“自由合作主义”的上述各种特点和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特征和机理。而且,“自由合作主义”也体现了20世纪美国国家构建的长期趋势中重要的一点:“国家安全国家”与美国式福利国家和“管理型国家”(managerial state)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促进的,有着基本一致的方向。
收稿日期 2009-06-15
注释:
①将national security state译为“国家安全国家”,非为最佳,而属于取“最不坏者”。一个译名中出现两个含义不等同的“国家”,不合汉语构词法习惯。有师辈学者曾建议笔者选用“政府”、“政体”、“体制”等对译state。实际上,笔者数年前的一篇文章中也曾用“国家安全体制”的译法[牛可:《国家安全体制与冷战知识分子》:《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10月号,第28~4l页]。但上述几个词的含义与state均有显著差别,不及“国家”准确;而national security之译为“国家安全”,已成通例。再者,这个概念的一个学术意义正在于其与“国家构建”问题的关联,就此可与“福利国家”和“管理型国家”等并称。所以,再三权衡之后,为求准确和学术史方面的合理性,仍作此译。
②有代表性的一例是,约翰·加迪斯对美国冷战战略的考察完全集中于其对外的方面。约翰·加迪斯著,时殷弘等译:《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原著出版于1982年。
③沃尔特·拉费伯:《美国、俄国与冷战(1945~2006)》(Walter LaFeber,America,Russia,and the Cold War,1945~2006),第10版,波士顿:麦克格劳—希尔2008年版。
④查尔斯·蒂利:《对欧洲国家构建的反思》(Charles Tilly,"Refi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 Making"),蒂利编:《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2页。相关综述参见:贾恩弗兰科·波齐:《国家形成理论》,凯特·纳什、阿兰·斯科特主编,李雪等译:《布莱克维尔政治社会学指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04页。
⑤威廉·H.麦克尼尔:《追求权力: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武装力量和社会》(William H.McNeil,The Pursuit of Power:Technology,Armed Forces,and Society since A.D.1000),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⑥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美国世界角色之非同寻常的起源》(Fareed Zakaria,From Wealth to Power: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⑦杰里尔·罗赛蒂著,周启朋、傅耀祖译:《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罗杰·希尔斯曼等著,曹大鹏译:《防务与外交决策中的政治:概念模式与官僚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布鲁斯特·C丹尼:《从整体考察美国对外政策》(Brewster C.Denny,See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hole),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⑧《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和《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鉴》(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都曾组织有关专题研讨。详见:《国防和民主社会研讨会》,《美国政治学评论》("National Defense and Democratic Society:A Symposium,"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43卷(1949年6月号);《军人政府》,《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鉴》("Military Government,"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第267卷(1950年1月号);《寻求国家安全》,《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鉴》("Search for National Security,"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第278卷(1951年11月号)。
⑨美国参议院政府运作委员会国家政策机构小组委员会:《国家安全组织》(Subcommittee on National Policy Machinery of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U.S.Senate,Organizing for National Security),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61年印行;杰克逊分委员会下有关研究的一个精编文集为:亨利·M.杰克逊编:《国家安全委员会:杰克逊小组委员会关于总统层级决策的文件》(Henry M.Jackson,ed.,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Jackson Subcommittee Papers on Policy~ Makingdr the Presidential Level),纽约:弗雷德里克·A·普雷杰出版社1965年版。
⑩盖伊·奥克斯:《幻想中的战争:公民防务与美国冷战文化》(Guy Oakes,The Imaginary War:Civil Defense and American Cold War Culture),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安德鲁·D·格罗斯曼:《为冷战做准备:美国的国内战线动员、国家扩张和公民防务(1946~1954)》(Andrew D.Grossman,"Preparing for Cold War:Home Front Mobilization,State Expansion and Civil Defense in the United States,1946~1954",社会研究新学院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迈克尔·克雷格:《掩蔽下的社会:美国的公民防务(1945~1963)》(Michael Kregg,"Sheltering Society:Civil Defense in the United States,1945~1963"),得克萨斯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
(11)例如,一个批判色彩很强,旨在揭露“国家安全国家”的反民主特性的历史文献汇编是:阿森·G.西奥哈里斯编:《杜鲁门总统任期:帝王式总统权和国家安全国家的起源》(Athan G.Theoharis,ed.,The Truman Presidency:The Origins of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纽约州斯坦福维尔:厄尔·M.科尔曼1979年版。
(12)丹尼尔·耶尔金:《破碎的和平:冷战的起源与国家安全国家》(Daniel Yergin,Shattered Peace: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波士顿:霍顿·米福林1977年版。
(13)小亚瑟·M.施莱辛格:《帝王式总统权》(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Imperial Presidency),波士顿:霍顿·米福林1973年版;《战争与美国总统权》(Arthur M.Schlesinger,Jr.,War and American Presidency),纽约:W.W.诺顿2000年版。
(14)厄内斯特·梅:《美国政治军事咨议体系的演变》,《政治学季刊》(Ernest May,"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Military Consultation in the United Srate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70卷(1955年6月),第161~180页;厄内斯特·梅:《作为冷战遗产的美国政府》(May,"The U.S.Government,a Legacy of the Cold War"),迈克尔·霍根编:《冷战的终结:意义与影响》(Michael Hogan,ed.,The End of the Cold War:Its Meaning and Implication),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228页。
(15)梅尔文·P.莱夫勒:《新路径、旧解释与研究视野的重建(主席演讲)》,《外交史》(Melvyn P.Leffler,"New Approaches,Old Interpretations,and Prospective Reconfigurations",Presidential Address,Diplomatic History)第19卷(1995年春季号),第173~196页;文安立:《新国际冷战史:三个(可能的)范式》,《外交史》[Odd Arne Westad,"The New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Cold War:Three(Possible)Paradigms," Diplomatic History]第24卷(2000年秋季号),第551~564页。
(16)彼得·伊文思、D.鲁伊奇梅尔、希达·斯考克波尔编:《重新探究国家》(Peter Evans,D.Rueschemeyer,and Theda Skocpol,eds.,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7)迈克尔·J.霍根:《合作主义》(Michael J.Hogan,"Corporatism"),霍根、托马斯·G.佩特森编:《解释美国对外关系史》(Michael J.Hogan and Thomas G.Paterson,ed.,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第2版,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148页。“合作主义”流派关注“国家构建”问题的典型例子之一是:艾米丽·罗森伯格:《传播美国梦:美国的经济和文化扩张(1890~1945)》(Emily Rosenberg,Spreading American Dream:Americ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pansion,1890~1945),纽约:希尔&王1982年版。
(18)迈克尔·霍根:《铁十字:哈里·S.杜鲁门和国家安全国家的起源(1945~1954)》(Michael Hogan,A Cross of Iron:Harry S.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1945~1954),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冷战和美国国内政治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动向述评,详见:安德鲁·D.格罗斯曼:《早期冷战与美国政治发展:对近期研究的反思》,《政治、文化租社会国际杂志》(Andrew D Grossman,"The Early Cold War and Amet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Reflections on Recent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Culture and Soctety)第15卷(2002年春季号),第471~483页。
(19)较近期的著述如:戴维·加布伦斯基:《国家安全国家的状态》,《参量》(David Jablonsky,"The State of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Parameters)2002~2003年冬季号,第4~20页;安娜·卡斯藤·尼尔森:《国家安全国家:无所不在和无休止的演进》(Anna Kasten Nelson,"Th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Ubiqultous and Endless"),安德鲁·巴塞维奇:《漫长的战争:二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史新探》(Andrew J,Bacevich,ed.,The Long War:A New History of U.S.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5~301页。
(20)梅尔文·莱夫勒:《权力的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和冷战》(Melvyn P.Leffler,A Preponderance of Power:National Security,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and the Cold War),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对“国家安全”作为一种研究路径的解说,见莱夫勒:《国家安全》(Leffler,"National Security"),霍根、佩特森编:《解释美国对外关系史》,第123~136页。
(21)相关研究综述可参见:马克·索洛维:《引言——冷战时期的科学和国家:模糊了的边界和有争议的遗产》《科学的社会研究》(Mark Solovey,"Introduction:Science and thc State during the Cold War:Blurred Boundaries and a Contested Legacy,"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c)第31卷(2001年4月号);乔尔·伊萨克斯:《冷战时期美国的人文科学》,《历史学杂志》(Joel Issac,"The Human Sciences in Cold War America," The Historical Journal)第50卷(2007年第3期),第725~746页。关于美国国家对社会科学进行动员和利用,参见:雷迅马著,牛可译:《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特别是第73~96页;乔伊·伊丽莎白·罗德:“社会科学家的战争”:《冷战国家里的专家知识》(Joy Elizabeth Rohde,"'The Social Scientists' War':Expertise in A Cold War Nation"),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22)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第181、184页。
(23)厄内斯特·梅:《作为冷战遗产的美国政府》,第218页。
(24)罗德里·杰弗里斯—琼斯:《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民主》(Rhodri Jeffereys-Jones,The CIA and American Democracy),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3页;杰弗里·里奇尔森:《美国情报共同体》(Jeffrey T.Richelson,The U.S.Intelligence Community),第3版,鲍尔德:西景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页。
(25)关于“军种战争”的详细叙述,参见:保罗·Y.哈蒙德:《国防组织:20世纪美国军事体制》(Paul Y.Hammond,Organizing for Defense:The American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07~226页;关于当事人的记述,参见:沃尔特·米利斯编:《福莱斯特尔日记》(Walter Millis,ed.,Forrestal Dairies),纽约:维金出版社1951年版,第145~149、160~165页。
(26)《福莱斯特尔日记》,第61~63页;杰弗里·多瓦特:《埃伯斯塔特和福莱斯特尔:国家安全伙伴(1909~1949)》(Jeffery Dorwart,Eberstadt and Forrestal:A National Security Partnership,1909~1949),得克萨斯学院站: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3页。
(27)《就陆军部、海军部的一体化及战后国家安全组织致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报告》(Report to Hon.James Forrestal,Secretary of the Navy on Unification of the War and Navy Departments and Postwar Organization for National Security,October 22,1945,Printed for the use of the Committee on Naval Affairs,United States Senate),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5年印行。以下称《埃伯斯塔特报告》(Eberstadt Report)。关于上文提到的日期,见: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60页;《埃伯斯塔特和福莱斯特尔》,第109页。
(28)《埃伯斯塔特报告》,第6页;霍根:《铁十字》,第33~34页。
(29)《埃伯斯塔特报告》,第6~14页。
(30)《埃伯斯塔特报告》反对军事组织一体化,尤其反对德国式的总参谋部,其立论依据正是维护文官控制军队原则,而这正是报告一再申述的主题之一。《埃伯斯塔特报告》,第15、35~36、84页。
(31)米利斯编:《福莱斯特尔日记》,第162页;多瓦特:《埃伯斯塔特和福莱斯特尔》,第110页。《埃伯斯塔特报告》的具体建议篇幅仅有14页,但其讨论和研究部分达200多页。
(32)阿尔弗雷德·D.桑德尔:《杜鲁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1945~1947)》,《美国历史杂志》(Alfred D.Sander,"Truman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1947~1947,"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59卷(1972年9月号),第374~375页。
(33)《埃伯斯塔特和福莱斯特尔》,第126~127页;阿米·B.泽加特:《设计缺陷:中央情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进》(Amy B.Zegart,Flawed by Design:The Evolution of the CIA,JCS,and NSC),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34)多瓦特:《埃伯斯塔特和福莱斯特尔》,第145页。
(35)文本见:Academic Source Premier数据库("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
(36)中文文献中通常将1947年《国家安全法》至1949年建立国防部这段时间的Secretary of Defense也译为“国防部长”,应属不确。在此期间尚无国防部,何来“国防部长”?
(37)此时尚未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职。
(38)战争中建立的“战略情报局”于1945年11月解散;中央情报组于1946年2月由杜鲁门下令成立,《国家安全法》将其人员、资产和档案全部移交中央情报局。
(39)约翰·米利特:《美国公共事务中的国家安全》,《美国政治学评论》(John D.Millett,"I.National Security in American Public Affair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c Review)第43卷(1949年6月号),第530~531页;威廉·弗雷伊:《国家军事体制》,《美国政治学评论》(William Frye,"The National Military Establishmen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43卷(1949年6月号),第543~555页。
(40)全名为Commission on Organization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又称为第一届胡佛委员会,以与1953年的第二届胡佛委员会相区别。关于第一届胡佛委员会,参见:佩里·E.阿诺德:《第一节胡佛委员会和管理型总统权》,《政治杂志》(Peri E.Arnold,"The First Hoover Commission and the Managerial Presidenc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第38卷(1976年2月号),第46~70页。
(41)《国家安全组织:行政部门组织专门委员会致国会报告,1949年2月》(The National Security Organization:A Report to the Congress by the Commission on Organization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of the Government,February 1949),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49年印行。关于当时学界和政界人士的相关讨论,见《美国政治学评论》组织的专题研讨——“国防和民主社会讨论会”("National Defense and Democratic Society:A Symposium")。有关讨论情况载于《美国政治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43卷(1949年6月号)。
(42)爱德华·米德·厄尔编:《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Edward Meade Earle,ed.),纽约:现代图书馆1937年版,第32、204页。
(43)《埃伯斯塔特报告》,第51~52页。
(44)著名政治学家厄尔(Edward Mead Earle)于194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召集的一次以“国家安全”为题旨的会议,讨论军事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关系,被认为对“国家安全”理念的传播有特殊意义。耶尔金:《破碎的和平》,第194、450~451页。
(45)阿尔弗雷德·桑德尔:《杜鲁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75页;罗伯特·卡夫:《费迪南德·埃伯斯塔特、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和对一体化国防动员计划的寻求(1947~1948)》,《公共历史学家》(Robert Cuff,"Ferdinand Eberstadt,the National Security Resources Board and the Search for Integrated Mobilization Planning,1947~1948,"The Public Historian)第7卷(1985年秋季号),第41页;《福莱斯特尔日记》,第163页,第167页。
(46)耶尔金:《破碎的和平》,第193~194页;相关讨论另见:加布伦斯基:《国家安全国家的状态》,第3~4页。
(47)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第26页。
(48)厄内斯特·梅:《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安全》(Ernest R.May,"National security in American History"),格雷厄姆·艾利森、格里高利·特雷沃顿编:《对美国安全的再思考:走出冷战,走向世界新秩序》(Graham Allison and Gregory F.Treverton,eds.,Rethinking America's Security:Beyond Cold War to a New World Order),纽约:W.W.诺顿1992年版,第94~106页。
(49)《埃伯斯塔特报告》,第17页。
(50)耶尔金:《破碎的和平》,第194页。
(51)桑德尔:《杜鲁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77页。
(52)西德尼·索尔斯:《国家安全政策的规划》,《美国政治学评论》(Sidney W.Souers,"II.Policy Formulation for National Securit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43卷(1949年6月号),第535页。
(53)耶尔金:《破碎的和平》,第219页。
(54)当时有代表性的学界对总体战的讨论,见1942年《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鉴》(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组织的专题研讨“为总体战而组织”(Organizing for Total War),第220卷(1942年3月号)。对总体战问题的经典论述,可见: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等译:《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489页。该书首版于1948年。
(55)《埃伯斯塔特报告》,第18~20页。
(56)莱夫勒:《国家安全》,第123~125页。
(57)肯尼斯·A.奥斯古德:《总体冷战:美国在“自由世界”的宣传(1953~1960)》(Kenneth A.Osgood,' Total Cold War:U.S.Propaganda in the "Free World,1953~1960"),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
(58)亨利·杰克逊:《主要问题》(Henry Jackson,"Major Problems"),杰克逊主编:《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页。
(59)如1949年夏开始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内部安全跨部委员会”(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Internal Security)。
(60)牛可:《自由国际主义与第三世界~美国现代化理论兴起的历史透视》,《美国研究》2007年第1期,第39~47页。
(61)文安立:《全球冷战: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我们时代的形成》(Odd Arne Westad,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2)阿隆·弗雷德伯格:《在堡垒国家的阴影下:美国的反国家主义及其大战略》(Aaron L.Friedberg,In the Shadow of Garrison State:America's Anti-Statismand Its Grand Strateg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66页;《为什么美国没有变成堡垒国家?》,《国际安全》(Aaron Friedberg,"Why didn't the United States Become a Garrison St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16卷(1992春季号),第134~135页。
(63)卡夫:《费迪南德·埃伯斯塔特、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和对一体化国防动员计划的寻求(1947~1948)》,第37~52页。
(64)阿隆·弗雷德伯格:《为什么美国没有变成堡垒国家?》,第129~132页;《在堡垒国家的阴影下》,第199~295页。
(65)保罗·A.C.考伊斯廷南:《军事—工业复合体》(Paul A.C.Koistinen,"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斯坦利·L.库特勒主编:《美国历史词典》(Stanley I.Kutler,ed.in chief,Dictionary of American History),第3版,纽约:汤姆森—盖尔2003年版;第376~378页。
(66)关于战后最初由学者和政府官员对普遍军训制度的讨论,见当年《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鉴》(Annals of American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组织的专辑(Universal Military Training and National Security)下的多篇文章,第241卷(1945年9月号)。
(67)《杜鲁门回忆录》,第66~67页。
(68)中文文献中通常译为“新面貌”。
(69)“深度国防”观念起源于二战时期,系指“从各个家庭和工厂延伸到海外战争前线”的国防体系,参见:安德鲁·格罗斯曼:《为冷战做准备:美国的国内战线动员,国家扩张和公民防务(1946~1963)》,第68、89页。关于时人对核战争压力下建立公民防务体系的必要性的阐述,见:克林顿·L.罗西特:《原子时代的宪政独裁》,《政治评论》(Clinton L.Rossiter,"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 in the Atomic Age," The Review of Politics)第11卷(1949年10月号),第413~416页。
(70)二战期间的用语是“civilian defense”。见:乔安尼·布朗:《“A代表原子,B代表炸弹:美国公共教育中的公民防务”》,《美国历史杂志》(JoAnne Brown,"'A Is for Atom,B is for Bomb':Civil Defense in American Public Education,1948~1963,"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5卷(1988年6月号),第69页。
(71)(72)格罗斯曼:《为冷战做准备》,第8~77、103~135页。
(73)格罗斯曼:《为冷战做准备》,第150~193页;简·安·库什玛:《为灾难做准备:紧急管理计划的执行》(Jane Ann Kushma,"Preparing for Disaster:Implementing Emergency Management Programs"),得克萨斯大学阿林顿分校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关于民防计划在州层面执行的一些情况,可参见当时纽约州民防委员会主任的一篇文章,劳伦斯·威尔金森:《公民防务问题》,《政治科学院通报》(Lawrence Wilkinson,"Problems of Civil Delense,"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第24卷(1951年1月号)。
(74)关于战后美国在公立教育中推行公民国防的情况,参见:乔安尼·布朗:《A代表原子,B代表炸弹:美国公共教育中的公民防务》,第68~90页。
(75)肯尼斯·奥斯古德:《总体冷战:美国在“自由世界”的宣传(1953~1960)》,第11~12页。
(76)肯尼斯·奥斯古德:《心灵和头脑:非常规冷战》,《冷战研究杂志》(Kenneth A.Osgood,"Hearts and Minds:The Unconventional Cold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第4卷(2002年春季号),第85~88页。
(77)斯坦利·L.福尔克:《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之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政治学季刊》(Stanley L.Falk,"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Under Truman,Eisenhower,and Kenned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79卷(1963年9月号),第416页。
(78)关于行动协调委员会和美国新闻署创建的过程及其与“心理战”的关联,参见:奥斯古德:《总体冷战:美国在“自由世界”的宣传(1953~1960)》,第70~83页。
(79)奥斯古德:《总体冷战》,第78~79页。
(80)摩根索曾区别出六种目标不同的外援:人道主义外援、基本生存外援、军事外援、贿赂性外援、威望外援和经济发展外援。汉斯·摩根索:《对外援助的政治理论》,《美国政治学评论》(Hans Morgenthau,"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56卷(1962年6月号),第301~309页。
(81)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对外援助计划的行政管理》(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Administrative Aspects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Assistance Programs),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57年版,第5~6页。
(82)沃农·W.拉坦:《美国发展援助政策:对外援助的国内政治因素》(Vernon W.Ruttan,United State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Policy: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Foreign Aid),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1、50~51、55~58、62~68页。USAID以往译为“国际开发署”。
(83)H.亨利·兰姆布莱特:《政府和科学之间麻烦不断而又至关重要的关系,及其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公共管理评论》(H.Henry Lambright,"Government and Science:A Troubled,Critical Relationship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第68卷(2008年1~2月号),第5~7页。
(84)哈维·M.萨波尔斯基:《科学和海军:海军研究办公室的历史》(Harvey M.Sapolsky,Science and the Navy:The History of the Office of Naval Research),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第37~38页,第77页;阿隆·弗雷德伯格:《科学、冷战与美国的国家》,《外交史》(Aaron L.Friedberg,"Science,the Cold War,and the American State," Diplomatic History)第20卷(1996年冬季号),第108~109页。
(85)弗雷德伯格:《科学、冷战与美国的国家》,第108~109页。类似题旨的讨论,另见:弗雷德伯格:《美国和冷战军备竞赛》(Aaron L.Friedbe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ld War Arm Race"),文安立编:《考察冷战:路径、解释和理论》(Odd Arne Westad(ed),Review The Cold War:Approaches,Interpretations,Theory),伦敦:弗兰克·卡斯2000年版,第207~231页。
(86)至1952年,国家实验室体系包括位于阿尔贡(Argonne)、伯克利、布鲁克海文(Brookhaven)、洛斯阿拉莫斯、橡树岭(Oak Ridge)和利佛摩尔(Livermore)6处国家实验室。其研究不仅涉及核科学,也涉及物理学和生物学领域里的基础性研究,见:J.L.海尔布隆:《美国的国家实验室体系(1947~1962)》(J.L.Heilbron,"The National Laborator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1947~1962"),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
(87)马克·索洛维:《引言——冷战时期的科学和国家:模糊的边界和有争议的遗产》,第166、168页。关于战后科学和公共政策的全面讨论,见:玛格丽特·罗西特:《二战后的科学和公共政策》,《奥西里斯》(Margaret W.Rositer,"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since World War Ⅱ," Osiris)第2系列第1卷(1985年),第274~294页。
(88)关于“大科学”和“国家安全国家”的关系,参见:彼得·加里森、布鲁斯·希夫里编:《大科学:大规模研究的发展》(Peter Galison and Bruce Hevly,Big Science:TheGrowth of Large~Scale Research ),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罗纳德·C.托比:《评论:国家安全国家中的大科学》,《美国史评论》(Ronald C.Tobey,"Review:Big Science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第12卷(1984年3月号),第135~138页。
(89)伊丽莎白·T.克劳福德、阿尔伯特·D.比德尔曼:《编者前言》(Elisabeth T.Crawford and Albert D.Biderman,"Editor's Introduction"),克劳福德·比德尔曼编:《社会科学家与国际事务》(Elisabeth T.Crawford and Albert D.Biderman,eds.,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A Case For A Sociology of Social Science),纽约:约翰·威利父子公司1969年版,第5~8页。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在战争中动员社会科学家的组织机制和人脉,对战后国家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的构筑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贝蒂·亚伯拉罕森·德桑茨:《美国学术共同体与美苏关系:研究分析处及其遗产,1941~1947年》(Betty Abrahamsen Dessants,"The AmericanAcademic Community and United States-Soviet Union Relations: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 and Its Legacy,1941~1947"),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论文(1995年)。
(90)克里斯托弗·辛普森:《大学、帝国和知识生产:导言》(Christoper Simpson,"Universities,Empire,and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An Introduction"),辛普森编:《大学与帝国:冷战中的金钱与社会科学》[Christoper Simpson (ed.),Universities and Empire:Money and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纽约:新出版社1998年版,第xii页。
(91)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可分别参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国际组织和国际运动小组委员会:《行为科学与国家安全,第四号报告》(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Movement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Report No.4),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66年印行,第1R~10R页;路易斯·默顿:《国家安全与地区研究:对冷战的知识反应》,《高等教育杂志》(Louis Mort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Area Studies:The Intellectual Response to the Cold War,"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第34卷(1963年3月号),第142~147页;罗伯特·麦考吉:《国际研究与学术事业:美国学术圈的一个组成部分》(Robert A.Mc Caughey,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 prise:A Chapter in the Enclosure of American Learning),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140页;布鲁斯·卡明斯:《边界错置:冷战中和冷战后的地区研究和国际研究》(Bruce Cumings,"Boundary Displacement: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辛普森编:《大学和帝国》,第159~188页;尼尔斯·吉尔曼:《掌握未来的人:冷战时期美国的现代化理论》(Nils Gilman,Man darins of the Future: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2)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系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国际问题中心的副产品。阿兰·尼德尔:《“真理是我们的武器”:特洛伊计划、政治战和国家安全国家中的政学关系》,《外交史》(Allan A.Needell," 'Truth Is Our Weapon':Project Troy,Political Warfare,and Govern ment-Academic Relations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Diplomatic History)第17卷,1993年第3期,第399~420页;唐纳德·布莱克默尔:《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初创年代(1951~1969)》(Donald Blackmer,The 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Founding Years,1951~1969,马塞诸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2002年版,第xi~xix页,第1~34页。
(93)朗·罗宾:《制造冷战敌人:军事——学术复合体中的文化和政治》(Ron Robin,Making Cold War Enem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Military Intellectual Complex),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4)保罗·哈蒙德:《作为跨部门协作的工具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解释和评估》,《美国政治学评论》(Paul Y.Ham mond,"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s a Device for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An Interpretation and Appraisal,"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54卷(1960年12月号),第899页;卡尔·英德尔弗斯、劳奇·约翰逊编:《致命的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Karl Inderfurth and Loch Johnson,eds.,Fateful Decisions:Inside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xiii页。
(95)罗伯特·卡特勒:《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进》,《外交》(Robert Cutler,"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oreign Affairs)第34卷(1956年4月号),第441页。
(96)“高位政治”和“高位政策”(high policy)的观念在冷战初期开始出现和流播,其基本含义是涉及国家生存和安全的政策领域,隐含于其中的原则是低位政治(low politics)服从于高层对外决策、国内政治不应该影响国家安全政策。简略说明见:I.M.德斯特勒:《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政策咨议:30年的经验教训》,《世界政治》(I.M.Destler,"National Security Advice to U.S.Presidents:Some Lessons from Thirty Years," World Politics)第29卷(1977年1月号),第172页。
(97)亨利·杰克逊:《重大问题》,第3、7页。
(98)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74页。
(99)德斯特勒:《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政策咨议》,第147~148页;桑德尔:《杜鲁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1945~1947)》,第369~370页。
(100)哈蒙德:《作为跨部门协作的工具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解释和评估》,第899页。
(101)《埃伯斯塔特报告》,第7页。
(102)1947年《国家安全法》的用语是:“就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的统筹向总统提出建议,以使各军种和政府各部门机构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事务上更有效地协作”,为此NSC“就与美国的实际和潜在的军事力量相关的目标、义务和危险予以评估和研判,并对……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各部署机构的共同利益予以考虑。”(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103)霍根:《铁十字》,第56~57页;安娜·卡斯藤·尼尔森:《杜鲁门总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变》,《美国历史杂志》(Anna Kasten Nelson,"President Truma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2卷(1985年9月号),第362~363。关于《国家安全法》起草过程中围绕NSC的争议,见:桑德尔:《杜鲁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1945~1947年》,第375~380页。
(104)尼尔森:《杜鲁门总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变》,第364~365页;桑德尔:《杜鲁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1945~1947)》,第387页。
(105)《福莱斯特尔日记》,第320页。
(106)福尔克:《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之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06页;尼尔森:《杜鲁门总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变》,第377页。
(107)尼尔森:《杜鲁门总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变》,第370页。
(108)西德尼·索尔斯:《国家安全政策的规划》,第535~537页。
(109)福尔克:《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之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07~408页。
(110)关于杜鲁门对NSC在决策体系中的政策协调和提供咨议作用的积极看法,参见: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72页。
(111)尼尔森:《杜鲁门总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变》,第373~374页。
(112)福尔克:《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之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15页。
(113)关于NSC心理战略委员会设立的详细情况,可参见:约翰·普拉多斯:《枢机中人:从杜鲁门到布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史》(John Prados,Keepers of The Keys: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rom Truman to Bush),纽约:威廉·莫罗公司1991年版,第50~56页。
(114)戴维·罗斯科普夫:《运作世界: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权力设计师的内幕故事》(David J.Rothkopf,Running the World:The Inside Sto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Architects of American Power):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04年版,第57~58页。
(115)关于艾森豪威尔的执政风格及其对NSC机制的影响,见:弗雷德·格林斯坦、理查德·伊默尔曼:《有效的国家安全咨议:重新发现艾森豪威尔的遗产》(Fred Greenstein and Richard Immerman,"Eff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ing:Recovering the Eisenhower Legacy"),卡尔·英德尔弗斯、劳奇·约翰逊编:《致命的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第46~52页;伊默尔曼:《一个艾森豪威尔修正派的告白:苦涩的重估》,《外交史》(Richard Immerman,"Confessions of an Eisenhower Revisionist:An Agonizing Reappraisal," Diplomatic History)第14卷(1990年7月号),第319~342页。美国历史学家对艾森豪威尔任期的评价前后有较大变化。其行使总统权的风格一度曾被广泛认为是“放手式的”(disengaged),但后来的研究表明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他牢牢地掌握着总统权。另参见:史蒂夫·尼尔:《作为总统的艾森豪威尔》(Steve Neal,"Eisenhower as President"),约翰·加拉蒂编:《历史的观点:(美国传统)名文选》(John Garraty,ed.,Historical View points:Notable Articles from American Heritage)第2卷,第5版,纽约:哈珀和罗1987年版,第393~394页。
(116)罗伯特·卡特勒:《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进》,第448~449页;福尔克:《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之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20~421页。关于PB和OCB的建立和运行详细情况,见:中央情报局:《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史》(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Organizational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uring the Truman and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华盛顿:中央情报局印行,[无印行时间],第31~48页。
(117)(120)卡特勒:《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进》,第452、442页。
(118)艾森豪威尔从就职到1956年1月的3年间共举行145次会议,而整个杜鲁门政府的五年多时间仅举行128次。卡特勒:《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演进》,第442页。
(119)(122)普拉多斯:《枢机中人》,第63、65页。
(121)德斯特勒:《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政策咨议:30年的经验教训》,第153页。
(123)此即通常所说的“国家安全顾问”(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1969年改称为"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沿用至今。
(124)约瑟夫·G.鲍克:《白宫办公厅与国家安全助理:水边线上的友谊与冲突》(Joseph G.Bock,The White House Staff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t:Friendship and Friction at the Water 's Edge)纽约:绿木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4页。
(125)关于NSC办公厅和国家安全顾问的源流演变,见安德鲁·普莱斯顿:《小国务院:麦乔治·邦迪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厅(1961~1965)》,《总统研究季刊》(Andrew Preston,"The Little State Department:McGeorge Bundy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1961~1965,"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第31卷(2001年12月号),第635~641页。
标签:军事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美国军队论文; 军事研究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陆军论文; 世界现代史论文; 国家安全局论文; 国家安全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