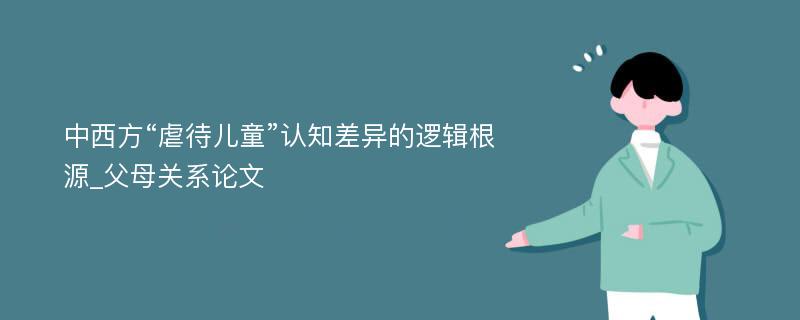
中西方“儿童虐待”认识差异的逻辑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方论文,根源论文,逻辑论文,差异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儿童虐待”(child abuse)是备受国际社会重视的社会问题,一般指有责任抚养、监管及有操纵权的人对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造成伤害的行为。当今,在西方国家,新闻媒体对儿童虐待案例有长期的追踪报道,学术界有多年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儿童虐待课程,大量专业论文发表在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工作、法律等主流刊物及关于儿童虐待的专门期刊上,特别是众多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致力于儿童虐待的防治工作,对受虐儿童的保护及服务已经成为儿童福利的重心。儿童虐待在我国和西方一样也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父母打孩子致伤亡、饿死女童、教师体罚学生、儿童性侵犯等案例常见于媒体。调查显示,在河北省1762个大学生中,76.2%的人在儿童期有遭受虐待的经历,儿童期躯体虐待发生率为59.4%,精神虐待为61.5%,性虐待为10.2%①。但儿童虐待问题在我国一直未引起政府、社会和学界的高度关注,主要表现在,没有明确的主管机构,没有儿童虐待报告制度和儿童保护工作程序,更缺乏儿童保护服务和相关的研究。司法部门对于那些没有造成受虐儿童重伤和死亡的案例“不告不理”,即使报告了也缺乏有效的干预和保护机制。因此,本文想从探讨中西方社会对儿童虐待的认识、重视程度以及为什么在处理过程会有差异问题入手,并试图从历史、文化、政治,特别是理论方面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内在逻辑和根源。 一、“儿童虐待”的社会建构及其历史逻辑 中西方对“儿童虐待”概念、问题性质及重要性的认识差异是历史形成的,深度探究还有其社会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 1.对“儿童虐待”问题的社会建构 虐待儿童现象在中西方历史上都长期存在,从首次在西方引起社会关注到被建构为“社会问题”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它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74年美国“玛丽·艾伦案”到20世纪40年代,欧美开始关注残忍虐待儿童问题。艾伦案是世界上首个因虐待儿童而被刑事检控的案件,由于当时缺少保护儿童的法律,而保护动物的法律比较有力,玛丽不得不被当作动物解救出来,唤起了人们对儿童虐待的意识②。1874年,美国成立了第一个专门防止虐待儿童的民间组织。1889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针对儿童虐待的《预防虐待儿童和保护儿童法案》(简称《儿童法》),第一次赋予了国家干预家庭的权力。随后,加拿大、欧州各国及美国相继立法保护儿童,但当时对儿童虐待仅是间断的关注。 第二个时期从1946年到20世纪70年代。儿童虐待首先在美国由一个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变成受到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并经历了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③④。这个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⑤:(1)“发现”阶段,1946年,美国儿科放射医生借助新科技X光发现许多不明原因的婴幼儿骨折及血肿,后来怀疑是父母或监护人所为;(2)“传播”阶段,1962年,美国儿科医生Henry Kempe⑥和他的同事发表了《被殴儿童综合征》(The Battered-Child Syndrome)一文,确定地判断X光片中的某些伤害是儿童父母故意造成的,将儿童虐待界定为一个临床可诊断的医学和躯体症状,并建议医生应该觉察和举报虐待案件。随后,对儿童虐待的关注扩展到社会组织、政府机构和媒体;(3)“巩固”阶段,即制度化应对阶段,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各国都针对儿童虐待问题颁布法案,明确了处理这个问题的责任机构,特别是美国1974年针对儿童虐待的第一个联邦立法《儿童虐待防治与处理法》通过,规定了专业人员(医护人员、教师和保育人员、警察和社工等)对虐待儿童的强制报告制度;(4)“具体化”阶段,虐待儿童成为公众、机构和专家自然地、长期关注的社会问题。20世纪60年代,儿童虐待属于医学问题,70年代,它被认为是超出医学领域的社会问题⑦⑧。到20世纪末,儿童虐待被认为是一个实质性的、严重的全球性问题⑨⑩,防治儿童虐待成为国际行动的发展脉络。 纵观虐待儿童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并很快在西方国家和地区得到呼应,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基础及发展逻辑,其形成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因素:(1)前期积累,从19世纪末开始,人们为防治虐待儿童和保护儿童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如政府为保护儿童立法,非政府组织为防止虐待儿童所做的努力;(2)社会发展和对“儿童”认识的变化,中世纪以前,儿童被看成是小成人,参与成人事务,并承担独立责任,不被认为需要特别照顾。中世纪以后有了“童年”概念,人们认识到童年的独特性和重要性(11),儿童开始被认为是弱小群体,需要特别照顾和保护,过去父母对待儿童的一些行为,现在看来可能是有问题的。20世纪,随着对“儿童”和“童年”的重视和研究,儿童的身体、情绪和心理需要不断受到关注,形成了对儿童权利的公共意识;(3)社会运动的影响,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妇女运动和70年代的儿童权利运动促使社会关注家庭暴力问题的严重性,重视保护妇女儿童;(4)科技的发展,X射线的发明为临床医学发现虐待儿童提供了技术条件和科学依据;(5)相关团体的推动,为儿童虐待问题积极倡议的三个利益团体及其专业人员起到重要作用(12),即司法团体、医疗团体和社会福利服务团体。此外,大量的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宣传都推动了儿童虐待问题的“传播”,并构建了形成的基础。 由于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认知等的不同,不同国家对社会问题的建构可能是不同的。正如在我国“儿童虐待”至今未被建构为社会问题,人们还没有把很多西方认为的虐儿行为看作是虐待儿童,客观存在的虐儿现象还缺乏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力量的持续关注和集体建构。 2.对“儿童虐待”概念的社会建构 在西方“儿童虐待”概念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在20世纪60年代,儿童虐待还只是指“被殴儿童综合症”,仅包括父母故意施暴造成婴幼儿可诊断的严重身体伤害;20世纪70年代,儿童虐待的对象由婴幼儿扩大到不满18周岁,形式由身体虐待扩展到还包括性虐待和非身体伤害,如心理虐待;20世纪80年代,儿童虐待包括对儿童福利负有责任的所有人对儿童造成的身体的或心理的伤害,以及忽视等多种形式和多种表现,“虐待儿童”(child abuse)一词完全取代了“殴打儿童”(baby battering)和“非意外伤害”(non-accidental injury);20世纪9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13)对儿童虐待的主流界定是“指对儿童有责任抚养、监管及有操纵权的人做出对儿童的健康、生存、发展及尊严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伤害行为,包括各种形式的身体或情感的有害对待、性虐待、忽视或疏忽对待、经济的或其它剥削”。虐待儿童概念的外延越来越扩大,这与儿童地位的不断提升和保护力度密切相关。 然而,我国至今没有“儿童虐待”的官方界定,仅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家庭暴力”和“虐待”有所界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以此可推断出我国的界定是“虐待”比“家庭暴力”严重。研究也发现,受访儿童和父母对儿童虐待的理解明显不同于欧美国家,认为父母恶意地、无缘无故地、经常地打孩子,造成孩子身体或心理的严重伤害才是虐待儿童。这也是国人觉得虐待儿童现象不多的原因之一。 分析发现中西方对儿童虐待概念的理解主要有两个区别:一是虐待主体不同,西方既包括家庭成员,也包括家外受委托照顾及管教儿童的人士,如教师、保姆、福利机构工作人员等,而中国法律对虐待、虐待罪的规定仅局限于家庭成员;二是虐待的内涵和外延不同,西方的虐待儿童几乎囊括了责任人对儿童的所有伤害行为,既包括实际的伤害,也包括可能的、潜在的伤害;既包括“作为”,也包括“不作为”,如疏忽照顾、独留幼儿在家导致儿童受伤害。我国的虐待是指“作为”造成的实际伤害,并具有持续性和经常性的特征。显然,我国儿童虐待的外延明显比西方界定得窄。 二、“儿童虐待”认识差异的文化逻辑 中西方对儿童虐待的认识差异与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和儿童观密切相关,不同的社会建构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内在逻辑。 1.中西方文化不同的价值取向 首先,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家庭、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中西方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西方社会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强调权利本位,注重人权、平等和自由,不强调个人对家庭的服从和义务。从提出儿童权利问题开始,儿童作为独立个人的权利就备受重视。而中国社会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强调义务本位,虽然已经开始重视人的权利及儿童权利,但尚无权利本位的法律文化;特别是在中国特有的家庭文化和伦理制度下,“家庭本位”的价值取向长期占主导地位,注重个人对家庭的服从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义务;“孝”处于中国家庭伦理的核心地位,“孝”不仅包括子女对父母的道德义务,还有“无违”的含义,如无违于父母的意志,“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儿童主体性的价值。因此,儿童作为独立个人的权利在中国社会尚未成为普遍的公众意识。 2.中西方不同的儿童观 儿童观是指成人社会对儿童的根本观点和看法,包括如何看待童年期的特点、意义、价值以及儿童的权利和地位等。成人世界如何看待儿童直接关系着他们如何对待儿童。 在西方儿童观主要经历了由“神本位”到“人本位”再到“儿童本位”的变化过程。在神学占统治地位的欧洲中世纪,建立在原罪的宗教信仰上的“神本位”儿童观认为“儿童是有罪的”,体罚被认为可以“将罪恶打出儿童的身体”而被接受。18世纪以来,伴随着对人的主体性认识的加深,儿童在启蒙运动的思潮中被“发现”,出现“儿童天生无辜”的思想,“神本位”的儿童观逐渐被摒弃,建立了“人本位”的儿童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形成了研究儿童的热潮,汇聚成了“儿童研究运动”,使“童年”这一概念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童年不仅被认为是根本区别于成年的人生阶段,儿童被认为在每一阶段都有其特点与需求(14)。因此,儿童作为不同于成人的特殊群体不应与成人一样承担为国家和家庭工作的责任,而应该受到特殊的照顾、教育和保护,于是欧美各国纷纷立法保护儿童。在被称为“儿童的世纪”的20世纪里,对儿童的研究空前繁荣,童年社会学的研究也使人们重新认识儿童群体的主体性、多样性和童年的重要性,西方社会尊重儿童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社会在儿童权利保护的立法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1924年“救助儿童国际联盟”制定的《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首次提出“儿童权利”概念,明确了成人负有抚养照护儿童的义务。195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扩展了儿童的权利,提出了儿童“最大利益”的原则,儿童成为权利主体。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把保护儿童权利的责任强加给各国政府,成为新儿童观的法律保障。西方现代儿童观强调以儿童为本位,认为儿童具有“人”的完整地位,而非“正在形成中的人”;童年期本身是有价值的,而不只是通往成人期的过渡阶段,童年期的经历会影响成年后的发展;儿童是权利主体,与成人一样拥有基本的人权和尊严,儿童与成人是平等的;儿童是具有独立主体性的人,有其特殊的需求。 然而,在我国从未发生西方社会的“童年革命”和“儿童研究运动”。“家庭本位”和“义务本位”的儿童观一直在我国居于主导地位,“子女是家庭的延续,儿童是家庭的附属品,其价值在于对家庭的贡献。家庭保护的目的不在儿童自身,而在通过儿童使家庭(家族)兴盛”(15)。正如,儿童长期没有独立的人格,父母乃至整个社会对儿童教育和照护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儿童“将来”的期望,而忽视了儿童“现在”的主体地位,儿童的权利和童年期的需要长期不被重视。1991年,我国签署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并制定了第一部保护儿童的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不仅比西方儿童保护立法晚了一个世纪,而且是在外力推动下的立法,缺乏西方那样的关于儿童权利的理论和思想基础以及法律准备,对儿童权利的认知和保护更多的是体现在法律条文中,《儿童权利公约》所体现的新儿童观并未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可。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不同的儿童观直接影响着各自对儿童虐待问题的态度。正如,西方社会极其重视儿童权利,侵犯儿童权利、破坏童年的儿童虐待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和忽视成为必然选择。而在中国儿童权利观念引自西方,儿童及成人的权利意识均不强,特别是当家庭成员侵犯儿童权益时,如父母“为了孩子好”打孩子不被认为是儿童虐待,往往被社会宽容,而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三、“儿童虐待”认识差异的理论逻辑 中西方在儿童虐待问题上的认识差异有其理论根源,它涉及对儿童、家庭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家庭正义”,特别是亲子关系等问题的认识。 1.儿童、家庭和国家的关系 关于儿童、家庭及父母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可以概括出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儿童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父母可以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自由处置;第二种观点认为,儿童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而是国家的公民,父母是国家的“代理人”,国家和社会基于对父母的信任,把儿童托付给父母照管和监护;目前占主流地位的第三种观点主张前两种观点的结合,父母和国家都对儿童负有责任和相应的权利(16),“儿童的健康、福利以及养育都与国家的命运及政府的责任息息相关”(17),父母对儿童的照顾和监护受国家和社会的监管。 从理论上说,国家对儿童的责任是通过父母或家庭实现的,只有当父母缺位或家庭缺失时,国家才全面承担照顾儿童的责任。西方国家对儿童的责任一般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一是制定政策法律,规定父母养育儿童的责任和标准;二是为父母养育儿童提供服务和支持;三是赋予除了父母之外与儿童接触的专业人员(社工、医生、教师等)监督父母养育行为,并举报父母对儿童不当行为的权利和义务;四是当父母侵犯儿童的权益时,国家权力机构介入家庭,严重情况下依法剥夺父母的监护权;五是当父母被剥夺监护权或不能履行监护责任时,国家提供替代性照顾。相比之下,我国国家实现对儿童责任的方式以及干预家庭的程度和西方不同,除了笼统的原则性的法律规定外,缺少父母养育儿童的标准、国家或社会的监督措施以及儿童和家庭福利服务等,这都使得在我国预防和干预儿童虐待缺少保障和立足点。 国家是否干预以及如何干预家庭内部儿童虐待问题,还涉及“家庭正义”即家庭内部正义的讨论。传统的西方政治哲学一般将家庭排除在正义之外,认为家庭是充满爱和情感的私领域,不适合讨论正义问题(18)。“非介入理论”假设家庭本身是正义的,强调尊重父母的自治和权威,奉行最低限度的干预原则,限制国家对家庭的介入行为(19)。但是,最低限度的干预原则往往忽视儿童的权利,特别是当家庭内部出现对儿童的虐待和剥削时。在这方面现代西方社会是这样去思考“家庭正义”问题的,它强调追求家庭内部的正义,追求保护儿童的最大权益,以致于国家干预的“介入理论”开始盛行,国家被附加了监管家庭和保护儿童的义务,政府被期待通过法律和社会福利手段介入父母子女关系,以避免儿童遭到虐待或忽视。然而,中国社会几乎不讨论“家庭正义”问题,国家很少介入家庭内部事务,父母如何养育和管教儿童被认为是家务事,只要没有故意造成儿童重伤或死亡,公共权力一般不干预。 2.亲子关系与权力关系 “亲子之间的关系成分不外情与权”(20),亲子关系既是一种基于血缘的情感关系,也是一种权力关系或支配关系。在当代主流研究中认识权力问题可以概括为两种理论模式,即权力的所有模式和权力的关系模式。前者认为权力是特定个体或群体的所有物,后者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的产物和社会的建构,一种关系中的有权者可能是另一关系中的无权者。据此可以把亲子之间的权力关系分为“客观权力”和“主观权力”。客观权力由家庭结构、经济关系等结构性因素决定,如儿童对父母经济上的依赖使父母对儿童拥有客观权力;主观权力是社会文化、政策法律等知识建构的结果,二者相互联系,共同赋予父母对儿童的管教权力。 然而,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政策法律对父母的权力有不同的建构。西方家庭人际关系基本上没有等级结构,亲子之间注重平等与友爱,父母的权力在国家监管中被限制,因此,父母打孩子在家庭伦理和法律中都是不被接受的。相比之下,中国父母的权力在长幼有序和“孝”文化传统中被放大,父母对儿童的暴力行为常被合理化为管教权力,而不被认为是儿童虐待。 四、“儿童虐待”认识差异的政治逻辑 中西方对儿童虐待认识的差异,特别是对这个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差异与不同的执政理念、法律制度和政府的关注点也有逻辑关系。 差异之一:我国政府强调和谐稳定是大局,相对于西方对“人权”的重视,我国更强调“人和”。相比较而言,西方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更偏重于正义,法律是西方追求正义实现的主要途径。而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导价值取向是和谐与稳定,目标为“无讼”,法律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工具,其功能也包括维护家庭的稳定,即“调解”成为其重要的司法传统,这是司法机关一般不剥夺父母监护权的原因之一,即使《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可以剥夺侵权父母的监护权,但实践中也难以执行。与西方法律先行不同,我国的立法长期滞后,至今没有具有可操作性的防治儿童虐待的法律,也没有儿童福利法,使现有法律中禁止虐待儿童的原则性规定很难落到实处。国家和社会不愿干预家庭内部事务,家庭内部更多地讲人伦和感情,而不是讲法律和权利,因此,我国对于家庭内部的儿童虐待一直缺乏有力的法律约束。 差异之二:尽管说防治儿童虐待是很多西方国家儿童福利的重心,但至今还未被我国视为儿童福利问题,还未进入政府议程。目前,从我国儿童福利领域的情况看主要矛盾是与社会稳定关系较大的弃婴、孤儿、流浪儿童和被拐卖儿童等问题,这仍是国家的传统责任,正如我们所关注的贫困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等问题急需解决。由于儿童虐待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对国家和社会稳定的直接影响不大,不被政府认为是社会问题和主要矛盾,也难以出政绩,因此难以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 根据台湾学者宁应斌(21)的分析,他认为,把“child abuse”翻译成“恶待”、“误待”还是“虐待”,也有政治意涵,因为西方“虐待儿童”概念并不仅仅是体罚之类的行为,还包括了“不当的”教养方式和环境,含义非常广泛,它可能把造成不当教养儿童的父母列入虐待儿童的范围。如果我国很多父母因不当教养、忽视孩子而涉嫌儿童虐待,那么,这既不符合父母和家庭的利益,也不符合政府的利益,政府目前缺乏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去干预和解决这样的问题。 差异之三:中西方对儿童保护的理解不同,我国政府关注“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而不是西方重视的“儿童保护”制度。在西方,儿童保护是指国家依法救助保护受到或可能受到暴力、虐待、忽视和其他形式伤害的儿童的各种制度、措施和服务,使儿童能有安全的成长环境,即防治儿童虐待。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儿童保护制度有四个基本要素(22),即儿童保护的责任主体机构、公民举报和专业人员强制报告相结合的责任制度、专门针对儿童保护的案件处理程序、替代性的国家监护制度。从这个角度说,目前,我国缺少这种狭义的儿童保护制度,虐待儿童仅被作为刑事案件处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按照责任主体把未成年人保护分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司法保护和社会保护。其中,社会保护是指政府和社会对儿童健康成长应该承担的保护责任,范围很广,但未聚焦于儿童虐待问题。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既不同于西方的儿童保护,也不同于西方从社会保障、社会政策角度理解的社会保护。这些理解和认识上的差异也影响了中西方对儿童虐待问题的重视程度。 五、我国应对“儿童虐待”问题的思路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西方对儿童虐待认识及重视程度的差异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不应该干预儿童虐待问题,因为,历史、文化和政治上的差异都不能成为规避儿童虐待问题的借口,文化准则不可以超越儿童的人权。特别是在《儿童权利公约》的法律约束力下,联合国拒绝任何国家以文化等因素为借口,声明所有联合国成员必须摒弃一切导致儿童虐待的文化行为或习俗(23)。公约中明确了政府保护儿童、对儿童虐待进行干预的责任:“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在受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这类保护性措施应酌情包括采取有效程序以建立社会方案,向儿童和负责照管儿童的人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采取其他预防形式,查明、报告、查询、调查、处理和追究前述的虐待儿童事件,以及在适当时进行司法干预。”(第19条) 我国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约国,从保护儿童的角度看,目前对虐待儿童问题的认识和干预是滞后的,法律和政府的角色是缺位的。从社会现实看,当今中国社会竞争激烈,家庭中的儿童在应试教育和升学压力下,往往容易受到家长溺爱和强权的双重压力,此外,还将面对各种形式的家庭暴力,家庭已经不能为儿童提供完全有效的保护(24)。因此,我们认为,整个社会需要对儿童虐待问题有所警觉,并给予更多的关注,我们应建立儿童虐待应对体系,使儿童保护制度更加全面和有效,实现保护儿童免受伤害的理念和目标。尽管,中国内地的国情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庞大的儿童群体、不发达的社会服务组织、不专业的工作人员以及各种传统观念,都使我国防治儿童虐待工作处于“万事开头难”的阶段,但我们都不应回避。我们认为,现阶段应对儿童虐待问题的思路如下。 首先,需要明确我国防治儿童虐待的政府主管机构。目前,我国的儿童保护工作分散在民政、公安、教育、卫生、妇联、共青团等多个部门,各部门各行其是,儿童虐待发生时可能没有主管部门提供及时有效的处置。因此,有了职责明确的政府主管机构才是把“禁止虐待儿童”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的行政基础。 其次,需要明确界定中国本土的儿童虐待概念。在针对我国基本国情又避免照搬西方界定的前提下,避免“儿童虐待”扩大化。我们认为,在目前我国公众对儿童虐待问题普遍缺乏了解和认识不足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提高人们对儿童虐待概念、形式、问题性质、后果和危害性的认识,自觉减少虐待及忽视儿童的行为。 再次,需要两手抓,一手抓干预,一手抓预防。要做到保护儿童免受伤害,儿童虐待就不能仅仅作为刑事法律问题来处理,而应该作为社会问题来处理,也就是说要基于社区,建立从预防到干预的全方位儿童保护体系。发达国家和地区大多建立了儿童保护“三级预防”的服务体系,具体地说:初级预防的目标是全体居民,主要措施有宣传教育、对儿童及其家庭的救助和支持性服务等,提高全社会的儿童保护意识;中级预防的目标是针对有虐待儿童风险的高危人群或家庭,主要措施是进行风险筛查、早期预测和家庭服务;三级预防的目标是针对那些已发生虐待的人群,积极控制和防止虐待再次发生,具体措施有从咨询、心理治疗、儿童和家庭福利服务到司法干预等。从现阶段看,对于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干预儿童虐待的资源十分有限,就应该以预防为主,并建立儿童虐待报告制度、儿童保护工作程序和国家监护制度。 最后,需要操作性强的政策法律指引,并建立多部门、多专业的合作机制。儿童保护很难依靠政府的某一部门去完成,它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比如服务的递送还需要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因此有必要出台防治儿童虐待的政策文件,明确儿童保护的主管机构及各部门在儿童保护方面的职责,建立横向和纵向均分工明确、职责清楚的儿童保护组织体系。由于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数量少,专业性和公信力不足,介入家庭困难,因此,现阶段社会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政府,政府应该承担起保护儿童的主导责任,发展以预防为本,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保护模式。 注释: ①王永红、陈晶琦:《1762名大专学生童年期虐待经历及影响因素分析》,[成都]《现代预防医学》2012年第39卷第118期。 ②DiNitto,D.M.(2007).Social Welfare: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6th Ed.).Boston:Pearson Education,Inc. ③Spector,M.& Kitsuse,J.I.(1977).Constructing Social Problems.Menlo Park,CA:Benjamin Cummings. ④D'Cruz,H.(2004).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hild Maltreatment.Journal of Social Work,4(1),99-123. ⑤⑧Parton,N.(1979).The natural history of child abuse:A study in social problem definition.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9(4),431-451. ⑥Kempe,C.H.,Silverman,F.N.,Steele,B.F.,Droegemuller,W.& Silver,H.K.(1962).The battered-child syndrom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81,17-24. ⑦Pfohl,S.J.(1977).The "discovery" of child abuse.Social Problem,24,310-323. ⑨Krug,E.G.,Dahlberg,L.L.,Mercy,J.A.,Zwi,A.B.and Lozano,R.E.,eds.,(2002).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⑩Pinheiro,P.S.(2006).World Report in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Geneva:ATAR Roto Press SA. (11)Aries,P.(1962).Centuries of Childhood.London:Cape. (12)Carter,J.(ed.)(1974).The Maltreated Child.London:Priory Press. (13)WHO (1999).Report of the consultation on child abuse prevention,29-31,March 1999,Geneva: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000. (14)Hendrick,H.(2005).Child Welfare:England 1872-1989.London:Routledge. (15)冯晓霞:《家长的教育观念与儿童权利保护》,[长沙]《学前教育研究》1996年第3期。 (16)Barton,C.,& Douglas,G.(1995).Law and parenthood.London:Butterworths. (17)Rose,N.(1989).Governing the soul.London:Routledge. (18)Archard,D.(2003).Children,Family and the State.UK:Ashgate Publish Company. (19)Brennan,S.& Noggle,R.(1997).The Moral Status of Children:Children's Rights,Parents' Rights,and Family Justice.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23(1),1-26. (20)Fraser,H.(2003).Narrating love and abuse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33,273-290. (21)宁应斌:《从虐待、恶待到误待儿童:“Child Abuse”的翻译与儿童性侵害的政治》,[台北]《性/别研究》1999年第5期。 (22)尚晓援:《中国弱势儿童群体保护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41页。 (23)Miller-Perrin,C.L.& Perrin,R.D.(2006).Child Maltreatment:An Introduction(2nd Ed.).CA:Sage Publications,Inc. (24)尚晓援、张雅桦:《建立有效的中国儿童保护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