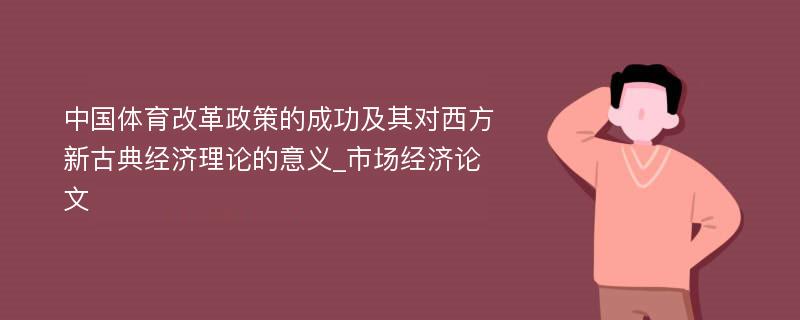
我国体改政策的成功及其对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改论文,其对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鹏同志在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所作的《报告》表明,我国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国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在体改中实施了可以被称之为“国家调控与市场机制并举”(以下简称为“国家与市场并举”)的政策,即:在使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又保持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包括行政命令在内的调控和管理。本文的目的有二:其一,说明中国采用“国家与市场并举”政策的必要性;其二,探讨这一政策性的成功对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意义。
一、采用“国家与市场并举”政策的必要性
“国家与市场并举”的政策之所以必要,其原因在于: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市场机制在我国的运行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从而不能顺利地发生应有的作用。如果对此不加考虑,放弃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和管理而单凭市场支配一切,那末,由于引入的市场机制不能顺利地发生作用,我国经济便会出现运转不灵的混乱状态,也就更谈不上体改的成功。市场机制在我国的运行受到限制的原因又在于我国下列三点特殊的国情:
第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缺乏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硬件。这些硬件包括通讯设备、交通工具、港口码头、市场设施等基本建设项目,而这些主要属于基本建设项目的硬件又是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所必需的。为什么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行需要这些硬件?
众所周知,任何经济社会的运行必须以相应的基本建设为前提,(斯蒂格里兹:《经济学》,诺顿公司,纽约,1993年,第1133页)而市场经济的社会更是如此。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中,价格讯号的变动代表了供求信息的改变;作为对供求信息改变的反应,资源和生产要素会在各厂商和各经济部门之间流动,并通过这种流动使经济社会的运行处于有秩序的状态。在这里所有的信息的传送和对信息所作出的反应都必须依赖于与通讯设备和交通运输有关的设施。如果不充分具备这些硬件,市场机制的作用就会受到限制。在其作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如果再放弃国家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其后果只能是国民经济的混乱状态。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占有的基本建设的存量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的基本建设的存量为数低微。以铁路为例,中国和美国的疆域面积大致相等,而中国拥有的铁路总长度还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由于交通工具和通讯设施等硬件的不足,所以中国的体改必须实施“国家与市场并举”的方针。
第二,由于中国在过去的长时期中推行集中的计划经济,所以它目前也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软件;这些软件包括商务法律、行业的成规、企业管制条例、群众的市场意识等属于非物质领域的事物,而这些事物的欠缺使市场机制难以顺利运行。
上层建筑必须为其经济基础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我们所引入的作为部分经济基础的市场机制,必须有相应的上层建筑为之服务。在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主要依靠当事人之间的契约的缔结和履行,而契约缔结和履行的成功与失败又取决于是否存在着完备的监督、管理和强制执行契约的法律条例规定。由于法规条文规定不可能照顾和涉及到有关契约缔结和履行的一切方面,所以除了法律条例规定之外,还需要行业成规和群众的市场意识作为补充。很可能由于这些原因,一些经济学者把必要的法律制度当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基本建设项目(斯蒂格里兹,同上引书,第1133页),而属于非物质领域的道德水平、社会行事的常规等也被看成为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因素。(斯特里顿与奥卡特:《公共物品、公有企业、公共选择》,圣马丁出版社,伦敦,1994年,第50—51页)事实表明:上述各种软件的不足确实会限制市场机制发生作用。例如,目前存在于中国的“三角债”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妨碍了它的市场经济的运行。在市场经济的运行受到妨碍的情况下,如果取消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其后果当然会和上面第一点相同。
第三,除了缺乏足够的硬件和软件以外,作为中国独特情况的人口压力也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只能在国家进行调控的状态下运行。
中国的人口居于世界各国的首位,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虽然中国资源丰富,但庞大的人口数量却使人均占有额相对贫乏。由于人口众多的人均资源的微薄,个人经济行为的轻微的变动加在一起便会对市场构成巨大的冲击,而市场机制只能通过供求的调节来解决比较轻微的经济波动;对巨大的冲击,它是无能为力的。当经济风暴到来时,西方金融市场的暂停营业等待风暴的平息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以中国的事态为例,春节期间的客流量的猛增几乎给中国的交通运输行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国家只有在事先作出计划安排,甚至动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各方疏导,才能缓解这一问题。然而,相对于整个国家人口的数量而言,中国春节客流量的比例却并不高于西方国家的圣诞节期间的同一数字。虽然西方客流量的比例与中国大体相同,然而,由于西方国家人口的绝对数量远低于中国,它们在圣诞节期间的交通运输的拥挤情况并不严重,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的供求关系的调整加以解决。
春运的事例固然可以显示国家调控在中国的重要性,但还不足以表明需要国家调控的迫切程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举另一个有关粮食的例子。世界粮食的总储备量约可供全世界人口两个月之用。以中国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来计算,世界储备粮可以维持中国八个月的消费。由于美国人口约为中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所以同一粮食储备可以维持美国四十个月之久。为了说明问题,假使中国和美国都遭受颗粒无收的灾荒。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全世界愿意而且能够运用储备粮来予以帮助,那么,世界储备粮仍然解决不了中国的灾荒问题,但却可以使美国渡过难关。因为,农业生产的周期约为一年,而全部世界储备粮却仅够中国八个月之用。这样,中国仍然会面临四个月的饥荒,其后果的严重程度当然是不言自明的。而对美国而言,足以维持四十个月的世界储备粮却可以使它渡过饥荒,绰绰有余。这个例子表明:人口压力使得国家调控和管理不但必要,而且还达到非常迫切的程度。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过去长期实施集中计划,以及由于中国所具有的人口压力这一特殊国情;所以中国不但不充分具备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进行的硬件和软件,而且还会面临市场机制难以解决的经济冲击问题。基于这些原因,中国的市场机制还不能完全和充分地发生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国家应当继续保持其对国民经济的调控和管理。这就是中国在体改中采取“国家与市场并举”的政策的原因。
二、对西方经济理论的意义
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于1776年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原理”;该原理的中心思想可以说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可以使社会得到最大的福利。既然如此,根据该原理便能得出一个结论,即:对市场经济管理最少的政府(或国家)就是最好的政府(或国家)。目前,这一结论依然是代表西方正统经济思想的新古典学派的一个重要教条,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新条。(哈沃斯:《反对新自由主义》,路特里季出版社,纽约,1994年,第1页)如果把这一教条应用于一国的体制改革,那么,其结论是:国家越多放弃经济调控的改革,在越大的程度上听任市场经济支配一切的改革便是最好的改革。对于这一结论,中国体改政策的成功提供了一个否定例证。不放弃国家调控和管理的中国体改政策取得了成功;与此相反,尽快让市场经济支配一切的“休克疗法”却在几个国家中遭受失败。
上述教条之所以与中国体改的成功相矛盾,其原因至少在于下列四点:
第一,上述教条忽略了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各种条件,如本文上一部分所提到的硬件和软件。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运行了很长的时期。在这一长时期中,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各种条件已经逐步形成,而且还达到了比较完备的程度。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市场在西方国家中可以发生较为完善的作用。然而,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指出,在一个类似中国那样的不充分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中,市场机制的运行会受到阻碍。这些国家如果盲目遵循听任市场支配一切的教条,其体制改革当然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甚至遭受失败,如许多实施“休克疗法”的国家所显示的那样。因此,西方学者柏特曼和鲁希迈耶认为,建立市场机制能在其中运行的制度框架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柏特曼与鲁希迈耶:《国家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林瑞奈出版社,伦敦,1992年)。
第二,上述教条也忽视了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的性质的不同。贪污腐化的政府为了某些个人的利益对市场机制的无端的干涉固然会带来有害的后果。然而,并没有理由据此而认为国家对市场的任何干预都是有害的。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市场的运行进行干预,而相当多的干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国家对外汇市场上的干预有助于该市场的稳定,从而有利于国际贸易的进行。当英国私有的汽车制造企业面临经营不善的困境时,英国行政当局取而代之,扭转了亏损的局面,并且取得了利润(斯特里顿与奥卡特,同上引书,第118页)。在中国的体改中,国营粮店稳定了粮价,对制止由于投资过多而引起的通货膨胀起着很大的作用。由此可见,必须把有利的和有害的干预区别开来;不能把一切的国家干预都说成是有害的,并据此而得到西方新古典学派的“管理最少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的说法。
第三,上述的教条顶多只适用于静态的情况,而对实际经济运行所代表的动态情况则完全不相符合。对“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唯一证明来自新古典学派的福利经济学,而福利经济学对该原理的证明又纯然建立在静态情况分析的基础之上。所谓静态情况系指经济运行中的内生变量仅仅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因此,当外界条件保持不变时,内生变量也保持不变。然而,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即使外界条件不变,内生变量在经济运行中也会改变自己并且对外界条件施加影响,从而,使外界条件反过来又影响自己,即使提出“看不见的手原理”的亚当·斯密本人也认为: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又取决市场的规模(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卷,丹顿父子出版社,伦敦,1954年,第15页)。这就是说:分工的程度越高,劳动生产率越大,从而产品的价格越低;价格的降低会扩大市场的规模,而扩大的市场规模又反过来使分工的程度提高。这种动态的情况并不仅限于分工与市场规模的关系;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许多因素都会造成动态的情况。因此,仅能适应静态情况的“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说法对以动态变化为主的经济运行的实践并没有现实的意义。
第四,上述的教条不仅脱离实践而且还更加脱离体制改革的实践。体制改革是一个改变过去经济行为常规的过程,以便取得经济上的较快的发展。在这里,“改变过去的常规”和“经济较快的发展”都完全是动态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教条更加不符合于实践。西方学者对各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研究表明:事实与该教条的主张恰恰相反,几乎一切成功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都是与国家的管理政策密切相关的。例如,韦斯与霍布森的研究甚至表明:英国产业革命的成功并不完全来自国家管理最少的“自由放任”,而当时英国政府的政策起着很大的作用。关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济在近几年中所取得的飞跃发展,他们写道:“与新古典学派正统思想(主要指“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说法—引者)相反,政府在这三个地方起着主要的作用来建立经济实力和出口的竞争能力”(韦斯与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普利特出版社,英国剑桥城,1995年,第12页)。西方学者韦德在另一本专门论述同一地区的经济发展的著作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韦德:《对市场的管制》,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按照世界银行的一本著作的研究成果,在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的世界中,“健全的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增加了它的重要性……这种政策会带来较多的益处,但是,错误的政策也会带来较多的害处”(世界银行《世界经济的前景和发展中国家》,美国华盛顿,1995年,第5页)。很显然,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经验是和上述的教条背道而驰的。
综上所述,新古典学派“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教条面临西方学者越来越多的否定意见,而中国“国家与市场并举”的体改政策的成功给这种否定添增了一个新的例证。中国体改政策的成功对西方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的意义即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