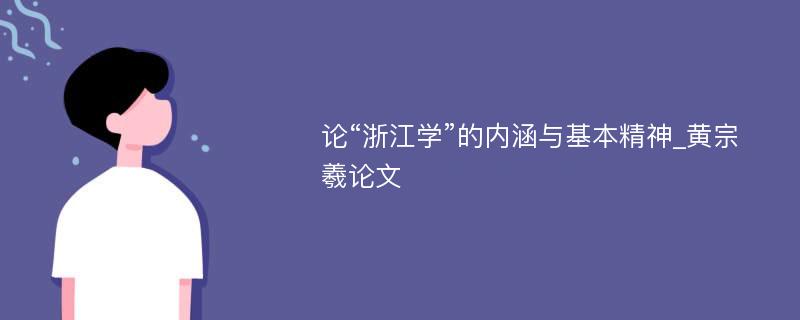
简论“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涵论文,精神论文,简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浙学”,简单地说,就是浙江地区的学术文化,或曰浙江特色的学术传统。然而作为一个独特的学术理论概念,一个专用学术名词,就不能这么简单地理解了。从一般意义而言,所谓“浙学”,应是对发生发展于浙江、形成了浙江特色而其影响波及于国内外的一种学术文化传统的理论概括,它代表着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人文传统与理性精神。
关于“浙学”的理论内涵,从这个概念最初提出至今,学者们就有异同之见,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定义。即便是在称谓上,也是众说纷纭:有直称“浙学”的,有以“浙东学派”、“浙东学术”代替或等同于“浙学”的,也有视“浙学”为“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之合称的。因此,很有必要对“浙学”概念的来龙去脉作一番历史的梳理,进而对“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作出理论的疏解。
一、“浙学”一词的由来
据我所知,最早提出“浙学”概念并加以理论界定的是南宋大儒朱熹。他统称永嘉(陈傅良、叶适)、永康(陈亮)之学为“浙学”,并严加批评,说:
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注:《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吕伯恭》,中华书局1994年3月版王星贤点校本第八册,页2957。)
又说:
江西之学(指陆氏心学)只是禅,浙学却专言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注:《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陈君举》页2967。)
可见,朱熹是将“浙学”视为“专言功利”、误导学者的“异端”而加以批判的。
到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则比较理性地意识到了“浙东学派”的存在并对其学术传统有所总结。他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浙东学派”一词,批评当时明史馆负责制定《修史条例》的人“其言浙东学派最多流弊”,并把姚江之学和蕺山之学归入浙东学统。黄氏还于崇祯年间汇编了一部集数十名浙东学者著作于一编的《东浙文统》若干卷。(注:参见拙著《黄宗羲著作汇考》,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版,第244页。)但黄宗羲所谓“学派”,指的是学术脉络,并非现代意义的学派,他对“浙东学派”或“浙学”的理论内涵也未作出明确的界定。
黄宗羲之后,自视“梨洲私淑”的清代大儒全祖望对“浙学”概念作了比较明确的界定并给予浙学以肯定性评价。全祖望所撰《宋元学案叙录》曾多次使用“浙学”一词概括浙江的学术源流、特色和风格,兹录如下: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孙复)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慈溪杨适、杜醇、鄞县王致、王说、楼郁)、永嘉之儒志(王开祖)、经行(丁昌期)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胡瑗)湖学相应……。(《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见《黄宗羲全集》第三册,页316)
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考所谓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门,其三则私淑也;而周浮止(行己)、沈彬老(躬行)又尝从吕氏(大临)游,非横渠(张载)之再传乎?……今合为一卷,以志吾浙学之盛,实始于此。(同上,卷三十二《周许诸儒学案叙录》,见《黄宗羲全集》第四册,页405)
勉斋(黄榦)之传,得金华而益昌。说者谓北山(何基)绝似和靖,鲁斋(王柏)绝似上蔡,而金文安公(履祥)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同上,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叙录》,见《黄宗羲全集》第六册,页214)
四明之专宗朱氏者,东发(黄震)为最。……晦翁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桀戾、固陋无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其亦足以报先正拳拳浙学之意也夫!”(同上卷八十六《东发学案叙录》,《黄宗羲全集》第六册,页394)(注:本文所引《黄宗羲全集》页码,均据《黄宗羲全集》增订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
全祖望的按语说明了三点:第一,他所说的“浙学”主要是指“浙东之学”,但也包括了“浙西之学”,其内部各派的学术渊源和为学宗旨不尽一致,但也有共同特色;第二,他认为“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学术渊源,都与宋初大儒胡瑗在湖州(地属浙西)讲学时形成的“湖学”相呼应,而安定“湖学”的特色是“沉潜”、“笃实”,以“倡明正学”、“讲明六经”、落实“治事”为目的;第三,“浙学”在当时的地位,堪与齐鲁之学、江右之学、闽学、关学、蜀学相媲美、相呼应,蔚为一大学统,对于宋元学风有开创、启迪之功。
继全祖望之后,乾嘉时代的浙东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首次对“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学派特色作出区分,并分析了各自的学术渊源。他说: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惟西河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
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注:章学诚:《浙东学术》,载《文史通义》内篇卷二,中华书局1956年12月版,页51~52。)
在章学诚看来,“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学术渊源及其学风虽然不同,但都是儒家之学,其根本之道是可以并行不悖、互相兼容的。而从章氏所述浙东之学的源流与特色来看,浙东学术的主流是从南宋四明学派、中经明代姚江学派(即阳明学派)到明清之际的蕺山—梨洲学派,其特色是“宗陆(王)而不悖于朱”。值得重视的是,章学诚所讲的“浙东学术”,并非单指浙东史学,而是涵括了宋明理学、心学的“浙东经史之学”。后代一些学者,把“浙东学术”或“浙东学派”单纯地理解为“浙东史学”或“浙东史学派”,而把明代王阳明及其学派排除于浙东学术之外,是失之于偏颇的(注:对这一偏颇,当代浙江学者已有反思。如王凤贤、丁国顺合著的《浙东学派研究》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即对北宋至清代的浙东学派了系统性研究,将其形成演变分作四个时期,认为北宋是“浙东学术的草昧时期”,南宋是“浙东诸学派的形成”时期,明代是“浙东心学思潮的兴起”时期,清代则是“浙东学派的全盛时期”。)。
二、“浙学”内涵之我见
我在1993年秋发表的《试论“浙学”的基本精神——兼谈“浙学”与“浙东学派”的研究现状》一文(注:该文系笔者于1993年9月应邀访问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时的演讲稿,首先发表于该所主办的《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3年第4期;又于同年10月提交“全国首届陈亮学术讨论会”,被收入赵敏、胡国钧主编的《陈亮研究论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中,在引证全祖望、章学诚等论述“浙学”源流、特色的思想史资料的基础上,对“浙学”的内涵作了个初步的理论概括。拙文指出:
所谓“浙学”,即发轫于北宋、形成于南宋而兴盛于明清的浙东经史之学。它并非单一的学术思潮,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术流派,而是内含多种学术思想、多个学术派别的多元并存的学术群体——在“浙学”内部,既有宗奉程朱的理学派,也有宗奉陆王的心学派,还有独立于理学、心学之外的事功学派。然而,这个学术群体内部的各家各派,在相互关系上并不是绝对排他、唯我独尊的,而是具有兼容并蓄、和齐同光的风格,从而体现了某种共同的文化精神——浙学精神。
现在检讨起来,我的这个概括重视了“浙学”的主流——浙东学派与浙东学术的发展演变及其特色,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但却又是相当粗糙而且有片面性的。之所以说它粗糙且有片面性,是因为这个“浙学”概念仍然是小浙学而非大浙学的概念,且对章氏所谓“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一语未予足够重视,忽略了“浙西之学”在“浙学”中应占有的地位。
我们应当看到,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学术史及其学术概念的涵义也是与时俱进、不断充实进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内容的,“浙学”概念也是如此。如果说,宋元学者眼中的“浙学”仅限于金华、温州地区的“婺学”与“永嘉永康之学”的话,那么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全祖望已经将“浙学”的领域延伸到宁波、绍兴等大浙东甚至包括了浙西地区,而且所包含的学术流派也不限于“婺学”与“永嘉、永康之学”,而且包括了“庆历五先生”、“甬上四先生”(即所谓“四明学派”或“明州学派”)以及姚江学派与蕺山学派了。及至清代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则在区分“浙西之学”与“浙东之学”并强调“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的同时,已经蕴涵着大“浙学”的观念了。
自章学诚以后,近现代以至当代的许多学者,从章炳麟、梁启超、钱穆、何炳松、姚名达、陈训慈到陈荣捷、刘述先、金毓黻、杜维运、余英时、何冠彪、詹海云、郑吉雄,以及当代浙江籍的众多学者(如北京的方立天、张立文、陈来、张义德,上海的冯契、谭其骧、潘富恩、罗义俊、杨国荣,南京的洪焕椿、杭州的徐规、仓修良、王凤贤、沈善洪、吴光、滕复、董平、钱明、何俊、杨际开,宁波的方祖猷、管敏义、金华的方如金、温州的周梦江等等),都发表过有影响的学术论著,从各个角度研讨、评论“浙学”或“浙东学派”、“浙东学术”的理论内涵、历史沿革、学派脉络、精神特质、研究成果等问题,从而把对“浙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新阶段。
限于篇幅,本文不拟一一罗列各家论“浙学”的理论观点与学术成就,而试图站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对“浙学”的内涵作一重新审视,申明并强调笔者关于“浙学”的基本观点。
我认为,关于“浙学”的内涵,应该作狭义、中义与广义的区分。狭义的“浙学”(或称“小浙学”)概念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以陈傅良、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渊源于东汉、酝酿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包括东汉会稽王充的“实事疾妄”之学、两宋金华之学、永嘉之学、永康之学、四明之学以及明代王阳明心学、刘蕺山慎独之学和清代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为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概念即“大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繁荣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泽惠于现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这个“大浙学”,是狭义“浙学”与中义“浙学”概念的外延,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既包括浙江的儒学与经学传统,也包括浙江的佛学、道学、文学、史学、方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传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涵盖了有浙江特色的自然科学传统。当然,“大浙学”的主流,仍然是南宋以来的浙东经史之学。
从总结浙江学术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而言,我们自然应当对狭义、中义与广义的“浙学”加以系统的研究与整理,但站在当今建设浙江文化大省的立场而言,则我们应取广义的“浙学”概念即“大浙学”概念,而不应仅仅局限于“浙东学派”或“浙东学术”的视野。
三、“浙学”的基本精神
如果从广义的大“浙学”视野观察与反思浙江的学术文化传统,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浙学”还是“浙东学派”,都并非是一个单一学派的连续性发展,而是多个学派“和齐斟酌,多元共存,互相融通”而形成的一种学术格局与学术传统,这样的学术格局虽然是异见纷呈,但也培养了某种共同的人文精神。浙江这块土地,虽然有浙东、浙西之分,但仅仅一江之隔,是不可能从人文地理上将其截然分开或将两者对立起来的。
事实上,在浙江学术史上,浙东、浙西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密切、互相影响的。例如,明末的蕺山学派当然属于“浙东学派”之一,但刘蕺山的弟子中却有好几位浙西籍学者,其中著名者如陈确(杭州府海宁县人)倾向浙东王学,而张履祥、吕留良(均为嘉兴府桐乡县人)则属于浙西朱学。在近现代,浙东、浙西之学更有相互融通之势,尤其是在省会杭州更是如此。如出身浙西杭州府的龚自珍、章太炎,其实堪称浙东学风的继承者与弘扬者。对此,当代浙西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早有所见。他在《近代杭州的学风》(发表于1947年4月5日的《浙大校刊》)一文中指出:“杭州于浙西已属边缘地带,隔钱塘江与浙东学术中心的宁绍相接,故其学风虽以浙西为素地,同时又深受浙东的影响,实际上可说是两浙学术的一个混合体。由混合而融化,迨其融化而后,遂自成一型,既非浙东,亦非浙西。”这是颇为中肯的意见。这对我们在当代坚持“广义浙学”的研究方向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在经历千百年的学术磨合过程中,“浙学”各派逐渐形成了以“实事疾妄、崇义谋利、经世致用、兼容并蓄”为特色的浙江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是从王充到陈亮、叶适、王阳明、黄宗羲、陈确、吕留良到全祖望、章学诚以至近现代的龚自珍、章太炎、鲁迅、蔡元培、马一浮等著名浙江思想家都一致认同并且以不同语言予以阐扬的浙江文化精神。
那么,浙江学者所倡导和积累起来的共同文化精神——“浙学”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我在上述《试论“浙学”的基本精神》文中将它概括为“求实精神、批判精神、兼容精神、创新精神”,又在《论浙江的人文精神传统及其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注:参见拙文:《论浙江的人文精神传统及其在现代化中的作用》,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一文中从五个方面概述了浙学人文精神的主要内容,即:“一、‘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和谐精神;二、‘实事求是,破除迷信’的批判求实精神;三、‘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四、‘工商为本’的人文精神;五、‘教育优先、人才第一’的文化精神”。
只要稍微具体地翻阅一下浙江思想文化史,我们就可以找出许多例证来证明上述浙学人文精神的真实性与普遍性。在此,我不想旁征博引,而仅仅列举浙江思想家中最有代表性的几句名言,期与读者共同体悟“浙学”的根本精神。
一是王充的“实事疾妄”精神。我们知道,“实事求是”这句经典名言,最早出自于班固手笔(见《汉书·河间献王传》)。其实在班固之前的王充,已经在《论衡》的众多篇章中表达了这一思想,特别是在《论衡·对作篇》中强调自己的写作宗旨是“《论衡》实事疾妄,无诽谤之辞”。所谓“实事疾妄”,就是实事求是、批判虚妄,所体现的正是一种求实的、批判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后来的浙江思想家如陈亮、叶适、黄宗羲、龚自珍、章太炎、鲁迅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
二是叶适的“崇义养利”思想。义利关系问题是历代思想家都要讨论的课题。自从孟子对梁惠王讲了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董仲舒又说了一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后,许多人以为儒家是“重义轻利”之徒。其实不然。孟子是以行仁义为大利故不必言利,而董仲舒之说则确有轻视功利之弊,所以遭到叶适的批评,称之为“疏阔”之语,指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叶适义利观的根本思想是“崇义以养利”(《士学上》,载《水心别集》卷三),是反对“以义抑利”而主张“以利和义”的(《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七),实质上是一种“崇义谋利”的思想主张。这种敢言功利的思想成了浙江人文精神的一大资源,并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三是黄宗羲的“经世应务”思想。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参与意识,这在浙江思想传统中表现尤其突出,而黄宗羲所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经术所以经世”(见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转引),正是浙学“经世致用”传统精神的典型体现。
四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在浙学传统中,历来有一种兼容并蓄、和齐同光的精神,如黄宗羲强调治学要善于做到“会众合一”(《万充宗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页417),章学诚的“道并行而不悖”之说,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到近代教育家蔡元培,更是一再强调学术上要坚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这不仅是继承与发扬了“浙学”传统,而且成了北京大学的优良校风与学风。
当然,能够体现浙学精神的远不止上述数言,但仅此数言,即足以反映出浙江文化底蕴的深厚,足以代表浙江人民的精神风貌。仅此数言,已经在浙江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正在成为推动现代浙江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动力。正因如此,我们对于浙学传统、浙学精神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更深刻的总结,并使之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