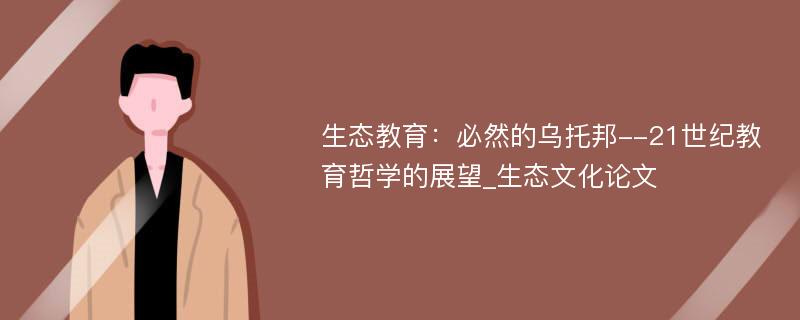
生态化教育,必要的乌托邦——21世纪教育哲学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哲学论文,生态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生态文化与生态化教育
考察人类的文化史可以发现,人类已走过了太古时代的自然文化,迈过了古代社会的人文文化,正在经历工业文明时代的科学文化。(注:余谋昌:《大鸟文化》,《哲学动态》,1997年第12期。)当科技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与进步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科技对自然的灾难性破坏,人类在渐渐丢失物质家园的同时,也痛感精神家园的迷失。于是在本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由若干先驱呼喊出了“拯救地球”、“敬畏生命”、“全球伦理”等口号,揭示了人类文化的最新走向:由科学文化转向生态文化。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将引发一系列的变革:首先是人类价值观的革命,即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代替人统治自然的价值观;其次是世界观的革命,即用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哲学,代替人类中心主义哲学,用关于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生态世界观代替机械论、元素论;另外,它还会引发人类思维方式的革命,整体的生态学思维如莱昂波尔德等提倡的“象一座山那样的思考”将代替机械论的分析思维。
尽管这种生态文化似冰山才露端倪,呼唤生态文化与伦理的声音在新科技革命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繁荣面前显得十分微弱,但转型的趋势已经出现,生态化这一大潮已突破了单纯的环境科学开始席卷人文、自然学科,最终将以一种文化形态渗透进人们的生活,形成全新的生态化社会。当然这种社会对于今天而言还是一种“乌托邦”,与此匹配的生态化教育也还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直接关系到人类自身生死存亡问题的生态化教育对整个人类历史来说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
事实上,生态化教育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倡导环境教育开始,学者们日益认识到生态化教育应具有丰富的内涵。如方创琳提出“生态教育”应包括六大方面内容(注:方创琳:《论生态教育》,《中国教育学刊》,1993年第5期。):生态意识、生态哲学、生态价值、生态伦理、生态文明、生态文化。任凯、白燕著的《教育生态学》(注:参见任凯、白燕著:《教育生态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则运用生态系统的观点对教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填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总的来说生态化教育的研究已经起步,但多局限于环境、生态结构及功能等具体领域,缺少哲学层次的思考。而在教育的价值观方面,“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依然处于上风,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丛书之一《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为例,11名委员虽不约而同地提到教育应为促进全球伦理学培养一些根本的普遍价值观,如对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等,但又明确地把教育和文化的最终目标定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把教科文组织的使命定为“建立一种真正的‘和平文化’”。笔者认为“和平文化”和“生态文化”有着很大区别,前者以人为本位,重地球村范围内跨越种族、国界以及意识形态的和平共处,无疑是积极的,但相对于后者,还没有突破人类本位意识,不能平等地看待自然,使人类在向自然的回归中获得人性的回归与自我的回归。可见我们对生态文化的认识、对生态化教育的思考还很不够,必须站在教育哲学的高度,审视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而生态化教育理念的引入应当会带来教育哲学诸范畴的一系列变革。本文仅就以下几个主要范畴可能产生的变化作一点大胆而肤浅的预测。
二、生态化的教育哲学构想
1.生态化的教育本质观
教育本质是教育哲学首先要研究的范畴。自1978年以来我国关于教育本质的论争一直延续不断,由教育的归属、属性、职能到人的主体性,讨论逐步深入,日益逼近了教育的本质。如鲁洁教授的《教育——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雷鸣强的《教育的本质是主体间的文化传承》等论文作为教育本质研究的新成果,都给人以新的启示。但冷静地分析上述定义,无论是人的自我建构说,还是主体间的文化传承说,都是以人、社会或文化为本位的,只重视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探索,强调人对自然界的超越性,而把自然这个重要的范畴丢在一边,缺乏对人与自然界受动与能动之辩证关系的考察。究其原因还是人类长期以来的“自我中心”意识的支配,“人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这种乐观主义的自信洋溢于教育本质讨论之中,教育与自然日益对立,人类忘记了自己是自然的子女,忘记了自然这个对人类而言依然是充满着神秘与威慑力量的客观世界。
因此生态化的教育不仅要关心如何把一个自然人造就成一个社会人,更关注人类如何学会与自然、与社会乃至与自身和谐共处。教育不仅要使人学会认知(learning to know)、学会做事(learning to do),还要学会共同生活(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即学会与他人,与社会,与自身也包括与自然和平共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会生存。它既不是原始“未区分”状态条件下的人受制于自然,也不是近现代“已区分”状态条件下的人践踏自然,而是人与自然互相尊重、互相依存的整体性生存。(注:李培超:《环境伦理》,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8页。)故教育的本质可以规定为:人之学习与自然、社会乃至自身和谐共处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在人类发展史中呈变化的态势:原始形态的教育常偏重于自然规定性,近现代越来越偏向于社会规定性与人类自身规定性,而将来随着生态化社会的来临,教育将最终实现向自然回归的整体规定性。
2.生态化的教育价值观、发展观
以往的价值观总是站在人类本位立场,以社会价值或个人价值衡量教育,致使教育史上出现了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教育目的之争。如今主体性问题的大讨论试图超越个人与社会的鸿沟,找到个人主体与社会主体(或称类主体)的融汇点。但与教育本质相类似,上述探讨忘记了自然的存在,忽视了教育还应具有生态价值:即可以通过教育帮助人类建立与自然、社会及自身和谐共处的关系,教育目的不应只盯着人、社会,而应关注自然、社会、个人的整体价值。
在人的发展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在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基础上又有进展,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培养富有创新意识与能力的自由的人已成为当代教育的重要使命,甚至有人预言人的潜力的发掘可以是无止境的。笔者认为这种发展观忘记了人也是自然的产物,人的发展不仅要全面、个性化,也应是可持续、终身的发展;不仅要合社会性的发展,而且要合自然性、乃至“天人合一”式的发展。过分密集的枯竭性的智能开掘如同对地球资源的毁灭性利用一样是十分危险的;过分夸大人的主体性也会走向反面,产生反主体性效应。可见,生态化的教育在价值观、发展观方面都将有更新的诠释。
3.生态化的道德教育观
19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等的兴起带来了伦理学的革命,与此相应,学校的德育也应随之变革,生态德育将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贯彻于学校、家庭及成人教育体系之中。令人欣慰的是在国际社会的倡导下,在大众传媒的呼吁下,许多学校已把生态伦理教育列入教育范畴。如广东深圳布心小学提出了“七心教育”(注:谢国基:《实施“七心”教育浅析》,《现代教育论丛》,1998年第4期。):热心献给他人、孝心献给父母、爱心献给社会、忠心献给祖国、关心献给环境、信心留给自己、恒心留给自己。其中“关心献给环境”就是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指出要培养学生生态是非感、生态荣辱感、生态义务感、生态参与感,并有具体的落实措施。希望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关心并研究这个课题,使生态德育这一新生事物得以健康成长。
4.生态化的审美教育观
美一般可分为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审美教育也大致遵循这样的分类,以三种美为主要内容。然而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社会美、艺术美日益占据了人们的审美空间,教育中自然美的因素日夜孱弱,审美教育几乎成为艺术教育的代名词。同时,三者的分离与对立也日趋严重,美育中“非美”的反自然因素不断增加,如某些标榜为“后现代”的艺术恰恰反映了人的自然性的扭曲,孩子们在摇滚、卡拉OK中长大,却很少听到更不会欣赏风声、雨声、鸟鸣声。生态化的美育观首先强调三种美的和谐统一,在生态美的标准下,凡违背生态和谐的事物、行为为丑,反之,维护生态和谐的则为美。这种新标准的确立将有利于美学和美育研究的深入,最终也将有利于教育这一学科群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真正统一。
以上分别从四个范畴大体预测了生态化教育下教育哲学的新面貌,不可能全面,还有许多不可回避的问题,如课程的生态化、教法的生态化、教学评价的生态化等等。总之,生态化教育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可能会对21世纪乃至以后世纪的教育以巨大的冲击。
三、生态化教育对中国
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思潮,生态化教育必然会影响中国。令人惊喜的是,生态化教育与中国的古老文明有着天然的联系。环境伦理学的先驱史怀泽认为,他的“敬畏生命”思想在古代中国就有文化基础,孟子、列子、杨朱等人均对他产生过影响。随着西方工业文明危机的逐渐暴露,不少西方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1988年诺贝尔奖在世得主们在法国巴黎聚会,会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几乎可以说中国古代文明就是一种生态化的文明,长期的农业社会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使中国人对生态化的社会与教育更有认同感。然而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历程中,为了赶超世界,为了发展经济,我国也走上了破坏自然以谋求发展的反生态之路,加上人口的沉重负担,全民教育水平的低下,我国的生态环境呈加速度的日益恶化,教育也走上了一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反人性、反生态之路。可见当代中国教育的生态化问题与环境保护一样迫在眉睫,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总之,生态化是一股不容回避的洪流,在21世纪的今天,生态化教育这个必然又必要的乌托邦或许会成为教育哲学的新热点、新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