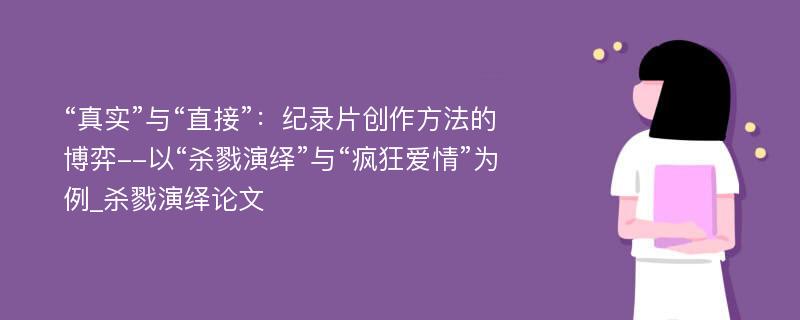
“真实”与“直接”:纪录片创作方法的对弈——《杀戮演绎》和《疯爱》的个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纪录片论文,真实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4)03-0020-05 在不少关于纪录片的论述里,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与真实电影(Cinema de Verite)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直接电影形成于1950年代末的北美,受到1920年代前苏联导演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的先锋纪录片形式影响,直接电影的先锋人物罗伯特·德鲁(Robert Drew)、理查德·李考克(Richard Leacock)和米歇尔·布鲁(Michel Brault)等人,以新闻电影拍摄的经验为基础,并借助当时诞生不久的便携式摄影录音设备,选择了前所未有的独立非官方视角来审视社会现实;而真实电影的根源则可以回溯到1920年代现代纪录片之父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eharty)的开创性纪录片作品,它的概念则由法国人类学者和电影人让·鲁什在他1961年的影片《夏日纪事》中确立,并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由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马里奥·鲁斯博利(Mario Ruspoli)和雷蒙·德帕尔东(Raymond Depardon)等人发展完善。从纪录电影发展史的角度审视,这二者确实有着相同的根源,在发展上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让·鲁什曾经直接把真实电影的诞生归功于加拿大直接电影的先驱之一米歇尔·布鲁(Michel Brault)给他所带来的影响)。与其他以叙事和观点表达为主旨的纪录片相比,它们以自由开放的姿态深入现实捕捉社会政治生活片段的方法,使它们在电影的形式上有广义相似的诉求,在美学和实践技巧上也多有互相借鉴。但当我们从方法论内核上仔细拆解这两种纪录片形式时,我们依然能发现它们细微但又是本质的差别。随着纪录片制作观念和理论的不断更新,这样的不同点逐渐变得明晰而又本质起来。它们影响了影片的形式、内在含义和观念表达,使分别遵循这两个原则而创作的影片走入了迥异的方向。本文以对2013年在世界范围内上映的两部有广泛影响的纪录片《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获2013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和《疯爱》(2013年威尼斯电影节参展影片)之分析为基础,尝试探究在纪录片的范围内直接电影与真实电影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异同,期望使我们对这两个理论概念能有一些更加深入而准确的认识。 印度电影大师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在一篇颇有洞见的论述纪录片“真实性”的文章中提出了“预设立场”(Preconception)问题。他以罗伯特·弗拉哈迪拍摄纪录片《摩拉湾》(Moana)的过程为例:当弗拉哈迪来到南太平洋岛屿塔希提的时候发现当地妇女已经放弃穿草裙而改穿棉布裙,这和他预想中的塔希提妇女形象相差甚远,在失望之余他立即定制了草裙作为出现在他影片中的妇女的服装。也因此,雷伊写道:“《摩拉湾》的真实性,是弗拉哈迪关于塔希提的预设立场主导下的主观真实,而不是塔希提生活的现实。”[1]381-382弗拉哈迪被誉为现代纪录片和真实电影之父,但当仔细拆解他拍摄纪录片的方法,如《北方的纳努克》和《路易斯安那故事》,我们会发现他几乎没有任何顾忌地改变被拍摄对象的外貌、活动甚至言语,以符合他主观判断中的“真实”。实际上,现代纪录片诞生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真实”作为主导概念,其含义不断被扩展而重新定义的过程。尽管弗拉哈迪的拍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纪录片的现实性和故事片的虚构性之间的界限,但他由“预设立场”出发确立的不变主观概念(在他的影片里是永恒的人、地域与自然的浪漫主义关系)为某种可以被归为“真实”的恒定不变表达而背书,成了日后“真实电影”在精神实质上得以依靠的重要支点。对于纪录片的“真实”方法论,“真实电影”的命名者吉加·维尔托夫①借用“电影-眼”(Cine-Eye)的概念表达得更为简单直接:“我,一部机器,给你们呈现一个世界,它的样貌只有我能看见。”[2]可以看出,“真实”在纪录片范畴内的指代已经悄悄偏离了广义上我们对其的客观性理解,而和电影拍摄者的视角以及价值取向紧紧挂钩。无论在内容以及形式上采取了何种与“现实”无限贴近的角度,“真实电影”在内核上很大程度上是为作者的“预设立场”所主导的。而这样的“预设立场”在影片开始拍摄之前即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意识形态的、理性的和感官认知的)牢牢扎根在创作者的头脑中。 从这个角度出发,由美国导演乔舒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指导的《杀戮演绎》无疑是一部带有强烈真实电影特性的纪录片。影片聚焦于1965年在印度尼西亚爆发的右翼政变以及接踵而来的对共产主义者和左派人士的大清洗——按照影片开始字幕的介绍,共有约100万人在屠杀中丧命。《杀戮演绎》遵循了真实电影形式上最基本的模式:它没有采用任何的史料或者具第三方色彩的观点,而是直接切入现实——导演将摄像机指向了当年亲自参与实施大屠杀的凶手,跟随他们的踪迹,纪录他们的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倾听他们以各种不同的口吻回忆讲述当年的杀戮经历。 奥本海默在这里潜在借鉴了五六十年代美国知名的汇编纪录片(Compilation Documentary)导演埃米尔·德·安东尼奥(Emile de Antonio)和他的追随者的方法论技巧,他们以搜集到的大量美国右翼人士和政府机构官方言论的影像资料为基础,在几乎没有置评的情况下以剪辑作为立场表达手段将其甄选汇编成为不同主题的纪录片,以展现保守右翼言论作为反对保守主义的证据,而达到反战反核等社会运动意识形态目的。②《杀戮演绎》所不同的是,在拍摄过程中奥本海默将这种“意识形态反证”方法论由对影像资料的第二手使用变为了现实中对采访对象的直接纪录。由于印尼特定的区域意识形态环境(该国至今还延续着右翼独裁政权的连贯性),使当年的杀手依然可以在此直白地回溯杀人经历,阐述此种意识形态指导下屠杀的“正当性”,其引以为豪的骄傲姿态跃然银幕之上。而当杀人者的叙述被放在一个与其对立的意识形态大环境下的银幕上播放时,它产生了实录“罪证”的强烈冲击效应而成为指控他们自身罪行的最有效证据。在对埃米尔·德·安东尼奥的研究中,很多人都指出他的影片例证了影像的某种非客观属性,即影像资料在作为“见证”的过程中可以因剪辑手段的使用而”背叛”见证者和阐述者叙述的初衷。显然《杀戮演绎》在这一点上进行了类似的尝试,它利用相当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对立分隔状态,抓取了“证言”而又背离了“证言”在其释放环境中的“客观状态”,而服务于创作者本身头脑中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取向,即我们在先前所谈论的“预设立场”。这才是从创作者角度出发的“真实“。从这样内在核心方法论去分析《杀戮演绎》,它无疑带有“真实电影”最强烈和本质的特征。 《杀戮演绎》的惊人之处不仅仅在于它通过纪录的方式展现“敌对”意识形态之真实,更在于它以新奇独创的方式大胆地让摄像机作为媒介,使电影制作者得以直接参与到了事件演变发展的进程当中:以制作一部重现当年“剿灭共产主义分子”过程的影片为借口,导演奥本海默重构了四十年前多个暴行场景,让杀人凶手以演员的身份重回其中扮演自己,再次体验杀人者与被杀者的双重感受,以此来逐渐影响甚至最终改变了“凶手”之一安瓦尔对整个事件的看法与感受。影片在最后甚至展现了在这一连串重构事件发生之后,安瓦尔近似于个人忏悔的独白。 德勒兹在他的著名著作《影像-时间》中曾以法国真实电影运动开创人让·鲁什为例来说明他所提出的概念“摄影机-知觉意识”(Camera-Consciousness):“摄影机-知觉意识不再被定义为它追踪或者自身所做的运动,而代表了它所能进入的思想联系。它演变为提问、回答、反对、刺激、定义、假设、实验……与真实电影的功能相符合,正如鲁什所说,真实电影的意义远超过电影的真实。”[3]24德勒兹清晰地意识到1960年代的鲁什发展出的真实电影已经完全超越了以摄影机为工具纪录现实的“简单”功能,而变成了创造“预设真实”的一种方法论。特别是当我们看到在法国“真实电影”运动的开山之作《夏日纪事》(Chronique d' un été)中,鲁什让集中营的幸存者玛塞琳·洛瑞丹(Marceline Loridan)身藏纳格拉录音机穿过巴黎的Les Halles而让摄像机拍下正面离她而去的著名镜头时,影片的“预设”情绪和价值表达透过这个非现实而经过精心调度的运动镜头汩汩而出。鲁什做法的动机与当年弗拉哈迪在拍摄《北方的纳努克》时为了影片的采光效果而截去纳努克人冰屋的屋顶或者在《摩拉湾》中让已经文明化的塔希提妇女重新穿上草裙类似:他们在“预设立场”的基础上主观能动地调动了包括摄像机在内的一切手段去参与人物的行为甚至改变现实事件的进程。弗拉哈迪为此甚至提出了“参与性摄像机”(Participatory Camera)的概念来凸显摄影机作为媒介让观看者参与到被拍摄事件进程中的方法。在此意义上,《杀戮演绎》的人为设计部分看似惊世骇俗,但究其本质无疑是对弗拉哈迪和鲁什创作方法的一次革命性延伸。它突破了纪录片中摄影机仅仅参与场景调度的界限,而让创作者以事件走向的设计者面目出现,不仅“见证”了拍摄对象的客观实体,而且主导了改变他们观念的事件过程,从而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切皆服务于真实电影经过深思熟虑后所推崇的终极目标:将拍摄对象无限推进创作过程本身,创造一种不存在主观与客观的“电影-对话”(鲁什语)。[4]纪录片电影人意图成为他们认定的“真实”的缔造者,正如德勒兹所言:“真实不是被发掘、塑造和复制,而必须是被创造的。”[3]146 然而,当我们脱离开真实电影创作者们对自身理论的论述,依然能发现来自外界尤其是和它几乎同源的直接电影的质疑。加拿大魁北克电影人,直接电影的开创者之一彼埃尔·佩鲁(Pierre Perrault)表示:“真实电影的标签让我十分困扰。它暗示了一种道德判断意图。我更倾向于坚持一种技术上的定义:直接电影或者现实电影……而真实,没有人有权利宣布全部拥有它。”[5]美国直接电影的开拓者罗伯特·德鲁这样描述他在巴黎看到让·鲁什等人拍摄《夏日纪事》的场景:“我很惊讶地看到真实电影的制作者们举着话筒在街上和行人搭讪。而我的目标是以不介入的方式抓取现实生活。我们之间(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有某种互相冲突的地方。他们的做法没有意义。带着摄影师、录音师还有其他六个人——总共八个人站在现场……而我的想法是只带一两个人,完全不引人注目地抓取瞬间。”[6] 实际上,在技术和实践层面,直接电影是以极简主义的姿态出现的,它遵循了比真实电影严谨得多的规则。以著名的直接电影作者弗雷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为例,他的所有纪录电影都严格按照既定的方法拍摄:素材全部采取同期录音,拍摄者的形象和声音完全不出现在画面中,电影成片没有配乐,没有画外音轨评论,没有对被拍摄者的采访,甚至人物对着镜头说话的镜头都不被采用(它代表被拍摄者意识到了镜头的存在,其行为和言语的忠实度则不能被保证)。在拍摄人员的构成上,怀斯曼自始至终坚持两到三个人的小规模团队,主要人员仅仅包括一名摄影师以及持录音话筒的他本人。与真实电影摄影机不同程度地“参与”意识截然相反,怀斯曼影片中的摄影机退到了一个纯粹观察者的位置,宛如一只追随拍摄对象的飞虫,完全不被注意但又忠实纪录了拍摄对象的言语、表情和行为。直接电影“肆无忌惮”使用的调度手段——包括改变拍摄现场的布局和采光,安排被拍摄对象的行动和话语言谈,甚至如《杀戮演绎》一般直接参与到被拍摄事件的进程当中去,成为改变事件性质的因子——在直接电影看来都是突破了观察者界限而对现实生活纯粹性不能容忍地破坏。实际上,真实电影与直接电影最本质的差异就在于对“预设立场”的不同认识。来到拍摄现场的时候,“真实电影者”以其对影片主题的自主判断和完整想像业已形成了清晰的拍摄目的,这成为他们调度现场拍摄的思维起点:但“直接电影者”仅仅是怀着对被拍摄对象的最初印象,期待在拍摄过程中观察、发掘和纪录人物和事件的发展过程,捕捉任何可能产生的结果。如果以一个形象的比喻来阐明这个最根本的区别:“真实电影”也许在一开始就自我赋予了一个“类上帝”的视角,以拍摄作为验证自己“真实”唯一性的证据,而“直接电影”则更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它所进入的世界呈现为一个未知不可预料的状态,一切要在成长的过程中才能被发现和认知。 以这样的标准来审视,王兵无疑是中国纪录片界中最忠实地实践“直接电影原则”的电影人。从2003年的《铁西区》开始,他就坚持所有的现场拍摄和录音工作都由自己一个人完成,他也从未因预设的拍摄目的而诱导或者指引被拍摄者做出超越他们自身意图的行为。他拍摄影片《三姊妹》的过程清晰诠释了直接电影的工作方式:在看望朋友母亲的路上王兵偶遇了影片的主人公小女孩,仅仅出于好奇他记下了小女孩所在的村落,其后带着摄像机返回,对小女孩和她的两个妹妹进行拍摄。对这个留守家庭,他几乎没有任何“预设立场”和先验的“拍摄目的”。观众在影片中看到的是三个女孩长篇而琐碎的生活片段,它看似没有固定的主题,但实则为我们勾勒了完整而感性的中国农村孩童的整体形象。在2013年上映的《疯爱》中,王兵将直接电影“纪录而不判断“的精神实质发挥到了顶峰:他带着摄像机来到位于中国云南的一座精神病院,以纯观察者的视角纪录下了这个封闭环境中特殊群体的日常生活。在影像质量上,《疯爱》粗粝、直接和不经修饰的自由风格和《杀戮演绎》处处的精心雕琢——尤其是片头和片尾充满象征意义的华丽刻意摆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杀戮演绎》中,“屠杀因由表述”的预设主题贯穿始终,使影片围绕着几个关键人物形成了完整的叙事链;而反观《疯爱》,王兵以“瞬间捕捉者”的良好直觉纪录下了十几段病人的状态片段,其中震惊、荒诞、乖张、痛苦、焦虑与平淡交互闪现,这些片段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线性连贯的叙事联系,而是呈并行状态展开。这样的构筑电影方式天然摒弃了明确主题的存在(也间接否定了“预设立场”的必要性),而是依靠组合方式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对特定封闭环境的整体认知。可以看出,尽管在具体拍摄方式上,《杀戮演绎》和《疯爱》都继承了某些共通的现实主义血脉,但拍摄“预设立场”的有无直接决定了二者在表现方法和观念传达上的巨大差异——《杀戮演绎》透过复杂的手段和调度力图证实的是电影拍摄者本身所持有的强烈意识形态价值取向,而《疯爱》则将影片呈现的方式与现实紧紧联系在一起(影片对拍摄内容摘选得精心细致,但对剪辑等后期过程则处理得谨慎克制,以对内容的影响最小化为原则),创作者自身的意图仅仅以视角选择的方式潜在保留在方法论实践的深处。 诚然,根据纪录片拍摄题材的不同,直接电影与真实电影各自表现出了不同的优势与劣势。怀斯曼始终把自己的拍摄限定在某个封闭机构或地域内部,从微观角度出发让他得以摆脱叙事的干扰而塑造群像式社会图景。王兵与怀斯曼在不自觉中高度保持了一致:无论是对铁西区,对三姊妹抑或是对精神病院的观察,他皆是从微观个体入手,犹如拼图一般将各部分组合而形成整体认知(如果说《铁西区》依然部分地依赖画面内人物的行为和语言对观众产生冲击,那《三姊妹》和《疯爱》则显然更注重在影片的不同片段之间建立非叙事性的电影化联系)。而对于一些与社会政治现实与历史相关的题材,擅长在意识形态上总领全局并始终带有鲜明道德判断色彩的真实电影则占据了优势,这也是为什么如《美好的五月》(Le joli mai)和《浩劫》(Shoah)这样的影片能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力。 “预设立场”的有无会不会对影片的客观性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随着电影理论的不断发展,影像客观性的讨论逐渐被理论家和实践者们认定为一个伪命题。实际上,即使拍摄者有一个忠实于现实本身的良好愿望,当他手持摄影机开始选取要拍摄的内容时,拍摄本身即已被他的主观视角所主导。而在剪辑阶段,如美国实验电影人苏·弗雷德里克(Su Frederich)所说:“一旦进入构建影片结构和剪辑电影素材的阶段,毫无疑问就开始了一个用自身观点塑造它的过程。”[7]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对真实电影与直接电影的辨识变得无关紧要?回到“预设立场”的概念,它对影片所产生的影响不在于客观性性质和程度上的异同,而在于区分开了两个创作中不同的角色扮演:参与者和观察者。这二者赋予了纪录片迥异的灵魂——从纪录片历史看,前者更多地投入了与社会运动、政治反思和散文化个人表达的创作中,而后者则聚焦于呈现微观的现实形态和不同的社会样貌,提供给观众更多的空间与依据去进行个人判断。在此基础上所涉及的客观性,本质上已经不再是有公共认同的单一客观判断标准,而是忠实于创作者自身的个人客观创作准则,它取决于电影人自身养成的价值取向、美学原则以及方法和立场的选择。或者说,它超越了“呈现什么”的范畴,而演变成了一个“如何呈现”的问题,正如萨蒂亚吉特·雷伊以最简练的话语精辟概括的:“我倾向于不相信他们正在说什么,但自始至终为他们怎样说的而吸引。”[1]382 ①大部分电影理论研究者倾向于认为“真实电影”的名称来源于吉加·维尔托夫二十年代初期所制作的电影纪录片系列的名称“Kino-Pravda”(电影-真理),在这一系列的类似于新闻片的短纪录片中,维尔托夫领导的电影小组把摄影机第一次对准了现实中的生活经验,拍摄工厂、学校和酒吧内普通人的活动,几乎没有采用任何现场调度,这种捕捉现实中真实存在瞬间的电影拍摄方法被维尔托夫认为是可能达到他所推崇的“电影-真理”状态的途径。 ②参见影片《猪年》(In the Year of the Pig,1968)、《美国难以直视》(America Is Hard to See,1968)和《原子咖啡馆》(Atomic Café,198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