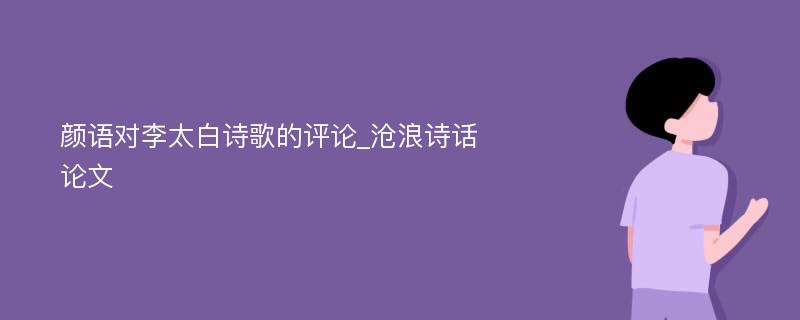
论严羽评点《李太白诗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白论文,诗集论文,论严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严羽的诗论遗产,除《沧浪诗话》外,还有一部二十二卷本的评点《李太白诗集》(下文简称《评点》)。这是一片丰厚的理论沃土,又是一片被遗忘的处女地。严羽诗论的研究者几乎未曾在此涉足,它对李白研究的价值也未引起应有的关注。王琦《李太白全集·跋》说:“李诗全集之有评,自沧浪严氏始也。”肯定其开创之功;可又鄙薄其“批卻导窾,指肯綮以示人者,十不得一二”,这就未免责之过苛,有失允当。理论拓荒者的某些粗疏乃至于幼稚,也饱含着筚路蓝缕的艰辛,开启着后继者的严密和成熟。直觉式的点悟虽然缺乏逻辑方法所具有的周详细密,然而从诸多评点的爬梳剔抉中却不难看到严羽对李白诗歌艺术的敏锐感受和闪烁着的理性光辉。在《沧浪诗话》中,严羽对李白创作经验的体认大都已抽象为理论的概括,是隐而不彰的,而在《评点》中则表现为探幽入微的品味和经验实证的阐述。二者的契合和互补,构成了完整、独特,有着丰富内涵的李白诗说。把《评点》和《沧浪诗话》结合起来考察,它对李白研究的意义就更见显豁。
“妙悟”说是严羽诗论的核心。他说:“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1〕”把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潜心体认视为通向“妙悟”的必由之路。他把论诗的最高标准定位在“入神”上。《沧浪诗话·诗辨》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盛赞李杜的诗歌达到了诗歌审美的这一最高境界:“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何谓“入神”?在《沧浪诗话》中,严羽对此未作具体阐述。陶明濬说:“真能诗者,不假雕琢,俯拾即是,取之于心,注之于手,滔滔汩汩,落笔纵横,从此达到性灵。歌咏情志,涵畅乎理致,斧藻乎群言,又何滞碍之有乎?此之谓入神。〔2〕”从严羽对诗的审美追求看,他主张“词理意兴”〔3〕的高度统一; 赞美“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4〕;认为诗“须是本色, 须是当行”〔5〕;推评“浑然天成,绝无痕迹”〔6〕。可见,“入神”应是“透彻之悟”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是基于对诗歌特性的透彻认知和完全把握而在创作中表现出的内容和形式浑然一体的完美结合。陶明濬揭示的对诗歌创作必然的把握和因此随心所欲而不逾规的自由创造达到的审美境界,庶几就是严羽所标举的“入神”。
李白的诗歌创作如何臻于“入神”之境?李白诗歌的“入神”具有怎样的个性特征?《评点》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作了具体、深入的探寻。
一
严羽论诗注重意、兴的结合和统一。意即情性、情意,兴为兴象、意象。严羽对李白意兴高度统一的形象概括和意境创造有冥心独造的感悟。在他看来,李白诗歌意兴的结合依其侧重点的不同,创造的境界也不同。
一是注重兴,侧重于事物、景象的描绘,而在事物、景象之外,却可使人领会到一种心灵的境界。王昌龄《诗格》云,“处身于境,视境于心”,“了然境象,故得形似”,谓之“物境”。然而仅得“形似”,难以唤起想象,产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严羽所论有别于此。他认为李白对事物、景象的描绘每多大笔勾勒,略貌取神,故能得其神似。《谢公亭》:“客散青天月,山空碧水流。”严羽评曰:“当此际者,直可澹然无语,不能举似。”“不能举似”,即无法从形貌上写出故交云散、盛会难再的景况;“直可澹然无语”,则云面对孤月在天、空山寂寂、碧水长流而生遐想和追怀,有言外旨、味外味。严羽常以“可画不能画”〔7〕或“可画难画”〔8〕一类的批语评李诗。“难画”、“不能画”的正是事物、景象的神韵。如评“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空宜”(《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云:“写山水情性,悠然、杳然,画笔所不能及。”评“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欲素愁不眠”(《长相思》)曰:“只二语不可画,不可赋,妙绝。”“红妆欲醉立斜日,百尺清潭写翠娥”(《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以斜日、清潭为映衬,全然为红妆美人传神写照,故又评曰:“难描难画。”他如,《赠宣州灵源寺仲濬公》云:“敬亭白云气,秀色连苍梧。下映双溪水,如天落镜河。”严羽评曰:“描写云天水色,作一合相,如此幻现。”这里的“幻现”二字不可等闲放过。它揭示的这种意境创造的审美特性是,作者借助“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9〕”诉诸读者的想象和冥悟,令读者完成对所反映的“音”、 “色”、“月”、“象”的体验;意境的创造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却有“言有尽而意无穷〔10〕”的审美韵味。这种意境创造正是严羽所崇尚的。
二是意兴相化、情景相融的“情境”。严羽认为李白诗多“情在景中,景在眼中〔11〕”的“好情境”〔12〕。在“情境”的创造中,情性、情意占据着主导地位,景象饱含着诗人的主观情思。“好情境”的创造关键在于“真”。“情境真便是好诗。”〔13〕这是抒情诗艺术经验的总结,用以品评感情真率、注重抒写主观感受的李白诗也切中肯綮。严羽赞叹“摇笔望白云,开帘当翠微。时来引山月,纵情酣清辉”(《赠秋浦柳少府》)为“好情境:对之可以忘愁、忘老,那得不淹留”?好就好在寄逸兴于山水,情真景亦真。他评“相思黄叶落,白露湿青苔(《寄远》其十一)云:“只须言景之凄凉。”因为景语即情语,“情在景中”。《江夏赠韦南陵冰》有句云“头陀云月多僧气”,涉想新奇,严评:“情境会处乃得此语,非虚想所能得。”指出正是情与景遇托起诗人奇特想象的翅膀。他评“雁度秋色远,日静无云时。客心不自得,浩漫将何之”(《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谓其“取境远,取情近,兴致应如此”;又说“天清一雁远,海阔孤帆迟”(《送张舍人之江东》),“情境旷远,可望可思。”这也表明,兴致、情性始终左右着诗人的“情境”创造。
一般说来,情与景遇,情融于景,情思由景物生出,诗人笔下的景物虽然染上了诗人的情思,但仍不失为冷静的客观存在,并未随诗人主观情思的变化而变化。李白则时常凭借强烈的感情赋予客观景物以生命。客观景物为诗人强烈的感情所改造,因之改变了本来面目,甚至可以随着诗人的感情意志行事。以情造景,移情于物,景被情化。严羽用“无情生情”来揭示这种“情境”创造的特点。“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无知无情的明月竟如此富有同情心,能够接受诗人的嘱托去慰藉远方不幸的友人。所以严羽评曰:“无情生情,其情远。”李白惯于引山川风物为知己,景物被人化了,人也随之而对象化,写景即写人。诚如严羽所评说的:“水色傲溟渤,川光秀菰蒲”(《赠丹阳横山周处士惟长》),“但称湖之‘傲’、‘秀’,其人可知”;“好风吹落日,流水引长吟”(《杭州送裴大泽赴庐州长史》),“有此光景,其人可知”;“白云遥相识,待我苍梧间”(《赠卢司户》),“云相识而待,此一片云,太白看得飞活,可与为友”。他又评《独坐敬亭山》云:“与寒山一片石语,惟山有耳;与敬亭山相看,惟山有目,不怕聋瞆杀世上人。”应当说,这类诗作才是更具李白创作个性的“情境”创造。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总结的“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的审美经验,在他对李白诗歌意兴的结合、统一的认知中,也作了反复的验证。《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虽无一字言怨,怨意却如盐着水,融于象中,不露痕迹。对此,严羽有独到的感受:“上二句,行不得,住不得;下二句,坐不得,卧不得。赋怨之深,只二十字可当二千言。”评《怨情》(“美人卷珠帘”),道是:“写怨情已满口说出,却有许多说不出,使人无处下口逼问,直如此幽深。”评《长门怨》其二云:“前首言愁已清微,此但举如此光景,不言愁,愈不堪。”评《长相思》“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亦云:“不说憔憔,却现出。”不说之说,便见婉曲、含蓄、隽永。他如,评《远别离》“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说是:“言‘不灭’,便煞;‘可灭’,意转永。”因为诗意翻进了一层,更显得婉曲。《送陆判官往琵琶峡》,因其“语短意长”,也被他推评为“是五言绝妙境地”。
三是直抒胸臆。直抒胸臆的意兴结合方式则侧重于意,即情性、情意溢出了兴象。既然“好诗”的首要标准是“真”,含蓄与否则毕竟是第二位的。物境的创造略貌取神而神出,情景的创造情景交融而“情在景中”,都有不直说、不说尽的审美特性。直抒胸臆则能达真情便佳。严羽论诗虽然提倡含蓄,欣赏蕴藉之美,却不专主含蓄、蕴藉;他认为诗的本体是“吟咏情性”,也就不排斥胸情的直接发抒。因此,他赞赏李白情感的奔放磊落,对李白诗歌因情感的奔突不可羁勒而溢出兴象的创作特性也颇为赏识。如评《襄阳歌》“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为“豪兴深情”。以“豪侠语,千古有生气”评说“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笔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表现的铮铮气骨。《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其二有句云:“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严羽感慨系之,评曰:“说尽炎凉态度,可以警世,可以平情,政不必温厚。”《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从画境描写联系到现实,诗人否定了自我一向所持的功成身退的理想,道是:“五色粉图安足珍,真仙可以全吾身。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杀人。”对污浊现实的愤慨喷涌而出。严羽为之击节赞叹道:“极破,极快,岂必以含蕴为佳!”可见,含蓄蕴藉和淋漓痛快两种迥然不同的美感形态可以殊途而同归,臻于审美的极致。严羽又引申说:“通篇皆赋题目,只此是达胸情,始知作诗贵本色,不贵着色。”他从李白以自然的方式达胸情之真,悟出了诗歌艺术的妙谛,也为他在《沧浪诗话》中倡导的诗“须是本色”的审美理想作了明确的阐释。所谓“作诗贵本色”,不就是指注重“吟咏情性”的真实和真率,不矫饰,不做作吗?
严羽对李白诗歌意境创造中“露”与“藏”、“有尽”与“无尽”关系的处理也有深微的感悟。《江夏行》:“忆昔娇小姿,春心亦自持。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谁知嫁商贾,令人却愁苦。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严羽指出,商妇这段内心独白“以嫁之前后言之,无遗情,有余情。”商妇的思和怨,一股脑儿作了倾诉,故曰“无遗情”;而由思而怨的心路历程和思与怨的跌宕交织,却在在耐人寻味,故曰“有余情”。《横江词》其五:“横江馆前津吏迎,向余东指海云生。‘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严羽评曰:“此诗四句一气。其意言内已尽,而言内更无尽。”何以“已尽”又“无尽”?“如此风波不可行”,从诗的表层意蕴看,确已见其言知其意,竭言而尽意;而李白急于渡江的神情,津吏之热情、关切和老于经验的自信,则要由语言的暗示去想象。至于自然风云的变幻是否寓含着对政治风暴的预感,则见仁见智,更要于言外去探寻。严羽揭示出李白“露”中有“藏”、以“有尽”概括“无尽”的艺术造诣,也就把李白直达胸情之作与那些“叫噪怒张”〔14〕、言尽意尽的浮躁浅薄诗作划清了界限。
二
在《沧浪诗话》中,严羽提出“诗有别趣,非关理也”〔15〕的主张,对宋人“尚理而病于意兴〔16〕”、“以议论为诗”〔17〕的抨击也不遗余力,似乎一味排斥诗中说理。其实,这是对严羽主张的误解。因为他接着还指出,诗的创作“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18〕“极其至”便是“入神”。说没有“多穷理”的修养,诗的创作便不能达到“入神”之境,不可谓不重视“理”;他盛赞“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19〕,并未排斥诗中说理。在严羽看来,诗中说理的是与非,要依据“吟咏情性”的审美原则作判断,以理性的思辨代替感情的激扬,用冷冰冰的哲理取代火辣辣的诗情,堕入了理障,违背了情性美的审美要求,自然为严羽所不取。“诗有别趣”,“理趣”也是一种“别趣”理为深厚的情感所裹挟,与意兴相契相融,则为严羽所首肯。境中含理,目击道存,诉诸情性和兴象,“不涉理路,不落言筌”〔20〕,便有兴致,有余味,而臻佳境。
李白的诗歌不乏议论说理,然而他的人生的思考总是伴随着感情的激荡,也伴随着高度概括的兴象显现。因而严羽认为李白诗的说理为“情中说理,无理气”〔21〕,与宋人的“尚理而病于意兴”有着根本的区别。《金门苏秀才》一诗云:“得心自虚妙,外物空颓靡。”说的是身、世两忘,便可超然而游于世外。前此诗中所写正是味尘脱俗的世外之境。严羽评曰:“此二语接上妙。若拆开独说,道理亦常淡耳。”说明理从境生,才有盎然的兴味。《梦游天姥吟留别》云:“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人生失意的深沉感慨饱含在东流水的概括兴象之中,以理中情之真挚感发人心。故严羽评曰:“甚达,甚警策,然自是唐人语,无宋气。”又如,评《东武吟》“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雄”云:“是豪上语。若‘犹’字、‘不’字一改,可成见道语?”评《南阳送客》“斗酒勿为薄,寸心贵不忘”云:“真情厚意,二语道尽。”也都是着眼于感情的抒发或引发来评论李白诗中的说理。
李白有的诗简直就是以说理的方式言情。议论是否合乎逻辑推导无关紧要,感人的艺术力量源于强烈的感情。《月下独酌》其二通篇说理,却旨在抒情。“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不合逻辑的“爱酒辩”,恰恰趣味盎然地抒写了诗人爱酒的情性。议论堂而皇之却近乎诡辩,故严羽说它“极豪率”;情性的表露富有情趣,故又说它“极雅蕴”,“政是佳境”。诗中又说:“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所谓“酒中趣”,是酸楚的甜蜜,是政治失意后精神归宿的追寻,个中情韵强烈而复杂。故严羽评曰:“‘何忍独为醒’,看得醒者可怜;‘勿为醒者传’,看得醒者可鄙。”《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云:“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秋兴”是“逸”还是“悲”,本就因人而异,偏偏以“逸”否定“悲”,从逻辑上说,颇有强加于人之嫌。然而,正是这种无理之理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突现了诗人高旷的襟怀和送别之情所独具的逸宕高朗的风致。故严羽评曰:“道其真情,非故为翻案。”
三
诗人才性各异、情感类型有别,艺术构思方式和情感抒发方式也就有所不同。《沧浪诗话·诗评》说:“观太白诗,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才豪逸,语多率然而成者。”所谓“要识真太白处”,主要就是要把握李白的才性特点、情感特质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李白独特的艺术构思方式和情感抒发方式。
何谓“天才豪逸”?李白在为崔成甫写的《泽畔吟序》中说:“观其逸气顿挫,英风激扬,横波遗留,腾薄万古。”这也是夫子自道。“英风激扬”、意气腾薄为“豪”;“横波遗流”、超迈旷远即“逸”。“逸气顿挫”离不开“英风”激荡其中,“豪”与“逸”是相辅相成的。严羽评“平衢骋高足,逸翰凌长风”(《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云:“白才真如此,可以自赠。”也是对李白这一才性特点的体认。
唯其才性“豪逸”,情感多具外放性质,一旦兴会标举、灵感冲动,诗思便通畅无阻,不仅“境每来会”,想象活跃,而且下笔琳琅,一气呵成。可以说,诗情喷涌、思疾语捷、一挥而就,是李白诗歌艺术构思方式和情感抒发方式的显著特征,他的诗也因之呈现出浑灏天成的艺术风姿。严羽对此有潜心的体认和独到的感悟。如评《古风》其三十一说:“寻常,新逸,力搜不得,偶摄亦不得,当是才兴所至,无复典格存于胸中,乃有此耳。”评《赠钱征君少阳》云:“赋情如丘山,而出口轻若蝉翼,真是逸才。”说李白诗多“一往豪情,使人不能句字赏摘”〔23〕。认为李白的诗歌是“才兴所至”、灵感冲动时天然凑泊的产物。
严羽说:“太白诗多匠心,冲口似不由推敲,能使推敲者见之而丑。”〔24〕又说:“盖他人作诗用笔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喷即是。”〔25〕这个比较敏锐地揭示出不同的艺术构思过程和语言提炼过程的区别,尤为耐人寻味。“用笔想”是苦吟诗人和提倡功力的诗人的创作方式。艺术构思过程和语言提炼过程分离,往往在构思过程完结之后,再下笔“力搜”,反复“推敲”,作语言的艺术提炼。“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26〕”,思苦而语奇,丧失天然的真趣。李白则异乎是他不屑于作形象概括和意境创造之外的语言雕饰。在《冬日于龙门送从弟京兆参军令问之淮南觐省序》中,他对自己诗歌的创作过程有过这样的描述:“观夫笔走群象,思通神明,龙章炳然,可得而见。”意即各种兴象伴随着诗思奔聚笔底,想象活动神妙活跃,缤纷的文采也随之出现。可见“冲口似不由推敲”的奥秘在于语言提炼的过程已包含在艺术构思过程之中;“但用胸口一喷即是”的敏捷,根植于他的才性和任情率真的情感抒发方式。语言提炼与艺术构思同步,便可意到辞工,不假雕饰,也因此而无工可见,无迹可寻,创造出明晰而又浑成自然之美。
严羽正是从李白这种独特的“匠心”来评说其诗歌“自然”的美学风貌的。他称赞李白的诗“情深思巧,却不费些子力,又非浅口所能学〔27〕”,“自然拈出,却使造揉者知丑”。如,评《见野草中有名白头翁者》,“皆是口头语,却不易到”。说《寻雍尊师隐居》一诗,“不必深,不必琢,但觉其应尔”。评《静夜思》云:“前句生三句,二句生四句,却一意说出,不由造作。”认为《梁园吟》“挂席欲进波连山”是“壮险语,却自然,非造非矫”。又评《春日游罗敷潭》“云从石上起,客到花间迷”二句云:“自然如此,拈出却生动。”这类评语在《评点》中几乎俯拾即是,可见其推许之重。
自然并非不要文采。风华不由粉黛,自然的文采是内在的华采。李白的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质朴的诗句饱含着诗情,以天然的风韵取胜。《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有句云:“衣貌本淳古,文章多佳丽。”严羽评曰:“衣貌华不得,文章淡不得,相易乃两成其美。”严羽赞赏的诗的华采正是朴中生采。因而,他评《秋登谢朓北楼》云:“入画品中。极平淡,极绚烂,岂必王摩诘?”“极平淡”的是诗外表的语言,“极绚烂”的是质朴平淡的语言蕴含的诗意诗情。说《天门山》“自然清遐”,《僧伽歌》的诗句作“本色语”,又“清超之极”,评“把酒尔何思?鹧鸪啼南园”(《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其二)“耳目之前,意想之外,悠然有余”,也无一不是指朴质自然的语言饱含着浓郁的诗情,有着内在的华采。
李白的诗因艺术构思的快捷有时不免带来语言提炼的不足,而失之于粗率。严羽对此也有直言不讳的批评。如,评《古风》其五十五“慷慨动颜魄,使人成荒淫”云:“‘慷慨’,句本魏文帝‘秦筝何慷慨’,而与下句不合。牵率来文,遂乖本咏,捷笔失检,往有此类。”评《战城南》结语用典“生割不化”,“虽豪情不拘,而率笔未善。”评《江夏赠韦南陵冰》“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云其“太粗豪!此太白被酒语,是其短处。”逐一看来,这些批评虽然未必都很确切,但作为李白创作的经验教训看,还是中肯的。
四
《沧浪诗话·诗辨》对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诗普遍存在的“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多所批评,指责他们的诗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的确,讲究字字有来历,在古人的书袋中翻跟斗,全然是作茧自缚,窒息了情性的自由抒写,跟“入神”境界的创造更是碣石潇湘,相去甚远。在《评点》中,严羽也在对李白创作经验的体认中阐发他的“用字不必拘来历”,“不必多使事”〔29〕的主张,磨砺他对江西诗派批判的武器。
李白的情性抒发重“本色”,下字用语崇尚真切自然,灵活洒脱。《评点》开篇,在评《古风》其一“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中,严羽便指出:“‘秋旻’有眼。若读《尔雅》太熟,但认作有来历,非知诗者矣。”他不厌其烦地论证李白那些从生活中提炼的语言“无典实可寻”〔30〕,有味,有表现力。强调用语“情事能达,不必深求”〔31〕。《胡无人》:“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严羽曰:“若言‘雪照天兵’便寻常,正不必引释出处,一有来历反无味矣。”评《春思》“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云:“‘识’字说得春风有心有眼,却又不落尖巧。”评《凤台曲》“天借绿云迎”亦云:“天亦借云,奇。‘借’字不必有来历,然不觉其尖凿,所以为佳。”
“不必多使事”并不否定使事,关键在于使事是否为“吟咏情性”所必须。写即目所见,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出于直寻,方能明晰而不隔,自然无贵于用事。钟嵘曾以古今胜语为例说:“‘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32〕然而情景交融的意境大抵只能寓托比较单纯的感情。李白的思想感情复杂。他一生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挣扎,胸怀壮志而奔走,却遭遇嘲笑和冷漠;纵情高歌理想,又悲叹失意和幻灭。雄豪与悲愤,旷达与颓丧,乐观与消沉,起伏激荡、错综交织。严羽指出,李白的诗“亦愤亦达”〔33〕,或“悲言不悲,其悲弥甚”〔34〕,或“因愁发雄,雄愈奋〔35〕”,或“情旷亦复情热”〔36〕。这种矛盾复杂的感情自非一一均可借情景交融的意境来达,不能不驱遣古人古事作比拟,使矛盾复杂的感情具象化、对象化。
使事能否“入神”则取决于用以抒写感受、感情能否活脱入化。《古风》其三十六:“抱玉入楚国,见疑古所闻。良宝终见弃,徒劳三献君。”用卞和献玉的故事,推想到和氏璧最终还是被毁,抒发忠直见疑、良才见弃的悲哀和愤懑。感情激越,讽托现实之意也翻进了一层。因此严羽评曰:“和玉以既剖为幸,白更深将来之嗟。卞只足痛,李倍伤心。用事如此,方有论、有情、有识。”拈出“有论、有情、有识”,揭示了李白用事高明之处和“入神”的特点。又如,他评《长干行》“绕床弄青梅”云:“‘摽有梅,匪媒弗得’,用自关情。 ”“用自关情”便妥贴。评《扶风豪士歌》“作人不倚将军势,饮酒岂顾尚书期”曰:“真豪语,如此使古事才有生气。”说《赠张相镐》其二“以留侯比镐,以李广不侯者自况,气不衰飒”。注重用事的“生气”,也就是注重用事要以我为重,一任感情抒发的需要自由驱遣。倘若“为事所苦”〔37〕,用事则成事障。李白用事以我为主,不拘枝节的真实,不受典故的束缚,旨在传神达情。《江夏赠韦南陵冰》“山公醉后能骑马,别是风流贤主人”二语,用山简醉酒事如同己出,状写人物,尽传其神,故严羽赞曰:“有韵致,便能使事化。”费长房见老翁卖药,市罢,辄跳入壶中。在李白笔下,药壶成了酒壶。《拟古》其八曰:“饮酒入玉壶,藏身以为宝。”意谓求仙既不可得,不如沉缅于酒,用事也活而能化,故严羽云:“用费长房事,乃入浑冥。”《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用夷、齐事云:“食雪首阳巅。”夷、齐“食雪”,事无考,然如此更可表现宇文与崔洁身全志的品格,自不妨添枝加叶而用之。严羽称赞这样用事“不泥故迹”。他又评《送贺宾客归越》“应写黄庭换白鹅”云:“但取黄白相映耳。即谓羲之写《道德》,贺写《黄庭》,亦不必检点用事之误。”可见李白用事之“活”与“化”。
李白诗歌运用语典也有融化浑成的特点。严羽于此也多所赞许。《君子有所思》云:“青冥天倪色。”严评:“‘倪’字想入,莫可端倪。如此用《庄子》,亦新、亦雅、亦别,不为道理所缚。”《赠黄山胡公求白鹇》云:“白雪耻容颜。”严评:“用《孟》义亦新变。”“新”、“雅”、“别”,无一不是创造性用语典的表现。《登敬亭山南望怀古赠窦主簿》云:“仙者五六人。”严评:“用《鲁论》不觉。”《送程刘二侍郎兼独孤判官赴安西幕府》云:“汉家草绿遥相待。”暗用王孙春草的典实,一表伫盼功成归来之意。严评:“用王孙事,隐秀,妙。”“不觉”、“隐秀”,亦即用典而不着痕迹。《周易》有“云从龙,风从虎”之说,李白则云:“激昂风云气,终协龙虎精。”(《献从叔当涂宰阳冰》)严羽评曰:“‘精’、‘气’字佳,‘精’字更难下。‘激昂’与‘协’字俱有力,有身分,意用与《易》语不同。”“意用”即师其意而不师其言。能够提炼出新鲜有力的语言达意传情,而臻佳境,非“入神”而何?
注释:
〔1〕〔3〕〔6〕〔16〕〔19〕〔20〕《沧浪诗话·诗评》。
〔2〕《诗说杂记》卷八。
〔4〕〔5〕〔29〕《沧浪诗话·诗法》。
〔7〕评《闻丹丘子于城北营石门幽居,中有高凤遗迹, 仆离群远怀,亦有栖遁之志,因叙旧以寄之》“春华沧江月,秋色碧海云”。
〔8〕评《采莲曲》“若耶溪旁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
〔9〕〔10〕〔14〕〔15〕〔17〕〔18〕《沧浪诗话·诗辨》。
〔11〕评《下寻阳城泛彭蠡湖寄黄判官》。
〔12〕评《赠秋浦柳少府》。
〔13〕评《赠别从甥高五》“贫家羞好客,语拙觉辞繁”。
〔21〕评《中山孺子妾歌》。
〔22〕评《寻高凤石门山中元丹丘》。
〔23〕〔25〕评《将进酒》。
〔24〕评《赠新平少年》。
〔26〕贾岛《送无可上人》“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二句自注。
〔27〕评《劳劳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
〔28〕评《金门答苏秀才》“鸟鸣簷间树,花落窗下书”。
〔30〕评《幽涧泉》“寂历似千古”。
〔31〕评《白日(田)马上闻莺》。
〔32〕《诗品·总论》。
〔33〕评《少年行》。
〔34〕评《古风》其四十九。
〔35〕评《独漉篇》。
〔36〕评《温泉侍从归逢故人》。
〔37〕评《梁甫吟》“帝旁投壶多玉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