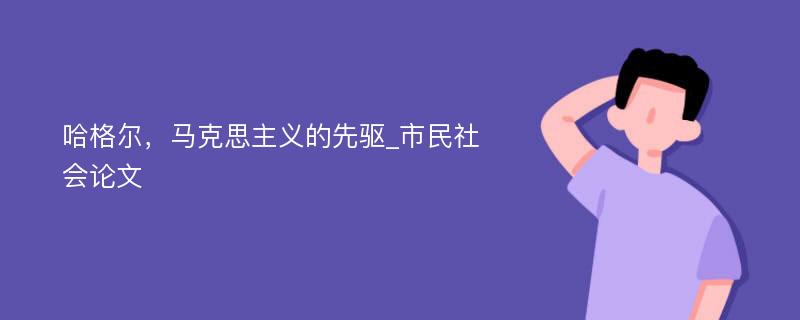
作为马克思主义先驱的黑格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先驱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黑格尔思想的核心特质是历史性概念,他相信,随着时间推移,人和社会的全部努力以发展为表征。作为一个哲学家,黑格尔最感兴趣的是哲学的历史性,他假定每个时代的哲学在它自己的时代具有独特的形状。然而,忽视同样归功于黑格尔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概念,乃是一个失误。在卡尔·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意识到,各种人类社会在时代推移中发展,或者说历史也是关于在时代变迁中出现的多种类型社会组织的记录。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学生,从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到《哲学的贫困》,在可以列出来的1841~1847年的著作文献中,他表明自己最熟悉的是《黑格尔全集》第一版(1832~1841)中收录的著作。马克思受黑格尔影响,或者说黑格尔在很多著作中论述的社会形态的历史学为马克思提供了理解社会形态本质的方法论。黑格尔教会马克思将社会模式概念化,并将国家看作历史的产物,正如他们发现自身是在社会条件中得到塑造的。
黑格尔不是马克思,他首要关注的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发展的哲学形状,但这并不意味着黑格尔忽略了自然——人类进化的物质条件。黑格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如果无视他肯定自然和物质因素有助于决定哲学和人类社会历史性的路径,则是对黑格尔的完全误读。
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优先看重精神的发展。作为主客体的统一,精神是思维的自我考察。思想将自身投入现实,思想在外部对象中形成,并赋予它们某种意义。基于自身创造性的反思,思想获得了自我认识。通过在外部对象中观察自身,思想表明自身的权力。精神是思想的自我意识,是思想的学习过程,或者说当思想在一个对象中认识到他自身的时候,他在自身中知其所是。精神是自我认同的权力,表明思想和存在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黑格尔知道精神不是永恒的,它不是柏拉图的理念,也不是基督教神学。精神有其诞生地,当自我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时候,精神的分娩就发生了。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第三卷《精神哲学》“主观精神”章中,黑格尔指出,当主体使自身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时候,精神就产生了。精神发展出二重性,发展出自然或曰人类学与主观精神的矛盾。黑格尔写道:
在人类学中,第一个东西是在质上确定的、束缚在自己种种自然规定上的灵魂(例如,种族的区别就属于这种情况)。灵魂从这种与其自然性的合二为一中走出来进入与自然性的对立与斗争中。……伴随这种斗争而来的是灵魂对其形体的胜利,是这种形体性的降低并完全降低为灵魂的某种符号,即成为灵魂的体现。这样一来,灵魂的观念性就在其形体性中显露出来,而精神的这种实在性就以某种本身还是形体的方式在观念上建立起来了。
在精神现象学中,灵魂现在通过对自己形体性的否定而提高为纯粹的、观念的与自己的合一,成为意识、成为自我,自为地与自己的他者相对立。①
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将人类的历史性分为三阶段:
第一种的社会状态严格地是家长制的独立;第二种是所有权和地主农奴间的关系;第三种就是公民的自由。②
将人类历史发展分为三阶段的过程,并非黑格尔独有的理念。历史三阶段论在18世纪得到了最突出的阐述,如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的著作所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③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资料卷收录的一篇研究充分的文章中,丹佳·威尔雷塞斯指出,当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的时候,他撰写了弗格森《论市民社会史》一书摘要。④在其后于1847年写作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引用了弗格森关于创新研究的段落。⑤ 1844年,马克思还读到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严厉批评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然而,马克思在1841年阅读了黑格尔的历史学著作和人类学著作,先于他了解斯密、弗格森或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其他成员。黑格尔在他逝世前的1831年也知道斯密和弗格森的著作,因此,三阶段论首先对黑格尔的著述产生影响,然后通过黑格尔,马克思了解到苏格兰学派对历史所作的三阶段分期。起初从苏格兰学派到黑格尔的这条理论线索后来延续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⑥
有必要在这里指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是一个完整的文本。我将在后面的段落中论证,《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情况也是如此。正如于尔根·罗雅恩的著作所证明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是由不同的草稿、不相连的页面组成的,反映了马克思对经济理论进行自我思索、内在沉思的踪迹。然而,并不能据此否定这个事实,不相连的这些草稿的全部内容表明马克思对斯密的借鉴以及他对苏格兰学派的批评。无法否认这个事实,《经济学哲学手稿》并非单一的文本,马克思在试图否定《国富论》作者的这些不相连的笔记本中对斯密有所影射。
在这篇文章后面的部分,我将描述黑格尔理解的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我的论述将分为四个部分:(1)历史的三阶段论的经济基础;(2)财产、阶级、种族和国家的变迁;(3)早期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和国家;(4)人类精神的三阶段论。
历史的三阶段论的经济基础
第一阶段:部落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最初形式,黑格尔认为,婚姻是道德生活最原始的样态。黑格尔将财产权视为最基本的人权,而当家庭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的时候,财产权就获得了家庭财产权的形式。占有仅仅发生在家庭谱系中。⑦ 然而,原始家庭是前农业经济(pre-agricultural economic)时代的组成部分。食物、毛皮等生活基本必需品是这种家庭从对动物的放牧中获得的。财产被规定为家庭对动物的所有权。
家庭也受制于历史,它演变为氏族,并从氏族变成了部落。部落的存在同时具有经济基础和地理基础。从经济上看,部落基本上以狩猎为主。从地理上看,部落的存在如黑格尔所说的“中亚细亚”具有土地干旱的特点,而从里海延伸到黑海的地理是以草原与平原来标记的。⑧ 在部落阶段,政治宪法的样态是父权制,或者说部落中的单一家庭控制权力,而族长是专制统治者。
在这一点上,有必要作两种区分,社会和市民社会是不同的,政治宪法和国家也是不同的。
家庭生活,作为家庭之延伸的氏族,作为氏族联合体的部落,是社会,或者说是个人交往的处所。“社会”这个词指的是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黑格尔以18世纪商业资本主义即工业革命为例来说明“市民社会”这个词。黑格尔从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借用了市民社会这个术语。我将在稍后的章节中阐述市民社会。社会存在于部落这个发展阶段,而市民社会是商业革命的产物。
政治宪法是政府的工具,或者说是规范社会的制度。然而,国家是道德的总体。国家是政治宪法和道德精神这两个因素的综合。部落生活缺乏道德精神,道德精神是在后来的历史时期实现的。据黑格尔所见,部落阶段已具备了政治宪法、宗法专制,但因为其革命发展阶段过早而不能发展为国家。
以父权制为主体的阶段是最低限度。个性是在场的,各个人在部落共同体内部交往,但主观自由的意识尚不发达。主体仍然将自己限定在部落环境中,自然仍然是自己的主宰,而不是将自己假定为控制自然的内在力量,由于这种自我的缺陷,部落的主体仍然无法体验自己的自由。如果没有权力意识来规定主体,真正的主体就不会产生。
财产、阶级、种族和国家的变迁
第二阶段:农业和大河系统
人类进入历史发展第二阶段的入口是经济革命创造的条件,从农业狩猎发展为城市生活。这种经济转变对某些地理条件有益。部落阶段的地理所辖为“中亚细亚”的草原和山区,而农业革命的地域网络乃是大河系统:中国的黄河和长江、印度的印度河和恒河、巴比伦的幼发拉底河以及埃及的尼罗河。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埃及不仅因为在地理上环绕这些大河系统而富庶,而且它们与海洋连通。中国东部与太平洋毗连,印度与印度洋相接,巴比伦与阿拉伯海连接,埃及与地中海相连,海上交通的可能性刺激这些帝国进行贸易投资。海洋鼓励了第一次商业革命,而且它们孕育了帝国。与部落存在于内陆不同,第二阶段这些帝国因海洋而得到拓展。
黑格尔对这些革命性变化的丰富论述表明,不仅农业得到了发展,早期中国、印度、波斯和埃及也因此实现了经济增长。正如黑格尔所见,波斯帝国内部的复杂性是独特的,它是中国和古希腊的过渡点,他以如下字句描述波斯的商业化转型:
这些城市根据两重需要而发生,——一方面是游牧生活被放弃了,从事农业、手工业和贸易,必须有一定的居室;古老的传说表明这一带平原地区一向为游牧民族所居住,而自从城市产生,那种生活方式就被放弃了。⑨
黑格尔选择以波斯作为历史发展第二阶段代表的意图在《历史哲学》的另一处具体描述中得到证明:
这个民族的法律和制度明确显示出非常的简单性。他们有四个阶级:祭司、武士、农民、工匠。没有提到贸易经商,足以看到这个民族仍然处于某种孤立的状态。州县、城市和道路的首领都被提到了,一切都只与市民法律而不与政治法律相关……还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找不到阶层,而只能找到阶级,同时这些不同的阶级之间没有不准结婚的规定……⑩
黑格尔不是地理决定论者,但他敏锐地意识到,地理环境对历史事件具有重要作用。早在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因描述美国边疆而对美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之前很久,黑格尔看到,边疆是减少社会骚乱和经济动荡的安全阀门。法国大革命爆发33年之后,1822年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讲授哲学史的时候,认识到边疆使悲惨的受压迫者通过移民而找到摆脱压迫的道路,获得经济独立的空间。由于意识到“移民的出路”起到了巨大的政治作用,黑格尔写道:“如果日耳曼森林那时还存在的话,法国大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了。”(11)黑格尔对历史的重新书写来自于这个信念,德国的边疆通过接纳巴黎的无套裤汉(sans-culottes)而朝法国移民者开放,而这将消除社会的仇恨,防止恐怖统治的降临。
黑格尔对开放空间之重要性的肯定再次显示了他对美国的乐观态度。黑格尔谴责奴隶制,显然他将南部联邦视为新兴国家的病灶。然而,他所设想的美国,这个面向太平洋的开放空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请柬。这个新兴国家没有经过中世纪,没有封建贵族这种包袱,因此新世界的开疆者有机会接受最现代的文化,得到欧洲文化的启蒙,不必经过黑暗时代的笼罩,就可以获得肥沃的土壤,因此他们能够盛开到新的高度。
第二阶段的经济发展引发了财产权性质的转变。父权制这个阶段的财产权由“放牧”这个术语规定,而当历史发展到商业阶段,财产权由“土地”和“企业家所有”这样的术语来规定。
这种财产权性质的转变发展为阶级的变化。黑格尔在课堂讨论中表明他对社会分层本质的深刻认识。早于马克思二十多年,黑格尔把握了政治的阶级划分及其起源的本质。黑格尔知道,社会分层引发了财产所有权的变化,而基于财产所有权的社会等级制度是阶级统治的基础。如果阶级以财产权为基础而得到划分,那么占有财产权将意味着富有的阶级霸占着权力。
黑格尔关于阶级分层的先进观念使他看到了阶级和阶层的差别。官僚阶级统治是中华帝国的特点。效忠于皇帝的官僚填补了帝国的统治机构。官僚不是因出生而世袭的,而具有很高的学历,他们需要通过国家组织的选拔录用考试,以便为帝国政府所选择。
种族制度是印度的特征。印度存在着三个种族:婆罗门被认为是神圣的,设立了印度教的教会;武士阶级,他们是提供生活必需品的商人,因为他们掌管着农业、工艺和贸易;首陀罗,或者说贱民,他们是印度的无产阶级,为了获得低廉的工资而工作。(在黑格尔看来,印度存在着四个种族,武士阶级和商人不属于一个阶级。——译者注)印度帝国的种族是世袭的,或者说通过DNA而得到合法化。种族制度仅仅因宗教霸权而提供了阶级的合法化。
在人类进化的第二阶段,国家首次亮相。在历史发展的第一阶段,即游牧时期,国家还不存在。黑格尔将中华帝国视为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国家。在这个第二阶段,有两种社会结构支持中国式的国家,它们是官僚阶级和家庭。前面几段话描述了皇帝何以因官僚阶级的拥护而具有权威,此外,皇帝的统治也因中国家庭的伦理准则而得到巩固。
因得到儒家传统的强化,中国家族成为服从道德的榜样。家族关系根据5种义务来构建:君臣、父子、兄弟姐妹、夫妻、朋友。是否完全遵守这5种义务,是衡量道德行为的标准。
沿用这种家族模型,皇帝被看做是国家的父道监护者,所有国民都被看做是他的孩子。正如孩子要向父亲虔诚尽孝并服从父亲教诲,因此中华帝国的政治思想要求国民的行为服从皇帝,就如同听从家长的权威,这是天经地义的。(12)
从哲学角度审视历史,黑格尔将第二阶段即农业和国家阶段,视为缺乏人类主体性的阶段。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是理性考察及其自我外化的评价,它使理性研究自身的创造,认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分界线必然存在。为了使精神开启自己的旅程,矛盾首先是必要的,或者说边界、否定必然在主体和对象化之间存在。在中华帝国,自我和自然、自我和国家之间的矛盾,还没有成为现实。由于绝对服从家族的道德的需要,由于假定皇帝为大家族的统治者,中国国民被纳入国家,因此就没有主体以及表现他自己的外化之间的分歧。精神仍然以潜在的方式沉睡着。
国家在中国确实存在,而在印度并未存在。种族制度将国民拘禁在遗传的社会定位上,因此泯灭了所有个性印迹。印度宗教,主要指印度教和佛教,都呼吁信徒让渡主体身份以听从自然的神秘主义。印度尽管存在着政治,但从未有过国家。黑格尔这样区分中国和印度:
第二点,假如中国是一个道德的专制政体,在印度可以成为政治生活遗迹的,就是没有一个原则、没有什么道德和宗教规律的专制政体,因为道德和宗教都以“意志”的自由作为它们必要的条件和基础。(13)
在黑格尔关于社会形态的历史理论中,第二阶段见证了农业和国家的出现,却没有主体的出现。黑格尔撰写了《历史哲学》、《哲学史讲演录》、《法哲学原理》、《哲学科学百科全书》、《宗教哲学》和《美学》,这些著作都从不同角度论述绝对精神的精神之旅。由于主体在第二阶段仍被拘禁在自然中,国家尚未唤醒自我,如果没有“我”,精神则无法达及自我实现。“我”的诞生必须等到下一个阶段。
早期资本主义
第三阶段:市民社会和国家
正如财产权具有历史性,阶级具有历史性,因而社会和国家也具有历史性。作为引入我探讨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论述的手段,显而易见的是,黑格尔相信国家的历史性。他在《历史哲学》中写道:
因此,最初的决定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别。政治宪法在抽象方面颇正确地被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然而这种区分引发了某种说法,认为君主政体自身还应再分为专制政体和纯粹君主政体;认为在最重要的“观念”划分的一切区别中,只应重视一般的性质,这并不是说上面的特殊范畴应具备一个“形式”、“类”或“种”,在其具体的发展中再予以充分发挥。(14)
黑格尔在上述阐述中区分了国家的四种形式: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通过采用这种本质上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三段论模式,黑格尔表明,国家也具有历史性,国家在特定的时期具有特殊的功能。
为了说明这段引言,首先有必要从两方面进行分析:(1)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分离;(2)政治宪法和国家的分离。
(1)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分离
在黑格尔看来,社会是逾越家庭的人际交往。社会涉及主体间性,涉及超越家庭的个人之间的交流。即使在游牧阶段,社会也是存在的,因为为了维持部落的生存,人与人之间需要进行肉类与毛皮的原始交易。市民社会是17~18世纪的发明,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反映。市民社会这个术语是18世纪观念的产物。苏格兰启蒙运动基于这个假设:早期资本主义贸易创造了人类合作的条件。苏格兰学派认为,早期资本主义基于人们相互依赖和相互需要,他们相信,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公式。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是市民社会,因为相互需要使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市民彼此相互依存。苏格兰哲学家、《市民社会原理》一书作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从商品交换角度审视公民道德的社会基础。(15) 黑格尔读过斯图亚特的著作,并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市民社会的合作原则将长期存在。(16)《法哲学原理》的“市民社会”章依据苏格兰学派的解释,即早期资本主义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是新的公民道德的经济保障。
(2)政治宪法和国家的分离
宪法涉及政府管理制度。政治宪法这个术语提到行政、立法和政府的司法机构。社会为政治宪法提供了手段。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为政治宪法的构建提供了框架。阶级关系就是决定政治宪法框架的一种社会结构。
任何国家都必然有国家精神。国家是政治宪法和民族精神的结合体,或者说只有当精神的实质进入组织机构的时候,政治宪法才能成为国家。黑格尔指出古代印度作为非国家政治宪法的例子。古代印度从未达到国家的水平,因为它缺乏国家精神,或者说缺乏秉持反对自然立场的精神实质。
通过采用财产权、阶级、社会、政治宪法和国家这5个范畴,黑格尔先于马克思揭示出关于政治宪法、国家和社会的阶级理论。他在《历史哲学》中写道:
因为在一个现实的国家和一个现实的政府成立之前,必须先有阶级区别的产生,贫富两个阶级必然极为悬殊,一大部分的国民已不能再用他们以往通常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人生的需要。(17)
黑格尔提出了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和国家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由五部分组成:
1.财产权是阶级的基础;
2.社会由阶级构成。在这一点上,我在讨论社会的时候,曾经提到古希腊和古罗马。市民社会在这里被排除在外,因为它源于后来的社会进化,是17~18世纪早期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形态;
3.社会的差别因阶级矛盾而产生,试图消解这些社会矛盾,导致了法律的诞生。在黑格尔看来,法律是试图消除阶级冲突的产物;
4.出于制定法律的需要,创造社会和解的条件,是政治宪法的基础。通过建立行政和立法机关,政治宪法使国家成为现实;
5.国家是一种政治宪法,或者说政府与国家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在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农业革命和早期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国家的第一种形式在古希腊出现。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将雅典描述为“政治的艺术作品”(18)。他这样描述是因为古希腊精神进入了政治宪法,并将古希腊政治宪法变成了国家。
精神是从外部对其自身存在的思想考察。使精神在场的前提条件是个性的存在,必须将“我”从自然中区分出来。“我”或曰主体是精神的前提条件,因为主观精神在外部对象中将自身外化。当精神在外部形式中对象化时,精神有可能观察自身,以审视其对象化,而精神在外部审视自身的这个机会是精神自我认识的来源,而“我”是精神的自我认知。
黑格尔意识到,地理是精神进化的决定力量,自然环境促进了精神的产生,在黑格尔的信念中得到表达。希腊的地理环境促进了个性的发展。伯罗奔尼撒和阿提卡之间的许多半岛是不同的,山脉将希腊分为很多山谷,所有半岛和山谷是使希腊政治发展适应城邦—国家形式的自然条件。安纳托利亚的山脉和地中海沿岸的港口形成了不同的国家,而这种地理决定论被看做是精神个人主义的地理决定论。当城邦—国家的居民使政治个性成为他们自我意识的一部分时,精神就产生了,而政治宪法成为国家。
精神在这种形式中抵达的高度被认为在雅典的城邦—国家中得到了体现。黑格尔认为雅典实现了民主的最初形式(19),并把雅典城邦视为国家最完美的形式。人和公民在城邦内部是合一的,结合私人家庭利益、政治权力和义务的个人是现实的。这种政治模式使私人性和公共性的重叠这种卢梭的梦想以及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成为现实。
黑格尔对雅典城邦的崇拜没有使他忽视城邦—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他意识到,“农业、手工业和贸易(特别是海上贸易)等实业各部门”(20)引起了城邦内部阶级斗争的恶化。黑格尔意识到阶级冲突的经济基础,这在如下引言中可以看到:
根据地位和生活方式区别了三个党派,它们是:裴狄亚安人——平原居民、富庶的贵族阶级;得阿克力安人——山地居民、葡萄和橄榄种植者、牛羊的牧人,这个阶级的人数最多;处于这两派中间的士巴拉利安人——海滨居民——温和派。国家的情况在贵族整体和民主政体之间动荡着。(21)
黑格尔不仅写到了阶级战争,而且还写到了财产权的分配和基于财产权的政治权力的归属。黑格尔将雅典阶级战争的缓和归功于索伦(前6世纪雅典著名的立法者,他制定的雅典法律使雅典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译者注),索伦通过将财产权在四个阶级中再分配,缓解了财产权不平等的基本状况。无产者除外,四个阶级中其他的三个阶级都被授权成为参与立法并使法律获得通过的广受欢迎的成员。但是财产权仍然因那些在政府中持有权力的人们而继续产生不平等,因为索伦改革只允许生活优越的人或者说富有阶级成为国家官员。政府中的立法、司法和行政职务为富人所垄断。
黑格尔关于财产权和阶级战争的历史性的意识在对罗马的研究中得到了确认。古希腊人看到主体和自然是分离的,与之相比,罗马人对个性的开启为政治宪法提供了精神因素,罗马也由此发展为一个国家。黑格尔确实将国家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类型,他认为罗马和雅典的社会结构是不同的,他把雅典标记为民主制,而将罗马共和国标记为贵族制。国家的形式具有历史性规定。
在黑格尔的描述中,罗马共和国的分裂被看做是阶级战争所致。(22) 这是对右翼革命终将到来的叙述,这场革命推翻了模仿东方专制的皇帝统治的共和国。(23) 在对罗马史的叙述中,黑格尔描述了一次革命的降临,因为与一个不衰退的阶级对峙,专制的帝王统治的贵族共和国覆灭了。对罗马的分析表明,黑格尔意识到,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决定力量。
在共和国中,贵族和平民是彼此对立的阶级。提庇留·格拉古和歧兹·格拉古兄弟试图降低战争的因素,但是却失败了。当黑格尔提到这两个“高尚的”(24)兄弟时,表明他们具有改革家的才能。
在关于贵族和平民之间阶级斗争的分析中,黑格尔注意到格拉古兄弟希望恢复的土地法。利辛尼亚(Licinian)土地法试图通过确立更平等的土地所有权分配的法律,通过限定公民应该拥有的土地所有权的数量,减少阶级仇恨。实现这种平等需要贵族阶级交出他们所拥有的超出其所有权限定的土地所有权。利辛尼亚土地法的最初颁布失败了,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到的阶级斗争证明了他的认识:经济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力量。(25)
黑格尔以经济发展来规定历史进化,这种观点在他对利辛尼亚之后的提庇留·格拉古和歧兹·格拉古的论述中得到进一步证明。在推翻罗马共和国这次革命之前大约一个世纪,提庇留·格拉古重新提出了利辛尼亚土地法。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阶级仇恨使共和国社会彻底分裂,提庇留的意图是,通过限制阶级之间巨大的财富差距缓解阶级对抗。黑格尔将提庇留的目的描述为“为自由公民取得财产,使意大利居民都能成为公民,而不是奴隶”(26)。黑格尔将提庇留描绘为“这个高尚的罗马人”,还说明他为罗马的右翼压倒了。同样的命运等待着提庇留的弟弟歧兹。由于无法调节阶级冲突,罗马共和国很快就被皇帝的君主专制取代了。
黑格尔以法国大革命为视角概述罗马史。黑格尔经历过法国大革命,在革命爆发的时候,他19岁,当他23岁的时候,他还经历过雅各宾派统治时期。黑格尔的生活赋予他理解阶级战争和革命的经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是阶级斗争的潜在力量。由于认识到所有权、阶级和经济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黑格尔对希腊史和罗马史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先驱性(proto-Marxist)的解释。黑格尔通过回忆法国大革命来撰写罗马史。在比较罗马皇帝的降临和拿破仑帝国的降临时,黑格尔写道:
因为从古到今的所有时期内,假如一种政治革命再次发生的时候,人们就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了。因此拿破仑遭到了两次失败,波旁王室遭到了两次放逐。经过重演以后,起初看起来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便成为真实和正当的事情了。(27)
尽管希腊和罗马的命运不同,黑格尔还是将雅典和罗马视为客观精神的例子。客观精神这个术语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带来了自我的外化,思想进入一个对象,并且塑造这个对象。当现象以理性为根据,或者说当理性成为现实宪法的决定力量,精神的进化发展到客观精神的水平。客观精神乃是实现现实理性的精神发展阶段。
因为国家的产生离不开理性的构成性影响,所以希腊和罗马这两个国家体现了客观精神。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对客观精神的阐述,作为客观精神的产物之一,有成就的劳动者们使国家具有未来。
但是希腊和罗马的衰败已经是往事了,新的国家精神成为历史的动力。日耳曼民族将世界历史引入第三个阶段。
日耳曼民族是基督教的受益者。罗马世界的分裂与衰落伴随着基督教在西方的传播。尽管中世纪的千年王国在15世纪衰落了,但它见证了欧洲海外探险与全球商业征服的开始。因欧洲的兴起而受到鼓舞的日耳曼民族成为欧洲哲学的中心。
基督教神学支持的德国民族精神开拓了主体性领域。马丁·路德是德国民族精神的体现者,因为他使得对主体性的信仰成为进入神学的门径。康德和费希特时代的德国哲学将路德的主体性延伸到思辨领域,因为18世纪的德国哲学强调,主观的自我意识在人类认识活动中起到关键作用。
在黑格尔分析社会形态的方法中,最重要的理论工具是历史性概念。黑格尔探讨社会制度的主要手段是时间转换观念。阶级的历史性是社会的时间转换的推进剂。正如财产权性质的转变产生了阶级结构的变化,阶级突变也导致了社会变迁。
黑格尔使用的第二种方法论工具是有机体概念。在黑格尔看来,社会形态的塑造基于有机体的单元。他以此为解剖模型来理解社会制度。黑格尔用生物学范式来把握社会制度在时代变迁过程中的运转。
有机体图景不仅在黑格尔的毕生论述中很常见,歌德也是有机体隐喻的拥护者,但黑格尔以有机体图景的普遍体现来把握社会特质。在黑格尔哲学中,归纳概念起到了重要作用,归纳意味着有机的整体有权塑造、决定该系统的各部分。黑格尔的解释方法是系统的,系统中的每个部分都被纳入这个系统的总体之中。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性在于对稳定利润的内在驱动,因此资本主义有机体的每个成员都由利润最大化的内在驱动来决定。
社会的历史性造成了政府和国家的历史性。政府和国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对社会变化的反映,是由社会形态所决定的。对于政府和国家来说,有必要随社会的变化而改变它们的结构。
黑格尔的方法是关于社会有机体、政府、国家和文化形式的历史学。黑格尔将这些形式中的每一种都看做是有机体的单元,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致力于研究三种这样的有机体单元:东方世界、希腊和罗马以及日耳曼。形式、有机体单元等理念与世俗时间理念有关。黑格尔的方法建立在历史、社会、政府、国家和文化形式的基础上,与世俗时间相对立。
黑格尔运用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探讨市民社会问题。《法哲学原理》的“市民社会”章体现了他的方法。
市民社会是关于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式。市民社会验证了社会历史学的方法。与社会早期形式不同,市民社会是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交换的社会形式。生产者需要消费者购买自己的产品,消费者需要生产者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两种需要相互交换就成为相互承认得以确立的基础。
《法哲学原理》的“市民社会”章包括如下阐述:
三 财富(与阶级划分)
在劳动和满足需要的上述依赖性和相互关系中,主观的利己观念转化为有益于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以满足的东西,即通过普遍物而转化为特殊物的中介。这种辩证运动的结果是,每个人在为自己取得、生产和享受的同时,也正是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产和取得。在一切人的相互依赖全面交织中包含的必然性,现在对每个人来说,就是普遍而持久的财富。(28)
黑格尔关于社会和国家的历史学,他对社会有机体的认识,基于社会形式并反映之。他在《法哲学原理》中阐述的国家理论是关于君主制国家的,因为这符合早期资本主义的基础。黑格尔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君主制国家是与历史变化相称的国家形式。
作为普鲁士的公民,黑格尔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君主制国家既保存了封建的德意志帝国,又通过在两个议会中赋予新的资产阶级以政治代表权而承认他们。尽管黑格尔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他所说的早期资本主义的君主制国家赋予有产者以选举权,让有产者阶级获得讲演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并使政教分离。黑格尔的君主制国家是对中世纪和新兴的商业阶级的折中。《法哲学原理》表明黑格尔意识到,在历史上新兴的早期资本主义必然被容纳到封建王权中。
黑格尔将社会区分为市民社会和国家两种形式,这种贡献是他留给马克思的最重要的遗产。通过指导马克思区分市民社会和国家,黑格尔开启了马克思探索这两个革命性概念的理论视野,国家的消失以及资本主义并非历史发展的终点乃是事实,而过去的其他经济形式注定要灭绝。
基于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马克思第一次在他1843年的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到“国家的消亡”的概念。这将使本文的主题转入到对马克思的“国家的消亡”这个术语的丰富内涵的讨论中去,而应当充分肯定的是,当马克思提到“国家的消亡”的时候,他并非主张无政府主义。通过研究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分歧的框架,马克思提出以市民社会替代国家。在1844年的论文《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重复了他关于黑格尔那篇论文的主题,并论述了社会如何在内部涵盖自身,当社会为资本主义所染指,其结构将成为国家制度。他认为政治制度不可能从社会结构中创造出来,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因为它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历史性概念使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必然消亡。正如上文已经表明的,当黑格尔确立了社会的历史性的时候,他为马克思预见到资本主义的消失提供了依据。因为历史证明,所有的社会都是历史变迁的标本,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资本主义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
黑格尔是德国三月前期(Vormarz)的自由宪政主义者,但他表述了蕴含革命潜力的社会政治理论。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反对雅各宾主义,在题为“绝对自由与恐怖”这一章,他对恐怖统治加以谴责(29),而他的历史性概念、他对社会和国家的区分、他关于国家反映社会基础的理念,则成为革命方案之组成部分的所有要素。马克思接受了这些要素,并以它们作为革命实践的理由。
在柏林时期(1818~1831)的著作中,黑格尔的方法论得到了清晰的阐述。这些著作包括他自己完成的以及他1831年去世后,他的学生根据他的讲义整理的作品。这些大部头系统发表在他的《全集》第一版中,这是在1832~1841年间由他忠实的朋友们出版的,他们在“永恒之友”协会中组织起来。在这些著作中,最清楚地表达黑格尔方法论的是《哲学科学百科全书》,这本书1818年在柏林出版。柏林时期的《历史哲学》、《哲学史讲演录》、《法哲学原理》、《宗教哲学》和《美学讲演录》等著作连同《全书》,都是《全集》第一版收录的。
马克思早期著作表明,他读过所有这些大部头。马克思1836年的诗包含他对黑格尔《美学讲演录》的参考。(30) 在他1841年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参考文献中,列出了《哲学科学百科全书》、《法哲学原理》、《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史讲演录》。写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法哲学原理》的批评开始于该书第261节。(31)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是目前学术争论的焦点。现在已证明“费尔巴哈”章不是一个完整的文本,而是梁赞诺夫对该书第一版的构思,他整理了这些分散的草稿,使它们看起来像是内在连贯的章节。(32) 然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圣麦克斯”章才是真正的马克思文本。
围绕“费尔巴哈”章的大量争论展开探讨并不是本文的任务。目前这篇文章的内容只是有必要指出,在“圣麦克斯”章中,马克思确实引用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历史哲学》和《哲学史讲演录》。
黑格尔研究社会形态或有机体的方法论后来为马克思采用。显然,黑格尔和马克思存在着巨大差异,我在本文中将讨论其中某些差别。但我更为关注的是确立考察社会有机体的方法问题,黑格尔发明的分析工具为马克思提供了方法。这位《资本论》的作者采用了黑格尔的社会解释方法。应当说在方法论方面,黑格尔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先驱,而马克思则是通过阅读黑格尔的著作采纳了这种方法。
人类精神的三阶段论
在讨论国家精神的时候,我进入了绝对精神领域。客观精神关注理性的释放、理性的推动力量,而绝对精神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例证。通过对自身产物的精神考察,绝对精神为自身赋予了力量。通过了解什么产生了精神而了解什么是自在之物,绝对精神达到了精神自我教育(self-tutorial)的水平。黑格尔认为国家是客观精神的产物,他从三个方面来描述绝对精神的自我表现,这些自我表现是艺术、宗教和哲学。
为了理解黑格尔的国家精神理论,有必要将历史发展的三个连贯的脉络概念化,它们是地缘经济、政治和国家思路,这些历史发展的旅程分为三个阶段。地缘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层面,这条脉络经过了三个阶段:部落、农业和商业。农业是第二个层面,而这条革新的路径也经过了三个政治阶段:宗法政治、希腊—罗马的贵族制和民主制、现代的君主立宪制。最后,艺术、宗教和哲学也经过了三个阶段,而从精神到绝对精神的过程与从地缘经济到政治的过程是一致的。艺术、宗教和哲学自身也是经过这三个阶段的范例。如历史发展到狩猎阶段,产生了相应的政治形式——宗法制,狩猎阶段也带来了与生产方式相一致的宗教、艺术和哲学的存在样态。
黑格尔的社会解释方法论是基于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是一个有机体的单元的理论。每个有机的总体都由地缘经济、政治和国家精神三个部分组成。黑格尔对国家精神以及从主观精神到绝对精神的历史性的讨论,基本上是对一个社会形态的文化结构的分析。在构成黑格尔的历史百科全书的著作中,《历史哲学》、《哲学史讲演录》、《宗教哲学》和《美学讲演录》成为他研究国家文化或绝对精神形成的概要。最终从地缘经济这个前提出发,黑格尔认为社会文化对国家精神或集体意识的形成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对国家精神的讨论中,我将把探讨艺术、宗教和哲学的语境设定在历史发展的这三个阶段之内。我对国家精神的讨论采用如下形式:
1.部落社会:(1)艺术、(2)宗教、(3)哲学;2.农业社会(东方国家):(1)艺术、(2)宗教、(3)哲学;3.农业社会(希腊):(1)艺术、(2)宗教、(3)哲学;4.商业社会(日耳曼世界):(1)艺术、(2)宗教、(3)哲学。
1.部落社会
黑格尔认识到,社会总体的文化结构是对地缘经济基础的反映,这个形态是对他关于部落社会分析的证明。在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狩猎层面上,哲学还没有出现,因为精神还没有使自身从自然中解放出来。
(1)艺术
艺术形式确实产生了,黑格尔以狩猎阶段的象征艺术标记这个时期。(33) 黑格尔认为象征艺术是缺乏的,因为大家都接受了“自身的规定和分化”(34),因为主观的形式并不具有超越的属性。在象征艺术中,精神从来没有个性化,从来都不具有某种人格,二者是在部落阶段将精神限定在自然中的进一步证明。
(2)宗教
部落的存在确实发展了原始的宗教意识。作为历史进步的第一阶段,宗教意识乃是“自然宗教”(35),或者说宗教信仰处于自我完全被纳入自然的层面。宗教巫术的第一个形式是实践的,而这意味着对万能的原始精神本性来说,物质是普遍的,所以仅仅对自然来说,人类能够诉求他们环境的改善。在《宗教哲学》中,基于17~18世纪的欧洲游记叙事,黑格尔对黑人的巫师和蒙古人的萨满这类神秘祈求上天的专门人才给予了描述。(36)
(3)哲学
哲学在部落阶段是不存在的,因为自然完全遮蔽或曰消解了主体性。由于没有自我的出现,没有主体和群体之间的矛盾,哲学就不能产生。哲学是对精神在主体性中在场的研究,或者说是关于两个独立的实体——思想和外部世界——的意识,缺乏分离的知识,而且还只是将精神解释为客观的,哲学就不能够实现。
在部落阶段,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都不存在。独立的主体是主体性能够体现自身的先决条件。
2.农业社会(东方国家)
(1)艺术
在描述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农业时期形成的艺术形式时,黑格尔关注的是中国和印度。尽管中国和印度的艺术形式有很多差别,但它们都是象征美学的实例。虽然中国没有发展叙事史诗这样的艺术范畴,而印度发展了,黑格尔指出罗摩衍那(Ramayana)和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是印度史诗的例子。(37) 史诗的美学范畴是衡量精神发展的重要尺度,因为史诗叙述了个人英雄的英勇行为,叙述了他们令人难忘的功勋所体现的个性。不管印度美学是如何发展的,中国艺术和印度艺术都具有象征意义,因为他们的神和偶像是无形的,没有个体的确定的形状,因而永远不会表达现实的美或历史上伟人的宏图壮志。
(2)宗教
在宗教信仰方面,中国和印度都体现了神秘宗教的发展(38),或者说中国和印度都处于自然宗教状态。中国和印度都是泛神论统治的,而泛神论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中国的泛神论有三种形式:在帝国统治中失去自我;在道教的自然神秘主义中失去自我;在佛教的涅槃中失去自我。印度的泛神论本质上有两种形式:在印度教的泛神论中失去自我;在佛教的自我牺牲(self-renunciation)中失去自我。中国宗教和印度宗教的主要原则是形而上学的物质实在,而在形而上学形式的自然中,自我消失了。中国和印度的自我消失的意识是明确的,自我在泛神论中消失,而欧洲日耳曼的意识是自己区别于外部物质世界的精神意识,继而建立了他们的外部统治。(39)
(3)哲学
与部落时期相似,哲学也没有在中国和印度产生。在这两种文明中,思想在儒家的道德求索以及道教和佛教的泛神论中得到了表述。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写道:
这种主体性就是个人意志的自我反省和“实体”(就是消灭个人意志的权力)成为对峙;也就是明白认识那种权力与其主要存在为一体,并且知道它自身在权力中是自由的。……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无从发现主体性因素。(40)
此外,在黑格尔看来,因为自我沉浸在普遍的物质实体中,历史没有在中国和印度形成。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的目的是通过进入永恒的物质时间而逃避时间,因而没有必要考虑非凡事件的时光之路。主观精神和绝对精神都没有在中国和印度出现,因为国家精神的观念是被纳入自然的永恒物质之中的。
3.农业社会(希腊)
在希腊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都产生了。不仅精神被创造出来,而且绝对精神的实现成为可能。希腊的国家精神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转折点。
(1)艺术
黑格尔指出,希腊的艺术类型是从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发展起来的古典形式。
黑格尔对古希腊艺术的认识是博大精深的,我只能选择荷马史诗和悲剧这两个例子,旨在概述他对古典艺术的阐释。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是对阿基琉斯和奥德赛的英雄业绩的赞美。在特洛伊战争这个语境中,《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诗意地表现了阿基琉斯和奥德赛的个人努力,他们都处于希腊历史的早期阶段。阿基琉斯和奥德赛的主观力量都决定性地处于任何泛神论之外,他们对历史过程产生了影响。
黑格尔认为,在希腊时期,戏剧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是索福克勒斯创作的《安提戈涅》。《安提戈涅》讲述了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是道德双重性的受害者,是忠实于国家还是忠实于家庭,这个选择将她撕碎了。《安提戈涅》在道德上的痛苦抉择表现了主体的内在矛盾。《安提戈涅》的结论表明,道德依靠主体性而不依靠形而上学的物质规定。
《安提戈涅》告诉人们,道德是由个人选择创造的,而不是遵循泛神论的结果。
(2)宗教
黑格尔指出,希腊信仰的是美的宗教。希腊宗教形成了希腊雕塑的象征意义,或者说菲迪亚斯(41) 的大理石雕像不仅对神而且对美化的人体都表达了敬意。希腊诸神都是拟人化的,他们在雕塑中表现的是两个世界的关系,神圣的世界根据人体来描绘,而人体因此是荣耀的。
在黑格尔看来,美是理念在感性形式中的实现。在造型艺术中,美意味着在感性中获得了理念。(42) 如果人体美表现为神的塑像,如果人体美成为神圣的标准,那么人体美在自身中得到了神化。对于摹绘而言,人类的形体美意味着人的偶像化。在《宗教哲学》中,黑格尔写道:“人性实现了自身的权利,得到了自身的确认,人的存在被具体地作为神来描绘。希腊的神如果是没有内容的,就不会为人类所熟知。”(43)
神的力量使人类具有英雄主义的素质,这种认识与使人类具有崇高的地位是等同的。太阳神阿波罗使人类的理性能力达到最高水平,这种信念也是导致人类理性偶像化的标尺。对人类能力的神化引发了对人类主体性的赞颂。如果人类在自身的范围内承载神的潜力,那么这将导致人类精神发扬光大。
(3)哲学
希腊也是哲学的诞生地,黑格尔认为希腊哲学是精神的领域。
黑格尔改变了对哲学的传统解释。从传统上看,哲学科学被解释为致力于发现精神与外部对象的一致性的尝试。黑格尔则将哲学规定为精神的自我认识。精神在哲学中通过考察自己过去的产物而培养自身的权力。
对精神而言,实现这种自我启示的两个前提条件是必要的。首先,精神必须从自身的产物中分离出来。为了观察某个对象,有必要站在这个对象的反面。其次,应当列出精神的产物,或者说对精神的以往产物的展示必须得到合理的体现,因此精神可以考察自己的生活历程。
希腊人使哲学的所有前提条件都成为现实。希腊人最先使精神几乎完全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他们是最早通过使主体成为现实而实现了观察能力的人。主体是自我意识,即反对外部世界的“我”,因此矛盾获得了审视外部世界的能力。自我意识的产生,是“我”及其对立面的矛盾的产生,也是主观精神的产生。
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出现使哲学成为可能。观察精神的产物,使精神有可能看到自己的履历。客观精神将精神对象化,而这种对象化是精神的个人简历。
以此为基础产生了绝对精神。哲学或者说精神的自我认识是绝对精神的一个方面。在对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创造中,希腊人确立了哲学的基础,而哲学也是希腊人对待历史问题的另一种理论革命。
《历史哲学》1~2卷致力于详述希腊哲学。在本篇文章中描述黑格尔对希腊哲学的充分论述是不可能的,我将确定三个重要的方面说明希腊对黑格尔哲学的重要影响。黑格尔的很多重要概念——确立了使其哲学成为可能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希腊。
在后苏格拉底时期,柏拉图发现了理念的作用。然而,柏拉图将理念置于先验的领域,而黑格尔将理念置于自我意识中。黑格尔采用了柏拉图的理念概念,将其从形而上学的栖居地移入主观的自我意识中。(44)
在后苏格拉底时期,亚里士多德发现了精神的目的论以及从潜在到现实的内在运动。亚里士多德第一次证明,思想的本来特征是从潜在的概念到自我实现的现实这一内在趋势。(45) 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主题是黑格尔哲学的关键因素,主观精神具有使客观精神对象化的内在趋势,黑格尔的这个理念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思考,即现实只是对潜在事物的实现。潜在的实质是趋向于现实。
前苏格拉底思想是黑格尔主义思想的某些主要原则的温床。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是其方法论的始祖。巴门尼德对黑格尔解释有机体的历史学作出两个贡献。它们是:思想与现实是等同的;否定是思想固有的功能。对巴门尼德来说,思想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思想的内在模式之一在于,思想与其自身的权力相矛盾。在这个方面,巴门尼德预见到斯宾诺莎所言——否定就是决定,黑格尔借用了斯宾诺莎和巴门尼德的相关思想。(46)
赫拉克利特为黑格尔引入了历史性概念,或永久生成的概念。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如果所有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化,那么生成就是宇宙的基本法则。黑格尔接受了来自于赫拉克利特的这个概念,在黑格尔的思想中,现实的静止的事物总是被生成的事物所否定,这种解释模式是黑格尔历史性的逻辑基础。(47)
4.商业社会(日耳曼世界)
黑格尔将日耳曼的历史分为三阶段:(1)公元5世纪日耳曼的入侵与罗马帝国的衰落;(2)中世纪和天主教会神权统治的确立;(3)路德对精神主体性的重新发现与改革。不顾这三个时期的差别,黑格尔对德国历史的分类表明,历史的进程体现了“精神自由的原则”。(48) 德意志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表明,自我决定这个理念乃是自由的实质。
德国在“精神自由的原则”的实现过程中受益,因为它是基督教崛起的推动者。在罗马帝国衰落期间,德国信仰基督教成为历史事实,当日耳曼的征服蔓延整个欧洲,他们成功普及了基督教。
(1)艺术
日耳曼世界的艺术类型是浪漫主义。当黑格尔认为浪漫主义艺术代表德国美学的时候,他没有提到千年的封建时代,而提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提到列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
浪漫主义艺术的主要特点是深刻的反思。浪漫主义艺术开始于意大利的城邦—国家,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将绝对的内在灵性理想化以庆祝独立和自由。古典艺术没有表达主体的内在心理状态,主体探索其内在的“我”,浪漫主义艺术在自我探索的过程中描绘英雄。(49)
古典艺术和浪漫主义艺术描绘死亡的方式不同。比如说希腊人没有认真对待不朽的问题,因为他们高度看重自然、社会和政治的现实。尽管希腊人开始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提升了主观精神,但他们仍然十分重视现实的直接性。相反,浪漫主义艺术受到信仰来世的基督教的启发,将死亡描绘为神和个人在一起的时刻。作为基督复活时刻的延续,浪漫主义艺术为死亡提供了新的意义,认为死去的个人是对自然的否定,是实现了主观精神和永恒生命复活的统一。(50)
(2)宗教
黑格尔将基督教标示为完善的宗教。(51)
基督教完善了宗教的进化,因为其原则是神和人的统一。基督是上帝和人的综合,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升天象征着人的灵魂与神融为一体。基督在宗教领域中体现了主观精神。
然而,这个完善的宗教也遭遇衰退,中世纪的千年时期见证了基督的宗教主体性的降低。天主教会摧毁了基督教的主观因素,使其走向反面,或者说篡改了对主观精神的信仰。基督教认为个人意识属于信仰的位置,而天主教将信仰移入专制体制。天主教建立在神职人员掠夺的基础上,将对个人意识的信仰替换为宗教专制。
路德体现了德意志精神,他扭转了这种歪曲。宗教改革使信仰返回个人意识。路德主义是一种恢复,或者说取回了基督的宗教主体性。宗教改革是一场宗教革命,推翻了对个人意识的颠覆,恢复了基督教的讯息:拯救是关于个人意识的事情,或者说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的统一诉诸自我意识。(52)
路德改革将宗教蔓延到哲学领域。路德的主观自由思想进入了德国哲学,因为德国哲学采用了路德的信仰自由原则,并将其重新规定为理性的自我意识的自由。德国哲学的显著特点表现为这个原则:主体的自我意识是宇宙的推动力量。
(3)哲学
唯心主义是德国的国家哲学。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确定现代哲学诞生于弗兰西斯·培根,或者说诞生于16世纪。(53) 作为经验主义者,培根是启蒙的创始人之一,唯心主义是德国哲学赋予启蒙的形式。
德国唯心主义延续了路德的传统,因为德国唯心主义从主观自由的领域开始思考。路德允许个人意识找到永恒的路径,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宣称,个人和宇宙是统一的。
延续路德的传统,康德将自己从英国经验主义中分离出来,他关注的重点是用于解释外部世界的精神范畴。康德是德国唯心主义的主要来源,他开始研究思想的内部结构,但他仍然将自己限定在理论层面。尽管康德开始研究理性的内部形式,但他没有拓展自己对实践哲学的分析,或者说没有研究精神在现实中何以是现象学的力量。康德关注的是理性的超越方式。(54)
费希特延续康德的传统,但他强调思想的对象化力量。费希特从“我”开始,重点在于解释“我”何以构成了外部世界,或者说费希特在实践哲学领域内部展开研究。费希特是将理念视为现象学力量或曰将自我植入外部世界力量的第一人。客体变成理性的,因为理性被置于其中。(55)
黑格尔延续了康德—费希特的发展线索。他接受了康德的思想,认为理性自身具有内在的运作模式,他通过将理性解释为在现象中将自身对象化的表现力,而使费希特思想注入康德思想中。黑格尔是现象学的发明者,他将理性置于外部对象之中,因而渲染了外在理性。(56)
通过审视主体在客体中的反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建立在主客体统一原则的基础上。这是一种实践哲学的形式,因为它主要关注精神活动,或者说主要关注理念在现实中的实际作用。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有一个客观因素。在黑格尔看来,精神不仅被规定为自我意识,而且与国家问题有关,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进入了客观精神领域。因为在这部完成于1820年的作品中,他赞美君主立宪制是后法国大革命时期最适当的政治形式。作为雅各宾恐怖统治的反对者而非政治改革者,黑格尔使君主立宪制成为个人自由和稳定联合的政治形式。(57)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也进入了绝对精神领域。黑格尔在他生平很多著作的精神之旅中提到了绝对精神。他成熟时期的著作和讲演是精神创造的代表作,黑格尔的描述揭示了精神的内部特征,是其迈向日益自由的视域的令人信服的依据。
黑格尔对历史三阶段论——每个阶段都具有地缘经济、宗教和哲学的分支——的探讨,表明黑格尔将社会有机体视为等级制度。每个社会有机体都依靠经济基础,因此有机体的发展将达到宗教和哲学水平。每个社会形态都由阶梯式上升的等级制度组成,开始于地缘经济,继而上升到哲学层面。
黑格尔的社会解释方法从基础条件——比如地缘经济开始。然后上升为第三个层面集体意识。尽管集体意识、国民心态是可以还原为基础条件的复制品,但它仍然具有自主性,对基础条件具有一定的影响。
结论
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社会科学的解释方法,马克思采用了黑格尔方法论的主要范畴。为了澄清我对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形态的解释方法的规定,对我来说有必要将我的论述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区别开来。
辩证唯物主义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发明(58),在20世纪它变成了苏联的官方标准。斯大林在独裁统治期间阐释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贬低。恩格斯塑造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基于本体论假设,以否定之否定、矛盾、质量互变这三个法则把握自然和历史,由于将历史视为对自然的反映,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的形而上学。
历史唯物主义的谬误来自于历史发展的线性观点。由于声称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之间不断的辩证冲突使历史沿直线抵达未来,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历史预言的形式。它是历史决定论观点的牺牲品,认为必然性推动历史前进。在这个方面,我也避免使用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的术语,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些术语指出经济基础和思想领域之间的因果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术语认为思想是复制的,是经济基础的镜像,我反对这种主张。思想领域受地缘经济影响,但它也是一个自由王国,或者说理性是自我决定的活动。
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方法论,或者说黑格尔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黑格尔用来解释社会形态运转的最重要的方法为马克思所借用。说黑格尔是马克思主义先驱,并不意味着黑格尔是共产主义者,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谴责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59),但这确实意味着黑格尔创作了解释社会制度运转的绪论,这个绪论不仅早于马克思,而且为马克思所采用。
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由非连续性和连续性组成。在非连续性方面,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思辨哲学,或者说扬弃了精神是现实的塑造者这个信念。对黑格尔来说,精神使理性现实化,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驳斥了黑格尔唯心主义。
然而,在连续性方面,马克思延续了黑格尔解释方法的主要成分。
马克思否定了黑格尔思辨哲学,同时接受了黑格尔的方法论,我认为并不矛盾。这是一个内容和形式的问题。马克思取消了黑格尔的内容,比如理念,却接受了黑格尔的形式,比如普遍性和特殊性。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理论的处理方法同上。在黑格尔看来,劳动基于精神的生产能力。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劳动概念这种形式,但为其替换了新内容。1844年的马克思仍将劳动概括为精神的产物,但他为其增添了新内容,而这个新内容是社会生产劳动。
黑格尔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因为马克思使用了黑格尔理解社会形态发展的分析工具。在《精神现象学》的著名“序言”、《哲学史讲演录》的“序言”以及《历史哲学》的“序言”中,除了其他思想之外,黑格尔将历史性的统治描述为社会形式。每个社会的本质以及理解所有社会的主要概念是历史主义。
此外,在上述提到的著作中,黑格尔将社会总体描绘为有机的单元。埃及、中国和印度、波斯、希腊和罗马以及日耳曼欧洲等部落的存在被描述为完整的系统。每个社会总体都普遍地内在分化出自身的特殊性。剖析是遍及黑格尔解释方法的核心图景。
马克思读过上面提到的所有“序言”,此外,马克思熟知收入《黑格尔全集》第一版中的所有材料。马克思没有详尽阅读诸如直到20世纪才出版的黑格尔的全部书目。然而,正如本文所提到的,马克思确实了解黑格尔的全部著作,而这些著作足以使马克思学会黑格尔解释方法的实质。基于对黑格尔的阅读,马克思转向黑格尔的社会分析公式。黑格尔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因为他是马克思的社会解释方法的来源。
黑格尔和马克思采用这个公式的结果不同。在这个方面,政治动机是决定性的。黑格尔用他的范式支持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而马克思用这种判断来解释资本主义剥削产生的社会形式。政治目的使黑格尔和马克思采用的最初的黑格尔主义诊断工具分化了,黑格尔鼓吹自由的君主制,而马克思用黑格尔的范式为无产阶级革命辩护。马克思主义先驱存在于马克思之前,马克思的成就在于,借鉴马克思主义先驱的方法并使之成为手中掌握的武器。(60)
总之,本文将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解释方法分为三个范畴:(1)历史主义;(2)有机体主义;(3)基础结构和集体意识。
(1)历史性是马克思借用马克思主义先驱解释社会的重要原则。历史研究表明,所有的社会都发生了变化,这个事实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提供了希望。
(2)借用马克思主义先驱的还有将社会概念化为有机的单元。每个社会都是根据剖析结构的模型建构的。统治的性质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普遍性。在有机的整体中,特殊的机构具有特殊的功能,但这些特殊性反映了普遍性。
(3)基础结构和集体意识。黑格尔教会马克思看到社会形态以地缘经济形态为前提,而这些社会条件影响了其后社会有机体的等级水平。黑格尔使马克思看到,基础条件对集体意识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黑格尔将集体意识、国家精神分为地缘经济、政治和艺术—宗教以及哲学三个阶段。对社会有机体的理解经由这三个层次而上升。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采用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解释模式。历时性是线性的、水平的或曰以时间为顺序的,而共时性是垂直的。对马克思来说,每个社会有机的单元都是共时性结构,或者说基础条件影响了集体意识、国家精神或文化心态的内部垂直结构。这并不意味着集体意识只是基础条件的复制品,只是由基础条件派生的,只是基始要素的“意识形态”。这意味着集体意识、国家精神或文化心态受到这些基始要素的影响,客观设定主观的标准,但是集体意识同样享有充分的自由,即自主性决定自我。
如同黑格尔,马克思相信,每个社会发展都可以被分为基础条件、政治结构和集体意识三个阶段。
马克思采用马克思主义先驱在19世纪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原理,黑格尔的分析方法使他得出两个结论:资本主义是历史的产物并将溶解在历史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的评价只能通过将社会形态视为一个有机体来实现,其中恒久的稳定性实际上决定了系统内部的各种定位。
注释:
① Hegel,G.W.F.,The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trans.A.V.Miller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1),Vol.III,p.27.
② Hegel,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trans.J.Sibree (Prome-theus Books:Buffalo,1991),p.101.
③ Waszek,Norbert,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d Hegel's Account of Civil Society (Kluwer Publishers ; The Hague,1988).
④ Vileisis,Danga,Der unbekannte Beitrag Adam Fergusons zum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ehtsverstandnis yon Karl Marx, Beitrage Zur Marx-Engels Forschung (Berlin:Argument-Verlag,2009),pp.7~60.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159页。
⑥ Levine Norman,“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of Law and the Origi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July-Sept.1987),pp.431~451.还可以参见我的文章,“The Myth of the Asiatic Restoration”,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ume XXXVII,No.I; Nov.1977,pp.73~85.
⑦(16)(28) Hegel,The Philosophy of Right,trans.T.M.Knox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2),pp.110-116.126-134.129~130.
⑧⑨⑩(11)(12)(13)(14)(17)(18)(19)(20)(21)(22)(23)(24)(25)(26)(27)Hegel,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p.88.183.177.86.121~123.161.44.85~86.250.252.258.258~259.285~313.315.310.302.309.313.
(15) Steuart,James,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Civil Society,Trans.Andrew S. Skin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2 Volumes.
(29) Hegel,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trans.A.V.Mill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355~364.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5~736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32) Taubert,Inge,“Manuscript und Druck der‘Deutsche Ideologie’:Problem und Ereignisse”,MEGA-STUDIEN,Berlin:Dietz Verlag,1997/2,pp.20~55.
(33)(34)(49)(50) Hegel,Lectures on Aesthetics,trans.T.M.Knox,Oxford:Clrendon Press,1979,Vol.1,p.313,p.429,pp.520~521,pp.522~523.
(35)(38)(39)(43)(51) Hegel,Philosophy of Religion,trans.Peter C.Hodgs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219,p.235,pp.235~260,pp.330~331,pp.109~110.
(36) Hegel,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trans.J.Burdon Danderson,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23,Vol.1,pp.230~235.
(37)(42) Hegel,Lectures on Aesthetics,Ibid,Vol. II,p.1045,p.1045.
(40)(46) Hegel,History of Philosophy,Vol.I,p.120,pp.252~253.
(41) 古希腊著名艺术雕刻家,为重建雅典做出卓越贡献,代表作《命运三女神》、《宙斯》等。——译者注
(44)(45)(47) Hegel,History of Philosophy,Vol.II,pp.1~49,pp.180~202,pp.282~293.
(48)(52) Hegel,Philosophy of History,pp.341~346,pp.412~424.
(53)(54)(55) Hegel,History of Philosophy,Vol.III,p.170,pp.423~479,pp.479~481.
(56)(57)(59) Hegel,The Philosophy of Right,p.10,pp.14~15,p.44.
(58) Levine Norman The Tragic Deception,Santa Barbara: Clio Books,1975.
(60) Levine Norman Divergent Paths,Lanham: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6.在写于《不同的路径》之前的文章中,我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采用连续性的解释。关于这些早期文章,参见Levine,“Hegel and the 1861-1863 Manuscripts of Das Kapital”,Rethinking Marxism(Vol.14,NO.4,2002),pp.47~58;也可以参见Levine,“Marx's First Appropriation of Hegel”,Critique (36~37 ; 2005),pp.125~156 ; Levine,“Corruption and Fate of Left-Wing Hegelianism” ,Critique,(Vol.35,No.1,2007),pp.79~102 ; Levine,“Hegelian Continuities in Marx,”Critique (Vol.37,No.3,2009),pp.345~370.
标签:市民社会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贵族等级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法哲学原理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哲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社会论文; 地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