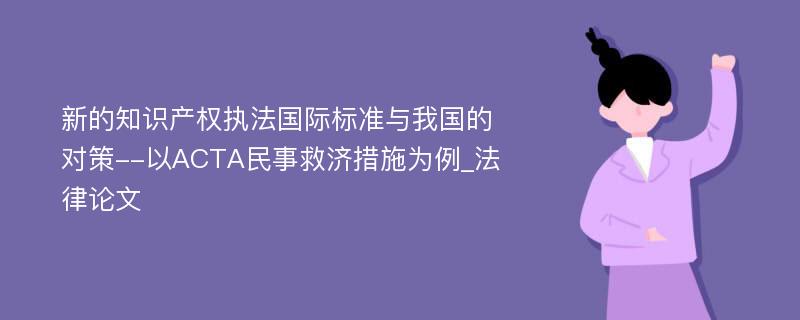
知识产权执法的国际新标准以及我国的应对——以ACTA民事救济措施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新标准论文,民事论文,知识产权论文,措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经日本在2005年G8高峰会议上倡议,2006—2007年,美国、日本、欧盟、加拿大、瑞士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始了《反假冒贸易协议》(以下简称ACTA)的初步谈判。2008年6月起,澳大利亚、墨西哥、摩洛哥、新西兰、韩国、新加坡加入了正式谈判。2010年10月东京谈判后形成了最后文本。①2011年10月1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签署仪式,上述谈判国中,欧盟、瑞士、墨西哥暂时还没有签署,但该协议开放签署至2013年5月1日。②
ACTA的目的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打击盗版和假冒行为,建立知识产权执法的黄金标准,提高知识产权侵权的救济水平,以超越TRIPs规定的现行国际水准。入世后,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已经符合TRIPs协议的要求。中国没有参与ACTA的谈判,也没有加入ACTA的国际义务,但是由于ACTA在很大程度上矛头直指中国——美国所宣称的知识产权侵权产品的主要来源国,中国必然面临发达国家要求接受ACTA规则的压力。因此,有必要仔细分析TRIPs协议以及中国现行知识产权法与ACTA之间的差异,知己知彼,以便合理应对。
ACTA的最终文本(2010年12月3日)共六章。其中第二章“知识产权执法的法律框架”是该协议的核心内容。从总体框架上看,ACTA第二章规定的知识产权执法与TRIPs第三部分规定的知识产权执法大同小异,包括了民事执法(含临时措施)、边境措施、刑事执法等内容,增加了“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执法”的内容。本文试分析ACTA有关民事执法(包括临时措施)部分的内容,比较其与TRIPs协议以及中国知识产权法之间的异同,并提出有关应对建议。
二、民事执法的标准:从TRIPs到ACTA
(一)禁令(停止侵权)的适用
如果一方当事人被司法机关认定为侵犯知识产权,则应该承担停止侵权的法律责任。这是知识产权侵权救济的必要措施。
TRIPs协议第44条就“禁令”规定:“1.同法机关有权责令当事人停止侵权,特别是有权在海关放行后立即阻止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进口货物进入其管辖范围内的商业渠道。如在某人知道或应该知道经营(dealing)该商品会构成知识产权侵权之前取得或订购该商品的,则各缔约方无义务给予司法机关此种权力。
2.尽管有本部分其他条款的规定,但是只要符合第二部分就未经权利持有人许可的政府(自己)使用或政府授权第三方使用而作出的规定,各缔约方针对这些使用所提供的救济可限于依照第31条(h)项规定的支付报酬。在其他情况下,应适用本部分所规定的救济,或如果禁令的救济与缔约方的法律不一致,则应作出确认侵权的判决并给予适当的补偿。”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1)TRIPs协议强调“停止侵权”的措施可以适用于“在海关放行后立即阻止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进口货物进入商业渠道”。这是因为停止侵权是针对不同的侵权行为所采取的措施,例如,要求侵权产品的生产商停止制造侵权产品;要求侵权商品的销售商停止销售侵权商品等。虽然各国法律一般都规定有禁止侵权产品进口的海关边境措施,但是,在海关没有能及时发现侵权产品入关而予以放行,而该侵权产品又尚未在国内市场销售的情况下(比如,侵权产品存放在某个物流企业的仓库中),司法机关就没有法律依据去及时制止这种侵权产品进入商业渠道了。TRIPs协议要求“在海关放行后立即阻止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进口货物进入商业渠道”,目的是将停止侵权的措施可以在这种特定情形下适用于不构成侵权的第三方。
(2)TRIPs协议允许对善意取得或订购侵权商品的经营者③不采取停止侵权的措施,而可以用其他救济措施替代,比如,支付适当的使用费。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对于善意取得的侵权产品的使用人,就可以不采取停止使用的措施;甚至对于善意订购了侵权商品而进行销售的进口商、销售商,如果采取停止销售的措施会导致过大的损失,也不一定必须采取停止销售的措施。在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中,法律也允许盗版软件的使用者在支付合理使用费的情况下,继续使用该软件。至于一般的盗版物的使用者或者假冒商品的使用者,因为本身就不属于侵权行为,更谈不上对其适用停止侵权的法律措施。
与TRIPs协议相比,ACTA删除了对善意取得或订购侵权商品的侵权人不采取禁令的例外,并将禁令措施“在适当情况下”扩大适用于“司法管辖权范围内的第三方”,而不仅仅适用于构成侵权的当事人。
ACTA第8条关于“禁令”的第1款规定:“在关于知识产权执法的民事程序中,各缔约方应当规定其司法机关有权责令当事人停止侵权,甚至可以责令当事人或者在适当的情况下责令其管辖权范围内的第三方阻止侵权货物进入商业渠道。”
这个规定的关键之处在于司法机关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责令其管辖权范围内的第三方阻止侵权货物进入商业渠道”。与TRIPs规定只是“隐含”在特定情形(限于已经清关的进口货物)下可以对侵权者以外的第三方采取法律措施以阻止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进口货物进入商业渠道不同,ACTA已经将“阻止侵权货物进入商业渠道”的措施泛泛适用于任何“适当情形”下的“第三方”。ACTA对这里的“适当情形”虽然没有作出清晰的规定,但显然已经不仅仅限于进口货物的情形;而可以阻止侵权货物进入商业渠道的“第三方”则可能包括侵权产品的仓储、运输方,以及侵权产品的使用者,特别是专利以外的其他知识产权的侵权产品的使用者(因为侵权专利产品的使用者本身就可以构成直接侵权而不是第三方了)。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如何解释“阻止侵权产品进入商业渠道”?是不是消费者购买侵权产品使用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进入商业渠道的行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假冒或者盗版商品的使用者,都有可能被采取禁令的法律措施,这就会将知识产权产权的保护彻底地延伸到侵权产品的最终用户头上。
中国知识产权法中,并没有规定对不构成侵权的第三方可以采取禁令的法律措施。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行知识产权法与ACTA的规定存在一定的距离。虽然我国现行《商标法实施条例》第50条规定,故意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仓储、运输、邮寄、隐匿等便利条件的行为,属于商标法第52条第5项所称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似乎可以直接对侵权商品的仓储、运输、邮寄、隐匿等人采取法律措施。但是,这仅仅限于“故意”、“明知”的情形,而对于那些善意的第三人(仓储、运输、邮寄等人)就不一定可以采取禁令措施了。因此,并不能从中得出我国知识产权法中已经规定可以对非侵权的善意第三方采取禁令措施的结论。
有学者认为:“对于中国知识产权法,将禁令救济延伸到第三方,并不是新鲜的事情。”其理由是:(1)在间接侵权的情形,如果第三方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或者侵权危险,发放禁令救济(责令停止侵害),顺理成章;(2)善意的销售者虽然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应该停止侵害(禁令救济)。④笔者认为,这是把中国法对间接侵权者的禁令救济看作是对不构成侵权的第三方的禁令救济。对于间接侵权者可以采取禁令措施,这确实不是新鲜的事情;ACTA却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要进一步对没有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方(包括善意的第三方)在“适当情况下”也要采取禁令措施,这显然在中国现行知识产权法中是找不到法律依据的。
至于ACTA删除了对善意取得或订购侵权商品的侵权人不采取禁令的例外,与中国现行知识产权法倒不会有多少冲突。因为中国知识产权法本身就没有规定善意侵权者可以不承担停止侵权的责任。相反,即便是善意侵权(如善意销售商)虽然可以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仍需要承担停止侵权的责任。⑤唯一可能有影响的是,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30条的规定,软件的复制品持有人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该软件是侵权复制品的,如果停止使用并销毁该侵权复制品将给复制品使用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复制品使用人可以在向软件著作权人支付合理费用后继续使用。那么,根据ACTA,盗版软件的善意用户是否仍然可以主张继续使用呢?与TRIPs协议第44条第2款的规定一样,ACTA第8条第2款规定,如果这些救济方式(指禁令)与缔约方的法律产生冲突时,应当可以获得确认(侵权)的判决并得到适当的补偿。也就是说,即便确认使用盗版软件行为是侵权行为,也可以通过适当补偿来获得继续使用,而不一定停止使用。因此,《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30条的规定也并不见得与ACTA会有大的冲突。
(二)损害赔偿的计算
损害赔偿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最重要的救济措施。TRIPs第45条对有过错的侵权行为规定了“弥补损失”的赔偿方式,而对无过错的侵权行为规定了“返还利润”和/或“法定赔偿”的赔偿方式:(1)对于知道或有充分理由应知自己实施侵权行为的侵权人,司法机关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足以补偿其因知识产权侵权所受损害的赔偿。(2)司法机关还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有关费用,其中可包括有关的律师费用。在适当的情况下,各缔约方可授权司法机关责令其返还利润和/或支付法定的赔偿,即使侵权人不知道或没有充分理由知道自己从事侵权活动。
TRIPs协议对于损害赔偿坚持过错责任的原则,只是在适当情况下,采用无过错责任的原则。TRIPs对于过错侵权和无过错侵权分别以“损失填平”和“获利返还”为标准来赔偿,这是因为合法的知识产权产品的销售价格一般来说总是要高于盗版假冒产品的销售价格,权利人的损失金额往往要大于侵权人的获利金额,如果仅仅“返还获利”,就可以使善意侵权人承担相对较轻的损害赔偿责任。当然,为了弥补权利人的损失,也不排除在返还获利的基础上再加上一定的法定赔偿,或者司法机关索性直接确定一个法定赔偿的金额。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的规定,如果出版者尽了合理注意义务,著作权人也无证据证明出版者应当知道其出版涉及侵权的,出版者仅仅承担停止侵权、“返还其侵权所得利润”的民事责任。这与TRIPs协议规定的“无过错责任”的精神是一致的。
ACTA并没有改变TRIPs协议规定的侵权损害赔偿的过错责任原则,也同样是以“足以补偿因侵权所受损害”作为赔偿的标准。但是ACTA第9条第1款进一步明确“在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赔偿数额时,缔约方的司法当局应有权考虑权利人提出的任何合法的价值估算,包括利润损失、根据市场价格或建议零售价所估算出的侵权商品或服务的价值”。按照权利人的利润损失来计算损害赔偿是符合常理的,而根据侵权产品的市场价格(不排除侵权产品的成本)所计算出来的金额则完全有可能超出权利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的金额,而不仅仅是“填平损失”了。因此,这将可能增加侵权人的损害赔偿金额。
ACTA第9条第2款也规定了根据“侵权获利”来赔付权利人的损害赔偿方法,但是,与TRIPs不同的是,这种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侵犯版权与邻接权和假冒商标的案件中”,而不仅仅是“在适当的情况下”适用,并且明确“缔约方可以推定侵权获得的利润为第1款中损害赔偿金的数额”。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权利人的损失会大于侵权人的获利,但是,也不排除在有些时候权利人的合法产品还没有投入市场销售或者投入不多,而侵权人的经营能力和营业规模却大于权利人,因而导致侵权人的获利可能会大于权利人的损失。这时,如果在“侵犯版权与邻接权和假冒商标案件”中可以一般地按照侵权获利来确定损害赔偿额的话,该损害赔偿额可能会在事实上高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中,虽然也规定了根据侵权获利来计算损害赔偿的制度,但其适用的条件在不同的法律中有所差异。如《商标法》第56条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而《著作权法》第49条则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这就是说,对于假冒商标案件,我国《商标法》的规定与ACTA的规定并无差异,即可以任意选择依据“侵权获利”来计算损害赔偿,⑦而在侵犯著作权以及邻接权的案件中,依据“侵权获利”来计算损害赔偿的前提是“实际损失难以计算”,而不是可以任意依据“侵权获利”来计算。不过,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对权利人举证证明自己的利润损失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如果权利人认为依据“侵权获利”来计算损害赔偿更为有利的时候,往往会以“损失难以计算”为由实现依据“侵权获利”来计算侵权损害赔偿的目的。因此,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著作权人希望依据“侵权获利”来计算损害赔偿,一般来说并没有太大的障碍。真正有障碍的是这样一种情形:由于中国政府普遍对作品的出版、传播实行审查制度,未经审查而出版、传播各种作品、作品的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将会违反有关出版、传播管理的行政法规。这样的话,如果一部作品在尚未取得中国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出版、放映、传播等许可证书的时候,就已经有盗版的行为发生了,而著作权人或者邻接权就这种侵权行为去主张司法救济,这时,司法机关是否可以依据侵权人的“侵权获利”来给予权利人损害赔偿呢?还是说,因为这个作品尚未在中国取得合法出版的许可,因而“没有实际损失”(不是“无法计算损失”),就不应该给予损害赔偿?如果依据ACTA的规定,只要是对享有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的盗版行为,不管其是否已经合法出版、传播,权利人均可以依据侵权获利来获得赔付,那么,损害赔偿就可以实现;而依据中国《著作权法》以及有关行政管理法规的规定,对于尚未合法出版作品的盗版能否给予权利人损害赔偿,就是个很大的疑问了。可以想象:一旦我国接受ACTA的这个规则,而又不打算对那些尚未在中国出版传播的作品被盗版后依据“侵权获利”来予以损害赔偿的救济的话,又会像原《著作权法》第4条规定“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一样,可能成为引爆中国和美国之间知识产权争端的一根导火索。
根据ACTA第9条第3款以及第4款,至少在“侵犯版权与邻接权和假冒商标的案件中”,在权利人的利润损失难以计算或者没有直接的利润损失,而侵权获利也难以计算或者侵权获利的数额明显不足以补偿实际损失时,还给缔约方提供了三个可供选择的损害赔偿计算方法:(a)法定赔偿;(b)推定赔偿;(c)至少就版权而言,额外赔偿。
就法定赔偿而言,ACTA与TRIPs协议之间并没有实质差异,只不过ACTA是把法定赔偿作为侵权损害赔偿的一个可供选择的计算方法,而TRIPs协议中,既可以选择单独采用“法定赔偿”,也可以与“侵权获利返还”并用。我国知识产权法中,也已经把法定赔偿作为计算损害赔偿的一种替代方法,但是,无论是《商标法》还是《著作权法》都明确,这种损害赔偿计算方法适用的前提是: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也就是说,权利人并不能任意主张选择适用法定赔偿。但是,这种差异在实践中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如果权利人希望按照法定赔偿获得损害赔偿的话,其只要不积极举证证明权利人的利润损失或侵权人的侵权获利,就可以要求法院判决法定赔偿了。就推定赔偿而言,根据ACTA对此的注释,有三种推定损害赔偿额的方法:(1)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数量×权利人合法销售该产品的单位利润;(2)合理的许可费用;(3)根据侵权人请求许可使用该知识产权假定所要支付的许可使用费。事实上,我国法院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计算损害赔偿的时候采用了类似方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4条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复制品发行减少量或者侵权复制品销售量与权利人发行该复制品单位利润乘积计算。发行减少量难以确定的,按照侵权复制品市场销售量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商品单位利润乘积计算。”第15条规定:“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商品销售减少量或者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乘积计算。”因此,就用推定的方式来计算损害赔偿而言,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与ACTA的规定并不存在什么冲突。就额外赔偿而言,ACTA并没有对这个赔偿计算的具体含义作出解释。有学者认为这一般是带有惩罚性的赔偿。⑧根据美国《版权法》有关“在特定案件中的额外赔偿”的规定(17 U.S.C.§504),这是指在其他损害赔偿之外,按照两倍于许可费的金额来进行赔偿。⑨而这种损害赔偿计算方法其实在我国知识产权法中也是存在的,如《专利法》第65条规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不管对“额外赔偿”作何解释,因为ACTA对于第9条第3款规定的三种赔偿方式是由缔约方作选择性规定的,我国知识产权法即使不作出“额外赔偿”的规定,但由于已经存在法定赔偿和推定赔偿的做法,所以并不会与ACTA有什么不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ACTA第9条第5款规定:在适当情形下,至少在侵犯版权、邻接权和商标权的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有权责令败诉方赔偿胜诉方法院诉讼费和适当的律师费。这就进一步明确了TRIPs协议第45条第2款规定的“开支”的含义,而且起码在盗版和假冒案件中,败诉方是应该赔偿胜诉方“适当的律师费”的。我国的《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中虽然都规定“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但是,这里的“合理开支”是否包括其支付的律师费,却不是很明确。司法实践中,法院的做法也不尽一致。因此,在赔偿胜诉方的律师费用方面,我国知识产权法与ACTA的规定尚有一定的差距。
总的来说,在损害赔偿方面,ACTA与TRIPs协议之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差异。我国知识产权法除了对尚未合法出版传播的作品的侵权是否可以依据侵权获利来计算损害赔偿,以及是否应该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方面与ACTA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别之外,也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冲突。
(三)销毁侵权产品和侵权工具
为有效地阻止侵权,TRIPs协议第46条规定:司法机关有权责令将侵权货物清除出商业渠道或将其销毁,还有权责令将主要用于制造侵权货物的材料和工具清除出商业渠道。但是,TRIPs协议对于司法机关采取此类措施是有限定的,比如,采取“销毁”措施的前提是“不得与现存宪法的要求相悖”;“在考虑此类请求时,应考虑侵权的严重程度与给予的救济以及第三方利益之间的均衡性”。
与TRIPs协议相比,ACTA特别注重采用“销毁”措施,而不仅仅是“清除出商业渠道”;但对采取这些措施的有关限定更加模糊甚至消失。ACTA第10条规定:“1.至少对于盗版商品和假冒商品,各缔约方应规定在民事程序中,应权利人请求,其司法当局应有权命令不给予任何补偿地销毁这些商品,特殊情况除外。2.各缔约方应进一步规定,其司法当局应有权命令在不得无故拖延且不给予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将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的原料和工具予以销毁或将其清除到商业渠道以外,这种清除可以使进一步侵权的风险最小化的方式进行。3.缔约方依据本条所提供的救济措施可由侵权人支付费用。”
可以看出:首先,ACTA不再提出将侵权物品“清除出商业渠道”,而仅仅强调根据权利人要求来“销毁”侵权物品,这实质上就意味着只要权利人提出要求,就可以一律销毁侵权物品,而且销毁的费用将由侵权人支付,这将对侵权人形成极大的威慑;其次,ACTA对销毁侵权物品的措施虽然也规定了“特殊情况”的例外,但什么是“特殊情况”,则语焉不详,与TRIPs协议要求这种措施“不得与现存宪法的要求相悖”相比,其适用可以更为普遍和没有限制;再者,TRIPs协议并没有允许“销毁”制造侵权商品的原料和工具,而ACTA却允许销毁,并要求“不得无故拖延”,这无疑强化了制止侵权进一步发生的措施。
我国《著作权法》第48条允许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在处理侵权案件时“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但第52条仅允许法院“没收侵权复制品以及进行违法活动的财物”,却没有规定可以销毁。而《商标法》第53条允许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侵权案件时,“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专门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但并没有规定法院在民事侵权诉讼程序中可以对假冒商品采取没收、销毁的措施。上述规定说明我国有关行政机关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中所采取的措施已经完全可以和ACTA的要求相符合。然而,在知识产权的民事执法程序中,却与ACTA要求销毁侵权物品或销毁制造侵权物品的原料和工具有明显的差距。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法学界通常把“没收”、“销毁”措施当做一个行政处罚措施,最多是一种民事制裁措施而不是一种民事侵权救济措施来看待。因此,我国《民法通则》以及《侵权责任法》中都没有规定“没收”、“销毁”侵权物品以及侵权工具的救济方式。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不能采取或者没有采取销毁侵权物品或侵权工具的措施。首先,因为“停止侵权”是制止侵犯知识产权的必要救济措施,而在很多时候,不销毁盗版物或假冒商品,是不足以制止侵权的。因此,为了达到停止侵权的目标,就需要采取销毁侵权物品的措施;而在有的时候,某个生产工具是专门用于生产制造侵权产品的,这时,不销毁该侵权工具也不足以制止进一步的侵权,所以,也就有了销毁侵权工具的必要。事实上,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有不少法院支持权利人提出的销毁侵权产品或者侵权工具的诉讼请求。其次,从法律依据上看,虽然我国民事法律以及知识产权法律中并没有规定“销毁侵权产品”等类似的民事责任方式,但是,我国加入的TRIPs协议已经明确规定司法机关有权责令销毁侵权物品以及将制造侵权产品的工具和原料清除出商业渠道(比如没收)。因此,法院起码在没收、销毁侵权物品以及没收侵权工具上拥有国际条约的法律依据。总之,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民事司法审判程序中可以没收、销毁侵权物品以及没收、销毁制造侵权产品的工具和原料,但是,这并不妨碍法院在必要的情况下采取没收、销毁措施。当然,由于ACTA对于司法机关采用销毁侵权产品以及侵权工具的救济措施抱着非常宽松的态度,如果毫无保留地接纳ACTA的规定,可能与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吻合,会造成很多财富和资源的浪费,甚至可能威胁到一些实施了侵权行为的企业的生存。
(四)责令提供侵权信息
由于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发明创造、文艺作品、商业标识等客体无形性的特点,当侵权人在制造侵权产品的时候往往难以被及时发现和制止,往往是侵权物品在市场和公众中流通或传播时,权利人才能发现侵权行为。而且,即便这时发现了个别侵权现象,权利人也往往难以直接获知这些侵权物品的来源和出处,因此,难以有效地打击和制止那些上游的、直接的侵权行为。为此,TRIPs协议第47条就权利人“获得信息的权利”作了规定:“各缔约方可以规定,除非与侵权的严重程度不相称,司法机关有权责令侵权人将涉及生产和销售侵权货物或提供侵权服务的第三方的身份及其销售渠道告知权利持有人。”
ACTA第11条就“与侵权有关的信息”的披露对缔约国作出了强制性的要求,并作出了进一步明确的规定:第一,权利人可以基于收集证据的目的,请求司法机关责令侵权人提供信息。这样,启动这个程序的主动权就可以掌握在权利人的手里。第二,被责令提供信息的主体不仅仅限于侵权人,也可以是被指控侵权的人;被责令提供信息的客体不仅仅限于侵权物品,也可以是被指控侵权的物品。也就是说,责令提供信息,不以侵权行为已经被认定为前提。第三,被责令提供的信息是由国内法规定的侵权人或者被指控侵权人所占有或控制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的范围可以包括涉及侵权的人的身份信息。与TRIPs协议不同的是,ACTA规定,这些涉及侵权的人员不仅仅是那些参与侵权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第三方”信息,还可以是“涉及侵权任何环节的任何侵权人”的信息。比如,在侵犯著作权的案件中,可以包括那些作品的非法传播者的信息;而且,与TRIPs协议不同的是,除了可以责令提供侵权物品的“销售渠道”信息外,ACTA还规定可以责令提供侵权物品的“生产方式”的信息,这对于认定专利侵权可能是十分重要的。第四,TRIPs协议对于责令侵权人提供信息要求“不得与侵权的严重程度不相称”,也就是说,在侵权程度不严重的情况下,是不应该采取责令提供信息的措施的。但是ACTA删除了这样的限制条件,只是要求在责令提供信息时“不违反关于特殊权利、对信息来源机密性的保护或者个人数据处置的法律”。
我国的知识产权法以及民事诉讼法中,虽然有证据保全的规定,但并没有规定在侵权案件中,权利人可以请求侵权人提供侵权信息。⑩而责令侵权人提供侵权信息制度与证据保全制度在制度的目的、机制和作用上都不尽一致,不可混为一谈。因此,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侵权信息的披露制度,虽然不违反TRIPs协议的弹性要求,但与ACTA的强制性要求可能会发生冲突。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我国发生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侵权人可以任意回避或者抗拒提供有关侵权信息。《商标法》第56条第3款规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11)《专利法》第70条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能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这些规定,如果假冒商标商品的销售商要免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就需要说明假冒商品的合法来源(提供者);如果专利侵权产品的使用者、销售商以及许诺销售者要免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也需要证明该产品的合法来源。这就大体上可以满足TRIPs协议甚至ACTA规定的侵权人披露侵权信息的要求。
(五)临时措施
TRIPs协议第三部分“知识产权执法”中专门有一节(第三节)规定了“临时措施”;而ACTA则把“临时措施”作为民事程序的一部分在“民事执法”一节中加以规定。临时措施在中国知识产权法以及民事诉讼法中就是指诉前禁令和诉前证据保全。
TRIPs协议第50条规定:“1.司法机关有权责令采取迅速和有效的临时措施以便:(a)防止侵犯任何知识产权,特别是防止货物进入其管辖范围内的商业渠道,包括结关后立即进入的进口货物;(b)保存关于被指控侵权的有关证据。2.在适当时,特别是在任何迟延可能对权利持有人造成不可补救的损害时,或存在证据被销毁的显而易见的风险时,司法机关有权采取不听取对方当事人陈述的临时措施。3.司法机关有权要求申请人提供任何可合理获得的证据,以使司法机关有足够程度的确定性确信该申请人为权利持有人,且该申请人的权利正在受到侵犯或此种侵权己迫近,并有权责令申请人提供足以保护被告和防止滥用的保证金或相当的担保。”
我国主要的知识产权法中都已经规定了与TRIPs基本吻合的临时措施制度。例如《专利法》第66条规定,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12)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关于颁发诉前禁令规定了一个前提要件:不及时制止侵权将会使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迟延”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呢?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一般来说,首先,如果这种损害难以用金钱弥补的话,比如非财产性的商誉损害等,就可以认为是难以弥补的;其次,如果预期的损害将远远超过被申请人的赔偿能力或者以后难以执行的话,也可以认为是不可弥补的。由于侵权一般都是可以用金钱赔偿来弥补的,权利人也不太容易证明损害赔偿以后难以执行——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很可能根据这个理由而驳回了诉前禁令的申请。
而TRIPs协议并没有规定“难以弥补的损害”是颁发诉前禁令的必要条件——虽然TRIPs协议第50条第2款确实提到了“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形,但只是规定:在这种情形下法院可以不听取被申请人的意见就采取临时措施。这就是说,“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形是一种少见的非常紧急的情形,而不是所有诉前禁令措施都必须是在存在“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形下采取的。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我国知识产权法对颁发诉前禁令所设定的前提要件要比TRIPs协议更为严格一些。当然,由于TRIPs协议并没有明确规定颁发诉前禁令的条件,因此,各国法律可以自行规定颁发诉前禁令的条件,我国知识产权法设定“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条件也并不违反TRIPs协议。
ACTA规定的临时措施制度从总体上看与TRIPs协议相差无几,比较明显地强化临时措施效力的内容有两点:
第一,与前述“禁令”措施类似,ACTA把临时禁令措施的适用范围也扩大到了“第三方”,而不仅仅适用于构成侵权的当事人,也不仅仅是阻止已经进口清关的侵权货物进入商业渠道,而是要阻止任何侵权货物流入商业渠道。(13)
第二,ACTA还对临时禁令和诉前证据保全的具体措施——“扣押或监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使得临时措施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富有实效。根据ACTA第12条第3款的规定,至少在侵犯版权与邻接权和假冒商标案件的民事程序中,各缔约方应当规定其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扣押或监管与涉嫌侵权行为有关的商品、原料和工具,以及至少在假冒商标案件中的书面证据,无论其是原件或是复印件。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ACTA有意无意地忽略了TRIPs协议中规定的临时措施的通知、审查程序,要求申请人提供信息以对商品进行辨别,撤销、终止临时措施的程序,也不再提及TRIPs协议第48条规定的针对权利人滥用执法程序而应该向被告支付开支(包括适当的律师费)等,(14)此举明显有偏袒知识产权权利人一方的嫌疑。当然,这并不妨碍各国国内法对此作出规定。
总之,我国知识产权法对采取临时措施方面本身就设定了较TRIPs协议更为严格一些的适用条件,加上ACTA又将临时措施扩大适用于不构成侵权的第三方,因此,我国法律与ACTA的要求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三、对ACTA的评判以及我国的应对之策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的同时又面临着知识产权假冒贸易的困扰,现有的TRIPs协议以及一系列国际规则似乎已经不再能够满足那些知识产权强国的现实需求。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已经迫不及待地需要制定或主导新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知识产权执法规则,以遏制全球范围内的假冒和盗版。于是,ACTA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杆新的大旗就被高高举起,建立知识产权国际执法新标准的目的已近乎实现,发达国家再次将发展中国家引到了ACTA这一知识产权国际新秩序的门口。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ACTA所确立的知识产权执法体系呢?ACTA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套独立于WIPO和WTO的新的知识产权执法国际体系。ACTA的序言也指出:“为知识产权执法提供有效和充分的手段,以补充TRIPs协议(的不足)。”从本文重点分析的民事执法措施来看,与TRIPs协议相比,ACTA确实有了一些质的飞跃,形成了所谓的“超TRIPs”执法体系。比如,将禁令措施和临时措施(临时禁令和证据保全)扩大适用于不构成侵权的第三方;将销毁措施应用到用于制造侵权产品的原料和工具上;把提供侵权信息的义务上升为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并适用于任何侵权环节;并明确规定了数字环境下知识产权执法的要求。但是,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整个知识产权执法的法律框架,还是具体的执法措施,ACTA基本上沿用了TRIPs的规定,并没有走出TRIPs太远。那些把ACTA看做是对TRIPs协议的一个巨大的颠覆性的超越的言论,不免有些夸大其词和耸人听闻。
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们应该如何应对ACTA带来的挑战?
首先,不要夸大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和ACTA之间的差距,而要大力宣传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与ACTA规则之间的一致性。由于我国客观存在的假冒和盗版问题,ACTA的订立或多或少有针对中国的意味;而且由于我国一开始就被排除在ACTA谈判之外(即便被邀请也不见得愿意加入),很多人自然地对ACTA产生一种排斥心理,而且想当然地认为ACTA会对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带来巨大的挑战。但是,从上面的分析来看,ACTA并没有太多超越TRIPs协议的地方,而我国作为WTO的成员,已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已经符合TRIPs协议规定的最低标准。因此,与ACTA的要求相比,也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相反,可以说,我国知识产权执法的法律制度在绝大多数方面已经符合ACTA的标准。如果我们一味突出、夸大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与ACTA之间在个别执法措施规定方面的差距,反而会给公众特别是外国人造成我国知识产权执法制度与国际标准相差甚远、我国的知识产权执法和保护因此很差的印象和联想,也正好让国外那些对我国知识产权制度抱有深刻偏见和不切实际要求的政客找到指责中国政府的借口和理由。有学者对“欧盟委员会自信满满地认为其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与ACTA完全相容,不存在任何需要修订的法律条文;美国、澳大利亚也不甘示弱,纷纷表示其域内法与ACTA不存在一点一滴的差距”的现象表示极不理解而“大跌眼镜”,(15)笔者认为这恰恰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高明之处:绝不认为自己的制度不够好。面对ACTA这样一个高标准的知识产权执法体系,突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与其的差距,强调其对我国现行制度带来的挑战,等于公开承认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国际标准差距甚远,这并不是值得光荣和骄傲的事情,相反只能成为某些国家对我国施压的一个堂皇理由。而如果我们坚持认为自己的知识产权执法制度已经基本上符合ACTA的要求,那么,面对有些国家要求我们接受这样一个既定的游戏规则时,我们就更有了选择加入或者不加入的底气和理由——因为即使不加入,我们也可以依据现有的法律制度进行有效的知识产权执法。
其次,我国要不要接受ACTA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一个国际知识产权谈判中的筹码。2009年11月公布的一份《ACTA正在讨论的要点摘要》文件明确指出:“ACTA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一些大的经济体,如中国、俄罗斯、巴西,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需要提高,将来需要签署《协定》。”(16)那么,我国应不应该接受ACTA规则呢?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确实在某些方面与ACTA的知识产权执法标准上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如果要接受ACTA规则,就自然需要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影响一些依靠假冒、盗版为生的企业和个人的生存。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假冒、盗版的大量存在确实是不利于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的,也是与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相悖的。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加大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力度,也是我国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而且,实事求是地讲,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好是坏,知识产权执法水平或高或低,并不简单地取决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律文本,更为关键是整个社会的法治水平和尊重知识产权意识的提升,即使我们接受ACTA规则,也不见得可以使我国的知识产权执法和保护水平产生急剧的质的变化。总之,虽然我国可以在现阶段对ACTA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但是,ACTA规则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则之间并不存在太多深刻的冲突,也与我国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大趋势不相矛盾。因此,接受或不接受ACTA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我国政府在国际谈判场合与其他国家进行政治博弈的一个筹码。在适当的时机加入ACTA,也可以是一个备选方案。
最后,ACTA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审视、评估、反思和构建我国知识产权执法制度的机会。ACTA主要是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达成的一个协议文本,可以说代表了当今世界知识产权执法的最高水准。从前面的分析来看,一方面,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执法体系与ACTA的某些要求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禁令和临时禁令对不构成侵权的第三人的适用;对尚未合法出版传播的作品遭受侵权的损害赔偿;胜诉方律师费的赔付;销毁侵权产品和侵权工具作为侵权的民事救济措施;权利人直接请求提供侵权信息的制度;导致不可弥补的损害不是颁发诉权禁令的前提要件等。对于这些规则,我们不应抱着“为反对而反对”的态度一概予以拒绝和否定,而应该加以客观、审慎地评估,判断其对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执法制度是否有积极的意义,然后决定在以后的法律修改中是否加以补充和吸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我国的知识产权执法体系和制度不仅已经和TRIPs协议、WCT、WPPT等国际公约接轨,甚至在有些方面已经超越这些国际公约的要求。但需要我们反思的是,当我们在吸收、借鉴这些国际规则的时候,往往只是简单地满足其对我们的要求,却忽视了其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防止权利人滥用救济措施等规定。比如,TRIPs协议允许对善意取得或订购侵权商品的经营者不采取停止侵权的措施;TRIPs协议针对权利人滥用执法程序,要求向被告赔偿损失并支付开支(包括适当的律师费);TRIPs协议规定采取“销毁”措施的前提是不得与现存宪法的要求相悖,而且在考虑此类请求时,应考虑侵权的严重程度与给予的救济以及第三方利益之间的均衡性。我国在构建知识产权执法制度时,也应该考虑这些更为精细的平衡机制。总之,只要我们自己精心构建起一个全面、有效、平衡的知识产权执法机制,那么,面对发达国家抛出的ACTA规则,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我们都能更加自信和游刃有余。
注释:
①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html/147937.htm,2011年10月5日,本文有关阐述以这个文本为准。
②新加坡政府法务部: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 Signing Ceremony,http://app2.mlaw.gov.sg/News/tabid/204/Default.aspx? ItemId=582。
③有学者将这里的“人”理解为侵权人以外的第三方,参见崔国斌:《反假冒贸易协议与中国知识产权法的比较研究》,《电子知识产权》2011年第8期。笔者认为,从字面上理解,这是指构成侵权的善意侵权人,而不是不构成侵权的善意第三人。
④崔国斌:《反假冒贸易协议与中国知识产权法的比较研究》,《电子知识产权》2011年第8期。
⑤中国知识产权法是否有必要规定对所有的侵权行为都采用停止侵权的措施,值得商榷。
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的规定,如果出版者尽了合理注意义务,著作权人也无证据证明出版者应当知道其出版涉及侵权的,出版者仅仅承担停止侵权、返还其侵权所得利润的民事责任。这与TRIPs协议规定的“无过错责任”的精神是一致的。
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据商标法第56条第1款的规定确定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时,可以根据权利人选择的计算方法计算赔偿数额。
⑧前引④,崔国斌文。
⑨COPYRIGHT ACT OF 1976(17 U.S.C.§504).Remedies for infringement:Damages and profits.(d) Additional damages in certain cases.—In any case in which the court finds that a defendant proprietor of an establishment who claims as a defense that its activities were exempt under section 110 (5) did not have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that its use of a copyrighted work was exempt under such section,the plaintiff shall be entitled to,in addition to any award of damages under this section,an additional award of two times the amount of the license fee that the proprietor of the establishment concerned should have paid the plaintiff for such use during the preceding period up to 3 years.
⑩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中,虽然没有全面规定侵权人提供信息的法律义务,但是,为了保护著作权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关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则已经对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侵害著作权的信息的义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3条以及第25条的规定: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为了查处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可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涉嫌侵权的服务对象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网络地址等资料。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或者拖延提供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没收主要用于提供网络服务的计算机等设备。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著作权人要求其提供侵权行为人在其网络的注册资料以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的规定,追究其相应的侵权责任。可以说,我国有关法规、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已经完全符合ACTA的要求,甚至已经超越了ACTA的要求。
(11)《著作权法》没有作出类似的规定,但该法第53条“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规定意味着:盗版物的发行商、出租者如果能证明合法来源,就可以免于承担赔偿责任。
(12)类似的规定还有,《商标法》第57条规定: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著作权法》第50条: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权利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
(13)根据ACTA第12条第1款的规定,各缔约方应当规定其司法当局应有权命令采取及时而有效的临时措施,以阻止当事人或在适当的情况下阻止在该司法当局管辖范围内的第三方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发生,尤其是阻止侵权货物进入商业渠道。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可以参看前文关于“禁令”的阐述。
(14)有学者指出,这种忽略到底是“无心”,还是“有意”,只能等待ACTA的后续发展。参见左玉茹:《ACTA的飞跃——基于ACTA与TRIPS协定的比较研究》,《电子知识产权》2010年第11期。
(15)左玉茹:《ACTA:我们的命运谁做主?》,《电子知识产权》2011年第8期。
(16)陈福利:《反假冒贸易协定述评》,《知识产权》2010年第5期。
标签:法律论文; 知识产权侵权论文; 知识产权法院论文; 法律救济论文; 知识产权服务论文; 赔偿协议论文; 商标法论文; 著作权法论文; trips协议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