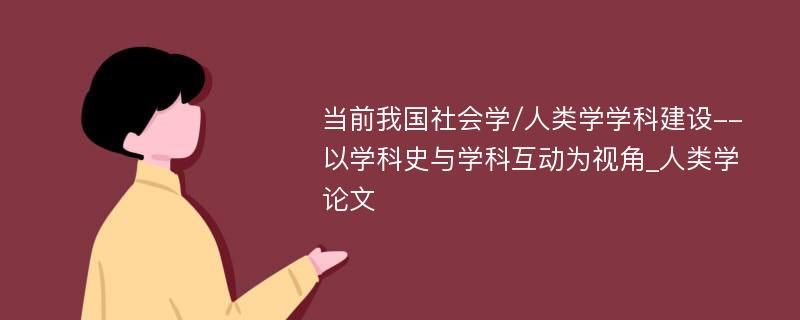
当前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从学科史和互为学科性角度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论文,人类学论文,学科建设论文,社会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专业目录中,“人类学”由原来在“生物学”下和“民族学”下改为在“社会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四个二级学科之一, 学科代号为030303 ,
与之并列的其他三门分别是社会学(030301)、人口学(030302)和民俗学(030304)。我想就个人的经历谈一些杂感,请同行们讨论、指正。
一、对学科的界定
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要有发展,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应该重视对学科定义或对象的探讨。在此想借用梁启超说过的半句话:“对他而自觉为我”。梁任公此话是在谈“何为民族”时说的,对我们现在的讨论也有启发。确立一门学科(discipline),实际上就是在科学的知识分类体系中为它划界区分他我,为它定位。郑杭生先生曾出版专著探讨社会学的对象,并对社会学下了一个定义:“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在社会学界还引起过小小的争鸣。①②对于民族学,林耀华先生曾经说:“民族学是一门以民族为对象的社会科学,它研究民族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是一门独立的学科。”③至于人类学,笔者以为,人类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主要通过分析田野工作所得的资料,运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从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两大方面来研究人类自身。依照郑先生的理解,一门学科如果不能说清楚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它就很难得到发展。而对一门学科的了解,除此之外也完全可以象英克尔斯那样,从历史的、经验的和分析的三条途径去进行思索④。
在中国人的传统中处事讲究的是“名正言顺”,即首先想到为学科正名。而目前恰恰是个“争名”十分激烈的时代。标志之一是: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教育部)分别采用三套不尽相同的学科分类标准。如国家技术监督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以民族学来统率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分类目录修订稿》(1996)中,社会学之下有人类学,民族学之下则有文化人类学。混乱是显而易见的。
二、人类学等诸学科的历史
人类学源起于欧洲,并在19世纪后半期形成其第一个理论流派——进化学派,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也在此时期得以产生。早期人类学以研究非西方资本主义的后进民族及其社会文化为学科对象,与研究自身社会运行的社会学有较大区别,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比较强烈。20世纪中叶以来,尤其是近30年来,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人类学研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不仅研究部落社会和乡民社会,也研究都市社会;不仅研究异文化,同时也从文化的比较中来反思自我,从而达到增进人类不同族群之间彼此了解、达成共识的目的。因此,社会学与人类学等学科在研究对象上无疑有了更多的交叉叠合。
人类学大约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中国学者对它作了本土化的尝试。在解放前的几十年发展中大致形成了两大流派。历史学派比较注重对历史、考古与体质的研究,功能学派则比较注重对当代民族与社会的研究。解放初期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人类学中研究体质的部分基本保留下来,但被归并到生物学或古生物学之下;研究人文与社会的那部分则被调整到历史学内,或以“民族研究”的名义得以延续。1979年以来,人类学得到恢复并且取得新的发展。率先建系并建有人类学博士点、硕士点的中山大学是依照文化人类学(含民族学、语言学和考古学)与体质人类学相结合的模式来培养学生的。其他院校分别设有人类学研究所、社会学人类学所、民族学与人类学所等。然而,人类学这些年来曾分别被归属在历史学、民族学或社会学等学科之下,学科地位变动较大。出于对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趋势的思考并参照国际学术界学科分类的惯例,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倡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三科并列、互相交叉、各得其所、努力发展”⑥。这种构想与今天侧重发展人类学的应用研究、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目标是一致的。社会学传入中国后也经历了与人类学相仿的中国化过程,它在解放后的院系调整时被取消,中断三十余年,直到1979年才正式恢复。
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源于西方的近代社会科学在当代中国面临的本土化、与国际接轨、跨文化对话等问题,与中国“被现代化”到一个与自身传统文化不太一致的世界学术规范体系中的现实是息息相关的。因此,谈中国的此类学科的发展,必须在顾及国外情况的同时充分考虑本国特点,否则,事事与西方的社会事实比照是无法解释中国实情的。值得注意的是,“中断”并非“一片空白”,它同样给今天的学科发展带来不容低估的影响⑦。下面所举的或许可算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在《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一书的“序·时代的召唤与时代的限制”中,“作为受业弟子”的张承志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我不大信任所谓民俗学或人类学;比如,我总怀疑背负着血腥的屠杀美洲原住民的历史的美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究竟有多少深度。它们应当与人类认识真理的规律相悖。受欧美影响而展开的中国民俗学人类学,说透了并没有提出过什么值得重视的认识——也许正是这一偏激感受的注释”⑧。读过这段写于1993年的文字,我不由心中一惊,费先生说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出身不正”不足为奇,“唯成分论”流毒遗患至今叫人叹息。可见人类学、民俗学在某些知识分子心中还没有扭转不光彩的形象。
还有一位研究中国人类学史的美国学者写下了一段评论,也颇有意思:
费孝通在1979年还是支持重建人类学的,到了1980年,他又改变了立场。从那时起,他就站到了反对人类学重建的行列中,说中国的人类学摆脱不了其殖民地的影响。有人解释说,费之所以反对,与他所受的英式教育不无关系,相对于南方学者赞同的美国模式的文化人类学来说,他更偏向于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另外一些人推测说,费认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地位刚刚稳固,没有必要耗费精力去重建另外一个有争议的学科。
不管他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到了1980年,费已经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来否决所有他不喜欢的学术活动了,即使他想这样做也不行。其他的社会科学家明确地反对他将人类学排斥在中国之外的观点。譬如,民族学家秋浦和中山大学的梁钊韬都坚持说,发展中国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民族学和人类学是行得通的,对中国未来的繁荣也是必不可少的⑨。
看来,反思学科“被取消”的历史,对于当前的学科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问题取向”·互为学科性·学科建设
关于学科建设近来有不少讨论,各种真知灼见都值得我们重视⑩。为了解决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实际问题,研究人员中有人主张不要去区分什么学科界线,只求以问题为中心,做所谓“问题取向的研究”,如区域研究等便是。这方面费孝通先生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他自言是“一匹不受学术领域中各科边界约束、四处乱闯的野马”(11),结果取得了个人的成功。不过这无法标志社会学或人类学或民族学的成功。我以为,打破学科界线、以问题取向搞研究,仅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应用研究取向或研究方法(approach)。由于它实际上含有所谓科际整合的做法,所以与“剩余学科说”相仿,对于发展一门独立的社会学或人类学学科(discipline)是有弊无益的,至少从学理上讲是如此。但是,或许是由于中华民族的特殊国情、或许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老一辈学科带头人在解放初期注重的并不是象现在所说的单一学科的定位划界。
费孝通在他的民族研究文集的“自序”中,表达了自己对社会学、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看法:
我所说的民族研究,实际上是指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其中自当包括少数民族的社会研究,所以也可以包括在社会学这个学科之内,要突出这部分研究的特点,不妨称之为民族社会学。……我是不主张把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区别成两门学科的。在我看来,它们研究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人类的社会。西方的学科分类有它的历史原因。他们认为现代工业化的社会和现代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可以分成两门学科去研究,即社会学和人类学。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自己的学术实践就在消除这个偏见,而把研究重点放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上。(12)
费孝通和林耀华在1956年主持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是年5 月在列宁格勒召开“全苏民族学会议”,林耀华代表中国民族学工作者出席并在大会上宣读了此文。1957年3月,民族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名为《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 事过不久,民族学与作为民族学家的费孝通都遭受厄运,一晃便是20年。80年代民族学枯木逢春,当年的两位作者都有了出版个人文集的机会。他们也都同样重视这篇论文的不同寻常的意义,分别将它收入集子当中。我们今天讨论学科建设,“书内书外”地重读此文让我获益匪浅。当年两位先生就已经指出:
把少数民族和汉族分开来作为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根据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由于民族主义的偏见,歧视殖民地的各民族,曾经把所谓‘文明人’的研究划在民族学或‘社会人类学’的范围之外。这是错误的。我们将以苏联民族学为榜样,批判这种资产阶级错误思想,而肯定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一切民族在内的,在中国的范围里,不但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
民族学在中国还可以说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因此还有许多人对于这门学科的名称、内容和方法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在这里不想从定义、学科分类上进行讨论。为了避免各种讨论成为学究式的辩论,我们认为最好从这门学科所进行的研究工作的本身来说明它的内容,而且只有在研究工作的发展中,一门学科的性质和范围才能逐步明确起来。一门学科的发展,我们认为,并不依靠开始时把范围划好,界碑树好,而是依靠密切结合实际生活所提出具体的问题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实际生活是丰富的、变化的,一门学科能从这个丰富和变化的泉源出发,它的工作也会是活泼的、常新的。我们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来为中国民族学提出它的任务的。(13)
我之所以选用1957年版的单行本,是因为80年代的两本文集对原文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删节。作为研究之用的再版文章,做如此技术性处理我认为是不严肃的、有悖历史的科学精神。至于当时“不划界”的做法的历史原因,则是可以讨论的,且也并不一定要“削足适履”、以今天的标准来度量。
目前,尽管在制度化的分类体系当中,“人类学”还未成为一级学科,但是它毕竟先与“历史学”、后与“民族学”脱离关系而朝“社会学”靠近了一些。如果要让我说一点直观的理解的话,那么,我认为值得注意的乃是,近几十年来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实践在客观上已经导致了所谓“‘民族’词义的狭化”和“民族学的广义化”。解放后不久,社会学即遭受批判而被取消,民族学的研究则被代之以“民族研究”。这段历史客观上对于铸就现在这门一级学科“民族学”具有不容低估的作用。许多学者把这段历史过程视为学科发展中的“空白”,我看是不确切的。与此同时,“民族”一词实际上在许多场合几乎约定俗成地都变成为“少数民族”的同义词。“民族地区”、“民族干部”、“民族语文”乃至“民族区域自治”等等字眼,都在潜移默化的语境中一定程度上为“民族学不研究汉族”作了语义方面的诠释。西方早期民族学和人类学方法论的整体观似乎也为“广义民族学”(14)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石。这门学科要担负起研究一个群体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学术使命,政治、经济、宗教、历史等等,无所不包。目前一级学科“民族学”其实就是广义而言的民族学,在它之下又有二级学科“民族学”与“民族理论”、“少数民族历史”、“民族经济”等并列。这种情况,可能与我上面指出的两点存在某种潜在的联系。
有位学者在英国社会学学会1988年年会上提交了名为《历史学对社会学的流通性》的论文。其中有一段话讲到“互为学科性”,读来让人颇受启发:
对各种知识方案的运作而言,学科化是一个重要条件,但这种条件有可能面临挑战,因此对那些涉入这些不同方案运作的人而言,互为学科性应该是其目标之一。在此,互为学科性被假设成:可借它取得特定的知识,而这也是它之所以被假定为值得研究的目标。(15)
由此看来,对于生活世界的认识和改造需要知识的整体性与知识体系的分门别类乃是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要说学科建设,那么即使是出于人为的划界也是必须的,经验研究和实地调查无法取代理论建构。而且,鉴于知识往往与权力黏结在一起,所以,学科建设的讨论难免隐含一些学术之外的利害关系。但愿我们的讨论能够摈除门户之见,走在健康的大道上。
标签:人类学论文; 社会学论文; 民族学论文; 民族社会学论文; 学科建设论文; 历史学论文; 费孝通论文; 民族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