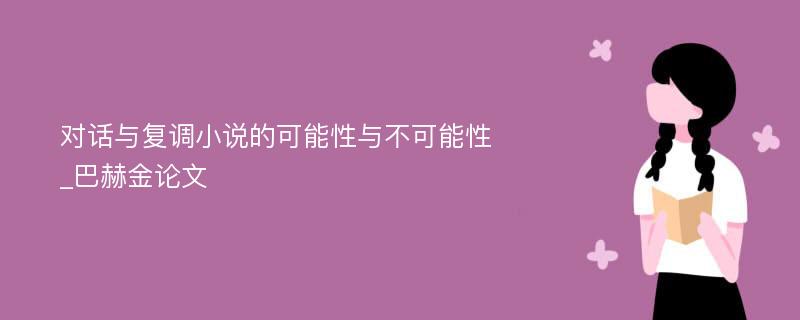
对话的可能与不可能及复调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可能论文,能与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源于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独到研究,其核心是对话哲学,巴赫金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一些“具有伟大却尚未解决的思想问题的小人物”,都是某些重大思想和价值的体现者,他们各自不同的自我展开广泛的对话,形成多元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具有“伟大思想”人物的“有声”的对话,使人类精神和生存领域的重大命题得到表现。在巴赫金看来,只有在这种由对话组成的复调小说中,主人公的主体性才得到充分发挥,而不是如那些所谓“独白体”小说的主人公那样,由于被纳入作者的独断式主观视野而贬低为物。
然而,如果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外部世界异己力量的强大,已使主人公沦于异化为物的存在状态,而小说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表现人的物化的可悲境地,那么,巴赫金所强调的人物的主体性是否依然成为作品不可或缺的要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人公具有如此卓异不凡的思想和如此丰富浩瀚的心灵,以至“全部现实生活成了主人公自我意识的一个要素”(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三联书店, 1988年,第83页。),主人公都是理解、追问、沉思自己命运或人类终极价值的思想家,但是,如果主人公已全然丧失支配自我和理解自我的能力,性格和思想消逝于命运的强力摆布之中,如果伟大的思想已不复存在,且思想的消亡和心灵的枯竭本身已构成小说的主题,那么,“对话”是否依然可能?这,正是卡夫卡等作家笔下所描绘的现代人的基本境遇,也是20世纪小说家所面对的重大问题。此情此际,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小说是否还可作为一种生动有力的艺术样式在卡夫卡年代继续发挥潜能?他的建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基础上的思想对话式复调理论该如何应对这一巨大变化?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阐释和探讨。
一、卡夫卡与小说中的非对话情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通过具有不同思想的主人公的对话表现了人类诸多重大主题,而卡夫卡小说却揭示出人类基本情境的另一方面——对话的不可能。在《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出场就失去了自己的声音,而只能发出怪异陌生的虫鸣。这一情节意味深长。对话的艰难和交流的阻隔构成了现代人类困境,卡夫卡作品成为其重要象征。米兰·昆德拉指出,每一时代的小说都和自我之谜有关。人们对自我的探求构成小说的历史。“什么是自我?怎样才能把握自我?这是小说作为小说的基本问题之一。”(注: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22页。)巴赫金划分复调和独白的区别,从根本上说,就是作家和主人公在对待自我和他人问题上的不同。然而揭示主人公自我以及自我所呈现的世界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最早的欧洲小说家通过行为来把握自我特性,但其后的狄德罗等人“对此表示了更多的怀疑”,于是理查森以及其后的歌德、司汤达等作家走上通过人物内心生活来表现自我的道路,直到乔伊斯、普鲁斯特而达到极致。然而这种心理观察越具体丰富,自我就越难在其中得到把握。昆德拉认为,现代小说新方向的真正代表是卡夫卡,因为“他构想自我的方式是完全出人意表的”。他问道:“K作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如何界定?既不是他的外貌, 又不是他的个人经历,也不是他的名字,同样也不是他的记忆,他的嗜好,他的情结。”他的行为受到可悲的限制,他的思想萎缩消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地位低微却思想卓越心灵丰富,对世界和自我具有清醒、痛苦和深刻认识的对话性主人公相比,卡夫卡的主人公呈现出强烈的非对话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外部力量的不可抗拒和对话主体的彻底物化。格里高尔莫名其妙地变成动物,被封闭在一只甲虫体内孤独地死去。K无缘无故地受到审判而终像一条狗一样被杀死。二、 思想萎缩成当下情境。卡夫卡不停地追踪主人公的思想活动和意识反应,发现这些反应全部集中于当下情境:在瞬时的环境中,当时当地该干什么?(注: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25页。)三、自我等同于命运。世界成为主人公的受难方式和消亡方式,而非人物思想的对象,或他们心中完整宏大的现实。主人公不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那样用精彩的对话表达世界,无思想的、茫然惊诧着沉默着的受难和消亡本身构成对世界和人类境遇的绝妙表达。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主要指具有不同文化价值的思想之间的互相独立的平等交锋,其间,独立和平等是先决条件。但是在卡夫卡小说中,人的独立平等已不复存在,代之以无端的奴役和摧残。世界抽空了人的灵魂,枯竭了对话的可能性,人甚至在尚未理解这个世界之前就已被消灭。即使在题材本应最具论辩意味的《诉讼》中,对话也变得极其困难和不着边际,更无所谓明显的价值主张之争。审判K 的是一个始终暧昧不明的法庭,K的申诉竟也如游丝般的无力, 他自始至终既不理解与他对立的现实,也不理解自我,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至于《变形记》和《在流放地》等作品,则是人类对话的不可能已达极致的象征。《在流放地》中,世界以机器刺入肉体使人受难死去的方式对他发话,而受刑者只能一边舔食稀粥,无言无语,一边从肉身的疼痛路径来试图理解机器对他的“言说”。这些形象无不力透纸背地揭示出人类非对话情境的特质。
非对话情境在卡夫卡以前的作家,比如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已有一定表现。正因为如此,巴赫金在论述复调小说概念时,将托尔斯泰的作品当作复调的对立面——传统的独白体小说的代表。事实上,无论巴赫金如何强调其局限性,托尔斯泰小说的非对话性,在卡夫卡时代具有不可忽视的现代意义。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一,面对死亡的不可言说的孤独。二,存在的平淡无奇与思想的缺席。
巴赫金以小说《三死》为例,批评托尔斯泰将三个毫不相干的故事,三个封闭的世界“在作者的包容他们三者的统一视野和意识里,联结到一起”,(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三联书店, 1988年,第112页。)托尔斯泰“自己对主人公有什么看法, 并没有让主人公知道”,“因而主人公也无法对此作出回答”,巴赫金对托尔斯泰“背后议论”主人公的做法持否定态度。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不会去描写三个死亡……死亡对于阐明生活不可能具有任何意义。托尔斯泰所理解的那种死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第115页。 )。死亡是完成性、终结性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永远未完成,永远在发展。于是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幸免于难,高谈阔论着上断头台前五分钟的感受,而托尔斯泰笔下伊凡·伊里奇等人的死亡却是终结性的,无可挽回的。
笔者以为,巴赫金批评托尔斯泰独白体小说作者在统一视野中任意支配议论主人公虽不无道理,然而他断言托尔斯泰式地描写死亡对于阐明生活毫无意义,并因这种描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根本不存在而否定死亡表现的价值,则失之偏颇。托尔斯泰笔下的死往往是平凡的死,无意义的死,正因为它平凡、孤独、沉默,不包含伟大的思想和主体的自由意志,没有充分价值,引不起“对话”又不可挽回,它恰恰揭示了人的被遗忘、被遮蔽的本真状态。这种状态是艺术难以表现却需要表现的。
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临近死亡的伊凡·伊里奇所作的对话全是一种虚假的应付,而他心中最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却无法表达也厌于表达。这种面对死亡的不可言说的孤独,在海德格尔那儿被称为“此在”的“绝对个体化”,(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三联书店, 1987年,第315页。)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论, 人面对死亡时的状态是不可替代、不可沟通的,是最“本己的”,亦即非对话性的。虽然《存在与时间》将托尔斯泰所描绘的状态赋予哲学形式,上升到本体论意义,不免有些绝对化,也引起了包括萨特在内的许多思想家的异议。(注:萨特《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1987年,第683页。)然而, 不可否认,这种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回避,被巴赫金所轻视,被托尔斯泰所倾心,被海德格尔所本体化、绝对化并赋予哲学形式的面对死亡的无言的孤独情境,这种难以沟通、难以交流的非对话情境,构成现代人类境遇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存在的平淡无奇与思想的缺席,是托尔斯泰笔下具有现代意义的另一非对话情境。托尔斯泰笔下既有列文那样以他自身为原型的思想探索型主人公,也有伊凡·伊里奇那样在日常生活中度过平庸一生的人,更有平凡普通的农民。小说的思想深度决不仅由主人公在对话中明确阐述、外在表现出来。无思想的人的极端境遇以及于其中产生的心理和行为反映,也可大有深意。托尔斯泰不愿赋予笔下每个人物复杂不凡的思想,而将这个“特权”留给自己,这种做法不应简单否定。生活本是平淡无奇的,普通人原本就缺乏可构成激烈价值冲突的思想。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赋予主人公更多的主体性,表面看更符合生活原貌,事实上,这样做恰恰给主人公都打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思想家的烙印。他们的痛苦和矛盾是思想家的痛苦和矛盾。而托尔斯泰笔下描写的如千百万普通人一样的主人公,尽管他们十分平常,其人生境遇却同样惊心动魄。
在现代世界里,思想的缺席以更加严峻更为独特的形态存在着。如果说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在平淡无奇的存在中,在思想缺席的情况下仍然具有丰富的感情世界的话,那么,在卡夫卡时代,思想的消失和情感的枯竭则是同时发生的。“现代的人……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归根结底,无非是外表上表露的那样而已。……你向他投过一瞥,从他脸上可以观察到毫无表情的呆滞和木然的神情。这种神情并不掩饰着什么内心活动……其实,这无非就是沉默而已”(注:萨洛特《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见柳鸣九编《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4页。)。这也是20世纪作家如加缪笔下的“荒诞人”的状态。“他(指莫尔索)极力要在自己身上发现的思想和内心反应(对母亲死亡的悲哀,对玛丽的爱,对杀害阿拉伯人的悔恨),在自己身上却找不到……”(注:萨洛特《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见柳鸣九编《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6页。), 他与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极为相似。尽管萨洛特把卡夫卡当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继承人,然而,在她看来,卡夫卡所继承的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人的交往和对话的大量作品中的唯一例外,即描写交往的彻底断裂和人的真正绝望的《地下室手记》。并且,萨洛特虽提到却未重视《地下室手记》同卡夫卡小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交往已断裂的地下人内心还在继续着激烈的对话和争辩,不同价值的冲突仍在内心进行(即巴赫金独具慧眼发现的“双声”现象),但是,对卡夫卡的许多主人公而言,对话不仅在他与别人之间不复存在,即使在内心世界,也已降到最低限度。“在这极限后面,一切情感都已消失,甚至蔑视与仇恨也已经消失,只剩下茫茫无尽的惊愕,永远的完全的不理解”(注:萨洛特《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见柳鸣九编《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7页。)。卡夫卡预言了这种“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的虽然活着却没有生命的人”的存在,20世纪的文学流派几乎无一不受其影响,而“在现实生活中也好,在文学中也好,似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一类的小说越来越少”;“当代的天才,顺乎卡夫卡这股风……再也看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种人出席重罪法庭受审了。”(注:格勒尼埃语,萨洛特《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见柳鸣九编《新小说派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第2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对话,思想冲突式的心理小说,在20世纪被卡夫卡式的情境小说所代替,这意味着卡夫卡笔下的那种非对话境遇,已成现代文学的不可回避的描写对象。
二、“对话式”复调小说与“对位式”复调小说
如果说在某些情况下,对话已成为不可能或已降到最低限度并非由于作者独白意识过强,而是由于人自身的物化,如果说,在20世纪卡夫卡式的小说已蔚成大观,那么,巴赫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总结出来的,以对话为基础的复调小说,是否已成明日黄花?复调小说是否已失去表现现代人类处境等重大主题的可能性?巴赫金眼中的复调小说建立在对话原则的基础上,如果承认对话乃复调小说的最根本的属性,那么在卡夫卡时代,它的式微当然是不言自明的。然而,答案并非如此简单。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所说的对话,包括主人公之间、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后来,他还将作者通过文本与读者的对话也纳入研究视野而对托尔斯泰刮目相看。前两者是巴赫金对复调小说的规定性描述,然而彼此之间又有根本区别。所谓作者同主人公的对话,只能从特殊意义上加以理解。首先,这种对话是单向性的。作者可对主人公采取“对话”态度,反之却不能成立。主人公可以作为作者心中的“他者”,另一种声音,另一对话主体,但在一般情况下主人公心中的他者只能也是主人公,除非作者化为主人公之一员。其次,所谓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事实上仅指作者的某种自我克制,即巴赫金所说的作者“不背后议论”,不强加观点于其身,面对他们;以“你”相待,把展示自我的机会留给主人公自己。美国批评家韦勒克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提出过质疑。他认为所谓复调中的作者与主人公的平等对话,不过是小说中的“戏剧化”、“场景化”而已,这与他人说的“作者隐退”、“作者的客观化”、 “非个人化”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注:René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Vol.7,p.358.)巴赫金所论述的复调的基本特征即对话性并不能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与其他小说截然分开。韦勒克还指出,这种做法既非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创,也非后继乏人,如狄更斯《艰难时世》中代表不同观念价值的几种“声音”就是显例,而海明威的《杀人者》完全由对话构成。(注:René 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Vol.7,p.364.)所以,巴赫金后来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首创意义”改称“典范意义”,不失为明智之举。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依然感到他对复调小说的几个方面的界说仍未“曲尽其妙”,复调小说的精神实质尚待开掘和阐明。
如前所述,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和海明威的《杀人者》都符合巴赫金的对话原则,后者甚至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更具对话性。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群魔》中却有不少作者对人物甚至写作状况的独白式评介。然而,《杀人者》一类作品,却缺乏某些本质要素使之成为充分意义上的复调小说。巴赫金理论意义上的对话小说,并不足以构成复调。
另一方面,在非对话小说中,作者却可以对主人公采取巴赫金的所谓“对话”态度。让我们再回到卡夫卡。在《变形记》、《城堡》等作品中,作者始终如摄影机般追随主人公,始终让他们在场,从不“背后议论”,也采取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作者对主人公的对话态度”(注: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三联书店,1994年,第122页。)。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的小说中,作者一般都不加评说,不背后议论,把机会留给主人公自己去表现。但这同一态度既可用来“待人”,又可用来“观物”,不同之处在于被提供自我表现机会的主人公是什么样的主人公,是充满主体性的人,还是被世界剥夺了主体性的“物”,以及他们以何种方式存在,他们又如何去呈现自己。
由此可见,无论是以主人公之间的对话还是以作者对主人公的“对话”态度为主的小说,都不能简单等同于复调小说。那么,对话同复调小说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如果说全面的对话性尚不足以形成复调,那么,要成其为复调,究竟还需要什么?这里,复调式多声部的结构要素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具备这样的结构特征,对话小说才可能成为复调小说。特别指出这一点有什么意义呢?这不是巴赫金早已说过、描述过的因素吗?巴赫金不是在论著中多次将复调小说比做音乐式对位结构吗?他不是十分明确地将自己的对话理论在微观与宏观,在局部话语与文本结构等层面作过多方阐释吗?
然而,巴赫金在构成复式音乐的“对位”与构成叙事的“对话”之间,却由于过多地强调了对话而掩盖了对位对复调的本质意义。而只要使用复调概念,对位结构就已作为前提存在于其中。重视对话,充分发掘人的思维和文化的对话性,自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是,从复调小说理论和文学创作角度来看,这种强调,却给复调理论带来某种局限。他在转引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爱的作曲家格林卡“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对位的,也即互相矛盾的”一语之后补充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生活中的一切全是对话,也就是对话性的对位。其实,就哲学美学观点而论,音乐上的对位关系,只不过是广义的对话关系在音乐中的一种变体罢了。”(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第79页。)这一结论似是而非。首先,生活中并非一切全是对话或对话性的对立,还存在非对话性的关系。并非一切都是“同意或反对关系,肯定和补充关系,问和答的关系”(注: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三联书店,1994年,第3页。), 大量存在的仅仅是不同而已。异质并存是对位,而非对话。巴赫金处处发现对话性,不免走入极端和偏颇。正如韦勒克所批评的,当巴赫金将对话无限延伸,甚至声称对话“已进入分子层面和最终直达亚原子水平”,这种对对话的强调已不可理喻。(注:René 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Vol.7,p.369.)其次,把对话看得比对位更为广泛普遍,恰恰颠倒了二者的关系。事实上,任何对话都是建立在对位关系基础上的,对位是对话的立足点。巴赫金本人的理论中有关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哲学论述,其出发点和逻辑起点就是“我”与“他”在时空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形成的视点差异。(注:参见巴赫金《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载《巴赫金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笔者以为,复调小说的最根本的立足点是对位,而非对话,尽管它并不排斥对话。以对位来描绘乐曲,更符合复调概念的音乐本性;以之解释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具有更大的理论涵盖力。
因此,有学者提出了“结构复调”(注: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三联书店,1994年,第185页。)的概念, 我以为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是对思想对话式复调理论的必要补充。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克服非对话与对话的二元对立,在新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复调模式。这一概念仍来源于对托尔斯泰小说的分析。巴赫金将《三死》之类由互不相干的异质成分共同构成的作品当作复调的对立面,即独白体。然而论者认为《三死》所体现的是有别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另一种复调形式,即通过某种命题的一致性将不同故事组成互为对立的复调形式,即“结构复调”。(注: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三联书店,1994年,第185 页。)这部小说中描写的三个死亡彼此毫不相关,不可能形成“对话”,却被纳入作者的主观视野,巴赫金认为这种作法是典型的独白体。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难道不也是由作者的意识加以组织,并同样被纳入作者的主观视野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为了替对话创造条件,要求将人物塑造成“具有伟大思想”、并能有效表达和参与对话的人,但只有在作者有意制造的主观视野中,主人公才如此“单一”地皆成为具有深刻思想和丰富心灵的人物。巴赫金再三强调限制作者的主观性,避免将意志强加于主人公,要在平等对话中将主人公的“他性”特征充分展露出来,然而,对主人公和情节作如此安排,恰恰表现了作者对作品的无所不在的控制。这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淋漓尽致的手法,并不像巴赫金所说的做到了作者与主人公的平等,反而再次体现了作者的无所不能。因此,许多学者都曾釜底抽薪地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话来反驳巴赫金的理论:他在批评一部戏剧时在笔记中写道,“艺术家决不能与他所描绘的主人公处在同一水平层次”。(注:René 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Vol.7,p.369.)
巴赫金对托尔斯泰式“结构复调”的拒绝,或许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认为它们有悖于艺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二是认为这种互不相干的、完成性的结构不能构成强烈的价值冲突和对话交流,缺乏充满张力的艺术生命,“对于阐明生活毫无意义”。在现实中,封闭式的死亡描写的确违背常理。死亡者最后的内心活动不可能被托尔斯泰这样的“观察者”从内部了解到。因此,在巴赫金看来,这样的描写是不真实的、无价值的。然而,这样看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一切文学作品都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任何小说都是一种艺术假定性的运用”(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第15页。)。如果说,依据真实性的要求,作者应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展示由充满主体性的不同主人公意识构成的多元世界,任何人的主体性都应得到尊重,那么,为什么作者就不能直接强化自己的主观性呢?事实上,所谓客观真实只不过是作家主体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罢了。既然文学艺术总是作者的创造物,总是某种客体,无论是充满主观性的主人公还是物化的,丧失主体性的主人公,都是作家主体性的体现。作家可以根据表现对象和主题的需要来加以取舍选择。巴赫金处处强调平等对话,尤其是试图在作者与主人公之间一反常规地构筑对话性的平等关系,与其说是一种诗学,不如说是一种坚定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主张。
由于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建立在假定性基础上,而现代文学往往是承认这一假定性并予以充分发挥的文学。所以,当巴赫金批评托尔斯泰违背现实逻辑地从内部描写他人死亡的心理活动时,卡夫卡却心安理得地让他的主人公在一天早晨莫名其妙的变成一只甲虫。面对现代主义的挑战,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不可避免地须作某种调整和修正。
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一个明显局限是研究对象仅为20世纪以前的欧洲小说,对于同时代的伟大作品却罕有涉及。这固然是由于他所处的特殊社会政治环境,但它不能成为我们在复调问题上裹足不前的理由,也不能阻止我们以现代小说创作实践来检验复调小说的适用度、生发性和艺术潜力。
三、米兰·昆德拉与复调小说发展的现代维度
在一篇题为《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的论文中,娜塔丽·萨洛特阐述了小说发展的现代走向,描绘了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小说到卡夫卡的情境小说的变化,以及两者之间在表现“交流断绝”这一非对话情境上的继承关系。显然,她强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与巴赫金理论阐释相反的特征。另一方面,她又在其新小说理论和创作中努力建构着对话与潜对话的可能性。(注:萨洛特《对话与潜对话》,见《新小说派研究》,第41—58页。)这说明对话与非对话,始终是人类不可偏废的两种基本情境,更应并存互补。
那么,在此基础上,是否有可能消解过于绝对化的对话与非对话、独白与复调的二元对立关系,而在综合层次上建立起更具多声部意味的复调小说?笔者以为,要达此目的,仍须强调“对位”结构的作用。以对位关系为主的复调小说,并不强求作者始终把自己放在与主人公同样水平上来进行对话,也不须迫使各部分之间形成交流碰撞,然而它又不排斥其间对话的可能性。由于对位比对话更普遍更基本,在对位基础上既可形成思想对话也可形成非对话关系。现代复调小说,应是以对位为基础而形成的兼有对话性和非对话性的小说。
昆德拉在论述小说的复调结构时,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与布洛赫的《梦游者》作过对比。从结构上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虽是复调小说的典型,然而昆德拉也从一个侧面指出其局限,即它们的每一线索,每一声部的文体是一致的,而布洛赫小说的革新意义在于五个部分在文体上有本质区别。他将小说、短故事、通讯、诗、论文等纳入复调的方法具有创新意义。(注: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74页。)其实,在此之前的乔伊斯等人的创作中,这种由文体差别带来的复式结构早已存在,如《尤里西斯》异常丰富的文体实验就呈现了斑驳错杂的多声部结构。事实上,与其相信昆德拉所述,把布洛赫小说当作现代复调小说的突破和创新的标志,不如说,现代复调小说的丰富性和表现力在音乐家出身的昆德拉本人的创作中体现得最为充分,最具代表性。昆德拉不仅具有深厚的音乐素养,而且他是有意使用多声部音乐结构来进行创作的,对复调小说具有某种自觉意识的现代作家。他并不像巴赫金那样反复强调“复调”作为一种比喻同严格的理论界说之间的差异性(从前文可知,这种理论界定偏重于对话),而是通过自己的创作证明“用音乐来比附小说并不牵强”(注: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75页。)。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昆德拉,复调小说呈现出其发展的现代维度。
维度之一,传统意义上的独白与复调二元对立的消解。
昆德拉的创作,更接近本原意义上的复调音乐,而非仅限于思想对话。他采用复调音乐中的变奏方法,使主题在多声部中对位展开。在不同的声部中,既有纯粹的独白体,又有地道的复调叙事,所以他的小说不能被单独看成传统意义或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或独白体小说,而是由独白和复调的不同声部组成更高意义上的复调音乐结构。比如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六章中对时世的评论,对历史上的神学问题的探讨,游戏笔墨的噱语,故事情节的开展,人物存在状况的“现象学”分析,不同文体、异质片段的杂然纷呈,独自形成一种复调结构,而它又在整部小说的大复调中担任一个重要声部。结构复调概念的提出者曾用“命题场”来描绘托尔斯泰《三死》式作品。在其中围绕着某些命题,作品复调式地展开。昆德拉小说更推进一步,命题场本身也构成对位关系,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轻与重,灵与肉,《笑忘录》里的笑与忘等命题场成对出现,以变奏曲的形式在多个声部中延伸扩展。这比普通命题场更具复调意味。
维度之二,游戏精神的渗透和对话与非对话情境的相互转化。
本文开头曾颇费篇幅地阐述非对话情境对传统复调小说的挑战,然而,在现代复调小说中,两者并非不能并存互补。在昆德拉小说中,对话与非对话都受到强调。有的声部大大加强了对话,渗透进更多的游戏狂欢精神。在《不朽》中,不同时代的人物,如歌德、海明威,被生死不论地拉入作品进行对话。《笑忘录》中,一群捷克诗人戴上彼特拉克、薄伽丘、莱蒙托夫、歌德的“假面”在俱乐部中对话,仿佛一场狂欢舞会。用巴赫金理论来阐释,这种安排具有纵向横向多层次的对话关系,既包括诗人们彼此之间的交谈,又可与他们的“假面”,即历史上的彼特拉克、歌德们构成亦真亦幻、亦分亦合的意义叠加和对话交流。另一方面,昆德拉又在小说中有意将对话性转化为非对话性成分。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一声部的主体部分是一堆“误解小词典”。它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反对话的。从内容上讲,误解代表沟通交流的失败和对话的破产;从形式上看,词典意味着活生生运行的话语变成凝固僵死之物,正是思想的物化、对话的死亡。
维度之三,复式结构中作者与主人公新型关系的建立。
昆德拉的复调小说不再拘执于作者与主人公思想水平孰高孰低、是否在同一层次上进行对话的问题。这一问题曾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中至关重要。如前所说,此问题成其为问题的前提,是艺术真实性和意识形态性两方面的要求。巴赫金的理论局限于现实主义范围,强调作者态度的客观化,尊重主人公的主体性。但是由于小说的虚构性、假定性的本质规定性,由于无论作家的客观性或主观性皆是作家主体性的体现,于是,以不再被隐瞒的虚构性、假定性为前提和出发点,作者同主人公之间的新型关系的建立也就成为可能。这种更为自由的关系,与复调小说并不矛盾,相反,它恰恰构成昆德拉等作家的复式结构作品的重要组成成分。如《不朽》中,作者与主人公处于一种特异的、悖论式的、逻辑混乱的关系之中。在作品某处,作者暴露自我、直接出面谈论自己构思女主人公时的想法,在另一处作者又叙述自己与某教授相遇交谈,随后该教授又与作者笔下虚构的主人公劳拉邂逅街头。于是,主人公与作者、虚构世界与真实生活世界交织在一起。这种完全违背真实逻辑的“元小说”手法,将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全然改写。不过,与一般“元小说”偏重于“解构”不同,昆德拉的充满悖论的复调小说依然是结构性的,是在一个复调变奏曲的音乐结构中,映现具有悖谬关系的不同声部。
维度之四,开放文本中作者与读者的对话以及多种对话潜能的发掘。
在后期的《小说话语》中,巴赫金走出作者与主人公的特殊关系,从更广泛的说者与听者的对话交流来考察文学作品,因而发现曾被他当作独白体典型的托尔斯泰的小说也具有某种对话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中那种文本内主人公与主人公的对话不同,托尔斯泰的对话指向读者,构成与作为当时社会意识的他人话语的争辩,后期巴赫金似乎认为这种特有的复调非托尔斯泰莫属。(注: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三联书店,1994年,第44和48页。)然而根据这一逻辑,似乎所有的小说都可纳入复调小说。此概念就失去了意义。事实上,我们早已论证了对话性并不意味着复调。上述两种对话都只具有单向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隐退,对主人公采取对话态度,对话则封闭于文本之内,并未对读者开放;而托尔斯泰直接面对读者使用,却又以独断态度议论主人公,削弱了主人公之间的对话主体性,此时,作者对主人公又是封闭的。两种叙事视角皆有局限。那么,能否在这似乎不可兼得的叙事方式基础上达到新的综合,形成一种既对主人公又对读者进行对话的开放性文本?昆德拉小说在这方面也作出一定的尝试。如许多其他现代小说一样,这些作品成分建立在文学艺术虚构性、假定性基础上,并且毫不采用传统小说中的逼真幻觉来掩盖这种文本虚构性。作者在现实世界和文本世界中自由穿行,与主人公、读者、作者自己进行对话,多种形式的对话在复调结构中以一定的变奏曲的形式组合在一起。对情节的叙述,主人公的对话,与读者的讨论,对时事的涉评,对创作动机的泄秘,主题的词义探讨,乃至笔墨游戏、学术考究等等,均展开广泛对话。这些特征在《笑忘录》、《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朽》中皆有出色的体现。
在20世纪众多小说家中,昆德拉是位兼有创作和理论上的复调意识之自觉,对复调音乐具有实际操作能力和透彻理解的作家,他的小说因而成为体现现代复调精神的成熟文本。它们与20世纪仅受到复调小说或理论的弥散性影响的那些现代小说是不同的。作为现代复调小说的典型形态,其建构意义值得充分重视。从前文可以看到,昆德拉的复调同巴赫金所阐释和凸现的陀氏复调已有很大差别,这也是世界文学现代转型之体现。巴赫金曾反复强调“复调”只是个比喻,它具有比喻的一切模糊性、相对性、近似性和多义性,不像一种纯粹建立在演绎基础上的理论界说那样逻辑严密、概念周全。但是,正因为它是一种比喻,却也保持了它的全部丰富性、弹性和艺术潜力。只有在一种自由开放的意义上理解和运用复调理论,才能更好地突破其局限,更大限度地发挥其艺术潜能。对此,复调小说的现代发展提供了颇有说服力的证明。
标签:巴赫金论文; 小说论文; 复调论文; 文学论文; 小说的艺术论文;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文; 变形记论文; 杀人者论文; 托尔斯泰论文; 主体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