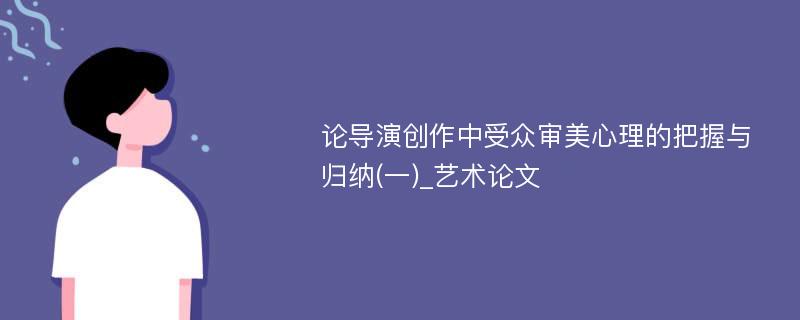
谈导演创作中对观众审美心理的把握与诱导(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诱导论文,中对论文,导演论文,观众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戏剧创作是为观众而存在的。没有观众,戏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一件艺术品的生命,不仅仅是由创作它的艺术家赋予的,也是由欣赏它的观众赋予的;艺术生命的延续,要靠观众的不断欣赏。”(《戏曲通论》第604页)戏剧的演出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创作,是依赖了作为审美感受的艺术欣赏,才能成立的。因此,戏剧创作必然要受到观众的制约。可见,注意处理好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关系,有效的把握、诱导观众的审美心理活动,树立观众创造性的审美观念,是戏曲表、导演艺术创造中,不可忽视的环境节;也是艺术家实现对观众审美感受的预见性成败的关键。
(一)
意象创造是戏曲处理与观众关系的独特方法。
什么是戏剧?说到底不过是指用不同的艺术手段、方法,来处理舞台艺术创造与观众的关系。
正是在处理这种关系上,中国戏曲艺术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见解,即采用意象创造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本质特征集中表现在戏曲对现实生活的不同美学评价及对舞台艺术真实的不同认识上。戏曲艺术对现实生活的不同评价表现为它在处理客体物象与主体情志的关系,在意象组合上(即主体情志与客体物象在对立统一中位置的摆法)是把意放在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把象放在矛盾的次要方面,是简于象,深于意的。戏曲舞台上所反映的决非是生活表象的东西,是度物象而取其真(对于事物本质的理解)。它不主张停留于对客体物象外在形貌的模拟,而是着重对客体物象深奥、精微的内在实质的探求。因此,在提炼生活的方法上,它不要求如写实戏剧那样模其形貌,依其规旨,一切求真、求是、求实,而是采用遗其形迹,取其神质的法则,以意为主导以象为基础,追求一种意象(物我)交融的境界。一切求象、求似、求意。艺人所说“虽则为戏,意当为真”正说明了中国戏曲不求实而求意的美学观点。中国戏曲美学所以被称为潜美学,正是由它的写意性所决定的。它是站在生活之上从上而下来俯视生活现实,突破了生活的自然形态,获得了广阔的创作自由。戏曲如果没有区别生活自然形态的自由,其舞台艺术真实就会失去鲜明性、感染力和表现力。正是由于这种自由,所以在戏曲艺术方法形成的过程中,在区别自然形态时,它不仅夸张了,而且有意识地改变了生活现象的外貌:由生活对象的具体(个别)演变成类型意象的抽象(一般)从而形成了戏曲的程式、行当、自由时空等表现手段和方法。最后在具体的形象创造中,再由类型意象的抽象转变为个性形象的具体(个别)。这样变化的结果,并不会失去它的现实主义。这是因为戏曲重意并不意味着不重视象,而是主张在现实的象的基础上,创造出更惊人的艺术的象来鲜明地表现意。在意象关系上,是既强调意(主体情志)的能动作用,又注意着客体物象的制约的。
戏曲意象创造的具体特性,体现在两方面:
(1)“得意忘象”、“立象存意”。
戏曲的意象创造方法,是戏曲艺术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并已成为了指导戏曲创作实践不可动摇的美学原则。
意象说源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体系(戏曲美学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戏曲中意象间辩证关系的特定性,是以传统的哲学思想为其依托的。戏曲审美意识的理论形态是离不开中国哲学思想传统的,它直接影响着中国人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戏曲的创作实践和美学思想上直接导致了意象交融的创造方法这一独特优秀传统的产生和发展。纵观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清代前期中国美学史上的三个黄金时代,无例外的都受着这种传统哲学思想体系的影响。
中国古典美学是以意象为中心的。意象的出现是魏晋南北朝,但它源于《易传》的“立象以尽意”。我国魏时的玄学家王弼曾说:“存象者,非得意者也。(照搬生活,不可能反映生活本质)象生于意,而存象焉,(为了艺术地反映生活,而以生活为依据的话)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这时就不是自然形态的真实了)。又说:“然则忘象者,乃得意也;……(这时虽不是自然形态了,但却反映了生活的本质真实)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艺术反映生活,又不是一般无二的再现)仔细体味这些话:存象非得意,忘象乃得意,尽意而象可忘。似乎正说中了戏曲意象创造的独特性及写意特点。它是要突破孤立的有限的象,由有限进到无限。是象外之象,是有无、虚实的统一。“得意忘象”要主观的表现得之于“象”的“意”,而“意”又是主观对客观的抽象认识——抽“象”而得“意”,写“意”又要舍“象”。戏曲主张一但从真实生活中获得了“意”,就不去模仿生活的本“象”了,而是去创造装饰化的艺术的“象”,(也即艺人说的“不象不成戏,真象不是艺”)。从而在以意为主导,以象为基础的基本规律的作用下,在人物形象创造、戏剧环境处理等方面达到主体情志与客体物象的对立统一。
我国南朝齐肖像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曾说:“若拘以物体,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餍膏腴,可谓微妙也。”魏晋南北朝的画家宗炳讲“澄怀味象”、“澄怀观道”,主张审美观照不是把握物象的形式美,而要把握事物的本体和生命,故要取之象外。正如宗白华所说:“艺术意境的创构,是使客观景物作我主观情思的象征”因而不是“固定的物象轮廓所能表现的。(见《美学散步》)”明代的徐复祚在《曲论》中说的就更清楚了,他说:“要之传奇皆是寓言,未有无所为者,正不必求其人与事以实之也。”综上所述,通俗讲即戏曲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但变了艺术之后,已不是现实生活的自然形态的再现了;这时的舞台艺术真实是高度的生活真实与高度的艺术真实的统一体了,也即真与假的矛盾统一。这正是戏曲“得意忘象”、“立象存意”的美学思想的实质。
(2)“虚从实来,实力虚在”。
中国戏曲艺术把生活和艺术划分为两个性质不同的范畴,生活是实,艺术是虚;艺术创造的过程即由实生虚的过程,也可以说是用虚来表现实的过程。为什么说艺术是虚?这是由戏曲意象创造的独特性所决定的。正因为戏曲认为艺术并不是对生活的模仿,而是用来表现艺术创作者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也就是说艺术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是经过艺术家改造过的生活,是在生活之实的基础上溶入了艺术家之意的结果。就戏曲艺术来说,没有实,生不出虚来;没有虚,不成其为艺术。因此,戏曲是在以实为本,以虚为用;虚由实来,实仗虚行这一戏剧美学思想指导下,来形成特殊的戏曲舞台艺术真实的概念的。
王骥德在《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上》中说:“戏剧之道,出之贵实,用之贵虚。”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谈真则易,说梦为难,非不欲传,不能传也。”(梦即是虚)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也说:“……弟传奇多梦语。”“因梦成戏”、“用之贵虚”正是戏曲意象创造的美学思想的体现。戏曲的舞台艺术真实的概念,是以既要虚又要实的美学原则为基础的,它认为“虚而不实必浮”(脱离生活真实,错误的理解艺术的真实要陷于形式主义,不可能深刻动人);“实而不虚必浊”(机械的摹仿生活,错误的理解生活真实要陷于自然主义);“虚从实来”(艺术创造以生活真实为依据)、“实为虚在”(现实生活为艺术创造提供了泉源)。这样的美学原则,就决定了戏曲艺术在表现生活时,必须采取借假演真,弄假成真。总是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虚实难辩,真假难分的。在戏曲艺术创造中,演员与观众徘徊于实感与幻觉之间,形成一种意化的生活幻觉,演员半真半假的演,观众用感觉联系的方式看,形成一种“程式的间离性与传神的幻觉感的结合”(阿甲)共同完成、欣赏着剧本规定的任务。这就是似与不似之间,这种浪漫与现实的结合,正是中国写意派戏曲美学的传统及审美准则。
当我们对戏曲意象创造的特性,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再来认识意象创造与观众欣赏之间的关系就便易多了。
戏曲舞台艺术的真实性是紧紧地依靠观众的逻辑判断和生活联想来完成的。意象创造所达到的似与不似之间的写意性,巧妙的为欣赏者安置了联系生活的线索。艺术家的意不是孤立于社会生活之外的,他的意和观众是相通的,作为社会成员的共同的生活经验,是它们之间相通的中介和桥梁。艺术家的形象思维物化为艺术时,它的审美价值还是潜在的功能,只有和观众的联想活动结合时,它的审美价值才转为实在的功能。正由于戏曲的意象创造解脱了一切固定性和写实性的束缚,扩大了生活表现的范围,这就不但丰富了创造者的艺术想象,同时给欣赏者联想作用(美感经验)的发挥提供了用“武”之地。更由于戏曲用虚拟的手法来概括生活,这同时也为观众想象的活跃创造了契机。朱光潜先生说,想象是欣赏过程中关键性的活动。王朝闻先生说,想象是“审美反映的枢纽。”正因戏曲采取了立象存意的美学原则,所以在具体的艺术创造中就不必做尽道绝,而是留有余地,让观众去猜想,以便点醒他们用自己的想象去补充表导演艺术创作中的空白。
精心设置“艺术空白”,是引起观众审美想象的重要关键。如果说生活是蕴蓄艺术家想象力的土壤,那么他设置的“艺术空白”也应该是激发欣赏者想象的一块“弹跳板”;没有基于欣赏者的联想作用而产生的想象力,就不能从作品中“跳”得很高。他们的审美感受,也不会得到升华。
《太平广记》“平曾”条载唐人平曾所献的《白马》诗,其中有两句“雪中放出空寻迹,月下牵来只见鞍”。诗人写白马却不写白马本身,只写雪与月,在马蹄印与马鞍之间留出“空白”让人去嚼味思索,用想象来补充白马的形象美。读者在“艺术空白”的感觉中体验的美,要比直观中的美感更含蓄、更凝炼、更强烈。南宋张炎曾说:“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词源》下卷)。所谓清空即指清虚、空灵。因此在戏曲导演创作中,不仅要千方百计发挥其自身的想象力去发掘隐藏在生活中不易发见、不易道破的本质特点,曲折地揭示事物内在的美感;而且,也要求导演能掌握戏曲意象创造的特征、规律,远用独创的技巧,来启发、诱导观众的想象力,调动他们对生活的感受(美感经验),来补充作品的艺术意境。当这两种想象力融合一起时,便会产生出强烈的思想、情绪的共鸣,这就是艺术魅力。
没有观众的想象也就没有完整的戏曲创作。而戏曲意化生活幻觉的方法,不仅有效地调动了观众的逻辑判断、生活联想,从总体上也对观众审美心理的活跃,起着不同程度地控制与诱导作用。所以说戏曲用意象创造的方法来处理与观众的关系,高明的很。
(二)
戏剧艺术创造中形象思维的规律,决定着戏曲创造与审美欣赏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个完美、真实的戏曲舞台艺术形象的诞生,仅仅通过二度创造的过程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导演对观众审美心理的把握、控制、适应与诱导;必须把观众的理解、联想,估计在完成剧场效果的因素之内。
所谓审美心理,就是指观众欣赏戏剧演出(或自然美及其它艺术品)时,所产生出的一种愉快的心理体验。这种体验,是观众内在心理生活与审美对象(戏剧演出)之间交流或互相作用后的结果。审美心理是一个系统结构,是多种元素融合而成的整体。多种元素或同类相辅,或对立互补,互相作用,互相制约。它是一种高级的精神现象。是一种涉及着多种高级心理功能的复杂心理状态,而并非是一种单一的“刺激——反应”。它主要源于视觉和听觉对象的和谐。它虽不同于生理感受,但又离不开生理感受;它不同于逻辑判断,但又离不开理性认识;它要涉及情感、想象、理解、联想等多种心理功能才能构成一种精神的和情感的评价。可见,在戏曲表、导演艺术创造中,观众的创造性参与是完成形象塑造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总体看表、导演的舞台创造过程,也即从理性指导到感性形象的产生,只完成了创造全过程的一半。另一半即从感性的接受到理性认识的复归,是由观众的创造性参与来完成的。
舞台艺术创造中的感性形象,是导演、演员经过对剧本、人物的分析、理解之后在理性指导下产生出来的。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的感受、体验、思想、情感,也包括了导演、演员对剧中生活的态度和理解。创造者的主观世界是通过剧中人物思想感情的折光而反射出来的。舞台艺术创造中,理性的指导与感性的形象二者是统一的;情与理是不可分割的,总谓之意(情与理的融合)仅创造出感性形象若从戏剧艺术创造中形象思维的规律而言仍未完成创造的全过程。因为在对艺术形象的观赏中,观众眼睛对具体形象、景物直观的终了并不意味着艺术感受的终止,而是导致欣赏进入一个更为深邃的思想感情方面的领悟。这种深邃的领悟,即从感性的接受到理性认识的复归。至此才算完成了艺术创造的全过程。而这一复归过程的最后完成,是离不开欣赏者的参与的。
唐代诗论家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曾以“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论诗。“象外之象”中的前一个“象”指作品本身的艺术形象,即艺术作品中所描绘的物象;后一个“象”是读者依据作品所描写的具体形象,通过想象和联想重新创造出来的意境和形象。虽然司空图本人也说:“……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但他透过这恍惚的用语确实抓住了艺术形象和艺术欣赏的两重性。
如温庭筠的《商山早行》诗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句,它并未向人们直言旅人的辛苦和艰难,而是将这种感情不露痕迹地深化在诗句所揭示出的空间和时间结构中,“鸡声”,“月”、“霜”、“茅店”、“板桥”组成了一幅现实的时空图画,创造了又黑又冷的早晨氛围,刻画了荒村野店的环境特征,它们一经与“人迹”细节并列间接地点出了人物的行动——行路;又组成了标示内在情感生活的运动形式的内在图画。诗人没直说羁愁,但通过欣赏者的理解、联想、想象的深邃性领悟,使欣赏者强烈感受到早行羁愁的意味。这一切的综合使欣赏者体验到行路辛苦的愁思。羁愁之思的象外之象就是这样产生的。这象外之象的产生,若离开欣赏者的联想是很难完成的。这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是象、景在欣赏者的意识中激起的反映,它是艺术形象的一种间接性境界。在欣赏过程中艺术形象由直接性向间接性的转化即意境产生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完成离不开欣赏者的创造性参与。从欣赏角度来说,艺术形象的实处提供对象的直接性,虚处则提供间接性,两者在欣赏过程中结合起来,就能充分调动欣赏活动的积极性。从此意义上说欣赏者也是创造者。欣赏者不只是用眼、耳直观艺术形象,并且还在想象中对它进行再创造。没有想象的再创造,欣赏者只能直观到艺术形象的感性外壳,无法神游于它所反映的生活境界中去并从中完成理性的复归,得到教益。
在艺术创造中没有实(直接性)就没有艺术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具体性、形象性,“实”是引起观众定向联想的契机;没有虚(间接性)观众想象的双翅也就飞不起来。虚为观众审美创造提供了较自由的想象空间。戏曲意象创造中,虚处由想象所创造的形象并非是唯心的,作为结果虽然是欣赏者想象的创造,但是作为原因早已包含在直接形象之中了。因为戏曲的意象创造只要求幻觉给想象留有余地,而并非全部由想象来代替幻觉。这就是意象创造的现实主义之所在,它是“虚从实来,实为虚在”的。如果说艺术创造中的虚处给观众的想象以回旋余地的话,那么实处则给想象以活动的根据和范围。当实的形象与虚处留待想象创造的形象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时,实的形象就有了启发性和指导性。因此说,戏曲创造与审美欣赏之间相互依存的特定性,正是由艺术创造中形象思维的规律所决定的。
(三)
戏曲意象的创造规律,决定着戏曲创造与审美欣赏的相互制约关系。
艺术形象的创造,不能离开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法则。在戏曲舞台上,基于演员的努力在观众的感受中把可见的东西与不可见的东西联系起来,使有限的形象具备生活的和思想的广阔而丰富的内容。而这种联系不是演员可以单独完成的,必须依靠欣赏者的“合作”。
有一文学掌故可以启发我们的理解: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是一个花鸟画能手。他常常以诗句为题,让应考画家按题作画择优录用。有一次他以“深山存古寺”为题招考天下画家。看到画题,难住了画家们,古寺藏在山里,怎么表现?若画在画面上,又怎么体现这个“藏”字呢?人们按照各自的意图绘画的结果都没有丢开那座古庙,只不过是有的画了整个寺庙,有的画了一角。分别隐现于山岭间、茂林中、峡谷内。只有一人画法不同,他既没画整个古庙,也没画古庙一角,而是只画了一个老和尚肩挑一副水桶到山下水势澎湃的溪间来挑水。结果就是这一张没画出寺庙的画儿却得中了。画面上虽未出现庙宇,一个老和尚下山来挑水,使人一下就会想到山里存有古庙,在山下又看不到,使人想到它是在深山里。可以说这幅画是“意在画外”,作者作为高明的注意依靠并调动了欣赏者的“合作”,使人思而得之。正如王骥德评《还魂记》(《牡丹亭》)所说它是“以虚而用实者也。”并说“以实而用实者易,以虚而用实者难。”这话是有道理的。
戏曲意象创造的方法,使戏曲创造与审美欣赏的对照关系表现的更为直接和明显。由于戏曲的写意性、虚拟性特点,就使得在没有借以进行动作的那些实物对象的条件下,凭演员的想象做出实物动作。舞台上没有门,但要真实地合乎逻辑地做出开门或关门的表演;舞台上并不存在江河、水流、船只和风浪,可是演员的表演要表现出在有河、有船、有风的规定情境中行为的真实性。这些在想象的环境中的表演反过来又引导观众在想象中出现河、船、风的景物形象并神游其间,舞台于是就成了变化万千的美妙世界。诸如扬鞭代马,摇橹象渡,张布为城……这些直接的表现,一方面需要演员在想象中创造,同时又需要欣赏者通过自己的想象使舞台上的间接表现经过形象思维的丰富、补充、理解、联想而收到具象真实的效果。如《马踏青苗》的趟马,一根马鞭随着演员的各种虚拟的舞蹈动作,在观众的想象中立刻出现曹操的坐骑在麦田坑坎中惊跑及人物急于将马治服的景象;《白蛇传》水斗中几面饰以水纹的水旗在演员手中一抖动,观众的想象中倾刻出现江海翻腾、白浪滔天的境界。这就是戏曲艺术创造与审美欣赏的相对照的制约关系。
这种对照关系由于戏曲艺术强烈的剧场性而更直接、鲜明。
在戏曲舞台创作中,舞台是被当作演出场所来理解和使用的。舞台空间不表现为某一地,演员就在空舞台上进行创造。通过演员的表演,舞台就不再是空的了。或山、或河、或花园、或楼台、或殿阁、或战场……充满了不同的生活景象。这些景象,是演员创造的结果,也是观众想象力作用的结果。加之演员在创造过程中坦白承认是在演戏,并大胆地承认观众的存在,认为观众不仅是艺术的欣赏者,也是在感受上的艺术形象的创造者,是戏剧创作集体中的一分子,其地位不只是事变的见证人,也是事变的裁判者。观众在欣赏过程中不只依靠感觉、直观、想象,而且也依靠相应的分析、判断,当然分析、判断——这种理性活动的产生,仍然来源于直接感受。因为人类的情感生活,是一种能动的结构,对于这种结构,不能直接用逻辑的推理去理解,而只能在直接感受中把握。戏曲意象创造中“虚”与“实”之间的对照制约关系,实质上是个别偶然与一般普遍的关系,只有当“实”与个别偶然相联系,“虚”与一般普遍相联系时,理性的成份在审美反映中才发挥作用。这时审美中的感知因素就成为了导向审美经验的出发点,理解为它指明了方向,情感成为了动力,想象为它添加了翅膀(或扩大了范围)。当这四种要素以一定比例结合起来,并达到自由谐调的状态时,愉快的审美经验就产生了。这就使艺术欣赏有了再创造,再评价的特征。因此,在戏曲表、导演艺术创造中要设法激发观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调动观众的创造积极性,使自己的创造在观众的参预下最后完成。
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精神活动,但二者通过戏曲意象创造的精神交往,就可形成一种神遇、心悟、契合的神应思彻、互相依赖、彼此对照的制约关系。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