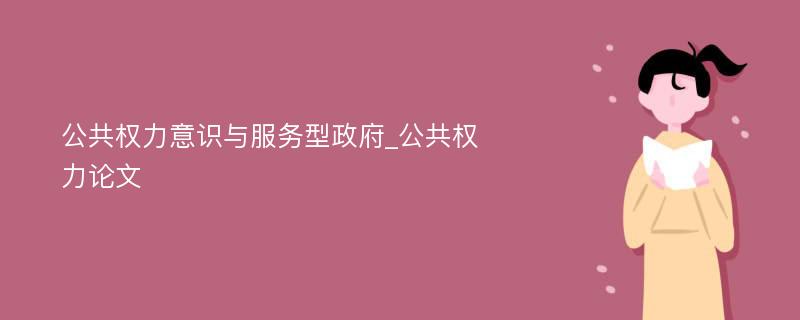
公共权力意识与服务型政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力论文,意识论文,服务型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0X(2007)03-0005-04
变革成了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基本特征之一,各种观点和新潮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各种现代交往方式占据了显著的位置;新的话语不断产生,无论是激进的还是颓废的,取决于人们自己的选择;人们对于别人看去不可思议的选择给予极大宽容,甚至无暇去顾及。在这种大众文化变化的背后则隐藏着公共领域的悄悄变革,这种变革的范围、程度及其影响可能超出了我们已有的判断,但公共服务领域仍然是人们抱怨最多的领域,人们会抱怨公共领域条文中美丽的词汇为什么不能在现实中展现它们的内涵?为什么媒体中公共管理者的形象会与自己身边的形成巨大的反差?为什么民众有许多良言计策却无法去创造更多一点的公共价值?这些抱怨表明人们心中有一个或是模糊或是清晰的更美好社会、更加理想的图景;另一方面仍然必须从公共服务领域中去寻找原因。这种努力不仅是学者、民众,事实上直接在公共领域工作的许多人也在努力。提出和实践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意寓可能是十分深刻的,公共服务的理念具有跨越意识形态的差异,更加平和和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日益全球化的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可以比以往的统治、管理和治理等更深入人心,它正塑造着公共领域新的话语体系和美好图景,但公共服务的寓意更大程度上乃赖于人们进一步去解析和建构,并且在无数的公共服务实践中加以创造。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公共权力的改革是公共领域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重新检讨公共权力与私权力的关系,重新界定公共权力的主体、范围、结构、形式和运行机制,至今这场改革运动并没有停止,而是不断引向深入。从文艺复兴以来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不断地为私权力的应有地位和合法性而提供种种理论支持;新公共管理理论不仅大加赞扬私权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并试图能用这些成功经验来改造公共领域,改造在公共领域中占核心支配地位的公共权力,用企业家精神重塑政府,企业化政府、市场化政府、解制式政府、分权化政府和多中心化政府等都是与此相关的理论,但公共领域的问题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公共权力也几乎被批得“体无完肤”而令人产生了有点厌烦去谈论公共权力的感觉,甚至似乎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可以绕开公共权力而从现象学、构成主义、话语理论中就可以富有自觉、全民性、带着真诚、参与式地解决,“以超越和包容现在的体制、组织和官僚制度”[1] 77。对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理解和图景建构至今已经有许多富有见地的成果,谢庆奎教授在总结近些年国内关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理解时,认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四个特征:民主和责任的政府、法治和高效的政府、实现合理分权的政府、为全社会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政府[2]。也有的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模式归结为七种:民主政府、依法行政、有限政府、廉洁政府、守信政府、创新政府和学习型政府,把服务型政府看作一种全新的政府运作模式,是以全新的服务理念为支撑的政府[3]。珍妮特·V·登哈特和罗伯特·B·登哈特教授阐述了新公共服务的基本理论内涵,其中心转向了以公民需求和公民权力所主导,而不再是为顾客信条所主导[4]。张康之教授认为当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超越了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时候,法律和道德就不再是工具,而是一种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模式,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甚至可以看作是人的本质[5]。但这种治理模式社会的来临需要一个建构过程,需要对公共服务型政府内涵的丰富和深化,需要公共空间的净化,需要公民公共权力意识的充分觉醒为前提。
对于政府传统组织结构的批评几乎是所有现代公共组织理论与组织观点的一个逻辑起点,但传统组织结构仍然十分顽强地在目前的公共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庞大的结成网络的无处不在的既定组织面前,人们的抱怨经常是苍白无力的,因为既定的组织在使我们不满意的同时,恰恰又是它在提供着各种满足。这也是传统公共组织形式几乎都会被认为与保守、官僚、迟钝、抑制创新联系在一起,并且它力量强大到只要没有从内部产生改革的愿望,外部一般化的力量不足以改变它的行为惯性。以理性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外部的力量想让传统的官僚组织作出自愿性调整都更多的是这种组织自身意识到,并愿意主动地作出改变的选择。提出并建构公共服务型政府便首先是这种意识的结果,而这种意识是源于对公共权力意识的变化。
公共权力意识是什么不容易说清楚,公共权力意识指向的是什么则可能作出判别,而公共权力意识指向不是什么则是容易作出判断的。使用公共权力的目的如果是为满足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同时有损于他人或其他团体的合理利益的倾向或结果,则不是公共权力意识的指向;对于公共利益受损和公共权力的滥用现象无动于衷、视而不见、冷漠麻木也不是公共权力意识的指向;对于公共组织包括政府部门出现了问题幸灾乐祸、甚至是推波助澜也不是公共权力意识的指向。公共权力意识有三层含义:一是公共责任,所有公民对公共事务都有一定的责任,相应的所有公民都有一定的公共权力,公共责任与公共权力是不可分;二是使用公共权力源于自身,但以多数人的利益为目的,在最大限度上不去损害少数人的利益,实现帕累托改进;三是公共权力的重要性应当得到正面、充分的认识,应有如它的重要性那样得到应有的重视,充分意识到公共权力对于现实生活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影响,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核心软资源,对经济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起着催化作用,有时甚至是支配作用。
对于公共权力的解析有各种视角,有运用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来解析公共权力,如公共选择理论;有从工商管理途径来研究公共权力,如企业家政府理论;也有从语言和现象学的视角来认知公共权力,如话语理论。但在这样的过程中公共权力意识没有被十分清晰地、热情洋溢地给予恰当的激发,人们追求公共权力却常带着模糊的公权意识,或者只有私权意识,公共权力常在一种曲解的情况下被利用。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无法避免奥尔森的“集体行动困境”,经常会钻入“阿罗不可能定理”圈套,不知不觉地走向哈丁的“公共池塘悲剧”的一个原因。一些人对公共权力爱不释手,所得到的是私权力运作规则的训练和教育;再加上不少公共权力实际拥有者正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公共权力,就更喜欢那种私权力的游戏规则和心理预期,甚至会暗喜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为他们如何用公共权力满足私欲、为个人谋私利出谋献策,且心安理得:原来如此!于是公共权力离它与生俱来的目标越来越远,在公众面前显露出来的已经足够让许多人失望,更不要说许多的潜规则所指导下的网络式暗箱操作行为;更有学者断言,“恰恰是这种东西(指潜规则),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6]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过程实质是对公共权力重新进行界定,重新确定公共权力的范围、运作模式和功能,无论是用法律的、政策的方式,还是道德的、伦理的方式,它们所调整的核心内容都是公共权力及其作用场。福克斯讲到在美国“尽管传统治理模式已经死亡,尽管学术界不停地为其举行送葬仪式,但其灵魂仍徘徊于公共行政研究的上空,并在所有的管理理论方面以及在几乎每一个实际的公共机构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1] 4虽然再也不可能去为传统官僚体制唱赞歌,但也有学者认为现阶段行政体制建设的目标仍是“完善科层制”[7];“科层制管理方式不仅现在是,而且将来也会是把千万人联合在一起去完成重大任务的唯一有效的组织方式”[8]。这里无意去评价传统公共组织模式的优劣,而是认为公共权力仍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过程中的核心主题。从某个意义上说,市场体制与市场力量的基础不在于市场本身,而是在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市场意识和公共权力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界定着市场的开放度和成熟度;同样支撑公共服务型政府不在于政府本身,而更多地在于政府部门与公民的公共权力意识。
制度缺陷、制度供给不足经常成为解释公共权力滥用的理由,但在“前腐后继”式、“网络”式和“集体”式腐败中从来不缺乏熟谙法律条文并直接与严格而又明显的法律规定相违背行事的“社会精英”[9]。“规章只会引起更多的规章;语言的歧义性使其无法作为一个充足的工具,来完全控制官僚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规章越多,对官僚行为的控制力就越小;从外部产生的规章总是与偷换目标、敷衍了事、按规章办事这样的官僚病联系在一起的”。“暂且不说人的行为太复杂多变,要将其束缚在文字规范中几乎是不可能的。”[1] 14,19这一点正如有“第一义不可说”、“我向尔道,是第二义”[10]。如果由于语境的差异、词汇的贫乏、有意的曲解、社会科学知识的不足、乃至智力结构的缺陷,很多时候连“第二义”也还难以达到。不同的意识指向就可能会对同样的公共权力做出截然不同的解释,而公共权力意识被扭曲的人就难以对公共权力作出属于它本应有的意蕴的理解。在一个公共权力意识扭曲的公共权力场中就十分容易看到这样的现象:思维前后矛盾、行动逻辑混乱、言行表里不一、拥有财富和社会地位却依然并不快乐、甚至不知道他们究竟要的是什么。扭曲的公共权力意识与公共权力本应有的规则发生了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会让人彷徨不定而产生焦虑。在乎短期感觉、追求虚浮夸、满足占有欲成为减轻这种焦虑的缓解剂,但公共权力意识扭曲这一病根如果没有祛除,缓解剂便永远都需要。在公共权力意识这一容器里装的不应是私权力及其规则,而应是公共权力意识,包括公共权力本身所应有的系列规则,这些规则不是私权力的一般性规则可以代替的。
对于当今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公共权力都是极其宝贵的具有创造价值的稀缺资源,是一种可以支配其他社会资源价值分配的力量。公共服务型政府提倡把使用公共权力看作是公共服务,可能会使人们轻视公共权力的作用,但权力本质上就是权力。对公共权力轻描淡写、淡化民众对某些公共权力的关注是许多公共权力实际拥有者惯用的做法。“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是让普通百姓不去想朝政之事吗?不去想它,不去探究它,又怎会知道公共权力使用的好坏,又如何培养他们的运用公共权力的能力?为什么会出现福克斯、米勒所描述的情况:“我们(在公共行政领域)的政治大师们所展现出的行为总是与江湖郎中、煽动分子,有时是骗子联系在一起,他们在虚假但却耀眼的人民意志的旗帜下阔步前行。”[1] 25公共权力意识的扭曲使得一些“政治大师们”认为那就是政治艺术,而他们的跟随者很多时候还会佩服得五体投地,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如此,那些被蒙上眼睛和耳朵的虔诚的民众则也一次又一次用自己的行动在纵容或鼓励着那种“艺术”。如果说有时还不是太露骨的话,那是因为在公共领域中确实有一些以民众利益至上的、公共权力意识很强的政治领袖和公共服务者,也确实有一些不那么轻易放弃公共权力意识的民众,哪怕这种公共权力意识被淹没在私利场之中。多数行为都是经过长期养成、是由潜意识支配而能不假思索地行动的结果。
福克斯认为“美国官僚极力从中推出的其伦理学的政体规范是正在消失的参照物。它们犹如海市蜃楼和彩虹,当我们接近时就消失无踪了。”[1] 29我们经常碰到的情形是正在着力去学习与仿效一种模式时,那种模式又被更替了,更为关键的是在一种参照系已经建立之时,它所赖以建立的意识基础就已经在发生变革了,所以如果没有在意识上的变革,学习任何别的模式都是落伍的,任何参照物都可能是一个陷阱,学习了一种既定的模式就可能因这种模式而抑制了在新的土壤原本就可能产生的意识。正如在技术领域,当一个技术在市场上很流行时,就意味着这个技术将为新的技术所取代,一个小公司可以靠模仿别的公司的技术而获得一些市场和利润,一个大公司则是困难的。一个大国的政体规范可能也存在与此相似之处,参照、模仿现成的模式或仅停留于既定的模式都意味着落伍。诺顿·E·朗认为行政管理的生命线就是权力,但在各种因素中,它在理论上最不受重视,而在实践中忽视这个问题又是最危险的。[11] 话语理论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话语的主题,对于公共领域而言它的最重要的话语主题是什么呢?无论是公共伦理、公共道德、公共精神、企业家精神,还是参与精神,无不关注的都是针对公共权力这一主题,离开这一主旨这些议论不会发生,也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
建构公共服务型政府理论需要认真思考几个问题,如果一个政府模式的建构离开它存在的基础——公共权力又将会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对公共权力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假以私权力的规则又如何去建构以公共权力为基础的政府呢?而如果不去正视过去存在的问题或截然地去否定政府过去的成功之处,又怎么可能来建构更富有魅力的未来政府模式?公共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民众的参与,而公众参与的首要前提是公共权力意识的充分觉醒。由公民的自觉责任意识、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等所构成的公共权力意识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语境基础,是公共服务自觉行为的前意识,也是培植公共领域优秀管理者重要的土壤,它对于公共领域人才辈出的作用可能超过任何学校和专门培训。公共权力意识的觉醒既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社会前提,也是它的过程指向。
值得担心的不是传统公共组织变革的惰性和思维定势无法祛除,而是能否在足够短的时间内找到一条真正适合的新途径。“废除一条旧的思维定势(或者叫范式)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找到一条新的来取代它。”[12]“如果一辆汽车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行驶,你怎样给它换胎?”[13] 变革公共组织也有如给一辆快速行驶着的汽车换轮胎,我们不能让它停下来进行诊断而决定采取怎样的行动,我们必须是在它不断往前发展的过程中采取措施。这也是为什么公共组织的改革比私部门的改革更难的一个理由,并且它可能导致政府治理体系改革可能由此深陷“卡夫丁峡谷”之中。[14] 而避免政府行为模式选择陷入“卡夫丁峡谷”之中,一是要避免拾捡语言、观点与模式的碎片,很多学者早就警告一个国家成功的行政改革的做法在另一个语境环境下却可能导致的是失败;二是要清醒地知道时髦语言的有限性,没有多少文章中的词汇有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以民为本”、“民有、民享、民治”这些词汇更能让人心灵神往了;三是正视现实,对于政府改革而言,必须从政府行为的核心——公共权力入手,应充分意识到它,解剖它,研究它,认识它,亲近它,发挥公共权力充分的正面功用,它应该不是某个阶层所特有,不是停留于学者的著作中,也不是只有少数人才会操作它,它属于大众,大众有责任去建构它、维护它,也要如同爱护私权一样去爱护它,否则勾画出来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则只能是空中楼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