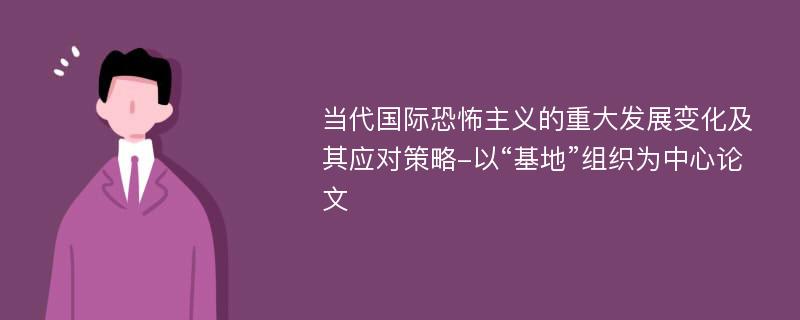
【社会治理与控制】
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重大发展变化及其应对策略
——以“基地”组织为中心
□兰 迪,刘思彤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710016 )
摘 要: 虽然尚处在“蛰伏期”,“基地”组织仍是我国目前难以忽视的巨大威胁。“基地”组织的发展变化受到两个因素影响,一是自身面对国际反恐怖力量打压下的结构转型与策略调整,二是其与“伊斯兰国”之间“合作—竞争—再合作”的关系变化。“基地”组织的危害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基地”组织的网络化、分散化的组织结构与本土化、“独狼”化的行为模式给诸多恐怖组织以“灵感”仿效;第二,“基地”组织与日渐衰落的“伊斯兰国”可能出现合流的趋向,从而形成国际恐怖主义的合力,进一步加大对国际社会安全的冲击力度。“基地”组织的发展变化将为我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严峻威胁。在应对以“基地”为首的国际恐怖组织的“转型”与“合流”问题上,必须坚持“预防与惩治并重”“治标与治本兼顾”的总体治理思路。
关键词: 国际恐怖主义;“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反恐怖策略
毋庸置疑,近五年来,伴随着反恐怖斗争的强化与扩大,加之“伊斯兰国”的竞争与挑唆,“基地”组织的势力与势力日渐衰落。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基地”组织在全球“圣战”网络体系下依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基地”组织的网络化发展,使其能够作为“圣战”意识形态的中心机体推动恐怖网络的横向扩张与纵向发展。“基地”组织对全球及我国的威胁依然不容小觑。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全党同志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总书记的发言既是对我国当前面临的复杂局势的准确判断,同时也是对我们当前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恐怖主义问题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反恐怖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实现,故而必须在科学认知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组织的基本特征、探明其发展、变化的原因基础上,准确制定合理可行的反恐怖策略,完成反恐怖工作任务,实现反恐怖工作的最终目标。
防汛减灾能力不断提升。保证城市防洪安全的南北两条主要入海尾闾中,独流减河治理圆满完成,永定新河治理二期工程已经开工;继续实施北运河、蓟运河治理和海堤建设、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新建14座中心城区排水泵站,完成4座积水地道提升改造;41项应急度汛、维修加固工程汛前建成生效。调整充实市防指组织机构,制定中心城区积水地区 “一处一预案”,完成防洪特征水位调整、高程系统统一和暴雨洪水还原计算,建成中小河流水文监测系统和防汛异地视频会商一期工程。
一、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重大发展变化之一:“基地”组织自身的衍进
“基地”组织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阿富汗抗苏“圣战”运动,之后目标转变为打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所谓“腐朽政权”,即“远敌”与“近敌”。需要指出的是,“基地”组织的第一任领导人阿扎姆及其继任者本·拉登对于“远敌”的认知并不完全一致。阿扎姆的战略具有明显的防御性,他认为“基地”组织的职责应当定位于保卫伊斯兰以避免外国势力的侵略,因此他将打击对象仅限定为干预巴勒斯坦和克什米尔的外国势力;本·拉登的战略更具有侵略性,并得到了扎瓦西里的支持。拉登将“远敌”界定为穆斯林世界以外的、争夺克什米尔和巴勒斯坦地区控制权的势力,并支持在“远敌”的本土展开袭击。
以2001年“9·11”事件为分水岭,之前的“基地”组织具有典型的分层等级型结构特征,是一支组织严密、层级清晰的军事化队伍。当前“基地”组织的发展变化具体表现在组织结构和行动策略等两个方面。
(一)“基地”组织的结构变化趋势:网络化与分散化
“9·11”之后,在国际反恐活动严厉镇压之下,“基地”组织已经由等级结构分明的组织(“基地”组织主要由咨询理事会、军事委员会、宗教委员会等机构组成)转化为由“基地”组织核心、附属组织(分支机构)、合作组织(外围合作伙伴)和非附属恐怖主义小组与个人组成的一个多层次的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其中“基地”组织核心、附属组织(分支机构)是恐怖主义网络的核心,外围的合作伙伴具有相当的自由和灵活性,恐怖小组与个人主要通过接受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来自发策动恐怖袭击。
1.网络化机构的组成与优势
其次,从攻击目标选择来看,“伊斯兰国”主张消灭所有不服从其极端主义教义的人,“任何与西方合作的穆斯林都不是真正的穆斯林,而是异教徒的帮凶,应该被处死”,[10]其目的在于挑起中东世界的教派冲突并利用这种冲突来开疆拓土、扩大势力范围。因而,“伊斯兰国”公开反对及批判所有的什叶派教徒;把所有不遵守“伊斯兰国”特有的伊斯兰教教义(脱胎于瓦哈比主义)的逊尼派教徒戴上“叛教者”的帽子,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而且理应处死。“基地”组织则试图尽可能团结一切普通穆斯林,不刻意渲染其与什叶派穆斯林的对立,力求建立伊斯兰各教派之间的统一战线“泛伊斯兰联盟”,希望通过“圣战”唤醒“沉睡的穆斯林”,故在确定“异教徒”或“叛教者”时较为慎重,避免打击扩大。本·拉登认为,“导致‘乌玛’(穆斯林共同体)分裂的根源是穆斯林群体基于民族、种族以及派系的划分。”拉登一直强调穆斯林应当共同行动,避免教派内部互相残杀,共同打击西方敌人。因而早在2005年“基地”组织就曾告诫扎卡维不要攻击伊拉克什叶派及其清真寺,“对他们应当传道,而非杀戮,除非他们主动发动攻击”,以避免引起穆斯林的反感。[9]“基地”组织的意图在于“争取”,即以对少数敌人的恐怖来争取多数穆斯林的支持;“伊斯兰国”的目标则是“威吓”,即通过对一切不服从命令的人施加威吓来迫使其服从。“伊斯兰国”显然是比“基地”组织更加极端的恐怖组织。
当前“基地”组织的结构具有明显的网络化特征。“9·11”事件前的“基地”组织在结构上存在一个以拉登为首的舒拉委员会,是整个组织的权力中心并由此向外辐射,作为最高指挥者和领导者组织协调各地区的恐怖活动。阿富汗境内“基地”组织的大部分训练基地在阿富汗战争中被严重破坏,在这些训练基地接受培训的成员不得已逃到世界各地。此外,“基地”组织原本的运行和结构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原本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领导人员及骨干成员在战争后缺位。由此“基地”组织开始向网络化、分散化发展,具体表现为最高领导集团负责输送意识形态和战略鼓舞,各个次级机构可以自主灵活地策划、实施具体行动,这些次级组织大多由若干较为分散的小型团体或者个体成员构成,在联合行动时,小组或成员横向联系组成特定行动团队,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并相互配合,共同高效完成实施恐怖袭击的任务。
另外,“基地”组织正在转变为全球“圣战”意识形态的发布中心和策源地。“毫无疑问,‘基地’组织在‘9·11’事件以后已经难以具备较强的能力来独自支持和策划大型的恐怖袭击事件。然而,在‘后9·11’时代,‘基地’组织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巴厘岛恐怖袭击事件’‘马德里恐怖袭击事件’和‘伦敦恐怖袭击事件’那样。‘基地’组织已经具备较强的能力为那些区域和地区的恐怖组织提供物资、技术和战略战术支持。更重要的是,‘基地’组织依旧是‘圣战主义’媒体中心,它依旧在激发着‘圣战主义’的情感,并努力争取广大穆斯林的同情心。”[1]在“9·11”事件之后,“基地”组织很快建立了“圣战主义”媒体发布网络机构,每天发布大量的恐怖袭击视频、“基地”组织的领导讲话、“基地”组织的官方文件以及“圣战”训练手册,从而构成了本·拉登最重要的宣传“机器”。
2.“基地”组织的机构调整与功能
所谓网络化结构是指国际恐怖主义在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实施高压打击态势下进行组织的一种新模式。网络化机构的特点是:首先,该结构不同于传统的金字塔型,无正式组织形式,各次级组织地位平等,缺乏传统的“上令下行”组织模式。其次,传统意义上的领导者只提供高层次的战略支持,领袖在精神方面引导组织成员,并不直接指挥和参与各个次级组织的具体行动。各次级组织比较灵活和自由,在行动策划实施方面具有较大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恐怖袭击,以及具体如何安排恐怖袭击方案。故而在计划制定直至逃跑路线的选择方面,具有传统模式难以比拟的安全性。最后,各个次级组织虽然具有高度自主权和自治性,却不是绝对孤立的个体。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是链接各个“孤岛”的桥梁。每个恐怖组织均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价值确信或政治目标,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能够独立行动,也能够在必要时相互配合、联动合作。
网络结构型兼具灵活性与安全性的优势。各个次级组织不必受到高层领导者的制约,可以自主机动地制定目标实施恐怖袭击。各个次级组织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除需要合作执行任务外,一般避免组织间的上下级联系,这样就保证了各个次级组织的安全。因此,这种组织结构可以避免出现分层等级制度的缺陷,即使某个首脑、领袖被抓获或击毙,也不影响整体的存在。以“伊斯兰祈祷团”为例,该恐怖组织在东南亚地区不断制造恐怖事件,对东南亚地区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从2002年到2004年,该组织先后有260名领导人被抓捕。但该组织并未因此走向终结,最主要原因就是其采用了这种网络状的结构模式,领导人的缺位不会影响各个次级组织的正常运行。目前诸多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结构转变为网络化结构,导致恐怖主义组织结构更加松散、简化,由许多小型的组织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恐怖主义组织。
同时,本·拉登的网络“圣战”模式也是其与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强化联系的最重要的通道。这些恐怖组织拥有招募恐怖分子,激化“独狼”针对西方敌人实施攻击的宝贵的资源。而“基地”组织在马格里布、索马里等地区的分支机构也建立了类似的媒体营销机构,并通过“基地”组织的“全球伊斯兰媒体阵线”发布信息。这种做法一方面有助于扩展各恐怖组织的全球影响,同时还能够“取悦”拉登及其领导下的“圣战联盟”。拉登在生前曾一度想将这些地方媒体统一化。
(二)“基地”组织的行动模式变化趋势:“本土化”与“独狼”化
如果要我挑一个创业能成功的最大关键,我总会认为就是毅力。表面光鲜的成功故事,背后九成九都拥有不为人知的艰苦历程,包括无数个难眠的夜,以及各种各样的挫折打击,在不放弃之前都还不算失败。
随着恐怖主义之结构的转变,“基地”组织的行动模式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9·11”事件及以前,“基地”组织挑选特定成员潜入目标国实施恐怖袭击,而“9·11”事件后“基地”组织采取了新的行动模式,在其目标国招募、吸收新的恐怖组织成员并建立特定行动小组,由他们完成策划实施恐怖袭击的任务。招募成员、组织行动小组、整合各方资源、制定行动计划及目标等任务基本上都由本土化的下属分支机构承担。
“本土化”标志着“基地”组织角色定位的变化。传统的“基地”组织行动的模式是由“基地”组织策划、指挥、招募、选派、实施暴恐活动,“9·11”即为适例。当前的“基地”组织日益成为“圣战”意识形态的发布中心,成为一个教唆者、煽动者。“基地”组织越来越依赖媒体、网络进行意识形态灌输,接受“圣战”思想洗脑的恐怖组织和个人则自发决定实施暴恐活动。
恐怖分子“本土化”也推进着西方国家反恐怖策略的转型。基于大量的“本土”恐怖事件均发生在欧美等西方世界,实施者多系具有西方国家国籍的移民后代,传统的针对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打击至上”反恐怖模式难以简单套用。强调社会融入、推进共同价值观念和预防社会不稳定群体激进化成为西方国家反恐怖策略的重要支柱,人权与安全、打击犯罪与保障自由之间的平衡问题得到更多人的关切。
2.恐怖活动“独狼”化
“独狼”化又称为个体恐怖主义。是指由不隶属于任何恐怖组织的个体实施恐怖活动的现象。“个体”并不意味着仅限于单独一个人,数人共同实施暴恐活动,但尚未形成组织的,也属于个体恐怖主义。[2]个体恐怖主义虽是由不隶属于组织的个人单独策划、实施,但是从其产生犯罪动机、决意乃至付诸实施、完成犯罪的整个过程中不能排除恐怖组织的煽动、教唆行为施加的单方向影响,例如恐怖组织通过网络进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输出、教唆犯罪故意、传授犯罪方法、提供犯罪技术等等。
这房子在旷野里,才会这么冷,青梅居的九楼,也有从旷野里吹来的风雪,青梅居会冷吗?应该不会的吧,那新建的房子,不是吹嘘有外墙保温系统吗?即使没有,新建的楼房,密封也好,怎么会任由这北风呼呼地吹进来又呼呼地吹出去?李倩倩、弟弟和妈,此刻都睡在那栋房子里,他们都不会感觉到寒冷。
复次,在攻击方式上,一方面“伊斯兰国”更善于利用新媒体、自媒体发动网络恐怖主义攻宣战,煽动、蛊惑青少年加入恐怖组织,或者刺激个人转化为“独狼”就地展开“圣战”;另一方面“伊斯兰国”拥有庞大的军事武装力量,能够与中东地区的政府部队展开正面的军事对决。与“伊斯兰国”相较,“基地”组织则属于典型的恐怖组织,主要采用爆炸、劫机、枪击等传统恐怖袭击方式,且成员较少,主要针对平民发动攻击,不控制领土,不主动攻击军队。可是“伊斯兰国”却拥有三万多名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有其控制下的领土,不仅有着稳定的经济来源,而且具备参与军事行动的能力。
当代个人恐怖主义的频繁发生与恐怖组织的战略战术变化紧密关联。恐怖主义组织通过源源不断地输出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等方式,诱导着各个领域的民众。例如2009年11月5日美国胡德堡军事基地恐怖袭击案。该案件由美军军官尼达尔·马利克·哈桑策划、实施,造成13人死亡,32人受伤,其犯罪动机是认为美国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教法存在“冲突”。警方事后查明哈桑本人深受“基地”组织的煽动。
当然,恐怖组织面向不特定对象实施的煽动并不能主导个人激进化的总体进程。毋庸说在外部因素介入整个社会化的进程中还需要个人因素和社会条件的充分具备才能够予以实现。换言之,从恐怖教义的宣扬到个人对极端理念的确信,需要一定的语境和情景,需要个人具备特定的生理与心理要素。没有人在对一种理念的认知过程中是纯粹单向的,是毫不加任何批判的。恰恰相反,是根据“先见”对这种理念进行的“再加工”和“再认识”。即使是一种认同,都包含着个人感性或理想心理的混合。因此,“独狼”的全球崛起既是恐怖组织战略战术变化的结果,也深刻反映着国际社会“经济-政治”不平衡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难以摆脱的困境与哀鸣。
为了进一步测试教练员对运动员文化教育的关注程度,通过询问教练员关于运动员上学期各科目成绩等级的方式来获得相关信息。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教练员对于运动员的学习是较为或非常关注的;个别教练员表示由于时间久了,或是忘记了,或是搞混了等原因而不知道运动员的学习成绩,这都表现出了部分教练员对运动员文化学习的轻视。
(三)“基地”组织发展变化的示范效应
必须承认,“基地”组织结构变化与新特征、新行为模式的出现,是内外因相互作用之结果。外因是美国为首的反恐联盟的持续打击,内因是新兴恐怖组织如“伊斯兰国”的竞争“上位”。因此,“基地”组织之转变实为迫不得已之结果。但是,“基地”组织并未因此消亡,反而能够继续存活,这说明网络化犯罪组织机构具有分层等级结构不可比拟的优势,进而也会给其他恐怖组织以启发,乃至效仿。“从‘基地’组织多年来的恢复力和生命力可以看出,在国际恐怖组织网络模式中,某个节点的断裂并不会影响整个网络的运转,各个节点之间的联系也为其赋予更多组织弹性,致使极端势力在处于低潮后常常能够重新崛起,他们的组织结构发展还有两个特点加强了这种恢复力和生命力,一是不断扩大社会服务功能,二是具有流动性特征。”[3]也就是说,社会矛盾和社会需求决定了如果不能从社会根源入手就无法彻底铲除恐怖主义,而网络化结构则赋予了恐怖组织在一定区域内继续存活的基础条件。我们发现,“伊斯兰国”正在由分层等级结构向网络化发展,碎片化的“伊斯兰国”具有了“基地”化的特征。
二、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重大发展变化之二:“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关系变迁
(一)“伊斯兰国”的渊源
1.“伊斯兰国”的兴起
近年来,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反恐的重点,全球大约70%的恐怖事件与这种类型犯罪有关。2014年6月29日,被称为“现今世界最危险的恐怖组织”的“伊斯兰国”宣布在其控制的伊拉克与叙利亚部分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家”,实行伊斯兰律法。“伊斯兰国”源自1999年建立的恐怖组织“统一和圣战组织”,2003年美国进军伊拉克后,该组织在伊拉克建立基地,主要攻击美国领导的联军部队、约旦政府和什叶派,制造多起自杀式爆炸恐怖袭击。2004年9月,组织领导人扎卡维宣誓效忠“基地”组织领导人拉登,从此更名为“‘基地’组织在伊拉克分支”。2006年1月15日,“‘基地’组织在伊拉克分支”与另外五个恐怖组织合并形成“圣战舒拉会议”,同年6月7日该组织又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出现巨大权力真空,当地恐怖组织活跃,也给了“伊拉克伊斯兰国”可趁之机。2013年4月9日,叙利亚当地恐怖组织“胜利阵线”加入“伊拉克伊斯兰国”,壮大了后者的实力。2014年,该组织的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将组织更名为“伊斯兰国”,并宣称对整个穆斯林世界拥有绝对统治权,此前还正式宣布与“基地”组织“各走各路”。[4]2014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纽约客》杂志采访时曾表示,“伊斯兰国”只是“基地”组织的“小伙伴”。然而,很快“伊斯兰国”以其迅猛的发展速度跃居“基地”组织之上,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犯罪的“领头羊”。[5]
2.“伊斯兰国”的架构
“伊斯兰国”不同于“基地”组织,具有分层等级结构的组织特征。分层等级型,又称“金字塔型”。这样的组织结构有明确的结构分层,复分为领导层,特定职责的次级领导,行动者与支持者。这样的组织结构较为严密,类似于军队,比较适合大型武装战斗,真主党、哈马斯、泰米尔猛虎组织等均采用该结构。以“基地”组织的分支组织“‘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简称“AQAP”)为例,AQAP源于“基地”组织沙特分支与也门分支,2009年沙特分支与也门分支合并,称为阿拉伯半岛分支,总部设在也门。在其创始人瓦赫希的策划和指导下,AQAP发动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2009年的美国达美航空公司航班圣诞节炸机未遂案、2010年美国时代广场爆炸案和2015年法国查理周刊枪击案。2010年联合国将AQAP列入恐怖组织名单。AQAP名义上隶属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是其一个分支,实际上与其关系十分松散,有着自己的领导集团,虽然成立时间很短,但在AQAP内部有明确的分工和不同的等级,主要由领导集团、军事部门、宣传部门和宗教部门构成。领导部门主要负责组织整体发展规划和具体恐怖活动的计划,军事部门主要负责汽车炸弹袭击、自杀式袭击、武装袭击等具体暴力恐怖活动的实施,宣传部门主要运用各种宣传手段招募新成员、在社会中建立支持组织的群众基础,宗教部门则构成组织成员的信仰纽带和精神寄托,起到坚定成员意志力、凝聚成员向心力的作用。[6]分层等级制的缺陷在于金字塔的最顶端即最高权威的领导者、组织者对整个组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必然成为国际与国内反恐行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整个组织会随着领导人的缺位而走向消亡。例如,泰米尔猛虎组织领导人普拉巴卡兰被政府击毙之后,该组织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迅速走向支离破碎的境地。
3.“伊斯兰国”的发展趋向
自2017年以降,受国际反恐怖势力的联合打击,以及伊拉克政府军的强势反弹,“伊斯兰国”呈节节败退之势,其在伊拉克与叙利亚国境内占据的势力范围不断缩小。面对反恐怖压力,“伊斯兰国”在组织形态与活动规律上出现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联立式(1)、式(2),并考虑断面Ⅱ—Ⅱ处变径的局部阻力损失和断面Ⅰ—Ⅰ、Ⅱ—Ⅱ间的摩擦阻力损失,推导出式(3),即断面Ⅱ—Ⅱ处的风速为
第一,在组织形态上,“伊斯兰国”网络化、扁平化特征初现,特别是受强力打击压迫,战略要塞连续失守,“伊斯兰国”正在由准军事化的割据势力向典型的恐怖主义组织转型。
第二,“伊斯兰国”的活动范围出现“碎片化”和明显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在2016年年末与2017年上半年,连续在东南亚和欧洲策划、实施重大暴恐袭击事件,这表明“伊斯兰国”在中东依然举步维艰,正在谋求向中东以外的其他地区、其他国家的薄弱地带寻求突破口,特别是欧美、非洲、东南亚与东亚等地。
第三,从“伊斯兰国”当前策动暴恐活动的具体方式来看,“伊斯兰国”已经很难再采取与政府武装进行“阵地战”的攻击模式,而是以不特定多数人较为集中的“软目标”为主要攻击对象,以武装攻击、自杀式爆炸袭击为攻击手段,以人数规模较小的恐怖小组或者“独狼”作为攻击主体,手段特别凶残,致死伤人数众多。
第四,从“伊斯兰国”的战略战术来看,该组织一方面继续保持同其他地区的恐怖组织积极联动,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其影响力还要继续派遣组织成员返回母国策划、实施恐怖活动,或者通过网络及其他媒体煽动当地的激进分子就地实施“圣战”。
(二)“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分”与“合”
1.“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分道扬镳”
“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作为近年来在国际社会中较为活跃的恐怖组织。 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伊斯兰国”的前身“统一和圣战组织”曾经在2004年宣誓效忠于“基地”组织及其领导人本·拉登,因而更名为“伊拉克‘基地’组织分支”。随着伊“基地”组织在中东影响力和实力与日俱增,其独立性也日益增强,其与“基地”组织之间摩擦、抵牾不断,二者关系愈行愈远、甚至“貌合神离”。在2010年以前,“基地”组织依然将伊“基地”组织视为其下级组织,还会命令后者去攻击特定目标,到了2010年至2011年间,“基地”组织与伊“基地”组织已经“破镜难圆”了,“伊斯兰国”多次发表言论批判“基地”组织已经偏离了先知的正确道路,毫不掩饰其对“基地”组织的敌意。2014年1月,“伊斯兰国”与叙利亚多股反对派武装力量发生激烈冲突,“基地”组织头目扎瓦希里多次提出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协商解决但均遭到“伊斯兰国”的无视和反对。2014年2月2日,“基地”组织正式发表声明,宣布“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不存在隶属关系。“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关系正式破裂,并且开始在多地进行势力范围的争夺。
2.“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差异
除了领导人的政治野心外,“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同,正是这些区别导致两个恐怖组织“分道扬镳”。
首先,行动战略不同。在处理“远敌”(西方世界)与“近敌”(中东的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方面,“基地”组织主张“先远后近”,即先致力于打击西方的“十字军”,然后再推翻西方资本主义扶植的阿拉伯世界的“傀儡政权”,“本·拉登认为打击‘远敌’更为重要,扎瓦希里也强调‘基地’组织的首要敌人是美国及其盟友和以色列。”[7]在这一战略主导下“基地”组织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十年里向西方国家发动了大量的恐怖袭击。“伊斯兰国”则主张“先近后远”,即它将在中东地区夺取政治权力与领导视为组织的第一要务,即包括伊拉克的什叶派政府、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以及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在内的“近敌”,其次才是将“政教合一”的政治权力与制度向全球扩散。因而不难解释为什么“伊斯兰国”“建国”后直至2015年7月才向印度、中国、索马里、高加索、菲律宾、阿瓦士、伊朗、埃及等其他国家宣战,并且“伊斯兰国”一直保持对西方国家的克制态度,直至2016年以来在面临反恐巨大压力下才频频策动对西方的恐怖袭击。
我国学者认为,两大恐怖组织战略目标的区别可以归纳为“‘基地’追求政策改变,‘伊斯兰国’谋求领土扩张。”“‘基地’的战略目标旨在迫使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称为‘远敌’的国家如美国、欧洲等改变其针对阿拉伯世界的政策,以维护和巩固伊斯兰信仰共同体(‘乌玛’)的荣光。而‘伊斯兰国’的战略目标则是开疆拓土,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主义国家缔结的《赛克斯—皮克协定》所划分的中东国家边界,重建‘哈里发国家’。”[8]事实上,早在2004年的时候,“伊斯兰国”前身“统一和圣战组织”领导人阿布·穆萨·扎卡维曾提出在伊拉克建立“哈里发国家”,“基地”组织曾明确表示反对,称建立“伊斯兰国家”并不成熟。与此相反,本·拉登也曾将“基地”组织策划、实施的恐怖活动视为建立“哈里发国家”的前奏,但是他悲观地认为自己在有生之年无法看到这个国家。[9]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基地”组织更加热衷于向西方国家和人民发动恐怖袭击,而不是攻城略地。总之,“伊斯兰国”不同于“基地”组织,自成立之初即将建立“哈里发国家”视作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并努力试图将其实现。
在该环节中,笔者将微课视频推送到高中数学翻转课堂平台,并向学生分发“课前学习案”,学生进入高中数学翻转课堂平台,观看微课视频,完成自学任务.
安全是施工根本保障,必须要落实下去,减少过程中不利因素影响。召开安全教育大会,对于近期状况进行总结,提高所有人安全意识,让行为举止更加规范。人员在进入现场的时候,要做好自身的安全防护,包括安全帽、手套、工作服等,可以减少对身体的伤害。横幅标语也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写上安全第一、安全施工、安全责任大于天等,无时无刻提醒人员要注意安全。由于工程量比较大,会用到机械设备,一定要由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禁止其他人员擅自使用。在施工中发展安全隐患要及时消除,防止情况恶化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入冬了,来暖气了。回想起以前那个零食不如现在丰富的年代,家里大人放在暖气上烘烤的苹果干、山楂干、地瓜干和胡萝卜干等,就成了孩子们的零食。在暖气旁边玩边吃,也成了多少人的童年回忆。其实除了它们,暖气还能做出各种各样好吃的。
最后,在组织结构上,“伊斯兰国”是典型的“金字塔式”分层等级结构,对外运用军事武装力量施以暴力征服,对内仿照国家建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并对治下人民施以极为严苛的“沙利亚法”。“伊斯兰国”在中央设立了“财政部”“国防部”“作战部”“宣传部”“内政部”“通讯部”“伊斯兰教法部”和“情报部”等多个部门,在地方一度下辖12个省。[11]“基地”组织则呈现网络状结构,其内部由核心机构、分支组织(如“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索马里青年党”“叙利亚支持阵线”与“呼罗珊集团”等)“圣战”盟友(如“伊斯兰教法支持者”“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以及恐怖小组、个人等四个层次、多个部分构成,核心机构负责意识形态的输出、战略战术的宏观指导,其他组织则在当地具体自主灵活地开展恐怖活动。
1.恐怖活动“本土化”
3.1.5 避免空气栓塞 空气栓塞是中心静脉置管护理最严重的并发症,可造成肺动脉栓塞引起患者死亡。特别对头高位和低血容量的患者尤应重视。输液器、肝素帽及三通管各个接头处要衔接牢固。在输液过程中应加强巡视,及时更换液体。
3.“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重新合流”
做法:1.先将面粉过罗,加30~35℃的水、鸡蛋、盐和成面团,当面团揉均匀后,饧放 30~40 min。
“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二者之间的关系发展走向表现为既合作又竞争的特点。尽管“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在战略战术、攻击目标、攻击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二者在思想根源上皆出自“圣战萨拉菲主义”,终极目标都是要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在面临紧迫的反恐压力的时候,二者会暂时停止纷争、展开合作。但是“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毕竟存在“政治路线”的分歧(例如“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围绕“谁是正统谁是异端”曾展开激烈的论证),更重要的是双方还要继续争夺“国际‘圣战’的领头羊”(截止2015年12月,已有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34个极端组织和暴力武装宣布效忠“伊斯兰国”,其中部分组织诸如“博科圣地”之前曾是“基地”组织的下属组织),这就决定了“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竞争关系。
汽车某时刻的行驶状态,经过一系列的汽车动力学仿真,首先得到路段的各加速度在坐标轴上的投影变化图以及x轴、y轴和z轴加速度合成图,即模m方向的加速度图,如图6所示。
三、当前国际恐怖主义重大发展变化对我国的影响
(一)“基地”组织自身发展变化对我国的威胁
第一,“基地”组织的网络化发展直接导致我国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增长。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包括以网络作为攻击对象的恐怖主义活动和利用网络作为攻击手段的恐怖主义活动两种。根据“基地”组织网络化的发展特征,可以预见的是,“基地”组织今后仍然会持续利用网络向我国发动“圣战”意识形态和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攻宣活动。特别是当“伊斯兰国”势力衰退,为了在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与“伊斯兰国”展开竞争,今后“基地”组织必然会加强网络宣传力度,扩展影响力。
第二,“基地”组织的“本土化”作战模式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9·11”以后,各国在加强反恐联合、反恐打击的基础上,纷纷加强了国边境的管控。例如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多起暴恐事件,均是恐怖分子欲出境不得而只能“就地圣战”。因此,未来“基地”组织欲加强对我国的威胁力度必然是通过虚拟通道而非实体通道进行思想渗透诱发本土的激进分子实施暴力行径,因此恐怖分子的本土化、年轻化特征将十分明显。
第三,“基地”组织的网络攻宣方式容易诱发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产生。尽管学界对“个体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仍存有争议,但是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矛盾凸显从而引发的“无差别杀人犯罪现象”增多,我国学者亦用“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来形容概括此类事情。传统意义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并无政治目的,主要是出于对社会不满、对个人前途的失望以及对社会发泄愤怒等犯罪动机。但是由于“基地”组织的“圣战”思想煽动,导致当前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也染上了恐怖主义色彩,这是不能不高度警惕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不同于有组织的犯罪,其行动更加灵活、突发性强、威力巨大,容易造成社会的普遍恐惧与紧张。
第四,“基地”组织对我国部分地区部分政府官员、公务员进行有意识地策反活动,危及我国的国家安全。我国应当加强对领导干部、公务人员思想教育和行为监督,防止“两面人”现象,对于受到极端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应当毫不留情予以处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近年来暴恐活动趋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即是基层政权组织、建设能力不足,部分共产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或者向极端宗教人士低头服软,最终导致宗教极端势力在基层社会蔓延。因此,必须以此为戒,加强基层政权的战斗堡垒功能。
2.2.1 部分输卵管切除联合端吻合术:该手术方式在临床中应用较少,其主要步骤为:游离患者输卵管系膜,切掉妊娠种植区域的部分输卵管,再采用显微手术,实施端吻合术。端一端吻合术适用于峡部、壶腹部近侧端妊娠,或破裂型切口不规律者;Gerfert术适用于伞端妊娠,但会破坏伞端的拾卵功能,导致日后妊娠率下降。
第五,“基地”组织的发展变化对我国恐怖组织具有传染效应。部分境外“东突”恐怖组织模仿“基地”组织,对我国进行网络攻宣,部分境内恐怖组织则以“基地”组织的发展战略为蓝本,实现组织的分散化、小规模化和碎片化,加强攻击的灵活性,降低组织被发现、侦查的可能性。
第六,“基地”组织还会继续吸纳我国的激进分子参与其训练营,发展恐怖分子,从而在适当时机回流在我国进行本土“圣战”。值得注意的是,自“伊斯兰国”面临中东地区的巨大压力同时,我国也再一次面临着“圣战”分子回流小高潮的危险,这种危险将在“基地”组织的进一步推进下日趋严峻化、紧迫化。
第七,从“基地”组织的基本战略规划——正确处理“近敌”与“远敌”的关系来看,我国本土并非“基地”组织的主要攻击目标。“基地”直接向我国本土发动暴力攻击的可能性不大,在历史上如此(拉登时期对“东突”恐怖组织主要给予物资帮助、人员训练和意识形态灌输,并不主动参与到对我国的实质攻击),未来一段时间内亦复如是。但是,我国在境外的人员、财产等利益可能成为“基地”组织攻击的目标,“基地”组织为了扩大影响力也会对其势力范围内的一些外国国家利益展开武力袭击。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存在着“基地”组织多个影响力、战斗力极强的分支机构,如“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等等。因此,我国海外国家利益面临着“基地”组织较为严重的威胁是比较客观的判断。
(二)“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关系变化对我国的威胁
如上述,未来“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存在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但是,必须承认,二者的分歧具有相对性,与“异教徒”世界相比,二者的共同性可能是更为主要、基本的方面。特别是在“伊斯兰国”成为“众矢之的”呈现节节败退之势的时候,二者相互支持、相互合作,“抱团取暖”的可能性相当高。历史上,“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都对我国国家安全产生过严重的直接或间接威胁。拉登时期的“基地”组织曾向“东突”分子提供过大量资助与培训,“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则直接将我国列为主要的复仇对象。这种威胁很可能由于二者的合作而更加显著。一方面,原来从属于“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恐怖分子可能复归或者投靠“基地”组织,另一方面“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可能共享情报,相互合作,共同出击。因此我国可能将面对“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两大组织合流后更加严峻的威胁与挑战。
四、我国的基本应对策略
(一)加强反恐怖国际合作
应当加强反恐怖国际合作,特别是信息情报机制平台的搭建与信息共享,加强域外刑事司法合作实践与制度完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国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加强反恐怖国际合作势在必行。同时,恐怖活动的跨国化与恐怖组织内部周密的组织形式,每一次恐怖活动的实施都经过详细策划而实施,恐怖组织不是孤立存在于某一个国家,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全球反恐怖合作是必然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在反恐技术合作方面,建立高效的全球反恐怖信息情报机制平台,共享反恐情报信息,切实增强反恐怖国际合作。目前,各国针对本国反恐工作现状制定了与之适应的反恐怖主义立法,在国际社会中尚未颁布一部切实有效的反恐怖主义立法,在域外刑事司法合作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加强反恐怖国际合作,加强域外刑事司法合作的相关制度完善是必然的要求。由于各国出于对本国国家利益的保护,在反恐怖国际合作方面存在意见分歧,这就要求各国树立大局观,强化合作意识,共同推动国际反恐。
(二)正确对待海外反恐行动
应当谨慎对待海外反恐行动问题,一方面要坚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另一方面选择合适的反恐策略,避免直接激化与国际恐怖组织的矛盾,造成与其直接冲突,防止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祸水东引”。在威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恐怖主义犯罪面前,要坚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不作妥协让步,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海外反恐行动中,要采取灵活性、机动性的反恐策略,谨慎采取措施,避免造成与恐怖组织的直接冲突,同时防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反恐行动上采取的“双重标准”破坏我国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谨防其在表面上积极进行反恐行动,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暗地里放任甚至支持恐怖组织对我国进行分裂的恐怖活动,企图将“祸水东引”。因此,在海外反恐行动中,要谨慎制定反恐策略,破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分裂我国的企图。
(三)强化网络反恐怖行动
应当加强对网络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在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广泛性与普及性使其成为恐怖组织新的恐怖活动实施地,恐怖组织利用网络传播恐怖主义思想、招募人员、进行网络恐怖心理战,并且利用网络窃取国家情报信息,攻击网络系统,网络恐怖主义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制造社会恐怖气氛,造成人们的恐惧心理,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须严厉打击恐怖主义。对于网络恐怖主义,既要“防范”,也要“打击”。重视网络技术的发展,加强对网络的监管力度,增强技术方面的实力,通过技术的手段保护网络系统,加强防范;运用技术手段攻击恐怖组织的网络系统,或者切断恐怖组织的网络通讯系统,有效控制其与外界的网络联系,严厉打击恐怖主义。
(四)着重社会综合治理
加强社会综合治理,从根源上缓和社会矛盾,减少滋生恐怖主义的社会土壤,特别是加强文化教育,培育抵制极端思想的能力,加强就业培训,避免一部分无所事事的年轻人陷入极端主义的泥淖。反恐怖主义的工作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家层面,要从基层抓起,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抓起,继续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扬社会文明风尚,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对极端主义思想的辨别能力,自觉抵制极端主义思想。加强就业培训,尤其是对于恐怖组织企图招募的青壮年群体,避免恐怖组织利用金钱等引诱失业的青壮年加入其组织,切断恐怖组织人员扩张的途径。
(五)继续坚持去极端化
加强去极端化建设,推进社会一般预防制度,强化对危安罪犯、恐怖主义罪犯的改造,推出一批改造好的“典型”“模范”,带动主动放弃错误思想、配合刑罚执行部门改造的风尚。推进社会预防制度,严厉打击邪教组织进行的活动,取缔所有邪教组织,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对危安罪犯、恐怖主义罪犯要针对其特殊性,对其进行个别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不能局限于读书、读报纸和上课等形式,要发挥改造好的“典型”“模范”的带头示范作用,让他们作为典型案例现身说法,使危安罪犯、恐怖主义罪犯主动放弃错误思想,积极配合刑罚执行部门进行改造
五、结语
本文首先从“基地”组织的自身发展变化与“基地”和“伊斯兰国”的关系变化两个角度分析了“基地”组织对我国的威胁是现实而又紧迫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张小虎先生指出:“犯罪是社会的一扇窗户,是社会变迁的晴雨表。”[12]从根本上说,我国的恐怖主义问题是内因具有决定性作用力的客观现象,是社会变迁时代变化的产物,社会紧张淤积难以化解的结果。单纯的打击并不能解决恐怖主义犯罪问题,只有在社会政策的配合下施以适当的刑事对策才能实现事半功倍效果。因此,治理我国的恐怖主义问题,必须从社会本身入手,才能治本兼顾治标。当社会和谐、矛盾和缓、国民均能够过上富足而有自尊的生活的时候,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恐怖主义必然无所遁形;只要社会公平尚无法充分实现,社会矛盾难以彻底解决,部分国民或者在贫困中苦苦挣扎,或者苦苦哀叹命运之不公,或者难以在人生旅行中体会到自尊、自爱,那么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总有可趁之机。
翻转课堂是目前国内外教育界研究和探索的一个热点,很多高校在不同的专业和学科中都尝试着基于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和创新,积累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也都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翻转课堂,也叫颠倒课堂,是一种教师创建视频,学生在家中或课外观看视频中教师的讲解,回到课堂上师生面对面交流和完成作业的教学模式[2]。它是一种将传统的课堂学习延展至课外学习的一种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课堂之外,借助于网络平台或移动工具,通过微课视频自学学习的一种方式。相较于传统的教师讲授模式,翻转课堂更加注重于学生学习的主导性,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是一个引导者,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式及个性化地学习。
【参考文献】
[1]Anthony Celso.Al-Qaeda’s Post-9/11 Devolution: The Failed Jihadist Struggle Against the Near and Far Enemy[M].New York:Bloomsbury, 2014:57.
[2]Ramd’ N Spaaij, The Enigma of Lone Wolf Terrorism: An Assessment[J].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2010:859.
[3]富育红.“伊斯兰国”南亚分支的性质、影响及发展[J].南亚研究,2017(3).
[4]查尔斯·利斯特.“伊斯兰国”简论[M].姜奕晖,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29-53.
[5]刘乐.“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关系探析[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2).
[6]周庆喜.“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J].国际研究参考,2016(9).
[7]郭强.“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比较研究[J].国际研究参考,2016(4).
[8]周明,曾向红.“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战略差异及走势[J].外交评论,2016(4).
[9]刘中民,俞海杰.“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探析[J].西亚非洲,2016(3).
[10]杨凯.“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在东南亚、南亚的扩张比较[J].东南亚研究,2015(5).
[11]王晋.“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的变形[J].外交评论,2015(2).
[12]张小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犯罪[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9:1.
Major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Their Countermeasures ——Centers on Al-Qaeda
LAN Di,Liu Si-tong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 ’an China , 710016)
Abstract :Although still in the “cracking period”, Al-Qaeda is still a huge threat that China is currently unable to ignore.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Al-Qaeda are affected by two factors: one i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strategic adjustment pressed by international anti-terrorist forces, and the other is the relation change of cooperation-competition-re-cooperation among the Islamic States. The harm of Al-Qaeda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First, the networked, decentralize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the localization and the behavioral model of “one-wolf” have given “inspiration” to many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Second, “Al-Qaeda” and the increasingly fading “Islamic State” may have a tendency to merge, thus forming a synergy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further increasing the impact on the secur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Al-Qaeda will pose a serious threat to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In dealing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o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headed by Al-Qaeda, we must adhere to the overall governance thinking of “both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and “both governing the symptoms and treating the root cause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l-Qaeda; “Islamic State”; anti-terror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773( 2019) 02-0051-09
收稿日期: 2019-01-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去极端化视域下的‘柔性’反恐怖策略研究”(17CFX01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兰 迪(1985-),男,内蒙古包头人,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反恐学、犯罪学和中国刑法学;刘思彤(1997-),女,山东潍坊人,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学生。
(责任编辑:李 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