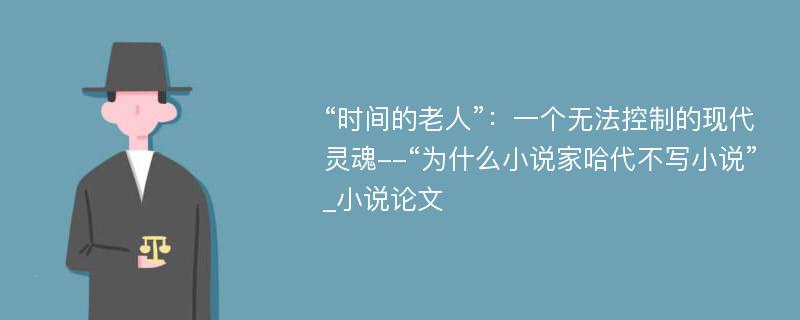
“时光老人”:难以驾驭的现代灵魂——“小说家哈代为何不写小说”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代论文,刍议论文,小说家论文,不写论文,灵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8)04-122-06
《枉费心机》等十五部长篇小说(其中十四部公开出版)和《威塞克斯故事集》等四个短篇小说集是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历近三十年(1867-1896)创下的小说业绩,它们坚实地奠定了作者在英国文坛的崇高地位,然而令世人惊讶与困惑不解的是赢得小说创作辉煌成就的哈代,在完成了引起巨大争议的长篇小说《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1896)后毅然辍笔小说创作,而将写作兴趣完全转向了诗歌。
一、“小说家哈代为何不写小说了”疑题
小说家哈代为何不写小说了,这一疑题引起聚讼纷纭。在众多意见中,“攻讦说”可谓播传最持久、认同面最广泛的一种解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正式辍笔小说创作前,哈代给后人留下的几段公开的“供词”:
如果这种事(指《无名的裘德》出版后遭到英美批评界猛烈的攻击,威克斐的主教甚至把这部小说焚毁示众,笔者注)继续下去,我就不再写小说了。[1](P7)
后来有人发现,《无名的裘德》是一部道德小说——严肃地处理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仿佛作者从来都没有在序言中说过小说的目的就是如此。随即谩骂停止了,事情平息下来,但这件事对人类行为产生的唯一影响,我能发现的就是对我的影响,即这段经历完全消灭了我继续写作的兴趣。[2](P260-261)
这些话暂不深究它们是否言不由衷,但千真万确出自哈代本人。据此,人们将哈代停止小说创作的原因归咎于外界的猛烈抨击和无端诋毁,这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
近年出版的一部关于哈代的新传记《饱受时代煎熬的哈代》(Claire Tomalin:Thomas Hardy:The Time-torn Man),对于哈代停止小说创作的个中缘由的解释也大致延续了这一观点。传记作者托马林认为:“哈代对外界的反应是很敏感的。《裘德》正式出版后遭到的滔滔恶评使他颇受打击。而此时在公众的激烈反应面前,他的情感生活彻底阻塞崩溃了,爱玛也公开宣布她讨厌《裘德》。在这种情况下他若再继续写小说、出版小说都将是极不愉快的事情。”[3](P156)托马林的观点在当今西方哈代研究界颇具代表性。不管怎样,近一个世纪以来,对哈代为何突然停止小说创作的争论中,拥“攻讦说”者甚众,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笔者对此有不同认识,至少不认为这是哈代停止小说创作唯一或是最重要的缘由。
事实上,用“攻讦说”来解释哈代创作体裁转向的事实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正如有论者所言,上述所引哈代的几段“供词”也许只可视为作者怀有别种用心的托词或借口,是哈代为自己“从小说转向诗歌的举动耍的一个障眼法”[4](p388)。但这种说法与“攻讦说”一样亦有臆测之嫌。稍加检视哈代各部小说作品的接受情况,便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几成通例的现象:哈代每一部小说的被接受历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从肆意批评攻击到褒贬参半再到赞誉称赏,几乎成为哈代所有小说的共遇。受此锤炼,对于外界的猛烈批评,在哈代来说无疑是习以为常的了,他不可能仅仅因为外界对其作品一时的否定而放弃心爱的小说创作事业。
也许持“攻讦说”者会作如是强辩:《无名的裘德》使哈代遭受到的非议和诋毁是他前所未见的,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反面批评的极限。但事实是,没有明显的迹象证明,《无名的裘德》是哈代所有小说作品中甫一出版便给他带来最坏遭际的作品。相反,有哈代亲口透露的许多事实和细节参佐表明,《德伯家的苔丝》出版后所遭受的抨击给哈代小说创作活动造成的压力,较之《无名的裘德》不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也是不相上下的①。
可见,单以“攻讦说”解释哈代停止小说创作转向诗歌写作的原因,是值得商榷的。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当代哈代研究专家聂珍钊教授在其专著《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托玛斯·哈代小说研究》中提出:“尽管哈代自这部小说出版后不再写作小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无名的裘德》出版后的不幸遭遇不能不说也是其中原因之一”[2](P261),笔者深以为然。对于“小说家哈代为何不写小说了”疑题的具体探讨,聂教授通过对哈代所有小说作品进行整体观照与系统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哈代的“每一部小说都不是独立的,小说和小说之间保持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一起构成了反映英国南部农村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历史画卷”,《无名的裘德》以反映破产农民的代表裘德“在现代城市中寻求出路的悲剧”为题材,它的问世标志着哈代“完成了描写威塞克斯农村社会在外部资本主义的侵入下逐渐毁灭的史诗性主题。也正是他完成了这个重大主题,他才最终停止小说创作转而写作诗歌。”[4](p208-216)聂教授从主题的完满性方面理解哈代为何停止小说创作,切入角度合理且论证令人信服,无疑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理解哈代停止小说创作的一种解释。
贯穿迷宫的通道往往不止一条,也诚如聂教授所言:“哈代自《无名的裘德》出版后不再写作小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批评界的外在压力外,我们认为时代的深刻变迁,他的小说表现题材的推移,所塑造的人物精神世界的微妙变化,以及如何拓展之前所开发的题材库等因素,给他继续小说创作带来诸般困惑和提出了艰巨挑战。这从哈代的小说封笔之作《无名的裘德》的实际情形看,《无名的裘德》为我们破解哈代在19、20世纪之交停止小说创作的复杂成因打开了一扇宝贵的窗户。下面我们将细读《无名的裘德》,从哈代小说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着眼,索解哈代停止小说创作之谜。
二、从“时光老人”形象看《无名的裘德》的现代主义因素
“时光老人”是主人公裘德的大儿子,也是小说中仅次于两位主人公的第三号重要人物。《无名的裘德》的主旨是揭示“一个工人的理想和悲剧”[5],从“时光老人”的思想意识、语言行动以及与周围人的关系考察中可以发现,在他的身上透示出现代主义的精神萌芽,“时光老人”可以视作从英国旧的时代传统异变出来的一个现代精神先驱的缩影与化身。
在《无名的裘德》中,传统的社会道德习俗导致了“时光老人”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并最终酿就了不可弥补的悲剧。“时光老人”生活在一个敌对的异己的世界中,这个世界阻碍着人的发展,扭曲着人的本性。通过他,哈代给我们展现的是一种异化的世界和异化的人生。“时光老人”处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碰撞交织的生存位置上,一方面,他为传统所禁锢;另一方面,他又想追求超前的生活方式,他在这种夹缝中痛苦地挣扎。“时光老人”对那个社会感到力不从心,以为通过死亡就可以得到解脱,最终以杀死弟妹并自杀的病态行为来获得解脱。“那个毫无价值的传统观念的社会,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扭曲人性的荒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的正常感情被视为邪恶,人的合理追求无法满足,人们简直成了孤立无援的可怜虫了。这正是现代文明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创伤。”[7]诚如小说中所指出的那样,“自然的意图、自然法律、自然存在的原因,就是为要我们按着她给我们的本能去找快乐——这种本能正是文明所硬要摧毁的”[8]。在这样的荒诞世界里,生存本身就毫无意义。所以“时光老人”常常流露出对生活的绝望和对死亡的向往这样的扭曲思想。作为个体存在,他的悲剧首先在于他生存在几个相互冲突的世界之中,他并不安于现状,而又无可奈何。哈代在他所处的时代就已经涉及到了异化这个主题,这种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否定超出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范围,迈进了现代文学的门坎,这不能不被看作一种突破和超越。
“时光老人”身上不仅有异化因素,同时也表达了对存在的荒诞感。“时光老人”怀疑自己的存在,常嘀咕“我就不应该生下来,是不是?”[8]可以说,作品中一再表达的主题之一就是:人在那个残酷的荒诞社会面前,主体意志无法施展,人格尊严无法保持,常态生活无以维系,正常心理横遭扭曲,人成了孤立无依、“被捉弄”的生物,坠入无奈的绝境,成为上帝脚下一只可怜的虫子,除了俯首听命,没有别的办法。正是因为对生存和社会环境的绝望,“时光老人”最后杀死了裘德和淑的孩子并自杀,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作为一个人物形象,“时光老人”不具备任何具体的现实社会特征,他看穿了“洪荒以来人类所有的愁苦”,对于人世的快乐,他认为“就没有一样可以发笑的”,而“待在这个世界上,不如离开这个世界好”[8],于是他选择了自杀。在这里,哈代向读者提供了一个人类生存状况的可怕寓言。我们知道,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现代派作家们致力于传达孤独、幻灭、荒诞性的人生体验。而哈代在作品中表现的世界是荒谬可怕的,人生是痛苦让人困惑的,未来是让人幻灭悲叹的。在同时代作家中,“几乎只有哈代用悲剧的眼光看待生活,这一点在精神上与20世纪的人生观一致。”[9]所以哈代的这部悲剧小说超越了他的时代,与现代主义作品热衷描写人类社会非理性的一面一脉相承,透露出现代主义的世界荒谬主题的先兆,具有浓郁的现代主义质素。
另外,哈代在表现“时光老人”这个人物时,着重反映的不是他的物质生活的贫困,而是精神上感到的压抑和孤独,“这种思想意识的混乱与动摇,不仅是个人的,而且也反映了西方社会的无序的精神状态,精神上无所依托,正是人在现代社会的精神状态,也是现代社会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10]“时光老人”的孤独感主要表现在他与周围人物之间在相互依存的同时却又彼此隔膜的孤独,这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所深切感受到的精神上的孤独。
“时光老人”是裘德与阿拉贝娜不幸婚姻生下的孩子,在思想精神上,他极度悲观沉沦,对外界始终保持着一种高度警戒乃至敌对的心理;在为人处世上,他与世格格不入,对人生也是一种完全灰色乃至绝望的态度。对于这些,我们可以从“时光老人”在小说中从一出现时的神态动作与心理活动窥见一斑。这一幕场景发生在“时光老人”前往伦敦探望父亲裘德住处的火车上。一只可爱的小猫一个劲儿地做滑稽可笑的动作,引得火车上的旅客哈哈大笑,而旁观的“时光老人”却始终没有笑容,一直紧绷着脸。作者这样写道:
他用又圆又大的眼睛注视着小猫,似乎心里在说:所有的笑都是因为误解发出的。只要你好好看一下,天底下就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发笑的事情了。……他现在是一个成年化装成少年的人,可是他的妆却化得很糟糕,以致他的本来面目从缝隙里露了出来。古代黑暗岁月里的海啸,似乎不时把这孩子从他初期的生命中高高托起,他于是转过脸去看一眼那汪洋浩淼的时光,而对于他所看到的好像满不在乎。[8](P253)(《无名的裘德》第五章第二节)
对一个处于少年懵懂阶段的男孩而言,本来应该对陌生的外在世界充满好奇和兴趣。然而“时光老人”却一反常情,仿佛一个看破万般世事的老者,任何事情都提不起他的兴致。他与周围的人们在价值观念上隔膜甚深,完全是一副悲观厌世者的怪面孔。他甚至认为在父亲裘德眼中神圣无比的基督寺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恐怖“监狱”。从他的言行可以看出,他的人生观、宗教观以及伦理道德观等都是偏离于英国传统的宗法观念体系的,而与以质疑和否定为基本价值立场的现代思想观念走得更近。另外,面对父亲和母亲的几度离合,“时光老人”作为长子却似乎完全超脱其外,对他来讲,这都是些无关痛痒的琐事,一切都无所谓。他像一个与世无争、与世无关的局外人;对待死亡,他也是毫不畏惧,为了减轻精神上的痛苦和生者的负担,他甚至轻易地选择结束自己尚还稚嫩的生命。“时光老人”的生与死都显得离奇无比,精神与行踪都完全悖逆于传统,他是一个“早出生了五十年的”现代人。在“时光老人”身上,我们不难捕捉到一种在高度物质化的世界里几乎不可避免的孤独感和被遗弃感,人在社会上孤立无依,没有归宿感。父母受到外界世俗的偏见和歧视,父亲丢掉工作,全家衣食无着,甚至到了要沦落街头的地步,所有这些都极大地加深了“时光老人”似乎与生俱来的悲观与绝望的情绪。在这里已不再是对个体的具体行为的描写,而是象征着全体人类孤独的生存状态,其中蕴涵着现代人的深刻的孤独。通过“时光老人”这一形象,哈代在作品中表现了在冷漠宇宙中,个体失去生命信仰、无所依托的精神漂泊感,失去爱与希望的孤独感,人与人彼此隔膜的孤独感。在这种痛苦的精神困境中,人类不能理解过去,又不能寄希望于未来,痛苦的灵魂不知该何去何从。这种心理上、精神上的孤独,是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精神体验。
“时光老人”精神上所集中呈现的上述特征——异化、荒诞和孤绝,是“新世界”来临人类精神特征的典型表征。从“时光老人”的形象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窥见后来一系列现代文学主人公的身影,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局外人》中的莫尔索等。正是哈代敏锐的观察,才使他注意到这样的新人的出现,并通过文学将他表现出来,使得他成为后来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个前行者和先驱。由此可见,“哈代是一个跨世纪的文学巨子,他的小说都是在十九世纪完成的,但是他小说中的新思想却已经跨入二十世纪。”[11](P68)
三、《无名的裘德》与哈代小说创作的困境
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整个西方世界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文学发展进程的事件。在思想文化领域,詹姆斯意识流学说的提出和迅速传播,“物理学带来了时间与空间的新概念,相对论打破了绝对观;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深入到了人的潜意识与下意识,佛罗伊德的性心理学用恋母杀父情结之类的观点来解释行为,一下子消除了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界限”[12](P3),以及叔本华和尼采的超意志哲学学说在英国知识界的广泛接受等。另外,英国的现代化进程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并进而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不安,如幻灭感、恐惧感和孤独感等——这便是如今所谓的现代精神的萌芽。上述所有这些,对当时人们从日常生活到内在精神面貌,从价值观到人类自身心灵的认识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所有这些也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哈代进行晚期小说创作时所处的时代大环境,较之他初登文坛时不同,正隐蔽地发生着某些不易为人察觉的变动。正是这些隐秘的变动,预示着人类精神世界与西方文坛内部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性思潮运动的悄然来临。如何准确认识和定位新的形势,如何创造恰当的文学形式以表现这样一个变动不居的新世界和裂变出的新人形象,是19、20世纪之交的英国作家共同面临的一个棘手难题,刚创作完《无名的裘德》的哈代自然也不能置身其外。对小“时光老人”的表现,便可视作家对上述问题做出的尝试性回答。
《无名的裘德》的文本将对现实主义成规的恪守和反叛各自推向了极端,使处于艺术成熟期的哈代付出一定的艺术代价,在文本的叙事中,情节与人物之间发生了断裂。正如有论者敏锐指出的:“《裘德》是一个存在着内部分裂的文本,主要表现为观念的不确定与艺术的不均衡。”[13]与此前的哈代小说文本在情节上刻意地遵循小说传统成规不同,《无名的裘德》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心理刻画上,则顺从了一个新的文学原则即现代主义的原则,超越成规,表现出两类突出的特征:人物形象的抽象化和人物及其话语的模糊性。这一点,在对“时光老人”的刻画处理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哈代对“时光老人”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新人形象的刻画一反其惯用的笔法,他未对“时光老人”这一人物形象的言语、行动与心理细节作写实性刻画,而是采用粗线条的象征化手法,用笔简练。作者似乎不愿在这一人物形象身上作过多的纠缠,让读者对其注目过多。这样的处理显然有悖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注重细节真实与性格典型丰满的文学主张的。这样的矛盾该做如何解释呢?依我看来,哈代之所以对这一人物作这样的处理,与其说是显露了作者独运的匠心,毋宁说是暗中透露了其难言之隐和难解之惑。哈代粗线条地运用象征的笔法处理“时光老人”,客观上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效果。“时光老人”作为人物形象朦胧而模糊,但却尖锐无比而让人难以忘怀。然而即便如此,换个角度看,在这部小说中,我们还是不难察觉到哈代对准确认识、理解和定位“时光老人”这一新人形象及其所代表的新的价值观念尚缺乏信心。哈代还难以将“时光老人”置于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对其做出准确而客观的判断与定位,在小说中,哈代一再用“幽灵”称谓“时光老人”,认为他“似乎异常缺乏一般儿童那前途有望的一切迹象”,他的心理是“病态的”。哈代无法清楚地说明与解释“时光老人”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更无法对其给予合理定位,因此以至于叙述者在对“时光老人”杀死自己亲弟弟妹妹并自杀的举动做出解释和评论时,也仅只能间接转用一位医生模棱而不确定的话:
我们中间正出现一些这样的男孩——这种男孩在上一代里从没听说过——这都是新的人生观念造成的后果。他们似乎过早地看到了生活所有的恐惧,而又缺乏坚忍不拔的力量去抵抗那些恐惧。将来人们会普遍不愿在世为人,而此事就是这种愿望的开端。[8](P311)(《无名的裘德》第六章第二节)
朦胧而模糊地处理“时光老人”这一威塞克斯农村农民破产过程中裂变出来的新人形象,在审美层看,哈代在处理这一形象时所显现出的疑虑和矛盾的情感态度,暴露出哈代还无法应对前文所提到的挑战。哈代对于“时光老人”的表现,一方面泄露了其眼界与认识上的局限,另一方面也将其在表现形式与刻画技法上捉襟见肘的窘状展露出来。完全采用传统的小说创作手法,是很难将现代人精神中的绝望、孤独以及与世隔膜的情绪完满地诠释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的。在19世纪末期的小说表现技巧库中,哈代还无法,至少是仍没有寻求到贴切的方法与恰当的形式,以表现当时急剧变动中的世界,以及如“时光老人”这样初具现代精神雏形的人物形象。正是由于对新人形象认识上的局限,难以在广袤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对其准确定位,以及困惑于不能寻求到更恰当的文学形式表现如“时光老人”一样的新人形象,这使哈代难以继续对自己以前所开发的题材作进一步的发掘与拓展。
哈代不仅需要解决时代给作家们提出的这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同时也要应对如何拓展自己先前所开发的题材库的挑战。在他小说创作的后期,尤其是在《无名的裘德》中,哈代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学实践回答和解决它们,然而我们却从中体察到作者的力不从心之感。这恰如著名英国文学史家哈里·布拉迈尔斯在评论《无名的裘德》时指出,该作品“在受苦受难的人类中横行无忌的恐怖超过了苔丝的苦难,而且也可以说超过了哈代对他的写作手段的控制。”[14]
概言之,与之前对威塞克斯宗法制农村社会的传统风习和田园生活以及农民的破产历程表现得适心应手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19世纪末期的哈代在小说创作上面对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些挑战至少涵盖如下三方面:(1)全面认识和准确定位如“时光老人”这样在威塞克斯农民破产过程中裂变出的新人和新的价值观念;(2)创造恰当的文学表现形式表现新人和新的价值观念;(3)对自己之前所开发的题材作进一步地发掘和延展,比如英国社会农村破产过程中裂变出来的新人前景何在。上述所有这些亟待解决的困惑,共同构成了哈代在小说创作事业上继续前行的障碍,它们是哈代的小说创作在《无名的裘德》后难以为继中不应被忽视的重要因素。正是因为这样一些在小说创作上一时难以排除的难题,加上当时外界对《无名的裘德》急风暴雨般的攻击,让晚年的哈代在《无名的裘德》之后便停止了小说创作,转而回到诗歌创作中。
注释:
①《德伯家的苔丝》出版后遭受的批评具体见《德伯家的苔丝》中译本译者序言和哈代英文版多版的原序言的相关段落,同时也可参看聂珍钊在专著《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托玛斯·哈代小说研究》(第204-205页)中对《德伯家的苔丝》出版后遭到的严厉批评事实的搜集与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