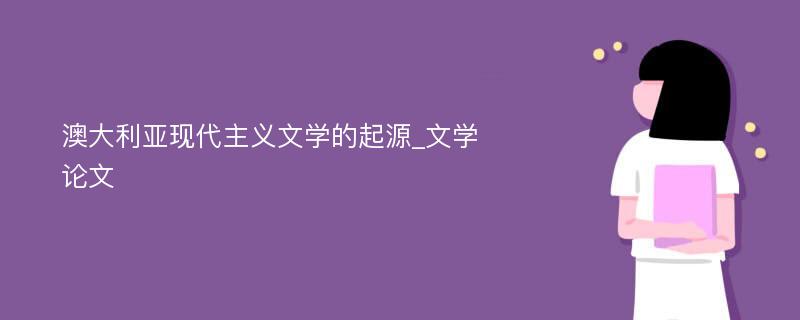
澳大利亚现代派文学的发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派论文,澳大利亚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二十年代是澳大利亚现代派文学的起点,尔后,两次大战间的二十余年可算是其萌发时期,在这二十年间,澳大利亚国内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萧条、二十年代的复兴和三十年代世界的危机。这些变化冲击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因而带来了文学的动荡时期,而国外文化新思潮的流入,国内文化界的流派兴起,为现代派文学的蕴育和产生提供了温床和土壤。
一、澳大利亚现代派文学端倪
我们知道,现代派文学的中心主题是着力表现人物孤独、疏远的内心世界,从叙述技巧上来看,主要是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来表现无所不知的意识流。依据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说弗菲的《如此人生》可称为澳大利亚史前的现代派作品。
如果我们要追潮澳大利亚现代派文学起源的话,我们发现最早是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具有现代派风格的诗歌,特别是自由诗的风格。1923年,悉尼创刊的《视野》杂志,在连续刊发四期之后,它就成了澳大利亚文艺复兴的一个论坛。其内容涉及很广,有古代作家的作品、文艺复兴的本身、浪漫主义运动等,但是它仅仅局限于那些充满生机很有希望的年青诗人,如肯尼恩·斯莱塞和罗伯特·菲茨杰拉德以及编辑杰克·林赛等。尽管他们这些思想在澳大利亚各处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对此作出反应,但这种思潮的本身已在澳土上生机勃勃地播下了种子,如当时对机械、汽车、现代技术持积极观点的未来主义思潮在三十年代许多短诗歌中都得以窥见。伯特伦·希金斯1933年在墨尔本出版的《莫底凯序诗》,可以说是澳大利亚第一部现代派诗歌的佳作,作品主要通过主人公莫底凯内心的独白揭示了古老宗教与代表新世纪的基督教之间的碰撞和交融。这部作品在风格和影响上等于英国早期的艾略特和之后的庞德的诗歌,其现代派处理的手法是在启示录和毁灭中寻找意义。这首诗作带着对澳大利亚的预示和展望在大萧条的高峰期问世,由于诗句比较晦涩难懂,影响的范围不甚广泛。
到四十年代末,澳大利亚一些小说就部分或全部采用了这种新的文学创作形式来表现其主题,如切斯特·科布的《莫法特先生》(1925)和《幻灭的岁月》(1926)、亨利·汉德尔·理查森的《理查德·麦昂尼命运》三部曲最后一卷《最后的归宿》(1929)、达克的《克里斯托弗林序曲》和怀特的《幸福谷》等,尽管这些作品全都是在国外发表的,但每一部都是以澳大利亚为背景创作的。切斯特·科布的《莫法特先生》(1925)和《幻灭的岁月》(1926)这两部小说都是在伦敦出版的,小说与乔伊斯在流放中写的《都伯林》有些类似,以悉尼郊区为背景来表现现代人生活的无聊和无意义。这些小说都采用了第一人称意识流的手法,小说的构思虽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颇为接近,但它没有像《尤利西斯》那样把“奥德塞”富有史诗意义的壮举作为一种象征来构筑框架和扩大其内涵,而只是在结尾部分采用了象征。理查森的命运三部曲最后一部《最后的归宿》,虽然保留了前两部小说十九世纪传统的创作风格,但却体现了一些现代派的手法特征,而且这种现代派特征对整个三部曲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这三部曲基于两种论点:一是宿命论,即主人公麦昂尼身体的疾病以及疯颠导致了最后的死亡;二是拜金主义导致了其精神上的压抑。作者在三部曲的最后一卷,通过梦境、想象和幻觉来突出麦昂尼个人内在性格的痛苦挣扎,小说一方面用宿命论来解释主人公的身体疾病和疯颠,另一方面又用现代派倾向表明,主人公精神上的压力也是拜金时代的必然产物。作品通过精神与肉体这两个方面的痛苦,使读者对整个三部曲有了一个再认识。这部作品还强调的一点是,欧洲的功利主义也同时被澳大利亚所吸收。
四十年代早期,我们还可以从霍普的诗歌中看到乔伊斯在《肖象》中的美学意识。霍普早期诗歌中的许多形象都带有超现实主义和弗洛伊德学派的特征。他在诗歌《索利达德的太阳和月亮》(1957)中则表明这些能够从这些非理性或他称之为“歇斯底里疯狂”的诗歌中体会到其内在东西。霍普对这些诗歌的内容并没有太大的抵触,而只是在其创作的手法上有所不同。在霍普四、五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他对艺术的主要贡献是他把这种形式和内容相互统一。之后,哈里斯和推崇先锋派和超现实主义的《愤怒企鹅》的艺术家和作家们组成了一个群体,他们积极提倡现代派的风格,以个人的经历和短暂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来从心理上定位。但这也遭到来自学术界的传统主义观念和马克思的宿命论两个方面的攻击,如哈里斯的超现实主义小说《植物眼》(1943),就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点。与哈里斯诗歌所表现的现代派技巧不同的是,斯图尔特和麦克斯尼他们为了体现这一手法从信手拈来的诗集中随意地挑选几行诗,然后拼凑起来以达到荒唐诗的效果。但评论家仅就荒唐这一点评论时指出,这类诗歌也应有个和诣一致的感觉,并以表面的荒唐来表达更深的内涵。
意象派直到六十年代才在三、四十年代广播剧的基础上以一种温和自然的方式体现出来,并且用以表达人物复杂的性格。令人惊异的是,一战之前在伦敦出现的意象主义竟然于澳大利亚作家诺曼·林赛的艺术观点完全一致,而斯莱塞和菲茨杰拉德都得益于林赛艺术观点的影响,他们利用具体而不是抽象的形象来进行意象派的创作。一战期间在瑞士发展起来的非理性艺术的最高形式达达主义,直到六十年代早期才在特拉萨和斯彻威特的幽默诗中给人留以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杰拉和阿特德的作品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后,五、六十年代勃拉特和伯克特的滑稽剧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尽管评论家在评论这两个剧本时认为它们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可能由于澳大利亚传统剧只注重事件本身而不关注方式,所以这类题材的作品还是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电影创作也同样如此,早期的电影大都以传统的澳大利亚人所熟悉的城乡背景和连贯一致的情节而吸引着观众,现代派对澳大利亚电影真正产生影响是到六十年代以后。
二、澳大利亚现代派文学发轫的特点
澳大利亚现代派文学的表现形式与在欧洲各国所体现的形式有所不同。欧洲现代派是对十九世纪的权威和拜金主义的一种反叛,而在澳大利亚它却是面对广为接受的活力论和达尔文主义宿命论的一种逆反。这一观点在二十世纪前叶的澳大利亚被许多知识分子所接受,尤为突出的是,澳大利亚文学史中被视为最富于活力和创新意识的诺曼·林赛所持的那种有机生命论的观点。他认为在当今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唯有审美价值是最高的价值,而这种有机生命的活力在创作过程中创造出的美感,则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永久的意义。林赛的活力论相当于牛顿古典机械论中的美学和生物学。二十世纪这些新的物理学和心理学给这些习惯于预见未来和宇宙标准的人们带来了信仰危机,而这些绝望的因素,自觉不自觉地都反映到那些没有信仰的诗人和小说家的作品中。在林塞早期的作品中,那种战后的精神颓废可在林赛的活力论中得以窥视,如“象征死亡的骷髅跟着他参加所有的聚会,这就象一瓶啤酒在他的公文包或大衣中。”(注: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111。),这种由维多利亚时代拘谨的道德观向现代化开放意识的过渡对林赛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这就象十九世纪末法国诗人离开古希腊的亚历山大一样。如果我们说用疏远和失落这样的词来解释先前一代作家对社会所做的关注的话,那么对二十世纪早期这种不稳定的反应,则表达了对超出宿命论意义观点所持的赞同态度。二十世纪的家庭已经不是十九世纪的丛林,而是产生“怪异思想的”(注: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204。)避难所。如《人之树》中的农夫,《沃斯》中的德国探险家及《来访者》中的画家都能召回已经死亡了的上帝和被遗忘的鬼神。堪称为现代派诗歌佳作的斯莱赛的《五铃》(1939),则通过对其亡友悼念的哀诗唱出一首对现代世界变革的婉歌,罗伯特·菲茨杰拉德的《隐藏的树身》(1935)也颇给人思考和回味。这两个诗人都想把他们十九世纪的活力论遗产和现代世界的不稳定性联系起来,但是当斯莱塞《五铃》于1939年发表时,世界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所以莱塞承认,在这一点上他的《五铃》是失败的。而菲茨杰拉德在他结构严谨的《隐藏的树身》和《论记忆》中也试图把这两者融为一体,特别是其后的《水中面容》(1944)则完全表达出对二十世纪的绝望。这种具有毁灭性但又带有启示性的嘲讽和浪漫以及所表现出的颓废情绪已成为现代派文学一种常规性的表现手法。不过,五、六十年代英国现代派作家的自杀、神精崩溃及早逝等情形在澳大利亚并未流行起来,这也许是澳大利亚现代派文学还给人们提供了一线希望的原故,这就如同林赛一样,他虽崇尚青春活力与激情,但与此同时他“对现代派文学又感到厌恶”。(注: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235。)用他的话来说“现代派艺术是一种怪诞,并不是一种自然进化的产物。”(注:Julian Croft,(New literature History of Australia),Penguin Books Australia Itd,1988,P411。)而恰恰是这一点,表明了澳大利亚现代派文学的发轫有别于它国之所在。
三、澳大利亚作家对现代派文学发轫的反响
澳大利亚作家对澳大利亚二、三十年代出现的现代派思潮的反应是持两种态度:一种是消极和敌视的,一种是积极的。
持消极和敌视的态度,主要来自国内一些人:国立图书馆、艺术画廊和一些专栏作家以丑陋和不能肯定为借口,对现代派文学艺术进行抨击,政府也籍审查淫诲、堕落之名对此进行抵毁,持保守思想的人则认为这是与澳大利亚道德标准背道而驰,以至与出版界保守力量联合起来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闻出版的受审与限制。另一种抵制还来自学术界的美学观点:传统的捍卫者认为,邪恶已入侵到真正艺术作品的艺术和美感之中,也入侵到皇家学院和最后的城堡墨尔本。当人们面对着黑人文化所引发的爵士音乐、立体派艺术和犹太人的财富所谓这些世界堕落的象征时,乃至二、三十年代初与英国有广泛接触的《公报》著名创始人之一P.R斯蒂芬森,也于1941 年象反对腐朽的犹太神秘主义一样开始反对现代派。与此同时,清教徒和美学力量结合起来,就对这一思潮作出更加有力的抵制。另外,对现代派持否定态度还来自于三、四十年代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强有力影响。
对现代派文学最早显示出积极倾向的是三、四十年代用这种文体创作的广播剧。例如,玛赛特·莫里利用想象以诗歌形式通过人物的对话对当今现实进行影射,这一成功掀起了四十年代广播诗剧的浪潮。三、四十年代的舞台诗剧在海外也一直是流行的,如安德森、奥登、艾略特、夫拉尔、伊斯沃德等作家的作品。1941年道格拉斯·斯图尔特的两个广播剧《雪中之火》和《金子般情人》在ABC广播电台播出之后, 在澳大利亚诗坛上又引起轰动。我们从斯图尔特的广播剧中还能够看到,以德国印象派为基础的舞台剧技巧与广播剧相结合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其舞台诗剧《奈德·凯利》的最后一幕中都得以充分地体现。出人意料的是,道格拉斯·斯图尔特这个传统诗的作家竟与充满活力论的诺曼·林赛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而使人们看到他们对现代派的某些手法所持的积极态度。到1940年,现代派作家所考虑的已不是二十年代引起人们轰动的那些自由诗的丑陋,而是以一种严肃的和超现实主义的丰富内涵重新再现这一题材。这种荒诞、滑稽而又带有启示性的修辞语言也通过广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汤姆斯的一些作品虽然是以自然主义的模式来创作的,但其心理学方面却采用了某些与二十世纪早期欧洲现代剧有些相类似的手法。另外有些短剧也用幻想和寓言等手法来表现,如《十字架》的人物几乎都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生活和白痴》和《妇女婚姻》等作品都是用寓言来表现冲突的。
杜拉斯·狄莫三十年代的剧本,也表明其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有趣的尝试。如在《妇女的心》这个剧本中,一个以客栈为中心的背景,则用来表示妇女的心,而在这个心的内里聚集的则是潜意识。之后还有些剧本,如斯蒂芬·休厄尔和路易斯·诺瓦拉的一些剧本都是以这种模式创作而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剧本是以传统的创作手法来表现其深刻主题的,如以自然对白和场景描写等手法表现的道德剧,甚至描述未来二十年澳大利亚宗教由于某种原因而被取代的一个寓言剧《过男人那种生活》也是用传统方式创作的。
四、现代派文学发轫对澳大利亚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
在澳大利亚文学中,使用这种典型的现代派手法最初取得明显效果的是,帕特里克·怀特创作出的一系列广播剧。他最早给人留下印象的是剧本《火腿葬礼》,这个剧本是集现实的背景、工人阶级的对话、诗歌的梦幻和借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把梦幻与现实相结合的技巧为一体而创造出的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他的独卷本诗集《耕作的人》(1935),则完全采用了格鲁吉亚语来表现三十年代的愤怒与焦虑。他的第一部小说《幸福谷》(1939)比起他的诗歌,无论在形式或手法上都更具冒险性与开拓性。他在这部小说中使用了大气外围的环境来与人的内心状态保持平衡,激发了幸福谷人们的梦幻心理,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并通过作爱等行为事件的描写与乡村永恒的生活韵律相比照来表现人类繁衍这一普遍关心的主题。这部小说内涵更多的是,使人们对澳大利亚生活中所产生的悲剧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怀特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大都如此完成的。怀特描绘各种人物内心世界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而且对二十世纪澳大利亚现代派文学创作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达克和斯特德还善于把现实主义和潜藏在日常生活下面无声流动的潜意识的东西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埃莉诺·达克三、四十年代的小说明显地表明了这种创作手法在澳大利亚的适应性,而且达克后来的小说也超出了他自己的创作视野,其《克里斯托夫的序曲》(1934)就是这期间在澳大利亚创作出的重要小说之一,他把罗曼蒂克的黑暗、瘸腿撒旦的妻子和为灵魂挣扎的金发女郎的护士以及倍受磨难的英雄医生等各种基因与因素融为一体,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澳大利亚所产生的混乱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进行准确细致的观察,既有理想主义的破灭又有宿命论的恐惧,并通过一个被人认为有精神病的生物学家的妻子来暗示,这是无法逃避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达克在其后来的小说《小公司》(1945)中,则明显地体现了其现代派风格的成熟。
在朱迪思·赖特的诗歌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蕴藏的一些思想是以现代派为基调的,而且表达了二十世纪中期西方文化的危机,如世界趋向于功利的堕落,原子弹的爆炸以及爱情的匮乏等。赖特的这种手法通过六十年代对自然界的贴近观察和描绘得以充分体现,如1963年发表的《鸟》,其主题都是用隐喻来表达的。与斯图尔德浪漫风格不同是,赖特的现代派风格大都是通过难以言表的内涵意义来体现的。这一时期表达这一主题的诗人大都以传统的韵律诗形式,从宇宙某一特殊点来进行观察、暗示和隐喻,这种风格被道格拉斯·斯图尔德大加赞赏。
在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早期显示出现代派倾向的另一个重要的小说家是姆乔里·巴纳德。在他的《柿子树和其它故事》(1943)这部小说中,细节的真实就很少,而象征的意味却很浓。她与夫劳拉·埃德肖合作,在这一时期创作了一系列有独特见解的小说,在《明天又明天》(1947)中,她运用充分的想象力以一种自我反省的叙述方式来表现其主题,而且在结构上还显示了某种后现代主义的复杂性和寓意性,即对现实寓言而不是再现现实。巴纳德1929年出版的题为《一座房子》的这部小说,也是以“现实历史”的手法来进行创作的,这也是三、四十年代很流行的一种创作形式。
面对着信仰危机、冲突与毁灭的冷战世界,韦伯比其他任何澳大利亚诗人都更多地关注着民族的认同问题。尽管韦伯早期的诗歌显示了某种对二十年代现代派的抵触,但在他四十年代的诗歌中,充满了那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 他的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维本·博依德雷德》( 1936),就是利用了多种声音和自我意识的叙述形式在结构上有所突破与创新的。韦伯还借鉴了斯莱赛在《库克船长的五个图像》(1932)中所开创的叙述技巧,并精炼和发展了斯特尔德1941年创作的广播诗剧。韦伯的诗歌也涉及了人物内心生活的烦燥及战后的喜悦。他在五十年代利用多角度的手法创作了一系列的诗歌,他试图通过这种探索性的诗歌来表达一种希望的感觉和治愈世界的愿望。这些诗歌大都是她个人的感受,这也就象韦伯长期与她自己的精神分裂症相斗争一样,她在《雷卡特在剧院》(1947)和《独自巡回》(1961)中,集中对探索者的内心活动进行了描述。韦伯认为利用大众的语言似乎更加富于表达,并能引人入胜。韦伯后期的许多诗歌仍带有广播诗剧的特点:形式活泼,充满活力的视觉形象和通过语言令人信服等特点。
五六十年代后期另一个重要的现代派小说家和诗人是伦道夫·斯托。这一时期他发表了五部小说,其中两部《归宿》(1958)和《圆木林》(1963)都是采用的了早期现代派小说和诗歌的技巧,来探索人物内心的孤独和澳大利亚自然主义的画面情景。斯托1965年发表的《旋转木马》是这一时期的另一部有关描述澳大利亚童年的重要作品,它以一个宿命论的形象描绘了一个家庭的结构,其中内含的旋转则象征着一种周而复始的良性的循环。
与斯托在澳大利亚国土上所描绘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彼得·波特的以“奇”和“怪”为特点的作品。斯托在这儿以一种恬静的不具主观色彩的中立风格把其罗曼蒂克的诗歌和歌谣与童年对澳大利亚的热爱相结合,创作出他的诗歌;而波特的风格则主要是在英格兰得到发展,他倾向于古典派,他的诗往往是从一个真空或“埋葬死人的地方”开始的(注: John Barnes,( The Writer in Austral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669,P241。)。 但是波特强调他作为一个诗人的重要性,他说他要对二十世纪欧洲文明的灾难有所感觉。波特的独到之处还在于他能够很轻易很流畅地把现代派早期的风格与三、四十年代英国诗人所采取的诗歌创作倾向溶为一体,把人们的怀疑不信任与个人无可奈何的感觉和谐地表现出来,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一个澳大利亚现代派诗人的地位。
就象帕特里克·怀特在其小说《战车上的骑手》(1961)、《坚实曼陀罗》(1966)和《活体解剖者》(1970)等作品中越来越朝着印象派方向发展一样,其他一些小说家则在现实世界和抽象世界这两者之间保持着一个等同的平行,而且以此来体现他们的现代派特点:如伊丽莎白·哈罗尔在其最好的小说《遥远的展望》(1958)中就描绘了一个来自宿命论家庭的青春少女,要不就与家庭彻底决裂,要不就重复其母亲乃至祖母的那种可怕的令人诅咒的人生遭遇。她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出版的小说中更加偏重人物心理流程的刻画,她的语言简炼,但对人物和场景的观察都是以低调进行的。
我们从上述这些现代派诗歌和小说的作品与创作中可以看到,澳大利亚早期的现代派文学是以一种动荡不确定的历史为背景的,而早期作品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对未知或可能性预示的一种探索和偿试。尽管三、四十年代处于一种动荡的时期,但是这一时期作品的核心仍然是很确定的,那就是无论人们对现代派文学持否定和排斥的态度或是持观望和赞同的态度,人们毕竟还是接受了它,而且这种接受的确定性就犹如人们必须要常常给花浇水施肥、必然有人会用那只永不休止的笔来写作一样。澳大利亚现代派文学发轫的特点,就是以这种形式得以体现的。正是那些善于在文坛上播种的开拓者们,以他们特有的时代敏锐性把澳洲本土文化与欧洲现代派技巧相融合才蕴育出现代派文学的艺术萌芽,为澳大利亚文学注入了新的生机、赋予了新的内涵,并为澳大利亚六十年代现代派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