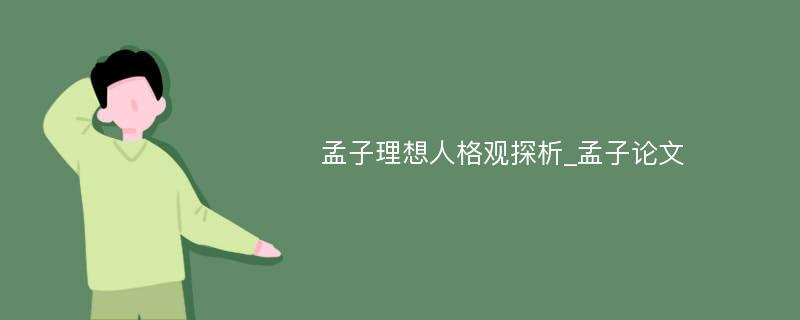
孟子理想人格观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子论文,人格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孟子生活在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的战国时期,这是一个充斥着“开疆扩土”和“霸业一统”行为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处士横议、豪杰辈出的时代。动荡的岁月激起了人们对美好人生和理想的追求,也激起了先哲们对人生的反思,孟子站在批判现实的立场上,绘制出一幅兼具独立精神和淑世精神的理想人格蓝图。
一、理想人格的基础
儒家一般都以圣人作为理想人格,孔子认为圣人不仅在道德修养上已达到极高的境界,而且能兼济天下,成就“博施于民”的政治功业。孟子的理想人格观在整体上承接了孔子的圣人人格模式,但在具体内容上则有所差异。在孔子看来,圣人规格极高,即使是尧舜也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圣人,自己就更不敢以圣人自居了;而孟子则将圣人标准降至一格,把孔子的“圣人”理想落实到现实中来。
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提出人格平等的思想,从而构成其理想人格成立的哲学基础。一方面,从人的行为本能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1 〕(以下引文只注篇名)孟子宣称仁义礼智之善并非强加于人的外来之物,而是每个人生来就具有的善性。另一方面,从逻辑上看,“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圣人与我同类者”。〔2 〕这里孟子又从“类”概念出发,论证了圣人与普通人作为同类在性善上是没有不同之处的。
基于人性的平等,在众与圣人之间,孟子没有严格划界,而是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为”,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因为,人性中本来就具有善的端倪,“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所以,个体只要将处在萌芽状态的潜在善性加以扩充弘扬,使之转化为现实的品性,就能成为德性高尚的人,反之,“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 〔3〕孟子举例说:“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4 〕圣人之所以为圣,关键在于率性而为,尽人伦之至,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追求。既然这样,那么无论是国君,还是庶民,只要努力学习圣人,修养心性,力行践履,就有可能与圣人同格,即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5〕
二、理想人格的内涵
孟子以“人性固善”这一先验设定为前提,逻辑地证明了人格平等的可能性,如何使这一可能变为现实,这首先要确定理想人格的追求目标,孟子提出了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的互补人格,追求“浩然正气”与“博施济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孟子的理想人格涵养基本上是一个由内而立与由外而达的双向互动过程。
(一)修己善其身
孟子认为,社会群体人际关系的道德和谐,是以社会个体的自我完善为基础的,所以,他十分重视道德观念上的自律与自重。孟子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6〕这说明提高人的内在人格修养是首要的, 而一个人的内圣最重要的又是培养一种独立精神。在先秦儒家中,孟子可算是最讲独立精神和主体意识的人,他继承了孔子“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7〕的儒家传统,进一步突出了人的独立意志。 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志既然是最高统帅,那么它首先必须是独立而有威信的,体现在人格内涵中,则为独立意志和人格尊严。
独立意志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这一言论似乎是清高自负的,甚至被斥责为“以己之长,方彼之短”〔8〕, 但孟子的自信是建立在坚守自己志向的基础之上的,他有自己的解释:“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9〕即是说, 君王仗势贪图享受,与我立志于古代圣贤之法相比是不值得称道的。孟子以自己志向高远来傲视王侯们的富贵高显,正是对独立意志地位的突出。
孟子坚持独立意志的人格观影响到他的君臣观,正因为孟子志存高远,不为干禄,所以,他在君臣关系上大胆地提出了相互对待的问题:“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而且“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10〕这就意味着,臣民虽然在权势地位上与君王有所差别,然而在个人意志上却是平等的、独立的。孟子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子那里,人的意志虽然是独立的,却又不是绝对悬空的,而是有所傍依的。当有人问孟子何谓“尚志”时,孟子答曰:“仁义而已矣”,即行仁义罢了。他把行仁义之实看成是做人的高尚境界与标准,“居仁行义,大人之事备矣”。〔11〕孟子对王宫巨侯的藐视也正是建立在坚守仁义基础之上的,他引用曾子的话说:“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12〕
孟子要求立志于仁义显然是对孔子“仁”学的继承,但又作了新的解释,“仁,人心也;义,人路也”。〔13〕朱子注曰:“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仁义都起源于人心的德性,只不过前者是从主观意识上说,后者是从客观行为上说。“居仁由义”,就是要求人们通过“仁”对主体之间的伦理行为进行反思,通过“义”对这一反思作出正确的裁断。
由孟子对“尚志”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孟子倡导独立的人格意志,还包括主体的独立判断。孟子继续扛起孔子“反乡愿”的旗帜,对那种人云亦云、毫无原则的“乡愿”之流,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当万章问老师什么是“乡愿”时,孟子说:“阉然媚于世者,是乡愿也”。当万章又问为什么乡愿为“德之贼”时,孟子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14〕这就是说,“乡愿”之流,欲非之则无可举,欲刺之则无可刺,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洁而似廉洁,他们的言行毫无原则,是是非非,如果说有什么标准的话,那只是“使当世人皆以为善则可矣”。〔15〕此等之人,不能独立判断是非,当然就不可能有尧舜气象。因此,要实现独立的人格意志,就必须反对“乡愿”。
与对待“乡愿”的态度相反,孟子非常赞赏独立的理性判断,他引用曾子的话说:“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16〕通过“反身循理”,作出裁决,正体现了一个人的独立判断能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在孟子看来,便具备了“好勇”的品格。
人格尊严 人的独立精神离不开人格尊严,孟子由人格平等的自我意识出发,不仅认为人应当持守自己的志向,而且还应该维护人格尊严。孟子的“大丈夫”人格就是在任何环境中都保持自己尊严,坚守自己操守的典范。
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7〕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遇,“大丈夫”始终保持着不卑不亢、刚强不屈的人格形象。那么这种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气节是如何塑造的呢?孟子认为,一个人的气象来源于他对美好道德情操的追求,最重要的就是对“道”的追求。“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尧舜之于天下,不以为泰”。〔18〕这就要求为人处世,必须维护“道尊”,“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认为人应该自重自安,不为外物所诱,不因贫贱而移,不因富贵而淫,自始至终地维护人格尊严。若出不能行道,便是苟取,若处不能尊道,便是苟活。若邦无道还当官领俸,则是士之大耻。
“道”落实到具体的人伦关系中,就是礼义忠信等内容。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19〕所谓“所欲有甚于生者”,就是指对人格尊严的维护。“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20〕朱子释曰:“虽欲食之急,而犹恶无礼,有宁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恶之本心”。〔21〕不先其本心,也就不会失去人格尊严。“呼尔而与之”、“蹴尔而与之”,都是不尊重对方的人格,不把人当作人看待,这是普通人也不能接受的。在受与不受之间,孟子坚持以礼义为原则,即使是君臣之间也应如此,他说:“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22〕
孟子进而指出,人如果以失去自尊为代价换取不符合“道”的身外之物,对于人格的培养是无所增益的,他提出:“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23〕对于为官入士,孟子的态度也非常明确,“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24〕人若沦为钻穴隙之类,那么即使是高官赫赫,也失去了自己的气节。孟子又曰:“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25〕这就是说,有志于“道”的人,本着“正己而物正”〔26〕的态度,时时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气节,维护自己的尊严,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做到自尊自洁。
基于对人格尊严的维护,孟子颂赞乐道忘势的圣贤之士。他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乎?”〔27〕这种乐自己的道,忘别人的势的风范,体现了大丈夫不卑不亢,刚强不屈的品格。孟子将“道”树之于“势”之上,认为人的内在道德价值高于功利价值,实际上是对人格尊严的高扬。因为“道”的真正力量对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是内在超越的,它属于精神的力量和权威,孟子追求理想人格的超功利性,是想弘扬那种用物质力量无法摧毁的精神力量。社会的“士”虽然没有足够的物质力量与物质化了的政治强权相对峙,但却可以通过“志于道”来维护独立自尊的人格。
当然,独立自尊的人格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精心培养和持守。关于人格成就的途径,孟子提出了“持其志, 无暴其气”的方法〔28〕。所谓“持其志”,就是指敬守其志, 孟子认为学者要象学奕那样专心致志,“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29〕所谓“无暴其气”,就是指致养其气。“志”与“气”之间是一个互动的循环过程,“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二者必须交相培养,以气养志,持志率气,才能达到“不动心”的境界。当公孙丑问老师所说的“不动心”相对于告子所说的有哪些长处时,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何谓“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30〕就是说,它作为气,充实无间而无所亏欠,“至大初无限量,至刚不可屈挠”,它作为气,借助于人间正道,由不歇的正义积累而成。朱子说:“人能养成此气,则其气合乎道义而为之助,使其行之勇决,无所疑惮;若无此气,则其一时所为,虽未必不出于道义,而不足以有为矣”。由此可见,孟子把浩然之气看成是人格力量的渊源,有了这股气,就有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和宁折不弯的“大丈夫”气概。
(二)达人济天下
“修己善其身”虽然是孟子理想人格的首要内涵,却又不是全部。在孟子看来,只有在修身养心的基础上,推己及人,兼济天下,才能使理想人格充实完满。
推己及人 孟子继承了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思想,进一步提倡推己及人。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31〕万物之理为人心所先天具有,其存放得失全在于主体的追求或舍弃。当一个人至诚无息地保持其善良本性,就会有莫大的快乐。而所谓“强恕而行”,就是努力按照推己及人之道行事,孟子把它看作为成就理想人格的便捷途径。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32〕这里用相互对待的观点说明:推己及人,不仅因为尊重别人而成就了他人的独立人格,而且也因为得到别人的尊重成就了自己的理想人格,它可以产生交互发展的效果。
孟子所说的推己及人,主要是指使人的善性得到推广,他要求仁德之士应该广泛结交天下善人,带动众人一道从善,即所谓“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33〕孟子还指出,人们在推广本心善性的同时,也可以学习别人的长处,“大舜有为,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34〕圣人乐善之诚,没有彼此之间,孟子希望人们在与人为善的道德实践中取长补短,不断完善人格。
然而,能将仁义礼智等善性推及到他人身上,仍然未必可以实现完满的道德人格,孟子追求的最高人格理想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可以说是推己及人思想的进一步升华,是人格化的天地与天地化的人格相互交融的境界。“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35〕便是这一理想境界的表述。它的意思是,君子所经历之处,人无不化,心所存主处,神妙不测,其德业之盛,与天地之化同运并行。
那么个体在社会人伦关系中如何才能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呢?孟子认为化、神之境来自于真善美的统一,“可欲之谓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36〕在这一主体精神境界递进的阶梯中,“神”乃是至善至美之境。孟子所说的“神”并不是一种人格神的存在设定,而是作为人格修养的最高精神境界,正如程子所说:“圣人不可知,谓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非圣人之上,又有一神也”。〔37〕正因为“神”并不指人格神,而是作为完美道德人格的精神境界,所以,它是可以去追求的,也只有以追求这一崇高精神境界为人格理想的目标,才能真正获得“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快乐情感体验。
兼济天下 孟子把社会理想作为完整人格的理想王国,希望君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38〕他的推己及人的人格观体现在社会理想上则是治国化民,兼济天下。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39〕这就是说,若能推亲亲之心及于他人,则能保民而王,否则将众叛亲离。
孟子宣扬推恩及民的思想,是为实现施行“仁政”,推行“王道”的社会理想。他对自己的“仁政”理想是充满信心的,认为当时的形势已经具备了实现王道的可能,即所谓“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40〕孟子对“王道”理想亦有具体描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41〕为了实现仁政、王道理想,孟子还提出了教化民众的方略:“民众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是故圣人忧之,使契司为徒,教以人伦”。〔42〕民众往往不知反求本心而放逸怠惰,这就需要设官而教以人伦。孟子甚至认为善教优于善政,他分析道:“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43〕教化人伦,不仅能博得民爱,赢得民心,而且还能造就出一大批深谙封建伦常的理想人格,更好地维持既定的统治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孟子要求普及理想人格乃是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奠基。
既然治国化民的关键在于将人格理想普遍化,将人先天具有的善性扩而充之,那么要实现社会理想目标,最重要的还是依靠主体的道德自觉,孟子将之归纳为“为与不为”的问题,而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试图以此唤起人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性。他引用伊尹的话说:“天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接着又评论说:“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44〕伊尹因为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而被孟子尊崇为圣人,“伊尹,圣之任者也”。〔45〕所谓“自任于天下”,就是主体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孟子认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46〕可见,以天下为己任同样是实现王道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孟子在宏扬主体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的同时,对那些不愿行仁政却推托其辞的统治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47〕他希望君王不要怪罪年岁以推托责任,而应自反修政,使天下百姓归之若流。
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虽然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持既定的统治秩序服务,但作为社会理想毕竟有其超越现实的闪光之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各国君王都留意于开疆扩土,常常以攻伐为贤,孟子提倡王道,反对霸道,要求发掘人性中的善端,培养人们美好的道德情操,毕竟反映了对安定和谐的生活的向往。他周游齐、宋、鲁、魏等东方各国,孜孜不倦地进行布道,可最后却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国君愿意真心诚意地实行王道,这使孟子的幻想一次次破灭。
三、互补人格观的提出及影响
当理想与现实的鸿沟无法跨越时,孟子便选择了互补的人格理想,即所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天下有道”或“达”时,则匡时救弊,兼善天下,当“天下无道”或“穷”时,则存心养性,独善其身,这是儒士根据具体情势来调整自己行为的方式,然而无论是得志而显达,还是穷困而落泊,其内在的精神品格是始终不渝的,仁义忠信之“天爵”,都是应该乐善不倦的。
当然,作为积极入世的儒家代表,孟子希望既能在人格修养上达到至高境界,又能在社会理想上实现兼济天下的目标,二者本是互动的统一。他之所以提出互补型人格,乃是对“道”不能行的无奈。以孟子周游列国为例,他在55岁那年二度适齐,与齐宣王多次论政,由于宣王认为他学说迂腐,所以,彼此距离越来越远,孟子准备离齐归乡时说:“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48〕一句“不得已也”,道出万般无奈,无奈之余,孟子仍然没有放弃淑世的理想。他在昼邑歇了三个晚上才离开,暗中希望齐宣王能派人追自己回去,可他的最后一个幻想还是破灭了。尽管如此,孟子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他声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49〕这与其说是清高自许之言,不如说是圣贤忧世之志。
孟子人格理想中的这一互补特征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的,它直接师承了孔子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50〕的思想,继而又影响了身后的历代儒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互补人格往往成为封建士大夫隐退和复出的依据,它一方面阻碍了人们在逆境条件下与世抗争的进取精神,另一方面对人们培养坚定的信念和美德又有积极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在无法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时,往往引身而退,但在退的同时,又随时做着进的准备,尽管这种机会是渺茫而难期的,但为了实现自己的信念,他们总是坚忍持志,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来自勉自励,把逆境看成坚定意志的考验。颜元就是这样的人物之一,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一直不懈地宣传,临终前还对学生们说:“天下事尚可为,汝等当积学待用”。
儒士之所以“积学待用”,而不苟得官位,归根于主体独立精神的支持。孟子的大丈夫人格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对激扬中华民族自尊自强的品格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宋代文天祥有“丈夫壮气须冲牛”之豪言,林逋有“大丈夫见善明,则重名节如泰山;用心刚,则轻生死如鸿毛”之壮语。在中国历史上,诸如此类的诗句不胜枚举,它体现了仁人志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气节与高志向。南宋理学家胡宏对“大丈夫”人格曾作过哲学的阐述。胡宏一生不耽仕途,他在《与秦桧之书》中说,功名利禄为其“志学以来所不愿也”,谓自己志在“立身行道”,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五峰先生所理想的“大丈夫”是“傑然自立,志气充塞乎天地,临大节而不可夺,有道德足以赞时,有事业足以拨乱,进退自得,风不能靡,波不能流,身虽死矣而凛凛然长有生气如在人间者”。〔51〕几千年来,孟子的“大丈夫”人格形象一直被颂赞。
综上所述,在孟子的人格观中,如果说其人格涵养过程是积极互动的,那么他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态度,则不无消极互补意义,但孟子始终予淑世精神与独立精神以相互充实的态度,所以,它对后世的影响在总体上仍然可以说是积极的。孟子所倡导的互补人格及其在后人身上的体现,反映了我们民族精神中对社会事业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人格修养上的浩然正气。我们今天研究孟子的理想人格观,如果能本着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的原则,将之推陈出新,那么它对现代人格的塑造和培养则不无借鉴价值。
本文于1998年1月11日收到。
注释:
〔1〕〔2〕〔6〕〔13〕〔19〕〔20〕〔23〕〔29 〕《孟子·告子上》。
〔3〕〔16〕〔28〕〔30〕〔34〕〔38〕《孟子·公孙丑上》。
〔4〕〔5〕《孟子·告子下》。
〔7〕《论语·子罕》。
〔8〕〔15〕〔21〕〔37〕朱熹:《〈孟子·尽心下〉章句注》。
〔9〕〔14〕〔36〕《孟子·尽心下》。
〔10〕〔32〕《孟子·离娄下》。
〔11〕〔26〕〔27〕〔31〕〔35〕〔43〕《孟子·尽心上》。
〔12〕〔40〕〔48〕〔49〕《孟子·公孙丑下》。
〔17〕〔18〕〔24〕《孟子·滕文公下》。
〔22〕〔33〕〔45〕《孟子·万章下》。
〔25〕〔44〕《孟子·万章上》。
〔39〕〔41〕〔47〕《孟子·梁惠王上》。
〔42〕《孟子·滕文公上》。
〔46〕《孟子·梁惠王下》。
〔50〕《论语·泰伯》。
〔51〕《五峰集》卷二。
标签:孟子论文; 大丈夫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孟子·尽心上论文; 独立人格论文; 国学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乡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