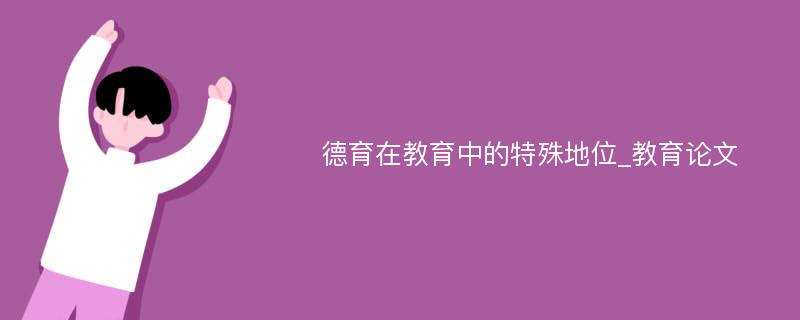
“德育”在教育中的特殊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育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是教育界至为关注的问题。我国如今有“以德育为核心”一说,更显示出对德育异乎寻常的重视。不过,这个判断的合理性尚待论证。或谓“德育在教育中从来都居于首位”,那就更须接受经验事实的检验了。关于这个论题,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德育在教育中的地位”本身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如何发生的?涉及“德育”在教育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它应处于怎样的地位,又须分析,其中所谓“德育”的含义是什么,“教育”的含义是什么?什么意义上的“德育”在什么“教育”范围内居于什么样的地位?总之,不能一概而论。
1 本来意义上的“德育”为“道德教育”。它是同智育、美育和体育对举的概念。这是狭义“教育”诸成分的划分,这种划分又以学生个人身心发展为基础。其中健康的身体作为精神发展的生理基础是“教育”的前提;“教育”旨在发展人的精神,特别是使个人自然的知、情、意心理成分发展为真、美、善的精神素养和情操,并使人的精神得到健全的发展,相应地要求教育中的“智育”成分、“美育”成分、“德育”成分保持较为均衡的关系,使精神发展与身体发展保持较为协调的关系,防止因偏废而导致学生精神失调、身体衰弱。这是德育、智育、美育、体育划分的缘起。
这是近代教育的基本观念。现代教育实践业已证明,近代针对中世纪教育弊端形成的教育观念和“教育”诸成分划分的意义相当有限,随着现代教育的演进,它已经趋于淡化。
1.它假定教育旨在发展学生的个性,并使学生的身心协调发展,使学生的精神协调发展。
这是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变时期针对在中世纪教育精神独裁统治下扼杀人的自然本性与独立人格的教育提出的假设;后来的经验证明,每个人出生后,都免不了要经历个体社会化的过程。现实的个性不纯粹是自然的心理倾向性与心理特征,而是不同的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显示出来的差异性。这样,原先基于发展个性的“教育”诸成分划分的构架,在现代就不尽合乎时宜;现代教育的趋势是,把教育(广义)作为实现个人社会化的过程,其成分不仅有智育、德育、美育和体育,还少不了社会教育,同时智育德育美育不仅陶冶个人的真善美精神与情操,还具有反映现实社会需要的内涵,以促进个体社会化。
2.“教育”诸成分中的“德育”,原指道德教育,而现代社会中学校所实施的道德教育已经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道教育;除了“德育”以外,还实施包含一定“政治教育”成分的“社会教育”。
如果说狭义“德育”一向受到重视,那么像我国这种包括品德形成、社会政治教养和陶冶精神与情操的广义“德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也就更加不可低估。
3.“教育”诸成分划分原先只是出于促使学生身心以及精神各方面健全发展的考虑,并不以此为学校教育工作职能划分的基础。
因为狭义“教育”是同“教学”对举的概念。学校对学生施加教育影响,主要诉诸“教学”,辅以称之为“训育”的教育举措。意味着即使“德育”也主要诉诸“教学”;为了提高“德育”成效,主要从改进“教学”入手。例如19世纪的德国,讲求“教学的教育性”,20世纪的美国,讲求课程的社会价值(其中包括学生的主动参与)。依杜威之见,课程的社会价值也就是其道德价值。如果说,就连狭义的“德育”都主要诉诸课程教学,那么像我国所实施的广义“德育”,单靠专门的“德育工作者”进行的“德育工作”,其成效也就可想而知了。
2 尽管任何时代的教育中,或多或少都具有各种成分,严格说来,把教育划分为德育、智育、体育之类,基本上是近代的事,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事。
1.中国古代教育基本上是道德教化。《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教育本身在于明“明德”、亲“民”,最终使人达于“至善”;《中庸》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之说,“教”即“修道”,把整个教育归结为德育的意向,再鲜明不过。
西方宗教统治的国家长期实施的宗教教育,同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在内容上虽有世俗性之别,实无二致。如今“教育”一词的含义虽与古代不同,但“教育”中的一义,即作为“道德教育”同义语的一义,在中国至今依然通用。(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西方德语“教育”一词亦含这一义。
中国古代“传道、授业、解惑”之分,非指工作分工。“授业”旨在“传道”;“授业”本身虽含有某种知识成分,毕竟不是科学知识,或者说,主要不是科学知识。把它视为”智育”,过于牵强;“解惑”是“传道”、“授业”的补充。要论德育的地位,在古代教育中可算是至高无上了;如以古例今,由以证明如今德育的重要,虽有不少尝试,实可不必。因为那种不以“智育”为基础的非理性的教育,是一种蒙昧。
2.西方近代黎明时期,自然科学勃兴,经过缓慢的过程,科学知识逐渐向教育渗透。在17世纪已经有人察觉:学校“一直到现在都只在追求智力方面的进步,没有别的”。(注:夸美纽斯:《大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新2版,第62页。)虽透露了“智育”的消息,毕竟言过其实。至少直到19世纪上半期,道德教育仍在整个教育中占有绝对优势。
17世纪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虽大力张扬“泛智论”旗帜,却对学校过分追求“智力方面的进步”,深感不安。他把“虔信”、“德行”与“博学”并举,而把教育的天平倾斜于“虔信”与“德行”一边:“虔信与德行是教育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除了《圣经》以外,教给青年人的一切东西(科学、艺术,语言等等)都应该纯粹当作附属的学科去教授”。(注:夸美纽斯:《大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新2版,第61、193页。)算是近代“德育第一”说的先驱;稍后,洛克把“教育”归结为“四件事情”:德行、智慧、礼仪与学问。其中所谓“智慧”似近于“智育”;实指在社会关系中善于自处的能力,“学问”近于“智育”,但“学问最不重要”。(注:洛克:《教育漫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132页。)抉择的意向也至为鲜明。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社会思潮风云激荡,传统教育的格局已经难以逃脱新世纪对它的审视。卢梭以全新的视野观照德育。他力主按人生的不同阶段,转移教育的重心:婴儿期以身体养护为重点,儿童期(2岁半至12岁)以感觉训练与积累直接经验为主,青年期(12~15岁)重心移向智育,到青春期(15~20岁),才把教育的重心转为道德教育、宗教教育以及性教育。因为他所认可的“道德教育”,是在理智发达基础上的教育,即理性的、自律的德育;18世纪晚期,在法国大革命的急风骤雨中,孔多塞为冲破宗教与封建的藩篱,砸碎人民心灵上的精神枷锁,主张排除教育中的宗教与政治思想成分,在国民教育中只实施智育,谋求国民的启蒙。尽管从那时起,智育逐渐形成,智育的地位缓慢地向上移动,但在此后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里,道德教育与宗教教育仍在整个教育中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在保守的德国教育中更为显著。
19世纪初,赫尔巴特把教育目的分为两个层次,即:“可能的目的”与“必要的目的”。前者指“多方面的兴趣”,即“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后者指“道德性格的力量”。“必要的目的”,也就是教育的最高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称“德行是整个教育目的的代名词”。(注:赫尔巴特:《教育学讲授纲要》,《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93页。)随后,黑格尔把“教育学”称为“使人们合乎伦理的一种艺术”。是因为他把教育理解为使人从原有的天性(自然本性)转变为另一天性(精神本性)的过程。(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0~171页。)要论19世纪上半期德育在思想家、教育家心目中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斯宾塞可算是在近代率先明确地把“智育”、“德育”与“体育”并列、分别加以论述的教育家。他的着力之点在于提高科学在教育中的地位。此后,在他和赫胥黎的倡导下,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语言科学逐步纳入普通教育课程。
赫尔巴特把“德行”视为可与他意向中的“教育目的”置换的名词,是由于他所用的是近于德育的那种“教育”概念,他把教育设想为从“管理”到“训育”、再到“教学”逐步递进与深化的过程;还由于他所认可的“教学”是“教育性教学”,是古典人文学科占优势的教学。所以,在他的体系中不存在如今所谓“教学”与“德育”的矛盾(其实,它们本不是对应的概念)。在课程变化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随着分化了的各种近代基础科学转为学科,各门学科知识系统化,学科门类、学科知识容量增加,教学越来越“智育”化,“智育”在整个教育结构中越来越膨胀,教师之间的分工越来越固定,加之在劳动力需要专门训练以后,教育同就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智育同德育的矛盾日益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3.19世纪30~80年代,西方英、法、美、德、俄诸国先后完成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后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传播,工人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自觉地投入斗争,资本主义文明出现危机;德国“有教养的等级”对此最敏感,认定随着物质文明的演进,精神文明日趋匮乏。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德育问题重新引起关注。
德育理论在杜威那里加大了演进的跨度。他对传统德育、特别是“直接道德教育”的效果深表怀疑,基本上放弃了狭义“德育”概念,但又比谁都更重视为他所放大了的“德育”。他把学校视为“维持生活和促进社会福利”的“社会机构”,主张在总体上以学校的社会价值衡量公共学校制度的道德工作和价值。“教育制度不承认这个事实遗留给它的一种伦理责任是不负责任的”。(注:杜威:《教育上的道德原理》,《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不只是一部分教师而是所有教师都应对社会承担“伦理的责任”;为此,道德教育不局限于“直接的道德教育”,主要诉诸“间接的道德教育”,即通过学校集体生活和发掘课程中潜在的社会成分,进行道德训练,而学校集体和教学本身不同于旧的一套。即在学校内部“重复社会生活的典型环境”,使学生作为“社会的一员”参与校内社会生活,置身于社会关系之中,并对社会生活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从中获得道德经验;学生通过参与实际活动所获得的经验,或者说,他们的经验不断改组、改造和变化,这是最可靠的知识,教育就是经验不断改组、改造和变化的过程。杜威的“德育”模式在牺牲系统的知识传授、严格的智力训练基础上消解了德育的矛盾,但也因此而撞到南墙上。此后,德育与智育作为工作分工,更为识者所不取。
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教育普及的程度提高,在若干国家升学竞争加剧,加深了智育与德育的矛盾,以至这个矛盾的处理成为令人困惑的难题,我国教育界也被卷入这种困惑之中。
3 从“德育”在“教育”诸成分中地位的变化中可以对“德育”地位问题获得进一步认识。
1.狭义“德育”原是同“智育”、“美育”、“体育”对举的概念,故“德育”在“教育”诸成分中的地位,只是把它同“教育”中的其他成分加以比较。由于“美育”、“体育”的实际地位不足以同“德育”比较,所以实际上是把“德育”与“智育”加以比较。这种比较的意义在于:基础教育为使未成年人社会化,不仅使学生掌握有关人自身、自然界、社会以及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普通的必要的知识和通用的技能、技术、一般艺术,而且要使他们能够正当地运用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因为某种知识与能力正当地运用,才对社会有益,不正当地运用反而可能对社会有害,而“德育”,不管是狭义德育还是广义德育,最基本的价值正在于使学生获得正当地运用自己的知识与能力所必要的起码的品德、社会政治教养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与情操。
不过,我国如今事实上是把“德育”作为与“教学”对举的专门工作,所关注的也就是“德育”与“教学”的比较。这种比较出于现实的考虑。这是由于教与学占有学校中大部分人力和教师、学生大部分时间与精力,而又是教师、学生、家长较为关注和不得不关注的“硬任务”;相对说来,“德育”是学校中的“软任务”。因为它不可能以量化的方式衡量教师的行为,其成效又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显示出来。
2.知识、技术,在事物发展规律与技术规律层面,是客观真理的反映。尽管每个人对知识、技术的理解与体验不尽相同,其客观标准是毋庸置疑的;“德育”涉及社会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问题。社会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虽然也有一定的稳定性,而在社会变革年代,传统价值观念动摇,旧有的成效逐渐失效,新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正在形成中,它本身较为脆弱,不够成熟,其正当性尚有待检验,也就缺乏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支持,还受到传统价值观念的干扰和习惯势力的抗阻,从而出现“道德危机”、“精神危机”。所以,每当社会转折关头,“德育”在教育中的地位问题便凸现出来。
3.知识、技术的掌握,虽也受到学生自身需要的影响,而在总体上并不与学生的个人利益冲突;道德问题、政治问题、法律问题涉及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同学生的个性、习惯、利益、需要、形成中的价值观念,可能合拍,也可能冲突。至少各种行为规范对个人行为有一定的限制或束缚。加之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冲突、道德标准冲突的环境影响,使得“德育”难有成效。这样,德育作为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其应有地位理应受到关注。不过,为了加强这个薄弱环节而大搞形式主义的“德育”,只能败坏德育声誉,事与愿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