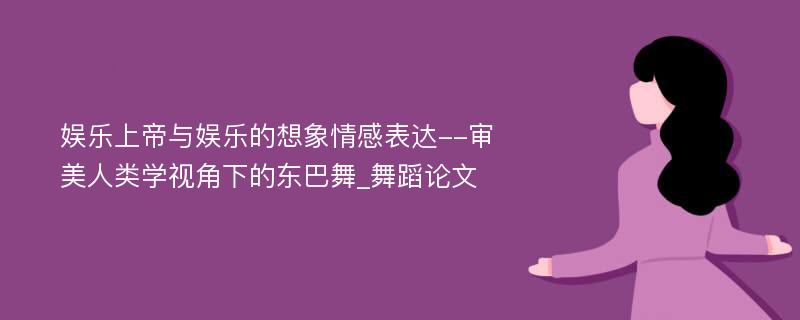
娱神与娱人的想象性情感表现——审美人类学视野中的东巴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性情论文,视野论文,东巴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7X(2007)06-0033-05
东巴舞具有宗教文化的神圣性、原始舞蹈的神秘性和现代舞蹈的娱乐审美性等特征。因此它是一种文化的、神性的和审美的舞蹈。它不但演示着人类幼年为生存而战、为生命而战的艰苦卓绝的惨烈壮举,而且潜含着人类童年为欢愉而戏、为兴奋而狂的天真浪漫的自由活动。跳舞在古代社会是人们生活中最具感召力和凝聚力的一种情感表现活动,正如库尔特·萨克斯所说:“当同一部落的人手挽着手一起跳舞时,便有一条神秘的系带把整个部落与个人联结起来,使之尽情欢跳——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包含如此丰富的内容。”[1](P1-2)在众多民族的原始宗教活动中,舞蹈也是取悦神灵和愉悦人心的最强烈的情感宣泄活动,这正可谓“谁不跳舞,谁就不懂得生活”。
一、东巴舞蹈源何在
东巴舞主要源头何在呢?有人认为其主要源头是纳西原始舞蹈,而有人认为主要是早期本教舞蹈。但我认为应从文化传承与文化交流两方面来回答。从文化传承来看,东巴舞大多源于古代民间和原始祭祀舞蹈;从东巴舞表演者特殊的社会身份也能说明东巴舞与民间舞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东巴平日各居其所,各耕其稼,有事时才为人占卜打卦,为人祝福,为人开丧超度,为人跳神驱鬼,为人祭祖等等。近代的东巴虽不如古时“神通广大”,但在人们心目中,他们仍知天晓地,善测灾祥,语通神鬼,能迎吉避凶,深受族人挚信和敬重。同时他们也以常人的身份参加民间非宗教性礼俗,耳濡目染各种民间歌舞。“这种平常而奇特的地位,使他们变成同时掌握民间艺术与东巴艺术的人,无形中起了使两类艺术双腿并行,相互吸收补益并保护其免于佚亡的作用。”[2](P34)因此,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东巴都不是全职的神职人员或宗教主持者,而是主“法事”兼从农事的“智者”,所以东巴舞自古就染上民间舞蹈的色彩。
虽然有些东巴舞源自纳西民间舞蹈和原始舞蹈,这只能说明它的“近亲”,但是它的“先祖”是什么呢?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即使下面从文化交流方面描绘的吸收其他宗教文化的线条也是十分粗略的。因此要探究东巴舞的全部来历,如果只说其来自纳西民间舞蹈和藏族本教或笼而统之地说来自佛教、道教,那么就显得太浅太近了,而且要从这些“近亲”中窥见其原初的形态和所有内涵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提倡从两方面深入研究东巴舞的来历,即从人类学方向探微东巴舞的“基因”,从文化交流的深处去感受它最初的脉动。这不仅只是为了弄清东巴舞的来历,最重要的是能从发生学的角度去发现舞蹈艺术更多的奥秘。当然这些工作是十分艰巨而浩大的,因此,本文只起抛砖之用。
从文化交流来看,它又在与周边各民族的交流中吸收了佛教、道教和儒教等文化中的舞蹈,如动物舞中的大鹏金翅鸟舞、孔雀舞、大象舞、青龙舞、飞龙舞是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形成,或者也可以说是直接吸收了佛教文化中的这些舞蹈;器舞中的灯舞、荷花枝舞也是受佛教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东巴舞中的降魔杵舞是受道教文化影响的舞蹈。正如前面所说,探寻东巴舞的秘密如果只做到这一步是不够的。从东巴经中的舞谱《蹉模》来看,戈阿干先生认为,全部东巴舞谱的来历,皆与丁巴什罗有联系,而丁巴什罗不但被藏族本教尊为教主,而且“他与古印度吠陀神话里的某些神祗的传说颇多近似之点。吠陀神话系统由雅利安人所创作。而雅利安文化与古代中亚、两河流域乃至埃及、希腊文化,在历史上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所以,要研究东巴舞谱,仅仅熟悉纳西族、藏族的舞蹈是远远不够的。它的来历极为遥远。我们只有把它放到古代东西方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去加以探幽发微,方能捕捉到它的某些古老神秘的内涵及其形貌。”[3](P567-568)实际上,戈先生所说的舞谱来历的遥远复杂就是舞蹈来历的遥远复杂,因此我们要想把握东巴舞的内涵和意义,也应该到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甚至跨过十字路口去探究它的奥秘,应该到神秘的舞圈中、神话中、神秘的图腾和巫术中去掘取它的秘密。作为一种宗教性或巫术性极浓的舞蹈,它保留了原始祭祀活动的鲜明特征,并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群体的恐惧和不安,因为在社会上尚无科学方法,而生、老、病、死、庄稼的生长、雨水、生殖,以及各种把握这一切的力量统统是些神秘莫测的东西”。[4](P103)
二、从文化舞蹈到审美舞蹈
说“从文化的舞蹈到审美的舞蹈”,并非说原始舞蹈不具审美意识,只是从舞蹈本身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关系来看,前者更紧密更不可分,而后者相对较独立较自由。实际上,原始舞蹈一样蕴涵审美意识,只不过不如现代舞蹈那么独立鲜明,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它显得遥远而神秘罢了。因此大部分研究者面对这种神秘的审美意识时,总会发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慨叹。但实际上,早在图腾时代,人类的审美意识已在脑海流动,只是这种意识被深深地湮没在图腾意识所体现的无所不包的宇宙观中,诚如郑元者教授所说:“图腾意识作为史前人类最早的宇宙观,它胶结着无数往后得以发展的精神颗粒,我们自然很难用单一的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意识去审视。”[5](P8)因此,就舞蹈而言,“从文化的舞蹈到审美的舞蹈”只是从舞蹈与人类物质生产关系的密疏而说的;此外,在远古时代,“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6](P29)因此,东巴舞蹈与其他艺术一样,它也是从文化的舞蹈转换为具有鲜明神性特征的审美舞蹈的。
东巴舞保留着原始舞蹈的显著特征和后期宗教舞蹈娱神和娱人的审美特征。追溯其原初形态,其社会价值远非文明社会之舞所能比,它“所曾经具备的伟大的社会势力,则实在是我们现在所难想象的。现代的舞蹈不过是一种退步了的审美的社会遗物罢了,原始的舞蹈才真是原始的审美感情底最直率、最完美,却又最有力的表现”[7](P156)。虽然纳西原始舞蹈未必都如格罗塞说的那样,是“原始的审美情感最直率、最完美却又最有力的表现”,但它具有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感召力是今天的舞蹈所无法企及的。泰勒也说:“跳舞对我们新时代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轻率的娱乐。但是在文化的童年时期,舞蹈却饱含着热情和庄严的意义。蒙昧人和野蛮人用舞蹈作为自己愉快和悲伤、热爱和暴怒的表现,甚至作为魔法和宗教的手段。”[8](P275)的确,舞蹈是原始初民的生命意识最强烈的体现,他们跳舞,“不是出于审美的需要,而是来自生存的欲望,是对生命的敬重”[9](P18)。但这也只能解释部分原始舞蹈,而不能包括那些模仿动物和战争的舞蹈。
人类最初的情感和意识同样是复杂的,为了表达这些情感和意识,他们会通过最便捷的媒介——自己的身体来实现。从人类生产工具的历程来看,从低级蒙昧时代到文明时代,人类采集狩猎、发明弓箭、学会制陶、饲养耕作和发明金属器具、发明标音字母和使用文字。在整个漫长的历程中,人们会因为狩猎、战争的胜利或失败、自然的恩赐或天灾而产生或喜悦或恐惧等各种情感,当要表达这些情感的时候,他们最有可能的就是叫喊或跳舞。对远古先民来说,舞蹈是一种强烈情感自然流露的行为方式,这正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0](P309-310)。诺维尔也说:“人类的感情达到了语言不足以表达的程度,情节舞蹈就会大大奏效,一个舞步,一个身段,一个动作,能够说出任何其他手段所不能表达的东西,要描绘的感情越强烈,就越难用语言来表达它,作为人类感情的顶峰的喊叫,也显得不够,于是喊叫就被动作所取代。”[11](P35)闻一多先生也说:“舞蹈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10](P317)
为何在古代社会原始舞蹈会如此盛行并能表达人们最强烈的情感呢?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总结了如下四个原因:(1)活动的快感;(2)发泄情感的快感; (3)节奏的快感; (4)模拟的快感。[12](P330)先民们在狩猎的过程中目睹了各种动物的动作,也体验了狩猎成功的喜悦,当他们要表达这种情感时,常常以舞蹈来实现,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他们“在自己的舞蹈中常常再现各种动物的动作。这怎样来解释呢?只能解释为想再度体验一种快乐的冲动,而这种快乐是曾经由于狩猎时使用力气而体验过的,……因此,模仿动物的动作,是狩猎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毫不足怪,当狩猎者有了想把由于狩猎时使用力气所引起的快乐再度体验一番的冲动,他就再度从事模仿动物的动作,创造自己独特的狩猎舞”。[12](P73)但这只说明了舞蹈表现喜悦和快乐的情感,实际上古代舞蹈不可能只有表现喜悦情感的舞蹈,而是还有表现恐惧、悲伤以及其他生命意识的舞蹈。而东巴舞中的那些动物舞、战争舞、器物舞也同样具有这些原始舞蹈的审美特性,虽然其最直接的功能是取悦神灵、祈福禳灾的,都与先民们的生命意识紧密相连,但它的深层同样反映出先民们狩猎成功或战争胜利的喜悦。既然先民们在他们的狩猎活动、战争或其他生产活动中获得了各种情感体验,并需要表达出来;同时在那种原始生活状态下,他们也具有本质上与我们类似的生命知觉,虽然这种生命知觉比起“现代人”来还很低,但如卡西尔所说:“人不可能过着他的生活而不表达他的生活。”[14](P283)因此,他们也要把他们的生命知觉、情感意识表现出来,于是他们通过原始舞蹈、雕刻、绘画等形式来达到目的。
此外,我们还应补充两项:(1)原始舞蹈还具有取悦神灵和感召社会成员的重要作用; (2)原始舞蹈也是人们物质生产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正如萨克斯所说:“艺术不会轻视面包,相反,艺术能提供面包以及其他维持生命所需的物质。……舞蹈不是一种仅为人们所能容忍的消遣,而是全部落的一种严肃活动。”[1](P2)这样说的根据是,在古代社会,生育、成人仪式、婚丧、播种、收割、狩猎、战争、宴会、日蚀月蚀、祛病禳灾都需要跳舞,从这个意义上说,“舞蹈实际上就是拔高了的简朴生活”[1](P3)。从众多类型的东巴舞来看,很多直接来源于纳西族原始舞蹈或再往前追溯的古羌族的原始舞蹈,但再往前追溯,这些原始舞蹈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只起源于先民对自然的恐惧,起源于游戏,起源于巫术,实际上,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事项,我们主张舞蹈与其他艺术一样,其起源是多渠道的。因为人类的恐惧、紧张、高兴、兴奋心理情感活动不可能长期单独发展,有了这些心理活动,就要寻找适当的方式以发泄这些内心情感。因此,巫术、游戏、图腾崇拜就成了先民们发泄内心情感的有效方式,而这三种方式常被人类学家、美学家、艺术家看作研究审美意识启蒙的重要方式。对于人类生命灵性律动的舞蹈来说,它的确是人类表达最强烈情感的有效手段,它的初期形态蕴涵了巫术、游戏和图腾元素,因此,原始舞蹈是我们进入人类审美意识世界的重要通道,而打开通道大门的钥匙就是图腾崇拜、巫术、游戏。东巴舞蹈也深深地打上了原始舞蹈的巫术性、游戏性和图腾性的烙印,因此我们可以从纳西先民的神秘舞圈和神圣的东巴舞场上进入纳西先民的心灵世界。我们仿佛可以在东巴舞中聆听到远古心灵的呐喊和生命激情奔流的涛声。
三、从神秘的图腾舞蹈探寻东巴舞的原始内涵
东巴舞包含着丰富的原始舞蹈,而从图腾艺术的维度探究这些原始舞蹈,有利于我们从发生学的角度打开东巴舞的一扇窗口,也能为我们寻找它产生的内驱力提供了一个视角。我认为对于东巴舞中的原始舞蹈来说,其产生的内驱力就是先民们因采集到丰盛的食物或成功猎获了动物时,狩猎受挫或失败时,自然灾害发生时,人生病或死亡时,所有这些都会使他们产生喜悦、羡慕、恐惧、崇拜等情感,所有这些情感都可能成为原始舞蹈的内驱力。这样,先民们内心的喜怒哀乐情绪,往往要由歌唱或舞蹈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以此重温和再现或“预演”他们的生活。在吸收原始舞的过程中,东巴们“把表达喜乐情绪的歌舞,变成了悦神的东巴舞蹈,把哀怒的歌舞,变成了斥神的东巴舞蹈”[15](P371)。把表现图腾敬仰情感的舞蹈强化为神性的舞蹈,也变成了娱神、降魔的东巴舞蹈。因此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东巴舞蹈是先民的审美意识搬到神坛祭祀仪式的民间舞蹈”[15](P371)。无论是本民族原始舞蹈,还是来自本教、佛教、道教的舞蹈,亦或是来自藏、纳西、白族共同的祖先古羌人的舞蹈,其原初形态肯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舞蹈,而是一些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舞蹈,这些舞蹈包含着纳西先民的生存需求意识、图腾或祖先敬仰意识以及审美意识,并且逐渐被强烈的宗教神性意识所统摄。
东巴舞的原始形态是先民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其他狩猎民族的群舞一样,是初民在进行原始狩猎活动之前的操练性活动或狩猎活动之后的表演性活动,这些操练性和表演性的活动本身并不是独立的活动,而是下一次狩猎活动的准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巴舞蹈的原始形态首先是作为文化的舞蹈随后才是艺术的舞蹈、审美的舞蹈,这样说的理论基础是“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的发生,远远早于其作为人类审美的对象”[16](P1)。舞蹈作为一种“表现虚幻的力”的艺术,它必然从文化的舞蹈向审美的舞蹈转变。它又如何从一种文化的舞蹈上升到审美的舞蹈呢?初民们在狩猎成功后所进行的那些模仿性的舞蹈时,他们尽情狂欢,他们凭借拙稚的舞姿表现他们“想象的情感”而不是身临其境的真实情感,他们在舞蹈中体验着胜利或成功的喜悦,此时的原始舞蹈随虽是生产的重要部分,但它已经具有模拟的快感这一审美张力了。
从图腾审美来看,由于纳西先民们的图腾如同神话一样,“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17](P113)所以他们发明了极富象征性的图腾艺术形象使各种想象力物化,正是这些形象浓烈的象征意味使图腾艺术具有了审美的又一个张力。正如郑元者教授说的那样:“图腾象征由于具有了‘自然的人化’的本质属性,也由于它自身具有一种张力的功能,所以图腾象征在变异、转换的过程中,逐渐由始基态变换为转型态,乃至于派生态,从而在客观上越来越偏向于艺术性的审美表达力。”[5](P117-118)东巴舞蹈中有不少舞种与纳西族的图腾文化密不可分,有与纳西先民四个主要氏族梅、禾、束、尤的原生图腾蛙、蛇、熊和猴有关的舞蹈,如《金色神蛙舞》、《蛇舞》、《熊舞》、《猴舞》,也有与纳西族次生图腾“术”(也作署)有关的“术”舞,还有众多的与纳西初民的“前图腾”——自然物崇拜(主要是动物)有关的舞蹈,如《虎舞》、《鹰舞》、《牦牛舞》等等,这就使东巴舞具有了鲜明的图腾文化的特征,这又给我们从发生学的角度研究纳西先民的审美意识打开了一扇窥视先民心灵的窗口——图腾崇拜。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求生存、求繁衍、崇拜超自然力、避免苦难、相互协作是人类的普同性渴望,而这些渴望在图腾艺术中主要就体现为生存欲求的表达。除此之外,图腾艺术还包括了信仰意识和审美情绪的表达,而人类心理的这些意识,在现代宗教艺术中也同样存在。所以卢卡契说:“即使人类存在的最原始阶段,也必定会产生一种对现实略为接近的意识的把握,否则这种生物(人)既不可能维持他们的存在,也不可能向更高的阶段发展。”[18](P2999)然而,人类发展史中古今人类的那些大致相同的各种心理情感意识,在不同的特定历史阶段,各种物化形象所体现出的每种情感意识是不同的,并且分化也会逐渐加剧,正因如此,才会有今天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各种艺术。但以上各种意识的分化与独立并不会凭空发生,对于审美意识而言,它还必须借助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客观物质对象的拓展,二是主体掌握世界的能力得到跃升及知觉感性的不断丰富。总起来就是马克思说的:“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19](P87)但还要强调的是,虽然图腾具有了审美张力,但我们不能说审美是那些图腾作品制作者的动机,事实上“图腾艺术作为图腾活动的物化形态,它得以产生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审美,而是别的什么”[5](P44)。因此,博厄斯把艺术形象的审美价值或效果看作图腾艺术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机是不恰当的,他说:“是社会生活中的图腾促进了艺术的发展,还是艺术促进和丰富了图腾的内容?根据我们的观察,……似乎应该肯定,图腾形象的丰富和完美,其动力来自艺术形象的价值。”[20](P260-261)对于审美是否是图腾产生的动机这一问题,郑元者教授有创见地指出,图腾产生的动机不是审美,而是人类渴望借助一种超自然力去抑制、征服其他自然力的心理动机,而这种动机又是由于人们面对严酷的实践活动而产生的各种恐惧心理造成的,他说:“史前的图腾意识和信仰正是由于史前人类在狩猎活动中的那种实践上的无能为力、那种生存需要的迫力所引发的,生存的现实性的压抑,使得他们在幻想中乞求与图腾物的‘同一’,借助于图腾的力量去抑制、征服其他自然力的潜在威胁。”[5](P45)正如《剑桥大学向托里斯·斯切特远征调查的人类学研究报告》宣称的一样:“在导致土著居民进行身体装饰的六种理由里只有一种是真正的装饰,其余的则依赖于社会条件、图腾标记、社会阶层、兄弟符号、医药及魔法等等。”[21](P237)爱斯基摩人熊图腾的例子也同样有说服力。尽管爱斯基摩人的祖先早在公元500年就创作了其崇拜的熊的木雕像,但这显然不是在审美动机驱使下的艺术创作,而是在图腾信仰这一原始宗教观念的动机下创造出来的,而且这种文化事项还具有普遍性。因此,图腾艺术是在图腾信仰的动机下创造出来的。
相应的,纳西族的远古图腾舞蹈也是在图腾信仰的动机下催生的,它是先民们敬神的重要形式,而一旦图腾文化发展成宗教文化,舞蹈也同样成了宗教仪式中的重要部分,甚至可以说,是高潮部分。而东巴舞蹈虽是一种宗教舞蹈,但它同样具有最浓烈的敬仰意识,或敬仰图腾,或敬仰各种保护神,因此除了宗教神性外,它深埋着原始图腾舞的生命意识、敬仰意识和审美意识。东巴舞之内涵犹如渊海,我们从图腾艺术的视阈初探其秘,只若在茫茫黑夜中通往远古先民心灵世界的历程中划燃一根小小的火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