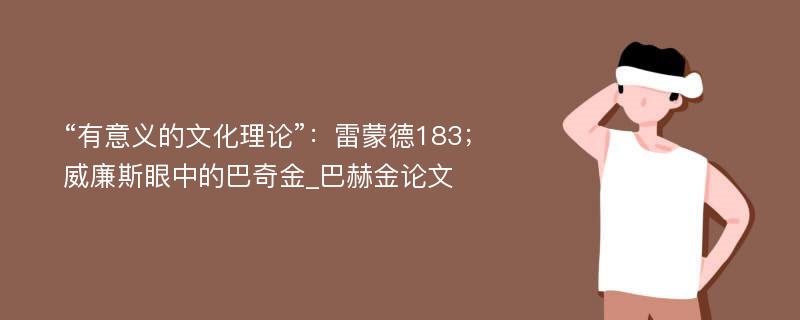
“有意义的文化理论”:雷蒙#183;威廉斯眼中的巴赫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有意义论文,雷蒙论文,威廉斯论文,眼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6—0103—06 特里·伊格尔顿在《纵论雷蒙德·威廉斯》一文中曾如此评价雷蒙·威廉斯:“当巴赫金的不倦努力在斯拉夫派符号学家们眼中还只是微弱的闪光的时候,威廉斯早已是一位‘巴赫金派’的社会语言学家了。先于于尔根·哈贝马斯许多年,威廉斯对交往活动理论的某些主要命题作出了论述。”①伊格尔顿的此番判断颇有深意:其一,在性质上,他揭示出雷蒙·威廉斯的社会语言学思想与巴赫金语言哲学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性关系——这决定了两者具有某种进行平行比较的“可比性”基础,也暗示了进行“事实联系”考察的影响研究的前提;其二,在时间上,他认为雷蒙·威廉斯社会语言学思想的成熟早于斯拉夫派符号学家。这里的“斯拉夫派符号学家们”指的是从1960年代开始兴起的以洛特曼为代表的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他们对巴赫金思想接受的时间始于60年代。②那么,雷蒙·威廉斯早在6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形成具有巴赫金式的社会语言学思想了吗?伊格尔顿对这个问题语焉不详,这是需要我们深入讨论的问题;其三,伊格尔顿又将雷蒙·威廉斯建立在交往活动理论的问题史中,并确立其“先于哈贝马斯”的定位,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巴赫金、哈贝马斯和雷蒙·威廉斯三者之间的理论联系呢? 一、70年代:聚焦《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 正当斯图尔特·霍尔组织“语言和意识形态小组”将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纳入讨论对象的时候,1977年,被视为文化研究学派的“精神领袖”或“学术顾问”的雷蒙·威廉斯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在该著第一章“基本概念”第二节“语言”中,威廉斯专门讨论了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③很难说这两次接受谁先谁后,但两者共同表示了英国新左派的文化理论思潮正式接受了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理论。④ 雷蒙·威廉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关语言的理论有两个特点值得特别重视:一个是它强调语言是活动,另一个是它强调语言有历史。但是让人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理论,即以现实的具有历史性的言语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的话语理论;相反,“它却把自身的那些限定性和局限化发展起来了。其中最明显的局限化就是把整个物质社会过程都归结为‘劳动’,而这一点又被讲得越来越狭隘。这在关于语言的起源问题和发展问题的重要讨论中产生了影响,而这些问题在进化体质人类学这一新学科的语境中一直被人们重新探讨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持的基本观点是以反映论为基础的,即语言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其反映的真实性成为判断其正确高下与否的最重要的指标,但是,“无论何时,任何一种构成性的实践理论(特别是唯物主义理论)在重新阐述语言的能动过程这一问题上,都会产生某种超出探究起源问题的重大影响——这种重新阐述大大超越了‘语言’与‘现实’这类分离的范畴。然而,正统马克思主义却依然陷在反映论中不能自拔,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方能在那些已被人们接受的抽象范畴之间建立起似乎可信的唯物主义联系”。⑤在回顾了从18世纪以来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相关的知识谱系,特别是分析了斯大林主义语言观之后,威廉斯把目光聚焦到了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上面,认为其最大的贡献在于“找到了一条足以超越那些影响巨大但又甚为偏颇的表现论和客观系统论的途径”。正因为沃洛希诺夫/巴赫金“把整个语言问题放到马克思主义那种总体的理论格局当中加以重新考虑”,“这使他能够把‘活动’(洪堡特之后的那种唯心主义强调之所长)看作是社会活动;又把‘系统’(新的客观主义语言学之所长)看作是与这种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而不是像某些一直被人们袭用的观念那样,把二者看做是相互分离的。……沃洛希诺夫由此开辟了一条通往新理论的道路,对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学术来说,这种新理论一直十分必要”。⑥雷蒙·威廉斯将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语言理论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语言是活动、是实践、是一种基于社会关系的社会行为。在雷蒙·威廉斯看来,“沃洛希诺夫的这些努力旨在全面恢复认定语言是活动,是实践意识的强调(而这一强调长期以来一直被削弱,并且实际上也被其自身的那种局限在封闭的‘个体意识’或‘内在心理’的做法所否定)。……沃洛希诺夫认为,意义必然是一种基于社会关系的社会行为。但要理解这一点,则必须先要恢复‘社会的’一词的全部含义:它既不是指那种唯心主义的化约(即把社会当做一种承袭下来的、已经造就好了的产物,一种‘没有活力的外壳’;认为除此之外所有的创造性活动都是个体的活动),也不是指那种客观主义的设定(即把社会视为形式系统……认为只有置于其中并依据这一系统,意义才能被生产出来)。从根本上讲,上述这两种观念都源于同一谬误——把社会的意义活动同个体的意义活动完全分离开来(尽管这些对立的立场对那些分离的因素各自评价不同)。与那种唯心主义强调所持有的心理主义立场相反,沃洛希诺夫认为,‘意识构成于并存在于符号的物质材料中,这些符号材料则是由某种有组织的群体通过其社会交往过程创造出来的。个体意识依赖于符号,从符号中产生,它也反映着符号的逻辑和规律’(《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第13页)”。⑦威廉斯对这个特点的把握无疑是将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语言理论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架。 其二,沃洛希诺夫/巴赫金注意到了语言“符号”的二重性,即“符号既不等同于客体对象及其所指示或表达的事物,也不单纯地反映着它们。因而,在符号当中,形式因素与它所携带的意义之间不可避免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关系(至此为止,他还是赞同正统的符号理论的)。然而,这种关系却不是任意性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对这种语言与现实关系的重新解释是建立在“社会语言”的认识框架内的,即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这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既如此,语言一方面具有“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这一点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具有相似性;但另一方面,语言“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又受到了来自社会现实的影响,用威廉斯的话说,“由此可见,我们所发现的并不是各自存在的‘语言’和‘社会’,而是一种能动的社会语言。(稍稍回顾一下实证主义理论和正统的唯物主义理论)我们又会发现,这种语言既不是对于‘物质现实’的单纯‘反映’,也不是对于‘物质现实’的单纯‘表现’。确切地说,我们所拥有的,是通过语言对于现实的一种把握;语言作为实践意识,既被所有的社会活动(包括生产活动)所渗透,也渗透到所有的社会活动之中。同时,由于这种把握是社会性的、持续的(不同于那些抽象的对立:‘人’对‘世界’,‘意识’对‘现实’,‘语言’对‘物质实在’等等),所以它出现在能动的、变化着的社会关系之中。语言言说所来自的、所论及的,正是这种经验——‘主体’与‘客体’(唯心主义和正统唯物主义的前提就是建立于其上的)这些抽象实体之间所遗失掉的中介性术语”。⑧也就是说,语言“反映”社会现实的程度取决于社会现实对语言的影响程度,这正是“语言”与“现实”关系的吊诡之处。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双重性所带来的理论难题呢?威廉斯认为,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语言理论具有了第三个重要的特点:“语言就是这种能动的、变化着的经验的接合表述[the articulation],就是一种充满能动活力的、接合表述出来而显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社会在场[social presence]。”按照他的看法,这种接合表述的特殊性其实最早已被形式主义所把握。“正是在反对这些消极被动和机械倾向上,形式主义作出了最大贡献——它坚持认为,通过符号进行的表意过程是一种特殊的(形式化的)接合表述[articulation]”。⑨特别注意的是,将语言视为与社会、经验的“接合表述”并非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观点,而是雷蒙·威廉斯所做的理论延伸。“接合理论”(theory of articulation)是英语的文化研究理论,尤其是伯明翰学派在实现“葛兰西转向”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新的理论范式。这种接合理论意在一方面既描述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形态的特点,但另一方面又不至于陷入还原论(经济还原论和阶级还原论)和本质论的陷阱。这种策略主义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后学”特征(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并使之成为“当代文化研究中最具生产性的概念之一”。(10)但是,沃洛希诺夫/巴赫金所强调的重点并非在此。如果说,正统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强调的是语言对现实的单向度反映的话,那么,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则将这种关系复杂化了。任何符号,包括符号的内容和形式,都受到有社会组织的人及其之间关系的影响,都受到他们相互作用的环境的影响。为此,他们为社会语言符号的研究确立了三条基本的方法论要求:“(1)不能把意识形态与符号的材料现实性相分离(把它归入‘意识’或其他不稳定的和捕捉不到的领域)。(2)不能把符号与从该时代的社会视角来观照的具体形式相分离(而且在此之外它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一种简单的物理东西)。(3)不能把交际及其形式与它们的物质基础相分离。”(11)对比这三条原则,丝毫没有雷蒙·威廉斯和斯图尔特·霍尔所说的“接合”的意思。 70年代中后期,威廉斯一方面已经注意到自己所提出的“情感结构”因为各种原因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另一方面则面临着对阿尔都塞—拉康式的对主体和符号问题的反思的回应压力,《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在语言层面转向以巴赫金小组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重视正是这种压力下的产物。不过,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威廉斯在此时发表此著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急欲解决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问题有关。因为威廉斯虽然与霍加特、霍尔关系甚密,但他并没有真正参与该中心的学术活动,而且从1961年直到1983年他都在剑桥大学,此后一直待在萨福沃登(Saffron Walden)小镇。不过,威廉斯在此时此刻发表展现其对巴赫金/沃洛希诺夫的关注,足以证明巴赫金小组对英国学界的影响,而威廉斯的态度也可以成为伯明翰学派学人接受巴赫金思想的佐证。 二、进入80年代:赞同巴赫金小组的社会学诗学 进入80年代之后,雷蒙·威廉斯对巴赫金的著作仍然保持了持续的关注。不过,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巴赫金最受西方文学理论学家们关注的复调小说理论、对话主义、狂欢化理论似乎一直未正式进入雷蒙·威廉斯的学术视野。至少在他的绝大多数著述中,很难找到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或引述。相反,雷蒙·威廉斯一直较为关注的是“巴赫金小组”时期,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梅德维杰夫/巴赫金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尤其是后者,成为80年代雷蒙·威廉斯学术生涯的晚期重点征引和讨论的对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尚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在此,我们仅能够以文本为对象,概述其主要的思想。 1989年,在雷蒙·威廉斯去世两周年之际,托尼·平克尼编辑出版了他的主要发表于80年代的论文集《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against the new conformists)。托尼·平克尼认为,雷蒙·威廉斯在1983年的《后现代主义的间离语言》一文中庄重宣布:“自觉的‘现代主义’的时期行将结束”,(12)在雷蒙·威廉斯的现代主义批判谱系中,巴赫金、卢卡奇的理论进入其视野。托尼·平克尼认为,“把现代主义确定为大都市的社会形式中的一个特定时刻,使这种分析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布莱希特的间离来自于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正如重新发现的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著作和他的同事们后来使威廉斯看出的,形式主义在其最早阶段也是对未来主义的理论化,如他在《文化理论的运用》中所描述的,即‘正是在极端的但却空洞的、尚未被接纳的时刻’。卢卡奇本人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后来可能被‘巴赫金化’了,正如威廉斯所做的那样,他从卢卡奇对表现主义的巨大威吓中挑出一个词,用于当代英国政治戏剧的各种困境”。(13)这似乎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巴赫金的某些思想开始成为雷蒙·威廉斯进行现代主义及其相关的文化理论反思的重要的理论资源。 在这本书中,与巴赫金(巴赫金小组)有关的共有三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是《语言与先锋派》。这篇文章是1986年雷蒙·威廉斯在格拉斯哥的一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不过,不知出于何种考虑,雷蒙·威廉斯在选编这本论文集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将之编入。托尼·平克尼在雷蒙·威廉斯去世之后接着选编的过程中,将之增补进来的。在这篇文章中,雷蒙·威廉斯引述了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梅德维杰夫/巴赫金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在讨论对于“现代”问题的态度时,雷蒙·威廉斯也注意到了,“我们可以从注意到这种语境中‘现代’的两种积极含义开始:‘现代’是一段历史时间,以及它特定的、然后变化着的特点:但‘现代’也是麦德维德夫和巴赫金批判它时所称的‘永恒的同时代性’,是对‘片刻’的领悟——它在实际上和理论上奔越过并排除掉变化的物质实在,直到一切意识和实践都是‘现在’。”在讨论形式主义理论的发展局限问题时,雷蒙·威廉斯指出,“由于形式主义的主张变成了文学理论中一种有影响的趋势,它灾难性地把它所针对的那些事实变得狭隘了。它限于拒绝被称为‘内容’和‘表现’的东西,甚至更加破坏性地拒绝了‘意图’,它在实际上没有领悟到那种特质的积极的文学用法的要点,伏罗西诺夫把那种特质称为‘多音调的’,一种内在的语义开放性,与一种仍然积极的社会过程相应,新的意义和可能的意义可以据此产生出来,至少在某些重要的词语和句子的各类之中”。(14)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多重音性”(multi-accentuality)亦即后来在《长篇小说的话语》中提出的“杂语”(或译“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的前身。由于巴赫金相关著作的英译本均在80年代之后才陆续出版(如1981年的《对话式想象》、1984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1986年的《言语类别及其他晚期文章》),雷蒙·威廉斯显然没来得及读到巴赫金的这些著作。 三、最终认识:有意义的文化理论 1986年,雷蒙·威廉斯进入生命中的最后时刻,他似乎有意站在整个文化研究、文化理论发展的全局高度来反思和前瞻。他接连发表了《文化研究的未来》和《文化理论的应用》两篇文章(演讲),其中对巴赫金思想的强调尤为显著。在《文化研究的未来》中,雷蒙·威廉斯明确展开了对“结构主义”作为“理论”的批评,认为“一种理论获得了成功,它把这种构成的情景按照它的方式合理化了,使它成了官僚主义的,成了知识分子专家的根据地。那就是说,它所形成的各种理论——形式主义的复活,各种较简单的结构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倾向于把人们在社会中的各种实际遭遇看成对社会的一般进程具有相对很少的影响,因为那个社会主要的内在力量在其结构的深处——在最简单的各种形式中——操纵它们的人们只不过是‘代理人’”。正是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中,雷蒙·威廉斯发现了“巴赫金小组”的价值,他认为,“早期对巴赫金、伏罗西诺夫、麦德维德夫所发动的这种现代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强有力的挑战,很少被听见,或者完全听不见。甚至(并不经常)当构成‘被’理论化时,构成分析的主要教训(涉及人们自己的构成和其他‘当代的’构成)也很少得到强调,而是更强调安全距离之外的学术研究”。(15)在《文化理论的运用》中,雷蒙·威廉斯更是从正面积极肯定“巴赫金小组”的理论贡献。 在《文化理论的运用》中,雷蒙·威廉斯对“巴赫金小组”时期的研究予以了高度的肯定,认为“正是在这个被唤醒的、但令人不满的阶段中,第一次重要的理论创新开始形成。我将首先考查也许可以称为的从维捷布斯克开始的道路。我的意思是指那场依然未被很好理解的、却很重要的运动,它涉及(不能确定,且无法摆脱)P.N.麦德维德夫、V.N.伏罗西诺夫和M.M.巴赫金,1920年代早期他们都在维捷布斯克,后来在列宁格勒工作。这也是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以说明社会分析和历史分析对于研究文化理论中一种创新的结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些理论活动的关键因素,是它们在一个仍然很活跃的革命社会里的复杂处境”。(16)在这篇文章所展开的威廉斯对巴赫金的接受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其一,雷蒙·威廉斯对巴赫金及巴赫金小组时期的发展历史已经相当熟悉。他不仅熟悉围绕巴赫金小组时期著作权的争议,而且还熟谙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及学术变迁。例如,他发现,麦德维杰夫“曾经是无产阶级大学的校长,曾积极介入过各种文学计划和通俗戏剧的各种新形式”。但是在斯大林时代,他和洛诺希洛夫都成了受害者,“而巴赫金则在这时被边缘化了”。尽管如此,“当这种批评出现时,它(标志着一次主要的理论上的进展)只是部分地、不完全地变成了直接的分析。但后来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巴赫金才能够完成那种毕生的工作”。(17) 其二,雷蒙·威廉斯充分肯定的是他们提出的“社会学诗学”的主张,这与他自己的“文化社会学”路径形成理论的呼应。“我们或许会盼望与早已著名的‘社会学诗学’的某种简单关系,在这种诗学中,读者的转换和艺术家地位的转换,可以被认为直接导致了一种新的、自信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19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与巴赫金小组社会学诗学的这种相互交织与对峙的局面又在1960年代的西方世界重新出现了。“紧跟着这些内在的和特有的力量线索,从1960年代起在西方出现的东西——它有时仍然被当作现代文学理论提出来,似乎它在出现的最初几年里没有得到全面的分析和驳斥——是那种早期的形式主义,它让自己成为对当时‘社会学诗学’的外在化的一种反动。麦德维德夫和巴赫金正确地把这种形式主义确定为未来主义在理论上的结果”。(18) 其三,在雷蒙·威廉斯那里,巴赫金小组所从事的理论创新作为“有意义的文化理论”,成为文化研究的最佳典范。在回顾了1920年代的俄国和1960年代的英法出现的相似学术情况之后,雷蒙·威廉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我要开始问:有意义的文化理论可能是怎样的,能够做什么。这个问题仍然比任何理论阶段的内在历史都更重要,只有在它确证了真实社会历史之内的关键联系和关键断裂之时,它才成为有用的。从上面对各种文本和个人进行挑选,这是学术批评最糟糕的遗产,它决定了依赖注解和批评的整整一代人的调子与自满,必须被一种同样持久的参与实践活动所取代,包括在各种新的作品和运动之中。”正是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雷蒙·威廉斯再次将巴赫金小组抬了出来。“用麦德维德夫和巴赫金的话来说:‘作品只是作为社会交往不可分割的各种要素,才可能进入真正的联系之中……进入联系之中的并不是作品,而是人,不过,他们是通过作品的媒介进入联系之中的。’这把我们导向了文化分析中的核心理论问题:我在开头界定为特定关系的分析,作品通过这些关系形成和运动”。(19)也就是说,巴赫金小组所确立的以社会交往为基础的研究范式,是最佳的文化理论的最佳选择。 四、余论:有关雷蒙·威廉斯接受巴赫金影响的两点辨正 在清理完雷蒙·威廉斯对巴赫金思想的接受历程之后,不难得出结论:(1)雷蒙·威廉斯是从1970年代开始接受巴赫金的理论;(2)从早期的对巴赫金小组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共鸣到后期的将巴赫金理论视为“有意义的文化理论”的自觉,显示出雷蒙·威廉斯对巴赫金思想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两个基本结论中,本文开头所提的后两个问题也初步有了答案: 其一,雷蒙·威廉斯在1960年代尚没正式接受巴赫金的思想,那么,他的社会语言学的思想倾向应该是另有来源,即,来自英国新左派思想的传统,它强化了雷蒙·威廉斯自觉地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关心无产阶级文化的角度对英国语言问题的思考。从雷蒙·威廉斯早年著名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来看,尽管他已经开始思考“语言”问题,如其从文化与社会角度对英国文学的思考以及对“标准英语的发展”变迁的考察,但主要还是从“语言作为对象”而非“语言作为方法”的角度进行的思考,其语言学方法论的自觉尚未形成。不过,其中有个细节值得特别注意:《文化与社会》于1958年出版之后反响强烈,多次重印。雷蒙·威廉斯在1963年版的“后记”中提到,他准备为该书写一个续篇《再论文化与社会》,其写法是“详细探讨关键词的历史”。应该说,这一研究思路的转变显示出雷蒙·威廉斯“通过语言反思文化与社会”方法论的自觉。正如其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序言中所指出的,这本书“应该算是对于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纪录;这类词汇包含了英文里对习俗制度广为讨论的一些语汇及意义——这种习俗、制度,现在我们通常将其归类为文化与社会”。(20)也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基础和研究取向,当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进入英语学界的视野之后,才可能引起雷蒙·威廉斯以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巴赫金思想对雷蒙·威廉斯的影响虽不具有“原发性”(即影响的最初来源),但却具有“催化性”(在关键时刻推动了接受者思想的自觉)。 其二,后期雷蒙·威廉斯对巴赫金文化理论的接受明显受到了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影响,以至于雷蒙·威廉斯主要是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建立巴赫金小组的社会学诗学与自己的文化社会学之间的学术联系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和“文化社会学”与巴赫金小组的以审美交往为特征的“社会学诗学”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比较,以及更重要的是他们共同面对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不同态度及其理论取舍。拙文《作为审美交往活动的“复调”和“对话主义”》(《人文杂志》2011年第5期)和《从马克思到巴赫金:审美交往的一段问题史》(《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4期)已从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问题史角度清理了马恩经典作家(马恩毛列)、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巴赫金小组之间的复杂关系。笔者认为:(1)马克思恩格斯对“交往”、“普遍交往”、“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等问题的讨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交往思想的基础;(2)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重视语言的中介性地位,但忽视了审美活动的维度;(3)真正讨论“审美交往”问题的,是巴赫金小组学者的贡献。雷蒙·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对语言是活动、实践,是一种社会行为的认识正是其在充分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对语言哲学的问题史之后得出的结论,其中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功不可没;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始于1976年的《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并成熟于1981年的《交往行为理论》。因此,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雷蒙·威廉斯的影响是在后者写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之后,而这正好与雷蒙·威廉斯对巴赫金文化理论认识的阶段性特征相吻合。 限于篇幅,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探讨在此仅略作讨论,深入的展开将另文详述。 ①[英]特里·伊格尔顿著,王尔勃译,周莉、麦永雄校:《纵论雷蒙德·威廉斯》,刘纲纪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2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02页。 ②巴赫金与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关系早已为学界所关注。从1970年代开始,俄罗斯学界就开始讨论两者的学术联系,近几十年来则更为集中。大体而言,以洛特曼为代表的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首先是继承俄国形式主义的学术传统,进而接受巴赫金的影响,拓展成符号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正因为如此,巴赫金之于洛特曼的重要性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而不是具有原初性的思想资源。这也即伊格尔顿在此所说的巴赫金还只是斯拉夫派符号学家眼中的“微弱的闪光”的含义。而雷蒙·威廉斯对语言问题的关注首先是从其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英国新左派立场出发的,从一开始就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进入语言问题,因此更倾向于巴赫金式的。 ③[英]雷蒙德·威廉斯著,王尔勃、周莉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雷蒙·威廉斯显然是对与巴赫金著作权相关的争论颇为了解,并且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问世后,曾于1929年和1930年两次出版,后一版本被译成了英文(由Malejka与Titunik合译,纽约和伦敦,1973年)。如今人们普遍认定,沃洛希诺夫是M.M.巴赫金的笔名,而后者即多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29年;后经重新表述,更新标题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63年)的作者;同样的情况在署名为‘P.N.梅德维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1928年)一书那里也出现过。尽管实际情况如此,我们还是依照惯例,以发表时的署名‘沃洛希诺夫’来引述《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这部著作”。 ④关于伯明翰学派是如何接受巴赫金的,参见曾军:《从“葛兰西转向”到“转型的隐喻”——巴赫金是怎样影响伯明翰学派的》(《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 ⑤[英]雷蒙德·威廉斯著,王尔勃、周莉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33—34页。 ⑥[英]雷蒙德·威廉斯著,王尔勃、周莉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33—34、35—36页。 ⑦[英]雷蒙德·威廉斯著,王尔勃、周莉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页。 ⑧[英]雷蒙德·威廉斯著,王尔勃、周莉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38、38页。 ⑨[英]雷蒙德·威廉斯著,王尔勃、周莉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8—39页。 ⑩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 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112. (11)[苏]B.H.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苏]巴赫金著,晓河等译:《巴赫金全集·周边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2页。 (12)[英]雷蒙·威廉斯:《后现代主义的间离语言》,《新社会》1983年6月16日,第439页。转引自[英]雷蒙·威廉斯著,阎嘉译:《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6页。 (13)[英]托尼·平克尼:《编者引言: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英]雷蒙·威廉斯著,阎嘉译:《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3页。 (14)[英]雷蒙德·威廉斯:《语言与先锋派》,[英]雷蒙·威廉斯著,阎嘉译:《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07—108、109页。 (15)[英]雷蒙德·威廉斯著,阎嘉译:《文化研究的未来》,《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23页。 (16)[英]雷蒙德·威廉斯著,阎嘉译:《文化理论的运用》,《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商务印书,2002年,第234—235页。 (17)[英]雷蒙德·威廉斯著,阎嘉译:《文化理论的运用》,《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35、237页。 (18)[英]雷蒙德·威廉斯著,阎嘉译:《文化理论的运用》,《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35、235—236页。 (19)[英]雷蒙德·威廉斯著,阎嘉译:《文化理论的运用》,《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45页。 (20)[英]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