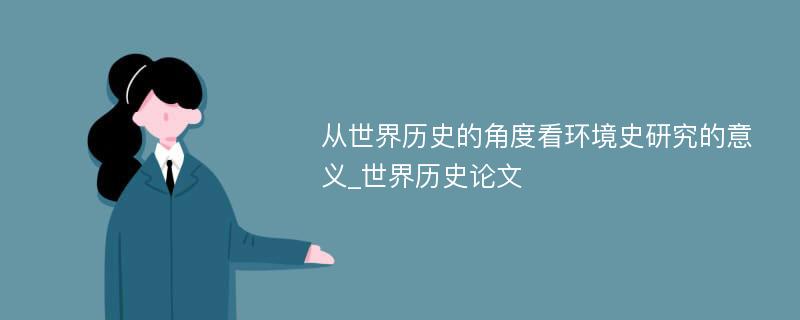
世界史视野下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史论文,重要意义论文,视野论文,史研究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08)06-0105-06
近20年来,在国际环境史学界,环境史研究的主题和内容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入,新作迭出,其中,世界史视野下的环境史研究成果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已有学者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环境史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它的国际化”,相关的跨国研究成果已在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①这是不难理解的。我们知道,环境史以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发展、变迁为基本研究对象。自人类诞生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人类单纯依赖自然发展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再转变为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有差异的地理条件下,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方式和结果是不尽相同的。这样,环境史研究者对人与自然的变动关系的考察就应该具有长时段视角和全方位意识,否则,局限于某个时代或某个地方来认识问题,常常会不得要领。同时,环境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历史学者的注意力转移到今人关注的环境问题上来,但是,大部分环境问题在20世纪之前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重要先例。这样,历史学者在关注并研究现代环境问题的同时,也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自古以来,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每一历史时期都具有塑造历史的作用”。就此而言,由于世界史具有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带着世界史视野从事环境史研究,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关于世界环境史方面的著作,J·唐纳德·休斯在《环境史是什么?》中专设一节,做了颇为全面的介绍。②这里仅以有中译本的《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以及《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等著作为例,从三个方面对世界史视野下环境史研究的意义略加分析。
一、充分揭示人类史与自然史之联结的史实
世界史视野下的环境史研究能够充分地揭示人类史与自然史之联结的史实,从而大大突破了以往历史研究聚焦于人类社会的传统,更新了关于世界历史上许多事物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说过,“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③但长期以来,这主要被当作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命题加以认识和定位。在历史研究实践中,历史一直主要被看做“人事的历史”,人类史和自然史则被割裂开来。及至20世纪下半叶,“环境史应运而生,并最终使自然和人类历史两个方面汇入到一条长河之中”,④因此可以说,将人类史与自然史联结的历史事实揭示出来,是环境史的一大贡献。由于世界史在时间上纵贯一部人类编年史,在空间上横跨整个地球,这样,世界史视野下的环境史研究就能够更加充分地揭示人类史与自然史联结的事实。从前面提到的本文主要参考的三部世界环境史著作中,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这一点。
《生态扩张主义》是美国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的代表作,⑤这里的扩张主义即人们原来所说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在这本书中,克罗斯比另辟蹊径,从生物地理学角度,对欧洲扩张的状况作了新的描述。他以人们熟知的历史片断为基础,重新勾勒了一幅欧洲扩张的全景图,同时对欧洲人如何扩张到西伯利亚、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在这些地方建立一个个新欧洲作了新的解释。《自然与权力》是德国环境史学家约阿希姆·拉德卡的代表作,⑥该书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主线,系统地勾勒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历史画面。《绿色世界史》是英国学者克莱夫·庞廷的作品,⑦虽因结构欠佳且无注释而让人诟病,但仍“是一部很受欢迎且广为使用的著作”。⑧该书从“绿色”角度审视世界历史,阐述“人类及其创造的各种社会与之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演变及其后果”,对历史上的环境问题按年代并分专题作了论述。
总的来说,这些世界环境史著作都阐述了这样的事实,即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地理范畴,其本身就是一种“存在”。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的,是丰富多样的生物群落,其中不仅有人类,而且有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等。历史从来就不是人类的独角戏,而是生命万物的大合唱。譬如,在《生态扩张主义》中,克罗斯比用很大的篇幅对杂草、动物和病原菌及其在欧洲扩张历史中的作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而在对欧洲扩张原因的解释方面增添了除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因素之外的许多新内容。在《自然与权力》中,拉德卡指出,名副其实的环境史不仅涉及人类和他的劳作,而且包括“羊和骆驼、沼泽和荒地。人们必须注意,自然有它自己的存在,它绝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组件和人们商谈的引文”。在这里,他所强调的是如何理解自然并认识自然在历史中的地位。他说,自然的“原始含义并不是野生,而是指事物的本质、理性秩序和抽象性质;这一语义学之链一直延伸到现代,但同时,自然这一概念又总是经常回到它最原始的意义,回到生长的世界,回到它的茂盛繁荣”。这样,人们应该怎样认识并研究自然在历史中的作用呢?他认为,如果真正地将自然作为一个历史的活动者,那么,在研究自然的时候,就必须理解自然的不可预测的影响之链。在《绿色世界史》中,庞廷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不能在一片真空中去理解。所有的人类社会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依赖于种种复杂的、相互联系着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地球上的生命和所有的人类社会都依赖于全部系列的复杂过程之中和相互之间的一连串精微平衡的维持。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环境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同样重要的人类对地球的影响。所以,在这部世界史中,我们看到了世界各地曾经存在的各种野生动植物的情景。譬如,中世纪早期,在比利时和德意志的荒野中仍能见到欧洲野牛,但到了18世纪时就只能在东欧见到了,⑨它的最后一头于1920年在波兰的比尔罗威查(Bialowieza)森林死掉。⑩
此外,这些著作还充分地论述到,在这个世界中,人类与自然万物早就结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人类自身的幸福“在许多方式上与动物和植物世界的生长、与潺潺而流的源泉的清澈和不倦相联系”;(11)同时,自然界也因人类足迹所至而发生着变化,自然并不是“某种业已形成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原始的自然”只是一个幻景。譬如,庞廷明确地指出:“在最近这一万年中,人类活动对世界上的种种生态系统造成了重大的改变。定居的普遍扩展、由农业而导致的农田和牧场的创造、持续的砍伐森林和清理其他野生地区、湿地上的排水,所有这些都逐步地减少了几乎所有种类的动物和植物的生长栖息之地。”(12)这就使我们真切地认识到,历史之所以要从自然史和人类史两个方面加以考察,是因为这两个方面原本是交织在一起的。
世界环境史对古往今来人类与自然联结的事实充分揭示的一个结果,即是大大突破了历史研究专注于人类社会的传统,对人们所熟悉的世界历史上的许多事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从上述著作均涉及的欧洲殖民扩张来看,无论是克罗斯比对欧洲扩张及其成功原因的解释,还是拉德卡和庞廷关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后果与影响的论述,都有许多新的论断。
克罗斯比在其著作中提出“生态扩张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本身即是对殖民主义理论的一大创新。他以此为指导,讲述了一个新版本的欧洲扩张故事。其新意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对“谁”在扩张或征服的问题给出了新答案,指出不仅仅是欧洲的人在扩张,欧洲的物种和微生物也在扩张,总之是整个欧洲生态系统的扩张;二是对欧洲扩张得以成功的原因作出了新解释,认为欧洲人扩张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其武器和技术的精良,而且与欧洲人带来的引起生物后果的“旅行箱生物”(portmanteau biota)有关,尤其与那些在本地人中引起“处女地流行病”(virgin soil epidemics)的微生物有关。拉德卡在《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中进一步指出,人们常常夸大了近代早期殖民主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经济发展是否随着美洲的发现真正形成了全球化格局是值得怀疑的。在他看来,“如果说近代早期殖民主义的时代特征按照传统历史学的标准开始动摇的话,环境史则赋予它一种全新的意义”。这是因为某些草药和野草、微生物和老鼠、兔子和绵羊以及牛马牲畜,在起初缺少自然天敌、食物供给充盈的新大陆上成片繁衍,其增长的速度比欧洲殖民者的增加要快得多。他也提醒人们不要忽视事情的另一面,即“许多美洲物种在欧亚大陆都显示了极强的生存能力并扰乱了旧大陆的生态系统,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土豆,其次有玉米、烟草、豆类、西红柿、道格拉斯针叶树和澳大利亚桉树,以及让人难忘的于19世纪摧毁了欧洲大部分葡萄种植业的梅毒病原体和葡萄藤虱”。庞廷在《绿色世界史》中同样重视欧洲扩张的影响,认为“从生态学视角看,欧洲扩展似乎更像传遍世界的破坏浪潮”。这些论述与分析无疑拓宽和更新了我们对殖民主义的前因后果的认识,同时还启发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随着殖民扩张、国际贸易和人员往来等人类交往,会出现生物入侵现象并引发复杂的后果,这是我们认识人类史和自然史之联结的一个方面;研究时,如果忽略了哪一部分,所呈现的将是不完整的历史画面。
二、深入认识环境问题及相关内容的历史特殊性
世界史视野下的环境史研究可以将其对象置于悠长的时间长河之中,从而能深入认识环境问题及相关内容的历史特殊性,避免时代误置。由于环境史研究是在现代环境危机和环保运动的推动之下凸现的,所以“人们发现,在世界环境史的主题中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从危机出发”的。(13)这确属实情,譬如《绿色世界史》开篇所述即是“复活节岛的教训”。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这样的问题:今天的环境危机与历史上的环境问题是不是一回事?从世界环境史著作所揭示的史实来看,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不是那么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因为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来的是不同的历史面相,由此反映出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从庞廷的《绿色世界史》中我们可知,在“人类史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漫长阶段,采集和狩猎群体对环境的影响总的来说还很小,“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也已经因一些动物被捕杀至灭绝而使得自己的存在凸显出来,同时他们也很精细地去更改环境”。这样,因捕杀野兽而致使很多物种灭绝,是采集和狩猎群体对他们的环境的最大影响,这在马达加斯加、夏威夷、新西兰等地清晰可见,在欧亚大陆、澳洲和南北美洲也各有表现。当人类史在经历第一次大转变而转向农业并进入定居社会之后,人类对环境施加的压力和作出的改变越来越大,这种改变的破坏性影响也是巨大的。这样,在农业文明阶段,环境问题的突出表现是自然的平衡和原来那种生态系统内在的稳定被破坏了。由此我们也就看到,在人类对自然环境首次进行最大规模干扰的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大片毁坏现象首先出现。此后,在印度河流域、中国、日本、中世纪埃塞俄比亚、地中海地区、古代希腊和罗马、美洲等地,都可以看到环境退化现象,乃至因环境崩溃而导致社会死亡的例证,譬如玛雅社会就是如此。而在农业时代,环境问题的产生,显然是与人类的生存需要息息相关的,换句话说,这个阶段的生态破坏主要是为了生存而造成的。当人类史在经历第二次大转变而转向工业并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随着人口和GDP增长的日益加速,资源消耗日益增多,环境问题的规模、类型、来源和影响等也逐渐发生很大的变化。其中,污染问题的演变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1)从规模看,“污染起初基本上是地方性的——一般只限于一座城市、一条河流、一处垃圾堆或一个矿坑。到了20世纪后期,污染已增加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影响到各工业区、海洋、整个大陆甚至全球的运行机制”。(2)从类型看,因人畜粪便和腐烂垃圾而造成的水污染在人类社会早期就成了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同时,因煤烟造成的空气污染在一些地方出现得也比较早,譬如在伦敦,13世纪就出现了对煤烟污染的抱怨。在整个19世纪,空气污染问题在英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更加恶化,其他晚一点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也大致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及至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来,“工业工艺以及由此造成的污染类型已有重大改变”,工业废弃物以日益增加的数量、种类和毒性污染着广大地区,酸雨也变成了世界性的问题。而“以光化学烟雾形式出现的新危害,显示了污染中最惊人的趋势之一——‘复合’效应”。(3)从污染源看,对于水污染来说,“现在问题不再是人类粪便的污染,而是现代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问题。工业废弃物已经造成了污染,而在农村地区,人工肥料和杀虫剂的残余物渗进河流”。至于工业污染的来源,直到大约1945年,主要是矿物燃料的燃烧和重工业生产如钢铁、其他金属和化学品。这之后,随着广泛的工业生产和新技术的使用,污染源越发的复杂,新的污染因子则层出不穷。(4)从影响看,工业污染日益波及远离污染源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在取自格陵兰冰盖的冰芯中,1800年后的铅含量开始上升,在最近的200年中增加了4倍”,甚至在远离北半球工业中心的南极冰原所取的冰芯中,也显示18世纪以来铅含量增加了4倍。污染不仅像这样扩散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到20世纪后半期开始影响生物在地球上生存的全球机制,体现在臭氧层变薄和全球变暖。由此可见,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极其复杂性的环境问题,这是“工业制造物品和增长财富的优越性所必须付出的部分代价”。因而,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物质富裕的结果——这或许可以说是“富困”问题,并且还会由于现代人无止境的物质消费欲望而加剧。这与前现代社会人类因生存所需对生态造成的破坏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
同样,拉德卡在《自然与权力》中也给出了许多具体例证,来说明今天的环境问题及相关内容与历史问题的差异性。譬如,在涉及土壤时,他说:“今天,土壤中的过度施肥成为环境负担的一个主要源头,相反,一千多年来,土壤贫瘠却是人们意识到的主要环境问题。”在涉及环境保护时,他说:“排外,如今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政治病理学的化身,在前现代的条件下绝对是有其意义的:在农业和畜牧业经济的微观世界里,彼此协调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事实上正是由于迁徙而遭到破坏的,与地域相关的经验和知识也因此而丧失。”所以,“如果历史学家固守当今环境意识的理想模式,就不能注意到过去的人们保护环境的日常行为方式”。此外,拉德卡还告诫人们,为了辨别某一特定事件在具体情况下是否真的造成了环境破坏,必须时刻准备观察。譬如,“灌溉系统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导致土地盐碱化和疟疾。因为它取决于具体的实践和环境,比如排水设备是否发挥作用,在水塘和水稻田里是否有消灭蚊蛹和疟疾病原体的宿主的小鱼和青蛙活着”。
这样,世界史视野下的环境史研究使我们明了,历史学者在研究环境问题及相关内容时,需要摆脱当今环境意识的束缚,注意它们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特点,否则,会造成时代误置。我们应追随世界历史的脚步,深入地探讨和估量环境问题及相关内容的历史特殊性。因而,“为了认识我们今天的环境行为是怎样铸就的,环境历史学家必须回到过去,走进时间的深处”。(14)
三、全面展现环境问题及相关内容的地区差异性
世界史视野下的环境史研究可以将对象置于广阔的空间视阈,从而能全面展现环境问题及相关内容的地区差异性,避免泛泛而论。
正如拉德卡在《自然与权力》中所说的,“环境史的主要魅力在于,它激励人们不只是在‘历史的遗迹’,而是在更广袤的土地上发现历史”;然而,“当人们徒步走过马洛卡(西班牙)、喜马拉雅山和安第斯山脉的梯田时,就会产生一种分裂的感觉:不知为什么一切都很相似,又都完全不同”。这表明,人与自然一同在广袤的土地上演绎历史而在各处留下的痕迹表面上看上去颇为相似,实际上则可能因自然、社会和文化等种种因素的作用而千差万别。从世界史视野下的环境史研究中,我们可以很好地领略这一点。
譬如《自然与权力》一书在论述某个问题时,非常注意通过对不同地区的比较来认识同一问题的地区差异性。对水环境和水利建设的论述就是如此。拉德卡认为,“对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而言,几千年来,水一直是头号环境问题”。而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水利问题的讨论一直围绕着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的“水利社会”理论而展开争论。魏特夫的这一理论的要旨是论证在所有的灌溉系统大规模发展的地方,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带有中央调控的社会组织。这样,他在“水利社会”中看到了专制集权的起源。拉德卡承认,魏特夫的基本思想至今仍不可彻底埋葬,而且他还引用伊懋可(Mark Elvin)的话说,“就如历史显现的那样,人们永远不能完全驱赶维特福格(学界惯译为魏特夫——笔者注)的幽灵”。尽管如此,他还是举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反的重要论据,如,“在从荷兰到斯里兰卡的许多地区,水利工程显然并没有导致中央专制,而且在那些与官僚的中央集权制相联系的地区,习惯上也不能证明水利建设历史地导致了中央集权”;还有威尼斯,这个常常被称誉的欧洲最古老的共和国,“贸然看上去是驳斥维特福格的水利的专制趋势的理论的有力证据”。就水利问题而言,拉德卡还以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作为典型的对比,通过转述希罗多德的有关论点,来说明埃及和巴比伦这两个国家在灌溉方法上的重大区别:“在埃及人们让河水漫过田地,而在巴比伦相反,人们通过手工劳动用桶把水浇灌到田里。”在论述自然保护时,拉德卡同样注意到了其地区差异性。他指出,“野生”自然并不具有超时空的价值,“只有当某一社会阶层不再了解什么是饥饿的时候,它才会欣赏荒野和岩石的美”。由此可见,荒野崇拜是以衣食无虞为基础的,中国人所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所包含的也是这个道理。于是,他特别强调:“在当今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第三世界,环境史所研究的内容自然是人的生存条件。当代第三世界最著名的‘生态妇女’汪达纳·希娃(Vandana Shiva)坚决反对将自然保护和人类粮食基础的保护区分开来的做法”。在论述技术的作用时,拉德卡特别提及技术与环境的适应问题,以此阐明当技术从其诞生和相适应的环境中分离出来而超越空间距离在世界传播的时候,会带来新形式的环境危险。“沉重的犁耕耘在不该它耕耘的土地上,结果导致水土流失”——技术传播史上的这种环境代价和教训,的确是值得注意的。同样,在一国内部存在地区差异的事实也为拉德卡所明晰。他指出“只有当人们重视中国北方和南方的根本差异时,才能理解中国环境史”。
同样,在《绿色世界史》中,庞廷对有关问题的分析也注意到了地区差异性。在阐述采集和狩猎群落在一个大陆范围内对动物种群产生的影响时,他说:“欧亚大陆上的物种的灭绝尚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这就是大规模的了。在澳洲,在10万年的时间内,大型动物的86%灭绝……可能性最大的解释就是这4万年内阿布里吉人部落的捕杀”;“同样惊人的是发生在南美的80%大型动物的灭绝,以及在这个大陆的北部大型动物的73%的灭绝”。在阐述定居社会的环境问题时,庞廷也指出,“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印度河流域,在中美洲的丛林之中,以及其他地方,脆弱的生态环境在压力下崩溃”;“在地中海地区和中国,情况是长时间中的逐渐退化,也严重地破坏了这些社会的资源基础”。还有,在分析人畜粪便等垃圾污染时,庞廷说:“一名18世纪末访问北京的英国使节惊奇地发现,人们并不将垃圾扔向街道。许多中国城市有组织良好的系统,人们将垃圾扔进房屋外的桶内,然后被一队队的清洁工运走,用于给水稻田施肥。”当然,这样的垃圾处理方法也会造成带有地方特色的问题。“在中国,凡是通常使用人的粪便作肥料的地方,20世纪初大约90%的人感染了蛔虫病,1948年,所有死亡人口的四分之一归因于粪便的传染病”。
这样,世界史视野下的环境史研究还使我们认识到,历史学者在研究环境问题及相关内容时,必须扩大所考察的空间范围,重视大环境与小生境的非同一关系以及各地区的不同,否则,就难免有根据一般的假设而编构的假环境史,或者由于泛泛而论所带来的局限。
总之,由于世界史视野下的环境史研究能够更好地把握环境史的核心内容,延伸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考察的空间界域,它不仅可以比较完整地呈现原本丰富多样的历史,而且可以尽量避免对环境问题之认识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因而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环境史学者必须注意加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环境史的研究。当然,世界环境史研究也离不开对中国环境史的探讨,在这方面,伊懋可教授的成就十分突出,他的研究不仅奠定了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基础,而且启发了国内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思路。(15)中国的环境史研究走向世界,显然是世界环境史和中国环境史的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注释:
①Richard Write,"Afterword Environmental History:Watching a Historical Field Mature",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70,no.1( Feb.2001 ),p.107.
②参见J.Donald Hughes,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06。中译本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页。
④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
⑤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许友民、许学征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⑥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王国豫、付天海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⑦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⑧J.Donald Hughes,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06,p.81.
⑨中译本在此处将东欧误译为南欧,原文见Clive Ponting,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llapse of Great Civilizations,Penguin Books,1993,p.162。
⑩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2页。
(11)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王国豫、付天海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12)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1页。
(13)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王国豫、付天海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页。
(14)约阿希姆·拉德卡:《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王国豫、付天海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页。
(15)伊懋可与刘翠溶合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从世界和亚洲的视野基本界定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定义、范围和方法;他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比较全面地研究了四千年的中国环境史。该书从大象的退隐着眼,既抽出了中国环境史的模式,又分析了中国环境史的特例,还探讨了中国文人的环境意识,被认为提供了一种“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参见包茂宏《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辑。
